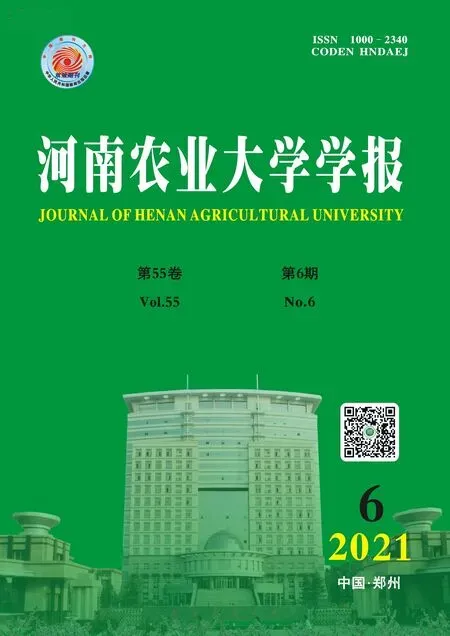植物根系觅食行为的功能生态学研究进展
张志铭,周芮宸,宋桃李,孔德良,钱建强,赵勇
(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根系是植物主要养分吸收器官,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根系生长必须适应所处环境,才能使植物在生存和竞争中取得优势。土壤养分分布具有高度空间异质性[1-2],植物会通过根系形态和生理的一系列变化,如范围(scale)、精度(precision)和速度(rate)等,来应对土壤养分异质性[3-5],这被称为根系资源获取(也常被称为根系觅食)行为(foraging behavior)[6]。根系觅食行为影响植物获取和利用养分的能力,与根系构型密切相关,同时也决定植物生存、竞争以及群落稳定性等诸多方面[7]。
为获取更多土壤“资源”,取得生长优势,不同植物的根系觅食行为存在很大差异,体现对环境适应策略的多样性;植物根系除自身适应环境外,同时借助菌根真菌获取更多土壤资源。菌根真菌是植物根系与土壤真菌形成的共生体[8],其共生历史始自植物登陆陆地,至今已超4亿年。目前已发现80%以上的植物种(>90%植物科)能够与菌根真菌形成共生体[9];在此共生体中,植物为真菌提供碳水化合物,而真菌帮助植物吸收土壤养分和水分,表现为合作共赢关系[10]。19世纪末以来,生态学者不断探索菌根真菌与植物根系的共生机制,其中对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AMF)的研究较多[11]。
根系觅食行为的影响因素众多,主要有土壤养分斑块属性(种类、强度、范围)、竞争植物、土壤微生物(菌根真菌)等[12]。生态学家提出多种学说来解释根系复杂而多样的觅食行为。揭示植物根系觅食行为,探究丛枝菌根真菌对根系觅食行为的影响机制,对于理解根系对复杂环境的适应策略,进一步认识植物群落构建及其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十分必要。本文主要从根系觅食特性与土壤养分异质性、根系觅食行为与竞争、根系觅食行为与菌根真菌、植物“碳投资”和菌根“养分反馈”之间关系四个方面综述相关研究进展。
1 根系觅食行为与土壤养分异质性关系
1.1 根系响应策略
土壤养分在空间上呈现斑块状分布,被称为养分斑块,可分为富养斑块(fertile patches)和贫养斑块(infertile patches)。富养斑块内根系增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根系接触到富集养分的区域就会大量增生,尤其是侧根密度的增加超过长度的增加[13-14],因此研究者认为,富养斑块能够促进根系增生。有研究认为,根系增生与其类型有关[15]。也有研究认为植物根系在富养斑块的增生不一定对吸收更多的养分有益,即“无效增生”假说[16-17]。在营养斑块中,植物在采用长寿命的粗吸收根还是快速觅食的细吸收根(吸收根即根枝末端起吸收功能的少数几个根级)这两种策略之间可能存在权衡(trade-off)[15]。此外,还有“另有所图假说”[18]和“植物竞争假说”[16]、“微生物竞争假说”[18-19]等。这些不同假说反映了根系对养分斑块采取的策略呈现多样化特征。
有研究认为,根系无法预测养分斑块的具体位置,因此根系行为应该是一种随机状态,遵循“随机游走策略”[20],该假说符合能耗最低的生存法则,目前较为盛行。但这种随机游走策略是有一定条件的,存在一定阈值和空间限制。例如,根系一旦遇到富养斑块,则大量增生,获取“效益”;如果一定距离内没有遇到富养斑块,则停止继续随机游走,不再浪费能耗,其他侧根再另选“新路”。“模块化结构假说”[4]认为,根系行为是受局部环境影响的结果,根系觅食行为是植物在受到某种刺激或感受到某种信号所表现出来的表型可塑性。还有研究认为,根系对养分斑块的响应规律遵从“临界值法则”[21]。该法则认为根系觅食行为依据觅食速率判定,当觅食速率低于其在整个生境的平均值时,会立即作出调整,离开原来行进方向。根系行为的主要调控因子为生长素,生长素合成与植物所处环境密切相关。缺磷环境下,拟南芥(Arabidopsisthaliana)通过增加生长素合成,进而调控根毛伸长及次生根生长,实现植物根系觅养[22];缺水环境下,植物根尖变得更细,有利于其深入到贫瘠土壤中,获取重要营养物质[23]。应对有效氮的不足,植物表现出两种策略,细吸收根植物以根系大量增生主动适应,而粗吸收根植物的根系可塑性较弱,主要依赖共生菌根真菌获取土壤氮素[15]。菌根共生使得根系觅食行为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替代性假说”认为,菌根真菌生长能够替代根系增生,借助菌根真菌的根外菌丝网络,根系活动范围可数十倍扩展。这种现象可有效节约养分资源、减少植物能耗,对提高竞争十分有利。研究表明,外来入侵植物更易与本土AMF共生,因而提高资源利用范围和效率,有利于其入侵成功[24-27]。
上述观点迥异的假说反映了养分斑块与根系觅食行为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除养分斑块属性外,根系觅食行为可能还与植物对养分的敏感性及试验植物生长期长短等有关。因此,不同物种应对养分斑块策略的差异可能是物种本身对特定环境最优的适应方式[28],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机制。
1.2 根系可塑性反应
反映根系响应养分斑块的两个重要指标是形态和生理变化,这两方面变化均被称为根系可塑性[6]。描述形态可塑性的3个主要指标为根系觅食范围(scale)、觅食精确性(precision)、觅食速度(rate)[5]。关于根系对养分斑块的形态可塑性反应,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差异。一般而言,植物根系觅养范围和精度之间存在权衡关系,植物会根据自身与环境条件选择更适宜植物生长的根系觅养策略[13]。CAMPBELL等[13]研究发现,根系较大的植物在富养斑块中觅食精确性较小,提出了根系广布性和觅食精确性之间负相关的观点。FARLEY和FITTER[29]则持相反观点,认为较大的植物根系遭遇养分斑块几率更大,根系增生应当是一种优势,所以觅食精确性较高。KEMBEL等[30]研究发现,物种数量会影响觅养范围和精度之间的权衡关系:物种数量较少时,二者之间呈现明显负相关关系,而当物种数量较多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消失。也有研究证实,群落内觅食精度较低的植物丰富度显著降低,这可能与群落内物种之间觅食精度及竞争力的差异有关[31]。GRIME[32]认为植物根系的觅养范围与精度之间仅在特定情况下存在权衡关系。EINSMANN等[33]研究证实,不同植物(乔木、灌木和草本)在广布性、精确性、敏感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表明异质条件下的根系增生不一定总能带来生长效益,生长的改善也可能只是植物生理、根系寿命等方面变化的结果。近期研究表明,入侵植物与本地植物之间根系广布性和觅食精度的权衡关系比较复杂[34]。也有研究认为两者关系因物种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有些入侵植物依靠较大的觅养范围来达到快速生长,有些通过提高觅养精度来增强与本地植物竞争养分的能力,还有些入侵植物的觅养范围和觅养精度都优于本地植物。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权衡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5]。
根系生理变化也是植物响应养分斑块的重要策略,代表性的有根系离子吸收速率、根呼吸速率、根内酶活性(如酸性磷酸酶等)、根系分泌物等。在响应先后顺序上,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有研究认为生理响应在先,形态响应在后。当植物遇到富养斑块时,用离子吸收速率明显提高来传递这种感知信号,然后再引起根系增生[35]。“BURNS假说”[36]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植物在富养斑块内生理活性最强,根系增生滞后,这种策略对节约植物碳消耗有益,符合能量原则。也有研究认为二者是同步的,即根系形态变化往往伴随着生理可塑性变化[37]。最近一项研究认为,在水分紧缺地区的植物不断优化自己的“投资效率”,更加高效地抓住稍纵即逝的养分和水分资源,促进物种的传播和扩散。由于环境的选择压力,这些地方的植物根系大都比较相似,多样性很低[23]。
2 丛枝菌根网络对根系觅食行为的影响
2.1 AMN的生态功能
AMF广泛分布于土壤中,菌丝体能够穿透根系皮层进入皮层组织内部,在细胞间隙中蔓延生长,根外菌丝通过菌丝融合的方式使菌丝体在植物之间相互连接成网状,构成丛枝菌根网络(arbuscular mycorrhizal network,AMN)[38-39]。借助这个网络,不同植物的菌根真菌与根系能够实现营养物质的直接交换[40]。植物的水分、养分和化感物质,甚至信号传递都可能借助这个网络[41]。植物群落中,许多菌根植物最初建植和生长都依赖菌根网络[42-43]。AMN是联系根系与土壤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可以极大扩展根系的养分获取范围。菌根真菌分泌的酶类、激素、抗生素能促进植物吸收和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对提高植物抗逆能力、保证成活、抵抗病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44]。菌根真菌还能提升物种生存竞争力,是入侵植物成功定居的重要原因[45]。由于AMF参与,根系表现出两种生存策略:一种为菌根策略,体现为粗根物种的AMF侵染程度高,依赖菌根获取资源;另一种为根策略,体现为细吸收根植物的AMF侵染程度低,主要是快速增殖细的吸收根,从而获取土壤水分和养分[23]。
2.2 AMN在根系觅食行为中的角色
通过菌丝体网络通道,营养物质在植物个体之间能够更迅速地转移,从而实现植物间营养物质和信息的合理分配和利用[46]。研究表明,植物不仅可以识别自身和亲缘关系近的植物,还能在其间传递信号物质,甚至可以与昆虫“互递信息”[47-48],这些功能被证实都与地下菌根网络系统有关。“菌根替代假说”[49]认为,富养斑块中菌根植物根系增生量低于非菌根植物,即菌根能替代根系增生。共生是一种保险策略,尤其是在干旱或土壤养分缺乏的地区[50]。AMN可有效改善植物体内水分状况,提高植物对干旱胁迫的耐受能力[51-52];接种AMN后可促进幼苗体内叶绿素和脯氨酸含量增加,调节植株体内各种内源多胺的分配比例,显著提高植株抗旱能力[53]。后续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同位素法示踪、荧光染料示踪以及氘水等研究证明通过AMN可将地下水资源分配给干燥的土壤区域。AMF可以合成特异性蛋白-球囊霉素相关土壤蛋白(glomalin-related soil protein),能够使土壤颗粒和其他有机物结合成团聚体,从而增加土壤渗透性、改进土壤结构,促进寄主对养分的吸收[54-56];也有研究认为,根系增生和养分吸收动力的改变对富养斑块的响应超过了菌根共生作用[57]。菌根真菌通常只影响那些在土壤中移动性很差或者土壤中浓度很低的元素[58]。养分充足时,菌根和植物根系呈现共生关系,而养分不足时表现为寄生关系[5]。缺磷条件下,AMF活性更高,菌根真菌能促进植物对磷的吸收,植物对其依赖性也更大[59]。在大多数生境中,氮是植物生长的限制性因素,但是菌根真菌网络可有效地提高宿主植物对氮源的吸收利用[16]。尽管如此,也有相反观点认为,在低N环境中,菌根真菌抑制植物生长[60-61]。不同类型的菌根和根系形态之间的营养觅食策略为互补关系[15]。通过菌丝体网络对土壤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从而调节宿主植物之间的竞争,其作用更像是一个“调节者”,起到平衡和缓解宿主植物间的竞争压力,对稳定植物群落多样性起到关键作用[62-63]。AMN则更偏向于将土壤资源运输给吸收能力较弱的幼小植物,从而促进幼小植株生长,通过这种方式提高植物群落丰富度和多样性[36]。也有研究认为AMN能进一步加剧植物间的生存竞争,也是入侵植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45]。然而,不同物种是否通过AMN调节养分资源分配以促进植物个体的营养平衡,目前尚不清楚。
当前,国内外对AMF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集中在AMF如何改善植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促进植物生长;另一方面是利用AMF进行生态恢复,主要包括对污染区域的修复以及提高植物抗逆性的作用机理[64]。AMN的调节效应不仅受植物种类影响,还与植物生长期或者AMF种类有关。土壤中的根外菌丝网可有效地提植物与AMN的结合,既可能产生积极的双赢效果,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植物是受益还是受害,现有研究结果尚存在分歧。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地下真菌网络与植物之间的关系远比想象的更为重要和复杂。AMN参与下,群落中植物根系行为特征的研究显得更为必要。
3 植物竞争下AMN对根系觅食行为的影响
群落是不同植物种共生的表现形式,共生使植物间关系更加复杂。AMN在植物之间传输营养物质,一方面降低了优势植物对资源的掠夺,促进了伴生物种的生长,进而维持植物群落多样性。另一方面,个体较大的植物在生长期间需要更多资源,导致植物之间的竞争加剧[39]。AMF与寄主植物还可能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竞争条件下根系响应的认识上还有较大分歧。一般认为根系对邻近植物的影响包括竞争和互利两种形式。养分斑块会影响植物间竞争,竞争能够促进植物根系增生[65]。植物也具有积极的一面,能够根据土壤营养分布状况与邻近植物的信息来调整自身根系分布[66-67]。“最小资源需求竞争理论”[68]认为,贫瘠土壤中植物间竞争最为强烈。单独种植的苘麻(Abutilontheophrasti)根系分布对土壤养分分布无显著响应,但是与同种植物共植且两植株之间存在富营养斑块时,它们的根系会倾向于重叠,进而加剧其种内竞争[66]。ZHOU等[69]对空心莲子草(Alternantheraphiloxeroides)的研究发现,养分斑块并没有改变其种内竞争强度,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同种植物相互识别并且避免种内竞争。不同植物种之间的根系不对称性竞争必然会引起群落内植株大小变异性的增加,从而影响群落结构[70]。已有研究发现,AMF能够改变群落中植物之间的竞争作用,但这种改变使植物间的竞争作用加剧还是缓解,目前尚无定论。“优势假说”认为一些个体较大的植物在生长期间需通过AMN获得更多资源,必然会导致植物之间的竞争加剧,“调节者假说”认为AMN能够平衡和缓解宿主植物间的竞争压力[63]。同位素标记法研究也证实这一观点,在群落中AMN连接同种或者异种植物时,AMN并不是将吸收的所有营养物质平均提供给不同宿主植物,而是会依据不同植物对养分的需求程度进行分配[42]。还有研究证实,遇到竞争时有些植物会采取躲避或忍耐策略,这样可以使邻近植物得以生存并提高群落多样性[66]。
由于AMN的调节效应不仅受植物种类影响,还与植物生长期或者AM真菌种类有关。根系觅食行为是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不同植物会产生不同的根系觅食行为适应养分异质性,植物间的竞争会影响根系行为,其中还包括自身以及与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权衡[5]。在资源受限的条件下,二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4 植物“碳投资”和菌根“养分反馈”关系
菌根共生体中,植物需要在“投入(碳支出)-产出(养分获取)”中权衡,作出应对策略。菌根共生体中合作关系取决于参与共生的生物体种类,并受一系列外部因素驱动。AMF可诱导转运蛋白穿透植物质膜而吸收养分[71]。AMF能够通过根外菌丝为宿主植物获取更大利益,这个利益可扩展到整个植物群落中,因此能调整植物间竞争关系,对稳定群落多样性有益[71]。“替代性假说”认为AMF能替代植物根系增生,减少植物碳消耗,提高植物生存能力。当前,比较流行的“投资-收益学说”认为“碳投资”越多的植物,从真菌获得的“回报”越大[72]。平均而言,植物把10%~30%的光合产物提供给AMF,而AMF回报给植物90%的养分所需[62,72]。“生物市场模型学说”也认为,共生体的资源交换是互惠的,碳与养分交换是相互调节的,符合“公平交易”[73]。然而,后续研究发现情况并非如此,AMF可能没有宿主特异性,碳投资和营养收益之间没有必然联系。AMF不一定能够精准识别自己的“碳投资者”,所以也就无法定向回报自己的“合作伙伴”[60]。菌根网络中的其他植物同样可以受益,有助于其他植物的幼苗建植,增加其存活机会[23,60]。但是也有研究者质疑这一观点,认为土壤生境的胁迫条件能够改变原有AMN运输营养物质的方向,这反而会抑制幼苗生长[74]。养分等资源的流动可能遵循“源-汇”梯度,向具有高吸收能力的共生体倾斜[43]。还有研究认为,在复杂的共生环境中,由于环境不可预知,资源供应也不稳定,根系会减少对共生真菌的依赖,变得更加独立。
上述不同研究结论既反映了物种间竞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反映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优势种必须调整其竞争策略,甚至弱化其竞争优势,这是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维持稳定的重要方式,也体现了复杂群落的矛盾与稳定统一的一面。
5 研究展望
根系觅食行为是决定根系构型的重要因素,也是物种竞争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对最终形成生长优势起到关键作用。生物界没有完美的适应,利他就是利己。与微生物的共生并形成AMN,这是加剧还是缓解了根系间的竞争?是否会导致觅食行为策略的改变?了解植物根系的生存策略与机制或许是破解这个谜的一把“钥匙”。
5.1 根系觅食行为的响应机制需进一步揭示
(1)根系觅食行为策略认识上的差异,反映出这方面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问题。根系对养分斑块的响应规律,土壤养分斑块对植物根系觅食的影响,如何影响其程度和方式?然而,现有研究结论尚无法判定和证实。揭示这种现象对认识植物竞争能力、研究其分布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2)根系可塑反应模式需要进一步证实。重点是生理响应和形态响应顺序与重要程度。菌根共生对富养斑块中植物根系形态可塑性的影响及对斑块养分吸收的作用也需深入研究。
5.2 AMN对根系觅食行为的作用需进一步证实
(1)根系觅食行为对邻近植物竞争的响应。目前关于AMN对根系觅食行为的影响以及响应机制、可塑性反应方面尚存在诸多争议。这些各异的甚至相反的研究结论可能是不同植物对养分斑块属性以及环境响应而表现出的差异,需要进一步厘清。
(2)AMN在根系竞争中扮演的角色。根系觅食行为对邻近植物竞争的响应还存在分歧。植物根系对邻近植物的影响包括竞争和互利两种形式。受植物种类、生长期、AMF、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AMF与根系是“互补关系”,充当“调节者”角色,起到缓解植物间竞争压力的作用,还是退出强势态势,使植物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是今后需要关注的研究课题。
(3)生态系统中植物、动物、微生物间的相互共生关系,特别是菌根真菌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作用是亟待深入的研究领域。地上与地下协同关系是下一步研究重点,把地上和地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地上生物量形成机制与光合产物调控以及地下根系水分养分吸收和碳分配间的协同性是今后研究重点。这方面研究进展对应用菌根类微生物恢复森林植被以及抑制和缓解森林衰退具有重要意义。
5.3 植物菌根间“投资-收益”关系需要进一步认识
厘清植物“碳投资”和菌根真菌“养分收益”间关系是阐明二者之间“利益”的关键。可以通过控制实验,采用13C脉冲标记法进行光合产物碳资源分配的研究,估算植物输入地下及其提供给AMF的碳量。将13C-DNA分离出来,并进行高通量测序,可以确定“养分回报”的菌根真菌类型。最终揭示碳源分配机制和根系养分吸收能力的关系,对“碳投入”和“养分回报”关系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