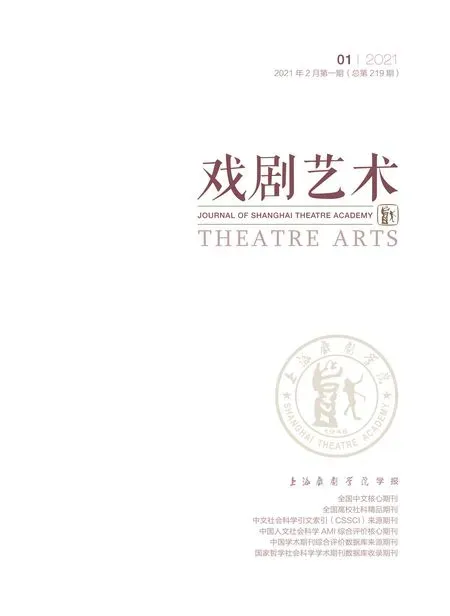对原始生命力的崇尚
——曹禺剧作的贯穿主题问题
陆 炜
这里谈曹禺剧作的贯穿主题,涉及的是从《雷雨》到《北京人》以至《家》的创作。因为创作了《家》(1942年)以后,曹禺开始寻找新的创作路子,但没有成功,而1949年之后的三部剧作,属于遵命文学,失去了自主的线索了。
研究任何一位文学家,概括和描述其创作脉络都是一个必须的研究课题。而这就涉及到了贯穿主题问题,因为找不到一个贯穿的东西,是无法统一地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脉络的。当然,这里说的贯穿主题应该广义地理解,不是说全部剧作都在写一个主题,而是指在各部剧作中贯穿着的一种基础理念。
无论是叫做贯穿主题,还是叫基础理念,笔者认为,在曹禺的剧作中,这个东西就是对原始生命力的崇尚。
一、前人对此的思考
对贯穿主题或基础理念问题,以往的曹禺研究者都有认真的思考,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回顾起来,大约有“社会批判说”“诗化现实主义”“母题说”“悲悯说”等几种。
社会批判说是最早提出,也是长期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剧评,就是把曹禺的剧作看成是批判性的社会剧的。按照这种思路,曹禺主要剧作的发展脉络得到如下的描述:在《雷雨》中,曹禺主要批判旧家庭,而《日出》则把批判扩大到社会,到了《原野》,则是把批判的视野从城市扩大到了农村。全面抗战爆发后,曹禺适应时代的需要,写了《黑字二十八》和《蜕变》两部直接反映抗战的戏剧。但此非他所长,所以他转回到他熟悉和擅长的批判旧家庭题材,创作了最成熟的剧作《北京人》,接着又改编了巴金的《家》,而这部同名改编作品仍然是对封建旧家的批判。
这种描述听起来有道理,很流畅,一般的教材、戏剧史多这样描述曹禺剧作的发展脉络。但此说其实有问题。第一,《雷雨》一剧,曹禺早就声明过“不是一部社会问题剧”。但曹禺的声明就被长期地置之不理。第二,《原野》一剧是写仇虎的复仇和良心挣扎,但由于该剧着力于写“原始的力”,似不符合社会批判剧的概念,于是评论界认为是失败的剧作,并说这是因为曹禺并不熟悉农村。第三,《北京人》作为公认的曹禺最成熟的作品,为什么在批判旧家庭的时候竟然出现“北京人”的象征形象,表达对猿人的崇拜?这一点好像无法解释,于是只好认为崇拜原始人是幼稚的思想,演出时把“北京人”的形象删除了事。曹禺的剧作数量不多,有这么三部主要剧作不符合,社会批判说便难以成为曹禺剧作贯穿脉络的完满解释了。
诗化现实主义概念。文革结束以后,曹禺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其中,田本相先生是成果最丰厚的代表性的曹禺研究家。田先生提出了“诗化现实主义”的概念来论说曹禺,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地申说。这一概念有其出色之处。因为这不是一个泛泛的评价,而是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成为现代文学主潮的众多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曹禺的戏剧不是仅仅反映现实、批判现实,而是达到了诗的高度,处于一个较高的美学层次。但这一概念也有不足之处。它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或者创作方法的术语,内涵不够具体清晰,它似乎满足于告诉人们,曹禺写戏就是有诗的情怀,就是达到了诗的美学高度,却并未把到底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高度作为追究的目标。
然而,研究要深入,在曹禺剧作中到底存在着什么高于一般现实主义的根本性的、贯穿性的东西,这一点必然要成为追究的目标。1990年,丁罗男先生在纪念曹禺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母题说”(1)丁罗男:《母题:从生活到艺术的重要中介——学习曹禺现实主义剧作的一点心得》,《曹禺戏剧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年。。丁先生的发言论述了母题的概念,提出在曹禺的剧作中存在着一个探讨“人”与“家庭”关系的母题。其实,同期进行类似思考的还有现深圳大学教授王晓华, 90年代初他在南京大学读博士,做的博士论文就以探索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为题,他认为“冲出旧家庭”的模式就是这种深层结构。丁先生在进行了很好的分析论述后,表示自己的看法还 “不成熟”。笔者认同这种谨慎。因为曹禺的剧作虽然多涉及家庭题材,但很难说是在探讨“人”与“家庭”的关系问题,各部作品的主题更难说是这一母题的展开。王晓华的“深层结构”说也很难成立,例如《雷雨》中,周萍要离家是要逃离蘩漪,并非“冲出旧家庭”,蘩漪要是想“冲出旧家庭”,就该考虑离婚,而不是揪住周萍不放手,而作为海归资本家的周朴园家,其实是当时最现代化的家庭,不是什么“旧家庭”;再如《日出》,无法用“冲出旧家庭”来解说;而《原野》则是一部野性的复仇的悲剧……但笔者认为这种思考非常有价值,是曹禺研究的重要推进,因为无论“母题”说,还是“深层结构”说,都已经把研究的关注点推进到了寻找曹禺剧作的根本性、贯穿性的东西是什么的问题上了。而“母题”的提法更是精彩,富有启迪的。
进入21世纪,笔者注意到刘艳在她的评传性的《曹禺》一书中提出了“悲悯说”(2)刘艳:《曹禺》(“二十世纪文学泰斗丛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刘艳认为,曹禺的人物塑造之所以丰满、杰出,因为他不是把人物简单地看做好人、坏人,他只是在写完整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曹禺采用着西方文化的视角,甚至是从人的“原罪”概念出发的。因此曹禺写人物有着一种对人类悲悯的情怀,这种情怀贯穿在他的各部剧作之中。
笔者对这种看法甚为赞赏。因为它符合曹禺剧作的实际且具有深刻性。刘艳注意到了曹禺剧作中被人们视而不见的重要因素和长期被人们感受到而说不清的东西,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什么曹禺在《〈雷雨〉序》中说《雷雨》写的是“天地间的‘残忍’”,要求观众“升到上帝的座”来看该剧的故事,为什么《雷雨》要写序幕和尾声,且用巴赫《B小调弥撒曲》贯穿始终。再如,为什么在《北京人》中令人讨厌的思懿和令人发笑的曾皓身上,甚至是《原野》中瞎了眼的恶妇焦母的身上,都有一点同情的色彩。“悲悯说”的深刻性在于从创作的文化立场来考察曹禺,使对曹禺剧作的解读脱离了习惯的社会学层面,站到了人类学层面。而这一点恰恰能够解释为什么曹禺的剧作能超越一般现实主义仅仅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层面,达到了诗意的高度。
不过,“悲悯说”似也不能完满解释曹禺的创作脉络。因为在各部主要剧作中,只有《雷雨》和《原野》是总体上具有对人类悲悯情怀的,《日出》一剧就和悲悯毫不相干,《北京人》一剧则是对北京猿人的狂热推崇和对现代北京人之孱弱的嘲笑,总体上并非悲悯态度。
本文的思考是对前人的延续,而这种思考是从注意到《北京人》的主题并非反封建开始的。
二、从《北京人》返观《蜕变》
思考曹禺剧作的贯穿主题,为什么不是从《雷雨》开始?从小处说,笔者的思考就是从认识《北京人》开始的。从大处说,则《北京人》是公认的曹禺最成熟的剧作,由此入手“却顾所来径”,回头梳理曹禺的戏剧创作是怎样发展到这部剧作来的,正符合逻辑。
《北京人》一般被看做批判旧家庭的反封建剧作,剧终,瑞贞和愫方冲出了这个家庭,寻找自己的人生,代表了剧作的进步性和创作意旨。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不合作者原意。因为瑞贞和愫方在剧中是相对次要的角色(愫方的戏份弱于曾文清、曾皓、思懿、江泰,大约是第五位,瑞贞除弱于上述五人,还要弱于曾霆和袁圆,最多占到第八位)。瑞贞在开幕前已经联系外边的人,决心离开曾家了,所以她在家是不动声色,逆来顺受,一句顶撞的话都不说。愫方留在曾家只为了爱文清,她离开曾家是因为终于看清文清已经无可救药。所以在剧中并不存在瑞贞和愫方与封建势力如何冲突的线索。剧情总体是按照曾家欠债,最终棺材被抬走顶债,而曾文清出门谋事,失败归来而自杀的过程展开的。作者的创作意旨可以从剧本的情节和人物的设置看出来,其构思可以概括为两个系列、三次交集、三次拯救。
两个系列,就是对比鲜明的两个人物系列。一个是已经落到借债维生的封建旧家曾家。这里的头号人物是36岁的儿子曾文清,他是个废物,只会喝茶、画画、玩鸟,他出门找事,其实是做做振作的样子,落魄归来,最终自杀。第二号重要人物是63岁的老爷子曾皓,他总说要为这个家再出门奋斗一番,其实只是一年一年漆他的棺材,为寿终正寝做准备。第三代,即17岁的孙子曾霆,正上中学,他不认可这个家,私下写了离婚书,让妻子瑞贞打掉肚里的孩子离开这个家。这个家靠文清妻子曾思懿维持,但她的打算只是老爷子死后要把现居的祖宅卖个好价钱。这是一个文明的、孱弱的、走向衰亡的人物系列。另一个系列是崇拜北京猿人的活力四射的人物系列,其中包含三个人物:有人类学家袁任敢和他的女儿袁圆,他们互称“老猿”和“小猿”,不拘礼法,成天打打闹闹,无拘无束。还有一个是袁任敢的科研考察队的卡车司机。他身高两米三,浑身是毛,绰号就叫“北京人”。
这两组人物生活在一起,袁家是租曾家部分房间住的房客。两家构成了文化的鲜明对比。这其实就是剧名的由来。如果不是为了对照北京猿人,那么曾家也不一定要是北京人,旧家到处都有,写成山东人、四川人都无不可。
在剧中,两组人物发生了三次具体交集。
第一次是曾家要撮合愫方嫁给袁任敢,为此请袁家来一起吃饭。愫方和袁任敢都没表态,这件事情就含糊着,但到了第二幕,袁圆报告说袁任敢的未婚妻就要到了,就是说嫁给袁任敢整个儿是曾家的一厢情愿。
第二次交集是曾家女婿江泰听了袁任敢说北京猿人后的大发议论。袁任敢这样对江泰说:
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3)曹禺:《北京人》,《曹禺全集》第2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449页。以下本文中引用《北京人》剧本文字出处相同,不再一一注明。
这段话其实就是全剧的核心台词。而江泰听后大发感慨,用长篇台词痛说曾文清和自己都是废物,真是祖先的“不肖子孙”。
第三次交集就是曾霆和袁圆的一大段戏。曾霆写了情书向袁圆求婚。袁圆则半真半假、玩笑似地应付他,说自己长大了要嫁给北京猿人这个“大野人”,因为他厉害,“一拳能打死一百个人”,而曾霆不过是个可怜的“小耗子”罢了。
三次拯救就是“北京人”的三次出场。第一次是第一幕结尾,债主盈门,气势汹汹,曾家已经无法应付,“北京人”一顿拳打脚踢,把债主打跑。第二次是第二幕结尾,曾皓被文清气倒中风,送不送医院,怎么去医院,曾家乱成一团,“北京人”突然出现(是瑞贞去喊来),把曾皓抱起出门。第三次是第三幕临近结尾,瑞贞和愫方要天亮前离开曾家,但大门被锁无法出去,“北京人”再次出现(是瑞贞去请来),这个哑巴竟然开口说话:“我们打开”,“跟我来!”接下来剧本写道:“【‘北京人’像一个伟大的巨灵,引导似的由通大客厅门走出。”
所以《北京人》要表达的思想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歌颂,呼唤原始的“北京人”的强悍力量。柳亚子先生在《北京人》重庆首演后写的诗体的剧评把这种意旨表达得淋漓尽致:
旧社会,已崩溃;新世界,要起来!只有你,伟大的北京人呀,继承着祖宗的光荣,还展开着时代的未来!
破碎的大家庭,已面对着不可避免的摧残!老耄的白发翁,还依恋着古旧的棺材!长舌的哲妇,自杀的懦夫,都表现着旧社会的不才!只有伟大的北京人呀!一分力,一分光,正胚胎着时代的未来!
多情的小姐,洗净她过去的悲哀!被压迫小媳妇儿,冲破了礼教的范围!跟着你,伟大的北京人呀!指点着光明的前路,好走向时代的未来!(4)柳亚子:《〈北京人〉礼赞》,原载1941年12月3日《新华日报》。转引自田本相《曹禺剧作论、郭沫若剧作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
从这种理解看,“北京人”才是表达剧作主题的头号人物。
但可惜的是,首演之后,人们虽然继续肯定《北京人》,却在演出中把“北京人”这一象征形象删除,《北京人》中对原始生命力的崇尚,被看做幼稚的思想,而曹禺也始终未敢提出辩驳。1949年之后直到2019年之前的历次演出,“北京人”这一形象始终不见于舞台。不过,无论怎样强调读者、导演有自己解读的权利,《北京人》的原意是批判现代人生命力的孱弱,歌颂、呼唤“北京人”的伟力,是明明白白的,无可置疑的。
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原意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曹禺回到批判旧家庭的题材,为什么推出一个“北京人”的形象,表达对原始人的崇拜呢?这是什么思路?于是我们返观他的前一部剧作《蜕变》。
在曹禺研究中,《蜕变》一向被看做是一部一般的抗战剧,甚至抗战宣传剧。因为剧本前部写了一所乌烟瘴气的伤兵医院,一片混乱和腐败,后部写这种局面得到转变,给人振奋。构思显得太简单。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来了个清廉、振奋的专员梁公仰,一番整肃,就风气一新了。改变社会风气哪里那么容易?这不过是提供光明和希望,好达到宣传效果罢了。所以,许多评论对它的肯定就是剧本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描写尖锐大胆,而梁公仰有点像共产党,剧本有进步的倾向,以至于该剧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打压。
笔者认为这种评论不得要领,也模糊了《蜕变》的历史地位。
《蜕变》并未受到打压,而是出现了重庆首演大获成功、报纸连载剧本、在上海连演一个月等盛况,而最说明问题的是国民党主管文艺戏剧的官员潘公展请来了蒋介石看戏。蒋并不是一个喜欢看戏的人,但亲临剧场看《蜕变》,这是为什么?解释大概只有一个:《蜕变》触及了一个重大主题:中国人的精神在抗战炼狱中再造、提升!这个立意比其他抗战剧本都要高。
这个主题是潘公展附会上去的,还是曹禺的原意?应该是后者。“蜕变”这个剧名就是证明。从这个意思看具体描写,就会发现简单的构思(前部乌烟瘴气,后部气象一新)自有深意。因为前部的暴露并不是指向某个人物或某个问题,而是把这种黑暗看成一个普遍性的民族素质问题、人的精神问题。前部的描写让人直接感受到压抑,觉得中国这样真没有希望。而后部描写的三年后的伤兵医院真实具体,让人感到这种面貌是中国完全可做到的,中国有希望!那位医术最高,富有正义和理想的丁大夫就是这种感觉的引导者和代言人,她原已灰心丧气决意离开,现在留下继续工作了。
但问题就来了。日寇侵华,中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国人的精神不振作,抗战胜利就没有希望,这个道理不是高人才明白,是政府、人民都明白。那么,这一个特别重大的主题,为什么别人都不写,唯独曹禺写了呢?为什么曹禺独立创作的抗战剧仅此一部,就写重塑中国人的精神的主题呢?
笔者的解释是需要把《蜕变》和《北京人》联系起来看。《北京人》表明,曹禺是个总在思考衰颓的中国人如何变得强大的剧作家。因为有这个思路。《蜕变》写重塑国人精神的主题就是很自然的。反过来,从《蜕变》推进到《北京人》也是自然的。这意味着《北京人》不是一部离开了抗战的戏,而是为抗战中的中华民族呼唤强悍生命力的戏。
笔者的这种理解是否讲得通呢?如果说两部戏都是在关注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问题,怎见得从《蜕变》到《北京人》就要延伸发展出崇拜原始人伟力的主题来呢?难道曹禺根子里就有一个崇尚野性的概念存在吗?
笔者认为就是如此。因为在曹禺前期的《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戏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
三、从《雷雨》《日出》到《原野》
要讨论《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戏的贯穿主题,或者说三部戏的基础理念,最方便的是从《〈日出〉跋》中的这一段话入手,因为这一段话承上启下,既回顾了《雷雨》《日出》,也开启了《原野》的创作:
我常纳闷何以我每次写戏总把主要的人物漏掉。《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傀儡。而我总不能明显地添上这个人,于是导演们也仿佛忘掉他。我看几次《雷雨》的演出,我总觉得台上很寂寞的,只有几个人跳进跳出,中间缺少了一点生命。我想大概因为那叫做雷雨的好汉没有出场,演出的人们无心中也把他漏掉。同样,在《日出》,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我反而将他疏忽了,他原是《日出》唯一的生机,然而这却怪我,我不得已地故意把他漏了网。写《日出》,我不能使那象征着光明的人们出来,……我以为这个戏应该再写四幕,或者整个推翻,一切重新积极地写过,着重写那些代表光明的人们。(5)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5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0-31页。本文以下引用《〈日出〉跋》文字出处同此,不再一一注明。
对这段话怎么理解?一般的理解可以是这样:这是一种文艺化的抒情。这个抒情甚至有点儿得了便宜卖乖的性质。因为作者已经写出了令观众叫好的两部杰作,却用这种表达方式述说自己尚未尽意的东西。笔者认为,这样理解固然合理,但当我们要探讨三部戏的基础理念的时候,对这段话一笑而过就不合适了,我们必须对其含义做严肃、实在的解读。
“漏掉”的“主要人物”指什么?无疑是指作者想表达的深层的主题。
首先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物,而是雷雨代表的精神。问题是,这种精神是什么?《雷雨》的演出都是按照具有反抗性的社会剧处理的,无论面对周朴园的蘩漪,还是控诉命运不公的鲁妈、作为罢工代表的鲁大海,都着力表现其反抗性,但曹禺的感觉却是“我看几次《雷雨》的演出,我总觉得台上很寂寞的,只有几个人跳进跳出,中间缺少了一点生命”。可见曹禺感到缺失的“一点生命”并非社会反抗性,那个“叫做雷雨的好汉”指的是人的野性。
对于《雷雨》是表现原始的野性,曹禺已经说得够多。在1935年写的《雷雨的创作》中,他就举出哥哥推窗子进入妹妹房间的场面为例,说“这种原始的心理有时不也有些激动一个文明人心魄么?”(6)曹禺:《〈雷雨〉的写作》,《曹禺全集》第5卷,第10页。在《〈雷雨〉序》中则说;“《雷雨》对于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7)曹禺:《〈雷雨〉序》,《曹禺全集》第5卷,第14页。本文以下引用《〈雷雨〉序》文字,出处相同,不再一一注明。到了《〈日出〉跋》,曹禺改了说法,称“主要人物漏掉”,主角就是“一个叫做雷雨的好汉”,意思就更明确了。剧名“雷雨”便是这种原始的力的爆发的象征。《雷雨》想表现原始的野性,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就是曹禺说的《日出》的主角。这里十分具体,主角就是那些幕后歌唱的打夯的小工们,曹禺以他们代表日出,代表希望。问题是这些人算什么人。
如果说他们就是无产阶级,或者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那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形象不能出场。在展现社会不公的《日出》中,上到资本家、交际花、富婆、面首、洋行买办,下到小职员、妓女、流氓打手都有出场,为什么工人就不能出场?《雷雨》中鲁大海的工人形象不是出场了吗,为什么《日出》中就不能呢?
这可以从《日出》第四幕中一段话的细读中得到解释。
方达生:不,不,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跟你求婚,我并没有说我要娶你。我说我带你走,这一次我要替你找个丈夫。
陈白露:你替我找丈夫?
方达生:嗯,我替你找。你们女人只懂得嫁人,可是总不懂得嫁哪一类人。这一次,我带你去找,我要替你找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跟我走。
陈白露:(笑着)你是说一手拉着我,一手敲着锣,到处去找我的男人么?
方达生:那怕什么?竹均,你应该嫁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一定很结实,很傻气,整天地苦干,像这两天那些打夯的人一样。
陈白露:哦,你说要我嫁给一个打夯的?
方达生:那不也很好。你看他们哪一点不像个男人?……(8)曹禺:《日出》,《曹禺全集》第1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41-342页。
那些打夯的小工算什么人,两人的理解不同。陈白露只认为他们是做苦工的穷人,方达生则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男人”。而方达生说的才是曹禺的意思,所以用他们来代表日出。
在《〈日出〉跋》中,曹禺明确地指出“方达生不能代表《日出》中的理想人物”。而在剧中,方达生是个表示“我们要做一点事,要同金八拼一拼!”的人,而对此表示,陈白露说:“这么说,你跟他要走一条路了。”这里的“他”,指的是陈白露曾经爱过、嫁过的那个诗人。所以方达生、诗人就是一种充满理想,要作斗争来改造社会的有文化的人。但曹禺认为这种人是书生气的,不属于“真正的男人”。
于是,那些打夯的小工是什么人呢?他们不是鲁大海,鲁大海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是一个敢于同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斗争的工人,而他们高于鲁大海。他们不是方达生,方达生是有文化、有理想,要作斗争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他们高于方达生。所以,那些打夯的小工其实是象征性的人物。他们并非社会底层的苦力,而是和整个腐朽的文明社会相对立的健全的人,所以被称为“真正的男人”。
对这种人,曹禺只有笼统的概念,即“很结实,很傻气,整天地苦干”,但意思很清楚,他们是没有文明社会的毛病的原始的强悍的人。由于他们是象征性的,所以无法出场,因为一出场就得有具体形象,呈现为社会中做苦力的形象,就不是曹禺的意思了。
如果说曹禺在《雷雨》和《日出》中都漏掉了主要人物,那么《原野》弥补了这个遗憾,在这个戏里,“主要的人物”出场了,这就是原始的力充盈而洋溢的仇虎和花金子。苍茫的原野正是这种野性的人登场的环境。在《原野》第三幕仇虎第一次上场的舞台说明文字中,曹禺对仇虎给出这样的描写:“他忽而也如他的祖先——那原始的猿人,对着夜半的原野震战着……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9)曹禺:《原野》,《曹禺全集》第1卷,第533页。在这里,须要注意曹禺对仇虎的赞美态度和“真人”这一提法。
其实,对《原野》在此不必多做分析,因为从三十年代的评论开始,到后来每个读过《原野》的人,都一眼就能看清这个戏是写野性的人,写“原始的力”。
于是,从“主要的人物”被遗憾地漏掉,到这种人物出场,从“一个叫做雷雨的好汉”到“真正的男人”再到“真人”,我们清楚地看到崇尚原始的生命力的概念贯穿在《雷雨》《日出》和《原野》三部戏中。
四、重新梳理曹禺剧作的创作脉络
当我们发现一条崇尚原始生命力的线索的时候,考察不是可以结束,而是涉及了两个问题:1.崇尚原始的生命力,这种思想的价值和地位是什么? 2.这个思想是怎样影响曹禺剧作的创作脉络的?
这两个问题都很大。但本文无可回避,必须给出自己的回答。
前一个问题是一个思想史问题。在此,笔者只限于从研究曹禺的需要提出两点看法:1.崇尚原始的生命力曾经是一种强劲的、流行的思想。2.曹禺在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抱着这一思想,与时代的思想进展有一个明显的差距。
中国清末以来的思想,大抵以“救亡”为中心课题。因为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又经历甲午之败、庚子之变、日俄战争,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局势已经是人所皆知,存亡所系,当时之谈“救亡”,比今日谈“伟大复兴”要广泛强烈得多。对如何救亡的思考,大体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具体表现就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就是变法改良,走君主立宪道路,还是发动革命,走共和国道路的思考。一个是低于政治的社会实务层面,表现的是“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等等思想。再一个是高于政治的文化层面,即关于文明如何延续的思考。这个层面可举出两篇影响极大的文献。一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此书一出,“物竞天择”,中国必须自强,否则就要被淘汰的思想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一是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该文气势磅礴,浩浩汤汤,主要是两个观点。一个是,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是个老人一样的“老大帝国”,所谓救亡,不是要修补、拯救、延续这个“老大帝国”,而是要重新创造一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少年中国”。另一个观点是“少年强,则中国强”。就是说创造少年中国,必须造就全新的中国人。此文一出,其思想也是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1918年,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该会于1919年7月1日成立,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学会宗旨。会员100多人所持的主义各不相同,包括了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各种思想。这个重要学会的成立,可看做一种思想史的标志。它至少说明自190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刚刚结束的时段内,创造少年中国是中国思想界共同认可的思想。
中国救亡必须造就新人。但新人如何造就?梁启超没具体说。但新人的品质要体格强健、思想全新、朝气蓬勃是不言而喻的。为造就新人,中国的思想家便要寻找各种资源,而原始的生命力是重要的资源之一,于是,向历史、向远古找回原始、野蛮的力量就是合乎逻辑的一种思想。
1907年,鲁迅写了一篇长文《摩罗诗力说》,内容是介绍几位反抗性的诗人。“摩罗”是恶魔的意思,腐朽的社会视这些诗人为恶魔,而鲁迅认为他们有延续文明的强大力量。该文在写了题解的文字后,接着就说到了原始力量的价值:
尼佉(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唯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发展既央,隳败随起,况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其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殆以此欤?……(10)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读完了这段话,我们发现它可以直接印在《北京人》一剧的演出说明书上!因为它就是该剧的构思、意蕴的完整说明。鲁迅引用尼采的思想,指出文明最初就是从野蛮中孕育的,如果文明是花,野蛮就是蕾,如果文明是果,野蛮就是花。“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曹禺说北京猿人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希望”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鲁迅说“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这不就是剧中曾家的状态吗?
如果再举一个例子,可以说到毛泽东。1917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长文《体育之研究》,痛论体育之重要。其根本观点就是“体育在人生中占据第一之位置”。他在文中根据有人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而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观点。还在文中提出了“小学教育以体育为主”的主张(11)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划生),《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写该文之时,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该校里有一口井,如今还是著名景点,因为那时候毛泽东等四个学生每天一起床就来到这里,不论春夏秋冬,打起一桶水就兜头浇下去。在毛泽东早年的文章和行为的背后,我们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信息,对原始生命力的崇尚就包含在其中。
简而言之,在焦虑于救亡的清末,在积贫积弱,被叫做“东亚病夫”的民国初年的中国,崇尚原始的生命力是一种强劲的、流行的思想。曹禺抱有这种思想是十分自然的。
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解体,停止了活动,出版了48期的会刊《少年中国》停办。解体是因为会员思想的分化:许多会员强烈主张学会“要有主义”,抱持各种主义的会员不能再统一于“创造少年中国”这一笼统的目标之下了。该会解体也可以作为一种思想史的标志。它说明中国的思想界已经推进到专注于国家、社会建设方略或社会理想的地步,关于文明延续的文化层面的思考已经退隐到后排、背景的位置去了。
1925年这个时间点也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它的现实原因是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国还是很混乱,在这一年,中国已经进入被叫做“国民革命”或“大革命”的北伐战争的前夜了,敏感的思想家、文化人甚至纷纷南下广东了。在中国思想的这一波推进中,政治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但尽管情况多样,中国的文艺家的思想普遍进展到关注和信奉某种社会的“主义”的层面,进入三十年代,则进入“左翼”或关注“建国”还是“抗战”的问题了。
但曹禺不是这样。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以人类学立场思考文明命运的层面。所以他在1933年写《雷雨》还是以对“宇宙间神秘力量”的憧憬为兴趣的,他要写“天地间的残忍”,要表现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他在《〈日出〉跋》中描述他写《日出》的状态,是由于对黑暗不公的社会的愤恨,使他受尽折磨,到了“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啃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打碎瓷器,割破了手,让血“快意”地流淌出来的地步。曹禺写道:“这样我挨过许多煎熬的夜晚。于是我读《老子》,读《佛经》,读《圣经》,……”显然,曹禺三十年代的思想和当时社会思想进程是隔膜的。但这种隔膜或差异,却是曹禺创作的某种优势,是其剧作与一般社会剧不同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雷雨》是要写“天地间的残忍”和对人类的悲悯,那么再写《日出》的思想发展逻辑就是从怜悯人类到消灭腐朽的文明社会。
对于《日出》作为社会剧,人们自以为理所当然该这样理解:对于剧中描写的社会,我们对黄省三、翠喜、小东西应该深深同情,对陈白露应该扼腕叹息,对潘月亭、金八应该仇恨,对李石清、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应该鄙夷,对“要跟金八拼一拼”的方达生应该抱有希望……这个社会,应该是方达生这样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上升到成立革命组织,依靠和领导工人将它推翻、改造,打倒压迫者,解放劳苦大众——不过剧本没写到这一步,只是写了“日出”之前,塑造了一批精彩的人物形象,这也就很出色了。但问题是,曹禺是我们理解的这个意思吗?
曹禺不是这个意思。《日出》所写的社会,没有要你斗争、改造来消除不公的意思,所以诗人、方达生这样的人物也是被否定的。《日出》的意思,理想人物只是那些幕后的小工(或像小工那样的人),太阳只属于他们。而其他所有的人,从金八、潘月亭到黄省三、翠喜、小东西,连同陈白露、方达生,都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的范围,统统打包作为一个要整个消亡的文明社会。所以这里的社会批判,不是要改良、要革命,而是像《圣经》中上帝要发四十天的大洪水,把堕落的人类社会整体消灭。当然,为了将来的希望,上帝留下了健康好人诺亚一家。那些幕后的小工,就相当于诺亚了。与《圣经》不同的只是这里没有上帝,违反天道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文明社会将自行睡去,希望属于那些代表太阳的“真正的男人”。
如果理解了《日出》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批判剧,那么接下来出现《原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这里,曹禺要让“真正的男人”或“真人”出场。这里的困难在于这个原始的人其实是观念性的,不是从历史中、现实中走出来的人,让他出场,描写的具体性很难解决:他长什么样?做什么事?曹禺写他奇丑,出现在苍茫的原野,但很多东西还是含糊(例如仇虎怎么带着镣铐还有枪?他的那帮“朋友”是土匪吗?怎么不来接应他?要去的“黄金铺地的地方”是什么?都很飘渺)。《原野》的神秘性,根源就在于此。
对于《原野》到底要写什么,曹禺长期沉默。直到1980年接受田本相采访,才这样说:“写《原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走另外一个路子:打算写一个艺术形象,一个黑脸的人,但不一定心黑。”(12)田本相:《曹禺访谈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33页。这个说法乍看起来没头没脑。但联系剧本实际,《原野》是以杀焦大星为中心作情节构思的,杀之前,酝酿、犹豫,杀之后,陷入心狱,精神崩溃。由此就可以明白,《原野》是要写一个表面丑陋、野蛮但内心善良的人遭受的人性悲剧。
由《原野》再看《北京人》,就会觉出后者的顺畅。对原始生命力的崇尚,《北京人》直接了当地表达为对猿人的崇拜,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在观念性的原始人如何出场上,找到了更好的处理。曹禺给了这个观念的“真人”一个现实身份:卡车司机。他是个巨人,由于经常要做猿人画的模特儿,他就被扮成猿人出场。曹禺又让他是个哑巴,因为他代表猿人,在现实环境里,原始人怎么说话都不合适。
由对原始生命力的崇尚的概念,我们还能够解释曹禺改编的《家》为什么偏离了巴金小说的原意。小说的主人公本是觉慧,曹禺却把主人公改成了瑞珏。因为写觉慧就是写思想解放了的青年的现实斗争道路,写瑞珏并大力丰满和美化,就把主题变成了写善良、健康的生命的命运。
在话剧《家》中,我们可以发现曹禺有意地建构起了他的所有主要剧作中都有的潜在的“深层结构”,这就是健康的原始的生命与腐朽的文明社会的对立。在《雷雨》中,这就是蘩漪那种走极端的野性和周朴园、鲁贵那种总想妥协、调和的理性的对立。在《日出》中就是文明社会和作为“真正的男人”的小工的对立。在《原野》中就是原野中的仇虎跟让他遭受“不公”的社会的对立。在《北京人》中,就是袁家和曾家的对立、北京猿人和现代北京人的对立。曹禺在话剧《家》中重建这种深层结构的举措就是新创造了一个人物冯乐山。在小说中,觉新娶瑞珏是父亲给他定的,在话剧中,曹禺让觉新的父亲去世,娶瑞珏是爷爷跟他说的,而爷爷是听信了冯乐山的主意。冯乐山这个伪善人是个极其可怕的人,他不娶小老婆,却用搜罗漂亮、“有慧根”的女子回家陪老母烧香拜佛的名义残害了很多女子。在剧中,冯乐山仍是用这个办法逼死了鸣凤,折磨死了婉儿。他破坏觉新与梅表姐的爱情,导致梅表姐的死亡,接着又要给觉民说媳妇,破坏他跟琴表妹的爱情。冯乐山、爷爷、陈姨太组成了强大的腐朽势力。剧中极写瑞珏用善良和爱对待觉新与梅表姐,但最终她被陈姨太逼着到城外生孩子而死亡。所以,腐朽势力扼杀一个又一个年轻健康的生命,就是话剧《家》的情节构造。
对原始生命力的崇尚的确作为基础理念贯穿了曹禺剧作。若非如此,曹禺的主要剧作(从《雷雨》到《家》)就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