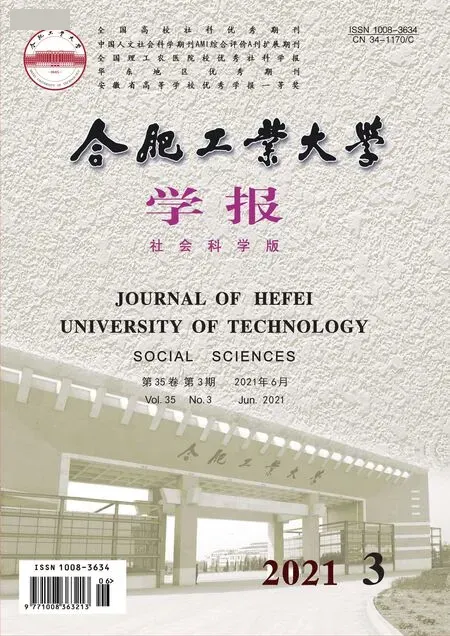析裘德的无名之因
李小敏, 朱蕴轶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无名的裘德》是托马斯·哈代于1895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同时这也是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小说描述主人公孤儿裘德渴求知识,却求学无门的一生,他的灵魂伴侣也因子女死后离开了他,他最后因病去世。虽然小说中裘德与表妹的婚姻不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但是,哈代却对此表露出了他的同情,这使他招致当时许多评论家的抨击,当时的维克菲尔德的主教也公开表明他已经将此书烧毁,并且希望图书公司停止出版该书。从此之后,哈代转向写诗,这本小说也成为天鹅最后的绝唱。但是20世纪之后,《无名的裘德》却因为其前卫的思想、新颖的题材以及高超的写作技巧而引起很多文学评论者的好评。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曾说过,时间是公正的评判者,人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哈代作品的内在优点。
《无名的裘德》全书包括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标题采用地理位置命名,即在玛丽格伦、在基督寺、在梅勒寨、在沙氏屯、在奥尔布里坎和别的地方、重回基督寺。裘德的一生都在这些地方流转,不同的地理位置记录他一生中不断转换的身份。同时,每个地理空间也展示出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裘德一直未能融入每个地方的生活。因此,本文从社会空间、身份建构以及意识冲突三个角度的互动来分析裘德在维多利亚那个时代虽然一生都对知识抱有无限的热忱,但却仍未成功的原因。
目前,国外关于《无名的裘德》的研究论文数量共约240篇左右,早期的论文涉及主题包括人物冲突类型、反基督教成分、性格与命运的关系、婚姻以及人物的异化;最近几年论文涉及的主题包括圣经原型、单向度的人物形象、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形象、男性关系以及环形情节等。理查德·德拉莫拉重点关注19世纪文学作品对男性之间不同关系的描绘[1];本杰明·坎农分析哈代如何将这部小说作为补偿媒介,以建筑材料所不能的方式将人物连接起来[2];卡洛琳·森普特探讨了小说中哈代作为作者的同情是一种“社会同情”的延伸[3]。国内关于该小说的研究论文数量为450篇左右,论文的数量在20世纪增幅很大。早期论文涉及的内容包括人物异化、宿命论、人物意识、悲剧分析以及精神分析;最近几年论文涉及的主题包括生态批评、婚姻、伦理学、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以及死亡主题。吴卫华从“俄狄浦斯情结”出发,探析了该小说的叙事母题,指出乱伦在外国文学艺术创作中是一个重要的传统[4];肖曼琼分析了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认为维多利亚的旧传统对人类的压迫,还有人与人之间迥异的性格造成了主人公的悲剧[5];丁世忠解析了裘德和淑之间的众多矛盾,包括理想与现实、肉体与灵魂以及爱情与婚姻,这些进一步造成他们人生的错位和迷惑[6]。
无论国内外的研究都从不同的视角并且十分细致地探讨了导致裘德混乱一生的原因,它们包括创作传统、社会制度、性格以及冲突等,但是大部分论文涉及的因素都是两者之间,冲突也是二元对立,因此本文想打破这种二元之间的讨论,将空间、身份与意识三者结合,探索裘德一生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的原因,以及裘德籍籍无名背后所承载的哈代的人道主义情怀,以使得文本分析具有多元互动的张力。
二、三维互动
艺术与现实在哈代看来是不对称的,他认为艺术比现实更能展现现实中的一些重要特点[7]。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生动地展示了地理空间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放大其在小说艺术中的作用。因此本文选取玛丽格伦、基督寺和奥尔布里坎三个地方来分析其中的社会空间作用、身份建构以及意识冲突,使我们能够对裘德的境遇有更深的理解。
1.玛丽格伦—“重要他人”—信仰萌芽
玛丽格伦是裘德成长的地方,也是他信仰发芽的地方。这个村庄年代久远、人烟稀少,但是,很多古老的树木、房屋和教堂却正被拆除,历史遗址正被新兴的建筑所取代。空间在历史的潮流中也是不断变化的,并且更新重组。空间的生产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社会空间是包括地理空间、政治、经济、宗教和风俗等一体的文化空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空间内相应地产生特定的人际关系[8]玛丽格伦这个原始自然的村庄就正处于向城市化转变的进程中,因为当时资本主义正在慢慢渗入农村,而新建的德国哥特式建筑还不被当时英国人所熟悉。
“空间转向”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空间的生产》这部书中,此书是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于1974年出版的一部关于社会空间的系统理论著作。在这部书中,列斐伏尔批判传统的社会政治理论,因为其只是片面地将空间视为一个可供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态的“容器”或“平台”[9]。从小说中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玛丽格伦是一个偏僻、落后,又带有一些愚昧色彩的地方,那里面的很多村民一直都没有走出过这个村庄,他们固守在这个方圆之地,根本不与基督寺或者外界打交道,以至于如维尔伯这样一个走街串巷卖假药的人都能被村里人奉为大夫。玛丽格伦不只是作为裘德小时候出生居住的村庄,这里也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裘德的受教程度、家庭经济水平以及其宗教意识,而这些也为小说在后继的其他空间里的情节发展做了铺垫。小说的主人公裘德作为哈代的人道主义关怀的载体,他从小就表现得与这个社会空间格格不入。在裘德还是儿童的时候,裘德看到砍树的,他会觉得树会疼;他走路舍不得踩死一只蚯蚓;每次捉完小鸟第二天会把他们放生[10]24。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裘德在给农夫赶鸟的时候会让鸟儿尽情地吃,然而他被农夫打了一顿并且被解雇。裘德被哈代塑造成一位热爱自然并且敬重自然的热血青年,他不会因为玛格丽特这个“空间”里的规约而改变自己的内心。从哈代对裘德的赞美和肯定,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热情颂扬积极、进取、自由的人道主义精神”[11]。意识总是体现人们的情感需求,最后落实于利益,可是裘德就像一位带有先进意识的少年意外落入这个村庄,他不仅不为自己谋取利益,反而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着想,这与整个村庄居民固有的利益需求不同,所以没有村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在裘德与艾拉白拉结婚后,这个小家庭中夫妻之间的更是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冲突。一个出身于屠户之家,只关注物质世界的富足;一个是充满浪漫主义的文艺男青年,更加在乎精神境界的养成。婚姻虽然可能会在冲动中开始,但是彼此之间巨大的观念差异最终不可能维持永恒美满的婚姻。
虽然裘德在玛丽格伦的身份仅仅是农民,并且他也不合群,但是他的身份始终保持着稳定性,因为在玛丽格伦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对于他的身份建构起“重要他人”作用的人。 “重要他人”指的是那些对我们社会化进程和心理人格塑造方面影响显著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最亲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们喜爱的老师和同学,甚至是一面之缘的路人或压根不认识的人。裘德的重要他人是费劳孙。费劳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裘德的老师,在裘德送他离开玛丽格伦时,他告诫裘德对畜类和鸟儿要怀有仁爱之心,并且他还给裘德的心里种下了“基督寺”的种子,此后基督寺在裘德心里代表着耶路撒冷、光明之地、知识之树,以及导师荟萃的地方。裘德说过,“那正是于我适合的地方。”[10]29他因此下定决心要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期望将来有一天能够进入基督寺。他为得到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书,答应帮维尔伯在村庄宣传,可是最后维尔伯根本就不记得这件事,至关重要的时候是费劳孙应裘德的请求寄给他两本书。裘德每天利用帮老姑太太送货的机会在途中自学,因为送货的那匹马认得在哪条路上走,也知道该在哪些人家门口停一下。可是这样的光景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在村民的意识中,他们认为裘德读书是贪玩的表现,所以他们口出怨言,还报告给当地的警察,谴责裘德违反章程,给路上行走的人带来安全隐患。后来裘德只能偷偷地在车上看书,遇到人就把书藏起来。尽管书本知识超过了裘德的自学能力,但他还是坚持不懈一点一滴地啃下来。后来,在裘德的第一次婚姻中,他的妻子艾拉白拉也并不理解他对知识的渴求,她认为裘德应该努力挣钱,最后他们只能分道扬镳。这一次失败的婚姻不但没有磨灭他对基督寺的信仰,反而使他记起小时候自己在路碑上刻下的记号:“往那面去 裘·范”[10]47,还有淑的照片的出现,其进一步唤起裘德去基督寺的意识,所以他带着一个全新的身份,向他信仰的地方全力进发。
2. 基督寺—求学的工人—信仰夭折
哈代将这部小说第二章中裘德的活动范围圈定在基督寺这个固有的空间里,因为只有在一定的空间中,作者描绘的裘德的无名形象以及他的命运才能更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一个人周围的世界是自身现实客观存在的前提,这如同一座庙宇对于神像的重要性[7]83。裘德在乡间学会了錾纪念碑、修理教堂式的自由石以及一般的雕刻,他把自己整理得干净利落,以一种全新向上的姿态来到基督寺。此时,他以一名工人的身份在基督寺立足,同时他又是一位怀揣梦想、渴望入学的学生。当裘德第一次漫步于基督寺的街道,这里的一切在他看来都充满了古老庄严的气息,并且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他能想象的所有的知识大师都可以云集于此;但是当他白天再一次走上大街时,这些学院在他看来却显得十分严厉野蛮,甚至一个大人物的灵魂也看不见。这一鲜明的对比旨在暗示裘德他未来求学之路的幻灭。由于裘德年轻力壮,他不仅白天工作一整天,而且晚上仍然要念大半夜的书,为此他还特地给自己的窗子挂上厚幔子,为的是不让别人知道他大半夜不睡觉[10]56。据聂珍钊阐释,哈代安排裘德到基督寺立足求学,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这代表裘德由一个农民向城市工人身份的转变,在哈代的全部小说中,裘德是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形象[12]。虽然他只是一位来自玛丽格伦的工人,但是他的职业意识却超过了当时伦敦工人们,甚至从现代人的职业意识来看,我们都不得不敬佩裘德。小说讲述了伦敦的刻叶状棱纹的匠人们是断然不肯刻给叶状棱纹作陪衬的牙子的,因为他们认为,刻一个整件物体的第二部分是有失身份的,但是裘德并没有这种想法,无论是哥特式的牙子活还是工作台子上窗棂活,抑或錾纪念碑、墓碑,他都乐意去做,职业在他看来无贵贱,每一种工作都值得认真完成。
为了使自己离梦想更近一步,裘德经常跑到城里那些有机会看到院长、寮长或者学院的其他首长的地方,然后他根据面相选择五位老师,并且给他们写信,表明自己渴望学习但是家庭困难。很多天之后,只有一位寄回寥寥几句的回信,而且信中也只是传达让裘德安守本分走自己的工人之路,不要见异思迁的意见。
对于裘德来说,入学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方法是参加公开的竞争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比赛,但是裘德以自学的方式即使十年也达不到竞赛的程度,因为这需要天赋以及他人的大量指导;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花钱买入学资格,但是按照他的储蓄速度,还得需要十五年之久。这些入学的途径没有一个是裘德现在可以选择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裘德来到基督寺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而且是整个小说致力阐释的地理文化空间的改变。空间的不断变化与重构都是历史的产物,只有结合历史的视角,地理空间的社会学意义才能被挖掘出来。裘德的求学之路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是教士,那时的教会需要掌握希腊文、熟悉经典的教士,这也就是裘德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原因。起初基督寺会从贫民中招收一些学生,后来经过岁月的演变,主流的入学者是牧师和乡绅的子弟;到18世纪中叶,牛津大学的入学者中贫民只占八分之一,贫民更是少之又少;在19世纪中期,英国颁发了一系列大学的改革措施,以前想上大学的贫民子弟可以通过在富裕人家做工,从而挣得每年所需的135英镑的学费,但是自从改革之后,这项制度被废除,贫民被彻底排除在大学圈之外,每个人入学都需要高学费和经受高强度的训练,并且由私人教师指导才能通过,这是贫困户所不能给予孩子的条件,这也就更容易理解裘德在小说中的处境。大学的入学考试需要具备一定的希腊文的水平,但是当时中学已经不再教授学生希腊文,这进一步使得贫民离求学的道路越来越远。到了19世纪末,牛津大学已然是上流社会的圈子,该校贫民学生的比例还不足百分之零点五[13]。牛津大学的前身就是当时裘德心心念念的基督寺大学。
福柯曾借助学校这样带有圈限的空间来研究知识和权力的密切联系,其认为圆形监狱的全景敞视主义同样适应于学校的监视,在这个知识运作的空间里,不同的知识领域构成不同的权力等级,上级监视下级[14]。院墙高筑的基督寺内,知识渊博的教授分别占据院长、首长或者寮长的地位,他们拥有学院里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随意让外界的人进入到学院习得知识,这势必会影响到学院权力的变动。无钱无权的裘德当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势单力薄的他不具备话语权,这表明了即使裘德努力上进,他还是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愿以偿地求学。在这些身份阶级与权力空间的划分之下,还暗藏意识形态的运作规律。
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下,作者哈代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情怀带有无助的色彩。对于意识形态中的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列出的前三项是:第一,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体系);第二,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公立和私立“学校”);第三,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5]。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16]。我们的意识形态带有主观的色彩,其源于我们的情感,因为所需的情感种类不同导致个体的需求也是不尽相同的,最后会上升为利益之间的争夺。对于宗教或者学校这样的国家机器,谁都想成为他们的主人,谁都想为自己所在一方谋取最大化的利益,这样的意识形态导致学校和宗教的规模愈来愈小,最后留在里面的都是金字塔上端的人物,而底层的人物如果进去比登天还难。这种意识形态与英国的私有制资本主义意识也是相一致的,他们追求为个体获取利益的精英式教育,他们崇拜个人英雄主义,为了个人的资源累积,可以无穷地剥削底层人民的利益。裘德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那些基督寺的院长断不会让不属于他们精英圈的外人来分一杯羹,裘德处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是难以取得上升之路的。因此,空间具有生产性,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更适合被看作带有丰富文化意义的场所,而不仅仅代表文化和历史产生的一成不变以及虚有其表的背景。裘德无论凭借多么艰辛的努力,也消解不了这种意识的冲突,他也改变不了自己求学的命运,根据哈代对裘德表露出的同情,可以捕捉到哈代的人道主义情怀,但是其带着被动无助的特点。
3. 奥尔布里坎—“社会认同”—信仰重生
在婚姻方面,裘德与艾拉白拉没有办理离婚,他的表妹淑也没有和费劳孙先生办理离婚,因而他和表妹未婚就同居在一起,并且后来有了孩子,因为这种无婚姻的伴侣关系不被当时社会所容忍,所以他们搬迁到遥远、陌生的奥尔布里坎。因为每在一个城镇住久,他们就会成为周围人讨论的核心,所以他们在奥尔布里坎也一直处于搬家的状态,流动的生活状态使得婚姻缺乏确定性,也使得信仰缺乏牢固性。《无名的裘德》中地理空间的转换,使得小说的立体空间完整化,而且地理空间的变更推动了裘德追逐信仰之路的发展,虽然每次空间的更迭都给裘德带来了挫败感,但是空间本身就是不同的社会进程和人类干涉形成的一种产物,相互影响的关系又使得它成为一种可以影响和改变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与方式的力量[17]。因此,在裘德举家迁往奥尔布里坎之后,他的信仰逐渐在此处重新燃起希望之光,他的意识再一次与当时的社会对抗,他自己再次屹立于个人心目中高耸的云端,仰视他人不可能看到的风景。裘德虽然在奥尔布里坎一直从事石匠工作,但是他也热心教育事业,因为自己受过挫折,所以他更能理解与他遭受同样境遇的工人,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会推动教育机会均等。他还参加了镇上的一个工匠进修互助社,这个社团囊括一切的教会派别,成员们的共同目的在于增长知识。因为裘德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还成为委员会的委员,可惜的是在人们知道他的婚姻状况之后,便对裘德冷眼相看,于是裘德自己离开了社团[10]329。裘德此时的悲剧可以贴切地运用塔菲尔和特纳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来阐释,他们认为,自我的身份与多个自我的环境还有附属团体相关联,在不同的环境中,一个人会根据自己所属的群体表现出相应的行为[18]。可是反观裘德,此时他是一名流亡的工人,并且成为了淑的丈夫,成为了孩子们的父亲,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与众不同的意识,他也从来没有试图去和周围的社会相融合,他一直对自己求学的信仰念念不忘。在为了谋生做面包生意时,裘德把一种点心取名基督寺糕,点心的形状全部按照基督寺的学院建筑来制作,甚至雕花的窗户和围廊,他都做得精致极了。虽然基督寺不能接纳裘德,但是裘德对它一如既往地留恋,即使处在奥尔布里坎,他还是想搬回去,希望可以继续居住在那,直至死去。在身份随之变化的人生旅程中,裘德始终没有与外界达到一致性,他梦想的身份失去社会的认同,并且外界赋予的身份也被他抛弃。空间形态的有效融合使得读者可以真实地体会维多利亚时期的气息,也能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等风俗[19]。
哈代以人道主义的情怀揭露了当时婚姻制度的不公和危害[20]。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令裘德无奈的是,人们知道并且默许公开场合妓女的存在,对酒馆里卖弄风骚的女侍也有些许的宽容,但是却不允许裘德和淑之间虽无婚姻却相爱相伴的模式。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结婚被认为是一件所谓“十分神圣”的事情,他们认为婚礼是上帝给予的,结婚意味着夫妻二人要共同承担上帝赐下的责任和义务。从社会道德的层面来分析,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意识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女性婚前是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贞操,这是夫妻结婚后得以顺利生活的条件,如果双方在婚前发生肉体关系,女方一定要想尽办法使自己嫁给男方;第二,责任和义务是夫妻结婚的首要考虑,结婚的基础不是我们现在歌颂的爱情;第三,双方一旦结婚则不能离婚,基督教的教义认为婚姻是上帝赐予的,人是不可能分开的[21]。裘德和淑对于婚姻的态度以及他们展现的婚姻意识与当时社会的规约背道而驰。裘德和淑都想结束自己先前的婚姻,他们认为现在是因为真心相爱才决定在一起的,可是这在旁人看来就代表他们丢弃了先前的责任和义务。淑认为,“你一旦按照盖有政府印信的文件同意来爱我,我按照政府的许可,在‘店内’受你的爱,那我就要怕你了——哎呀,那太可怕、太腌臜、太叫人恶心了。”[10]275裘德和淑都认同没有必要因为一纸婚约把双方束缚在一起,他们追求的是自由和享受,而这些会因为结婚而大打折扣,爱情也会因此被消磨掉原有的光彩。因为他们对于结婚仪式的看法如此与众不同,所以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就同居生活在一起,这使得传统的维多利亚人难以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艾拉白拉凭借当时的婚姻制度,三番两次将裘德套入自己所设的圈套。在小说的开头,艾拉白拉将裘德从求学的道路引入悲剧婚姻生活之中,在小说的结尾她又将裘德从原本已经破碎不堪的生活引入心灰意冷的死亡之路。哈代本人对当时封建传统的婚姻制度持否定的态度,他不顾外界批评辱骂,勇于跳出当时的局限,设身为以裘德和淑为代表的人群考虑,显示出其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
三、结 语
身份建构和意识冲突能够赋予小说文本中空间分析的连贯性,与此同时空间也会为传统的身份建构和意识冲突提供新的思考和阐释模式,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裘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和历史。本文通过对裘德所处的社会空间、身份建构和意识冲突三个要素之间关系的分析,旨在使我们全方位地了解裘德对于自己的婚姻、学业以及人生之路的坚持都是不被他所处的世界所容纳的。每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体,可是裘德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想法,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而这恰恰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但是作者哈代对于以裘德为代表的群体抱持着同情的态度,为无名的裘德正名,这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闪现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