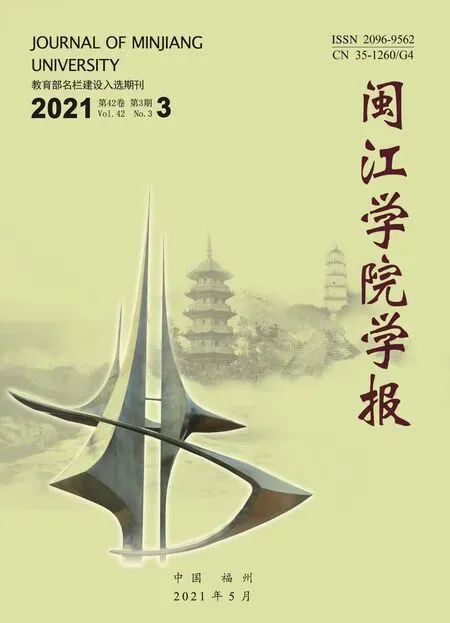王文兴对古典文本的重构
——以《聊斋志异》和《明月夜》为例
吴飞鹏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王文兴是台湾地区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创作,以激进的西化和先锋的文字实验,塑造出极其鲜明的文本特征。但同时,自他执掌现代派的阵地刊物《现代文学》开始,他就对中国古典文学体裁的创作和文学批评,表示出扶持的态度。这从他在《现代文学》上刊登当代作家的古典诗词作品和文学评论的举动,便可见一斑。而他本身,也对研读中国古典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台湾大学执教期间,王文兴就长期开设相关课程,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从上述的两处历史痕迹来看,这位激进的现代派作家身上,表现出了异常夺目的古典美学气质,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学史现象。本文即从批评和创作两方面,集中探讨王文兴身上的“现代”和“古典”的交融现象。依据的材料,也相应地分成两拨,一是他对《聊斋志异》的文本细读和蒲松龄人生精神的建构,一是他根据清人笔记《履园丛话》创作的短篇小说《明月夜》。在具体分析中,间及他不同阶段的小说文本和散文评论。
目前两岸学界对王文兴与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一是他的文字实验与古典语言间的关系,包括对文言文和古典诗词的精简、韵律、节奏等语言特色的追认和借鉴(1)这方面的研究,以台湾“中央”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新刻的石像——王文兴与同世代现代主义作家及作品研究》(洪珊慧撰)第三章第一节“王文兴的古典”对王文兴作品、访谈、讲演内容中相关话题的系统梳理为代表。另可参看黄恕宁、康来新主编《无休止的战争——王文兴作品综论》(下)“语言”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陈云昊《从“图画”到“书法”——论王文兴的现代主义写作》(《华文文学》2018年第4期)。;二是他的写作风格与笔记体小说之间的关系(2)如洪珊慧论王文兴“一页”小说《最快乐的事》与唐五代笔记《云仙散录》“一行文”风格之相似(《新刻的石像——王文兴与同世代现代主义作家及作品研究》,桃园:台湾“中央”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73-76页),柯庆明论笔记体小说的写作方式和风格与《家变》之关系(《台湾现代文学的视野》,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等。;三是他对古典文学内容元素的取资(3)如洪珊慧论王文兴短篇小说《明月夜》“结合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灾异、梦境、神秘、预言、巧合等各种重要元素,以现代小说的方式呈现一段玄奇”(《新刻的石像——王文兴与同世代现代主义作家及作品研究》第三章第三节《中国训诂、谶纬之学的现代演绎:〈明月夜〉》),吴霞《“魅”力纷呈:王文兴对古典文学元素的引用与创新》(《闽台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鲜少论及王文兴与古典文学主题、古典作家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对王文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辞”“意”之关系多有阐发,却在“道”的层面尚付阙如。当现代派作家面对古典文学传统时,会否在“道”的层面上产生交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文兴近来已经接受天主教为自己的宗教信仰,那么他的人生观中还存留有来自传统的精神痕迹吗?本文论述王文兴在批评和创作两方面对古典文本的重构,其最终目的即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一、王文兴对《聊斋志异》的批评
在王文兴的古典文学价值谱系里,《聊斋志异》高于《红楼梦》。理由有三。首先是《聊斋志异》的文字胜过《红楼梦》,其次是“想象力”与“体制”。
(一)《聊斋志异》的语言
《红楼梦》使用的是白话语言,而在评价中国文学的语体时,文言文胜于白话文,是王文兴一贯的主张:“文言文,坦白地说,乃诗之语言,是白话文提炼而成,是白话文里的精粹。”[1]15他之所以要下这样分明的价值判断,乃是由于在从事写作之初,他已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时代所通用的文学语言无法满足自己的审美追求。于是他焦虑、困惑,辗转其中,然后必须做出改变:
这场战争的开始,约在我廿岁的时候,我忽然间发觉我所习惯的文字表达发生了问题,问题一:我写的跟任何人的并无不同。二:我的文字杂乱无章,读不到平稳的节奏。我那时正在读佛楼拜尔,莫伯桑,和托尔斯泰,我在他们的语言中都听到十分动听的声音,低沉徐缓,像大提琴的鸣奏一样。自此,我誓将与生俱来的语言抛弃,因为我觉得原有的语言稚性未脱,慌慌张张,是不可原谅的耻辱。我从新领悟中,尝试了几篇小说,即《母亲》《大地之歌》《草原底盛夏》。但我知道,我看到了方向,而在这几篇内,我与距离的目标相差尚远,我总觉得每一句话,都还未写到预期的效果。[1]195
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是语言和内容的双重革新。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所使用的文学语言,虽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改造,而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革命成果,但那个时代的白话语言正是新鲜的、激进的。他们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开拓(或者说引进)新的内容、主题和表现手法,就足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先锋系。然而,等到白话文学语言的规范建立、成熟并广为传播以后,它势必又将成为新时代的先锋派眼中的陈腐之物。于是,在台湾地区,就出现了王文兴这一批现代派作家对白话文的文学功能的集中讨论和质疑。例如,白先勇强调“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余光中批评五四作家“放逐了旧文字”却没有“创造新文字”,以及王文兴的“文字是作品的一切”之观念,所有这些不满的声音,都在呼吁适应“现代文学”的“现代语言”。他们称之为“诗之语言”。(4)相关论述,分别见白先勇《故事新说——我与台大的文学因缘及创作历程》(收于《树犹如此》,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4年),余光中《下五四的半旗!》(《文星》第七十九期),王文兴《家变·序》(新版)(台北:洪范出版社,2000)。不论是历史现场的发声,还是之后的回顾和当下的坚持,都代表了这批作家群体的一贯主张。白话文没有诗味,非革新不可。从此,王文兴开始了战斗般的语言实验。从《家变》到《背海的人》,可谓日趋极端,其中糅杂白话、文言、方言等的语法语汇,再加上西文句法,甚而有用注音符号直接表示者。而另一方面,对古典作家而言,文学语言的问题便不存在,既然文言文天然地就是“诗之语言”,他们的写作就无须进行先期的反省和领悟。文言文是古典的,旧的,但同时是“非现存”的,对于革新派而言,相对于“现存”,有时候“非现存”就是一种革新,或者说象征着一种革新的战斗姿态。《聊斋志异》(后文简称《聊斋》)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下,率先进入王文兴的批评视野。
以文言写作的《聊斋志异》固然“出格”于五四以来的文学语言传统,但蒲松龄想得到王文兴的独家推崇,还要战胜古代浩如烟海的文言文书写者。而他所凭借的,则是王文兴指出的《聊斋》胜过《红楼梦》的另两条理由:“想象力”与“体制”。
(二)《聊斋志异》的“想象力”
在这一批评语境中,王文兴对“想象力”的定义包括人物刻画、复杂情节以及诗意境界(超现实境界)。[1]15-16尤其是诗意境界(超现实境界),在“想象力”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而这恰恰是蒲松龄最擅长的文学创作之一,在古代的文人小说家中堪称卓绝。蒲松龄承继了魏晋六朝的志怪和唐传奇的双重传统,在《聊斋》中独运匠心,创造了许多极富诗美的“幻境”,来供各类小说人物(广为人知的,是尘世的书生以及山野的狐鬼花妖)活动其间。除了下文将要讨论到的《寒月芙蕖》,我们先以《翩翩》中的那处深山岩洞为例:
入深山中,见一洞府。入则门横溪水,石梁驾之。又数武,有石室二,光明彻照,无须灯烛。……居无何,秋老风寒,霜零木脱,女乃收落叶,蓄旨御冬。顾生肃缩,乃持襆掇拾洞口白云为絮复衣,着之温暖如襦,且轻松常如新绵。……后生思翩翩,偕儿往探之,则黄叶满径,洞口路迷,零涕而返。[2]444-446
小说主人公罗子浮浪游娼家,黄金用尽,被驱赶出来,衣衫褴褛,又一身臭疮,流落于街市乞讨。为人世所厌弃的他,踽踽无立锥之地,境遇极悲惨。尔后入深山中,得翩翩垂青,在溪流沐浴之后,全身疮疤就能脱落痊愈,剪芭蕉叶为衣,就能变成柔软称身的丝绸。一切饮食,皆能变幻。蒲松龄一路细笔写来,到想象秋风起,缀白云为棉絮时,这个远离浊世、自给自足的仙境的营造,就达到了审美愉悦的高潮。因为人世的黑暗和污浊,给予蒲松龄太多的压抑,他借以超脱自我的笔触,便对渲染诗境情有独钟。王文兴从现代派的角度发现了这一点,由此进入《聊斋》,并汲取为自己的文学营养。他的更多个人体验,将在下文仔细论述。
(三)《聊斋志异》的“体制”
这里最后要提到的,是他对《聊斋》“体制”的认识。在王文兴看来,这部容量巨大的文言笔记集,囊括了“社会写实,心理分析,童话,言情,侠义,侦探,政治,灵异,乌托邦,科幻,象征,表现”等等,“试想,写作当时早在十七世纪,只是世界各地小说艺术的发轫初期,而《聊斋》已具备了几乎一切廿世纪都拥有的型式”[1]16。即是说,产生于古典时代的《聊斋志异》,在王文兴看来,完全具备了“现代文学”的内质。再加上先天具备的“诗之语言”的优势,无怪乎在王文兴的“文学战争”中,他一旦“发现”了蒲松龄,就难掩“同道之士”的崇敬和“信仰之情”[1]16。
王文兴认为《聊斋》胜过《红楼梦》的3个理由,从上述结合台湾地区现代派的文学环境所做的分析来看,并非简单的文本比较,或古典文学价值谱系的重新梳理,其实质是王文兴对《聊斋》“现代性”的挖掘和确认,他的目的,乃是要将《聊斋》从古典文学的谱系中单独摘出。用他的眼光来看,《聊斋》就是一个产生于古典时代的超古典文本。因之,对《聊斋》展开现代式解读,就不会像对其他古典文本那样显得牵强附会,而恰恰是去发挥它未尽的“应有之义”。王文兴要用“3个理由”去先期解放《聊斋》的阐释空间,这是王文兴在中国古典文学脉络中重新“发现”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相契合的文本时的珍惜和慎重。他的这种回溯式的寻找,起始于他本人的阅读兴趣和审美趣味,终而发展为沟通中国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自觉。而这种批评的自觉,扩而充之,就自然衍生出小说家日后《明月夜》的创作自觉来。
回到《聊斋》。《重认〈聊斋〉——试读〈寒月芙蕖〉》(1974)是王文兴对《聊斋》文本进行现代式细读的一个典型。《寒月芙蕖》的故事,记载了一位以高明法术来警醒世人的济南道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神通。首先,王文兴提取《寒月芙蕖》的主题为:
《寒月芙蕖》的重点不在故事,也不在人物,是一篇着重哲学意识的小说。型(形)式上,它是一篇单纯的文以载道的寓言。文以载道不一定就是儒家的道,西方文学中载的多为基督之道,《寒月芙蕖》载的是道家之道。……《寒月》所要表达的道理,简单的说,就是“镜花水月”的道理。套句现代人的白话,就是:“现实”与“幻象”二者间的难以区分也就是illusion与reality的affinity。[1]17
蒲松龄在这篇小说中塑造的道人形象,是按照典型的史传体例,撷取他在世俗时间中的几个独立事件,虽然前后不相连属,但凭借着人物的线索贯串起来。而这种传统的连缀叙述方式,在王文兴将该小说的形式定义为“哲念的表达”的寓言体后,就上升为以“现实与幻象不分”的主题为线索一以贯之,而不再是人物。无形之中,这篇小说的叙述手法就打破了传统。这种革新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被解读出来的革新的姿态,对王文兴而言当然是一种精神同道。
此后,王文兴对《寒月芙蕖》展开了逐段细读,全部的用力都在阐明蒲松龄是如何熟练地运用诗意的文字和想象力来突出这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其中,小说的核心场景是水亭大会时,有贵人感叹良辰美酒,高朋满座,唯有风景欠佳。时值寒冬腊月,水塘枯槁,这位贵人却希望有“莲花点缀”:
少顷,一青衣吏奔白荷叶满塘矣。一座尽惊,推窗眺瞩,果见弥望青葱,间以菡萏。转瞬间,万枝千朵,一齐都开,朔风吹来,荷香沁脑,群以为异。遣吏人荡舟采莲。遥见吏人入花深处,少间,返棹白手来见,官诘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见花在远际,渐至北岸,又转遥遥在南荡中。”道人笑曰:“此幻梦之空花耳。”无何,酒阑,荷亦凋谢,北风骤起,摧折荷盖,无复存矣。[1]23
王文兴认为这是“全篇发挥得最透澈的地方”,“幻梦之空花”恰切地点出了小说的主题。寒月的莲花,突然出现在冷湖之上,接天莲叶无穷碧,又在一段酒饭的功夫,由开而盛,再至衰败摧折,道人的幻术正在于警戒世人:“这个过程就是人世间一切生老病死,从繁华走向衰败的过程——这瞬息就是人生的缩影,从而让人感觉到人世的无常,一切的一切都无非是一场春梦而已。人世究竟是真象,是幻觉?”[1]24
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一直是王文兴写作的重要主题。比如,他的短篇小说《日历》写一个17岁的少年,闲来无聊,伏案手绘日历,一边历数着自己的年岁增长,终将一张大白纸填满,因为再也找不到继续绘画的空白,少年开始认真思考起“这就是生命的终点了吗”这样一个严肃的命题。始于为快乐而游戏,却以伤心落泪收尾。《日历》就是一个少年某一天的突如其来的人生苦闷。[3]69-70另一篇《命运的迹线》,写一个小学生假称获传相手之术,向班里的同学一个个宣布他们将来各自的命运。主人公因为生命线的短促,被判定30岁就会死掉,这造成了他内心极度的恐慌,以至于最后用刀片人为地延长生命线,却几乎因此丧命。[3]125-140而《海滨圣母节》中,主人公因在海难中向妈祖祈祷而获救归来,他决定在妈祖的祭日舞狮酬答神恩,却在节日中死于过度劳累。[3]107-124如此种种,都透露出现代派的一个重要的书写对象——对人生/命运的焦虑。而通过细读《寒月芙蕖》,王文兴借以阐发因应的解决之道:“能了悟‘镜花水月’,能超脱‘镜花水月’的人,无所不能,无往而不利。”[1]26济南道人就是蒲松龄为众生树立的这样一个典范,神通广大的道术,象征了“人生的焦虑”解决以后,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
在另一篇解读文章《〈聊斋〉中的戴奥尼西安小说——〈狐梦〉》里,王文兴更是把《寒月芙蕖》的主题进一步推衍为《聊斋志异》的普遍性主题:
刚才曾说Dionysian style(5)即酒神风格。这篇小说的风格所在,它还有另一种风格,就是现实与梦境难分的风格。我们所说的Dionysian风格,也就是作者和毕怡庵的哲学态度,同样的,现实与梦境难分的风格,也是这篇小说的哲学态度。而且不但是这篇小说的,甚至是《聊斋》每一篇小说的哲学态度。换言之,蒲松龄对人生的看法是如此,他认为对人生的态度,无须把现实和梦境分得太清楚,人生应把它看成介乎梦境和现实之间的混沌部分。依“现实和梦境”而言,狐梦应该是全部《聊斋》中的一节,它是属于整个整体的小说。因此就全书来看,《聊斋》是一部组织严密的文学作品。[1]47
在这个意义上,《聊斋》全书以寓言的结构(包括每一篇的独立结构和全书的整体结构),呈现一个象征性的文本,既投射为具体丰富的各种人生形态,又全部归结为“介乎梦境和现实之间的混沌”。明了这种混沌,就意味着超出了对任一端(现实/梦境)的执着(6)“现实”固然不可执着,“梦境”其实亦如是。对二者之一存有执念,皆不能“得道”。,从而实现了自我的解脱。王文兴对于《聊斋》这一人生观的抽绎,与其说是蒲松龄的设意,不如说是他自己的求解脱于现代人的人生/命运焦虑。不过,这种阐释建立的基础,确是蒲松龄在古典时代感受到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之力(在连年的科举失意中沉浸、反思)。这一人生命题与几百年后的现代人相通,所以,这一根本性的现实依据并非出于王文兴的幻设,那么,这种阐释对于《聊斋》的文本而言就独具信服力。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恰如其分的文本中,把握到古典时代一颗鲜活的心的跳动,《聊斋》主题的“现代性”,当是王文兴倾心于这部文言笔记集的第4个理由。
二、从《聊斋志异》到《明月夜》:超脱与回归
20世纪70年代的王文兴对《聊斋》的推崇相当狂热。但21世纪以来,他又重新梳理了古典文学的价值谱系:
《聊斋》固优美,但日后读到其他笔记小说,方知优于《聊斋》之作亦不在少数。……中文方面,影响最大来自杜甫……此外亦称许《履园丛话》的钱泳、苏辙、王安石、桐城诸人、刘大櫆、吴挚甫。[4]
以上文字似乎表明,随着王文兴创作实践的发展,《聊斋》已经淡出了他的文学视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部笔记小说集,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从《聊斋》向《履园丛话》的倾斜,直接反映在《明月夜》(2006)的写作上。这篇小说就是紧紧围绕《履园丛话》的一则记载展开的。但我们同时能够注意到,《聊斋》的地位在王文兴这里虽然降低了,但从《聊斋》中提炼出来的“人生介乎梦境和现实”的主题却得到承袭,并被进一步详细地书写(虽然依托的是另一个古典文本)。与《聊斋》相比,这是一篇真正的现代派作品,无须阐释即带着与生俱来的现代主义基因。为了因应作品主题本身所笼罩着的迷离色彩,王文兴运用成熟的叙述技巧,成功营造出与之相匹配的一种极迷幻的文风。
为了清楚地呈现这一书写效果,接下来就借用王文兴批评《聊斋》的方式,对《明月夜》展开一次细读。
小说采取了一个特别的开篇方式:全文录入《履园丛话》记载的那则材料。因为对整篇小说以及接下来的分析都至关重要,故不以烦琐为嫌,转抄如下(7)以下引文,皆出自《明月夜》,除成段引用外,间有引语,不另出注。:
嘉庆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门外地名南台,人烟辐辏,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间,忽有两童子衣朱衣连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边火烧宅,珠娘啼一路。”闽语谓夜为晡,屋为宅,妓女为珠娘,以方言歌之,颇中音节。连歌三日,不知其为谁氏子也。居人以其语不祥,遂告邻近,于中秋夜,比户严防,小心火烛。至期,绝无音响。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边起火,延烧千余家,毘连妓舟,皆为煨烬。至五月初一日晡时始熄。计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数至八月又十五日,适符“八月十五晡”之谣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亲见其事。[1]351
这则笔记的核心情节是关于一场大火灾的预言,而因为人们的误解,预言并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在抄录文言文材料之后,王文兴又紧接着给出了全文的白话文“语译”。从第三段起,他才告诉读者,这则笔记是一个叫刘基培的人偶然间翻到的,那么,开头所录的文言文和白话翻译,都是刘阅读的产物。按这种处理方式,《履园丛话》的记载就产生了双重性质:既是当年大火事件的实录,又是小说人物的阅读记忆。而这个记忆,在另一个叙事层面,构成了整篇小说情节发展的全部动力。
这位刘基培,是一个即将去福州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台湾学者,临行前却偏偏看到了这则记载福州大火的史料。他想起自己的外曾祖曾在福州任官,他的母亲又恰好跟《履园丛话》的作者钱泳同姓。以及,作者又特地介绍了刘基培所参加的学术研讨会的议题,是“朱子的学术和生平”,而此朱熹之“朱”又与彼朱衣童子之“朱”(火)相同。总之,在故事的开端,作者要极力渲染的(借助小说人物自己的联想以及叙述者的补充),正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这种巧合,配合以高悬于小说篇首的那则笔记原文,让读者和刘基培都莫名地觉得,这趟福州之旅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很可能是一场火灾)。这种联系之所以是莫名的,因为它根本缺乏科学依据,但同时又千丝万缕,牵扯不清。
就在这种恍惚的状态下,刘基培动身了。此后,王文兴的叙述,最大的特点,就是按照《履园丛话》原文的语序,几乎是逐句对应地展开全篇的情节。比如,笔记的开头是一个时间标记“嘉庆乙亥八月初”,而作者也率先交代了刘基培故事的时间:“时为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到十八日”。刘基培一到福州,就被安排在“福州城外的西湖”边的宾馆,这对应笔记里紧邻的下一句“福建省城南门外”,而显然作者有意强调了两个地点同属城外和水边的相似之处。接着,与笔记“衢巷间,忽有两童子衣朱衣连臂而歌”相对应(在语序和情节的双重层面上),刘基培发现宾馆柜台处,“有两个红衣服的服务员”,“两个人,看来有点像,简直就像是兄弟”,他们之后出现在宾馆前的大花园里,“坐的那个正在拉一把胡琴,有琴声扬抑,但他们未唱歌”。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天,正与笔记“连歌三日”对应。他们遗留的歌单上有曲名“月儿弯弯照九州”,而两童子所歌中同样有“月”的因素。柜台换成一个穿白制服的服务员后,刘基培询问红衣服务员的下落,居然得到“哪有两个人——这儿都只有一个服务员”“穿红制服的?没有啊,我们哪有穿红制服的?”这样的回答,正与笔记所载“不知其为谁氏子也”吻合。当天晚上,刘基培忽然闻到燃烧的气味,原来是花园里有一堆小火,正在燃烧垃圾,虚惊一场。这个情节,也与笔记“至期,绝无音响”对应。就在刘基培放松警惕的时候,一天的半夜(对应笔记里的“夜半”),“他开门,他看见走廊都在大火之中”:
走廊上,那两个,红制服,服务员,手臂扣挽着手臂,正走过来,一人拉着提挈的胡琴,共同高咏:“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边火烧厝,珠娘哭一路”,以“台语”唱咏。四周都是奔跑的人,有说:“火从南台来的!”有说:“到处都是火!城里城外,都在烧。”……但见每一棵树都烧起来了,是一株株的火树。园子里都是奔跑的人。有些是女人,发出嘤嘤的哭哎。他想,应该,逃到,湖面,上去。但,所见,湖面亦是──一片火海。他怎么逃得出去?他看天,天也在烧,看到几只鸟,像火鸟一般,打天高坠下来。[1]357
这是个梦,一场火梦。它像第三个故事,内容则是笔记和现实的混合体,有笔记的元素,如手臂扣挽着手臂、高咏、南台、女人等,也有现实的元素,如红制服服务员、胡琴、花园等。这个火非常大,全城起火,天地都在燃烧,大家都很恐慌,完全一副末日的景象。作者特意着重描写这个恐怖的场景,既是对应笔记“洲边起火,延烧千余家,毘连妓舟,皆为煨烬”的叙述,又以详尽的扩充,使人可以充分想象嘉庆年间,福州南台那场真实的大火所造成的可怕情景。诚然,这是刘基培的梦境,但它对梦中的刘基培而言,无疑是再真实不过的体验。而另一方面,它又像是对嘉庆大火历史现场的追忆,那时的福州城一片火海,与这个梦里的场景又有什么两样呢?所以这梦的描绘对那个历史事件而言,同样是一定意义上的真实。在阅读记忆、现实经历和梦境的混合状态下,醒来的刘基培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感受:
这一个梦,他觉得,就跟真的一样。他觉得,他像:经受,真的,一场之火浴一样。他想:真的假的,中间有什么不同?[1]357
王文兴在《明月夜》中通篇贯彻的是用逐句对应(同时在语序和语义两个层面进行)的手法叙述主人公刘基培的故事,使得整个故事与小说开头第二段的白话文语译具有了同等的性质,即是对《履园丛话》那则笔记的另一种“翻译”,一个是用白话文翻译文言文,一个则是用(现实)故事翻译(历史)故事。这种苦心构造、深入小说每个细节的“翻译”结构,显然是王文兴特地设计来与小说的主题相契合的叙事发明。它产生了如影随形的互文效果,就像《履园丛话》的阅读记忆如影随形于刘基培的这几天思绪中一般,使读者和小说人物同时陷入了“梦境”(历史)和“现实”难以区分的混沌之中,那么,这篇小说的主题,就不是归纳而得的,而是体验而得的。所以,王文兴不忌讳于直接在小说中点出主题,因为他这个时候的点题,恰恰完成了作者与小说人物以及读者之间最深刻的共鸣。
王文兴的“翻译”还在继续。刘基培醒来后,苦心计算“八月十五”的预言时间与火梦时间的关系:“他如今想通了,当是八个明灿的月夜,从他来以后算起,十五是十之五,半夜的意思。”这对应笔记在大火以后补叙的文字“计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数至八月又十五日,适符‘八月十五晡’之谣也”。但钱泳的笔记之所以记载预言的算法真相,是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大火,而刘基培只是做了一场火梦,却还要把自己目前的时间,代入进去计算(事实上,在现实中,那两个服务员根本就没有唱出预言之歌)。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所谓人生“介乎梦境和现实”不会因梦醒而终结,反之,它恰恰是“人生”本然的状态。在之前对《聊斋》的解读中,王文兴同样在强调这一点,但那时的他同时在寄寓一个情怀,即当世人醒悟了人生的混沌状态时,就能超脱而出,成为济南道人那样清醒的“得道”之人。而《明月夜》并非如此,王文兴用这个信号传达出他的新的观念:人生的混沌,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无所谓觉悟和超脱。所以刘基培一直都没有觉悟,更不论超脱,他沉浸其中,反复计算,并孜孜不倦。在小说的最后,他依然如此:
接待他去鼓山的人来了,走到他坐的石凳前,恭恭敬敬的递上他底名片,他看了看上面,写的是“王”“茂”“才”三字。一路,他问那人,认不认识一个,“王子若”,那人茫然。又迂回说,他想找一本书,叫《履园丛话》,他听见过没有,那人也茫然。[1]358
《履园丛话》的原文到王子若出场为止,王文兴的“翻译”叙事也到此为止。可以说,刘基培九天的福州之旅,正是一段介乎梦境和现实的人生经历。九天,也成为整个人生的一个象征。这篇小说,王文兴将人生的焦虑,用一种无害的方式呈现(不像《日历》《命运的迹线》《海滨圣母节》等早期小说那样呈现现实的残酷),并化解于一种混沌的人生观中,造成一种迷离的状态,虽然不是泾渭分明,像《聊斋》中的济南道人那样超脱物外,却让人感觉到一种人生的朦胧美和神秘感。可以说,这是王文兴让“人生介乎梦境和现实”的主题回归平凡人的境界,回归本然,但同时也更加真实,更加充满美。与济南道人式的人生相比,刘基培式的人生,其意义就在于体验“介乎梦境和现实”的生存状态,而非为了超脱。王文兴的创作《明月夜》,并不是在教化,他只是向读者展示人生本来的样子。这是《聊斋》与《明月夜》主题的同中之异所在。而这个差异,恰恰反映出王文兴对人生思考的一个变迁的过程(跨越30年)。
三、结语
关于人生的状态,中国古典美学向来有一个极富特色的命题:人生如梦。这个命题,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出现,又在各个时代的知识阶层中传播、接受,出入儒、佛、道,辗转于宗教和世俗之间。蒲松龄及他的《聊斋志异》,或许没有如王文兴所断言,在全书的结构上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精神寓言,但《聊斋志异》承袭这一美学渊源,序列于此脉络之中,则是毫无疑义的。王文兴从《聊斋志异》进入古典美学的这一精神空间,把“人生如梦”进一步发挥为“人生介乎梦境和现实”,强调它的混沌状态,并在《明月夜》的书写中,用恰当的素材和结构手法完全展示出来。相比于“人生如梦”,“人生介乎梦境和现实”不仅解构了前者命题中的“人生”,同时解构了“梦”,它的无法清晰界定、复杂多义,无疑更具现代主义的精神。人生问题一直是王文兴追索和创作的对象,其间起伏纷繁不定,但如果从《聊斋》到《明月夜》的这条脉络加以考察,王文兴关于人生“真相”定格了的认识,已经隐然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