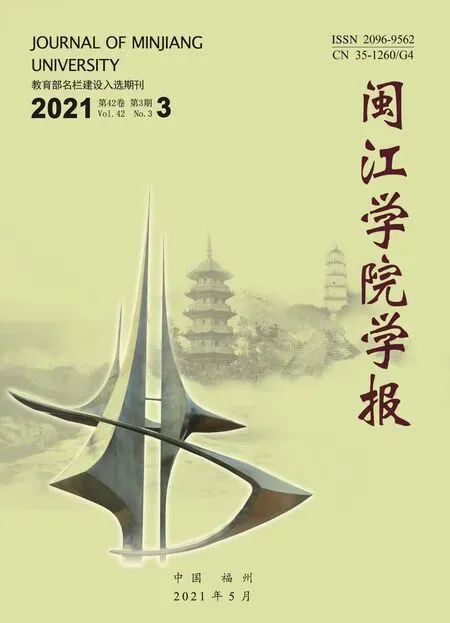《尚书》名称源流考
陈罕含
(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台湾 新竹 30013)
“《书》之所起远矣”[1]868,早在西汉,儒生就有如此感叹。作为书名的“尚书”,它并不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2]2 064那般,如今只是“空有其名”,难以指实。不论传统古书与新近的出土材料,还是古人、今贤的讨论成果,都不断厘清了“尚书”的“名”“实”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欲专门考察《尚书》这个名称的源流、定名及此名称开始流行的时代。全文分为三部分进行讨论:首先,在“尚书”二字中,代表它书籍性质的“书”字含义为何,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确定的是,在先秦时期,“书”的指涉为何?其次,“夏书”“商书”“周书”的称谓该如何界定?再次,“尚书”的“尚”字含义为何,且更重要的是:“尚”字加诸《书》上,可追溯到什么时期,以及这种名称从何时开始流行。
一、“书”的界定
商代甲骨卜辞与记事之辞中未见“书”字,两周铜器铭文中“书”字像手持笔书写状,“书”的本义就是“书写”。[3]许慎言:“箸于竹、帛谓之‘书’。”[4]竹、帛乃以部分代表全体,指一切书写载体。汉语的动词往往兼具名词词性,反之亦然。不论是书写的动作,还是书写下来的文本,皆可称“书”。这与“歌”“舞”既是动词,又是名词是一样的。可是,早先并非人人皆持笔作书,书写者往往由专人负责。战国以前,书写活动基本局限在贵族阶层,尤其是与国家政治运作相关的部分,以后代的角度来看,它们多属公牍、档案的范畴。
(一)早期史料中“书”的分类
1.命书、赉书
如西周中期《免簋》:
王受(授)乍(作)册尹者(书),卑(俾)册令(命)免。[5]2 456
陕西眉县杨家村挖掘的四十二年逨鼎上有铭文:
尹氏受王釐书,王乎(呼)史淢册釐逨。[6]
赉书主于赏赐,命书则包括“任命、赏赐、诰诫”[7]。周成王驾崩,太子钊继位,《尚书·顾命》载曰:
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曰……[8]240
册命仪式结束后,受命者“受策以出”[2]1 826,“受书以归”[9]。
2.载书
载书,又称“盟书”“盟载”“盟”“载”,《左传·襄公九年》:
晋士庄子为载书。[2]1 943
它是列国或贵族团体间的昭神盟约书。20世纪出土的侯马载书与温县载书一般被认为是春秋末晋国所藏,以朱书或墨书写在石、玉上。[10-11]
3.刑书
刑书本由专人保管,不对民众公开,仅在听狱治罪时使用,见《尚书·吕刑》:
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8]250
而《左传·昭公六年》:
郑人铸刑书。[2]2 043
则铸鼎在外,律令条文公开化。
4.书函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2]2 005
“玺书”特指君主封泥之“书”,钤盖印章意味文书具备法律效力。发出书函的行为可称“寓书”“诒(某人)书”,回复书函的行为可称“复书”,阅读书函的行为可称“读书”。
5.计簿
先秦周室、诸侯国皆有各类档案记录,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记录户口、地理、物产、税收等数据的文簿,作为王朝统治的关键命脉,《周礼》为此专设“司书”一职[12]。萧何所抢救的秦“图书”亦属于这一类。[13]234
6.礼书
礼书是关于典制或礼仪操作教程的记录文本,《左传·哀公三年》:
命宰人出礼书。[2] 2 157
可见礼书亦由专人管理。《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曰:
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2]1 861
无论此处的“周礼”是否为一专有名词,它都已经被人用文字记录下来。
7.卜祝文
卜祝文包括龟书、筮书及其前身的兆象、繇辞记录、册祝文等。《尚书·金縢》:
史乃册祝曰……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王执书以泣。[8]196-197
“乃并是吉”之“书”,《释文》引马融云“卜兆书”。“金縢之书”乃先前“册祝”之“书”,伪孔《传》云“史为册书祝辞”。占兆书与今本《周易》有密切的关系。[14]《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2]2 029,其中有“易象”,即鲁国历来筮象记录。
8.史书
《左传·庄公二三年》曹刿谏鲁庄公曰:
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2]1 779
《国语·鲁语上》亦载宗人夏父展诰庄公:
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15]
君主的言行不论好坏,皆由史官负责记录,并且把记载下来的“书”保管在档案库中。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上文所引的《左传》《周礼》诚然皆战国中叶后才写定,但载书、刑书、计簿等都是政治性文件,可见把“书”当作公牍的传统用法仍被保留下来了。同时,以上八类仅是举例而言,我们不能把眼光盯住“书”这个字眼而不探究它的实质,例如“载书”“命书”完全可以不称“书”,仅称“盟曰”“命曰”,如《左传》:
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2]1 821
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繄伯舅是赖。今余命女环,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旧,敬之哉!无废朕命。”[2]1 958
(二)先秦“书”的语义分析
如果按照“箸于竹、帛谓之‘书’”这种界定,一切书写记录的文本都是书,这显然不符合先秦称“书曰”“周书曰”等所隐含的认定。孔《疏》当年驳王肃“书者,以笔画记之辞,群书皆是”[8]115,应该也是依循类似的逻辑。文体分类的总体趋势往往是愈分愈细,春秋以来,常常可见“书”与“诗”“礼”“春秋”等并称。先秦“书”可指某种文类(1)近来不少学者皆持类似观点,如何定生《读诗纲领·一·诗三百原不称经》中说到:“‘诗’的本原,不过表示一种文体——有韵之文——和‘书’之表示其为散文文体一样,所以‘诗书’连文,便可包括古代文籍的全部;我们也可以说,‘诗’只是一个文籍的类名”(《定生论学集——诗经与孔学研究》,台北: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第3页);(美)艾兰:“如果我们将《书》定义为一种文献体裁的话,《书》就是任何声称是实时记录古代君王讲话的文献”(《论〈书〉与〈尚书〉的起源——基于新近出土文献的视角》,《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马士远:“早期所称说的《书》是与《诗》《礼》《乐》相类别意识产生后的结果。在其与《诗》《礼》《乐》类分之后,其同类性质的数据仍不断纳入其中,同时也有一些同类数据不断被淘汰或丢失,故在此种意义上讲,《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作为类观念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的,而不是作为一部固定的典籍而流传的”(《周秦〈尚书〉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等。,如赋、颂、铭、箴、章、表等一样。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分得出某类记载才能被称作后世认为属于《尚书》的“书”?以上所举命书、载书、刑书、书函、计簿、礼书、卜祝文、史书这八大类,它们都与政治有关。无怪乎《荀子·劝学》会说:
书者,政事之纪也。(2)杨倞《荀子注》“书所以纪政事”的解释似乎没有把“纪”的意思训解清楚。下文:“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与“纪”相呼应的是“止”“分”“纲纪”,可知“纪”当训解为纲纪、准则。(王先谦:《荀子集解》,台北:艺文出版社,2007,第118-119页。)
换言之,书教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远”,而且要经由“疏通”(《礼记·经解》),领悟古今之变与不变者。根据见存的《尚书》与《书序》(除了《禹贡》《金縢》(3)孔颖达已经看出,《禹贡》“史述时事,非是应对言语”,《金縢》“叙事多而言语少”。(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6、196页。)),只有君主对大臣的训话或任命,大臣劝诫君王,或君与臣、臣与臣相与言而涉及政事者这一类“以笔画记之辞”才是被后世归入《尚书》的“书”。在《尚书》中,“书”的范围明显缩小了,载书全然不见;刑书只有《吕刑》一篇,主要内容还不在刑律本身;计簿、礼书仅有《禹贡》《尧典》《顾命》部分内容约略相关;卜祝文也仅有《金縢》稍存梗概,相较于《诅楚文》,卜祝内容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尚书·召诰》:
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8]211
这篇书当然是政治文件,又《洛诰》: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8]217
虽然对象是祖、父神灵,这篇由史逸作的“册”依旧是政治文件,而且是让文王、武王安心他们开创的基业不会被动摇的重大政治文件,然而周公用的那篇“书”,以及史逸作的这篇“册”能加书名号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它们的内容固然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只有在归档后,为了避免与其他的“书”“册”混淆,以便识别,这才加上某标题。不管哪个王朝或诸侯国所保存的这类记录,古人称引其中的某段或某句话,都可冠以“书曰”。由于被称引某段或某句话一定出自某一专篇,因此“书曰”的“书”仍应加上书名号。就像某种古文字的汇编库、搜索某种主题众多的网站,只要从中撷取数据,还是得在注明出处时,加上专有名词号。尤其当儒生秉承孔门传统,以《诗》、《书》、礼、乐等先王学教授时,虽然“儒分为八”[16],彼此选编的“书”内容不一致,但各家本门使用的那本“书”确确实实是本专书,至多只能说此《书》非彼《书》。
综上所述,先秦“书”的语义可粗分为二:
一是广义的“书”,指一切书写记录的文本。
二是狭义的“书”,指《尚书》这种文类作品,它以君主训话或任命臣民,大臣劝诫君主,或君与臣、臣与臣相与言而涉及政事这一类的纪录为主,兼及其他相关的政事典章。与“诗”一样,会被选作贵族子弟的学习教材。
从造字原理来看,广义的“书”在前,狭义的“书”在后,但是从铜器铭文与传世史料来看,早先见到的“书”的确都属于公牍一类的作品。至于何时开始,“书”从纯粹的公牍、档案,逐渐转为某一类由文件编纂而成的书籍专称,史阙有间,殊难断言。《论语》两度称“《书》云”: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7]59(4)所引《书》文断句有两种可能:一为读至“兄弟”,一为读至“有政”。笔者浅陋,难以断定,暂且阙疑。参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四《为政下》,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7-163页。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17]160
配合孔氏门人记载“《诗》《书》,执礼,(子)皆雅言也”[17]97,以及“子路使子羔为费宰”,表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17]130,意谓当官仰赖的乃具体历练,无须参考古代施政教训的记录,大概至春秋中叶后期,对于某些人,“书”已经成为某一批古代文件撰集的专称了。这与《左传·襄公十三年》“君子”评论时,称引“《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2]1 954,《襄公二三年》“君子”评论时,称引“《书》曰:‘惟命不于常’”[2]1 975,前者见诸《吕刑》,后者见诸《康诰》,时代正相印合。如果将《隐公六年》“君子”评论时称引《商书》,《庄公八年》庄公称引《夏书》,《僖公五年》宫之奇称引《周书》也考虑在内,则春秋初叶,“书”已经成为某类文件总集的专称了。
二、“夏书”“商书”“周书”称谓的界定及流传
先秦古书常引“夏书”“商书”“周书”等,“书”前加限定语,本身就是一种分类信号。既然“书”可作为文类之称,那么“夏”“商”“周”该如何界定呢?长久以来,这似乎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人们按照后世情形推想,已经习惯把“夏”“商”“周”当作三代了,如孔颖达《论三代易名》引《易纬》:
因代以题周。[18]9
“夏”“商”“周”的确是界定语,但如果胶以“世代”释之则不免有扞格处,孔颖达已有所觉察:
《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18]9
他注意到“犹是殷世”与“周”代的冲突,所以把《周易》的“周”当作地名来解释,同时,融合周地、周人、周代三者,并以别殷,然孔氏受限于时代,观念尚未清晰。如今不论是传统史料的既有线索,还是近来的出土材料,都为突破三代单线继承发展的旧有认知提供了有力证据。(5)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指出:“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沉浮而已。”(《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75页。)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夏书”等称谓的实际意义。
战国之前,乃城邦形态的政治,只是当中某一国力量特别强大,就成为了宗主。从后世来看,当然可以说“周”代表一个时期,但也可以说它是拥有京畿地区的国,只是在法礼上,这个国同时也拥有天下。既然如此,“周书”的“周”既代表某地区的城邦,又代表来源久远的一个城邦以及一个古老的部族。“夏书”“商书”亦然,这些称谓兼具部族、地域、时代多重意义。
后世以《尚书》中《夏书》《商书》的某些篇章较诸《周书》文字平浅为怪,是因为认定“夏书”为夏代人所写,“商书”为商代人所写,三代相隔渺远,理应“夏书”“商书”比“周书”更加艰涩难读。这种观点恐有片面之嫌。《尚书·周书·多士》周公当着“殷遗多士”说: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8]220
根据《竹书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3]16换言之,五百年前,商朝的官方“典”“册”都留存下来。商王室就算不再膺任天下之主,而只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宋公,其后裔纵使未必全盘善加保管这些“典”“册”,但总尚有一些政治文件流传至后世。只要还有人认为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智慧,或加强族群的认同感、荣誉心,就会将之整理成一可资使用的书档。一旦整理,就会遭逢一现实的困境:殷先人最晚的文件已隔两百五十多年(6)《史记》卷四《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司马迁:《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20页。),遑言在此之前的“典”“册”,随着时光推移,措辞、语法、叙述方式都变了,那些人预设的读者如何能通晓这些佶屈聱牙的文件?在不违背主旨的前提下,以当时通行的文辞训读重写,势在必行。颇类似司马迁要将《尧典》《禹贡》《皐陶谟》等纳入《太史公书》时一样,非得在某些地方易以别的词汇。《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国欲以诸侯之师伐楚,面对楚国使者“风马牛不相及”的诘问,管仲搬出三百年前对齐国老祖宗姜太公的任命之辞: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2]1 792
以既有史料而言,“五侯”“九伯”“夹辅”“周室”都首见于此处(7)西周早期的《保卣》《保尊》已有“五侯”,但那是指太保麾下的“殷东国五侯”,并非五等诸侯之谓。又西周早期至晚期,习用的是“绍夹”或”夹绍”而非“夹辅”,如早期的《盂鼎》可见“绍夹”,晚期的《师訇簋》《禹鼎》,“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铭文皆用“夹绍”。,可见这段话已经不是西周初委任状的直接复述,而是改用当时贵族们容易理解的词句叙述。
此外,见存的《尚书》中有四篇非常值得注意。按照《书序》所言:
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8]159
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8]177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8]223
它们既非出自君王之口,又不是当事人对君王的劝诫,纯属大臣个人间的言论,所谓“微子若曰”“父师若曰”“周公若曰”“公曰”,为何会有史官记载下来?尤其是《微子》,乃私下密议出亡,必然会屏人耳目。略加深思,或许就不难明了了。不论周公是否称王,他摄行王权这一点,自古以降无二说,则当时他的话就如同王的话,当然得记档。同样,不论按照《竹书纪年》还是按照儒生的说法,伊尹曾有一段时间为最高领导。《竹书纪年》曰: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2]2 188
《太甲·序》云: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8]163
在这期间,无论伊尹是主动将自己的言论视同王言,交付史官,或者史官从某个来源搜集到而追录,都乃情理中事。微子降附周室,被封为宋公,“代武庚”为殷后,“奉其先祀”[13]196。既为国主,他的言论当然归入《商书》的档案中。换言之,《汝鸠》《汝方》虽然片言只字不存,但以《微子》的情况来看,这应该就是当初他与父师、少师的言论,只是重写版而已。
如果上述推论无大谬,“夏书”可以是夏代后嗣——杞所述,“商书”可以是商代后嗣——宋所述,此所以孔子能用杞、宋二国“征”考“夏礼”与“殷礼。[17]63需补充说明的是:“夏书”虽未必为夏代所写,但历史观念的形成,绝非朝夕之事。古人叙述前代故事,一般不会凭空悬想,往往有其传闻依据。
因此,结合上节关于“书”这种文类的分析,“夏书”“商书”“周书”即夏、商、周三朝及其后代子孙保存、搜集的本国历代以君、臣训诰为主的记录档案。(8)“虞书”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待日后再另撰文讨论。
三、“尚书”名称伊始考
作为先秦“书”篇选集的《尚书》(不包括伪古文部分),它的出现迟于“夏书”等“书”类档案。“《尚书》”之名,以往多依伪孔《尚书序》所说,认为乃伏生所取:
济南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8]115
孔颖达疏曰:
“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者,此文继在“伏生”之下,则言“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书》之名,名已先有,有则当云“名之《尚书》”。既言“以其上古之书”,今先云“以其”,则伏生意之所加,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8]115
孔氏借此解释了一大现象:
以“书”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诸引《书》直云“《书》曰”。若有配代而言,则曰“《夏书》”,无言“《尚书》”者。[8]115
他已观察到先秦古书引《书》时,但称“《书》曰”或“配代”称《夏书》《商书》等,而从未见“《尚书》”之称。今所见先秦传世典籍与孔氏眼见必大有间,而不见《尚书》之名则如旧,除了一个“例外”——《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前人多采纳王念孙之说:
“尚书夏书”文不成义。“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则夏书,其次则商、周之书也。此涉上下文“书”字而误。[19]
然在原文能够解释得通的情况下,似以不改字为当,屈万里就指出:
其所谓尚书者,意谓上古之书,乃泛称而非专名。[20]
孔颖达既以汉孔安国“亲见伏生,不容不悉”[8]115,又以先秦诸引《书》无言“《尚书》曰”为证,认定《尚书》之名起于伏生。暂且不论此《序》乃假托汉孔安国之名,仅从史传所载来看,历史上汉代的孔安国根本不可能见到伏生。(9)据《汉书补注》卷四九《晁错传》、卷四《文帝纪》,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事疏》当在文帝十四年(前166)冬匈奴三寇边境之时,则此前以太常掌故受《尚书》伏生所至迟为文帝十三年(前167),伏生时年已九十余。又据《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孔安国任临淮太守不久后辞世,为“蚤卒”,安国生年当在孝景前三年(前154)后,此时伏生若尚在人世,已百余岁,与呱呱之子间恐难有一面之缘。参朱晓海:《读易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6年,第64页。当然,推论过程有误,不代表结论一定错误,这仍有待于后文进一步考辨。
《尚书正义》《经典释文》等古书称引汉、魏人关于《尚书》名称的解说,并没有伏生命名的说法。除伪孔《序》外,明确提出《尚书》命名者的还有另外两家:
一为刘歆《七略》的“欧阳氏先君说”,《初学记》引曰:
《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复立于学官。三家之学,于今尤为详。[21](10)又《太平御览》:“刘歆《七略》曰:‘《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立于学官。三家之学,于今传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按《七略》亡佚年代,据钟肇鹏《七略别录考》指出:梁、陈以来,已流传不广。《唐六典》有著录,说明开元时中秘还有此书。徐坚奉勅撰《初学记》,或尚及见《七略》,而《太平御览》大概就是转抄了(《文献》1985年第3期)。再者,《御览》“始”“先”二字稍嫌义复,不如《初学记》所引辞义为顺,且欧阳《尚书》先立于学官,“复”字似不可少,《御览》又失之,故本文以《初学记》所引为据。
按《史记》载伏生以《尚书》教授欧阳生[13]341,惠栋认为欧阳生指欧阳容[22]893,其说概是。《尚书》传至欧阳高立为博士,“为《尚书》欧阳氏学”[22]893,则刘歆之称“欧阳氏”应即欧阳高,“欧阳氏先君”当即欧阳家传《尚书》的始祖欧阳容。
二为郑玄及其所据纬书的“孔子说”,孔颖达疏曰:
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书赞》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璿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尚”以尊之。’又曰:‘《书》务以天言之。’”[8]115(11)亦可参《经典释文》卷一《序录·尚书》:“郑玄以为,孔子撰《书》,尊而命之曰‘《尚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综上,唐以前关于《尚书》命名者有三种说法,一为西汉刘歆《七略》的“欧阳氏先君说”;二为东汉郑玄的“孔子说”;三为晋伪孔的“伏生说”,为唐孔颖达《正义》所接受、阐扬。以下试以传世典籍、出土文献检验三家说法的可信度。
子承父业、遍校六艺群书的刘歆既将命名者归汉,但现在可见的汉以前典籍却未见此名。然而,出土材料却给我们带来新的视野,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易传《要》篇首现“尚书”二字。谨录《要》篇出现“书”字的相关语句于下:
(3)故《易》之为书也……[23]118
(4)而《诗》《书》、礼、乐不□百扁(篇),难以致之。[23]119
按(2)、(3)以《易》为“书”,第一节已说明原因,兹不赘述。廖名春认为(1)中“《尚书》与《周易》并称,其为书名无疑”[24]158,其说有理,而在(4)中,配合行文,即径称为“《书》”。要之,“《尚书》”之名,《要》篇已见。《要》篇所处三号墓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从一并出土的几篇《易》传作品的内容、形制来看,绝非汉初所作,至迟亦在战国结束以前。[24]157若以上推论无大谬,则《尚书》之名,非待汉而起。那会早到什么时候呢?当然不会早到孔子,否则即使他家不采,《论语》《孟子》以至战国末年之《荀子》等儒门著述,绝不会无见《尚书》之称。
其实,首度命名“《尚书》”,与此名被社会广泛接受,二者似为不同层次。虽然《要》篇赫然见《尚书》之名,但是西汉初年所撰《新语》《新书》《淮南子》等著述,仍称“《书》”。到了《史记》,屡称“《尚书》”,如《晁错传》“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13]305,《太史公自序》中又称其父谈到“《尚书》”[13]359。然不得不怀疑,在《尚书》称谓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把后来观念代入先前语境了,如《三代世表》他提到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13]54,但显然孔子时尚未有《尚书》之名。《史记》之行文已然透露,司马迁时《尚书》之称日用已久,几乎莫知其源了。社会上遂兴一类以《尚书》自孔子编定成书即用此名的模糊印象,郑玄及所据纬书的论述或滋养于此种氛围。而《尚书》之名逐渐风行,似要到武帝一朝。就学界、上层社会来说,当时名儒董仲舒著书已称“《尚书》”[25]349与“《尚书大传》”[25]361,《汉书》录昭帝始元五年诏书明举“《尚书》”[1]104。就更为广泛的基层社会而言,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通俗字书教本《急就篇》罗列:“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其后,《汉志》据《七略》,正式以“尚书”二字纲领《六艺略·书类》,首列: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1]867
紧接着“《经》二十九卷” “《传》四十一篇”直到“欧阳《说义》二篇”[1]868皆蒙前“尚书”文省。至此,似有必要重新审视“百篇《尚书》”“孔壁《尚书》”“古文《尚书》”等提法是否符合实情。不论是《书序》,还是见知孔壁的《书》篇,似乎都未体现“《尚书》”之名。何况,孔壁所出应该是战国以前的书籍,当时哪来的《尚书》之名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何以《尚书》之称自武帝以来鸣腾于世呢?终极解释应该是“约定俗成”,其中,客观存在的位势是否可为“善名”(《荀子·正名》)傅翼呢?比如,西汉初、中叶传授《尚书》的老师宿儒教学、著述时如何称用,官学所定正名为何。众所周知武帝时《尚书》博士唯有欧阳高,可谓当时对此经最有发言权之人。如此看来,刘歆《七略》提出“欧阳氏先君名之”的背景,会不会来自欧阳家后代的追述?即“尚书”此名闻自“家先君”?至于“家先君”自创还是述自师传,后人可能未必清楚。沿此理推溯,欧阳容得伏生亲炙,他关于《尚书》的认知应该大部分来自老师。《大传》乃伏生授课、弟子笔记汇总,南宋以后渐亡。今可见辑文皆称“《书》曰”,未见称“《尚书》”(12)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百部丛书集成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年。)与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辑录《白虎通》卷六《巡狩·总论巡狩之礼》所引“《尚书大传》”时,皆将文末“《尚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归入《大传》中,二家做法似可商榷。考全文曰:“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叶时月,皆为民也。《尚书》曰:‘遂觐东后,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尚书大传》曰:‘见诸侯,问百年,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改衣服制度为畔,畔者君讨;有功者赏之。’《尚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大传》紧接着《书·尧典》文,以训说天子巡守、觐见诸侯的具体事宜,而“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乃群后朝天子时考验、显扬功绩之事。不知伏生如何解说此二句,然考《大传》佚文引《书》体例,多见“故(《书》曰)”,或下连“(《书》曰:……)此之谓也”等承接语,此处无见。又相对于《大传》它条辑佚文从不见称 “《尚书》”,《白虎通》却往往见称,是以窃以为末二句《尚书》似非《大传》所引,乃是《白虎通》作者所加,以申说巡狩考绩的经典依据。。当然,辑文并非全文,固不足以断定《大传》无称“《尚书》”。然而,上文提到,为《大传》作《注》的郑玄提出“孔子说”,可见《大传》应该没有提到伏生称己名“《尚书》”之事,又阅览《大传》、欧阳《章句》等传说的刘歆提出“欧阳家先君说”,可见完本《大传》的确很有可能仅称“《书》”,无“《尚书》”用语。笔者不敢断言伏生无用《尚书》之称,即使不用,也不代表他对此称毫不知晓,只能根据《七略》等说法推测:欧阳家对于此称之推广或助力不小。
综上,《尚书》之名起自战国结束以前。传统孔子、伏生、欧阳氏先君三说,虽未必然,不过古人之所以如此理解,皆因认定上述人选有资格、亦有足够影响力命名乃至推广。不过就事实来看,《尚书》之名直至汉初似仍未流行。自武帝一朝始,此名逐渐为上层以至于中下层社会所接纳,“约定俗成”之外,可能亦受到学官“正名”的影响。据《七略》等线索,虽不敢断言《尚书》之名起于何人,但亦可见出汉初、汉中叶欧阳家《尚书》传人对《尚书》名称的推广或有助力。
四、结语
随着古、今前贤学者探究的深入与出土材料的不断验证,《尚书》早已褪去了它“河出图,洛出书”(13)《汉书·艺文志》在介绍《尚书》来源的时候,用到《易·系辞》的话“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古老神秘面纱。与其他经典比如《诗经》为“诗”类文献的集成之作相仿,《尚书》是“书”类文献的汇编本。从纵向的时间来看,它晚于“书”作为文类与 “夏书”“商书”“周书”称谓的出现时间;从横向的共通性来看,“尚书”这一名称的“书”字,不间断地继承了“书”从西周以来一直作为政治公文档案的性质。而“尚”字加诸《书》上,战国末叶应已出现,同时汉初、汉代中叶欧阳家《尚书》传人对这一名称的推广应有所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