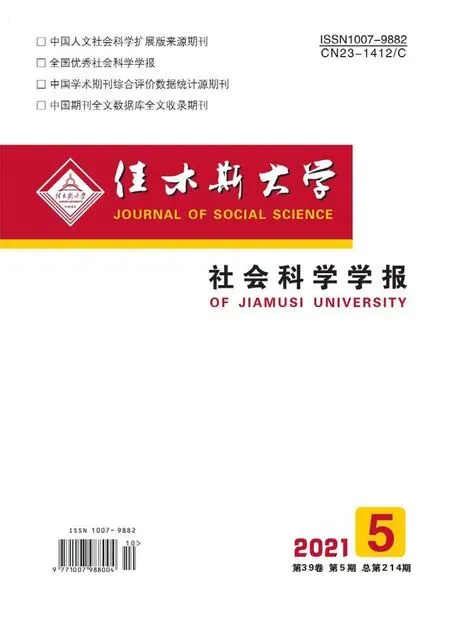宋徽宗个人因素对宋末政局的影响 *
邵京涛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遵循其必然规律,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偶然因素,“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解读中,历史人物的心理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故本文试图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对宋徽宗的性格形成过程作初步探析,进而揭示宋徽宗个人因素对北宋末年的政治局势所产生的影响。
一、宋徽宗的性格形成
宋徽宗自幼长在宫中,据他自己回忆:“及哲宗即位,群臣多言废立,太后云:‘章疏已焚之。’所须衣物,或哲宗自买。朕时尚幼,哲宗最友爱,时召至阁中饮食,皆陶器而已。”[2]卷520而宋徽宗尚在蹒跚学步时,他的父亲宋神宗就因病去世了,因此,他对自己的父亲应该没有太多记忆。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神宗的灵柩被送出皇宫,葬于永裕陵。徽宗的生母钦慈皇后陈氏,坚持留在太庙为神宗守灵,她终日沉浸在对神宗的追忆中,身形日渐消瘦,终因悲伤过度,忧思成疾,不幸离世,而彼时的宋徽宗不过才年仅四岁。由此可知,徽宗的父母在其成长过程中,并未能对其性格形成产生较大的影响。
考察《宋史》及其他相关史料,宋徽宗赵佶的性格形成与两个人的教育和影响密切相关,其中一位是他少年时期的老师傅楫,另一位则是其姑父驸马都尉王诜。《宋史·傅楫传》云:“傅楫字元通,兴化军仙游人。少自刻厉,从孙觉、陈襄学。第进士,调扬州司户参军,摄天长令,发擿隐伏,奸猾屏迹。……徽宗以端王就资善堂学,择师傅为说书,升楫记室参军,进侍讲、翊善。中人莅事于府者,多与宫僚狎,楫独漠然不可亲,一府严惮之。”[3]11021-11022说明傅楫是个为官正直、洁修勤勉、不徇私情、不俯权门之人。宋徽宗即帝位之后,升傅楫为司封员外郎,历任监察御史、国子司业、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其时适值曾布当国,曾布“自以于楫有汲引恩”[3]11022,便欲将其收为己用,但是却没想到“楫略无所倾下,凡命令有不当,用人有未厌,悉极论之,虽屡却不为夺,布大失望。”[3]11022后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傅楫以龙图阁待制知博州,最终卒于任上,宋徽宗“念其藩邸旧臣,赐绢三百匹”[3]11022,以示恩宠。
傅楫在作为皇子侍读的几年里,上疏主张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改革,他认为皇室教育应该更多地关注礼仪与德才,请求朝廷将授课内容限定在《论语》《孟子》以及《孝经》等范围内,不再过多地去关注诗书创作[4]。宋代的理学家都格外注重个人品格的培养,而且试图提供一种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即中庸之道。程伊川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5]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中和常行之德也”。中庸的内涵,即执两用中,刚柔并济[6]。宋徽宗的老师傅楫亦常以中庸之道来对其进行教化和引导,据《宋史·傅楫传》记载:“帝以旧学故,多所延访,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静自然为言。他日,李清臣劝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尝道此。’”[3]11022现代心理学认为,个性心理包括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两个方面。而一个人性格品质的形成,除了由社会环境因素决定之外,其先天的倾向情绪性、活动性、反应性均在胚质之中有其根源。其实,徽宗早年并不是一个纨绔子弟,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以及后期所具备的艺术造诣上体现出来。正如《宣和遗事》所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7]徽宗自幼便逸群绝伦,举止不凡,“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①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8]5-6。当时的皇室贵戚、纨绔子弟整日无所用心,多以声色犬马为乐,过着腐朽的寄生生活。惟有徽宗每日陶醉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自得其乐。因此,在其十六七岁时,便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
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丰富的人生经历所塑造而成,宋徽宗的性格亦并非在登上皇位后就保持一成不变。钱穆先生强调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研究历史:“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9]3-4历史人物身处其中,自然也要顺应时代发展之规律。运用历史心理学的方法去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时,应该明白:随着周遭环境的变化,人物的心理也会随之产生变化,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也会因时而变。宋徽宗生活在权力斗争如此激烈的皇宫之中,遇事必然也会变得敏感。既然想要暂时远离政治权力斗争,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沾染上一些书生习气,“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而迨到宋徽宗成年以后,他的姑父王诜就开始扮演起其人生导师的角色。据蔡絛《铁围山丛谈》记载:“(徽宗)初与王晋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画本崔白,书学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8]6因为自小没有父母的陪伴与教导,宋徽宗的行为逐渐变得轻佻放浪,后来又与驸马都尉王诜相从甚密,二人臭味相投,徽宗受到王诜的影响,是故其行为也逐渐变得轻佻放浪。“自来书生习气,议论多而成功少。北宋之徽宗,工诗善画,兼有文学家、美术家之长,天然不适宜于政治生活。”[10]73而这一点,在徽宗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酷似其姑父驸马都尉王诜,个性喜好亦与其如出一辙。王诜出身官宦人家,会迎娶宋英宗赵曙之女蜀国公主为妻,官至驸马都尉及定州观察使、利州防御使。蜀国公主,即魏国大长公主,宋神宗赵顼的妹妹,嘉佑八年(1063年)被封为宝安公主,之后“神宗立,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下嫁左卫将军王诜”[3]8779。王诜虽身为皇亲国戚,但是却颇为喜好交友,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均为挚交好友。不过,王诜迷恋于声色犬马,贪图物质享乐,其日常生活极尽奢华之能事,苏辙的《王诜都尉宝绘堂词》对此就曾描绘道:“侯家玉食绣罗裳,弹丝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觞,白日一醉万事忘。……朱门甲第临康庄,生长介胄羞膏粱。四方宾客坐华堂,何用为乐非笙簧。锦囊犀轴堆象床,竿叉连幅翻云光。手披横素风飞扬,长林巨石插雕梁。清江白浪吹粉墙,异花没骨朝露香。”[11]卷7此外,王诜在日常生活中行事也十分地放浪不羁。他虽然已经迎娶了蜀国公主,但是却依然不知道满足,仍不时地出入烟花之地,到处寻花问柳。《宋史·魏国大长公主传》记载:“主性不妒忌,王诜以是自恣,尝贬官。”[3]8779由于公主性不善妒,驸马王诜便越发地放纵自己,“不矜细行,至与妾奸主旁,妾数抵戾主。薨后,乳母诉之,帝命穷治,杖八妾以配兵。既葬,谪诜均州”[3]8779-8780。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宋徽宗赵佶于烟花柳巷之中,经王诜言传身教,自然耳濡目染,难免也变得轻佻放浪,以致“声色狗马,昼夜荒淫,国计民生,罔存念虑”[12]156。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因病去世,徽宗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由于哲宗没有子嗣,时任宰相的章惇主张依照礼法,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赵似,或者立申王赵佖,而向太后则主张立端王赵佶。最终,向太后在曾布、蔡卞等人的支持下,将端王赵佶推上帝位。宋徽宗即位以后,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但是向太后只听政七个月便去世了,继而,宋徽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据《宋史·曾布传》记载,“时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国,邪正杂用”[3]13716,以示其“本中和而立政”[3]10986,这一举动亦符合宋徽宗性格特征里面的中庸倾向。因其自身放浪不羁的文人气质,和为宋代祖宗礼法所约束限制的皇帝身份相互矛盾,这就使得徽宗很难安心做一个中规中矩的守成之君。逮到徽宗亲政以后,格外注重对皇权的掌控,多为乾纲独断,而实无兼听之明。北宋蔡絛所撰的《铁围山丛谈》就曾提及徽宗独揽权纲之举,“及政和三四年,繇上自揽权纲,政归九重,而后皆以御笔从事”[8]109。一个人的动机、认知以及情感等心理因素都是非理性的[13]8,宋徽宗虽贵为帝王,但是他仍然有其自身弱点和个人好恶。
二、宋徽宗个人因素对宋末政局之影响
迨至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宋廷派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与童贯出使辽国。而当童贯一行人踏上归途,行至卢沟河附近时,燕人马植“夜见其侍史,自言有灭燕之策,因得谒。童贯与语,大奇之”[3]13734,遂约马植俱归,易其姓名为李良嗣。其后,马植得以觐见宋徽宗,说与女真夹攻辽朝之利,并进献攻取燕云之策。《宋史·赵良嗣》记载:“荐诸朝,即献策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3]13734此计深得徽宗嘉赏,正中其怀,满足了宋徽宗好大喜功之心理,史载:“帝嘉纳之,赐姓赵氏,以为秘书丞。图燕之议自此始。”[3]13734决策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往往不是绝对理性的,而是会产生系列的认知偏差,亦即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这些错误知觉进一步影响决策者的判断,从而产生错误的决策和行为”[13]8。
燕云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所,亦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据《大金国志校证》记载:“燕云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关;昌平之西乃居庸关;顺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东北乃松亭关;平州之东乃榆关;榆关之东乃金人之来路也。凡此数关,乃天造地设以分番汉之限,一夫守之,可以当百。”[14]30政和七年(1117年),蓟州人高药师见辽国生乱,“自海道奔登州,言女真攻辽,夺其地大半。”[15]3登州守臣王师中具奏其事后,宋徽宗又再一次产生了收复燕云故地的想法。于是,“诏武义大夫马政与其子承节郎扩,及平海军指挥使呼延庆”[14]4随同高药师以买马为名,自登州(今山东蓬莱)乘船浮海出使金国,与其相约共同夹击辽朝。迨至宣和二年(1120年),北宋与金朝最终订立了“海上之盟”。宋徽宗欲借此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以成就前人未竟之事业,从而达到其名垂青史之目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他才做出收复幽云失地的决定。宋徽宗之所以会产生“错误知觉”,主要是由于外在的环境和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决策者对外在环境信息掌握得不够充分,以及决策者自身的认知能力、情感状态、动机、人格等内在心理因素都会导致错误知觉的产生[13]11。然而,“宋之兵力,远不逮汉唐,北敝于辽,西困于夏,国势为之消耗焉”[16]。从当时宋朝自身的军事实力来看,其实尚并不具备收复燕云失地的能力,如果硬要勉强为之,最终只会使宋朝陷入到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之境地。
《宣和遗事》记载:“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7]宋徽宗的日常生活过于追求奢靡,在位期间重用蔡京、蔡攸、童贯、朱勔、高俅、王黼等奸佞之徒把持朝政,专权误国,致使宋朝的统治日趋腐败。“蔡京既相,怀奸植党”[10]70。“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3]13723,“纷更法制,贬斥群贤。增修财利之政”[10]70,其后更“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10]70,荧惑宋徽宗追求侈靡的帝王生活,并曲意引用《周易》“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兼必豫”之句,“倡为丰、享、豫、大之说”[3]13724。崇宁元年(1102年)三月,宋徽宗命宦者童贯置造作局于苏杭,负责供应宫廷御用器具的制造。此外,宋徽宗还异常垂意于花石,于是蔡京便命朱勔到处搜罗花石造作供奉之物,号称“花石纲”,随后再用船只从水路运送至汴梁(今河南开封),以便于营造延福宫和艮岳。至崇宁四年(1105年)十一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事。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搜岩剔薮,幽隐不置。民间有一花一木之妙,辄令上供。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10]70正如王桐龄先生所论:“其党童贯、朱勔等,逢迎帝旨,大兴土木,东南之民不堪骚扰。于是方腊之乱与宋江之乱相继而起,竭全国之力,仅得荡平。而对辽问题复起,金人乘之,大举南寇。至钦宗靖康元年,始下诏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贬蔡京,诛蔡攸,而事已无及矣。”[17]故也难怪元朝史官在编撰《宋史·徽宗本纪》时,特言以宋徽宗为戒:“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3]418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前锋抵达黄河岸边,此时已经成为太上皇的宋徽宗急切地想要逃离京师。“宋钦宗便遵从太上皇谕旨,以蔡攸为恭谢行宫使,宇文粹中副之”[18],选定正月初四为徽宗东幸之日。但是,局势发展之快出乎意料,金军正月初三便开始抢渡黄河,于是宋徽宗当天晚上便出通津门仓惶南逃,一直逃至镇江方才停下。然而,到达镇江不久后,宋徽宗又重新过起了奢靡享乐的帝王生活,俨然忘记金军寇边的威胁,“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19]185宋徽宗一行人到镇江以后横征暴敛,挥霍无度,“官兵日给六千余缗,而小民献议者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矣”[19]185,“财物所须,悉科于民,民力重困”[10]70。镇江的地方官员为了能够加官进爵,便大肆搜罗东南珍奇,进献方物给宋徽宗,致使民间怨声载道,“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19]185。宋徽宗在镇江行宫权纲独揽,与汴京朝廷进行分庭抗礼,俨然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嗜利苟得者干请行宫,其沸如市,不复知有朝廷矣”[19]185,对宋朝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与之相对,徽宗出逃后留下的开封残局,便只能由钦宗一人来收拾。《宋史·李纲传》称赞钦宗的“恭俭之德”,谓之:“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以守宗社可也。”[3]11241太子赵桓的“恭俭之德”与宋徽宗穷奢极欲的生活作风完全相反,因而不为徽宗所喜爱。其实,早在宋徽宗禅位之前,宋廷之中就已经开始围绕着皇位继承权,展开了一连串激烈的政治权力更替斗争。面对金人南侵的严峻形势,宋徽宗空作夙夜忧叹之态,却无应对之良策,最后迫于形势,逼不得已才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宋徽宗治国才能的欠缺。
一言以蔽之,宋徽宗赵佶的个人因素对北宋末年政治局势的发展演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20]3414北宋末年衰乱的直接原因,即“徽宗一代之弊政,引起内乱,遂以引起外患者是也”[10]70。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21]397。
[注 释]
①徽宗葬于永祐陵,是故宋人常以“祐陵”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