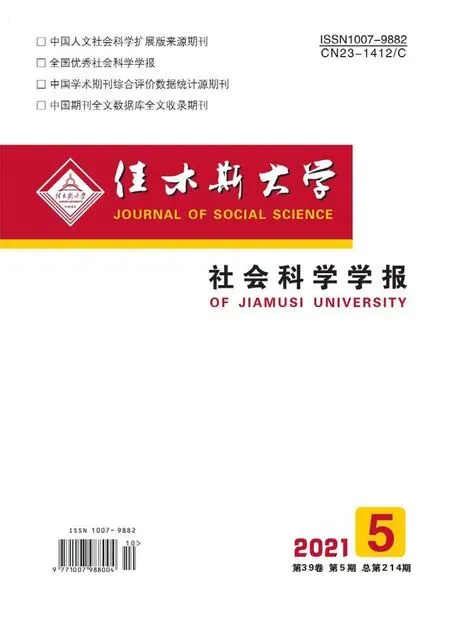朦胧夜色中的人性追寻 *——《夜色温柔》的伦理启示
周天楠
(东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一、序言
《夜色温柔》的故事背景设置在美国和欧洲,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展现了美国绚丽浮夸的“爵士乐时代”的社会生活场景。小说主要情节描写了一对貌似天作之合的美国夫妇——精神科医生迪克与富有却身患精神分裂的妻子妮科尔,以及女影星罗斯玛丽之间的古老的三角恋主题。在这场婚姻中,健康的主人公迪克从最初的积极乐观、富于魅力却逐步沦落为精神萎靡、长醉不醒的废人,最终陷入被康复的妻子抛弃的境地。这一悲剧主题说明了当代物欲膨胀的异化世界对人精神的摧残与人际关系的虚伪、脆弱。当然,文学经典的伦理诉求向来都是多声部的,小说围绕着这一主题预设了致命的伦理结且衍生出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伦理冲突与伦理选择,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为现代社会追求及时享乐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提供了道德指引。
很多评论家认为《夜色温柔》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续篇,而主人公迪克是盖茨比的翻版。但实际上,两部著作相隔九年,对于相似的题材,菲茨杰拉德所采用的透视角度是全然不同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揭示了美国梦的浪漫与虚妄,与之相较,《夜色温柔》情节则更加凄婉动人,人物形象也更贴近生活,对内“深入探析了迪克·戴弗的精神隐忧”,对外“诊察了社会和文化的广泛病态。”[1]70玛乔里·K·罗林斯高度赞誉《夜色温柔》:“以超俗、深邃的眼光,形象地再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图景,具有永恒的、超越时空的人生意义。”[1]26亨利·丹·派珀亦明确指出:“与许多正统历史学家的真实陈述相比,他的小说使我们更接近于那个世界。”[2]1
二、异化的代际伦理
“代际伦理”是指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代际关系中父母对子女除了履行抚养的责任和义务外,还要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起到正向的引导作用,教给他们伦理原则以及做人的道理。但倘若父母出于某些原因没能称职地履行对子女的伦理教育便会使孩子的成长出问题。反过来,子女对父母不仅应孝其身,更要孝其心,对于父母来说,没有什么比继承祖辈的教导成为立足于社会的“伦理人”更好的报答了。所谓一叶知秋,家庭的代际伦理与整个社会的风尚息息相关。菲茨杰拉德在《夜色温柔》中书写了各种代际关系的生活情态为我们呈现了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画卷和历史变迁,刻画了美国日渐恶化的代际伦理的窘境与混乱的社会道德状况。
“在人类文明之初,维系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禁忌是古老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3]15伦理禁忌是悲剧的基本主题,是主人公不幸与痛苦的根源。《夜色温柔》预设的致命伦理结即妮科尔与父亲沃伦打破了乱伦禁忌,致使妮科尔精神错乱。美丽迷人的妮科尔出身上流社会,家境富庶,惜少年丧母,父亲在照看女儿时却与之发展成有悖伦常的恋人关系,“我们就像是恋人一样——后来我们突然就真的成了恋人——事情发生后我真想一枪毙了自己”[4]155,沃伦在精神病医生多娒勒一再追问下坦白道,异化的亲子关系毁掉了女儿原本幸福的人生。然而,悲剧发生后,沃伦却似乎更关心事情会不会传到美国去,会不会影响他的家族声誉与社会地位。因此在留下一大笔钱后,“绅士”沃伦就把妮科尔丢在了精神病院。出于对乱伦后果产生的道德恐惧,他逃到瑞士寻求安宁,不顾对孩子的伦理责任和义务,直至临终也不肯见女儿。而对于尚无判断能力的妮科尔,父亲的冷漠加之对自我本性的憎恶等同于双重抛弃,致其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妮科尔的悲剧意义在于教诲,警示人们乱伦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让人们必须遵守这一伦理禁忌。
同样缺乏父爱的还有第二女主罗斯玛丽,父亲去世后母亲是她最好的朋友,在生活与事业上一直引导着她。但父爱的缺失,使她缺乏与男性的正常人际交往,也会导致她自身的性格缺陷。她的母亲强悍精明,随着罗斯玛丽在电影界一举成名,埃尔西太太的“投资”热情被迅速点燃,她在经营女儿的同时功利地为其精心策划社会关系网,择选“金字塔”交往对象。在商品社会,“社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交易,每个人都急于会见高价的商品人,与之接触从而获利或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5]38-45初遇迪克夫妇,埃尔西太太便看出他们非富即贵,当女儿因爱上迪克这个有妇之夫而痛苦地哭泣时,她怂恿道:“去吧,不管发生什么,权当增长见识。要么伤害你自己,要么伤害他——但不论怎样都毁不了你的。”[4]46显然,这位母亲并没有对女儿有正确的教育与引导,没有教会她自尊与自爱。“教育的目的是抑制子女恶的自然天性,塑造其精神天性,使子女成为有伦理道德的人。以子女的喜好为依据,是有违人性教育的,其结果是唐突孟浪,傲慢无礼。”[6]371
小说中迪克的母亲早逝,而父亲从头至尾并未出场,直至逝世。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迪克陷入回忆:父亲是位善良的牧师,“祖籍美国古老的弗吉尼亚州,去世后被安放在教堂的墓地,与一百个姓戴弗的、姓多尔西的以及姓亨特的人埋在一起”[4]243,这些似乎暗示着父亲的美德传承自古老的祖辈——那些具有诚实勤恳、宏伟气魄与豪爽精神的老一辈的开拓者。他教导迪克懂得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良知、尊严、礼貌和勇气”[4]242,使迪克从小立下志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勇敢又睿智的人,但这都太难了。他还想被人爱,假如他能做到的话。”[4]160论语有云:“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可见,真正的孝道是不改父母的教导。然而,与我国“父慈子孝”的双向父子伦理模式不同,西方社会“孝亲”的概念原本较淡漠,再加上经历战争的迫害与社会突变,就更不要提继承父辈遗志了。因此,迪克父亲的突然离世象征着传统伦理道德的消亡。迪克在墓园驻足,感到:“在这儿已了无牵挂,相信自己也不会回来了。‘再见了,父亲!再见了,我所有的先辈。’”[4]243这一场景标志着他与传统教化的最终割裂,也预兆了他此后因投身物欲,放纵沉沦而终将招致噩运。他的毁灭,也是因为他渴望被人爱,受人敬仰——成为名人——这种名利的渴望战胜了父亲所强调的诚实、谦恭、勇敢等美德。透过纷繁的、物欲横流的世界,菲茨杰拉德敏锐地透视了消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以及金钱意识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三、奢靡的消费伦理
消费伦理主要研究消费活动中的道德观念、道德关系、道德规范等问题。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罪恶,这些罪恶都是文明制度的产物”[6]476,其特征之一就是消费、享乐的社会风气,这种新的消费伦理不再劝诫人们克勤克俭以便老来享受,而是以各种方式宣传鼓励人们无节制的物质享乐和消遣。战争所带来的身体与精神创伤和随之而来的肆意挥霍的消费观,使很多美国青年在人生的迷途中得过且过、悲观失望。对金钱与财富的追逐造成了人际间的利益冲突,也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与社会的混乱。
迪克·戴弗曾有过人生的辉煌时期,医学博士,获得过奖学金,也曾著书立说钻研学术,更重要的是他外表英俊、性格迷人,被人们称为“辛运的迪克”。他的崇高理想是“当一名自古以来最优秀的精神病医生”[4]158。然而讽刺的是,当遇到精神分裂的妮科尔后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规划,虽有违职业伦理道德,他还是爱上了他的患者,这与有钱有势的沃伦一家正打算为妮科尔“买个医生照看她的计划”[4]186不谋而合,于是戴弗医生娶了个精神病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灰烬谷的巨幅广告招牌——埃克尔堡医生的眼睛虽透视了美国社会的病态却无能无力——因为他是眼科医生。)他们的结合象征着精神病专家迪克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对“爵士乐”时代出现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变态的治疗:“在巴黎,他整夜都把她楼在怀里,而她服了苯巴比妥后仍然睡不沉;凌晨,不等她开始精神错乱,他就用温存呵护话语安抚她,于是她又进入梦乡。不等她醒来,他就在隔壁房间通过电话安排好了一切。”[4]198
对于沃伦家那个“婚姻买卖计划”,他嗤之以鼻,筑起工作的堡垒捍卫自己的家庭与尊严:“他单独外出只坐三等舱,喝最便宜的酒,衣物稍有点奢侈都要责罚自己。这样,他保持了一定的经济独立。”[4]202可当弗朗兹医生找他投资二十二万美元合办诊所时,沃伦家立即毫不犹豫地出资赞助,暗地里却鄙夷:“你是我们的了,你迟早得承认,装什么独立性,可笑。”[4]211至于去不去工作他们倒并不在意。“为了拥有他,让他永远不思进取,扮演他现在的角色,妮科尔对他的懈怠总是予以鼓励。她不断地给他买礼物,给他钱,让他淹没在她所提供的物质享受之中。”[4]203小说中对于妮科尔花钱如流水有大量详尽的描述,通常采用列明细的方式:
“她买了彩色念珠、沙滩上用的软垫、人造花、给洋娃娃配的袖珍家具,还有对虾色的一块新品种布料,此外还有十二套游衣,一个橡皮短吻鳄,一副金子和象牙镶嵌的旅行象棋,送给阿贝的几块亚麻手绢……”[4]63
她买的东西有需要的,但大部分是用不上的或送人的。菲茨杰拉德随后揶揄道:“妮科尔是大量创造力和辛劳的产物。为了她,一列列火车从芝加哥开始它们的行程……美国的整个体制,随着它轰轰烈烈地向前推进,为像她这样的大批购物者提供了一个红火的局面。”[4]64妮科尔的财富如此之多,使得迪克的工作变得好像实在没什么干头,“他在大房间里待着,听着电钟发出的嘀搭声,听着时间的流逝……”[4]203毕竟,“‘劳动光荣’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新的工作伦理是‘自由职业者最幸福’。”[7]
为了打发时间,他们甚至在法国买下部分山村,成为里维埃拉海滩的主人。于是,把海滩打造得极尽奢华,吸引客人来拜访刷存在感成了他们生活的主题。他们与一群才华横溢却又放浪形骸的客人们一起纵情享乐、逃避现实。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即迪克为他的享乐付出了意料不到的代价:他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与做人的起码准则,开始感到沮丧,陷入精神空虚的绝境。他发现遁入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显然行不通,于是他又选择了遁入酒精,“陶醉的酒一下肚,精神就会放松。”[4]207他新交的朋友大多酗酒,尤其是阿贝·诺斯,经常喝的不省人事,后来阿贝在纽约一家非法酒店给人打死了。迪克伤心欲绝,他喝更多的酒,为了阿贝的死,也为逝去的十年青春,他“不知怎的就像个职业舞男一般为沃伦家卖命,让自己的能量全部锁进了沃伦家的地窖里。”[4]239阿贝的死象征着迪克精神的死亡,与盖茨比的肉体死亡相比,这种精神上的死亡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造成主人公信念丧失的,正是这恶浊的浮华世界与上流社会的险恶用心,他们相信,在消费社会,人人都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在这样的人事环境中,鲜有人能坚守住勤劳、正直,独立自主之类美德。当然,“人们自身对金钱的贪婪与对上流社会奢靡生活的向往也会使人变得媚俗,丧失做人的尊严,最终只会落得无尽的痛苦与悔恨。”[8]134
四、堕落的两性伦理
与我国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理念相同,基督教宣扬的两性伦理道德的核心就是禁欲主义,然而在中世纪晚期,这种“道德伪善、压制个性、反对自由”的思想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抗议与批判。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反传统的知识青年们感受到了现代意识的冲击,他们认定,古老的清教主义是旧文化的根源,是时代进步的绊脚石”[9]57,甚至“任何阻止自我表现或妨碍充分享受的传统、法律或规则都应该被打破并废止。”[10]55因此,一切道德标准都松弛了,作为这个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性欲的闸门被打开,“几个世纪及清教传统标志的羞涩、廉耻或犯罪感对它不再具有影响力”[11]160,那是充斥着性、酒精、毒品和变态的美国,一切都笼罩在爵士乐强烈的光雾里。
小说中最变态的无外乎沃伦与十五岁的女儿妮科尔罪证确凿的乱伦罪,然而出于对这一事件的深刻印象总会引发人们对此类关系的怀疑,即中年男子与未成年女孩的关系,类似案例随处可见,几乎构成了“乱伦主题”。如小说中反复提及的使罗斯玛丽一举成名的著名影片《老爸的女儿》,迪克的观后感是:影片结尾处罗斯玛丽与父亲团聚的镜头表现得恋父情结太过明显。由此可见影片的风靡代表着社会上人们普遍不道德的心理状态。迪克虽对此有所警觉,但却依然陷入这种不伦之恋。如迪克与妮科尔初次相见时,彼时迪克28岁,妮科尔16岁,“她的青春和美丽深深打动了迪克。她粲然一笑,那是一种动人的、孩子般的微笑,不由得使人想起所有逝去的青春。”[4]161
这种“恋童”心理在他与罗斯玛丽的婚外情中就表现得更明显了,迪克34,罗斯玛丽17,“她的身体发育微妙地徘徊在孩提时代的边缘——她差不多长大成人了,但身上仍有那股子稚嫩。”[4]4当罗斯玛丽跟他表白时,迪克起初慈父般地拒绝道:“晚安,孩子,这是很可耻的事,让我们把它忘掉吧。”[4]76而当他听到科利斯谈及罗斯玛丽与一个纽黑文小伙子在火车上的风流韵事后便开始时常神经反射般地产生性幻想:“我放下窗帘你介意吗?”[4]103最终,三年后,他们成功地“放下了窗帘”,结果迪克发现他并不爱罗斯玛丽,罗斯玛丽也不爱他,他和罗斯玛丽在一起只是放纵自己。他怨恨沃伦一家,也讨厌那些虚与委蛇的朋友:“我已经白白浪费了8年时间来教这些阔佬体面做人的起码知识,不过我还不算全完,我手里还有很多张王牌没有甩出去。”[4]239他对美丽的女人是见一个爱一个。当妮科尔错怪他勾引一个病人15岁的女儿时,他产生了一种内疚的感觉。当他和出租车司机打架被带到审讯室时,一群人误以为他是奸杀5岁小女孩的罪犯并向他发出嘘声,他稍后叫嚷道:“我要发表讲话,这也许是我干的——”[4]278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妮科尔还注意到迪克对孩子不大自然的兴趣。菲茨杰拉德试图用原本扮演道德良心角色的迪克·戴弗的极端堕落(鉴于伦理禁忌)象征着欧美国家人们从自尊、自律的生活转向放纵、放荡的生活。
这种道德堕落的转变也同样发生在妮科尔身上。受到重创的妮科尔一度生活在自责、自卑的情绪中,她的创伤能否被治愈有赖于能否获得新的伦理身份,使她能够忘却伤痛,重构自我。她爱上了给予她温暖的、帅气的迪克(也许掺杂着某种对父亲的“移情现象”),迪克察觉后曾试图逃避她,但在追求迪克的过程中,精神分裂的妮科尔却神奇地表现出很深的心机,她就像荷马诗句里“诡计多端的塞浦路斯女儿”“巧妙地盗走了聪明人的智慧/不论他是多么小心谨慎”。当他们在阿尔卑斯山最终定情时,这边是:“迪克真感谢上苍给了他一个存在,哪怕这只是她湿润的眼睛中的一个反映也好。”[4]185而另一边:“妮科尔是成功在握,自制而冷静,我得到了他,他是我的。”[4]185“突然,湖对面暗红色的山坡上,传来一阵轰响,人们正用大炮在轰击酝酿冰雹的云块,好把它们驱散。”[4]185大炮声击破梦幻,标志着迪克幸福的结束。
婚后,迪克对妮科尔悉心照料,他们的爱使她逐渐忘却伤痛,重构自我。但妮科尔对迪克过分的依赖却使迪克疲惫不堪:“最近妮科尔把我整垮了——我要是一天能睡上两小时,那都是奇迹。”[4]231后来,迪克的生命力似乎逐渐转移到了妮科尔身上,此种迹象从克特与丈夫弗朗兹的谈话中似乎可以得到印证,克特评论道:“妮科尔没有生病”,而是“把她的病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罢了,她应该去演电影”[4]284,而且,“迪克已经成了酒鬼,他已经不是个正经人了。”[4]286再后来,妮科尔越来越不依赖迪克了:“我几乎是个完全的人了,现在我不就脱离他独自在这儿了吗。”[4]341而迪克也似乎抱定继续沉溺的决心了:“以前他总是想着创造东西——现在似乎只想破坏。”[4]316
健康的妮科尔想要摆脱颓废的迪克获得新的伦理身份:“她并不需要永远和他在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她就必须再成为别的什么。”[4]327她想起一直暗恋她的汤米:“别的女人不也有情人吗——为什么我不能有?”[4]327“整个夏天,她看到多少人受到诱惑为所欲为并未受到惩罚,于是得到鼓舞。”[4]344终于,她和她的情人都得偿所愿。此时,宾馆外面“一声巨响撕裂了空气:啪——砰!是战舰在召唤美国船员回船”[4]351,船员们纷纷与他们的情人(妓女)告别。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女子在汤米和妮科尔所在宾馆的阳台上与情人挥别,她叫喊着扯下自己粉红色的三角内裤当旗子挥动,“这时,船尾升起了星条旗,与这面粉红色的旗帜争相媲美。”[4]351此处的讽刺与象征是不言而喻的,菲茨杰拉德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时代的不负责任和道德堕落,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其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汤米和妮科尔之流会使美国变成什么样子。妮科尔回到家来到迪克的工作室,迪克冷冷地看了看她:“我刚才在想我对你的看法——”“为什么不在你的书上添上这个新的分类呢?”“我想到了——就把它叫作精神变态和神经官能症病外谈'——”“我不是到这儿来让人讨厌的。”“那你为何要来,妮科尔?我无法为你再做什么。我正在想办法救自己。”[4]356在菲茨杰拉德看来,那些纵情声色的人们都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但对美国这个淫欲炽盛的流行病,精神科专家也束手无策。
五、结语
菲茨杰拉德对小说的结尾处理颇耐人寻味:迪克大抵是搬了几次家,“不是在这个小镇,就是在那个小镇”[4]372上挂牌当普通医生,回到了最初那种骑车的简约生活,“给人留下了风度翩翩的印象”并有“很多女性崇拜者”[4]372;学术上也有所建树,如:“发表医学课题的重要论文”或在“大众卫生保健会议上就成瘾性毒品问题作精彩的报告”[4]372,种种可喜的迹象似乎呼应了前文迪克试图自救的说法。但菲茨杰拉德笔锋忽转又可疑地写道:“后来和一个杂货店姑娘混到了一起,并且还卷入了一起医学诉讼”,于是又换了个“很小很小的小镇”[4]372。这个结局与其说是“夜色温柔”,不如说是“夜色朦胧”。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局使学者们面面相觑,不明所以,但大都认同“沉沦”这一主题:“小说以戴弗医生的迅速沉沦结束——他的沉沦并非没有原因,而是有着太多的原因,其中没有一个是主导原因。”[1]29但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主题都不是单一的,是要留给读者更广阔的阐释空间的,菲茨杰拉德这种余音绕梁的处理手法反而更加富有艺术魅力并激发着人们不断揣摩研究的热情。
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的悲剧使尼克看透了这个“鬼魅般的城市”,于是尼克最终放弃了在纽约学做证券交易的计划,决定回到中西部的家乡去,远离这个浮华的商业社会,迪克的隐退或许也是一种逃离,而逃离并不意味着就是失败,这是迪克同时也是作者在面对伦理两难时所做出的伦理选择。在那个时代普遍的道德败坏中,逃离是“在经历伦理无序之后,向原有伦理秩序的回归。”使“人性因子,即人类的理性意志,在与兽性因子的对抗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人也因此回归为真正的伦理意义上的‘人’。”[12]68-72(当然,如果不懂得反省自身的沉沦,而一味的指责外部环境的责任,那么逃离到达的终点只能是歇斯底里和迷惘的气氛。)由此可见,迪克看似悲剧式的结局在伦理意义上并不悲哀。也许,当迪克归隐前站在沙滩高高的阶梯上俯视海滩上的芸芸众生并默默在胸前手画十字祈求上帝保佑这片海滩时,便已决意去实现梭罗在《自然》中所描绘的愿景:
啊,自然!
我宁愿生活在荒野丛林,
做你的孩子,做你的学生,
也不愿去做人间的皇帝,
或不折不扣的忧患的奴隶;
我愿享有你黎明的刹那,
放弃城市中寂寞的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