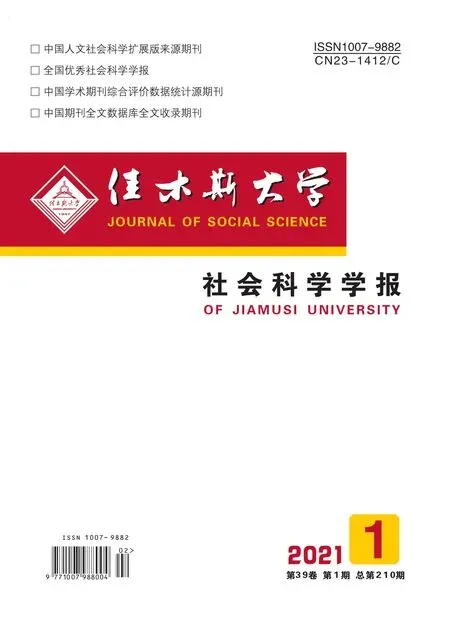隐藏的罪恶:日本细菌战罪行与七三一部队*
刘汝佳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日本细菌战档案资料分批分次地解密与公开,使得各国学者对新证据的挖掘不断深入,就笔者视野所及,学术界多侧重于受害者死亡人数、战后诉讼以及细菌战罪行本身,而对日本细菌战中有关中日双方心理层面的分析尚待明确了解、确切把握和准确判断。由于此领域的研究横跨军事史、医学史、心理学等领域,因此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对这段“大历史”中的“小历史”进行对比,剖析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等因素以外的诸多影响。曾有共同社社会部记者这样问日本一桥大学历史学者吉田裕教授:“为什么日本可以如此暧昧地对待战争责任、赔偿问题,一边不被追责,一边还能不断地发展经济呢?”吉田裕回答说:“那还不是从美苏冷战得的最大好处。美国为了抢先把日本拉进自己的阵营,说服有关国家,让有关国家放弃对日赔偿要求。”[1]
一、资料总体情况
(一)田中利幸其人
田中利幸(Toshiyuki Tanaka,たなか としゆき),生于1949年5月26日,日本历史学者,专攻战争犯罪军事史,西澳大学博士,曾为广岛市立大学广岛和平研究所教授,现为德国汉堡市的德国社会研究所的“纷争时性暴力”研究项目成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客座研究员。从2015年4月开始主要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作为历史评论家执笔参与演讲及和平运动。曾向日本以外的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日本慰安妇》(JAPAN'S COMFORT WOMEN)等,曾用过女性笔名田中由纪(Yuki Tanaka),因此,当被美国议会报告引用时,其日本女性笔名和本名引起了误解;在日本新闻报道和论文中也曾错以田中由纪作为作者名被介绍过[2-4]。另外,在日豪出版的著作中,也曾用过笔名[5]难波哲和赤坂正美。
(二)资料内容概述
日本历史学者田中利幸以笔名田中由纪(Yuki Tanaka)撰写的英文著作《隐藏的恐惧》(Hidden Horrors),1996年由美国西方视角出版社(Westview Press)出版发行[6],其中在第五章侧重研究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及其相关细菌实验及细菌战计划。该出版物进一步印证了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是在日本最高层的授意与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活体人体实验及细菌实验。毋庸置疑,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秘密细菌战部队;总部设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郊区。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开发、生产和测试。作为其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对人体和动物进行实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一些有关其活动的文件曝光时,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活动的细节才为人所知。这些文件出自美国军方组织,如盟总第二参谋部(情报部门)的助理参谋长办公室和军法署署长办公室。这些记录的实质性部分是美国占领军直接从战后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前成员手中缴获的资料,但这些信息之前从未公开过。
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Ishii Shiro),是一名京都大学毕业的著名医生,1928年前往欧洲研究有关细菌武器的情况。当石井四郎1930年春季返回日本时,他敦促军方领导人提供一种研究细菌战并发展能够实施细菌战的方法与手段。当时尽管美国还没有开始这方面研究,但其他西方国家都在积极参与细菌武器的研究。1932年石井四郎在军方的全力支持下在东京设立了军事医学院防疫实验室。同时,石井四郎在伪满洲国哈尔滨东南100公里北洼地建立了一个秘密小组——东乡部队。之所以选中偏远的伪满洲国,主要是因为研究人员想对人体进行医学实验,而这些实验在日本是很难开展的。在东乡部队建立伊始就开始使用中国囚犯进行人体实验。因此,在东京主要进行的是细菌武器的防御措施研究,而在伪满洲国进行的则是细菌武器的攻击使用和实际生产研究。
1925年日内瓦公约禁止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石井四郎显然知道自己的计划违反公约,但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细菌武器的潜在有效性。石井团队寻求所有可以研制武器的细菌和病毒,并用这些细菌与病毒研发疫苗以保护日本军队。
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前身是1936年的东乡部队,该部队改组并扩大为关东军防疫部,又称石井部队。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研究、实验、防疫给水和生产。关东军在新京(今长春)建立了支队,即防治动物疾病的若松部队(Wakamatsu Unit)。这两支部队均在日本帝国总部批准下成立。1938年在哈尔滨东南部25公里处的平房区宣布了一个特殊的军事区,而当地的居民都被驱逐。一个庞大的细菌武器生产机构开始运行。1940年8月1日,石井部队更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其真正的目的与其描述却恰恰相反),虽然该部队1941年后被通常称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设立第七三一部队后,军事医学院的教职人员被派往伪满洲国,参与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事实上,早在1936年即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成立前几年,石井四郎就从日本各大学招聘优秀青年医学专家。
由此可见,日本历史学者田中利幸从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建立以及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的经历入手,进一步证实了石井四郎是在国家支持下建立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并有预谋开展细菌实验及细菌战。尽管自1939年就限制使用细菌武器,但在1940年9月之后,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研制的细菌武器被广泛应用于战场。在浙江省,1940年9月18日至10月7日期间使用了六次细菌武器。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成员——篠塚良雄(Tamura Yoshio),战后证明他在1940年7月上旬至11月上旬期间大量生产霍乱、伤寒和副伤寒杆菌。他还报告说,1940年初约10公斤伤寒杆菌被空运到南京。约在同一时间270公斤伤寒、副伤寒、霍乱和鼠疫菌被运至南京和中国中部供日军在战场上使用。从篠塚良雄(Tamura)和其他来源的证据表明,在1940年左右日本主要用伤寒和霍乱作为细菌武器。至于影响,据报告显示,每次使用武器导致伤亡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
二战爆发后,日本人继续对中国人使用细菌武器。在1942年6、7月份,他们在浙江省的金华地区喷洒霍乱、伤寒、鼠疫和痢疾病原体。这是为了报复美国对日本大陆的第一次空袭,在这场空袭中,日本东京和名古屋遭到了轰炸。在此番空袭后,盟军飞机降落在中国机场,至此日本认为这是中国与盟国的合作。然而,在金华的病原体攻击中,日本人也成了疾病的受害者,发生了大量的日本人员伤亡,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超过1700名日本士兵死亡。
众所周知,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使用了大量的中国人进行实验。许多反抗日本侵占的中国爱国志士被捕并被特别移送至平房,他们成了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实验品(Guinea Pig);有证据表明,一些俄罗斯囚犯也是受害者。日本人称被用作实验的囚犯为“马路大”(日语音译,日语字面意思为“木头”)。每年的军事警察和国民警察围捕约600名“马路大”特别移送至平房。当他们被实验时,需要从主监狱区转移到单间,这些“马路大”感染特定病原体,这些特定病原体或用注射或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源传染。然后,“马路大”会被观察,其症状包括取血和组织样本也会被精心记录。囚犯们生病后,通常会被人体解剖,然后在特定场地被火化。
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医生也是如此。他们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然后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回到他们舒适的住处,并未对他们所作所为感到丝毫不适。“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本身”,显然在所有重大方面与“奥斯维辛本身”有异曲同工之处。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医生所从事医学研究的目的本该是挽救生命,而不是利用生命;然而,他们能够无怨无悔地生活,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良知,他们显然保持了良知,但仅仅是对实验对象以外人群的道德责任,而不是对他们的实验对象。双重身份使他们用囚犯做人体实验,以拯救日本人的生命为由来迎合高尚的道德情操,并表现出他们忠于天皇。好与坏的标准取决于“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本身”,而不是来第七三一部队之前的医生经历,因为这些医生是在头脑清醒的前提下从事所谓常规的医学工作,所以他们应当承担自己所犯下的医学伦理罪行。
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医生能够麻木自己的心理,包括称囚犯为“马路大”,以及用数字代替他们的名字称呼囚犯,这样,囚犯在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医生眼中被非人性化,利用这种心理距离,从而避免医生出现同情受害者的心理。心理学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从这一理论角度出发,中国爱国志士在面对残酷人体实验时放弃了自身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直接追求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与麻木无情的日本军医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还可以采用需求分析方法来研究行为动机,更好地解释了人际和社会交互作用后的个体行为动机。由于社会普遍认同中国爱国志士忽视自己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以及白求恩希望的只是全体中国人民都能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一样。总而言之,中国人体实验对象和白求恩在生理需求这一最基本层次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直接达到自我实现需求的最高层次。
与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医生相似,德国纳粹医生也用不寻常的方式来描述他们自己与受害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或否认德国纳粹医生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如美国学者波特教授在其著作《解密日本细菌战历史:军医中将石井四郎的故事》中提到的,“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石井四郎等医生用人体来做实验的这种滔天罪行恐怕只有德国纳粹医生门格勒博士之流才能想得到,门格勒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石井四郎居然可以完成。”[7]
三、中、美、日学者相关研究
作为第三方国家的美国学者谢尔顿·哈里斯教授,在其《死亡工厂》一书中提到:“从1931年到1932年日本占领满洲的那时刻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的‘科学者’在中国满洲整个区域范围内进行了细菌战(BW)和化学战(CW)的研究。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积极支持下,这些‘科学者’在满洲各地建立了很多秘密基地。在那里,他们不受任何当局干涉,可以用动物和人自由地进行实验。日本在它的占领期间,事实上把满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实验室。”[8]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对石井四郎和其他战犯逃脱正义审判负有直接责任,然而,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决定不是麦克阿瑟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有文件表明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美军参谋部也参与了决策,也有间接证据表明杜鲁门总统也是知道这一决定的。杜鲁门总统相信“多米诺效应”,即除非共产主义受到遏制,否则沦陷的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在决定“赦免”之时,苏联已经将人类送入太空并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冷战开始了,对于杜鲁门总统来说,美苏之间的战争很快就会打响。在这种前提背景下,石井四郎的机密情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美国为获得对苏联作战的优势而“赦免”石井四郎,与此相似的是,日军军医在苏联仅仅服刑两年后于1952年被遣返,这也就理所当然了。
作为日军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能被允许活下来,甚至从美国获得一笔救济金,其原因是美国盲目、轻率地希望能迅速“打败共产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比起将一名罪犯绳之于法要重要得多,无论这名罪犯是多么的邪恶,无论有多少无辜的人因他而被折磨致死。麦克阿瑟知道石井四郎干了什么,但是他毫不在意;莱希知道石井四郎干了什么,他也不在意;杜鲁门也知道石井四郎干了什么,他同样不在意。二战结束时,美国有了一个更大的敌人。为了战胜这个敌人可以和恶魔谈判,并让他苟延残喘,这样美国就可以学会以更有效和更快速的方式杀死苏联的共产党人。
美国学者肯尼思·波特教授认为:“日本和美国政府必须重新审理这起案件,审判已经死亡的石井四郎,这样日本人才能洗涤良知,日本才能成为和平国家。石井四郎一定要接受审判,他的所作所为才能被公之于众。”[9]
日本侵华期间,出现的“特别移送”事件绝非偶然,它是日本加紧侵略战争的步伐,为早日实现称霸亚洲的梦想,开始以活人为材料进行人体细菌实验,进而发动细菌战。“特别移送”的人员有许多来自国境军事禁区——伪满洲国国境要塞防线地区。“特别移送”行为在日本侵华细菌部队中普遍存在,被日军“特别移送”的部分被害者被冠以“苏联谍者”的罪名,大部分被害者是当时以各种方式参加过当地抗日武装斗争或其他抗日活动的,甚至有平民百姓。[10]
日本学者莇昭三教授在《十五年战争中的医学犯罪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课题》一文中写道:“为此参与过战争中的医学犯罪的医生、医学者,虽然感到那些行为是违反人道的,但既然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已不可算专家,甚至出于上级集团的归属思想而进行人体实验的那些人不能称为医生,也不能称为科学家。当时虽然还未确定《纽伦堡审判规则》,即使没有相关规则,但医学伦理的不损害人命原则应该始终是医生、医学者加以判断的第一原则。”美国麦克·法兰兹布劳(Michael J.Franzblau)教授2003年时要求日本医学界对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问题做出深刻反省,他警告说:“避而不答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问题就等于丧失体面。”莇昭三教授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我认为日本医学界此时此刻需要深刻反省,对被敷衍过去的战争时期的医学犯罪,重新自问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战后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问题被披露出来之后,日本医学者、医生还要袒护他们,这同他们把事实关在心中的自卑感也有关系。他们为什么感到自卑呢?因为他们当时已经知道石井部队在做什么,即共有公开的秘密,如果这就是他们始终沉默的理由,那么他们的沉默就是犯罪。”[11]
四、余论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档案资料,为同类学术研究中一隅之见。通过本文发现的新档案资料,分别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需求分析方法的心理学角度出发来研究行为动机,对照中国爱国志士面对麻木日本军医放弃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直接追求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更好地解释人际和社会交互作用后的个体行为动机。由于社会认同,中国爱国志士忽视自己的生理、安全需求,像白求恩希望的只是全体中国人民都能过上自主的日子。与此同时,基于对中、美、日学者的资料整理与研究,不仅较为全面地再现了日本细菌战及其侵华这段历史,并且可以客观地体现了日本侵华期间从计划到实施细菌战等战争均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主动攻击性行为,而非被动卷入其中。日本战时的人体实验对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挑战是显然的。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纽伦堡法典》不仅奠基了当代医学伦理学,至今仍对医学研究和实践的伦理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至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医生和研究人员在日军占领区,特别是在中国进行的人体活体实验,日本医生所进行的细菌实验、细菌战是以国家利益、科学与医学的名义对活人进行蓄意的伤害、杀戮与折磨。然而,由于复杂的政治与历史原因,包括美国政府的刻意包庇,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赖和当时中国政府的相对沉默等,日本医生的暴行并未为世人所知。由此,从日本战时的医学暴行在心理、医学、社会与伦理的相互联系角度出发,提出了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医学伦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