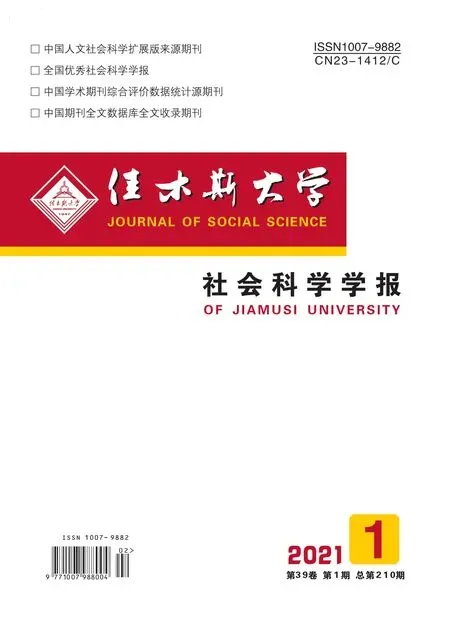我国古代防控疫情的方法、路径及其当代意义*
仇小敏,肖红旗
(1.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2.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成县 742500)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多灾多难,古代先民频繁遭受瘟疫等自然灾害的肆掠。回望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我国古人与瘟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时有发生。根据现有资料记载和不完全统计,秦汉以降我国社会流行瘟疫大大小小有近千次之多。每一次疫情的发生,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对于历代的执政者来说,都是一次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考,但也因此积累并增长了许多防控瘟疫的经验和智慧。当然我国古代人民群众防控瘟疫的方法和路径很多,在这里主要从最重要的方法与路径入手,即:构建防控疫情的专门机制、做好防控疫情的预防工作、采取防控疫情的隔离措施、探索防控疫情的治疗技术、维护防控疫情的社会秩序。今天我们正处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肆掠的关键节点,反观我国古人防控瘟疫的斗争经验与博大智慧,不仅会给我们对疫情的认知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朴素的经验与启示,有助于提高我们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化水平,还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了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
一、构建防控疫情的专门机制
《说文解字》有云:“疫,民皆疾也。”[1]早在商代甲骨文就有关于“疫”的记载。为防控各种疫情,我国早在周朝就建立了相关机构专门治理瘟疫。主管人事的“天官”中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其下设“疾医”一职,“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2]我国秦朝就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秦时严苛的律法规定,“巧者有辠(罪),定杀”,“当迁疠迁所处之;或曰当迁迁所定杀”。《云梦秦简·疠》记载:“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疠。来诣。’讯丙,辞曰:‘以三岁时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无它坐。’令医丁诊之。”[3]《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录了秦代的战“疫”制度,建立专门的“疠所”,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顾,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这可能是我国设立隔离治疗制度的开始。秦代还设有专门的军中隔离医院——“庵庐”。汉代也大都沿用。南朝设“六疾观”,北朝设“别坊”。北魏世宗永平三年颁诏:“敕太常于闲敝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4]唐朝设“病坊”,由佛教寺院负责承办。唐·释道之《续事僧法》记载:“收养病疾男女别坊,死士供承,务令周给”。又载“释智岩……后往石头城病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灌,无所不为,徽五年二月七日终于病所。”[5]宋代设“安乐坊”,后又更名“安济坊”。元朝建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护是政府许可的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有太医管理,一旦发生疫情,医护要参加治疗。元代的医疗资源分布别具特色,不在中央设医学校,而是在各地方成立医学校,为各地的医学教育提供良好的场所,久之就形成了“在朝有太医院,普天之下各道,各路及府、州、县,莫不有医官焉”的环境,使得即便是较远的地区也会有医官对其进行救治,等等,这些都是当时我国为防控瘟疫而成立的专门机构。
到了明朝政府就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疫病预警和治疗专门机制。例如,不仅设立钦天监对天灾和流行疫病的预测和记录并进行总结,还在中央和地方专门设置了监察机构对流行疫病进行预警和疫情上报,地方官员在爆发天灾、疫情时可直奏报皇帝和内阁。这是秦汉以来封建政府主动设置的、积极介入的防疫机制。同时,明朝继承以往的朝代所设医药专门机构且将其职能具体化。太医院收集民间优秀医生的药方和治疗方法,同时还收集民间的药方和治疗方法;当流行病爆发时,太医院邀请民间医生参与疫情防治,针对不同病情撰写药方以求能在最短时间内控制疫病的流行。太医院不仅是全国最高的医药管理机构,还是培育医学人才的专门学校,更是诊治疾病的最高级医院和制药厂,负责医药储存、制备等;设置从属于太医院的尚医局以应对疫病防治,尚医局直接对爆发疫病地区进行预防和治疗并进行医药典籍整理、研究工作。尚医局设立在经常爆发大规模流行疫病的地区,如江淮等地,明代最早的尚医局就在这里。为防控突发疫情,明朝还有覆盖全国的司库储备救灾物资和药物,司库与尚医局配合共同防治突发流行急性疾病。清政府还设立“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防疫检查。据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查看有无出痘诊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诊平愈,方得进港内。”[6]
从上述情况观之,我国古代建立专门的瘟疫防治机构机制,虽然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果,其效能也不一定都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却为防控各类流行性瘟疫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和基本遵循,是我国古代瘟疫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重大进步,为古代乃至今天应对防控突发疫情提供了机构保障,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制度基础。
二、做好防控疫情的预防工作
由于瘟疫具有传播速度快、难控制、死亡率高等特点,所以瘟疫一旦发生就影响到老百姓的正常社会生活、社会交往,涉及到普通群众的财产安危、生死命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局政权的存亡兴衰,其后果不堪设想。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防控疫情策略,所以必须事先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做好预防工作,做到未雨绸缪才能更早更好全力防控,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疫情的发生,也才能确保尽早得到彻底治理。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为了预防疫病在社会上和老百姓中的发生与流行,我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预防的重要性。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智慧的古人早就将“未病先防”应用于流行急性传染病的预防领域。《黄帝内经》就是现有文字记载中最早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以酒避疫”。那时的古人认为酒是粮食之精,使用粮食酿酒,既考虑到营养价值的均衡,又充分考虑到酒的杀菌效果。“酒为百药之长”是历代中医实践的结果,并将其制备成药酒,增大其药力。酒的药理作用被医学工作者发展,制备为酒精在现代医学中广泛应用。屠苏酒就是用大黄、白术、佳心、桔梗、易椒、乌头等药碎细,用袋盛,十月晦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晓取出,置酒中煎数沸,起到“一个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的预防作用。饮雄黄酒则可防治各种毒虫咬伤。《肘后备急方》中葛洪用艾叶烟熏预防瘟疫,并首次提出用雌黄、雄黄、朱砂等消毒物制成虎头杀鬼方进行空气消毒以控制环境预防瘟疫传染。
明代“以毒攻毒”的人痘接种术被中医在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中从自然界中找到并在临床应用中突破。明代儿科医生万全在他所著的《家传痘疹心法》里就详细说明了人痘接种法的使用。人痘接种法是为预防天花的,清代钦定太医院教科书《医宗金鉴》记载了多种人痘接种法,并极力推崇水痘法。清代还重视人居环境防范疫情。清代《痘科金镜赋集解》中载:“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7]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就对中国的人痘接种技术有很高的评价:“我听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是我国古代医学对世界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做好环境卫生,讲究个人卫生。古人还讲究环境与个人卫生。在周朝官府要民间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来防疫,《周礼》就有记载在端午节时期,南方一些地区就将混有黄酒的石灰水洒于角落,以抑制瘟疫。孔子提出“色恶不食臭恶不食”,“不宿食祭肉……出三日不食之矣”。出土的秦简记载,凡客入秦国城时人马车等都要火燎烟熏消毒。秦代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记载用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还注意到病从口入,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等劝告。《金匿要略》说:“六畜自死,皆疫死,不可食之”,“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含之”。还有诸如“勿食鼠残食”、不食“猪肉落水浮者”“六畜自死”等食物的习惯,很好地表现出人们对于饮食的看法,即王充《论衡》所说:“饮食不洁净,天之大恶也”。在宋朝温革著的《锁碎录》也指出,“沟渠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晋代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指出:“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食。”唐代名医孙思邈要求:“常习不唾地,勿食生菜、生米、陈臭物;食毕当漱口数过;食毕当行步踌躇。”[9]常沐浴可以使污秽和病菌远离自己,正如《淮南子》所云:“汤沐具而姐風相吊”。而它作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早在秦汉时期就己成为一种习惯,汉代更是制定“休沐”的法律将其大力推行,即《汉宫仪》所载:“五日以假洗沐,亦曰休沐”。
清代陈虬在《瘟疫霍乱答问》中还强调居住环境清洁和自身卫生是防疫的良法。也认识到了水与健康的关系。李时珍《本草纲目》就有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10]《太平御览·人事·口》:“福生有兆,祸来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蚁孔溃河,溜沉倾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11]《淮南子·修务训》 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猎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12]《文昌帝君阴骘文》中也讲到:“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因为“逆天道者,天必诛之”[13]。
古人还效法自然,从模仿动物运动而创出健身之术,认为人的身体是个整体的自然循环的生态系统,如华佗所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穀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14]。所以他模仿虎、鹿、熊、猿、鸟(鹤)五种动物的动作创作出的“五禽戏”、蛇拳等民间武术,中和阴阳,增强自身体质,提升免疫力以抵抗病毒,融合万物而生成抗体。正如气功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项运动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发展而来的,流传至今。这应该是预防瘟疫发生的最佳方法和路径,对于今天做好瘟疫各种防御工作都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三、采取防控疫情的隔离措施
隔离是控制传染源的重要措施,其原则是将传染病人或带病原体者在传染期间安排在适当的地点,使与其他入群分开,进行治疗和护理。在古代经过长时期与瘟疫作斗争的实践经验,就有医师认识到瘟疫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一项十分必要的防治措施。所以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落后,防控瘟疫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主要是控制隔离。隔离被瘟疫感染的病人或死者,控制传染源自古以来就是最好的防疫、抗疫方式。对此我国古代早有记载。
据记载,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伯牛患麻风时就被安置在一间空置的屋中。《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早就记录了秦代的战“疫”制度中就有记载说,一旦发现瘟疫情况属实,当即组织隔离治疗。公元2年青周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就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专门医院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治疗。汉代不仅有“病迁坊”隔离麻风病人而且在汉代就开始运用隔离措施防疫,如《后汉书·孝安帝纪第五》就有载道说:“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大医循行疾病……赐棺木。”[15]即官方对瘟疫患者的尸体进行隔离,有效防范疫情传播。早在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政府规定朝臣家有病人,感染三人以上者,虽然自己没病,但百日不得入宫。公元242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16]
唐朝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治疗病人,相当于现在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明代隔离措施上也较完备和科学。政府在城外开阔地建立简易的棚户安置受灾疫民、发放针对疫情的药物,有专人负责赈灾食物和生活用水安全,并经常用药物对环境消毒防蔓延;对身亡难民以死者为大,保持亡者最后尊严,在远离人烟之地挖掘“义冢”安葬且以焚烧防传染。明代《北巧风俗》提到了北元地区的百姓“化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17]。
谨探视、少接触。清政府隔离措施比明朝更严格,严格地检查外地进京人员,封锁疫区,幽禁疫者。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王孟英在《重订霍乱论》强调疫情传播阶段聚集性活动和近距离接触要避免,其认识之深刻在今天仍具指导意义。郑光祖《一斑录》指出,“历观时疫之兴,必甚于俦人罕至人家深庭内院,故养静者不及也”[18]。医学家陈耕道在《疫痧草》指出,“无宜六不宜”:“凡入疫家视病,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诊脉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切不可使病人之气,顺风吹入吾口又须闭口不言”。[19]清代著名医家熊立品在《治疫全书》中进一步提出瘟疫流行时节的“四不要”原则,即“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20]
由此可见,在疫情流行时期,隔离的方法要比服药更为有效。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使用控制隔离办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瘟疫传播扩散,防止疫情扩大。我国古代的隔离措施也能有效控制疫病传染的几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防控作用,实在是值得肯定和点赞。
四、探索防控疫情的治疗技术
我国古代由于受社会生产力状况、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加上又由于缺乏病理研究,基本上仅仅处于只是认识到其危害而无有效医药治疗方法的阶段,所以治疗瘟疫大多是巫术与医药并存。在治疗方法上是巫术与医药长期同时并存的。虽有官医和民医致力于对流行急性病病理的探索,但巫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消失,即寄希望于佩戴有“祝融、夔龙”等神明的饰品而免受疫病侵害。在早期我国个人相信疫是由鬼神作祟而产生的,如《释名》所云:“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21]有时候对于“巫”的信任程度要远高于“医”。古代有识之士则对神明大多持否定态度,《史记·扁鹊列传》中记载扁鹊“信巫不信医”的病人为不治者,从医生的视野批判巫术而倡导病人相信医生、正确用药,但是信医是主流。瘟疫病毒不会离人类而去,人类同病毒的较量,真正的武器还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永远是我们祖先生命的保护神。
东汉末年,全国各地连发瘟疫而洛阳、南阳、会稽等地疫情严重,史载十年内死于传染病的人有三分之二,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张仲景家族也深受其害,他目睹惨景,立志医学,将前人的医学知识和自己医术结合用于临床,擅长诊治“伤寒病”,并著《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创立六经辩证体系,以辩证医理论证多种传染性瘟疫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案,其中“麻杏石甘汤”成为后世治瘟疫的良方。华佗以青嫩茵陈蒿草用于临床实验,治疗流行性“黄疸病”取得良好效果。当代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出“青蒿素”治疗疟疾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佐证了我国中医的伟大。唐宋以后,由于交通的便利,人口大量频繁流动,天花发病人数尤其是婴幼儿激增,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悲剧不断。因此,医家非常重视天花的研究与治疗。
明清时期政府非常重视疫病灾害的突发和防控,对于疫病的治疗等措施的运用超过了以往朝代,所以治疫医药也比较发达,而且基本实现了程序化制度化,使我国中医在世界医学上独树一帜。李时珍受太医院邀请担任太医,在此期间,他翻阅并研究了太医院收藏的珍贵医药典籍,其中可能包括汉代《神农本草经》、唐代的《唐本草》、宋代的《本草图经》等,并受启发而著《本草纲目》。医学界的大难题——瘟疫也是他着重研究的内容,书中记载了多种治疗瘟疫的方法。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历疫情、现场勘查,收集、整理并研究大量资料之后潜心编著成《瘟疫论》,该书专门分析并总结了各种流行病的病因、病症和诊治方法且从理论上开创了我国流行病防治理论的先河,是我国瘟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专著。清代吴瑭纯中药治疗瘟疫后期病症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使用。其《温病条辨》一书是治疗温热病较有系统的一部温病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另一书《吴鞠通医案》使温病学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叶天士著《温热论》在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上,首提温病先侵肺后入心脏而显外部症状等观点,概括了瘟疫的发展和传变途径,成为认识和治理外感瘟疫病的总纲,发展了我国古代的瘟疫病理学说。
我国古代研发防控疫情的医药医术主要是中医,具有丰富的医学智慧,我们要珍惜,老祖宗传承中医药技术不能丢,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22]
五、维护防控疫情的社会秩序
由于我国古代瘟疫频发,总有一些不法之徒趁机想发国难财,给社会防控瘟疫秩序带来了严重困难甚至破坏,所以古代统治阶级已经开始运用法律武器来防治瘟疫,严厉打击各种抗疫期间的违法行为。例如,我国的法律很早就有了保护环境资源,保护环境卫生的规定。《逸周书·大聚解》载周公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3]《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24]有人认为这是禁止向街道倾倒垃圾的规定,用重刑惩治破坏环境的行为。西周时,治国的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强调“德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礼记·月令》将人与环境的关系全部纳入礼法范畴,如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并“掩胳埋胔”;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毋伐桑柘”等等。秦将这些内容编入《田律》,《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百姓犬人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25]又如“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对于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也要惩罚主管者没有禁止,与之同罪,“其穿垣出秽物者,杖六十;主司不禁,与同罪。”[4]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国古代先人认识和防控瘟疫的能力与经验虽然十分有限,既无法真正从病理上全面彻底科学认知瘟疫,也无法完全有效防控瘟疫,但却善于从实践中总结、归纳历代历史经验、教训,也发展出了一套比较简单的、实用的而且有些至今仍在使用的防治、管控和治疗的相关机制,真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明清两代对于流行病的防治措施为近现代防御瘟疫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但是不论是从维持自身的统治需求还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科学精准是我国古人防控疫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体现着我国医学医术医药的发展与繁荣,也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提高了我们中华民族防控疫情的能力与水平,而且也推动了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发展,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积累了中国经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做出了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