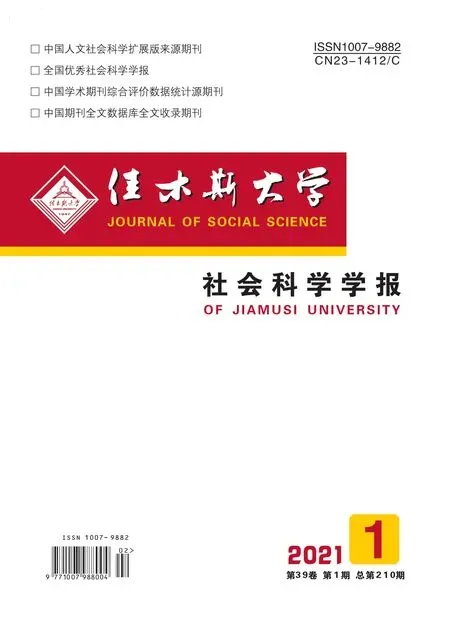女性性别意识的发展历程*
——门罗小说《男孩和女孩》的二元对立因素解析
姚匀芳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25)
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加拿大的契诃夫”。门罗的短篇小说多以安大略省为背景,具有地域性特点。她非常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以此反映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矛盾和心理挣扎。《男孩和女孩》是门罗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重要篇目之一。小说描写了叙述者“我”作为姐姐,在成长过程中以亲近父亲,排斥母亲来表达自己对“女孩”身份的反抗,但在弟弟逐渐长大后,叙述者才发现男孩和女孩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最后叙述者不得不接受自己作为“女孩”的身份和命运。
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出版之后,人们对《男孩和女孩》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叙事学的视角来看,李琳认为《男孩和女孩》中“叙述者对父母形象的描述过于片面化,而这种片面性恰好反映了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的内心渴望和困惑。”[1]16-19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童心丹认为《男孩和女孩》“从女性的视角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体现了门罗的生态意识和生态关怀。[2]43-44从空间理论的视角,陈瑶琼认为《男孩和女孩》中的性别“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表明父权语境下性别空间表征对女性成长的制约和束缚”等。[3]163-164这些研究为我们阐释《男孩和女孩》提供了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参考材料。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视角来看,小说通过三组二元对立结构,展现了男权社会下男性的地位优势以及女性的生存困境,说明女性想要通过依赖男性的方式去改变自身弱势地位是难以成功的。女性只有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重新定义女性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属性,才能摆脱被动、从属的地位。
一、空间对立与男性性别认同
《男孩和女孩》描写了叙述者在现实世界的真实空间与她描述的幻想空间的二元对立,体现了她对父亲所属空间与对母亲所属空间的情感对立。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它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如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历时与共时等成对概念为基础,从“结构成分中找出对立的、有机联系的、排列的、转换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复合结构。”[4]102著名的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就认为“只有通过找出文本中的代码或二元对立才能解释文本中隐藏的信息。”[5]97因此,通过分析小说的表层对立结构,可以探究其深层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
小说对父亲所属空间的肯定和赞美显示了叙述者对父亲男性身份的认同。剥狐狸皮的地下室、狐狸养殖场和广阔的室外都是属于父亲的空间。在叙述者眼里,父亲所属空间里的一切都蕴含着神秘和美好。父亲在地下室宰杀狐狸,在长木板上剥狐狸的皮毛,场面本应是血腥的、残忍的,但叙述者忽视了这些场面的残酷性,转而认为狐狸的气味和血的气味“如同橘子和松针的清香。”于是叙述者把现实世界里充满暴力、血腥的地下室空间描述为充满清新气味的幻想空间。现实中父亲用零头废料搭建的破旧养殖场,在叙述者看来设计精巧,井井有条,还把它比作“中世纪的小镇”。叙述者惧怕冬天的夜晚,但不惧怕室外冬天的夜晚。室外暗夜里凌冽呼啸的寒风声在叙述者看来只是“老怪物在大合唱”,并不觉得可惧,因为室外是父亲的空间,受他掌控。由此可知,现实世界里血腥、破旧、令人恐惧的真实空间,在叙述者的描述下变成了温暖、庄严、神秘的幻想空间,从而导致在同一空间里真实空间与描述地幻想空间的对立。
与对父亲所属空间的描述相比,叙述者对母亲所属空间的描述则与之相反。母亲所属的空间非常有限——除地下室以外的整个室内,包括卧室、厨房。对叙述者来说,当她从地下室到卧室,即从父亲的空间到母亲的空间以后,“这一切提醒我们璀璨的、温暖的、安全的世界似乎失去了,渐渐消沉下来。”[6]148叙述者认为母亲所属的空间是没有安全感的,因此冬天的夜晚让叙述者害怕的不是室外,而是屋里。屋里地板中间的方形洞口、竖放的军用油毡、柳条编的婴儿车、放蕨类植物的篮子、有裂缝的陶瓷罐等,叙述者认为这些东西“看起来十分悲惨”。黑暗中躺在自己的床上,就像“躺在我们狭小的救生伐上”。结霜的窗户“高大、阴森、惨淡”。与暗夜里寒风呼啸的室外相比,为叙述者提供防御的室内反而成为叙述者惧怕的对象。由此可知,叙述者对不同空间场景的描述并不在于空间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模样,而在于叙述者对该空间的主观情感倾向,反映了叙述者对父亲所属空间的认同与对母亲所属空间的排斥。
叙述者对母亲所属空间的情感态度的对立,暗示了叙述者在成长过程中对父亲身份的认同,其深层实质在于叙述者对男性身份的认同。父亲所属空间的踏实、安全、温暖与母亲所属空间的阴暗、悲惨、令人恐惧等作为叙述者笔下两个不同的世界,彰显了父亲形象中拥有的勇气、力量和作为决策者的男性气质。在男权社会背景下,父亲作为男性拥有着对一切的主导权和决策权:如果说狐狸养殖场是“中世纪小镇”,那么父亲作为养殖场的建造者,必然会是该小镇的统治者;在地下室,父亲也同样是狐狸命运的决策者;面对广阔的室外社会,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困居于家庭,父亲则是整个家庭对外界社会的权威代表。父亲的这种权威性甚至蔓延到了母亲所属的空间:父亲靠卖狐狸皮毛养活家人,皮毛交易商送给父亲英雄的挂历挂在厨房门的两边,这一意象时刻彰显着父亲在家庭里的权威性和重要性。与男性相反,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服从的地位,所以儿童更愿意从男性,即父亲身上寻找强者赋予的安全感。因此叙述者对父亲所属空间的美化和赞同,实质是受男权社会影响,对男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利和威严的认同和肯定。
二、分工对立与女性性别反叛
男权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有着明显的分工领域:男性属于社会,承担外部交际、赚钱养家等责任;女性属于家庭,承担生养子女、照顾家庭日常生活等责任。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工根深蒂固,是那个时代加拿大式家庭的典型形态。叙述者作为两性分工的参与者,她对父亲和母亲的分工表现出了对立的情感倾向。对于父亲从事的工作,叙述者是怀着主动、积极、向往的态度。比如,叙述者为能拿喷壶接水但弟弟不能拿而“颇为自豪”,因为那是父亲的喷壶,意味着父亲的重视与授权。叙述者很乐意成为父亲的帮手,所以在父亲向饲料推销员介绍她是他新雇的帮手时,叙述者为此“激动得脸都红了”。在叙述者看来,成为父亲的帮手意味着她有能力接手父亲的工作,因此她极力向父亲展示自己的工作能力,以证明自己能够成为父亲的接班人。
对于母亲的工作,叙述者则充满了厌恶、逃避和排斥的态度。叙述者了解并认同男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但她身边所有人都说她是个“女孩”,所以她极力想要摆脱“女孩”这个身份,以证明自己不是“女孩”。每次她被母亲分派任务,总是非常不情愿去做,或者等事情一做完,就跑出母亲能找到她的范围。对叙述者来说,属于母亲的活儿“特别令人情绪低落”,而父亲的事“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因为叙述者认为她去帮母亲干活,将来便只能接手母亲的工作,这是她所不愿意的,所以叙述者极力想在父亲面前表现,证明自己有能力从事男性负责的工作,摆脱大家对她定义的“女孩”身份,从而摆脱女性从事的工作。
通过描写父亲和母亲各自所属的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小说表面上显示了叙述者对父亲所属分工的亲近和热情,对母亲所属分工的冷漠和排斥,实质是反映叙述者对她作为“女孩”的女性身份的反叛,展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困境。男性和女性作为性别的两方,本应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在男权社会里,男性的地位和作用被大大提高,他们掌握了社会上大部分权利和资本。女性的家庭工作不是生产性的,它没有为家庭和社会创造经济价值,所以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生存,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作者艾丽丝·门罗本人的母亲在嫁给她父亲之前曾是小学校长,结婚以后便只能辞职做家庭主妇,她母亲的经历也是那个时代加拿大女性共有的命运。叙述者不想重复母亲的生存状态,所以她寻找一切机会在父亲面前表现,借此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父亲的帮手,从而摆脱母亲——女性承担的工作,向父亲——男性的工作靠拢。
三、功能对立与女性性别妥协
两性不同的生理差异和性别特质,是叙述者反叛女性身份失败的根本原因。“性别本质决定论”认为,“男性具有男性化特质,例如理性的、精神的、勇猛的、攻击性的;女性具有女性化特质,例如非理性的、肉体的、温柔的、感性的、母性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7]这种生理差异使男性和女性扮演了不同的社会角色,也使得二者在对待同一事件时会产生不同的思考和抉择。
叙述者习惯于编睡前故事,她在前期故事里作为拯救者与后期故事里作为被救者的角色对立,体现了叙述者潜在的女性意识和女性性别特质。叙述者经常在夜晚等弟弟莱尔德睡着以后,给自己编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是我最完美的私人时间”,编的“都是我自己的故事”。[6]149说明叙述者的故事内容只受自己内心想法的影响,而不受外界评论的干扰,所以编造的故事能够反映出最真实的内心。在叙述者前期的故事里,她的世界充满了勇气、胆量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叙述者会在爆炸的楼房里救人;会在狼威胁校园安全时,保护老师,把狼射杀;会骑着一匹好马走在街上,答谢小镇居民对她的感激之情。这些故事展示了叙述者拥有的勇敢、可靠、有力的男性特质,反映了叙述者内心对于男性英雄形象的向往和追求。
当叙述者再长大一些以后,其编造的故事重点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同样的开场,或是遇到火灾,或是遇到野兽,它们先是使叙述者身处危险的境地,然后叙述者会被学校里的某个男生拯救,但这些都不再是故事里的重要内容。“故事中最详尽的往往是我的样子,比如我的头发有多长,我穿了什么衣服。”[6]163在叙述者的故事里,她的形象从前期的拯救者转变为后期的被拯救者,即从救人的英雄转变为被男性拯救的美丽女性,使整个故事成了“英雄拯救美人”的结构模式,这和童话中“王子拯救公主”的结构模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说明了叙述者作为儿童,在传统童话的影响下,接受了女性处于弱势的定位,并在潜意识里认同男性是作为女性的拯救者形象而存在。由此可知,叙述者在故事中角色的对立转变,体现了叙述者内心深处拥有的柔弱、感性、浪漫等女性性别特质,也暗示了叙述者在自我的心理世界里接受并默认了她的女性身份。
叙述者与弟弟莱尔德,在面对相同事件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情感态度和选择,反映了女性和男性在性别特质上的对立,这也成为叙述者在现实世界里不得不妥协于自己女性身份的主要原因。在观看杀马场景时,叙述者和莱尔德二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叙述者内心感到害怕,以致“腿有点颤抖”,只是表面仍故作镇静地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莱尔德却没有感到惊恐,也没有不安,“而是冷淡的,专心致志的”观看。作为皮毛商,父亲会买别人的老马,宰杀后用来喂养狐狸,以此获取狐狸皮毛维持家庭的生计。面对杀马场景,叙述者感受到的是怜悯、血腥与恐惧等女性感性的一面,莱尔德则是专心致志地学习如何杀马的过程,反映了男性客观、冷静与理性的一面。后来在面对家里养了很久的老马弗洛拉,它在被宰杀时挣脱,叙述者为了马第一次违抗了父亲关栅栏门的命令,并尽可能把门敞开,“而莱尔德则跳上跳下,尖叫不已:‘关门’!‘关门’!”[6]161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男性的莱尔德和作为女性的叙述者,他们在面对同一事件时展现出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两人各自具有的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的对立。 放马逃跑事件的最终结果就是叙述者因违抗命令,失去了父亲的信任。在马逃跑后,莱尔德和父亲他们开着卡车一起去找马,叙述者则自己回了家,暗示莱尔德替代叙述者成为了父亲的帮手,而叙述者只能回归家庭接手母亲的工作。晚餐时,莱尔德告发了叙述者放马逃跑的事实,父亲用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说:“她只是个女孩子。”父亲的话把叙述者放在了男性的对立面,强调她只是一个女孩,这意味着叙述者前期为反叛女性身份所作的一切均以失败告终。面对父亲的这句话,叙述者心想:“我没有反对,即使心里也没有反对。也许这是真的。”[6]164反映了叙述者从心理世界到现实世界对自己被称为“女孩”的女性身份的妥协。
门罗通过描写叙述者对男性性别身份的认同,到对自身女性性别身份的反叛和妥协,反映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的性别意识发展历程。前期叙述者作为儿童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于是她成为父亲所代表的男性和母亲所代表的女性的两性性别旁观者。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叙述者感受到了父亲,即男性的优势地位,所以极力向父亲一方靠拢,厌恶并排斥母亲的一切。在这个阶段,作为旁观者的叙述者以为两性的性别区分,在于社会结构中两性所属空间和分工的不同,因此便以自己主观的情感态度去看待和评价父亲和母亲的所属空间和分工。叙述者和莱尔德的对立,使叙述者从性别旁观者变为代表女性性别的一方,由此意识到男性和女性存在本质的性别差异。文中叙述者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接受,并不是由于叙述者认可女性身份,而是叙述者知道她无法像父亲和莱尔德那样成为冷漠的强者,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做出违背内心的选择。作为家庭里的绝对权威,父亲对叙述者是女孩的身份定义,使叙述者永远失去了改变自身女性命运的勇气和决心,完成了她从心理世界到现实世界对自己是一名女性,即弱者的身份定位,也是她对男权社会所建构的女性性别文化身份的妥协。
四、结语
《男孩和女孩》以独特的儿童视角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艾丽丝·门罗小说中重要的代表篇目。小说通过描写叙述者从积极地反抗者到消极的接受者的对立转变,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约束、改造和压迫,说明女性想要通过依赖男性的方式去改变自身弱势地位是难以成功的。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传统社会是“建立在性别之间的统治和剥削的社会关系”之上的,它导致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8]40这种二元对立源自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只认可二项中被社会所尊崇的一项,即所谓的中心或本源。因此在男女二元对立关系中,前者属于统治和优先地位,后者则永远被排斥在边缘,成为他者。门罗通过小说揭示了加拿大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生存困境,反映了女性只有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重新定义女性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属性,才能摆脱被动、从属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