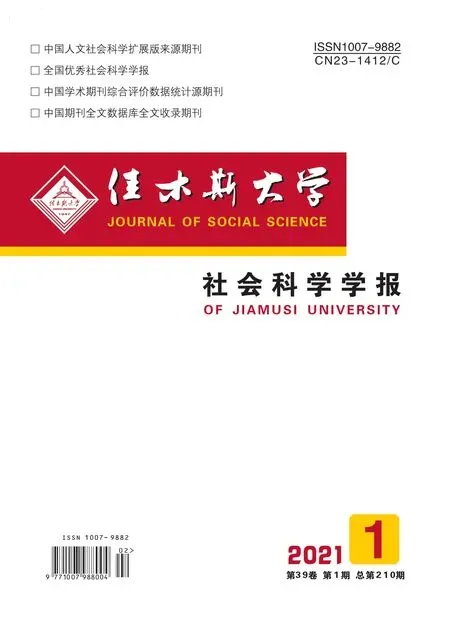田汉早期话剧中的文人弱者形象*
许梦雪
(齐齐哈尔大学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161006)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新浪漫主义”风潮,之后十年间众多现代作家都开始在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捕捉革命青年精神上的漂泊无依和知识分子心理上的苦闷情绪。田汉先生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创者,在其早期话剧作品里同样抒发着这种忧郁的感伤。1929年是田汉创作生涯里由早期过渡到中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时期他的学生们和漂泊着的革命青年促动他向“左”转,这相当于一次集体的思想哗变,使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徘徊在小资情调里诉说感伤,而应该传递出战火的诗情。因此,本文根据田汉话剧创作的情感基调及创作特点,将1929年及之前的创作视为其早期作品进行研究。其中以《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南归》等为代表。田汉的早期作品里不仅在“新浪漫主义”的笼罩下塑造出一个个热情漂泊者的形象,更在其悲凉的心境下刻画出文人弱者的形象。
文人通常指有文化、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但在田汉的早期剧作里却赋予很多社会的底层人以文人的特质,他们或是流浪者、是艺人、是侍女、甚至是“傻子”。其中无论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还是为宣泄人物内心情感而塑造出的具有文人特质的形象都无一例外蕴含了被压迫着的弱者气息。他营造的是这些文人在时代的束缚下,从不同的心理特征出发却不约而同的走向精神层面的忧郁感伤,表现出被压抑者的苦闷愁绪。他的早期剧作在内容上主要追求的是场面和意境,将戏剧冲突预设在规定情景里,让文人弱者的情感在一种诗化了的意境中得到升华。
一、意境中文人的感伤情怀
田汉在戏剧创作上始终怀着一种文化兼容的态度,善于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利于自己创作的艺术形式,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1927年田汉在担任上海艺术大学(后改名为南国艺术学院)校长时召集了一些艺人和艺术爱好者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艺术鱼龙会”的戏剧公演活动。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在当时对旧剧强烈批判的背景下,这次戏剧公演活动是话剧与戏曲的第一次公开和解。所以说田汉是中国古典文化与现代极具变化思潮的交汇点上的巨人。他对古典文化的吸纳与他从小学习诗词歌赋、观看传统戏曲有深厚的渊源。正是由于他从小被古典文化深深滋养着,逐渐沉淀在他的生命深处及情感深处,从而使他形成一种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相结合的审美取向。
因此,田汉早期的话剧作品深得中国传统戏曲之古典美,他注重对审美主体的心灵写意,表现人物的主观情绪,营造一种抒情的意境美。陈祥耀谈到“意境的意义包含了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形象。在作品中,作家的思想感情(意)通过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境)而表现,艺术形象又是通过作家的思想感情而创造。这就是文艺创作的“意”与“境”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1]53-61正如田汉早期剧作中的感伤情怀与文人弱者形象的结合所达到的这种“意”与“境”的统一,从而形成飘渺、诗情的意境美。
田汉早期话剧中所蕴含着中国传统戏曲之古典美,并善于用一些意象营造优美的意境,以淡化故事情节的方式突显其心灵的写意性,从而形成其早期话剧作品里浓厚的“诗情化”特征。有研究者评价田汉早期戏剧缺乏艺术趣味,主要提出其人物关系的搭建不够复杂及戏剧冲突的张力不足等问题。如今暂且抛开当时田汉独当一面的艰苦条件不谈,在“急就章”的创作环境下赶出来的作品可能会在情节的铺设方面有时考虑的不够周到,以及在人物关系及规定情景的搭建上不够周严。我们就算忽略田汉创作过程中来不及推敲和思考的条件,也不能片面的认为情节简化就是缺乏艺术性。结合中国传统戏曲里简单的故事情节来思考就会发现田汉因受其影响而借鉴了诸多因素,如对人物情感的深入挖掘,对意境的营造等。
叶朗谈到“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学理性的感受和领悟。”[2]107-110田汉早期的话剧创作中将情节淡化而通过对文人的细微刻画所营造出来的意境美正使得我们获得这种哲学理性的深层感受和领悟。作品《古潭的声音》,其情节虽然极其简单,但其中隐含着的神秘意境却让人回味无穷。诗人把舞女美瑛从尘世的物质诱惑里解救出来,期望着肉的沉迷能得到灵的觉醒,并想要以艺术之美感召她,但最终这个不断飘摇着的灵魂却被深不可测的古潭夺去了。这种绝望的无助感,激起诗人向夺其所爱的古潭复仇的决心,而捣碎古潭既是死亡也是弱势群体的反抗。美瑛跳入古潭,是精神上受到难以抗拒的诱惑,生命由终而始。诗人跳入古潭,是心理上受到难以化解的打击,生命由始而终。正如田汉所说“这样一来我们才不会像从前一样对于‘艺术’,对于‘女孩子’有许多幻想,也才不会有那么深的幻灭底悲哀了。”[3]106这更加充分的说明田汉始终把文人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来思考,并给予他们同情和怜悯。
田汉在戏剧创作中善于刻画人物,能很快抓住人物的性格特点,而在其早期话剧中所描述的文人性格的缺失是他创作里的一大闪光点。他在《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中谈起自己早期的剧作:“它们同表示着青春期的感伤,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彷徨与留恋,和这时代青年所共有的对于腐败现状底渐趋明确的反抗。”[3]29同样地,他的作品里飘渺的意境之中透露着的感伤、彷徨、留恋与反抗,使人物在迷茫的内心世界里性格呈现出不确定的缺失状态。作品《咖啡店之一夜》里的林泽奇,他是一个生在有钱人家上得起大学的知识青年,却被家庭的包办婚姻围困,所能做出的有力反抗只能是借酒消愁,并因自己要爱而不能去爱声称自己是一个迷了路的孩子。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他面对封建家庭的强势压迫却无力反击,显示了他是一个渺小的弱者;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他不敢冲破家庭的束缚却在别处吐露内心忧愁,体现了他性格上的懦弱,缺失了刚烈的反抗勇气,剩下的只是多愁善感与脆弱无能。剧中的李乾卿则更甚,已经当了无情的负心汉却仍标榜自己的弱者地位以寻求对方的同情与谅解从而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他回应秋姑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你责备我的话,我没有一句敢替自己辩护的。可是你不能说我全然没有良心。……你也要可怜我,因为我是一个弱者,我的心灵被旧社会的阴影,遮得一点儿光明都没有了。可是我也没有法子,所以求你成全我们现在的幸福。……我的心里,也是顶难过的。”[4]124由于他性格的缺失让这里的诉苦前后明显矛盾,既已经辜负了秋姑娘却又强调自己的可怜,即使同样是被家庭包办的婚姻所束缚,也不用再祈求得到无奈抛弃的恋人的祝福,这让人无法确定他心底里到底爱着谁。如果完全是被逼的选择又怎会有幸福可言,但若没有被压迫而负心,又为何苦言自己是一个被旧社会笼罩着的弱者。因此,只能说是性格上的缺失与徘徊不定使他流露出内心的烦躁。
《湖上的悲剧》里的白薇为爱“死而复生”之后却又得知恋人已结婚生子,甜蜜的幻想被完全打碎后再次决然的选择死亡。即使不想破坏别人的家庭但得知恋人仍深爱自己却依然要自杀,显示出其性格的刚硬,而缺失了女性应有的柔和。这种强烈的反抗意识看似过于冲动,又让人感觉合乎情理,死亡总有很多理由,但活着却需要莫大的勇气。作者正是赋予她这种完全的反抗精神来折射出她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对于现实生活的幻灭感与深深的绝望,死亡成为她性格上缺失了稳重的唯一选择,用悲剧的结局体现出文人的弱者地位。
二、时代背景下的追梦人生
前面谈到田汉早期话剧里文人弱者的感伤,而这种感伤在他的作品里其实是一种审美,也是一种对生活无着、情感无依的漂泊的无助感。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做着梦、不断追寻梦的青年,这么一个有责任、敢担当的文人让自己笔下的青年传达出弱者的漂泊之感是他的生命意义之所在。田汉在进行早期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一代的青年文人开始追求民主和科学,迫切的想要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大批留学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见识了异国的繁盛先进之后再看到祖国的贫弱,那种探求社会变革的想法便愈加强烈。他们高远的理想在像暴雨来临前一样沉闷的社会现实与纷乱的政治现状下被打败,使得这群知识青年的内心生发出一种幽深的幻灭之感。正如田汉早期主张以电影打造“银色的梦”一样,想要宣泄个人的苦闷只靠理想与热情远远不够,他笔下那些与他同样怀揣梦想的文人志士在时代背景下的追梦人生也显得虚无缥缈。
对于田汉的早期话剧来说人物情感的起伏是事件发展的关键,情节的铺设和人物关系的搭建都是沿着情感的传递来营造不同的场面和意境。田汉对于情感的抒写向来是迎合着整个社会状态而不断变化的,在其早期剧作里主要表现出文人的苦闷情绪。这是由于时代的洪流不断冲刷着文人们的热情,从而使他们的人生被孤独和凄凉所浸透。如《咖啡店之一夜》里通过对婚姻的束缚、爱情的丢失等外在社会现实的冲突描写,集中体现这种外在冲突给主人公内心带来的强烈冲击,将心灵感伤的刻画作为剧作的重心,把外在冲突当成心灵变化的历程。这种着力表达文人们主观苦闷情绪的创作基调,正是田汉早期很多戏剧中的共有特征。如《南归》《获虎之夜》等都在描写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下着重于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使这些文人弱者呈现出一种灵与肉不可调和的痛苦。
《南归》这部极具浪漫的幻想和诗意的抒情作品里塑造了一个随处漂泊、无家可归的流浪诗人,军阀混战让他家破人亡,封建势力逼死他爱着的姑娘,满心创伤的他流浪到南方想要留下将养伤痕。这时,故事却以他来晚一步出现戏剧性的转折,从而使他错过了想要追求安宁幸福的生活机会。他的心头充满怅惋与无奈,只能继续孤鸿似的撑起残翼迷茫的飞翔。正如田汉所言“是的,在这年头的人间确是没有那种许我们好好的将养伤痕的地方,‘不能斗争的只有死灭’!”[3]112由于没有养伤的地方,这些知识分子剩下的只有的无助、无依、无望是社会对他们的冷漠所造成的,从而使得这些文人志士在微弱的处境里只能暗自感伤。《获虎之夜》里黄大傻在眺望灯光时的倾情诉说是被作者赋予了文人的特质,正如陈瘦竹指出“与其说是一个农村青年,不如说是一个感伤主义诗人。”[5]62这里作者借虽不是文人的黄大傻之口宣泄出文人弱者于时代下的悲凉境况,他对嫌贫爱富的社会现状表现出苦闷、迷惘之感,流露出哀婉、忧伤之情。
田汉进行早期戏剧创作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由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弱势及身份地位的低下,使得这些人空怀着满腔爱国热血,他们想拯救我们的民族、变革我们的社会只能成为空谈和虚妄。此时,高远的理想与世态的炎凉之间形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面对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田汉只能以文人在现实生活里不得志的凄凉来揭露这种失衡状态。“田汉的感伤,作为反抗的少年诗心、作为理想与现实或者说灵肉失调矛盾中的苦与闷,作为一种诗意人生的情调,是田汉剧作浓郁的抒情氛围与独特的诗意境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理智与热情的结合,是那样的紧密;它的主观抒情性,渗透着强烈的现实意义。”[6]58田汉早期剧作中主观的抒情很容易被读者感知,但这些主观的情绪所寄托的愁苦则是在远大理想的鞭策下才得以抒发出来的,这一点不能被忽视。
正如《梵峨璘与蔷薇》里体现的田汉对艺术与爱情的尊崇并寄改造社会的希望于剧中人物身上,通过对前革命家的理想刻画,使文人秦信芳陷入绝望的心境得以化解。然而原本准备牺牲自己的幸福以成全恋人艺术梦想的艺人柳翠正是田汉笔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精心描绘出的一个文人弱者的形象。柳翠与秦信芳追梦哀愁的形成是由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与高远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果。“解救神”李简斋的出现给予这两个弱小的文人以实现理想的机会,这显然是作者对社会现状的一种强烈期盼。同样的社会期盼在《灵光》中也有体现,田汉将女留学生顾梅俪陷于恋爱的苦闷中作为一个引子,继而引出一个《浮士德》式的梦,梦醒后顾梅俪幡然觉悟,要与男友一起回国。一个做救治人民身体上痛苦的医生,一个从事为拯救人们精神上痛苦的文学。作者以两个人的力量影射出两个大团体的努力方向,表现出两个文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力量虽然弱小,但确有着崇高的理想。作品以弱势群体知识分子的宏愿来呼吁人们应当提高自己的觉悟为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三、弱者形象承载的美学追求
谈田汉早期话剧中蕴含的美学思想,必然要从他对新浪漫主义的认识开始,才能更好的理解新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观念在其早期作品里的集中体现。“田汉眼中的新浪漫主义,是指继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各国的……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它既不是所谓悲观主义的,也没有神秘主义的虚无与幻灭感,相反,倒有较强的现实感与针对性。”田汉曾强调:“所谓新浪漫主义,便是想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窥破眼睛所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6]24由此可以看出,田汉早期剧作所追求的新浪漫主义主要是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来对灵的世界进行诗意的窥探。尽管1916—1922年间田汉留学日本,但他仍然心系祖国,漂泊在异国的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并将所了解到的中国青年文人的现实状况体现在他的早期作品里。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他依然选择以艺术为武器来唤醒民众和改造社会。在新浪漫主义思潮的笼罩下,关于文人弱者形象的美学追求则主要体现在对其外部动作的淡化及内部心理动作的强化,这种心理动作的强化主要来源于其归属感的弱化。
田汉早期话剧中蕴含着的传统戏曲之古典美随情节的简化而将人物的外部动作淡化,从而极力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动作。作品中的文人弱者在失去外部动作支撑的情况下显得社会地位更加渺小,却使得人物内心的愁绪更加丰富饱满,甚至像沸腾的水一样溢出身体,透过精神的飘荡而吐露不尽。知识分子们的身体被外部环境所束缚,心灵却极力挣脱牢笼。田汉在其剧作里试图以人物心灵上的超脱来调和灵与肉的外在矛盾。在《苏州夜话》里作者淡化了人物的动作,仅借画家刘叔康与学生杨小凤的谈话将故事情节讲述清楚。这时,人们的着眼点已不再是外部动作是否具有戏剧性,而是感受着刘叔康的悲惨遭遇,更是惋惜他那被无情的现实所打开的“艺术之室”。艺术作品就这样毁于一旦,看似是残忍的军阀烧了一屋子的画,实则是冷酷的现实粉碎了所有文人志士的梦想。正如田汉所言“当时那一个世界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初接触社会的真实,固而渐次打破了那沉酣的美底幻梦底那一种世界。”[3]291文人们刚接触到的真实世界竟是如此心灰意冷,“他们气了,一顿刺刀就把我那幅费了五年心血刚画成的《万里长城》一块一块地给划破了,那就像一刀刀地割着我的肉!”[4]117接着又将整个屋子点燃,他们划破的、烧毁的不仅是一幅“万里长城”的画,更是将文人内心“万里长城”般的创作激情与爱国情怀揉碎了再扔向深渊将其毁灭。
另外,《颤栗》这部控诉封建家庭的悲剧中除了私生子开始想要杀母却误杀了狗的戏剧动作外,剩下的都是借母亲之口讲述故事的情节。母亲因早年的私情生下这个儿子,在不断哀求中得以保全他的生命,但却由于心中的怨恨而对他百般苛刻。在母亲与私生子说出真相的同时表露出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女人本是弱的,你娘又是弱中的弱者,要不然她早自杀了,现状让她死在她自己的罪孽的手里吧!”这之前她诉说了儿子成长道路上所受的不公待遇,表现出儿子是一个弱者的形象,但又哭诉自己是弱者中的弱者希望得到儿子的怜悯。剧作中透露出死亡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观念,而在痛苦中活着才是最大的弱者。其中私生子想要求学而不得的凄凉处境正是映照着当下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悲凉遭遇。这种淡化戏剧的外在冲突,而着重刻画文人弱者的内心活动并以期揭露社会现实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审美趣味。
田汉留日归来后本想与众多文人一起建设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而在诸多原因的干扰下他离开群体另辟蹊径,在1924年创建了《南国》半月刊。对于在艺术上有着“独立癖”的田汉而言,战争、封建、资本等因素的集体摧残致使他的理想一次次破灭。这让原本外出留学没有归属感的他在回国之后依然有着漂泊无依的迷惘。前面谈到文人弱者心理上的强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归属感的弱化,这便与田汉早期作品中所营造的文人漂泊者的形象有一些相似之处。
在作品《南归》里那个流浪着的文人极度的失落与彷徨,他的家不在了,爱人也不在了,就连一心挂念他的春姑娘也即将嫁于他人,最后的安定之所也不能收留他。就这样,他的归属感一点一滴的从他现实的世界里抹去,无处宣泄只能以悲凉的歌声来抚慰自己内心的凄苦。他更像在大时代里迷失自我的孩子,由于归属感被现实剥夺而默默发出弱者的苦闷感伤。《名优之死》虽表现的是一个艺术家的悲剧,实则是借此揭示了文人们在现实社会里失去归属感,批判了摧残艺术及文人的强恶势力。其中一代名优刘振声为艺术而生,又含恨死于舞台,这是由于在徒弟刘凤仙情感与艺术的双重背叛下,使他失去了心灵的慰藉,从而丧失生的意志。田汉早期话剧中将“艺术至上”的观念以及文人归属感弱化的流露抒写到极致的是《古潭的声音》和《湖上的悲剧》。一个是诗人拯救了舞女美瑛在物欲社会中不断消沉的肉身,却没能感召到她的灵魂,最终跳进幽深的古潭,诗人因不甘屈服于现实中的失败而以自己的牺牲去捣碎那神秘的古潭;另一个是诗人杨梦梅看到死而复生的情人白薇又在自己面前死去,再次感受这种得到后失去的痛苦,却又要为情人的嘱托及家庭的牵挂而绝望的活着。这两个文人一死一生,死的解脱了凡尘没有归属感的忧愁,生的被这种更加弱化的归属感凄惨的笼罩。
四、结语
田汉作为动荡时代里的一个热血青年,年少时便登上文坛,曾接受过西方唯美主义的熏陶并与新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想相结合,将其渗透到自己的早期创作中。他善于兼收并蓄,将古今中外文化之精髓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因此,他的早期剧作虽受到西方戏剧思潮的影响,却又与中国的传统戏曲紧密结合,以淡化故事情节、淡化戏剧动作、深化人物情感、深化人物内心的形式刻画出一个个迷失在大时代里的漂泊无依、缺乏归属感的文人弱者形象。这些文人弱者的感伤与苦闷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剧中人物以真情的流露与倾情的诉说映射出那个时代文人们的迷惘与悲凉,这是田汉早期剧作中最具时代意义的一类人物形象。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以审美的方式,还是以政治的启蒙来看待田汉所塑造的这些文人形象,将他们放在任何时代都永远不会枯朽。
所以,他的这些早期剧作中文人的弱者形象在他整个创作生涯乃至中国话剧史上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