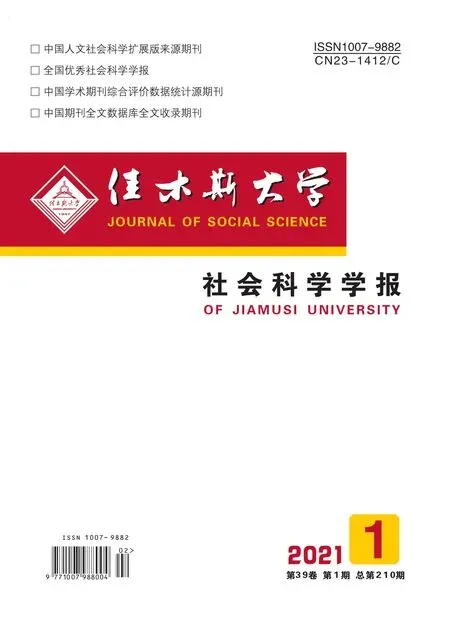虚拟现实内的道德边界*
马开兆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一、虚拟现实
关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这一概念的源头追溯,尚无定论,自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信息技术腾飞,作为计算机领域的新技术,类似的概念便陆续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如人造现实(Artificial Reality)、赛博空间(Cyberspace)。从技术而论,虚拟现实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结合相关科学技术,生成与一定范围真实环境在视、听、触感等方面高度近似的数字化环境,用户借助必要的装备与数字化环境中的对象进行交互作用、相互影响,可以产生亲临对应真实环境的感受和体验。”[1]2-46虚拟现实不是实体,而是对现实模仿的现象,它创造一些在效果上存在但在物质世界中不存在的东西,它的真实性来自于相应信息赋予参与者的感知。参与者可以佩戴类似头盔、手套等电子设备作为信息传输的中介,使自身以一个虚拟身份进入一个由计算机数据重构的三维图景,并与周围环境交互,从而获得一种在感知上令人相信的真实。希利斯(Hillis)将数字虚拟现实定义为“在技术中构成的个人体验”,它“将技术的世界及其呈现自然的能力,与社会关系意义的广泛重叠领域结合在了一起。”[2]48-59
伯迪(Grigore C.Burdea)指出,虚拟现实技术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沉浸(immersion)、交互(interaction)和构想(imagination),这强调了个人在虚拟中的主导作用。现在虚拟现实的沉浸式体验一般是通过电脑屏幕或是特殊的显示设备而实现的视觉体验,辅助以声音效果和触觉反馈。尽管这些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算机内部数字化环境和外部电子设备双重作用下带给参与者的真实感,但这些设备并不是必须的。重要的是通过设置某些条件引导参与者自身进入到事件发生的虚拟环境,所有的事件必须以“我”的视角发生。交互是虚拟现实的核心,意味着参与者可以直接操作虚拟环境的某些方面,进行修改创造而非被动地接受。构想则是虚拟对现实的超越,在虚拟现实中参与者可以完成现实中无法完成的行为,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与喜好创造虚拟事物。
虚拟现实存在着更为严格的界定,如提供封闭式的空间、采用与视觉理解直接相关的影像,感知环境的方式等。但这些更为具体的说明,无非是基于沉浸、交互、构想三个维度的延伸。只要参与者能够以自我的意愿与虚拟环境发生交互,就可以被广泛理解为虚拟现实。虚拟现实的沉浸感、交互性、构想力会随着技术更迭而愈发真实完整、自由开放,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实现任何想象的行为,并使这些行为具象化。因此,一个虚拟现实系统在原始规则上允许那些现实中不道德甚至法律禁止的行为。尽管目前部分高精尖领域以外,几乎没有能够将不道德行为高度具现化的虚拟现实程序,但该技术有着继续发展的可能性。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地用于模拟参与者与其他虚拟或真实环境交互的虚拟现实程序投入大众的生活,甚至影响社会交往方式。那么虚拟现实中的行为是否应该被限制,在多少程度上受到限制,限制规则以何为依据等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二、虚拟行为与道德争议
虚拟现实对社会交往及人类认知影响的深刻程度取决于该技术的发展程度。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可分为多个阶段,并最终导致诸如本体论、实在论层面上的问题。[3]63-72当下处于虚拟现实技术发展的初步阶段,该技术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涉及人类现实与虚拟之间的所有问题,那么伦理思考的范围将会是无限的。因此,为了使相关行为道德问题积极有效,我们需要将虚拟现实技术假定在某一发展阶段内,即沉浸于虚拟现实的主体并不脱离现实,参与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与虚拟对象进行交互;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保持同一性;参与者能够意识到与之交互的是虚拟环境。总之,一个现实的个人在虚拟环境中的行为规范是我们讨论的主要对象。
关于虚拟环境下部分行为的道德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以部分开放式的角色扮演类游戏为例,它们符合虚拟现实的基本特征,玩家能够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游戏里的行为与境遇,通常还可以与其他玩家在虚拟环境中发生交往。驾驶、购物、运动等几乎所有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都可以在虚拟环境下实现,还可以参与金融贸易、州长竞选、夜店赌博等虚拟社交活动。而枪击、抢劫等在现实中会面临牢狱之灾的行为在其中更是家常便饭。这些玩家根据自身意愿而进行选择的非必要行为,亦可针对其他玩家。“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4]11根据自由主义者的主张,虚拟现实的不道德行为不仅是被允许的,还应得到辩护。虚拟现实中的行为不会影响现实中的他人,而行为只有在关涉他人、社会时才拥有道德性,因此这些行为与道德无关。并且一个人从这些虚拟行为中获得快乐而没有人由此遭受损失,符合任一效用论。但虚拟现实技术并不是私人的,现实的人仍有可能遭受影响,因为他们会知道有一个以他们这一类人作为模拟参照物的虚拟人出现在虚拟现实中,或他们所热爱的其他事物成为了被模仿的对象。如果这些带有他们现实特征的虚拟形象遭受了不道德的行为,那么他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自己遭受了此类行为而感到不适。社会认同心理,使得个人会因为其所从属群体中另一人的遭遇而产生情绪上的变化。认为对虚拟角色的任何行为都与现实无关的观点,实则无视了他人群体的情感并侵害了他们的人权。提倡虚拟现实是自由与私人领域的论调,所缺乏的是对我们行为主观性与意志力的意义和背景的考虑,并忽略了其造成的超出个人接触范围的社会后果。部分抵制者指出,“具象色情既不非虚构也非虚拟:对妇女的实际剥削和暴力在其中发生。并且在色情作品中的虚构情节与许多女性经历的实际行为如此相似,以至人们不能说色情作品是虚构的。”[2]48-59尽管对象是虚拟的,但参与者的行为本身是真实且非道德的。
虚拟现实技术与其他媒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构建起一个在观感上极其真实的世界,而这种真实性会随着系统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扩大。这就意味着它们涉及了实践,人们有机会“亲身”体验道德禁区,了解认知犯罪分子的行为、感知、技能及思维方式,且不会遭受严重的惩罚。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同一行为在虚拟现实和现实中必然联系,部分人认为让个人实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可能会完成的愿景,减少了在现实中相关行为的可能性,或是让个人的情绪欲望得到宣泄以消除社会不良行为的动机。但非道德行为在虚拟现实的出现就意味着其至少“延迟或鼓励了真正在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5]23-28,并阻碍了道德发展。这一论点可以得到义务论和德性论的支持。康德强调,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视为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虚拟人虽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仅是一堆数据的模拟,但把真实他人当做目的的义务仍旧可以要求我们尊重虚拟人物。普遍的道德原则允许理性对“谋杀真实人”和“谋杀被感知得像真实人的虚拟人”两个行为作出区分,并禁止前者,但两者在感觉层面上可以无限接近。个人的道德判断与行为不是完全基于理性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下的情感,[6]2105-2108义务的界限就模糊起来。人类心理存在这样一个特征,即在一个领域实施残酷或不道德的行为必然会延续到其他类似的领域。因此,德性论要求我们避免残酷地对待动物,以阻止我们残酷地对待他人。对动物残酷的人在与人打交道时也会变得残酷,而对无声动物的关怀则发展了对人类的人文关怀。既然对动物的残酷会导致对人类的残酷,那么对虚拟人的残酷也会导致同样的后果,因为针对他们的行为更加接近对真实人的行为。在对待虚拟人物时与在对待现实的他人时所表现的行为与情感是相似的。麦考密克指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的延伸,通过“参与对过度、放纵和不法行为的模拟,你会伤害自己,因为你侵蚀了自己的美德,使自己远离了幸福目标。”[7]31-36残酷地对待虚拟人物会败坏我们的德性,削弱我们的道德义务,并在与他人相处时变得冷漠残酷。
三、虚拟现实的道德规范
虚拟现实与现实之间可以无限相似,使得其内容相较于其他媒介对现实社会有着更大的冲击力。对于虚拟暴力行为的否定,在于暴力在现实中是不可接受的,不仅因为该行为侵害了他人权益,更因为行为本身于正当性而言是不道德的。虚拟现实不只是传统媒介的拓展,虚拟现实中的暴力行为与电影中的暴力行为,两者之间的道德价值区分不止于它们对现实影响的可能性与程度不同。颠覆性之一在于前者涉及了自我实践,因此参与者就有了单独的道德地位,而非现实道德的延伸。有理由相信,虚拟现实中行为的道德性评估不再依赖于相仿行为在现实中的道德性,其道德价值是自足的,是基于虚拟背景而得到评估。
若个人认为某个虚拟现实程序不符合现实的道德规范,便可拒绝参与其中。既然虚拟现实系统可以提供用以判断道德价值的完整背景,那么可供我们判断参与其中的行为就其背景而言是否道德的依据为何?换而言之,如何在虚拟现实的环境内建立起就该行为本身为目的的规范?如果缺乏规范,我们就必须“诉诸实用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然后寻求使他们合理化的方式。”[8]23-28一种 方式是沿用已经存在着的行为规范,即现实道德,把虚拟对象当做真实的对象来对待,把虚拟环境当做真实环境一样来约束自己。因为虚拟现实的大门阻隔了身份的连续性,所以现实中的“我”与虚拟中的“我”可能会根据环境而采取不一样的道德立场。那么评估一个虚拟行为的道德价值与评估小说中某角色行为的道德价值并无二致。一旦虚拟环境要求参与者献祭虚拟的女儿,那么他就是阿伽门农。
这一方式是可能的,但不一定是合适的。谋杀行为的非道德性来自于现实背景对其的解释,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既然虚拟现实拓展了现实,就意味着谋杀行为的道德价值可以基于拓展了的背景而被重新评估。关键在于不引入外部因素的情况下,如何评估虚拟道德规范的产生以及它们的意义。现存的道德规范并非凭空杜撰、一蹴而就的,它依循社会历史的发展。“造世伦理学”[9]160-165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现有的道德框架,虚拟现实只是改变了道德的内容而没有改变它的形式。既然是现实的人进入到了虚拟,那么思考道德的方式就不会改变,康德的“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做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10]39-40在虚拟现实中仍旧可以成立。重构道德规则就意味着参与者在虚拟现实中有着怎样的道德诉求,这取决于一个虚拟现实程序设置的目标。
契约论的道德规则来自于“一种利益的一致,因为社会合作使所有人都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仅仅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11]2总之,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人们选择一种社会道德来相互约束。但虚拟现实可以创造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现实的各种限制再次消失了,道德也就失去了其产生的条件。事实上,尽管我们于客观现实的世界之外构建一个虚拟世界,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重要联系,虚拟世界的限制来自现实世界,并且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带着这些限制以防止道德分裂,只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并理解它们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才能寻得一个认识两个世界及其缺点的解决方案。虚拟现实是现实的派生物,它们的意义必须由现实赋予。一个可以无限制开放的虚拟现实程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必须有一个朝向限制,给参与者设置一个范围目标,而这个目标的意义来自于现实。虚拟现实的道德边界,取决于虚拟现实在多少程度上拓展了现实,又在多少程度上受到了现实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