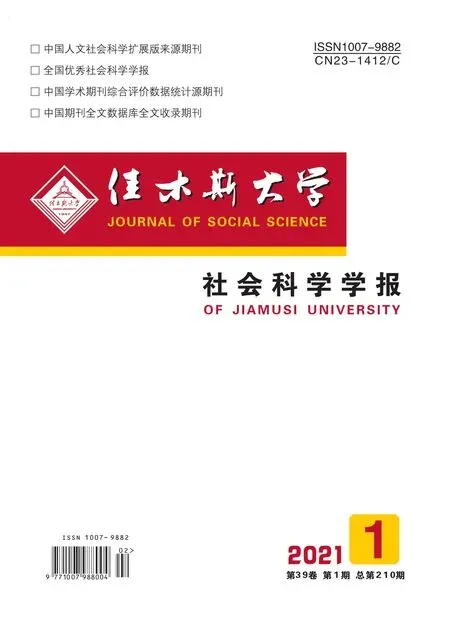梁漱溟科学观探析*
金 丽
(合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作为挽救民族存亡危机的钥匙,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各种学派的不同争执。唯科学主义者将宇宙万物的各个方面都通过科学知识加以认识与解释,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祖,率先举起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态度鲜明地提出自己对科学的看法。他的科学观是在西学东渐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结合自己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理论和叔本华的意志论的理解,提出处理儒学与科学关系的方案。他的科学观在今天对于正确看待儒学与科学关系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
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科学主义是指将所有的客观事物都放在“自然程序之内”,确信只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程序的所有方面的关系”[1]17。这里所有方面既包含了生物、物理自然科学的方面,也包含了社会、心理等社会科学方面。这种科学主义带来了思想界的大论战。最为代表性的便是丁文江、吴稚晖等科学主义者与张君劢、梁启超等玄学者之间的“科玄论战”。科学主义者将一切纳入科学的范畴,从自然到社会无所不及,认为可以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来研究世界万物包括人生观的问题。现代新儒家既接受民族振兴需要发展科学的现实,也接续儒家道统,重释儒学与科学关系,寻找儒学与科学相融相生的解决之道,给儒学复兴提供合理证明。
梁启超的“科学万能”破产的惊呼给思想文化界带来影响颇大。1919年,当梁启超从欧洲旅行结束之后,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引发了他对造成这种战祸和社会危机的思考,正式宣布“科学万能之梦”的破灭。他称,“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希望科学成功换来“黄金世界”,结果是人类像沙漠中迷路的旅人,追寻着影子般的“科学先生”,“没有得着幸福”,却是“许多灾难””,“欧洲人做的科学万能的大梦”终归破产。[2]20梁启超从西方社会危机的根源——西方文化出发,开始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拯救西方文化的方法,作为一名曾经热烈介绍西方文化的学者,他的这番评论很容易引起当时人们对科学功能和价值的反思,也让更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鼓舞,唤起他们对科学主义的反对之声。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中,梁漱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印度人的出世思想”到“中国的儒家思想”[3]111-118。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先驱,开始了对科学主义思想的批判。
第一,对科学主义残害人性的揭露。西方文明造就了几百年的经济变迁,科学满足了人类征服自然,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手工业小生产组织逐渐被机械大生产所取代,贫富悬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此的经济其戕贼人性——仁——是人所不能堪”,[4]157资本家与工人生活枯燥乏味,人与人之间冷漠,缺少情义。“谁同谁都是要算帐,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4]145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导致人类放弃向内追求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人性丧失,这些都是科学主义带来的恶果。
第二,对科学作用有限性的分析。在众多文化形式之中,他选择科学与宗教的比较,从中发现科学作用的局限。他认为,科学对应的是知识,称“知识有成就”便是“有科学”[4]38;宗教是一种人生态度,是“超越现实世界的信仰”[4]38。在阐明科学的作用时,他明确指出,科学和宗教分别属于知识和行为。“知识并不能变更我们行为,行为是出于情志的”[4]95。梁漱溟明确划分了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分别属于知和行的范畴,同时指出了作为科学的知识不能对行为做出约定,换言之,科学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科学无法像宗教一样给人提供一种精神皈依。
第三,对科学取代哲学的批判。科学与哲学(玄学)在认识活动中表现形式不同。他称科学通过理智来认识活动,但是理智通过综合抽象出概念把握事物的现象,却无法认识宇宙本体。“宇宙的本体”是“‘生命’,是‘绵延’”[4]80,理智的方式是无法认识本体的,只有依靠直觉才能达到。同时理智作为一种认识工具和手段,无法认识人的内心生活,也只有直觉才能达到对自我生命的体悟。用直觉认识生活时,主客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开。“直觉所得”即使用语音文字来呈现,但是“一纳入理智的形式”意思就不对了。[4]80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的发达,易使人误以科学方法解决哲学问题,这种滥用科学的结果是,“乖其根本,而且终究弄不成”[4]78。
梁漱溟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站在科学主义盛行导致的后果来分析科学存在的局限,尤其是科学无法通过理智来解决人生领域的问题,而这些只有通过东方之学来弥补,东方之学是通过直觉向内体认生命,改造生命的学问,这也正是西方科学与东方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二、对科学与哲学的区分
第一,研究对象有别。科学与哲学(玄学)研究对象有着根本差异,科学面对的是具体现象,而哲学面对的是生命本体。科学研究的现象“多而且固定”,玄学研究的本体“一而变化、变化而一”。[4]37他以中西方看病为例,指出中医看病求的整体,认为“整个人病了”,而西医寻求病灶,认为“这人的某器官某部分病了”,[4]36中西之别在药品性质上也体现了出来,西药通过它的化学成分来分析它的有效性,而中药不去剖析哪一种药的作用和性质,他的性质作用放在整体上看性质效用。由此看出,玄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表达知识的话语是不同的,具体而言,科学方法得到的是“知识”,玄学方法得到是“主观的意见”,或者说西方人所用的观念“明白而确定”,而中国人所用的观念“有所指而无定实”。[4]37
第二,认识方法不同。科学与哲学(玄学)在认识活动中的方法迥然有别。西方科学重“理智”,中国哲学重“直觉”。中国人所用的认识方法“是玄学的态度”,有所指而无定论,西方人所用的“是科学的方法”,观念有所指而具体,[4]37为了说明两者认识的区别,梁漱溟借用佛学术语“现量”“比量”和“非量”来解读。“现量”就是感觉(Sensation)。他举例道,例如品茶的茶味,看到白布的白色,这些都是“现量”。对茶的知识都来自我以前对茶的颜色和味道的感觉为起点,从而形成对“茶”的概念。“比量”是“理智”。以茶为例,对于茶的概念,既综合不同种类茶的共同之点,同时也将茶与别的东西予以区分。这种综合与区别的作用就是“比量”。“非量”是直觉。知识是由“现量和比量构成”,但是“现量的感觉”与“比量的抽象概念”之间还应当有“直觉”的作用。直觉认识的是“一种意味精神、趋势或倾向。”[4]72-74以中国书法为例,我们欣赏某人的书法可以“得其意味,或精神”,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是直觉的作用。直觉不同于感觉和理智,他可以直达对事物现象的本质认识。
第三,功能作用有异。西方科学的产生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经济的发达和社会的变迁,人类开始成功地征服自然,也给自身带来了灿烂的物质文明,然而他们也暴露了不可掩盖的弊端,人情淡泊,精神空虚,造成人们内心的苦闷无法排解。而这些弊端恰恰可以借助中国哲学的力量化解。在中国所有哲学当中,孔子的儒学替代了西方宗教,为人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而这些作用是科学难以完成的。他称,宗教是一种信仰,要求信徒遵守戒律。但是中国自古受孔子影响至深,“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5]107-108。孔子儒学一方面通过道德教化要求人民自律向善,一方面通过礼乐文化陶冶情操,从而达到修身养性的境界。
梁漱溟对于科学与哲学的划分,进一步证明了哲学特有的价值,从而为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科学和东方文化为代表的儒学相遇如何化解冲突提供了理论支撑。近代的中国科学不发达,背后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他进一步通过“文化三路向”的比较分析,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
三、以儒学的复兴化解西方科学弊端
梁漱溟虽然对科学与哲学做出了区分,但是却肯定了古代儒家文化中蕴含着科学的思想。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他在“人类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是“开化最早”,虽然科学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没有进步,但是中国文化“所走之路不十分反科学”。[6]203这里说明了,科学没有取得进步,是历史积累的多方原因造成的,中国文化本身不是完全排斥科学的,换言之,中国儒家文化本身与科学是有着相容的可能一面。科学在中国很早“曾有萌芽茁露”,后来不见科学的进步,是因为科学的“萎缩荒废”,中国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而是永远不能进步到科学了”。[5]48这里明显看出梁漱溟的态度,儒家文化在过去虽然没有孕育出科学,但是至于未来能否发展出科学也未有定论。
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影响至深。柏格森认为生命进化的特征是多样变化的。他将生命进化的过程生动地比作成炮弹爆炸的过程,他称,生命进化好像“炮筒里射出的炮弹”,生命运动恰似“一颗炮弹突然之间炸裂成了碎片”,而“这些碎片本身也是炮弹,”它们又炸裂成碎片分散开来,“如此继续”“经历了无比漫长的时光”。[7]88梁漱溟将其生命多样性的理论运动到了文化问题思考之中,从而引发了世界文化的三路向的解读。
重视易的生生思想。梁漱溟将柏格森生命哲学融入到了儒学之中,因此他对孔子的学说解读不离“生”字。他认为孔子人生哲学之源是“生生之谓易”的思想。由“生”字可以知道所有孔子生命哲学的真谛。他列举了孔子有关“生之赞美”的语句,天地之间的大德就是“生”,“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种大美是“生”之道;“天下至诚”能“尽其性”,人若能像万物一样能够“尽其性”,则可以辅助“天地之化育”,与天地一起造化万物;作为圣人之道就是仿效天地变化,遵循天地发育万物之理,顺其自然,“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4]117由此看出,孔子生命哲学不是所谓纲常礼教的规范,而是与天地相契合的生生不息之道。
在文化三路向说中比较说明各种文化的优劣所在。梁漱溟称文化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要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就应该分析“文化的根源的意欲”[4]31。他的这一论说,为文化的不同路向划分提供了合理性的解说。他认为,人类有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4]57-58,西方、中国和印度三种文化分别对应上述三类生活,因此,他们的文化走向特征分别是意欲“向前要求”“自为调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西方文化着力征服自然,侧重用理智研究外在世界,从自然科学兴起之后,一切科学化,结果是“有科学而无玄学”[4]37,中国文化着力内在修为,侧重用直觉研究内在生命,一切玄学化,结果“有玄学而无科学”,[4]37印度文化着力“厌生活”“求出世”[4]88,侧重用现量研究无生本体,一切宗教化,结果有宗教无科学。
肯定世界未来的文化趋势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认为,西方秉持“为我向前”人生态度,从而导致了西洋人饱受精神之苦,“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生了罅隙”,这种向外追求的人生导致生活受苦的境地,他们如今虽然外表生活富丽堂皇,但是内里生活枯燥乏味,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生命哲学便是“唯一的救星”。由于西方的生活将一切置于理智方法之下,一切都变成了可计算的物质,直觉可以改变这种理智带来的“逼狭严酷的干燥乏味”,而直觉正是中国哲学运用的方法。所以他得出结论,“现在的世界直觉将代理智而兴”[4]168,那么,“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4]187。换言之,世界未来文化也是儒学的复兴。
梁漱溟提出的世界未来文化是儒学复兴,一方面化解了科学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在深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叔本华的意志说的影响下,创建了文化三路向理论,并且通过三个文化的优劣对分,证明儒学复兴的合理性。他的文化理论看似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但是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四、评析
第一,梁漱溟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核心仍是儒学的弘扬。20世纪初,科学被泛化上升为一种主义,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在知识学术领域,趋向建立以科学为核心的霸权;在生活世界领域,科学“开始影响和支配人生观”,甚至触及到个体的存在;在社会政治领域,科学摄入到“各种形式的政治设计”。[8]152可以说科学无孔不入地扩展它的领地,从文化层面、生活世界和社会领域,无处不见它的身影,科学主义成了新的价值信仰权威,但是这种科学主义权威最终窒息了科学本身的自由宽容,反而成为了一种僵化的教条使其失去了科学性。科学作为一种方法,他不可能是万能的,他不可能解决包括精神现象在内的世间所有问题,这是有悖科学精神的。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科学主义负面影响逐渐凸显,从而推翻了科学万能论。科学本身就是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类带来福音,也会给人类造成灾难。
梁漱溟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和他所弘扬的儒家文化是分不开的。他称,“西洋人可怜”,因为要既要面对“物质的疲敝”,又想“精神的回复”,但是只依靠“希伯来那点东西”,找不到出路。而在当时中国,科学是作为反封建反专制的武器,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拥抱,梁漱溟在这样的环境下被迫为孔子正名。他表示,不应该谈到孔子时“羞涩不能出口”,应该大声疾呼要“做孔家生活”。[4]2-3并且他将儒学做了真假区分,孔子开创的“真儒学”因为后来传播中的歪曲篡改,失去了其中“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成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三纲五常“被诅咒为吃人礼教”,[9]312其原因就在于此。他的这种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思想,也是与他本人弘扬的新儒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第二,梁漱溟对于科学与哲学的区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某种程度上却忽略了两者的联系。由前所述,梁漱溟尤其强调了两者差异,甚至将其对立起来。他称科学和哲学分别运用的是理智和直觉认识世界。理智是“无私的,是静观的,自己不会动作而只是一个工具”[4]150,直觉是情志活动,“在直觉、情感作用盛的时候,理智就退伏;理智起了的时候,总是直觉、情感平下去,所以两者很有相违的倾向。”[4]123
梁漱溟强调了科学与哲学的区分而忽略了两者相同性,这与科学主义者重在两者相同性而忽略两者差异性截然不同。科学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王星拱认为,科学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哲学应该向科学靠拢,才能立足。他称,科学一日千里的变化,似乎将属于哲学的领域“侵略殆尽”,哲学是否“有其本身范围”,“还是一个问题”。[10]210他进一步指出,哲学要和科学一样,都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哲学“具有科学的精神,方能成为哲学”。[10]231
科学与哲学隶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梁漱溟过分强调了两者的区别,而不承认两者的联系,王星拱片面强调了两者联系,将哲学的一切归入科学的范畴,而忽略了两者差别,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合理的。
第三,梁漱溟“意欲”概念是其文化哲学的核心,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思考,但是其过分夸大了意识的反作用,否定物质决定意识作用。他的文化三路向说的提出,有个核心的概念——意欲。他认为,文化的根源在意欲,意欲决定生活,那么自然形成了生活决定文化这样的逻辑思路。他的这种唯意志论的文化观深受叔本华和柏格森的影响。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处与叔本华的意欲“略相近”。[4]31叔本华的这种意志是世界的本体,宇宙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意志的产物,但是意志本身的盲目性造成了无止境的追求。叔本华的理论被柏格森称作自由地创造意志,“生命冲动”造成了宇宙万物的进化,所以生物的进化也被解释为意志的创造。
梁漱溟的这一解释,忽略了人类是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万物,文化也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这一方面。他的“意欲决定观”受到早期共产党人杨明斋的批评,他引用了梁漱溟一段佛未出家遇到人生问题的论说,来说明意欲是受物质和自然现象的支配,来反驳梁漱溟的“文化意志论”。证明意欲“不是产生文化的本因”,它只是人类生理在“神经系上的一种表现”,[11]9人类生活的根本在物质,物质作为文化产生的原因中,地理经济为主,其次是教育和民族的遇合。杨明斋是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观的基础之上,体现了鲜明的唯物主义的立场。
第四,在对待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上,仍旧是“中体西用”的翻版,这和他文化理论本身是矛盾的。他在提出印度、西方和中国文化的文化三路向时,明确表达了对待这三种文化的态度,对待印度文化是“排斥”“不能容留”,对待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却“根本改过”,对待中国文化是拿出“中国原来态度”。[4]189-190他举例说明了印度文化的不足取,同时对于西方文化他采取的是引进其利,拒斥其弊,而中国原来的态度就是儒家的“安分、知足、寡欲、摄命”[4]67的态度,重返宋明朝“讲学之风”,以孔颜乐处的人生态度排解青年的困惑与苦闷,只有如此,才能让缺乏生机“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4]199而这正是吸收融和西方科学和民主两种精神下的各种思潮的结果。
梁漱溟对五四时期活跃在思想界的两种文化论调,他是持以反对态度的。这两种文化论调,一是《东方杂志》为主要阵地,杜亚泉、章士钊为代表的“中西文化调和论”,他们主张中西文化各有优劣,西方物质文明发达,而中国精神文明充裕,中国文化可以“一面开新,一面复旧”;一是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要代表,他们反对儒学和封建礼教,提倡西方民主和科学,主张向西方学习,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批判改造中国文化甚至将取而代之。对于前者,梁漱溟称,根本精神不同的两种文化是无法调和的,文化虽有方向不同,但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这样不存在“调和两偏而得其适中”[4]187的新文化。而对于后者,梁漱溟称,他没有给出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也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因为“无根的水不能成河”[4]192,“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4]199,中国才有新文化。
由此看出,梁漱溟一方面指出了中西文化属于两种精神,据此指出中西文化不能调和,而另一方面又表明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融合和儒家的态度,这就没有逃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这也说明了在五四时期中西两种文化冲突背景之下,心系中国文化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他反对科学主义,但是并不反对科学精神;他认为儒学在未来与科学又融合的可能,但是并没有提出合理的融合方案。最后他在文化三路向理论下,通过三种文化的比较,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可以看出,梁漱溟科学观中正是体现了他坚守着儒家本位和呼吁儒学的复兴的立场,从而也被后世称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