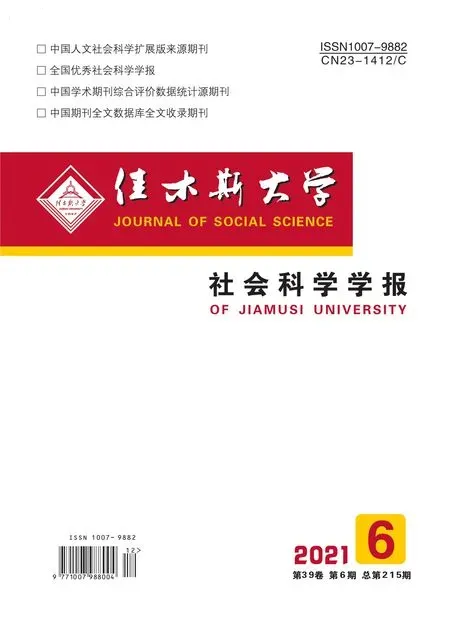老子“慈”义哲学内涵管窥*
李福龙
(西藏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一、研究评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评述
老子的“慈”上承“道”而下接“德”,体现着老子哲学精神的内涵,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但是,对于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中的“我”,即“慈”的主语则存在不同地理解。与此对应,对于“慈”的内涵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汉代的河上公开启了注解《道德经》的先河。他认为,第六十七章中的“我”指的就是君主,而作为“三宝”之首的“慈”的含义是“慈爱”:“爱百姓若赤子”[1],他认为“慈”体现为君主对百姓的慈仁与宽爱。现代学者陈鼓应先生则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来释“慈”,他认为老子因处于战乱的年代,看到战乱爆发的原因:“慈心”的缺乏。所以,老子提倡人们要“慈”:“爱心加上同情感。”[2]刘笑敢先生对“我”有不同身份的鉴定,他认为“慈”是圣人的一种境界:“一方面,‘慈’是圣人对天下的悲悯之怀,另一方面圣人之慈之深到了单向而不求回报的境地。”[3]而计春华则认为“我”至少有两个身份:“‘复守其母’——‘慈’之性、‘圣人常无心’——‘慈’之心。”[4]李振纲则侧重于政治方面地解读:“‘慈’作为一种本真自然的情感,有慈柔、慈政、慈战诸义。”[5]张松如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慈”是“‘道’的原则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具体运用。”[6]任继愈则有不同的理解,他把“慈”释为“慈柔”。但他认为“慈柔”是一种消极退让。他说:“老子对待当时剧烈大变革的态度,主张退守以自保,而反对任何作为。”[7]
(二)问题的提出
“三宝”与老子的“道”和“德”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承接关系,正如熊铁基所言:“‘三宝’是《老子》六十七章的主题,也是《老子》之学的主要意旨,几乎《老子》的每一篇都能见到此意,成为践行大道的具体和主要的内容。”[8]所以,对于“三宝”的正确把握有助于理解《道德经》全文的思想主旨。同时,对于“三宝”的诠释也要通过与其它章节之间地相互印证,从而使各个章节之间呈现“一贯”的解释关系。
如上所述,把“我有三宝”中的“我”,即“慈”的主语鉴定为统治者、父母、圣人等特定身份,则会存在如下问题:其一,正如《礼记·大学》所言:“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9]“慈”是一种“上对下”的特殊对待关系,而这种“上”的特定身份并非生来就有。即是说,在转换为“上”的特定身份之前,其本身就是“下”的特定身份。因此,不可能随着身份地转变就持有“慈”这一宝,如何随着身份的转变而同时拥有“慈”,这是一个待解释的问题。其二,把“我”解释成君主、父母等特定身份,则限制了“得道者”的范围。依照《道德经》全文的思想主旨,与父母和君主相对应的子女和臣民同样有“得道”的可能性。其三,不同身份之间地混淆。正如上文中所言,把“我”同时界定为“母”和“圣人”这两种或多种特定身份,但这些不同身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父母可以是圣人,而圣人并不局限于父母这一特定的身份范围。其四,主语和宾语、应然和实然关系的混淆。主语是“我”,宾语是“三宝”,谓语是“有”,这是一种实然的状态。而陈鼓应先生则曲解了这层关系,把实然的“有”解释成应然的“希望”。
把“我”解释成父母、君主和圣人等这些特定身份,则必然把“慈”的主要内涵界定为“慈爱”和“慈政”。这种鉴定至少会存在如下困境:其一,从正反面来讲,使“慈”失去了辩证的本质,无法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10]7(以下章次,如无特殊说明,原文皆引王弼版,只注明章节)等章节和字句之间形成良好的一贯解释关系。其二,从内外关系来看,无法解释第六十七章的“慈,固能勇”,对内施行“慈政”与对外战争的胜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性。其三,从全文词义关联来议,词义互训不通。老子在第六十九章中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此章是除第六十七章外,唯一谈到“宝”的相关章节,从词句文义来看,“慈爱”与“轻敌”词义相甚殊远。其四,缩小了解释范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从本质上看,“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因。换而言之,“道”指向的范围是万事万物,“慈”的范围亦应对应着万事万物,而不能仅局限于“政治”和“伦理”。
综上所述,“我有三宝”之中的“我”指的是老子本人,从更宽泛的层面来讲,指的是第十五章中的“善为士者”,即得道者。但是,此处的“我”不能解释为圣人,因为从全文的思想主旨来看,圣人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而且得道者的身份是承“道”而来,而不是依据特定的伦理身份。“慈”,从本质上来讲,是“负阴而抱阳”(四十二章)充满辩证色彩的“慈”;从范围上看,是站在天地的视角——超越特殊的伦理身份“以万物为刍狗”(第五章)的“慈”。
二、“慈”之要,在于“寻道”
《道德经》第六十七章说:“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此章具体阐述了“我道”大的原因,即“得道之人”拥有什么样的特质,其中的“慈”尤为关键。
《说文解字》释“慈”:“爱也。从心兹声。疾之切。”[11]由此可知,“慈”的基本含义是“慈爱”。历来解读者,也大多认为老子所说的“慈”即是“慈爱”。作为三宝之首的“慈”是不同于儒家所提倡的“慈爱”观点。首先,“慈”的对象不同。“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9]在儒家看来,“慈”是父母对子女表达爱的方式,而且应把“爱”做到极致,所以此处用一个“止”字来表达此程度。老子的“慈”是承“道”而来,“道”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道”本身是一个变动的东西,所以,“慈”不是对固定事物状态地描述,它是应接所有事物的一种心境和态度。其次,“慈”的根基不同。儒家认为,父子之间应正其名分,作为父母应该去慈爱子女,这种爱的根基在于承认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一致性,即儒家的“慈”以人性论作为前提。老子不言先天的心性,直接把人的生命概括成三个不同的状况。他说:“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第五十章)。为什么有人会“生”?而为什么有人会“动之于死地”?在老子看来,其关键是在于能否对“道”有正确地把握。最后,“慈”的目的不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0]312儒学作为一种道德哲学,孟子的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儒学为学的宗旨,体现了整个儒学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道家的入路不是道德意识的,因此工夫与儒家不同,但仍有修道的工夫。”[12]“慈”就是最重要的修道工夫,其目的在于追求并践行“道”。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老子的“慈”是不同于儒家提倡的“慈爱”观点。“慈”是“寻道”的一种方法,其目的在于“得道”。万物的产生都要追根于“道”,既然“道”是万物最初的根源,那为何还需要有个“求道”的过程?北宋理学家张载主张体用一源的“气”学说,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批评老子之学具有体用殊绝的弊端,他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13]张载站在自己的哲学立场来批判老子的生成观,这显然偏离了老子思想的原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老子认为,可以被言说的事物,其生命具有有限性。所以,作为万物本源的“道”,它只能以“无形”和“无名”的方式存在。老子在阐述“道”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时说:“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道”作为万物之始,但万物并非都能体现出“道”的精神。因为对“道”而言,万物的存在具有平等性。王弼把这种平等性概括为:“不塞其原也。不禁其性也。”[10]26换而言之,“道”创生万物,但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十章)。即是说,“道”生万物,但却不主宰万物,让万物自由地生长。许多综合因素促使万物生长和成形,具体有:“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第五十一章)。即是说,万物最初是由“道”而来,但“道”的伟大之处在于赋予万物自身的“德”,万物因“德”而有其形,其形在环境中孕育、成长。由于“道”的不主宰性和环境的塑造性,使万物与“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想要弥补这种差距,就必须要提高个人的主观意识,这是求“道”者必须要有的认知。
“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另一方面在事物的运行过程中显现出来,即所谓的“规律”。事物虽然有规律可循,但事物总是处在变化之中。那么,如何才能掌握处于变动状态中的“道”呢?老子认为,事物处在变动之中,但人心不能随物而动。寻道者必须以静制动,从而使自己处于主动的位置。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第十六章)。事物虽然处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的状态之中,但是运动中有其“常道”。把握住“常道”就可以顺应着“道”;不知事物运行的“常道”,就会使自己陷入凶险的局面之中。此处老子也解释了为什么“生之徒十有三”和“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其根本原因在于躁动而失道。
三、“慈”之功,要在“能勇”
“道”具有至高无上性,而“慈”是寻“道”的首要心境。有了“慈”再“勤而行之”(第四十一章),就能使自身的行为合乎于“道”;自身行为合乎于“道”,便会同于“道”;同于“道”,自然就会“勇”。老子在第六十七章中说:“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所言之“天”超越了人格神意义上的“天”,此处的“天”指代客观规律。即是说,持有“慈”,就可以认识万物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规律就可以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变动。能在现实中顺应“道”,这就是“勇”。“勇”必须以“慈”作为前提条件。它是指在拥有“虚静慈柔”的心境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淡定与从容的态势。而与之相对比的就是舍去“慈”而表现出来的“勇”,这种“勇”的结果就是“死焉”。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第七十三章)。此处老子并不是教人退缩和胆怯,恰恰相反,这其中蕴含着智慧与力量。
“慈,故能勇。”而什么才能算得上是“勇”?现实世界中又有什么事物能体现出“慈”的特质和表现出“慈”的效果——“勇”呢?老子纵观天下万物,认为水,牝和婴儿具备了真正的“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天下生命事物的孕育和成长都离不开水的滋养,但水仅只是辅助万物生长和发育,而不借机去主宰万物;辅助万物有成,却不与万物争抢功劳,使自己处在最低下的位置。水处在最低下的位置,这是由水的柔弱性所决定。水经常以柔弱的状态存在,但“水”的“柔弱”并不是软弱无力,“‘柔弱’是力量的柔性使用;老子提出的‘柔’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柔实力。”[14]“水”的柔弱之性中还带有刚健的能量,这种能量足够可以攻破任何的阻碍。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第七十八章)。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和水相抗衡,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水的性质。但并不是所有的“水”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显然,一两滴水是不可能具有“虚静慈柔”的态势,更不可能具备“攻坚强者”的实力。“勇”是一个动和静的结合体。有动才能体现出“勇”的动力和活力,而处静才能够畜积动能。老子在第六十六章中更是近一步指出,所谓的“水”就是“江海”。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是创生万物的原初动力,万物因“道”而始成性和成形。因为这种创生作用具有无形和无名的特点,而且“道”创生万物却不主宰万物,所以“道”创生万物之后,生命如何传递和接替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老子认为,无形的“道”创生有形的万物,而在“道”产生万物之后,就由万物自己去延续自身的生命。能被感知的事物,其生命具有有限性。如何使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的存在?其中的关键在于生命的接替和传承。在延续生命的过程中,“牝”扮演了这个关键的角色。“牝”不仅在生命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牝”有“虚静慈柔”的能力,这种能力蕴含着巨大能量,能产生效果。老子说:“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第六十一章)。即是说,“牡”惑于贪欲,因而有躁动之性。躁动就会降低自己的行动能力和判断能力。而“牝”具有虚静慈柔的能力,所以它能胜过“牡”。
由无形的“道”转向有形的“牝”的生物过程,“道”的作用是创始,而“牝”则发挥了传承生命的功能。对人而言,生命的初始状态即是婴儿,由于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受到外部坏境的干扰,所以婴儿的生命也具有“慈”的特质。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峰虿虺蛇不螫,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五十五章)。婴儿意念柔慈,所以自身能表现出“勇”的特质。婴儿的“勇”表现在对外和对内两方面。首先,婴儿对外部环境有极强的适应性,老子认为即使是面对毒性最强的毒虫和毒蛇,它们也不会去螫婴儿;即使是遇到攻击能力最强的猛兽和攫鸟,它们也不会给婴儿造成伤害。其次,婴儿对自身身体有极强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来源于自身身体和精神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婴儿自身骨骼和筋脉柔软,却能把东西抓牢固;还不知道男女之事,但男性特征表现十足;婴儿整天哭泣,但声音却不会沙哑,老子认为这是婴儿和气充足的缘故。概而言之,由于婴儿自身能够“专气致柔”,所以能表现出对自身和外部环境的超强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就是“勇”在婴儿身上的具体表现。
四、“慈”之用,体现“无为”
老子在《道德经》里,共有三章提到“慈”,其具章节和内容如下:
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从这三章提到的“慈”来看,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原文出现的是“孝慈”,而第六十七章出现的是“慈”。但从全文的思想主旨来看,这三章的重心均不在谈论“孝慈”问题,而是在谈“有为”和“无为”的问题。“有为”指的是“不自然”和“不真”。“无为”指的是“顺道”和“真实”。第十八章即是说,在一个六亲和睦的状态下,“孝”和“慈”就会得到自然地彰显,它不需要去刻意地提倡;只有在亲戚间不和睦的时候,才有提倡“孝慈”的必要性。此时需要劝子女做到“孝”和劝说父母做到“慈”。而这种提倡的行为,从侧面反映出此时既没有真实的“孝”,也不存在实质性的“慈”。概而言之,只有在“无为”的状态下,“孝慈”才会有实质的内涵。第十九章更是进一步指出,倡导“仁”和“义”的这种“有为”方式,最终会出现假“孝慈”。所以,绝弃“仁义”,真正的“孝慈”才会显现出来。由此可知,老子认为只有在“静”的状态下,才会凸显出“孝慈”的本质。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均从反面来论述“孝慈”,而第六十七章从正面来论述“慈”。老子为什么以辩证的方式来谈“孝慈”?其用意在于以伦理范围的“孝慈”凸显致“大道”层面的“慈”。第六十七章中的“慈”直接就是承“道”而来的“宝”,体现着“虚静慈柔”的辩证本质,其中有其实质性的内涵。“慈”包含了真正的孝慈,同时又是对“孝慈”的超越。由此可知,老子说“孝慈”旨在突出“道”本真的“慈”,“强调了道德之‘本’即内在德性本真对道德实践的根本作用,并揭示了老子反对‘舍本以逐末’以及由‘逐末’而导致道德虚伪的批判精神。”[15]
老子批判虚伪的道德精神,其要旨在于阐述真正的道德精神;道德精神以道德实质作为基础,道德实质以“慈”发用。老子的“慈”是观“道”的正确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再继而以持之不懈地努力就会“得道”。而“得道”之后就会形成自己的“慈”实力。拥有这种“慈”实力之后,老子提倡顺“道”而“无为”。为什么“慈”要如此地使用呢?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第四十二章)。从根本上讲,万物都是由“道”所生成,而“道”本身是有着阴阳一体的“和”气。“慈柔”方法就是依着“道”的“和”气而来。如果有势就妄为,就是刚强的表现,这种表现必然会丧失“和气”,而“和气”的丧失就是失“道”,失“道”的最终结果就是身危。所以,老子最后总结说:“强梁者不得其死”。
五、有无之境
“慈”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要义、贯穿于老子哲学的始终、体现着老子哲学精神的内涵。观“道”、得“道”和用“道”的三个阶段均离不开“慈”。老子的“道”是以恍惚的方式存在,所以它不可被定性。老子的“慈”是承“道”而来,所以它本身具有辩证的本质。这种本质可以被概括为:“有无之境”。观“道”之慈:“从无到有”。“道”是宇宙的本体,万物都是由“道”而生。但是,“道”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生育万物,而不把万物占为己有;让万物有作为,而不会自恃有功;使万物成长,但却不强加自己的意念。万物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能不能“得道”,关键在于万物自身。自然界本身具有“虚静慈柔”的能力,它处处体现着自然之道,所以老子说:“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而人有欲望,所以求道之人必须要法于“自然”,而且必须要通过学习,最终才能掌握客观事物中呈现出的“道”。持“道”必先志于“道”。由此可知,得“道”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法“自然”之“虚静慈柔”,再加上自己的行动而“得道”,“得道”之后就可以“用道”。用“道”之“慈”:“从有到无”。“得道”之后,自然就会转化成为一种硬实力,这就是看得见的“有”。老子形容说:“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万物都可以自化,这就是强大实力的表现。但是,即使有强大的实力,也必须要保持“虚静慈柔”,不能去侵犯别人或是破坏它物。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三十章)由此可见,从得“道”到用“道”就是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概而言之,老子的“慈”即是“虚静柔慈”之意。“虚静”中有其实质内涵,“故能勇”;“勇”于“慈柔”与“无为”,故回归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