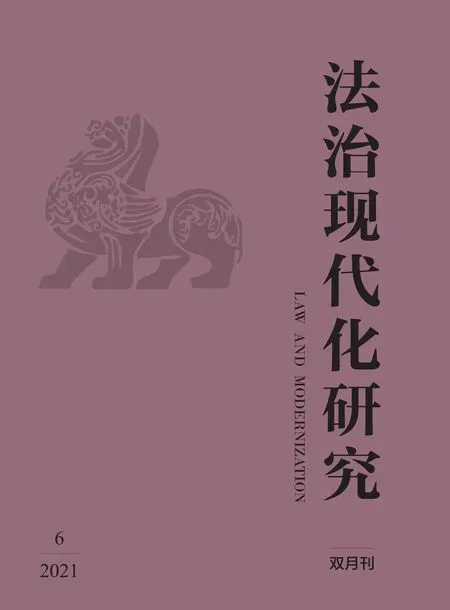论同时伤害的特例
[日]桥爪隆 著 王昭武 译
一、 引 言
日本《刑法》第207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暴力伤害他人的,在不能辨别各人暴力所造成的伤害的轻重或者不能辨认何人造成了伤害时,即便不是共同实行者,也依照共犯的规定处断”(“同时伤害的特例”)。该条规定的是,即便不能证明暴力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仍然有可能以伤害罪来处罚行为人,因而其合理性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1)平野龙一认为,该条规定存在违宪之嫌,参见平野龍一『刑法概説』(1977年)170頁。同样的观点,参见松宮孝明『刑法各論講義〔第4版〕』(2016年)44頁。但理论上未必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不过,日本最高裁判所最近就此规定作出了明确的判断,围绕该规定的相关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2)有关“同时伤害的特例”的最新研究,参见杉本一敏「同時傷害と共同正犯」『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9号(2011年)49頁以下;樋口亮介「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研修』809号(2015年)3頁以下;辰井聡子「同時傷害の特例について」『立教法務研究』9号(2016年)1頁以下;照沼亮介「同時傷害罪に関する近時の裁判例」『上智法学論集』59巻3号(2016年)73頁以下;豊田兼彦「暴行への途中関与と刑法207条」『浅田和茂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2016年)667頁以下;玄守道「刑法207条の研究」『浅田和茂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683頁以下;安田拓人「同時傷害の特例の存在根拠とその適用範囲について」『山中敬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下)』(2017年)81頁以下;大谷實「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を考える」『判例時報』2332号(2017年)3頁以下;日高義博「同時傷害の特例の法意および適用範囲」『判例時報』2332号(2017年)7頁以下;高橋則夫「『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の規範論的構造」長井圓先生古稀記念『刑事法学の未来』(2017年)1頁以下,等等。
鉴于此,本文以针对近年的判例的理解为中心,就同时伤害的特例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进行探讨。
二、 第207条之旨趣
(一) 举证责任倒置的第207条
例如,在X、Y作为共同正犯对A实施暴力致A受伤的场合,即便无法查明究竟是X还是Y的暴力行为造成了该伤害结果,X、Y也当然应该对所有伤害结果承担罪责。这样,作为共同正犯处罚的意义就在于扩张因果关系,其结果是,无须就犯罪结果与个别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举证。第207条之所以规定“依照共犯的规定处断”,其旨趣想必正在于此。亦即,在“二人以上实施暴力伤害他人的”场合,即便该伤害结果究竟是否是由行为人自己的暴力行为所引起这一点上并不明确的情形(“不能辨认何人造成了伤害时”),或者,虽然是由行为人本人的暴力行为引起了伤害结果,但无法确定自己的暴力行为所引起的伤害结果的范围或者程度的情形(“不能辨别各人暴力所造成的伤害的轻重”),也完全可以(就所有的伤害结果)以伤害罪处罚行为人。为此,通说认为,本条是就暴力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的因果关系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倒置。(3)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新版第4版増補版〕』(2015年)38頁;中森喜彦『刑法各論〔第4版〕』(2015年)18頁;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6版〕』(2012年)45頁;山中敬一『刑法各論〔第3版〕』(2015年)57頁;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6版〕』(2015年)30頁;高橋則夫『刑法各論〔第2版〕』(2014年)56頁;林幹人『刑法各論〔第2版〕』(2007年)55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49頁;伊東研祐『刑法講義各論』(2011年)41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2016年)65頁;佐久間修『刑法各論〔第2版〕』(2012年)42頁;橋本正博『刑法各論』(2017年)71頁。因此,如果行为人能够就自己的暴力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或者能够对与自己的暴力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伤害的范围进行举证),就可以排除第207条之适用。
一般认为,尽管本条采取的是“依照共犯的规定处断”这种表述,但这只是意味着遵从共同正犯中的因果关系的判断,而非直接肯定成立共同正犯。(4)指出这一点者,参见日高義博「同時傷害の特例の法意および適用範囲」『判例時報』2332号(2017年)8頁。不过,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本条也包含着推定存在共犯关系(意思联络)的旨趣,因而,(1) 除了能够举证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之外;(2) 对于能够举证不存在共犯关系的情形,也应该排除第207条之适用。(5)持这种理解者,参见齋藤信治『刑法各論〔第4版〕』(2014年)25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61頁。另外,有学者则将第207条理解为,承认无意思联络之共同正犯的特别规定,参见玄守道「刑法207条の研究」『浅田和茂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707頁。这种观点试图限制本条的适用范围,应该是基于一种正确的问题意识。然而,本条规定的是“即便不是共同实行者,也依照共犯的规定处断”,显然,对此只能理解为,即便是明显不存在共犯关系的情形,也仍然可以适用。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被认定不存在共犯关系的情形,也当然适用本条规定。(6)关于这一点,参见杉本一敏「同時傷害と共同正犯」『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9号(2011年)55頁;樋口亮介「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研修』809号(2015年)7頁。另外,学界也有观点主张,本条之旨趣在于“共犯关系的拟制”,参见西原春夫「判批」『判例タイムズ』254号〔1971年〕88頁。不过,如果该观点“拟制”共犯关系的目的仅仅在于,对不允许反证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基于因果关系之推定而得出结论进行解释,那么,其实质上与因果关系推定说并无不同。
这样,通说观点一直认为,本条规定的是暴力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因此,例如,X与Y在相互之间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均对A实施了暴力行为,对A造成了伤害,但难以确定具体究竟是X的行为还是Y的行为对A造成了伤害,对此情形适用第207条的结果是,X与Y中的某一人尽管与伤害结果的发生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由于其无法证明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最终就被处以伤害罪。这样的话,显然难以否定,这种结论是与“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利益原则)相抵触的。
(二) 第207条是否是加重暴行罪
正是出于对通说的这种疑问,近年来,学界展开了这样的研究:不是将第207条理解为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而是试图认定符合该条的暴力行为具有实质的违法性。将该条所规定的暴力定位于加重暴行罪的观点,就是其中的典型学说。例如,辰井聪子教授认为,由复数行为人实施的暴力的同时犯,由于各人的暴力具有很容易将事态升级而引发重大伤害结果的危险,因而本条加重了暴行罪的刑罚,以与伤害罪相同的法定刑予以处罚。(7)参见辰井聡子「同時傷害の特例について」『立教法務研究』9号(2016年)12頁以下。正如辰井聪子教授所言,对于那些客观上处于危险状况之下的暴力行为,该行为无论是否引起了伤害结果,均予以加重处罚,作为立法论来说,是完全存在探讨的余地的。但是,作为解释论而言,如果将本条理解为加重暴行罪,那么,即便已经明确行为人的暴力与伤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对此类情形不作为加重暴行罪适用本条,就不存在理论上的一贯性。在本文看来,仅凭加重暴行罪这种理解,尚难以合理解释,为何本条的适用对象仅限于难以确定暴力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8)进一步而言,由于加重暴行罪是以客观上处于危险状况之下的暴力行为作为实行行为,因而,作为其故意,就势必要求对危险状况存在认识,这样一来,就有极大地限制该条适用范围之虞。关于这一点,参见高橋則夫「『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の規範論的構造」長井圓先生古稀記念『刑事法学の未来』(2017年)10頁以下。
对此,樋口亮介试图从下面这两点找到第207条固有的违法性:(1) 在很容易反复实施严重或者性质恶劣的暴力行为的状况之下实施了暴力行为;(2) 由该暴力行为引起了难以证明伤害之原因的事态,对此难以进行适当的处罚。(9)参见樋口亮介「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研修』809号(2015年)10頁以下。这种观点是在将第207条之暴行罪理解为加重暴行罪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将伤害原因变得不明确这一点本身作为本罪之违法内容,从而成功地将“不能证明暴力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事实纳入本罪的构成要件。不过,第(2)点的视角意味着,将本罪定位于(不仅仅是针对身体的犯罪)一种针对司法的犯罪,然而,对原本属于伤害罪之特例的第207条做这样的理解,究竟是否合适,就不无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并且,按照这种观点,“因果关系不明确”属于构成要件的内容,(10)关于这一点,参见樋口亮介「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研修』809号(2015年)10頁。那么,在本文看来,对于这一事实,就要求能够举证达到了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11)另有观点尽管与“樋口说”前提不同,但主张就因果关系不明确这一点(其中任何一种暴力行为都有引起伤害结果的盖然性),检察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参见仲家暢彦「同時犯」石川弘=松本時夫編『刑事裁判実務大系⑼身体的刑法犯』(1992年)267頁。但本条的适用对象终究是那些不能证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而且,“因果关系的不明确得到了证明”难道不就是“无法证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吗?
将本条理解为加重暴行罪,明确了第207条的实质性处罚根据,对此应该予以高度评价,但作为对现行法的解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为此,作为对第207条的解释,就不得不遵循通说观点,将其理解为有关因果关系之推定的规定。当然,像第207条那样设立利益原则的例外,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仍有质疑的余地,(12)从程序法的角度对此规定的研究,参见三井誠『刑事手続法Ⅲ』(2004年)80頁以下,酒巻匡『刑事訴訟法』(2015年)481頁。但作为立法论而言,还是应该研究如何对本条进行修正,增设对一定危险状况之下的暴力行为予以加重处罚的规定。然而,现行刑法存在第207条之规定,这是客观事实;并且,只要没有认定,该条规定因违宪而无效、被排除适用,那么,作为解释论来说,就应该充分意识到本条只是一种例外规定,在对其用语进行解释时,应严格地限制其适用范围。(13)持这种问题意识者,参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50頁;小林憲太郎「判批」『判例評論』699号〔『判例時報』2323号〕(2017年)26頁。
三、 对最高裁判所平成28年判例的探讨
(一) 案件事实
对第207条的解释而言,最高裁判所在平成28年(2016年)作出的决定(下称“最高裁判所平成28年判例”)(14)参见最決平成28·3·24刑集70巻3号349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想首先确认该决定的判决逻辑。
该案的案件事实大致如下:
位于本案建筑物4楼的某个酒吧是本案案发现场,被告人A、B是该酒吧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工作。被告人C此前曾作为客人来店消费,案发当日也以客人身份在店内就餐。被害人X于当日凌晨4时30分许来到该店,在店内就餐之后,在结账时因用信用卡结账引发争执,随后表现出焦躁的样子,在尚未支付部分餐费的情况下走出店外。A、B紧随其后追至店外,在4楼电梯口追上X,二人经过共谋,在早晨6时50分许至7时15分许,对X实施了暴力行为(第一次暴力)。具体而言,A在4楼电梯间脚踢X的背部,使其摔倒在楼梯转角附近,并且,在X进入电梯之后,又将其面部撞向电梯护板,并将其拽至建筑物的电梯间;B将X的头部撞向放置在电梯间的立式烟灰缸;而且,A还用拳头与烟灰缸的盖子击打仰面倒地的X的面部,还将X的面部与头部撞向地面,B也脚踢X身体,并骑在X身上进行殴打。
C于早晨7时4分许出现在4楼电梯间,看到酒吧工作人员D正试图阻止A、B,但在D与A离开X身边之后,C马上脚踩倒在地上的X的背部等部位,被B制止之后返回了该酒吧。此后,C再次出现在4楼电梯间,旁观A与B脚踢X的情形,并于早晨7时15分左右,实施了脚踢躺在地上的X的背部等暴力行为。
此后,A拿走了X的驾驶证,并将其带回酒吧,让其写下了愿意支付餐费这一旨趣的协商书。其后,A、B继续在店内工作,C也继续在店内就餐。X在酒吧大门附近的地上瘫坐了一会后,于晚上7时49分许,突然走出店外。D马上去追,在本案建筑物的楼梯处追上并抓住了X。晚上7时50分许,C为了打电话,来到本案建筑物的4楼电梯间,得知D正试图阻止X逃走,遂走向D抓住X的现场。并且,直至晚上7时54分许,C又对X实施了下述暴力行为(第二次暴力):C扶住楼梯的两边把手,将自己的身体腾空提起来,踩住处于睡姿的X的面部、头部、胸部,并且,像踢足球那样,几次踢打X的头部、腹部等部位,踢打已经开始打呼噜的X的面部。
此后,X因急性硬膜下血肿引起的急性脑肿胀而死亡。第一次暴力与第二次暴力均有可能导致X的急性硬膜下血肿这一伤害结果,但无法查明究竟是哪一次暴力引起了X的这一伤害结果。
检方通过适用第207条,以伤害致死罪起诉A、B、C三人。一审判决认为,(15)参见名古屋地判平成26·9·19刑集70巻3号26頁。即便是因第一次暴力引起了X的急性硬膜下血肿这一伤害结果,“也能够推定,第二次暴力更加恶化了该伤害结果,因此,无论怎样,都能认定第二次暴力与X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就缺少适用同时伤害致死罪之规定(《刑法》第207条)的前提,该规定原本是为了避免出现对于致死这一结果无人承担责任这种不适当的情况而作出的特例”,并以此为理由,否定适用第207条,在判定C成立伤害致死罪的基础上,判定A、B仅成立伤害罪。(16)另外,作为判决书的“旁论”,对于第一次暴力与第二次暴力能够被谓为同一机会之下,该判决还判定,A、B在实施第一次暴力之后,他们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能认定他们对C会实施第二次暴力存在预见,因此,两次暴力不能被视为同一机会之下所实施的暴力。相反,控诉审(二审)则判定,(17)参见名古屋高判平成27·4·16刑集70巻3号34頁。一审判决重视的是,不管怎样,第二次暴力均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一审判决“不探讨与实际发生的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直接研究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可以被认为,违反了以暴力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作为要件的《刑法》第207条所规定的内容。这样理解的话,(一审判决)就没有看到,在本案中,出现了对于急性硬膜下血肿这一伤害结果的发生,最终谁也没有被追究责任这一结果”,进而以此为理由,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二) 最高裁判所平成28年判例之决定要旨
最高裁判所最终驳回被告人的上告,并依职权作出了下述判决:“规定了同时伤害的特例的《刑法》第207条的做法是,鉴于在二人以上实施暴力的案件中,很多时候难以特定属于引起伤害结果之原因的暴力,因而,即便无法举证存在共犯关系,也例外地按照共犯来处罚。作为适用该条的前提,应该要求检察官证明各个暴力行为均具有引起该伤害结果的危险性,以及各个暴力行为是在能够被评价为外形上等同于共同实行的状况之下实施,亦即,(各个暴力行为)是在同一机会之下实施。在(检察官)进行了这种证明的场合,各个行为人只要不能举证,自己参与的暴力行为没有引起该伤害结果,就应该说,其不能避免承担针对伤害的责任。并且,在由不处于共犯关系的二人以上的暴力引起了伤害,并且由该伤害进一步引发了死亡结果这种伤害致死的案件中,如果属于《刑法》第207条之适用前提的上述事实关系得到了证明,那么,只要不能举证自己参与的暴力没有引起属于死因的伤害,根据该条,各个行为人就应该对该伤害承担责任,并且,还应该对以该伤害为原因而发生的死亡结果也承担责任……在这种事实关系得到证明的场合,即便是像本案那样,能肯定其中的某一暴力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也没有进行其他解释的理由,因而也不应该妨碍该条的适用。原判决在作出了与上述内容相同旨趣的判断之后,有关第一次暴力与第二次暴力的机会的同一性,要求(一审)在针对其意义等进行适当理解之后,尽力进行进一步的审理与评议,并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一审,这是适当的。”
(三) 本决定的意义
1. 第207条的旨趣
本决定并未就第207条之旨趣作出具体的判断,只是判定,在检察官证明了一定事实关系的场合,“各个行为人只要不能举证,自己参与的暴力行为没有引起该伤害结果,那么,就应该说,不能避免承担针对伤害的责任”,由于对暴力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被告人就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因而可以说,该决定接近于通说观点,即认为本条是有关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不过,该决定认为,针对检察官的“证明”,被告人只要“举证”(不存在因果关系)即可,这里刻意地使用了不同的表述,因此,也许还可以这样理解:对于被告人一方的反证,不要求达到与检察官相同程度的证明责任。(18)不过,这样考虑的话,如何理解本决定所使用的“即便无法举证共犯关系(的情形)”这一表述,就会成为问题。
2. 第207条的适用要件
根据本决定,检察官需要证明:(1) “各个暴力行为均具有引起该伤害结果的危险性”;(2) “各个暴力行为是在能够被评价为外形上等同于共同实行的状况之下实施,亦即,(各个暴力行为)是在同一机会之下实施”。学界也一般要求具备这两个要件。(19)参见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6版〕』(2012年)46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50頁。可以说,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也作出了与学界一般观点相类似的判断。
其中,就第(1)个要件,想必不存在异议。为了可以推定暴力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以各个暴力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具有存在因果关系的盖然性为前提,因此,作为其归结,就必须能够认定各个暴力行为存在引起该伤害结果的危险性。就本案事实来说,既然对X造成了急性硬膜下血肿这种伤害,就需要能够证明,各个暴力行为伴有能够作用于X的脑部的有形力,并且,该有形力达到了足以引起属于急性硬膜下血肿之原因的重大脑部外伤。
对于第(2)个要件,即机会的同一性,学界也一般认为,应该要求具备该要件。不过,由于并不能直接从第207条的表述中推导出该要件,因此,基于什么根据,而且,在什么范围之内要求机会的同一性(同一机会性),就成为问题。关于这一点,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是出于必须存在“能够被评价为外形上等同于共同实行的状况”这一理解,而要求存在同一机会性。那么,问题在于,如何判断“能够被评价为外形上等同于共同实行的状况”?如果从字面含义来理解“能够被评价为外形上等同于共同实行的状况”,既然以能够被等同视为“共同实行”的状况为必要,那么,就仅限于在时间上或者地点上同时或者连续地实施了暴力的情形,才有适用本条之可能。不过,即便是成立共谋共同正犯的情形,由于被评价为“共同实行了犯罪”(《刑法》第60条),因此,也有可能这样理解:即使时间上或者地点上的连续性并不充分,但只要存在有可能被等同视为“基于共谋的共同实行”的外形即可。关于这一点,追溯至要求同一机会性的根据进行探讨,就不可或缺。
另外,本决定肯定的是,“原判决……有关第一次暴力行为与第二次暴力行为的机会的同一性,要求……尽力进行进一步的审理与评议,并撤销第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第一审”,因此,需要注意的是,最高裁判所并未就本案案件事实具体判断是否存在同一机会性。
3. 对伤害致死罪的适用
本决定明确表示,可以通过适用第207条,以伤害致死罪来处罚行为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最高裁判所昭和26年判例业已肯定,(20)参见最判昭和26·9·20刑集5巻10号1937頁。就伤害致死案件可以适用本条,但并未具体说明理由。(21)另外,该判决作为明示“成立伤害致死罪,止于以伤害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必要,不以对致死结果的预见为必要”的判例,也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本决定也难言显示了充分的理由,由于(1) 适用第207条的场合,行为人应对伤害承担责任;(2) 能够认定“由该伤害进一步引发了死亡结果”这一因果关系,因此,本决定也能评价为,本决定显示了对死亡结果也应承担责任的逻辑。亦即,这里的理解是,对“伤害”承担责任这一评价,已经包含着对“由伤害引起的死亡结果”也承担责任这一判断。
4. 能认定暴力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
本决定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即便能肯定其中的某一暴力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情形也有适用第207条之可能。如前所述,鉴于C实施的第二次暴力的严重性,一审判决认为,(1) 由第二次暴力造成了急性硬膜下血肿这种伤害结果的场合;(2) 即便是由A、B实施的第一次暴力已经引起了急性硬膜下血肿这种伤害结果,但第二次暴力显然会使之更加恶化的场合,无论是其中哪一种情形,都能认定第二次暴力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2)在本文看来,严格意义上讲,对于第(2)种情形,仅限于能够认定,是因急性硬膜下血肿恶化而提前了X的死期的场合,才能认定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本案不存在适用第207条的前提。原判决(二审判决)认为,第207条终究是以暴力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的情形作为其适用对象,因而不应该以暴力与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作为问题,进而以此为理由,撤销了一审判决。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虽然没有另外提出特别的理由,但肯定了原判决针对这一点的判断。
即便第207条适用于伤害致死罪,但那终究不过是,根据第207条,被告人对形成死因的伤害结果承担责任的自然归结而已。由于并不存在有关同时伤害致死的特别规则,因此,首先应该探讨是否对伤害结果适用第207条,而不应该跳级,直接探讨暴力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此意义上,原判决(二审判决)的逻辑是妥当的。不过,对于一审判决,也完全有可能这样理解:其不仅仅是探讨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探讨最终形成的急性硬膜下血肿这种伤害与第二次暴力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问题。亦即,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C实施的第二次暴力,要么引起了急性硬膜下血肿;要么恶化或者扩大了已经发生的急性硬膜下血肿,形成了最终的急性硬膜下血肿,因而是存在某种影响的。因此,一审判决的理解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已经对因果关系——由C的第二次暴力引起了最终形成的急性硬膜下血肿——进行了举证,因而不存在适用第207条的前提。如果这样理解一审判决的立场,即便X没有死亡,既然已经证明暴力行为与(最终发生的)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势必也应否定适用第207条。(23)指出这一点者,参见松尾誠紀「判批」『刑事法ジャーナル』49号(2016年)189頁;安田拓人「同時傷害の特例の存在根拠とその適用範囲について」『山中敬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下)』(2017年)83頁。
但是,这种解释也不妥当。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以与最终的伤害结果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是否适用第207条的问题,那么,先行行为人只要能够举证,“自己参与的暴力行为并未引起该最终形成的伤害结果”,就能够避免承担伤害的责任,因此,只要能够举证,后行行为人的暴力行为至少恶化或者扩大了当初的伤害即可,这样一来,就会明显限制第207条的适用范围。(24)关于这一点,参见松尾誠紀「判批」『刑事法ジャーナル』49号(2016年)190頁以下。不过,也许还可能存在这种的理解:既然探讨的是第207条的合理性,该条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毋宁说这是一种更为恰当的解释。并且,如果依照这种解释而排除本条的适用,最终的结果就是,作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为了在“并非自己引起了急性硬膜下血肿,而是恶化或者扩大了已经发生的急性硬膜下血肿”这种评价的限度内,让C承担伤害(致死)罪的罪责,那么,就会出现对于“已经发生(被认为已经发生)的急性硬膜下血肿”这种状况的发生本身,谁也不承担责任的事态。(25)相反,有观点认为,“如果重视第207条的例外性质,这一点就应该是甘愿接受的”。参见安田拓人「同時傷害の特例の存在根拠とその適用範囲について」『山中敬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下)』(2017年)96頁。当然,很多时候很难直接从急性硬膜下血肿的恶化或者扩大这一事实本身开始,将其认定为或者记述为“伤害结果”,因此,在那种场合,即便是以上述第(2)点的认定为前提,也不得不认定,C引起了最终形成的急性硬膜下血肿这种伤害结果。(26)否定成立伤害罪的承继的共同正犯的最高裁判所平成24年决定(最決平成24·11·6刑集66巻11号1281頁)被理解为,在因自己的暴力行为而恶化了业已发生的伤害的情形下,对于后行行为人,也是就作为整体的伤害,肯定成立共同正犯。关于这一点,参见石田寿一「判解」『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4年度)458頁以下。但是,那只是为了便于将伤害结果记述为犯罪事实而作了那样的认定,在上述第(2)种情形下,C的量刑责任还是应该在终究只是扩大或者恶化了业已发生的伤害这种评价的限度之内进行判断。但是,按照这种理解,谁也不对急性硬膜下血肿这种伤害的(起初的)形成本身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样考虑的话,即便第二次暴力与最终发生的伤害结果之间显然存在因果关系,但如果无法明确该伤害究竟由哪一暴力行为所引起,就应该认为,还是不能排除适用第207条的可能性。作为对该条用语的解释,只要未能明确究竟是哪一暴力才是形成伤害的原本的原因,就应该解释为,符合法条明文规定的“在不能辨认何人造成了伤害时”。
四、 第207条的适用范围
(一) 同一机会性的判断
1. 与共同正犯具有外形上的类似性
下面想基于对最高裁判所平成28年判例的分析,对于第207条的适用范围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首先需要研究的是同一机会性的判断。
如前所述,最高裁判所平成28年判例将同一机会性定位于“在能够被评价为外形上等同于共同实行的状况之下”。也许可以说,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正是因为第207条规定的是“即便不是共同实行者,也依照共犯的规定处断”,才要求即便不能认定相互之间存在共谋,但至少应该存在外形上能够被评价为共同正犯之实行的状况。
如果将这种理解更进一步,那么,在存在时间上或者地点上的接近性,存在类似于实行共同正犯之状况的场合自不必说,对于参与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人际关系,彼此认识到相互的存在,或者发展至暴力行为的动机存在共通性的情形,也有以存在类似于共谋共同正犯之外形的状况为理由,肯定适用第207条的余地。(27)像这样重视与共同正犯现象之间的类似性的观点,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新版第4版増補版〕』(2015年)35頁;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6版〕』(2012年)46頁;高橋則夫『刑法各論〔第2版〕』(2014年)57頁。例如,经营风俗店的X与该店董事Y,碰巧发现了拿走风俗店现金并隐匿踪迹的店铺原工作人员A,在对A实施暴力行为之后(第一次暴力),让其乘上汽车,开往X经营的风俗店,在达到店铺附近之后,得知情况的店长Z又对A实施了暴力(第二次暴力)。对于该案,东京高等裁判所平成20年判决(28)参见東京高判平成20·9·8判タ1303号309頁。首先否定Z与X、Y针对第二次暴力存在共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本案各个暴力行为“是A被置于三名被告人中的某人的支配之下的一系列的过程之下所实施的行为”;并且,三名被告人的暴力行为均是“以A的行动为契机的行为……其经过、动机也基本上是相同的”;Z对第一次暴力存在认识,且自己也实施了暴力;而且,X、Y也已经充分预见到Z会去责问A。为此,尽管第一次暴力与第二次暴力之间在时间上相差1小时20分左右,地点上相隔20公里左右,仍以“三名被告人的各个暴力行为能够被认定为,社会一般观念上在同一机会之下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为理由,判定适用第207条。由此可见,本案判决重视的是参与者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暴力行为的过程与动机的同一性、对其他参与者实施的暴力存在认识或者预见等情况,进而肯定了同一机会性。(29)关于这一点,参见中川深雪「判批」『警察学論集』63巻8号(2010年)175頁以下。可以说,即便不能认定存在共谋,如果能够推定存在共谋的相关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累计,那么,即便时间上或者地点上的连续性并不充分,也能认定存在同一机会性。(30)因此,有关是否存在共谋的间接事实,与有关(共谋被否定的场合的)暴力的同一机会性的间接事实,实际上是重合在一起的。指出这一观点者,参见森田邦郎「判批」『研修』728号(2009年)92頁。按照这种理解,对于参与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相互之间显然不存在共谋的案件,就需要对时间上或者地点上的连续性进行严格判断。例如,在饮食店内,客人相互之间发生冲突,X对A实施了暴力,大约40分钟之后,饮食店店主Y被横卧在店内通道的A的态度所激怒,将A拖出店外,并对其实施了暴力。对于该案,札幌高等裁判所昭和45年判决认为,(31)参见札幌高判昭和45·7·14高刑集23巻3号479頁。Y实施的暴力与X实施的暴力完全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且,X与Y之间“没有任何特别关系,彼此也没有实际认识到对方实施的暴力”,因而应否定适用第207条。(32)针对该裁判例(注意,不是“判例”——译者注)的分析,参见辰井聡子「同時傷害の特例について」『立教法務研究』9号(2016年)5頁以下;照沼亮介「同時傷害罪に関する近時の裁判例」『上智法学論集』59巻3号(2016年)74頁以下。
2. 若干探讨
首先从结论上讲,本文认为,这种重视与共同正犯之间的类似性的问题解决路径并不妥当。正如反复强调的那样,第207条规定的是,即便显然不存在共犯关系,也仍然有可能适用(“依照共犯的规定处断”),而非推定存在共犯关系。本条之所以规定“依照共犯的规定处断”,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技巧而已,其目的在于推导出这种结论:即便有可能是由其他参与者的暴力行为引起了伤害结果,仍然要将这种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因此,作为本条的适用要件,逻辑上就鲜有要求具备共同正犯类似性的必然性。(33)持这种理解者,参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51頁。另有观点虽然持这种理解,但同时认为,既然有必要对第207条的适用范围附加某种限制,那么,以本条的法律结构或者法律效果为线索,要求与共犯关系具有外形上的类似性,就具有一定合理性。参见杉本一敏「同時傷害と共同正犯」『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9号(2011年)56頁。而且,在实际的刑事判决中,就正如上述东京高等裁判所平成20年判决所显示的那样,很多时候,在对是否存在有关暴力的共谋存在争议的案件中,如果最终否定存在这种共谋,是否适用第207条就会成为问题,然而,如果作为第207条之适用要件,强调共同正犯类似性,那么,该条就难免会被当作否定存在共谋的界限案件的“兜底条款”而被广泛地适用。(34)指出这一点者,参见高橋則夫「『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の規範論的構造」長井圓先生古稀記念『刑事法学の未来』(2017年)17頁。
一般认为,在数人的暴力行为相互竞合的案件中,很多时候难以确定哪一暴力行为是造成伤害的原因,因而,(暂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合适)第207条原本是转换暴力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因此,同一机会性要件也应该被作为佐证暴力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极其困难的基础事实来理解。(35)持这种理解者,参见小林憲太郎「判批」『判例評論』699号〔『判例時報』2323号〕(2017年)26頁。亦即,正因为是在同一机会之下,数人的暴力行为发生竞合,要明确各个暴力行为的具体内容就极其困难,为此,就(好不容易)能够承认举证责任的转换具有一定合理性。这样,机会的同一性就应该被理解为,使个别的暴力行为的内容变得极难举证的一种外形上的状况。按照这种理解,原则上需要存在时间上或者地点上的接近性,不过,对于这种接近性不充分的情形,能够肯定机会的同一性的情形就应该被限于,由于暴力行为的参与者持续地支配着被害人,或者犯罪现场与外界是隔离的等情况,因而可以被谓为,第三者类型性地难以实际认识到犯罪行为状况的情形。(36)另外,也有学者分下面两种情形来论述机会的同一性:(1) 能否被评价为,属于一系列的暴力状况下的兴奋状态的一环(时间上或者地点上的接近性就成为重要的判断标准)?(2) 难免会继续实施暴力的不稳定状态、对被害人的支配状态,是否仍然在持续(人际关系、物理性环境就属于重要的判断因素)?参见樋口亮介「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研修』809号(2015年)10頁以下。如果从这种视角来看,在前述东京高等裁判所平成20年判决中,被告人一方的相关人员物理性地持续支配着被害人,与之相对,在前述札幌高等裁判所昭和45年判决中,被告人被扔在(谁都可以自由进出的)饮食店内长达40分钟,应该说,这是很重要的区别。相反,发展至暴力行为的过程、动机的同一性,则未必属于重要的视角。
(二) 对其他犯罪的适用可能性
1. 伤害致死罪
如前所述,对于伤害致死罪,判例也肯定具有适用第207条的可能性。学界虽然也有学者持肯定说,(37)参见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6版〕』(2015年)33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51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2016年)66頁;松宮孝明『刑法各論講義〔第4版〕』(2016年)44頁(认为肯定说也有一定合理性);高橋則夫『刑法各論〔第2版〕』(2014年)56頁(通过适用第60条,承认成立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但应该说,否定说属于更为有力的观点。(38)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新版第4版増補版〕』(2015年)36頁;中森喜彦『刑法各論〔第4版〕』(2015年)19頁;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6版〕』(2012年)47頁;山中敬一『刑法各論〔第3版〕』(2015年)63頁;橋本正博『刑法各論』(2017年)72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64頁。
第207条是仅限于伤害结果之归责的规定,因此,当然不能直接适用于死亡结果。但是,在因数名行为人的暴力行为引起了属于死因的伤害的场合,就完全有可能通过适用第207条,将该伤害归责于各个行为人(成立伤害罪)。并且,既然就伤害结果被归责,与该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后续结果(例如,伤害的扩大、后遗症等等),势必也应归责于行为人。在本文看来,按照这种逻辑,对于由伤害结果引起死亡结果的情形,就完全有可能通过适用第207条,以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为理由,认定成立伤害致死罪。
否定说重视的是,第207条仅仅只是一种例外规定,从而力图将其适用范围控制在成立伤害罪的限度之内,其问题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不管伤害程度如何,都可以适用第207条,因此,不可否认,对于因数人的暴力而给被害人造成了无法痊愈的、程度极其严重的伤害的情形,也可以通过适用本条,让所有参与者承担重大伤害的责任。如果考虑到,在重大伤害的延长线上会发生死亡结果,那么,通过适用第207条,对由伤害所引起的死亡结果进行归责,也不能说不妥当。事实上,要对伤害致死的案件适用本条,就要求能够举证,各人的暴力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达到能够引起属于死因之伤害的程度,因此,如果严格要求对此进行举证,想必不会过度扩大第207条的适用范围。
另外,第207条虽具有推定暴力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机能,但不具有推定伤害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机能。因此,例如,虽然能够确定X、Y的暴力行为各自形成了某种伤害,但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伤害成为最终的死因,对此就不能适用本条。最终还是应该限于,无法确定成为最终死因的伤害究竟是由X、Y中的谁的暴力行为所引起的情形,才可以适用第207条,X、Y由此承担伤害致死罪的罪责。
2. 其他犯罪类型
本文认为,即便能够像这样通过适用第207条而认定成立伤害致死罪,但不应该超出该范围,承认对抢劫致伤罪、强制性交等致伤罪也可以适用第207条。(39)否定适用于抢劫致伤罪的裁判例,参见東京地判昭和36·3·30判時264号35頁;否定适用于(刑法修正之前的)强奸致伤罪的裁判例,参见仙台高判昭和33·3·13高刑集11巻4号137頁。相反,也有观点承认,有适用于抢劫致伤罪、强制性交等致伤罪等犯罪的余地,参见樋口亮介「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研修』809号(2015年)16頁以下。的确,无法否认,此类情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数人的暴力行为相互竞合的结果是,难以确定被害人的伤害结果(甚至死亡结果)究竟是由谁的暴力行为所引起的。但是,第207条承认的是,成立作为暴行罪之结果加重犯的伤害罪,但抢劫致伤罪、强制性交等致伤罪中的被害人的死伤结果,则并不一定仅限于作为犯罪手段的暴力的加重结果。如果重视第207条终究只是一种例外规定,就应该认为,第207条之适用应限于伤害罪、伤害致死罪。(40)持这种理解者,参见渡辺恵一「同時傷害の特例」『研修』591号(1997年)83頁以下。
不过,由于抢劫罪与暴行罪处于法条竞合的关系,因此,在伤害罪的限度之内,存在适用第207条之可能。(41)对此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参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64頁。例如,X对A实施(基于暴力的)抢劫行为之后,第三者Y马上又对A实施了暴力,结果对A造成了伤害结果,但无法确定,属于伤害结果之原因的暴力究竟是X的行为还是Y的行为。对于此案,虽然不能通过适用第207条而肯定X成立抢劫致伤罪,但是,在X也是暴力行为的行为人这一点上,与前述暴行罪的情形并无不同,因此,也完全有可能通过适用第207条而认定Y成立伤害罪。(42)因此,对于X,就有肯定成立抢劫罪与伤害罪之想象竞合的余地。
(三) 存在部分共犯关系的情形
学界最近热烈探讨的是,暴力行为的行为人之间存在部分共犯关系的案件。例如,【案例1】X对A实施第一次暴力之后,Y才参与进来,其后,基于与X的共谋,Y实施了第二次暴力,由此对A造成了伤害,但难以确定伤害的原因究竟是第一次暴力还是第二次暴力。在这种场合,X既参与了第一次暴力也参与了第二次暴力,显然应承担伤害罪的罪责。就Y而言,是否对第一次暴力成立承继的共同正犯就属于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判例的旨趣,(43)参见最決平成24·11·6刑集66巻11号1281頁。Y仅对与自己的参与存在因果关系的暴力承担共同正犯的罪责,因而仅就第二次暴力承担共同正犯的罪责,但是,能否通过适用第207条,认定Y成立伤害罪就成为问题。(44)持肯定态度的裁判例,参见大阪地判平成9·8·20判タ995号286頁;持否定态度的裁判例,参见大阪高判昭和62·7·10高刑集40巻3号720頁。对于其他裁判例的分析,参见豊田兼彦「暴行への途中関与と刑法207条」『浅田和茂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2016年)671頁以下。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如果广泛承认承继的共同正犯,根本就不会出现是否适用第207条的问题。正因为对暴行罪、伤害罪否定成立承继的共同正犯,是否有可能对后行行为人适用第207条才成为问题。
对于【案例1】中的Y那样的后行行为人,学界有力观点否定适用第207条。(45)持否定说的学者,参见中森喜彦『刑法各論〔第4版〕』(2015年)19頁;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6版〕』(2012年)47頁;山中敬一『刑法各論〔第3版〕』(2015年)61頁;高橋則夫「『同時傷害の特例(刑法207条)』の規範論的構造」長井圓先生古稀記念『刑事法学の未来』(2017年)16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2016年)64頁。否定说认为,之所以规定第207条,是为了避免出现下述不当局面:尽管数人的暴力行为相互竞合,但最终谁都不对伤害结果承担责任。因此,在已经有先行行为人X对伤害结果承担责任的场合,就无法再适用第207条。由于X对(由第一次暴力行为或者第二次暴力行为所引起的)伤害结果施加了因果性这一点是明确的,因而,这种理解就以这种情形不符合“不能辨认何人造成了伤害时”这种文理解释作为根据。
正如前面看到的那样,最高裁判所平成28年判例判定,即便是某个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承担责任的情形,也无碍第207条的适用,因此,判例看上去似乎是排斥了否定说的这种理解。(46)持这种理解者,参见前田雅英「判批」『捜査研究』65巻9号(2016年)61頁。但是,对于最高裁判所平成28年判例也有这样理解的余地:该判例重视的是,如果否定适用第207条,那么,即便C对死亡结果承担责任,但是,就属于死因的急性硬膜下血肿这种伤害的形成,却无法向任何人追责。因此,即便是以最高裁判所平成28年判例为前提,也并非不可能采取否定说。(47)关于这一点,参见豊田兼彦「暴行への途中関与と刑法207条」『浅田和茂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2016年)680頁。然而,就【案例1】中的Y而言,即便其不是基于与X的共谋,而是单独实施了第二次暴力,也要适用第207条,因而,对于基于与X的共谋而实施了第二次暴力的情形,出于与未基于共谋的情形保持均衡的考虑,也应该肯定适用第207条。(48)持肯定说的学者,参见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6版〕』(2015年)33頁;林幹人『刑法各論〔第2版〕』(2007年)57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2010年)52頁;伊東研祐『刑法講義各論』(2011年)42頁。针对这种观点的批判是,基于共谋实施的犯罪,其违法性并非总是高于作为单独犯的犯罪,因此,不应该刻意重视与单独犯之间的均衡。(49)参见長井長信「同時傷害の特例について」能勢弘之先生追悼論集『激動期の刑事法学』(2003年)427頁;照沼亮介「同時傷害罪に関する近時の裁判例」『上智法学論集』59巻3号(2016年)93頁以下。不过,如果对【案例1】中的Y否定适用第207条,那么,如果能证明其与X之间存在共谋,相反会得出更有利于Y的结论。这样的话,检察官原本应该就X、Y针对第二次暴力存在共谋进行举证,但是,按照否定说的观点,却难免会出现举证上的混乱:(由于结论更有利于被告人)辩护人极力举证存在共谋,而检察官则相反会主张X与Y之间不存在共谋。这样考虑的话,对于【案例1】中的Y,还是应该肯定适用第207条。即便是作为对该条的文理解释,以“不能辨认”究竟是第一次暴力的主体(X)还是第二次暴力的主体(X与Y)之中的“何人”(X,或者X与Y)“造成了伤害”为理由,肯定说也完全有可能得以正当化。
另外,按照这种理解,对于那些肯定存在“共犯关系之解消”的案件,也有可能适用第207条。例如,【案例2】X、Y共同对A实施了第一次暴力之后,Y脱离了共犯关系,然后,X又单独实施了第二次暴力,但无法查明,对A所造成的伤害究竟是由第一次暴力还是第二次暴力所引起。在这种场合,对Y而言,虽肯定其就第二次暴力解消了共犯关系,但仍然有进一步适用第207条的余地。(50)作出了这种判断的裁判例,参见名古屋高判平成14·8·29判時1831号1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