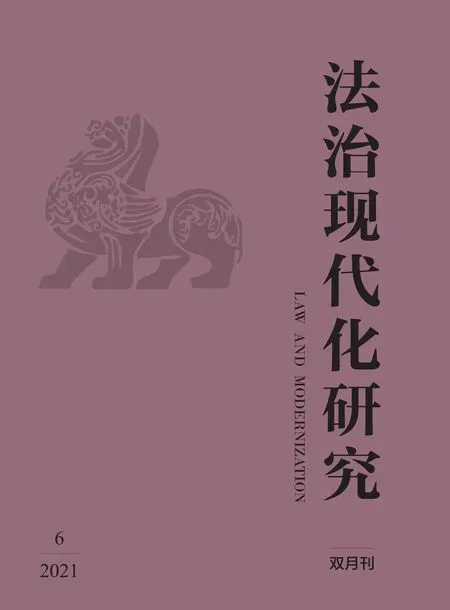均质时间与法治现代化
王奇才
面对全球化进程,我们常常试图从一些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脉络中寻找关于法治发展和法治理论研究的灵感,也包括尝试将其引入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研究,希望为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开发出新的智识资源。近年来,随着印度崛起和中国人文社科对外交流的深入,印度(裔)学者的理论也进入了中国学者研究的视野。(1)例如“西天中土”计划,其宗旨是“梳理、比照印中两国各自不同的现代性脉络,推动两国知识界与艺术界之间高层次的交流,促进两国社会思想与当代艺术的交织互动”。就法治研究而言,我们显然不应当局限于寻找印度法学家关于法治和法律发展的论述,还可以拓展到其他学科来发现有助益的思想学说。
就关于法治现代化的历史叙事而言,印度裔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庶民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又译查卡拉巴提)所著的《边缘化欧洲: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一书,(2)参见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对法治在印度历史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批判。从法学研究的视角来看,查克拉巴蒂的相关论述,引发了笔者思考以下问题:我们如何去看待法治与现代化的关系,后殖民理论对此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知识批判?
一、 “转型叙事”中的法治
(一) 法治与“转型叙事”
人们常用“转型”来表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化,各种关于这一变化过程的叙述可以称为“转型叙事”。转型叙事的内容,在不同的论者那里有不一样的表达,包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宗教社会到世俗社会、从专制到民主,等等。转型叙事构筑了一种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化图景,表达着一种社会进步的历史主义观念,法律和法治在其中扮演着一种特殊角色。
查克拉巴蒂认为,“大多数的现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叙事都离不开这样的历史演变带来的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话题是发展、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虽然这些话题经常隐含在话语之下)”。(3)[印]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谁可以为“印度”的过去说话》,陈恒译、陈韵校,载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迪佩什·查卡拉巴提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这里的历史演变及“演变叙事”(transition narrative),就是本文所说的“转型叙事”。而印度历史叙事中“未能彻底完成的转型”,查克拉巴蒂指出这正是庶民研究的核心问题。(4)查克拉巴蒂认为,印度历史学家萨卡尔的现代印度故事,“坐落在这三者(分别是农民阶级那个神秘正义王国的梦想、左派的社会革命理想、彻底的资产阶级转型)缺位的‘悲哀地尚未完成’之中”。在这种“历史没能如约完成它的天命”的背景下,庶民研究提出:“正是对这种民族未能成就自己的历史经历的研究,这种由于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不能够领导民族取得对抗殖民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并完成一场19世纪经典式的——或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正是对于这种失败的研究构成了殖民地印度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前引③,张颂仁等书,第54-55页。
在西方现代性扩张的进程中,法治是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被推广到印度的。转型叙事的两端,是中世纪和现代。“‘中世纪一度被称作‘残酷的暴君’,‘现代’则叫‘法治’。”(5)前引③,张颂仁等书,第55页。那么,这样一种对立又是如何建构起来、为了什么目的呢?查克拉巴蒂引述和批评亚历山大·道尔的相关论述来说明这一点。
亚历山大·道尔在为英国国王所写就的《印度斯坦历史》中提出,英国应当将自己的“部分根本的法律进行延伸,以确保他们的征服”,这种“根本的法律体系”就是英国的“法治”,其对立面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同时归君主掌管”的缺乏自由的状态,法治的对立面因而是缺乏自由的、“暴政”状态。转型叙事的内容,是“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开始,印度人要被转变成法律主体,管理他们的政府将会受到私人财产(此乃‘公共繁荣之根基’,道尔如此说道)以及公共舆论的压力,同时也受到一个法制机构的约束,这一机构‘行使法律正义,它必须独立于法律以外的任何东西,否则官员(法官)就会变成暴政手中的压迫工具’”。(6)前引③,张颂仁等书,第56页。在这种暴政与法治、中世纪与现代、封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转型叙事中,“印度”处于一种“未完成”“不足”的状态,原因在于,“(印度人)在未来多年内享有的是臣民的权利,而非公民的权利,因为他们不够格”。(7)前引③,张颂仁等书,第57页。
通过这种建构性叙事,法治成了转型叙事的目的,法治与印度传统治理方式成了对立物,建成法治是为了成为“英国”那样的现代文明政体,但英国又是殖民地的宗主国,在印度尚未取得独立、摆脱殖民地身份的语境中,印度在法治和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重要的是,判断这种“未完成”状态的标准,并不是经验意义上的“英国法治”,而是一种抽象的、“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这不仅是因为,“英国法治”中“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直到2009年随着联合王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的建立才最终实现,还包括在这种“传统—现代”的转型叙事之中,人们实际上是在“现代法治观”的意义上来看待法治与现代化之关系。
关于现代法治观和古代法治观的区分,在史克拉(Judith Shklar)看来,现代法治观念是一种有限政府的原则,其基础是法治必然需要“一种保持适当均衡的政治制度,在其中,权力以这样一种方式受到权力的制约:无论是国王的迫切要求还是立法机构的武断意志都无法对个人造成直接的冲击”。(8)Judith N. Shklar.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Allan C. Hutchinson and Patrick J. Monahan (eds.), The Rule of Law: Ideal or Ideology, Toronto: Carswell, 1987, p.4.洛克林认为,法治与分权的观念和政府官员不得侵犯私人行动领域的原则联系在一起,与古代法治所代表的理性之治对伦理和智识维度上的高要求和古代法治仅适用于少数人相比,现代法治则要求覆盖到每一位社会成员。(9)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1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代法治”和“古代法治”的区分只是来自西方传统,并不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区分。那种与英国“现代”法治相对立的印度古代治理模式被称为传统“暴政”,是“传统—现代”转型叙事所欲革新的目标。
“传统—现代”转型叙事把法治视为现代化的标志和目的,把异于法治的治理模式视为传统的象征和标志,其问题不在于对传统治理秩序之性质和类型的总结是否精确,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人治”“礼治”还是“古代法治”哪种表述对于传统治理秩序来说更准确,而是对转型叙事的认同体现了对“传统—现代”转型叙事的普遍认同。在这种现代化转型叙事中,法治不仅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建设法治同时还是这种转型叙事的目的,而“当下”则是“法治”尚未建成的“未完成的”“不足”的状态,“过去”是“现代法治”所要革新的对象。
对这种叙事的认同,在殖民地印度时期,是由英国的殖民统治和部分印度民族主义者所共同建构的。“不管是罗姆莫罕·罗易(Rammohun Roy)还是般吉姆·昌德拉(Bankimchandra Chattopadhyay),对于这两位19世纪印度最著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大英帝国的殖民是印度必须经历的一个监管时期,惟有经历这样一个修炼的过程,印度人才会为获得如下两样被英国人吹捧又拒绝给予的东西做好准备:公民权利和民族国家。”(10)前引③,张颂仁等书,第57页。而在今天,在评价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抵制法治之时,巴里·温加斯特认为,“为了赢得法治,自然国家必须进入由限制准入秩序到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这意味着,脆弱自然国家必须变为初级自然国家;基本自然国家变为成熟自然国家;而成熟自然国家按照入门条件开始转型。只有在这一发展阶段,国家才能够开始创造法治的制度和组织基础”。(11)[美]巴里·温加斯特:《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如此抵制法治》,鲁楠译,载[美] 詹姆斯·J. 赫克曼、罗伯特·L. 尼尔森、李·卡巴廷根等编:《全球视野下的法治》,高鸿钧、鲁楠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二) 法治与现代化
在法治现代化研究中,一个常见命题是:法治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法治与政治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必然关系。常包括以下具体表达:法治与政治现代化互为目标、互为条件;法治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政治现代化是施行法治的基本目标;政治现代化是建设法治的必要基础,法治文明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法治与现代化两个概念互相建构,体现的是现代性需要通过法治这个概念才能得以阐明和理解。查克拉巴蒂认为,“‘政治现代性’的现象(即国家现代机制的统治、官僚政治、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不诉诸某些范畴和概念就无法对世界的任一处地方进行思考,而这些范畴和概念的谱系是深入到欧洲的知识甚至理论的传统中的,一些概念,诸如公民权、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公共与私人的区分、主体的观念、民主、人民主权、社会公正、科学理性等等,都承载着欧洲的思想和历史。如果离开这些或其他相关的概念——这些在欧洲的启蒙运动至19世纪期间形成社会思想思潮的概念——我们简直无法思考政治现代性。”(12)[印]迪普希·查克拉巴蒂:《边缘化欧洲的构想》,吴晓佳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
在这种关联中,通过建构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主义转型叙事,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必然目标。如果说在殖民地印度时期,这种转型叙事是通过殖民者和本土精英共同建构的、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那么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后的更为晚近的时期,法律与发展运动中的西方援助与本土需求同样起着建构这种转型叙事的作用。本文将以“华盛顿共识”为例来分析这一点。
1. 华盛顿共识与转型叙事
1989年,由于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与会者达成的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主要包括10个方面:① 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 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 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 实施利率市场化;⑤ 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 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 放松政府的管制;⑩ 保护私人财产权。(13)关于华盛顿共识,参见江时学:《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的改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而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善治和“结构性调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条件,以包括法治、减少腐败、采用西方商法等作为善治的内容,目标是为实现华盛顿共识中的目标创造经济和法律上的条件,(14)参见David P. Fidler.“ A Kinder, Gentler System of Capitulations? International Law,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and the Standard of Liberal, Globalized Civilization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5,No.3 (2000).特别是强调要建设一个拥有客观、可靠和独立司法体系的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华盛顿共识”的思想基础,是强调不再由国家垄断治理权力,转而强调由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理论对治理的定义。因而,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新的现代叙事模式,即从国家垄断治理权力的现代治理模式,转型走向更新的、更现代化的公私合作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
这种转型叙事强化了法治在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位置,从国家的政治结构细化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进一步强调了法治对于政治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法治与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作了更强有力的建构。同时,这种转型叙事存在着援助国和被援助国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凸显了法治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之间的关联性,也让我们有可能在关注殖民地历史之外,从新的视野来看待“传统—现代”转型叙事之中法治的定位和局限性。
2. 法治作为一种资格
近年来有关全球治理的讨论中,法治不仅成为在民族国家这一层面是否实施了好的治理或者善治的一个标准,例如赫斯特认为国家实行法治与否意味着全球治理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15)参见Paul Hirst.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in Jon Pierre edited, Debating Governance: Authority, Steering,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2-33.还关系到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资格。以是否贯彻法治作为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制”的资格判准的思路,与罗尔斯所说的“正派的人民”(decent peoples)和“法外国家”(outlaw states)的区分(16)[美]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相比,既有延续发展也有不同。(17)童世骏认为:“罗尔斯用‘正派’来形容‘peoples’而避免用‘法外’来形容‘peoples’,表明他不想对一个民族的成员进行道德谴责,而只想对代表这个民族的政府作道德谴责。”参见童世骏:《全球政治中的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载“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8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7月10日。
在《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ForgingaWorldofLibertyUnderLaw:U.S.NationalSecurityinthe21stCentury)中,“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提出了一种关于未来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制的主张。报告提出要发展全球性“民主国家协约”,以及美国应促使世界各国政府达到PAR标准的建议。“民主国家协约”(Concert of Democracies)将把世界上采纳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集合一起,加强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PAR是英文Popular(受拥戴的)、Accountable(负责任的)和Rights-regarding(尊重人权)(18)中译本,参见《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徐昕、刘祖魁、朱亮译,载“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a8b1b748852458fb770b566e.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7月10日。的英文缩写。报告指出:“我们应当建立国家级、地区级、地方级政府官员与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关系网,并使之制度化,以创造众多的渠道使已经达到PAR标准的国家和未达标的国家合作解决共同问题,并以沟通和劝导的方式使那些旨在捍卫法治下之自由的价值和实践得以传播,构建一个自由体制。”(19)参见《东方早报》对斯劳特的采访:《普林斯顿计划设计者:美应欢迎中国成亚洲领导者》,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1/10/content_7631292.htm,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7月10日。
福山的研究中也包含着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所组成。拥有全部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20)[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2页。与福山的观点相比较,“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PAR标准对现代政治秩序之看法的共同之处,在于把法治作为良好的现代政治秩序的标准之一。
关于这种思路的局限性,笔者认为不能以法治/非法治、民主/非民主、代议制/非代议制这样的标准来区分甚至限制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立法的资格:按照法治来区分民族国家主体资格,违背了国家行动体之间平等的原则;忽略了民族国家之外其他类型行动体的重要性,例如各种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忽视了法治概念的争议性和开放性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重要意义。(21)参见王奇才:《法治与全球治理:一种关于全球治理规范性模式的思考》,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183页。在此,笔者想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将法治建构为现代化的目标,与把法治确定为经济改革目标和接受援助的条件、把法治作为参与全球治理体制的资格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其建构是通过描绘一种关于法治发展不均衡的叙事策略而得以实现。
二、 “等待时间”中的法治
(一) 法治与发展不均衡
1. 法治指数与法律发展不均衡
法律发展不均衡是法治研究的常规课题。法律发展的不均衡,不仅表现为国家和国家之间法律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也表现为一国之内各地区之间的法律发展不均衡和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法治指数和治理指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原因之一。(22)关于法治指数和治理指数的兴起,参见Juan Carlos Botero, Robert L. Nelson, Christine Prat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of Justice, Governance, and the Rule of Law: an Overview”, 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 No.2(2011).
以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为代表的法治评估的实践表明,法治评估得分是国家和地区间发展差异的比较标准之一。(23)参见WJP Rule of Law Index, 载“World Justice Project”, http://worldjusticeproject.org/, 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7月10日。也就是说,法治指数的出现,意味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法律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同一套法治指数来加以量化评价,而法治指数的评价对象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法律发展水平上的表现(performance)。帕沙·查特吉指出,“21世纪任何一个拿着社会指标数据本的本科生,都可以根据生活指标、道德指标、治理的质量、人类发展以及其他评估性指标,来对全世界的国家进行排名……文化不再是不可通约的。但是现在可以就其结果来看,将其判定为对标准的偏离,从而对其进行规范化(normalized)。全世界的政府都被纳入同样的概念领域中去。国家间的所有偏离,都可以根据同样的计算方式进行比较,并最终据此对国家进行分级”。(24)[印]帕沙·查特吉:《政治社会的世系:后殖民民主研究》,王行坤、王原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在此,笔者想论及三个关键词。一是“同一”,它意味着在同一时间点或者特定的时间段,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法律发展水平可以被同一套法治指数加以量化评价;意味着通过建立以法治为基准的规范化标准,去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对于法治评估标准的偏离程度,对传统治理模式不符合“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的方面予以指出和加以批判。二是“表现”,它意味着通过法治评估上的分数,不同国家、地区法律发展的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25)赵鼎新认为,绩效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该政权经济绩效和/或者道德功绩以及捍卫领土的能力”。参见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龚瑞雪、胡婉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以一种量化的方式呈现。(26)关于法治评估与绩效合法性的一个初步分析,参见王奇才:《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法治评估的兴起》,载《云南大学法律评论》(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三是“差异”,它意味着通过法治评估的结合,人们认识并认可了法律发展的不均衡性,而法律发展的不均衡性被人们所认可,原因在于人们认同了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法律发展既是政治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又是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撑之一。
经济发展与法治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经典问题。自马克思·韦伯以降,(27)参见大卫·M.楚贝克:《马克斯·韦伯论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载“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http://www.legal-theory.org/?mod=info&act=view&id=9407, 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7月10日。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纷纷讨论了法律作为经济发展基础性机制的重要作用,并用经验性的证据论证了正式法律体系(28)例如“法与金融”理论的研究,参见胡昌生、龙杨华:《“法与金融”理论述评》,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和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是法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其联系不仅限于形式法治理论所要求的内容,如正式法律制度以及作为形式理性法代表的成文法典,还包括实质法治理论所要求的民主和权利等内容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历史主义的论述策略中,法律发展水平与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被紧密地建构在一起。法律发展的不均衡性,体现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的不均衡性。法律发展面临的阻碍,与政治、经济方面所面临的阻碍亦密不可分。
2. 国民素质与政治发展不均衡
在政治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上,一个常规的前提性约束被表述为:国民素质能否承担得起现代政治民主政体的要求?
对国民素质之反思,是前殖民地国家回应西方现代化冲击的一种常见模式。通过这类反思,民众如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格”公民,民众是否具备建设现代民主政体的公民素质,成为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一种公共话语前提。基于此,对诸多社会公共议题的正反辩证论述,常常以一种既需要政府加强管制、又需要民众积极参与的表达出现。这种表达之中,时常隐约包含着对民众是否具备现代公民之政治素质的怀疑和否定。对公民政治素质的否定或者消极评价,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不同社会群体对特定时空建设现代民主制度之困难和障碍的共识。日常生活中不时出现的有关国民素质的消极事例,也常常被用以证明和强化上述共识。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前殖民地国家现代性历史内部的紧张。查克拉巴蒂指出,这种紧张之所以出现,是在如印度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政治现代性的历史与本质在作为公民的庶民或者农民两个方面上产生了紧张。“一是必须被教育成公民的农民,他们因而是属于历史主义的。另一个是尽管缺少正式的教育但他或她已经是公民的农民。”(29)前引,查克拉巴蒂文。查克拉巴蒂还引述帕沙·查特吉的讨论,“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叙事版本里,只有农民和工人这样的庶民阶层,才需要背上‘不足’的十字架,因为只有这些人才需要接受教育,通过教育来消除他们的无知、狭隘或者是虚假意识”。(30)前引③,张颂仁等书,第58页。也就是说,面对政治现代化和发展的“不足”“未完成”的状态,需要背负责任的是被认为需要接受教育才能具备政治现代性所需“素质”的庶民,庶民在经受教育成为公民之前还处于一种“前政治”的状态。
查克拉巴蒂认为印度学者古哈对农民意识是“前政治的”的观念已做了明确批判,庶民的历史编纂(研究)质疑了资本主义必然会使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假定。对资本的普遍主义叙述的质疑,引向对“欧洲政治想象”背后的人类处于单一的、永恒的、阶序的历史时间框架之中的质疑。而对国民素质之怀疑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欧洲政治想象”为基础而建立的“民众必须被教育成公民才能进入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对“受教育而成为公民”的潜在的、根深蒂固的认同,与对“经践行而成为公民”的表面鼓励与实质否定,使得民众进入现代政治始终处在一种“想象性的候车室”(imaginary waiting room)(31)在中译本中,imaginary waiting room被译为“想象性的等待空间”,但从查克拉巴蒂对历史主义线性时间结构的批判来看,翻译成“空间”似乎并不准确,笔者暂译为“想象性的候车室”,以表达在等待获得资格登上现代性列车之意。参见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p.10.之中。这种历史主义的时间安排,正是查克拉巴蒂所批判的对象。
在查克拉巴蒂看来,欧洲历史主义思想的线性时间叙事,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地区建立起了一种阶段论、有先后的政治现代化路线。按照这种叙事,在受过教育、经过规训而成长成为公民的现代政治主体与前政治的庶民/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等待时间”,而只有在完成了某种历史发展阶段、进入到某种状态之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才会阶段性地进入到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而查克拉巴蒂认为,印度庶民研究揭示了农民(庶民)已经是实践的现代政治主体,并不是需要教育才能成为现代政治主体
对本文的研究而言,查克拉巴蒂所指出的殖民地印度法治叙事处于一种“不完整”的状态,其“不完整性”涉及多重“不完整”,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① 从“民众”到“公民”之转变的不完整,民众始终难以成为宗主国意义上的完全状态的完整的“公民”,而这种不完整状态又成为拒绝达到现代政治之完成状态和现代民主的理由之一;② 从“暴政”到“法治”的转型一直处于“等待时间”之中,转型时期法治会始终以抽象地、“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作为参照物,并继续和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③ 相对于“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的完备性,殖民地法治的“未完成性”将会长时间存在。
(二) 法治与线性时间结构
有关法治在殖民地印度之命运的讨论,对查克拉巴蒂而言是为了引出对欧洲历史主义思想的线性时间叙事的批判,对于本文而言则是为了将欧洲历史主义思想的线性时间叙事引入法治现代化的讨论之中。将是否具有法治作为“前政治的”和“政治的”区分,是把法治纳入现代线性时间结构之中。查克拉巴蒂的讨论揭示了这种思路的要害,即它将法治与现代民主政体更深层次的时间观和时间性联系在了一起,在意义阐释的层面来追问法治与时间的关系,与一般意义上将法律效力与时间期限相关联的思路具有明显区别。(32)关于通过“深描”的方法来阐释美国宪法史中不同历史观的意义,参见丁晓东:《美国宪法中的时间观》,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如果说“传统—现代”转型叙事将法治吸纳,并将法治作为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和目的,那么在欧洲历史主义思想的线性时间叙事之中,通过对发展不平衡之必然性的论证,法律发展的不平衡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相关联并得以正当化。在朝向“超真实欧洲”或者现代法治这一目标的途中,法律发展水平的落后、法治发展阶段的差异,意味着法律发展水平较低、法治发展阶段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尚处于一种等待法治成熟或者具备充分条件的阶段。这样,在历史主义的线性时间结构里,就法治发展的阶段而言,成功建立起了一种得分有高低、时间有先后、水平有高下的划分。从而,宗主国与殖民地、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以“有无法治”“法治发展水平高低”为标志的“现代与前现代”“发达与欠发达”“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二元化对比结构。不仅这种对比结构的正义性存在争论,而且这一结构是时间性的,并强制性地将人们的政治想象纳入到这种对比结构之中思考。
在现代化后发地区也就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出生成长的研究者,该怎么去看待后发地区的政治发展和法治发展?笔者认为,从查克拉巴蒂的研究看来,“后发”这个概念本身就预设了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后发”不仅意味着出发的落后性,还意味着相对于现代化的“完成状态”,后发国家将长时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而判断是否达致“完成状态”的标准和参照物——不管是主动或者被动的——是“超真实的欧洲想象”。并且,一国内部对法治建设进程在其行政区划间的比较,如果建立在“发展速度不均衡”和线性历史观之上,那么就蕴含着区域间在法治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现代化进程上的相对差异,造就了一国内部法治发展的“等待时间”。这样,不仅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建立了一种“等待时间”意义上的线性时间叙事,更在非西方地区内部建立起来一种同样的时间结构。对抗这种时间结构,不是要拒绝某种“舶来的法治”,也不是要对一国法治现状给出发展阶段意义上的判定,而是应当通过反思法治发展阶段划分背后的现代线性时间结构安排,开放出法治理论的可能性。
我们应当避免这样一种困境:捍卫自身主体性常常是以一种对经验意义欧洲加以批判的方式来进行的,但这种批判以及对自身发展状态的判定,却是以源自欧洲的“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为标准。如果我们以“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为标准并陷入现代线性时间结构之中,那么作为一种发展目标同时又是一种发展手段的法治而言,在这种时间结构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先行者”和“落后者”。相对于“先行者”,“落后者”在这种时间结构中,其法治将处于一种“未完成”“不发达”的状态,也就是处于一种“等待时间”之中。
那么,查克拉巴蒂的“边缘化欧洲的构想”,是想开放出历史乃至法治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吗?在《边缘化欧洲》一书的导论中,查克拉巴蒂曾指出,(33)参见前引,查克拉巴蒂文。历史主义的叙事提出了一个普遍主义的、阶段化的内在统一的叙事,这样一种叙事是一种演变叙事或者转型叙事,是一种“超真实欧洲想象”的普遍化。在这种想象被复制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在生活方式、社会架构和国家体制等方面对“超真实欧洲想象”的扩展、复制和使用,使得建构第三世界主体性的过程中,这类主体处于一种“等候状态”之中,或者说处于一种不足、欠缺、未完成的状态。同时,这种扩散本身与暴力、压迫相并存。这样,暴力与“等待时间”相结合,时间成了一个空洞的、永恒的历史时间,吞噬了欧洲历史之外的其他历史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法治成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标志物,法治也是“进步”“文明”背后的西方线性时间结构的代言词和表现方式。但现代法治的暴力一面也不应被掩盖和忽视。这种忽视会使得“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戴上美好善良之治的面具,甚至会被主张多元现代性和非西方法治的理论所采纳、将法治视为自身现代化主张的一部分,同样也将法治的美好一面视为转型社会的发展目的。这种进程实际上是把“从没有法治/非法治走向有法治”“从初级阶段的法治走向高级阶段的法治”视为转型社会的发展逻辑,而这仍然没有脱离本文所说的“转型叙事”和“等待时间”。
三、 “均质时间”中的法治
(一) 反思法治现代化的“关键时刻”
转型叙事和“等待时间”所期待或承诺的,是在未来某个时刻实现“真正的法治”“完美的法治”或者“完成状态的法治”,指向了法治发展的不均衡性,存在着诸如高级阶段/初级阶段、先进/落后之类的阶段划分。那么,由法治的某一阶段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是否存在“跃升”的关键时刻呢?
在法律发展史上,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现代法典曾被视为法治现代化的阶段性标志,制定民法典是达到现代法律体系成熟阶段的必经阶段;建立以法典化为代表的形式理性法体系,不仅是法律制度的发展目标,更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于是,在制定一部民法典的问题上,不仅经验意义上的英美法律制度发展有着显著不同,而且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和变化也常常被忽视。卡内冈曾指出:“今天的欧洲人生活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法律制度之下,这些制度下的法律几乎已经千篇一律地法典化了……毫无疑问,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一如他们各种各样的语言。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从欧洲历史的时间纬度来看这种‘自然状态’其实只是晚近的事情(只能回溯一两个世纪),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欧洲联盟的兴起将会使它变成一个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时期。”(34)[比]R. C. 范·卡内冈:《欧洲法:过去与未来——两千年来的统一性与多样化》,史大晓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将“制定民法典”作为法律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时刻”,表面上看是来源于法国和德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真实经验,并异于英美现代化进程的法律制度实践,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对抽象的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认同,从而将法典化视为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标志和“关键时刻”,这就是上文所述的“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出于对这种“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的认同,我们可以甚至还应当忽视个别国家在经验意义上的不同,而必须聚焦于这种法治想象的观念化的、抽象化的特征。
以法典化为标准,在法治发展的时间序列上,不同国家似乎可以更容易地被划分为现代与前现代、发达与落后、初级与高级等类型,其背后是上文所指出的进步的、线性的历史观。这再一次表明了在这种基于进步历史论的线性时间结构中,“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是现代化的成熟状态;相对于此,法治的后发国家处于一种“不成熟”状态或者“未完成”状态,在等待着某种“关键时刻”,一举进入成熟阶段,又或者迈入朝向完成状态的下一个阶段。
本文想要讨论的,不仅是这种“等待时间”以及线性时间结构对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影响,还想进一步讨论这种线性时间结构的时间性及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对于“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来说,将法典制定和制度移植作为其重要特征和标志,其基础是印度学者帕沙·查特吉所说的“现代性社会空间分布在空洞的、同质化的时间中”。(35)前引,西北大学出版社书,第174页。基于同质化的时间,现代法律制度像资本一样、或者说伴随着资本,在空间上流动和扩张,当其遇到阻碍之时则认为是遇到了前现代时间。
问题在于,对于以民法典为标志的“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来说,如帕沙·查特吉所指出的,这种同质化的时间是空洞的、乌托邦的时间。朝向法治现代化成熟阶段的“等待时间”具有某种永恒性。也就是,以“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为标杆,我们始终在等待下一个“关键时刻”,以进入到完成状态的“超真实法治现代化”状态之中。
(二) 本雅明与均质时间
本雅明将均质的、空洞的时间(homogeneous, empty time)置于现代性的核心。(36)关于查尔斯·泰勒对本雅明以及世俗时代的时间性所作的评论,参见[加]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6页。在其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中,本雅明认为,“历史主义理所当然地落入了普遍历史的陷阱。唯物主义史学与此不同,在方法上,他比任何其它学派都更清晰。普遍历史连理论的护甲都没有。它的方法七拼八凑,只能纠合起一堆材料去填塞同质而空洞的时间”。(37)[德]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张旭东译,载《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如何理解本雅明意义上的“均质时间”?查尔斯·泰勒认为,本雅明以“均质的、空洞的时间”对现代意识加以标识并作为现代性之核心,“依此观点,时间成为类似空间的容器,填进去什么都无所谓”。尽管查尔斯·泰勒认同,一方面,“牛顿式的空间和时间仅仅只是容器而已,在容器内,物体可以被四处移动(甚至非物体,比如‘真空’,在这里也适用)”,另一方面,“宇宙论术语中的时间识别使之成为一种对属人的、历史的事件根本不在乎的容器。这些事件即是我们人类在此星球上活生生的实践。在此意义上,宇宙论时间(对我们而言)是均质的和空洞的”,但是查尔斯·泰勒也认为相对于西方社会内部“更高的时间意识”,“均质的和空洞的并没有充分叙述出现代时间意识”。(38)参见前引,泰勒书,第72页。
在西方社会内部理解“均质时间”,本雅明是试图通过批判现代性的均质时间来创造一种被本雅明称为“弥赛亚时间”的新型时间。中国学者胡桑认为,本雅明思想的核心“是弥赛亚主义,它试图创建一种新型的时间,即弥赛亚时间,这有悖于现代启蒙理性所依赖的线性时间。现代线性时间借助数学和技术的扩张制造出一种均质而空洞时间。现代性计划依靠进步的历史观展开,这种历史观不断地舍弃、遗忘过去,使人类越来越远离起源”。(39)胡桑:《弥赛亚时间的结构——论本雅明哲学中的神学》,载“散文吧”,https://sanwen8.cn/p/1a5Dp7L.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7月10日。现代性计划的展开,特别是其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张,一如上文所指出的,造就了殖民地与欧洲之间“先进”和“后发”的不平等结构,其中伴随着暴力、法律移植与“等待时间”式的历史叙事。
阿甘本指出,“正是借助本雅明所谓的均质而空洞的时间,现代性才得以在全球肆无忌惮地扩张,它要求一个普遍、均质、无差别的世界”。(40)前引,胡桑文。这与科耶夫所提出的“普遍均质的国家”具有同质性。(41)对科耶夫的“普遍均质国家的讨论”,主要是针对科耶夫的《法权现象学》一书的相关讨论而展开的。参见[法]亚历山大·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在霍斯和弗洛斯特看来,科耶夫的“普遍均质国家”是一个法权国家(Rechtsstaat),是“通过跨国宪政论克服传统国际法的局限,促成超国家的司法秩序形式”。(42)[美]霍斯、弗洛斯特:《普遍均质国家的可倡导性》,载[法]科耶夫等:《驯服欲望:施特劳斯笔下的色诺芬撰述》,贺志刚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这种法权国家的实现形式是“通过互相承认民族法律达到司法一体化”,并且霍斯和弗洛斯特认为,美国国际法学者施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已经描绘了“跨境司法合作怎样成为解决因全球化而引起的不同国家法律冲突时被广泛采纳、且常常成功的方法”。(43)前引,华夏出版社书,第108-110页。然而,施劳特的观点是,与政治主权没有多大关系的国际司法合作在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间进行得最密切和最有效,但是在非自由国家间求助于政治主权的承认仍然是主流。(44)参见Anne-Marie Slaughter. “International Law in a World of Liberal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03(1995), p.6.霍斯和弗洛斯特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评论。正如上文所论及的,施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后来曾是上文提及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主要成员,(45)参见前引,“中国网”文。也是《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作者之一。(46)参见G. John Ikenberry,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普遍均质国家”和“均质时间”共享着普遍历史的历史主义叙事,在其中,西方与非西方、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仍然存在着线性历史结构中先后阶序之分,落入了“普遍历史的陷阱”。
本雅明所说的“落入普遍历史的陷阱”的历史主义,正是查克拉巴蒂在《边缘化欧洲》一书中所批判的历史主义。(47)参见前引,查克拉巴蒂文。并且帕沙·查特吉在《政治社会的世系》中指出,政治所栖居的现代性空洞的、同质化的时间是“资本的乌托邦时间”(utopian time of capital)。这种资本的乌托邦时间“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线性地联系起来,并为所有那些关于身份、民族、进步等等的历史主义想象创造了可能性……空洞同质化的时间在真实空间中并不存在——它是乌托邦的时间。现代生活的真实空间存在于异质性的时间中,这里的空间是不均匀而稠密的”。(48)前引,西北大学出版社书,第175-176页。
(三) 开放法治的可能性
面对“普遍历史的陷阱”和空洞的“均质时间”,如何进行法治现代化的思考显得尤为关键。延续上文提出的思路,笔者认为,研究者需要进入法治的意义世界,开放出法治的本质争议性。在“法治与全球化”的研究中,人们曾寻找一种最低限度的、最大共识版本的法治,而问题在于,法治本身的本质争议性及其开放性、批判性,有可能被一种“最低限度版本的法治”压制了。
1. 最低限度版本法治的局限
在全球化研究中,或者说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制度传播移植的意义上,形式法治理论被视为一种弱的或者说薄的(thin)、较小争议性的法治理论,或者说一种最低限度版本的形式法治理论更有可能被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广为接受。
梁治平认为形式法治概念所阐述的原则是不可回避的,同时也有利于看到法治的限度,并且“由于其形式化的特征,将这样的法治概念应用到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社会时(在这里是中国),既可以保持其基本意蕴,又能适当地考虑到这些特定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状况,并为法律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留出空间”。(49)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载梁治平编:《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或者说,一种基于形式法治理论的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将会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可接受性。(50)参见梁治平:《“中国特色”的法治如何可能?》,载《文化纵横》2011年第3期。梁治平还引证了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所主张的在跨文化研究中形式法治理论可以提供最大公约数的观点(51)参见Randall Peerenboom. “Ruling the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Law:Reflections on the Rule and Role of Law in Contempory China”, Cultural Dynamics 11, No. 3 (1999).来强调形式或程序法治的优点。
笔者曾认为,形式法治理论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冲突的语境中更能够获得认同,或者形式法治理论更能够包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冲突,能够作为某一种全球治理规范性模式的基础。(52)参见前引,法律出版社书,第182-183、88-93页。但是,形式法治理论本身正如梁治平明确指出的,各种程序性或者形式性的“法治理论之间的共同点比理论家本人愿意承认得更多。这并不奇怪,因为所有这些理论实际上是同一历史文化的产物;它们出于同样的经验,有同样的制度基础和实践背景,它们甚至出于同一种思想传统,即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和法律传统”。(53)前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书,第100页。
无论是梁治平所讨论的法治与中国社会转型,还是笔者曾讨论的法治与全球化,以及本文所讨论的法治现代化,其中的共同点正是法治被视为转型叙事的目标、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和手段,并建立在现代法治的可移植性、公约性、普遍性之上。这样,根据那种“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无论是提出一种最低限度的形式法治观,还是提出某种具有实质伦理价值版本的法治理论,其重心可能是我们如何“更现代”,或者我们如何走在一条比经验意义上的欧洲“更加现代”的现代化道路上,以及我们的法治观和法治实践如何可能“更现代”、更先进。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查克拉巴蒂的研究中,其对“欧洲政治想象”的批判也是有限定的,对“欧洲政治想象”框架在社会正义问题上的批判力持肯定态度。前文所提及的那些与法治密不可分的概念,如公民权、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主权、社会公正、科学理性等,“影响巨大,它已经历史性地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基础,在欧洲及其之外地区建立起对社会不公正的批评”。(54)参见前引,查克拉巴蒂文。2010年,查克拉巴蒂在上海所作的《作为漂移能指的西方:殖民时期与当代印度的文明与教养》演讲中进一步提问,一种政治传统或者一个超级大国,“想真正有效地支配世界的时候,你将为你的受害者提供怎样的批判工具,让他们如何反过来批评你的统治?换言之,你将从自己内部的传统中创造出怎样的资源,以供别人批评你自己?”(55)[印]迪佩什·查卡拉巴提:《作为漂移能指的西方:殖民时期与当代印度的文明与教养》,载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如果说欧洲政治想象为它的受害者、受压迫者提供了内在于欧洲政治想象的批判工具,有助于在欧洲政治想象的普遍历史框架中对社会正义问题的讨论,(56)查克拉巴蒂还指出:“被殖民者有时会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赋予其一些他们会尊敬的多元化特征,并用这些特征来批判殖民者。这些被赋予的特征必须构成一种共同的普遍性的运动,以使之能够联合反帝、反西方人的批判武器。”前引,上海人民出版社书,第285页。那么对正在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是否也存在一种类似的要求呢?这种在自身内部创造出矛盾和批评以供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思路,显然不同于在全球多元文化中找寻一个最低限度版本的法治观。
2. 法治概念的本质争议性
法治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而确定一个概念是不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57)参见W. B. Galli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in W.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Chatto&Windus, 1984,p.161.最重要的依据在于这一概念在其基本价值负载上是否有本质上的争议。麦考密克指出:“法治原则既是社会财富,也是人类的财富;正义、民主及社会正义等等也如此。所有这些财富构成了盖瑞所说的‘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它们永远无法被完整地贯彻,并且其中任何一种价值观在某种情况下都可能与其他价值观发生碰撞。一旦某一价值观被认为有优先于其他价值观的权利,那么就无任何机会在必然会发生竞争的理想之间达成必要而合理的妥协了。”(58)[英]尼尔·麦考密克:《法治国家与法治》,载[德]约瑟夫·夏辛、[德]容敏德编:《法治》,阿登纳基金会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人们并不否定法治概念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但就本文关于法治现代化的讨论而言,试图从法治概念的本质争议性开放法治的可能性,至少具有以下方面的特点和要求。
(1) 开放法治的可能性,不能抛开与法治概念本质争议性紧密相关的实质法治理论的内容。根据塔马纳哈的归纳,实质法治理论按照由弱到强的顺序包括以下内容:个人权利如财产权、隐私权、订立契约的权利、自主的权利;人格尊严的权利(right of dignity)和/或者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社会福利如实质上的平等、福利和社区保护(community preservation)。(59)参见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History, Politics,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91.这些实质法治的内容主要来自查克拉巴蒂所说的“欧洲政治想象”,是本文所说的“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些内容一方面构成了后发国家内部讨论社会正义问题的基本概念背景,另一方面也是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提出批判的重要工具。例如,在“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权平等原则与1955年万隆会议所主要讨论的人权问题相关。“在1955年的万隆,没有人对世界上的主要人权问题存在什么疑问: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持续存在阻碍了人权。经济发达且大多数为民主国家的欧洲诸国(不考虑当时在弗朗哥和萨拉查独裁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全球化范围内是主要的人权侵犯国”,(60)前引,西北大学出版社书,第315页。而主权平等原则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
(2) 开放法治的可能性,应当注重发掘当下法治实践的意义,并以此参与有关法治概念本质争议性的讨论。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实质/形式法治理论之区分为代表的关于法治概念本质争议性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全球化本身在价值、制度等方面的争议性。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国家有自身历史和独特文化。法律意义的创造是总是在一种本质上是以文化为媒介的情况下发生的,创造的过程是集体性的和社会性的。(61)参见Robert Cover. “Foreword: Nomos and Narratives”, Harvard Law Review 97,No.4(1983); Robert Cover. “Violence and the Word”, Yale Law Journal 95,No.1601 (1986), p.11.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许多重大实践问题的法治意义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揭示,才能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质疑和保留,也才能通过参与法治概念的本质性争议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例如所有权制度、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一国两制”等具有鲜明特色和丰富经验的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还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对话能力、能够参与法治本质性争议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以“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为核心的法治现代化叙事,能够占据话语霸权和处于强势文化地位(62)关于法治传播与强势文化的关系,参见於兴中:《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载於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的原因。
基于上文的分析,本文认为,以法治为目标的转型叙事,不仅包含了“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是现代西方政治秩序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还表达了欧洲现代政治想象在时间问题上的一种基本假设,即不同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化的时间顺序存在差别,法治的发达/落后之分是这种现代线性时间结构的一种表达方式。对西方现代法治之扩散的批判,不应局限于对源自西方国家的具体法治模式、制度设立和规则原则之可移植性和适用性的批判,更应当对支撑“超真实的现代法治想象”的“均质时间”做剖析和反思,进而寻求开放出被“均质时间”以及“传统—现代”转型叙事所限制的法治概念的争议性,乃至发现法治和历史的其他可能性,这对中国的法治现代化研究和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