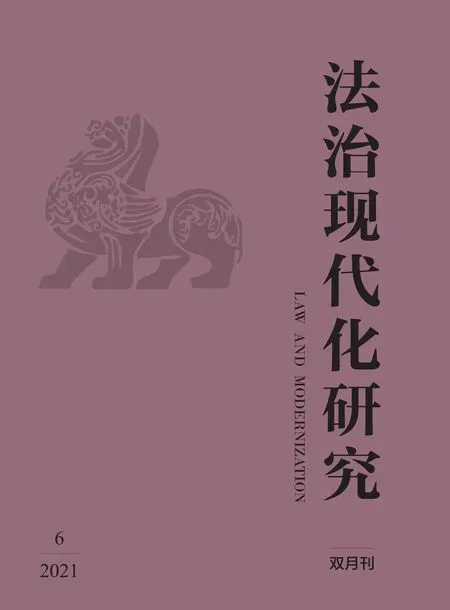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百年土地政策试点的法治省思
杨登峰
一、 引 言
试点是中国共产党最具特色的制定政策和推动改革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1)《树立改革全局观积极探索实践 发挥改革试点示范突破带动作用》,载《人民日报》2015年6月6日。但如何使“试点”能够真正迈开步子、趟出路子,是当下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事实上,试点基本贯穿整个中国共产党党史。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试点就成为湘赣根据地探索土地政策的有效方法。此后,试点在中国土地政策和其他领域长期使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试点进一步在各改革领域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认真回顾中国共产党改革试点的历史,深刻认识其特质,充分总结其经验,无疑有助于促进试点更好地“迈开步子、趟出路子”,为改革开放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试点涉及方方面面,在一篇文章中全面考察不大可能。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社会,土地政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上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土地政策变革试点每每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制度重大变革的突破口。透过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试点的百年历史,基本可以管窥中国共产党所有政策试点的全貌,并为政策试点汲取经验。故本文选取百年土地政策试点历史作为考察对象,以期达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和“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是当前改革的基本遵循。试点属于改革的组成部分,不能例外。针对试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全面依法治国决定》)和立法法已经确立了先行先试授权制度,(2)“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第13条。但这能否保证试点迈上法治轨道,仍需考察。为此,本文对百年土地政策试点的考察主要着眼于法治视角,借此管窥所有政策试点所面临的法治问题。
二、 百年土地政策试点历程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息息相关、一脉相承,每一次土地政策变革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而每一次土地政策变革都以试点的方式展开。因此,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试点的历史可以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统一起来,大致划分为1921—1949年、1949—1978年、1978—2012年和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现就各个阶段的土地政策试点情况分述如下。
(一) 1921—1949年的土地革命与改革试点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大致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减租减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四个阶段。土地政策试点主要集中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三个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八七会议”上决定用革命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和庙宇等的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的农民耕种。(3)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再次确认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给农民耕种的总政策。(4)在这段时期,中共中央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或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共有”的主张。党的六大进而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遂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但这些政策是原则性的,地主如何划分,没收的土地为公有还是私有,分配时以乡(村)还是以镇为单位,按人口分还是按劳力分,按面积分还是参考贫瘠程度分,这些都不明确。土地政策试点由此萌发,典型的有毛泽东1928年2月至7月在井冈山根据地和邓子恢1928年8月在闽西永定溪南里进行的土地革命试点。这一时期的试点,不仅存在于分田过程中,也存在于查田过程中。查田,即检查分田政策的执行情况,纠正分田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例如,1933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召开查田动员大会后,先在瑞金叶坪乡进行试点,后又推广到该县的云石区、任天区、武阳区乃至全县。在获得必要经验后,才于6月至8月在中央苏区全面展开。(5)参见钟日兴:《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确立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在政策实施对象、范围、额度等方面同样存在较大探索空间。为此,各根据地也采用了试点方式摸索经验。例如,华中地区的淮北根据地,1939年冬在永城地区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颁布条例及办法以明确减租减息的标准。(6)参见马洪武主编:《永恒的记忆: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10页;徐建国:《减轻封建剥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再如,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在相继制定《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于同年5月至6月,把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沭、费滕边作为试点县,并把沂水县埠前庄、马牧池作为试点村,开展减租减息试点。(7)参见陈国庆:《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137、142-145页。1943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创造了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亲自蹲点,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经过典型试验,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一般”的工作程序和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8)参见董志凯、陈廷煊:《土地改革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拉开序幕。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确立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目标,主张通过反奸、清算、减租、退租、退息等有偿、温和的方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9)参见张卫波:《实现耕者有其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同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又提出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不过,除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外,多数解放区认为条件不成熟,不宜立即实行。(10)参见前引⑨,张卫波书,第25-30页。后来,中共中央将减租减息调整为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耕种。这样一来,反奸清算、减租、退租、退息、和平征购和没收成为同时采用的土改方式,但试点仍在土改中得到应用。例如,陕甘宁边区决定在土地未分配区域通过减租与征购方式进行土改后,先在绥德、庆阳、关中的县、区、村开展试点。(11)参见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二) 1949—1978年的土地政策调整试点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调整主要集中于1949年至1966年,涉及减租退租、土地改革、合作化,以及1956年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等,每次政策调整都从试点开始或穿插了试点过程。
减租退租试点是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和新中国的成立,在新解放区推行的减租退租运动中开展的。新中国成立时,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改,土地改革依然是主要任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新中国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为此,1949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在华北的城市近郊和若干地区以及河南的一些地区进行土改试点。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规定,1950年秋收后,各地要根据情况相继开展分配土地的改革,在分配土地前应一律实行减租,并按照“召开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同讨论”“召开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宣传政策”“选择有代表性的乡村进行试点”“在试点成功基础上全面铺开”的步骤进行。(12)参见前引,罗平汉书,第330-332页。其中,试点是减租运动的必经程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试点以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为起点。该法颁布之后,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个大区迅速进行土改。各大区和各省全面发动土改前,先进行土改典型试验,再分批推进。土改典型试验是准备土地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13)据学者统计,到1950年11月初,华东有700个典型试验乡;中南的湖北省这年10月开始进行33个乡的土改试验,江西省8月份开始典型试验;西北的陕西省关中地区完成了10个乡的典型试验。有关统计数据还表明,1950年11月,中南土改委员会曾对江西、湖南两省土改试点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发现有20%的试验乡完成了试验任务,30%的试验乡农民尚未发动起来,另有50%介于二者之间。参见前引,罗平汉书,第371-372页。在试验的同时,各大区制定并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实施办法,根据本地实际,对土地改革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细化和补充,使土地改革法更具操作性。(14)参见前引,罗平汉书,第372页。
合作化试点是在互助组基础上进一步的集体化,(15)互助组是我国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劳动组织,土改以后得到广泛发展,基本特征是自愿互利、互换人工和蓄力、共同劳动,有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是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逐步转化,分初级社和高级社两种层级。(16)初级社,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互助组基础上发展而成。在初级社,农民将私有土地、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分社统一经营和使用,产品实行按地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但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同时抽取一定的公积金。高级社,即高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初由初级社发展而成,规模比初级社大,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1958年,高级社发展为农村人民公社。初级社试点最先在东北和山西等老区开展。始于1951年3月的山西长治合作化试点在国内形成较大影响。(17)参见马社香:《农业合作社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高级社试点其实早于初级社。1950年陕西就试办过一个集体农庄。但正式试点应以1951年12月中共中央试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为标志。该《决议(草案)》指出,要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每省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1952年全国试办了10个,1953年试办了15个。(18)参见高华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64页。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各省、市和各自治区党委应注意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些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地方,可根据发展生产需要、群众觉悟程度和当地经济条件,按照个别试办、由少到多、分批分期的步骤逐渐发展,将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至1955年底,除广东、云南外,全国试办了17 000多个高级社,参加的农户为47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19)各地试办合作化的程度不一样。据统计,到1955年底,辽宁省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全省总农户的58%。试验不过两个月,从1956年1月开始,农业合作化就以办高级社为主,全国争先恐后“进入社会主义”。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宣称“率先完成社会主义合作化”,“第一个进入社会主义”。参见前引,高华民书,第266、268页。
1956年的包产到户试点是在整顿高级社、摸索建立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主要包含四川省江津县、浙江省永嘉县、广东省钟山县、江苏省盐城地区和江阴县、陕西省城固县和武功县等地。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包产到户试点,有的是从专管地段责任制试点开始的,如1956年春浙江省永嘉县试点;有的是在包工包产到生产队试点基础上进行的,如四川省江津县试点;有的是在试行“三包一奖”(20)“三包一奖”,即把一定产量任务和应付的工分数以及合作社应开支的生产费用包给生产队,年终结算,超产受奖,减产受罚。节余劳动工分和费用归生产队支配,超支由生产队负担。基础上进行的,如1957年江苏省盐城地区试点。(21)参见前引,高华民书,第266、351-354页。1957年“反右”运动兴起后,包产到户试点受到严厉批判,遂告终止。
“大包干”试点是人民公社时期对生产责任制的改革试验,是对“三包一奖”的变革。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一大二公”带来的平均主义问题很快显露出来。1961年3月,中共中央开始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史称《农村六十条》),以解决这些问题。(22)《农村六十条》先后有四稿。第一稿于1961年3月中央广州会议讨论通过,主要从缩小社队规模和确立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来克服生产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以恢复和确认社员的私有财产权和家庭副业来限制生产队内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第二稿是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在北京工作会议修改通过的。这次修订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恢复了按劳分配。第三稿是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这一稿把农业生产基本核算单位确定在生产队,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度。第四稿于1977年开始修订,仍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同年,河北、湖北等省份的一些单位开始试行“大包干”,(23)即由生产队向大队承包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国家公粮和征购粮,剩余的都归生产队;生产队除按规定提取一定生产费和管理费之外,全部按工分分给社员。把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9月27日邯郸会议上,河北省的“大包干”试点经验得到毛泽东肯定。(24)参见《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1961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把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即实行“大包干”。为全面落实“大包干”,中共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和全国省、地、县各级党委负责人亲自下乡调研,并在各县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从而形成调查试点之风,典型的如邓子恢1961年10月在闽西连城新泉公社调研的北村、龙岩后田、邓厝、孟头等大队开展的试点。(25)参见前引,人民出版社书,第404页。
(三) 1978—2021年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1978年是改革开放开启之年。这一伟大壮举的序幕由农村包产到户试点拉起。这一时期不仅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调整,城市土地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 1978—2012年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从1978年到至2012年的30多年间,农村土地制度共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制、农地使用权抵押制三次改革,每次都从试点突破。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六十条》吸收“大包干”试点经验,确立了以生产队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土地经营制度,并宣布“至少三十年不变”。相较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本经营单位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但并未解决生产队内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民生产积极性仍未调动起来。当时中央政策仍明确禁止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即便1979年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也没有改变这一政策。然而,这一制度被闻名全国的安徽肥西县山南小井村和凤阳梨园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试点突破了。试点很快促成国家政策重大调整并在全国推行,最终形成了当前作为农村土地基本制度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6)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始于1989年。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即将农民永久、无偿使用宅基地的制度改为按一定标准收取一定使用费的制度。(27)收费方式有平均收费法、累进计费法、宅田挂钩法和等级作价法等。平均收费法,即收费标准以略高于大田承包金的原则,每平方米收费0.10元。累进计费法,即对标准内和超标准宅基地采用不同标准收取费用;宅田挂钩法,即宅基地超过标准扣减承包责任田或宅基地分摊提留;等级作价法,即以质划级、按级作价。参见杨重光、吴次芳:《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十年》,中国大地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这一改革首先在山东德州等地试点。(28)参见前引,杨重光、吴次芳书,第70页。1989年5月底,山东省有8个市地的33个县(市、区)、301个乡(镇)、4 315个村开展试点。(29)参见韩立达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山东省的试点得到山东省政府和国务院的认可。1990年《国务院批转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请示通知》规定:“进行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强化自我约束机制。”不过,由于后来各地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现象严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1993年7月印发的《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决定停止收取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和农村宅基地超占费。这一改革暂告中止。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农业结构调整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大量农民进城,土地抛荒严重,禁止耕地使用权流转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农地使用价值、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成为新需求,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改革试点应运而生。200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从2008年下半年起,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各选择2至3个有条件的县、市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探索林权、水域滩涂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受此影响,一些地方开展了农地使用权抵押试点,如山东省寿光市和枣庄市、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试点。(30)这三个试点被称为寿光模式、枣庄模式和法库模式。寿光模式是山东省寿光市采用的,它在办理产权证的基础上,以产权证为据抵押贷款,抵押物包括农民住房、大棚和承包土地等。枣庄模式是山东省枣庄市采用的。农民先以其土地使用权加入合作社,合作社再用土地使用产权证作抵押向银行进行贷款。法库模式是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采用的,与枣庄模式基本相同。参见前引,韩立达等书,第63-65页。
2. 1978—2012年的城市国有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城市土地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国有土地有偿出让与转让制度改革两种。城市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首先于1981年在深圳特区开始试点。1984年广州也参加试点。(31)1984年7月1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广州市征收城镇土地使用费试行办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使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均按本办法的规定交纳土地使用费”。不过,1984年9月,国务院提出要征收土地使用税。同时,财政部发文禁止地方开征土地使用费。虽然如此,这一年,北京、上海以及辽宁抚顺市等地仍开展了征收土地使用费的研究和试验。(32)参见前引,杨重光、吴次芳书,第55-56页。直到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颁布《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以税代费制度落地,这一试验才最终停止。
土地使用税仅解决了土地无偿使用问题,但未解决土地无偿取得和不能转让的问题。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与转让改革随之而来。1987年3月,国务院提出在沿海开放城市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设想,并要求先在沿海城市试点。随后,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深圳、上海、天津、广州、厦门和福州为试点城市,要求它们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通过拍卖、招标、协议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以一定价格、年限及用途出让给土地使用者,出让后的土地可以再转让、出租、抵押。(33)参见前引,杨重光、吴次芳书,第220页。1987年下半年,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34)1987年,深圳于9月9日、9月29日与12月1日通过协商、招标、拍卖方式出让了三块土地。参见前引,杨重光、吴次芳书,第107-108页。随后,珠海、福州、海口、广州、厦门、上海等城市也开展了这一试点,最终促成城市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和转让制度的形成。
(四) 2012年至今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农村家庭耕作方式的局限性进一步彰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新阶段。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二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三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3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为此,党和国家先后推行了“三项制度”和“两权抵押贷款”改革试点以及“三权分置”改革试点。“三项制度”改革试点始于2014年。2014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对三项制度改革试点作了具体部署,决定集体建设用地可直接上市,尝试对超标使用的宅基地收取使用费,允许进城落户农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随后,这一改革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县(市、区)进行试点。(36)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2015年2月25日)。“两权抵押贷款”改革试点始于2015年。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对新时期“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作出安排。随后,这一改革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县(市、区)开展试点。(3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2015年12月27日)。“三权分置”改革试点始于2016年。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推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即“三权分置”改革。《意见》指出,“三权分置改革”是“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下简称‘三权’)分置并行,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意见》要求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充分认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保持足够历史耐心,审慎稳妥推进改革,由点及面开展,不操之过急,逐步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安排”。在《意见》指导下,试点工作全面展开。
综上可见,从土地革命战争时起,试点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土地政策的必要方法,始终如一,可谓“凡改必试”。
三、 百年土地政策试点特质
进一步考察这些试点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试点有其独特性。
(一) 试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践行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试点过程也是试点基本理论的形成、运用过程。新中国成立前的试点为毛泽东实践认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随后毛泽东实践认识论为试点提供了思想指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贯彻了实践认识论,并成为改革试点新的指导思想。
1929年12月,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思想,提出讲话要讲“证据”。他说:“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3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39)前引,人民出版社书,第109、112、115页。这些论述,体现了毛泽东对实践认识论的早期看法。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全面阐述了实践认识论。他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40)前引,人民出版社书,第284页。毛泽东实践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重要成果。观察中国土地政策的试点过程可以看出,试点其实不过是毛泽东实践认识论的实践化,且已进一步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代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可以看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立足于实践认识论,与试点的工作方法相融通。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思想起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度成为党和国家根本性的思想共识,先行试点、由点到面继续构成党的政策形成与执行的基本方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4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实践中,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就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先行试点。”(4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工作时指出,五年来,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判断和论断,“这个历程很不平凡,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规律、深化认识、统一思想、正确决策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2页。
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试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实践。这意味着,在本质上,改革试点是对改革设想的验证,其根本价值在于发现主观认识的错误,即试错。这造成了改革方案(拟定中的法律制度或政策)的暂时性、局部性和不确定性。
(二) 试点具有实施或创制土地政策两种属性
百年土地政策试点表明,试点具有实施与创制两种功能属性。
实施性,即试点是为执行中共中央土地政策进行的。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和邓子恢在闽西永定溪南里开展的土地革命试点,就是为执行中共中央的“八七会议”以及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而进行的。抗战时期的试点,如1942年山东省滨海地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试点,是为执行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确定的减租减息政策而实施的。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绥德、庆阳、关中地区开展的土地征购试点是为执行“五四指示”而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试点是为执行1950年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而进行的。合作化试点,除了1951年初山西长治等地自发进行的外,都是对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和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的执行。(45)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每省一个至几个。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提出,各地党委在制订合作化规划时,应注意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61年各地开展的“大包干”试点,除了河北、湖北两省是自发进行的外,都是为执行196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而进行的。2014年开展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和2015年开展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以及2016年开展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其实都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相关内容的执行。可见,实施性是我国土地政策试点的一个基本属性。
试点的实施性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在于探索既定政策的最优执行方式,而不是验证政策的正确性。这种情况下,试点本质上是政策逐步推进或波浪式推进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推行政策的一种渐进式方法。1943年减租减息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造的“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亲自蹲点,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经过典型试验,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一般”的工作程序和方法,(46)参见前引⑧,董志凯、陈廷煊书,第62页。就是对这种试点性质的经典表达。
创制性,即试点是为探索新政策进行的。地方、基层、农民自发的试点多属于这一类。地方党委和基层组织推动的创制性试点较多,如1951年山西长治初级社试点、1956年浙江永嘉包产到户试点和1961年河北等省“大包干”试点等。山西长治初级社试点是在省委支持下由地委推动的。中共中央是在地方试办合作社的推动下才于1951年12月提出合作化设想的。(47)参见前引,马社香书,第1-6页。1956年浙江永嘉包产到户改革试点则是由县委推动的。当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的宣传文章。受此影响,永嘉县委于5月选派干部到雄溪燎原农业社开始试验包产到户责任制。1961年中共中央确定“大包干”政策并进行试点之前,河北等省已经先行进行试点并取得经验。此外,1981年深圳特区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试点、1989年山东德州的宅基地有偿使用改革试点等,也是由地方党委推动的。历史地看,上述试点最终被中共中央政策吸收,地方政策最后演变为中央政策,成为中共中央政策试点的先声,为中央土地改革政策的形成发挥了探索功能。
农民自发试点的典型是1978年安徽小井村和小岗村包产(干)到户试点。1978年秋,安徽大旱,麦子种不下去,省委决定把部分耕地借给农民耕种。在“借地”过程中,有的社村,如肥西县山南小井村,干脆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户,包产到户就在这种“明借暗分”过程中开启。(48)最先试验包产到户是小井村还是小岗村,有不同说法。对本文而言,先后之分没有太多意义。凤阳县梨园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也是在农民面临严重生存危机时自发开展的。那份印有18个红指印的“生死承包契约书”足以说明这一点。(49)参见武文胜、艾琳:《1978小岗村改革始末》,载《读书文摘》2013年第5期。1979年春播时,由于这些试点的促进,尽管中央还明确禁止,省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安徽省委还是决定把山南作为包产到户的试点,试验一年。省委意见传达后,不仅山南普遍推行了包产到户,其他县也自主试行了包产到户。(50)山南区试点后,包产到户很快席卷了整个肥西县,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40%。1979年,推行包产到户的除肥西外,还有宣城、芜湖、无为、肥东、长丰、颍上、固镇、来安、全椒、嘉山、阜南、六安等县,包产到户大有覆盖全省的势头。参见马社香:《对山南小井庄包产到户试点的回顾与思考:周曰礼访谈录》,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历史表明,这些试点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壮举,很快转化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自觉的大范围的试点,最终导致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
不过,试点的实施性与创制性并不是决然分离的,实施性试点也具有一定的探索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中共中央政策在某些方面不明确时,试点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创制功能,如1928年毛泽东和邓子恢开展的土改试点对土地分配方式的创新实践;二是当中共中央推行的政策,特别是执行方法具有裁量空间时,试点对于政策执行方法具有探索性。
试点的实施性与创制性区别意味着对两种试点的组织实施与评价标准应有较大差异。实施性试点因是对中央政策或国家法律的执行,试点的试错功能少有发挥空间;创制性试点是对新制度或新政策的局部性探索,试错功能的客观发挥对于改革推行至关重要。
(三) 土地政策试点一定程度上也是法治试点
土地政策试点虽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展开的,但在本质上也是土地法治改革试点。从与立法的关系看,百年政策试点大致可分为“先试点后立法”模式和“先立法后试点”模式以及介于其间的“先制定条例草案后试点”和“先制定试行法后试点”等模式,总体呈现政策试点与立法试验交相辉映、相互促进的法律制度演进特质。
“先试点后立法”是毛泽东在井冈山采用的试点模式,具体包括拟定初步方案、局部地方试点、调研并总结经验、召开大会制定土地法、全面实施等5个阶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从1928年2月到5月,毛泽东先后派毛泽覃或亲自到江西宁冈大陇的乔林、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中村、湖南桂东山田、江西永新西乡塘边一带进行分田试验。(51)参见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毛泽东还先后到宁冈和永新深入调查,写下《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在此基础上,1928年12月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井冈山土地法》,在根据地全面推行分田政策。从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观察,井冈山试点、闽西永定溪南里试点、陕甘宁边区和平征购试点、新中国成立后新解放区的土改试点等为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特别是1950年土地改革法的制定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1950年土地改革法确立的土地制度不过是上述试点经验的法律化。(52)这些制度包括: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而非所有土地,对公地采取征收的方法,对富农土地仅在特定条件下征收,在原耕地基础上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民,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并适当考虑土地远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而非共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试点、包产到户试点、城镇国有土地有偿转让试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农民承包经营权流转与抵押制度试点、宅基地有偿使用与抵押等制度试点等,最终都推动了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制定和修订。
“先立法后试点”是为实施法律(或中央政策)进行的试点,典型的如邓子恢在闽西永定溪南里进行的土改试点,具体包括调研讨论、拟定分田方案、民主表决立法、局部试验、全面推广5个阶段。1928年8月,邓子恢在福建永定县溪南里开展分田运动。他先深入群众,召集农民一起开会讨论,定出分田方案,(53)不同于井冈山土地法,溪南里土地法在分配土地时采用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的方法。参见前引,杜润生主编书,第81页;苏明辉:《论〈溪南里土地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然后召开全乡群众大会讨论,经苏维埃政府通过。(54)有的文献认为是经全乡群众大会讨论,如前引,苏明辉文。有的文献认为是经苏维埃政府讨论通过,如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页。但通过后,不是立即全面实施,而是先在金砂乡试点。试点后,才在溪南里全面推广。(55)参见前引,杜润生主编书,第81页;前引,苏明辉文;前引,余伯流、凌步机书,第311-312页。1929年6月,邓子恢到龙岩开展土地分配工作,推行了《溪南里土地法》。当然,《溪南里土地法》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为取得经验,龙岩县委仍先在白土后田进行试点,然后在各区乡普遍实行,也算是先立法后试点的实施性试验。(56)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119-120页。
“先制定条例草案后试点”模式,即在拟定条例草案后进行试验,而后根据试验情况调整并制定正式法律。“条例草案”是立法的先期工程,针对草案进行试点,试验性质更加明确,功能也发挥得更加充分。这种模式首先在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土地征收制度试点时采用。1946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以贯彻减租,并采用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57)前引,罗平汉书,第55页。据此,边区政府于1946年12月26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草案》。随后,绥德、庆阳、关中三个分区派出大批干部到未分配土地的县、区、村开展土地征购试点,如绥德新店区试点。1947年2月13日,边区政府基于试点经验对《条例草案》进行修订,并公布了正式的《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58)参见前引,罗平汉书,第55-57页;前引⑨,张卫波书,第30-31页。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化过程中也采用这一模式。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即后来的高级社——作者注),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依据决议草案进行的试点自然也属于“先制定草案后试点”模式,只是这个是决议草案,不属于法的范畴。后来的“大包干”试点也采用的是这种模式。1961年3月中央广州会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后,河北、湖北等省就进行大包干试点并得到毛泽东肯定。(59)参见薄一波:《〈农村六十条〉的制定(六)》,载《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4年第9期。同年10月,中共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和全国省在各县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经试点,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不过,这个条例仍称草案,且一直是党内法规;其间,虽有人提议立法,但终没有以法的形式出现。(60)参见薄一波:《〈农村六十条〉的制定(三)》,载《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4年第6期。
“先制定试行法后试点”模式,即为执行“试行法”进行的试点。“试行法”指名称中包含“试行”或“暂行”的法律文件,既然为“试行”或“暂行”,就应具有试验性。不过,较之于“草案”,“试行法”更为正式。这种模式最早于抗战时期在山东减租减息试点中采用。1940年11月11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1942年5月15日,中共山东分局相继制定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和《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明确了减租减息的方针、方法、步骤和具体要求。随后,山东分局按照从典型示范、中心突破到全面铺开的步骤,把莒南、临沭两个县作为试点县。鲁中区委把沂水县埠前庄、马牧池作为试点村,鲁南区委把费滕边作为实验县,胶东区委把文登县的万家庄、牟平县的昔垛山区等作为试点区,开展试点。(61)参见前引⑦,陈国庆书,第132、135-137、142-145页。新中国成立后,试行法仍然被大量制定,为实施试行法的试点自然也不在少数。
总之,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试点史也是中国土地法治试验史。不论是对执行性试点还是创制性试点,总是牵动着法治的神经。按照法治逻辑评价,土地法治试验的模式不同,试点的正当性不同。“先试点后立法”与“先制定条例草案后试点”模式的正当性低,“先立法后试点”与“先制定试行法后试点”模式的正当性高。
四、 百年土地政策试点经验
中国共产党百年土地政策试点推动了我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但期间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分析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可得出以下几点经验。
(一) 主体:尊重和激励地方、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
纵观百年土地政策试点史,可以看出,地方、基层和群众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始终发挥先锋作用,许多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都是由地方、基层或普通农民通过试点推动的,是基层改革带动了国家改革,这再次印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著名论断。(62)“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为了人民干事创业,依靠人民干事创业。”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日。
在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变革过程中,1928年毛泽东和邓子恢作为井冈山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的地方负责人,在充分听取农民意见的基础上,确立的“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法,不仅为当时土地分配工作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也为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分配工作提供了经验,最终被土地改革法所吸收,成为我国土地改革的最重要制度之一。在从新民主主义土地制度向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变革过程中,在中共中央提出合作化政策之前,1950年陕西的高级合作社(集体农庄)试点和1951年山西长治的初级合作社试点已经开了先河。在集体生产责任制探索过程中,河北、湖北等省于1961年率先试行了“大包干”,从而在1962年《农村六十条》中确立了以生产队为基本经济核算单位的经营制度,这一制度实施了16年。包产(干)到户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而这完全是由地方、基层和农民自发推动的。1956年浙江永嘉、四川江津、广东钟山、江苏盐城等地的试点是在中共中央政策不够明朗的情形下由地方基层党组织推动的,1978年安徽小井村和小岗村试点则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明令禁止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正是由于地方、基层和农民不屈不挠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共中央才于1980年9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决定把包产(干)到户作为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办法;于1982年发布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公开承认包产(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合法形式。(63)参见前引,武文胜、艾琳文。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中共中央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强调,地方、基层和群众改革试点的空间缩小,但一些改革如山东农民宅基地的有偿使用试点仍然成为中央土地政策变革的先声。
地方、基层和群众往往是改革利益的最大关切者,最贴近和了解工作和生活实际,因此,他们不仅富有首创精神,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往往更符合客观实际。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时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6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时指出:“万里同志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认为‘一切新的创造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群众的实践’。”(65)习近平:《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自己也反复强调要积极发挥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2012年,他指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66)前引,外文出版社书,第68页。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再次强调:“事实充分证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2018年,他再次强调:“我们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既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又坚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确保了改革开放行稳致远。”(67)前引,外文出版社书,第188-189页。
从法治角度看,要尊重和发挥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就必须在法律上确认地方、基层和群众参与试点的主体地位。同时也须注意,赋予地方、基层和群众的试点主体地位可以凝聚改革力量,汇聚改革智慧,但也会导致试点的盲动性和无序性。
(二) 体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试点成功的根本保证
政策试点的顺利推进和全面推广是衡量试点成功与否的标准。考察百年政策试点可以发现,地方、基层与群众试点成果要实现由点到面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方案不仅要符合客观实际、取得好效果,更要上下协调,得到上级特别是中共中央的认可。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百年土地政策试点成功的根本保证。
政策试点的路径与性质不同,上下级之间的协调难度不同。我国的土地政策改革试点,首先,可以将决策路径为标准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自上而下的试点,即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等决定开展的试点,地方试点单位只是执行上级的试点决定;自下而上的试点,则是由地方、基层或人民群众自行开展的试点。其次,如前所述,我国土地政策试点可以功能为标准分为实施性和创制性两类。实施性试点旨在执行上级政策或法律制度,创制性试点则在探索创制新的国家政策或法律制度。这两类可排列组合成四种。其中,所有的实施性试点与自上而下的创制性试点,试点都是执行上级决策、政策或法律的,一般会被上级密切关注,阻力小,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的概率大。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试点、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征购和土地改革试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试点、1961年邓子恢在闽西推行的“大包干”试点以及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和“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等莫不如此。
但是,自下而上的创制性政策试点,因其会突破现行国家政策或者国家法律,面临的风险更大,能否成功推广完全取决于能否取得上级的认可和支持。典型的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试点,虽然内容、性质和效果基本相同,但1956年浙江永嘉试点和1978年安徽小岗村与小井村试点的最后境遇截然不同。浙江永嘉试点起初也得到县委、地委甚至省委部分领导支持。但到第二年3月,浙江省委、地委转而反对,试点遂告失败。(68)参见李云河:《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遭遇》,载《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5期。安徽小井村和小岗村试点后,虽然第二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文章,对包产到户进行批判,但因得到省委书记万里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终得全面推广。(69)参见吉景峰:《凤阳农民大包干纪实》,载《上海农村经济》2008年第7期。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相似的是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1989年山东省德州等地的试点,起初虽然得到山东省政府和国务院的支持,但因条件不成熟,后来也中止了;2014年中共中央推动的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则在国务院安排下,得以有序推进。除了这些改革试点之外,1950年陕西的高级社试点、1951年山西长治的初级社试点、1961年河北与湖北等省的“大包干”试点,这些试点尽管与当时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相左,但由于得到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肯定,最后都上升为中央政策从而在全国顺利推广。
在百年土地政策试点过程中,试点决策或审批主体及其权限并不明确,目前见到的仅有合作化时期关于试点审批权限的规定。1954年11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明确指出,试办高级社由省一级领导机关批准。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规定,这一时期试点的批准权下放至县、区。但这属于中共中央推行的试点。从有关文献看,许多自下而上的政策试点都是由上下级领导通过个别沟通方式推动的。例如,1951年山西长治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是省委书记与地委书记个别磋商推动的。试办后,华北局领导不同意,地委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并取得支持,试点得到推行。(70)参见前引,马社香书,第4-5、46页。1956年浙江永嘉包产到户试点源于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一文。受此文启示,永嘉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向地委农工部部长请示,得到支持并决定在永嘉三溪区燎原社试点。试点后,得到县委认可,从而全县开展“多点试验”。改革开放以来,改革试点如火如荼,对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献,但对于改革试点的决策主体及其权限,仍缺乏明确规定。《全面依法治国决定》要求先行先试“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但迄今还没有就此制定专门的程序性法律。
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张蓝图抓到底,抓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不能拍脑袋、瞎指挥、乱决策,杜绝短期行为、拔苗助长。另一方面,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及时总结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我们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71)前引,中央文献出版社书,第48页。这一论述不仅为处理顶层设计、整体推进与摸着石头过河、重点突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指引,也为处理改革试点过程中的上下级关系提供了指引。
应该说,“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与“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整体推进”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从法治视角看,欲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就必须用法治手段完善改革决策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基层、群众之间改革试点的决策权限以及改革试点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三) 权责:参与者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由法律明确
百年土地政策试点过程中也曾出现令人痛心的案例,地方、基层和群众曾因改革试点而遭受迫害,改革对象或第三人的权益也曾因改革试点失控而造成损害。
地方、基层和群众曾因土地政策试点遭受迫害的事件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典型案例当属浙江永嘉包产到户试点。这次试点被叫停后,受1957年“反右”运动影响,不仅试点受到批判,许多参与试点的干部被划为“右派”,撤职开除,甚至判刑入狱,家属也受牵连。例如,当时积极推动试点的县委书记被定为“中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副书记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工厂劳动改造,妻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县委农工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县农业局局长被开除党籍、撤销公职;农工部干事被划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3年,剥夺政治权利21年。(72)参见前引,高华民书,第266、384-385页。这虽然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特殊现象,但也说明,改革试点决策者、实施者的权利保障非常重要。借由这个历史事件,就可以理解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推行包产到户改革时,何以会签订试点生死契约书。
改革试点过程中也存在损害改革对象或第三人权益的现象。1929年7月召开的党的闽西“一大”就认为,1928年闽西永定溪南里试点工作,“烧了一些不该烧的屋,杀了一些不必杀的人,焚烧商人账簿,没收丰稔市的商店,则是犯了盲动主义缺点”。(73)孔永松:《关于〈溪南里土地法〉主要内容的考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试点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晋绥根据地兴县木栏杆村土改试点。该村有2 000多亩土地,除了居住在其他村的地主的1 000多亩,整个木栏杆村人均土地不到3亩,无一户靠剥削为生。张氏兄弟的土地略有长余,但也是普通种地农民,其他40多户都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如此一来,这个村子就找不到地主。于是,在上级领导指示下,试点工作队便采用查三代的办法,只要其祖父、父亲够得上地主或富农,就将其划为破产地主或富农,甚至只要祖坟有围墙、石碑,就将其划为地主或富农。张氏弟兄辛苦劳作积攒了200元大洋埋在地下,被工作组挖出,定为地主并被枪毙。(74)参见前引,罗平汉书,第118-120页。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
目前,全面深化改革不仅面临任务艰巨的问题,也面临动力不足问题。为此,党中央提出“要宽容改革失误”与“建全容错纠错机制”。《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区分”的思想,对宽容改革、容错纠错机制作了具体指示。(75)参见前引,外文出版社书,第225页。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专门就容错机制的实施作了详细规定,重述了习近平关于改革容错的基本思想。长远来看,这些规定还需要进一步法律化,尤其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加以细化。
要承认地方、基层和群众的试点主体地位,发挥其首创精神,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手段确认其试点的权力(利)和职责,还要对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特别规定,使试点决策与实施主体的权、能、责法定化。要使试点得到人民的支持、顺利推进,就必须针对试点的局部性、暂时性和不确定性等特殊性,用法律手段切实保护试点对象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四) 程序:以法定程序保障试点的充分性与客观性
除了试点参与主体和试点对象权利保障问题,期限太短、缺乏正式评估从而使试点效果缺乏客观性,也是百年土地政策试点中暴露出的问题。
试点效果的客观性取决于试点范围的广泛性、试点期限的适当性和试点评估的科学性。而试点范围、试点期限和评估方案要根据试点事项来确定。农业生产周期多为一年,影响农业产量的因素多元而复杂,通常须试点多年才能见分晓。但在我国土地政策试点过程中,有些土地政策试点的时间太短,范围过窄,往往用新闻报道和个别调查替代了科学评估。合作化试点是这方面的例证。初级社于1951年在山西长治等个别地方试点,年底就开始试办高级社。1952年全国仅试办10个,1953年全国仅试办15个,随即合作化高潮就在全国兴起。1956年1月,北京率先完成社会主义合作化,第一个进入社会主义。(76)参见前引,高华民书,第266、268页。1956年秋不少地方就发生“闹社”“退社”风潮。对于当时的农业合作化,邓小平认为速度太快:“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7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7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应当说,合作化改造之所以过急过快,与当时没有客观地对待合作化试点不无关系。
对于改革以及改革试点评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就强调:“实践告诉我们,有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有偏差,要扭转回来很不容易。我们的政策举措出台之前必须经过反复论证和科学评估,力求切合实际、行之有效、行之久远,不能随便‘翻烧饼’。”(79)前引,中央文献出版社书,第42页。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又指出:“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新经验新创造,要及时总结提炼,在政策制度层面固化下来。要做好改革评估工作,加强改革举措评估、改革风险评估、改革成效评估,确保各项政策制度切合实际、行之久远。”(80)《凝心聚力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把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载《人民日报》2019年8月1日。
从目前试点实践看,制定试点方案时都明确规定了试点期限,但试点期限过短者不乏其例;试点也得到评估,但评估的科学性仍有待加强。因此,要保证试点的充分性和评估的科学性,有必要对试点期限、评估等必要程序通过立法作出原则性规定。
五、 结 语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改革试点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变革方式。大多数改革试点,尤其是创制性试点,不仅具有变法性,还具有局部性、暂时性和不确定性,不能“先立(修)法后改革”,从而成为改革与法治共同推进的难点所在。针对试点法治的特殊性,《全面依法治国决定》和立法法已经确立了先行先试授权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矛盾性,但并未解决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试点的所有问题。
中国共产党百年土地政策试点史首先表明,从土地革命战争时起,试点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或执行土地政策的必要方法,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从试点开始,通过试点推行;政策试点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而非西方的实用主义,根本目的在于揭示主观认识的可能错误,其本质是试错;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试点并不全部具有创制性,相当部分的试点是为执行中央政策或法律进行的,实施性也是其重要属性之一。不论是创制性试点还是实施性试点,都属于法治试验的范围,共同推动着土地法律制度的深刻变革。
中国共产党百年土地政策试点史还表明,最富开拓性的制度变革试点是由地方、基层和群众的推动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地方、基层和群众自发的试点,没有上级特别是中央的认可和支持,很难取得成功。此外,在土地政策试点过程中,试点参与者以及试点对象的权利也曾遭受侵害,试点中也曾经出现盲动主义和形式主义现象。对于我国改革试点中面临的法治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系列要求,当前急需的是尽可能地加以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以明确试点主体、试点审批体制与程序、试点参与者的特别权力与责任以及试点的基本程序。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是在“以史为鉴”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思维导向下进行的实证性研究,旨在揭示试点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历史地位、特点性质和成就经验等问题,由此提出的制度建构问题则是后续要研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