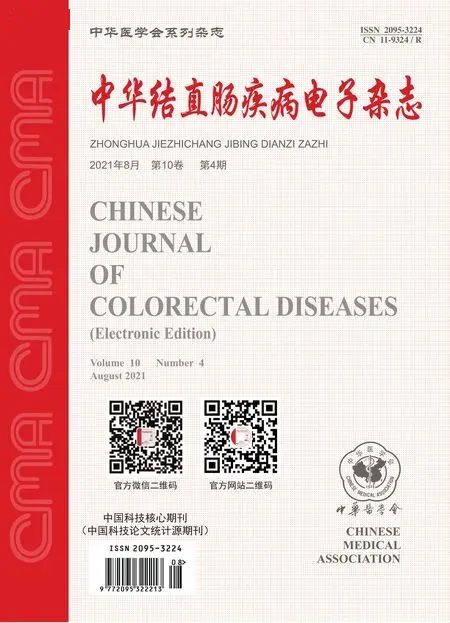循环生物标志物在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预测中的应用
周小妹 罗波 梁新军
直肠癌是世界上致死率较高的四大肿瘤之一[1],目前直肠恶性肿瘤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是新辅助放化疗。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LARC)中,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认为新辅助治疗能导致约21.1%患者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先前研究显示评估pCR的标准方法是对组织学标本的检查,并且进一步观察到达到病理缓解的患者有肿瘤组织的消退;但是临床反应并不总是与组织学变化有关,可能也与循环中的标记物有关;所以需要进一步的对循环中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进行研究,由于循环标志物在癌症治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为预测患者是否对新辅助治疗有无应答提供了依据。因此本文对预测性循环生物标志物在直肠癌新辅助治疗中的应用进行了总结。
一、循环肿瘤细胞
离开原发肿瘤部位,通过血管和淋巴系统在血液中传播,并导致远处继发性肿瘤形成的上皮细胞被定义为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2-3]。CTCs转移是导致大多数肿瘤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且外周血中CTCs又被认为是导致转移的主要原因。所以对外周血中CTCs精准的检测和分析对研究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但是在大多数肿瘤患者的外周血中CTCs的浓度并不是很高,一般维持在1~10个细胞/10 mL之间,这使得CTCs的研究更具有挑战。尽管如此CTCs仍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恶性肿瘤的研究中。目前CTCs主要被用于部分疾病的预后判断和治疗方案的参考,比如转移性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4-6]。CTCs正成为新型抗癌治疗和疗效评估的有效预后因子[7]。
通过细胞搜索系统的方法,Magni等[8]检测并计算了85例LARC患者中的16例(18.8%)在nCRT之前的CTCs数,中位数为1个细胞/7.5 mL,范围为1~27个细胞/7.5 mL。尽管术前CTCs的数量与患者的临床或病理特征无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但在连续的时间点上,CTCs计数显著下降:术前24小时的CTCs计数为7.5%,术后6个月的CTCs计数为4.8%(分别为P=0.021和P=0.047)。几乎63%的LARC患者对治疗有病理上的完全或部分反应,他们在nCRT前和手术前的CTCs计数与CTCs数量的减少有显著的相关性(P=0.02)。
Sun等[9-10]通过微流控设备的技术[11],对LARC患者在nCRT前后血液样本中的CTCs进行了计数。nCRT前CTCs水平明显高于nCRT后(两项研究均P<0.001)。根据Dworak TRG评分,在对有反应和无反应的患者进行分层后,在无反应组中,nCRT后CTCs计数和nCRT前后CTCs水平的百分比差异(定义为∆%CTC)均有统计学意义。根据ROC曲线,∆%CTC值在第1次和第2次研究中正确分类的准确率分别为80.6%和86.0%。
最近,Troncarelli等[12]通过评估胸苷酸合酶(TYMS)和紫外线切除修复蛋白RAD23同源物B(RAD23B)的预测价值进一步探索了CTCs在直肠癌患者接受nCRT后的作用。这项研究结果显示,CTCs中的TYMS mRNA和RAD23B蛋白的表达可能预测nCRT的无应答反应,并避免对在新辅助治疗后能达到pCR的LARC患者进行根治性手术治疗。
二、循环肿瘤DNA
在癌症中检测到的由肿瘤细胞凋亡、坏死后释放到血管中的DNA为循环肿瘤DNA(ctDNA)。ctDNA是长度约为60~110 bp固定的几个DNA片段,它主要以核小体的形式释放入血。血流中的ctDNA可以反映肿瘤细胞的分子变化,如突变[13]、甲基化特征[14]和微卫星不稳定性[15]。
Sun等[16]观察了34例LARC患者和10例健康人血浆中的ctDNA水平,发现LARC患者血浆ctDNA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新辅助治疗后LARC患者的血浆ctDNA水平下降。缓解者在接受nCRT治疗后不仅代表非凋亡(或可能是肿瘤)的ctDNA的较长片段降低了,而且代表总ctDNA的较小片段中较长片段的比例也降低了。这些发现与之前报告的结果一致[17]。这表明ctDNA水平的降低可能是放化疗诱导肿瘤消退的结果。此外,在治疗后血浆ctDNA上的KRAS基因第12位密码子突变频率显著降低,缓解者(治疗前:66.7%,治疗后:10.0%,P<0.001)和无缓解者(治疗前:83.3%,治疗后:16.7%,P=0.01)均显著降低。相反,在nCRT前,缓解者的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无缓解者(分别为88.9%和50%,P=0.04)。
循环肿瘤特异性DNA甲基化虽然和肿瘤性疾病的预后及疾病状态有一定关系,但是MGMT和直肠癌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Sideris等[18]表明,MGMT表达状态和直肠癌新辅助治疗的预后之间没有联系,然而Shalaby等[19]又证明了血液和肿瘤组织中MGMT甲基化与直肠癌的治疗具有很好的关系。所以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MGMT甲基化与直肠癌治疗之间的关系。
最近Tong等[20]也对局晚期直肠癌患者的基因进行了分析,并且比较了30例转移性直肠癌的患者血液中ctDNA和CEA水平对新辅助治疗反应的预测评估。结果显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通过CT检查能够检测出20个疾病进展事件;然而ctDNA预测进展事件明显高于CEA[分别为16例(80%)和6例(30%),P=0.04]。并且当ctDNA和CEA都预测到这些进展事件时,ctDNA的升高明显早于CEA的变化(P=0.046)。此外有28名直肠癌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后进行长达2年的ctDNA的监测,有6/28例(21%)的患者出现了复发,但是在这些复发的患者中有一部分在复发时和复发前就已经出现了ctDNA的升高,由此可以看出检测ctDNA可以应用于临床预测新辅助放化疗的疗效。
三、循环中的miRNA
长度为19~25个核苷酸的小分子microRNAs(miRNAs),而且能高度稳定地存在于血液中[21]。有研究检验循环miRNAs作为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预测LARC患者肿瘤放化疗耐药的潜力。
Azizian等[22]检测行同步放化疗的42例LARC患者血浆中5种miRNAs的表达谱。他们证明了miRNAs的表达水平在不同的时间点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在治疗前和治疗结束后,miR-18b和miR-20a水平的降低(≥4%)与术后淋巴结阴性分期显著相关(分别为P=0.023和P=0.024)。以miRNA下降4%为界值,应用ROC曲线评价术后淋巴结阴性分期的miR-18b和miR-20a的鉴别能力,特异性分别为50%和57%,敏感性分别为67%和75%,阳性预测值分别为35%和41%,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9%和85%,准确度分别为56%和62%。研究者认为,对两种miRNAs血浆水平降低的评估可作为预测nCRT反应不良的生物标志物。
使用组织微阵列技术,D'Angelo等[23]分析了38例LARC患者术前活检组织中miRNAs的表达谱显示:11个miRNAs被鉴定为能够区分有缓解和无缓解的患者。其中miR-125b是由ROC曲线确定的最有希望的分子,其曲线下面积(AUC)为0.9026(P=0.0007)。测量发现同一患者术前血清中miR-125b的表达水平与在肿瘤组织中观察到血清miR-125b反映的相同表达谱,相对于癌胚抗原(CEA)而言,区分无缓解患者的能力明显较高。(AUC=0.7821,P=0.008和AUC=0.5781,P=0.416)。
Yu等[24]描述了一种类似的方法。在pCTR敏感和nCRT耐药的组织之间鉴定了表达不同的16个miRNA的分子特征(P<0.05)。经定量聚合酶链反应验证后,选择miR-345作为87名LARC患者血清样本分析的候选物,因为miR-345会在血清中增加且在无缓解患者中观察到miR-345是最显著的。无缓解患者血清中的miR-345水平显著升高(P=0.002),计算出ROC曲线AUC值为0.69(P<0.001)足以区分缓解者和无缓解者。并且在42名LARC患者的验证组中将循环中的miR-345的发现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从而得出结论,miR-345可能被用作个性化治疗策略的外周血预测生物标记物。
四、循环蛋白
多项研究分析了治疗前外周血CEA水平与治疗反应的关系,当CEA水平在2.5~5.0 ng/mL范围内则反应出与完全缓解相关[25]。但没有真正评估或确认CEA在预测患者对nCRT的反应的预测能力。有一项研究报告了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30%和83%),而另外两项研究报告了ROC曲线AUC值,从0.63到0.65的CEA水平作为患者反应的预测因子[26-28]。CEA水平与临床参数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数据的结合可以提高预测性能[29]。根据对低CEA和高CEA水平患者的简单比较,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CEA是一个有潜力的预测生物标志物。然而,在这里很难区分真正的预测值和CEA内在的预后能力[30]。除了nCRT前的CEA水平外,新辅助治疗后CEA水平的正常化与pCR相关,且最近有研究表明[31],癌胚抗原指数下降的LARC患者在新辅助治疗后更有可能达到病理完全缓解。
碳酸酐酶-IX(CA-IX)是在肿瘤缺氧时产生的一种肿瘤特异性蛋白[32]。Hektoen等[33]评估了接受短程新辅助化疗和nCRT治疗的LARC患者的循环CA-IX水平。结果显示:在随后出现肿瘤降期和淋巴结阴性的患者中,初始化疗后血清CA-IX升高。
金属蛋白酶可溶性组织抑制因子-1(TIMP-1)在结直肠癌患者的血浆和肿瘤组织中显示升高[34]。在直肠癌患者中,观察到nCRT后TIMP-1有增加,提示TIMP-1在接受了nCRT的LARC患者中具有潜在的预测作用[35-36]。也有研究显示TIMP-1较CEA更能提供更强的疗效预后信息[37]。
Dreyer等[38]评估了79例直肠癌患者在nCRT后系统性炎症标志物的变化,其中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的比值与nCRT的不良病理反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2)。并且有研究强调其作为接受nCRT治疗的直肠癌患者总体生存率和复发率的预测指标[39]。
五、循环多肽
循环多肽组是生物标志物的另一种来源。肽组是一种亚蛋白质组分,肿瘤分泌的蛋白酶积极参与微环境入侵,并产生蛋白质片段和肽扩散到循环系统[40]。
最近,利用纳米多孔硅胶芯片(NSC)采集血浆多肽,对nCRT前的直肠癌患者的循环多肽进行分析[41]。通过一个简单的MALDI-TOF/TOF分析,鉴定了肽特征,显示了缓解者和非缓解者的LARC患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应用随机森林分类来改进结果,并确定了三种肽的子集潜在地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提供了77.8%的总体敏感性、91.7%的特异性和86%的总体准确性,以及AUC为0.92。
六、抗肿瘤免疫相关细胞因子
抗肿瘤免疫反应细胞因子也可能具有预测价值。有研究显示白细胞介素-6和白细胞介素-8在内的细胞因子与直肠癌的nCRT有关[42]。Tada[43]对35例直肠癌患者在nCRT前后的血清样本进行了多重免疫测定,检测了IL-2、IL-4、IL-6、IL-10、干扰素-γ(INF-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单核细胞区划蛋白-1(MCP-1)、C-C基序趋化因子配体-5(CCL-5)、TNF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和可溶性CD40配体的浓度。虽然在进行nCRT之前,细胞因子水平与对nCRT的反应没有显著相关性,但在进行nCRT之后,无缓解者的白细胞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显著高于缓解者,而且在进行nCRT之后,缓解者的可溶性CD40配体和CCL-5水平显著降低。
七、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
许多研究评估了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LR)对nCRT反应的关系。Caputo等[44]检测了87名直肠癌患者在nCRT前后的NLR和衍生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d-NLR)。nCRT后较高的NLR和d-NLR与nCRT反应差和术后并发症显著相关。Dong等[45]将959名直肠癌患者分成7个研究队列评估NLR在直肠癌中的预测价值,研究结果表明NLR的升高与总体生存期(危险比=13.41,95%可信区间=4.90~36.72),无病生存期(危险比=4.37,95%可信区间=2.33~8.19)和无复发生存期(危险比=3.64,95%可信区间=1.88~7.05)相关。
八、结论
综上所述,循环中的肿瘤细胞、游离核酸、蛋白质和肽等细胞和物质会随着肿瘤负荷、治疗效果和疾病复发而变化,所以循环生物标志物的检测给评估肿瘤治疗疗效预测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微创方法。近年来的研究虽然不断提示生物标志物对新辅助治疗后直肠癌完全缓解的潜在预测价值的证据,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优化分离和纯化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方法和检测方案标准化是未来重要的方向,因为这是获得良好灵敏度和正确评价结果的关键。另外,大多数研究本身无法达到生物标志物预测价值的正确研究设计或纳入病例数量有限,因而需要更加合理的临床研究设计。特定的肿瘤生物标志物和液体活检预测nCRT的治疗反应对于优化直肠癌局部治疗是非常有前景的,同时对于检测残留疾病和早期复发癌症也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