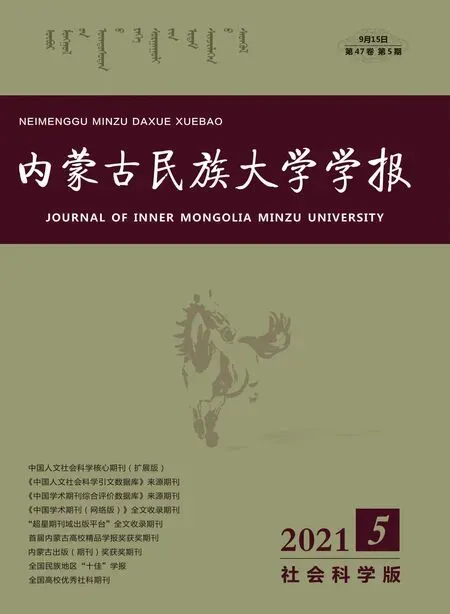试论先秦文学中的北方民族
温一格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2)
由于坐落于亚洲大陆东端,地势形态丰富,气候特点多样,有着极大的地理区域的差异性,我国从可追溯的历史时期以来就存在着同样丰富且复杂的人类活动与区域文明的构成状态。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依赖于不同地理区域下迥然不同的自然资源,有依草原生存发展的游牧民族,也有定居耕耘的农业民族,亦有结合狩猎、采集、农耕多种生产方式的山地民族。丰富而多样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促使了多样的民族及文化形态的形成,草原占据了我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四十,是我国国土资源的重要构成,生活在中原以北的广袤草原之上的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各个民族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蓝天白云之下风吹草低,牛羊成群,绵延万里而一望无际,草原的广袤总是为人们津津乐道。从地理区域而言,杂草丛生、间或有耐旱树木的广袤区域被称为草原,从这样的意义来说,在黄河流域以北,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其间宽阔苍茫的大地就是令人神往的草原。在这个北方生态圈内,与地理区域相匹配的“逐水草而居”的以游牧游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应运而生,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在生产生活方式与精神风貌上有所区别的独特的北方诸民族。据有文献记载的上古时期始,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聚居地周围,就存在着多个被称为“蛮、夷、戎、狄、羌”的、与中原地区的定居种植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其他民族(部落),如果说中原黄河流域所形成的是旱作农业文化,那么北方的“戎、狄、羌”等则开启了游牧文化之歌。
《史记·匈奴列传》阐明唐虞时期居于北方的以“畜牧”为生存方式的部落有“山戎、验狁、荤粥”,三国时期韦昭与唐代司马贞均认为,殷商时期北方有“獯(荤)粥”,可能为汉代匈奴的别称;而王国维则在其《鬼方、昆夷、猓狁考》①中考证后世匈奴人的祖先就是“鬼方”“薰鬻”“猃狁”。由此可见,以中原地区政权的更迭为时间佐证,居于北地的诸多民族的继承与更迭、分崩与融合也同时在上演。夏商时期,北方民族可见(但不限于):獯(荤)粥、鬼方、危方、下危、土方、翳徒戎、西落鬼戎、龙方、犬戎、北羌、羌方等;西周时期可见:鬼方、北戎、燕京之戎、狄(隗、翟)、犬戎、猃狁等;春秋时期可见:东胡、楼烦、林胡、朐衍、北戎、白狄、隗、大戎、义渠等;战国时期可见:东胡、匈奴、林胡、朐衍、义渠等。②
这些不同的名称,我们可以理解为散居于黄河流域北部与西部广袤草原的游牧民族的不同政权集团,他们的活动范围远及大漠南北,近在今河套、陕甘晋冀北部等地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起来的部族、政权,或集中,或分散,与中原政权相互动,在悠久又深厚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反复上演着战争与和平、对峙与交融的悲喜剧。
一般来说,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深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基础,而具有政权性质的区域性统治的建立,可以被视为民族文化和文明建立的标志,而政权的产生与文明的建立,也就必然会与其他的政权、文明产生交往与互动。从文献记载来看,北部、西部的游牧部族早在上古时期就产生了政权建立的可能性,并与中原农业部族发生着联系——《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北逐荤粥”的冲突式接触;《竹书纪年》(古本)提到淮夷、于夷、方夷、畋夷、玄夷、岐踵戎各部落政权在夏朝建立的时候就存在(在没有考古佐证的出现前无从谈起其与夏朝建立的先后顺序);《尚书·禹贡》也说:“织皮昆仓、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虽然历史文献在此方面记录略有缺乏,但起码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有不同生产生存方式的部族集团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些文本以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线索为佐证,记录着北方民族与中原形态各样的互动。
首先,从现存甲骨文来看,商朝时期除了在河南商丘、洛阳地区建立政治统治的殷商政权之外,还有人方、土方、鬼方、羌方、戎方等民族文明。之所以均有一个“方”字,意味着生存区域的差别——“方”是对商朝政权而言的其他地区的文明的通称,而这些政权多被认为是有着典型的游牧民族文明特点的,如经济和社会生活以游牧为主,但也有少部分农业与畜牧的定居形式(同时还可能掌握着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这类部族多生活在北部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界),且能征善战。甲骨文中多记录北方部族与商朝以冲突为主的接触与互动:“方”“土方”等时有“侵田”“征我”之事[1],殷商对北方部族的征伐亦在《周易》中有所体现——商王武丁曾亲自率兵征伐鬼方:“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既济》)[2]563;“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周易·未济》)[2]575,“鬼方”恐怕就是夏商时期北方游牧诸族的泛称③。此外,与商接触较多的北方游牧(或半定居畜牧半游牧)部族还有多个以“戎”为称的政权以及与戎有紧密关系的多个“羌”部族。商王妻妇好曾征战于戎,陷入军事包围④,殷人曾将大量俘虏的羌人作为人祭……这样的为了扩大部落(政权)的土地、增加财产、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对人祭的复仇等原因而产生的互动必然以战争为主。除战争外,东方、北方、西方的戎部族⑤、羌部族与商的政权也并非完全地、彻底地对立,两方的互动还存在着其他形式,如通婚、朝贡、聘问关系,部分臣服于商政权的戎、羌族人在商朝内供职等。
至周时,完备且版图广大的中原政权由此开始,与北方诸民族政权的互动也更加频繁,形式也更加多样。北部荤粥、戎狄侵周先祖古公亶父,迫使其退避于岐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邑于岐山下居焉。”[3]《史记·周本纪》也语:“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止于岐下。”[4]可见在周未入主中原成为主体政权时,就已经与北部民族发生了接触;而武王伐纣时,有庸、蜀、羌、髦等各民族率兵相助;西周初年,臣谏簋铭文载成康之际邢侯对戎作战之事,小盂鼎铭文载康王命盂伐鬼方之事。
随着周王朝疆域的扩展和统治的稳固,北方民族与周王朝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除了互相征伐之外,其他方面的接触也逐渐增多。在《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述中,周成王有“成周之会”,戎人各国(部族)均有物相奉。《竹书纪年》载西戎曾分别在太戊二十六年、祖甲十三年、穆王十三年有使者来周献上牲畜。[5]《穆天子传》载犬戎曾于雷首之阿献马。[6]战争也依然存在:季历、穆王曾伐西落鬼戎,征犬戎,且“俘二十濯王”“取其五王以东”。[7]由“二十翟王”与“取其五王”可以推断出,西落鬼戎和犬戎实际上有着不同的领兵首脑,应是由诸多部落组成的联盟。
基于游牧民族惯于迁移的特性,与周的战争使得他们有了向中原地区战略性接近的倾向,时常出入于泾水、洛水之间,对周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至宣王时,其活动范围已经逼近王畿。不其簋、多友簋、师同簋、逨簋的铭文均详细记载了宣王、夷王、厉王时期与猃狁、戎的战事。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猃狁的战争更是有着诸多的感慨:“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小雅·六月》)中原地区的人民对二者的战争有着深重的困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小雅·采薇》)面对侵扰,周王亦予以回击。“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小雅·出车》)无论是金器铭文的直陈记录,还是《诗经》这样的抒情文学,这些记载都表明了周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对政权和人民的巨大影响。发展至西周末年,北方政权甚至加入到了周内部的政治倾轧之中——申侯联合西戎、犬戎伐周,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使得周不得不迁都洛阳,退出渭水流域。
其次,西周之后,春秋战国至秦的大一统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文史典籍的极度丰富,我们看到了关于周政权西部、北部民族政权的更多记载——《春秋》《左传》《国语》《周礼》《礼记》及诸子文献中,周王及其下各诸侯与北方民族集团的交往不仅愈发频繁密切,且接触形式除战争外,也愈发复杂。
第一,可见会盟之事。会盟在《左传》中记载颇多:鲁隐公“会戎于潜”,同年,狄又与戎“盟于唐,复修戎好也”(《隐公二年》)[8]23;鲁桓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桓公二年》)[8]84;“卫人及狄盟”(《僖公三十二年》)[8]488;鲁公子遂“会洛戎,盟于暴”(《文公八年》)[8]585;“白狄及晋平,夏,会晋伐秦”(《宣公八年》)[8]695;晋悼公“使魏绛盟诸戎”(《襄公四年》)[8]939,“白狄朝于晋”(《襄公二十八年》)[8]1141。可见在于鲁、晋等有实力的大诸侯国之间,“狄戎”等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的会盟关系多是互惠互利的,于中原诸侯而言,“和戎有五利”[9]289被陈述得清楚明白,甚至与北方民族政权会盟,便可直接影响在中原称霸——晋国的“复霸”之路得益于晋悼公时期魏绛“和戎”之策下与诸戎的会盟。对于北方民族政权而言,会盟维持的和平关系也利于自身的稳定发展,但是同盟关系有时也并非非常稳定:“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10]208,为人所诟病。
会盟关系之下,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对中原政权的依附关系,主要是依附如晋国般的中原霸主。陆浑戎本于秦国之周,迫于秦的驱逐而依附于晋,军事与外交上皆以晋国马首是瞻,可见鲁成公六年伊洛之戎、陆浑戎等随晋伯宗侵宋,而在楚国逐渐发展崛起后,陆浑戎开始在晋、楚两国之间来回摇摆。这种依附关系对戎而言,显然是逊于结盟关系的,外交上不自主,军事上也要完全顺从所依附国,有时甚至会遇到所依附国的许多非礼待遇——被范宣子阵前侮辱(襄公十四年),有时甚至要在军事方面付出巨大代价。
第二,姻亲关系换取和平或联合的手段,在周及其下诸侯与北方民族政权的交往中亦屡见不鲜,尤其可见晋国与狄有着长期通婚关系。《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又说晋献公伐骊戎而携骊姬归后生公子奚齐。[8]239《僖公二十三年》载重耳奔狄后纳狄女季隗,随者赵衰娶狄女叔隗。《国语·晋语》更是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记载了晋献公娶戎女一事对晋国政权产生的长达数十年的影响。统治阶级的通婚行为尚如此频繁,我们不难推断,在民间尤其是与北方民族相毗邻的秦、晋(包括“三家灭智伯”后的赵、魏、齐)、卫、燕等地的普通民众,与北方民族的通婚姻亲关系亦非常普遍。
然而,在丰富多样的互动接触中,最为频繁的仍是武力冲突和博弈。我们必须看到,北方民族由于其所处地理区域与气候的特点和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人民的安定和富足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取决于大自然所带来的物质生产资料,而这就意味着当自然环境和所给予的物质生活生产资料难以达到人民生活的刚性需求时,必然会导致向南——中原地带靠拢,随之而来的是以疆域和物质资料为目的的战争。以秦晋为主要代表的中原诸侯,亦不断蚕食北方政权(以戎为主)的领地——周平王迁都洛阳后,关中地区实际处于狄戎的控制之下,秦人的兴起与晋国的发展,实则都是在与戎狄的斗争和博弈之中实现的,特别是晋悼公时魏绛“和狄戎”的策略为晋国赢取了大片疆土。这样的相互征伐接触,使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纷争、矛盾开始出现,但随着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交往的不断加深,政权发展的谋划也在逐渐加深,其征伐也不仅仅是初期以地盘和物质资料为目的的生存性战争,而是频繁参与到了中原各诸侯的倾轧博弈之中,成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交往接触、相互筹谋的重要形式,这在《春秋》《左传》中屡见不鲜。从“隐公七年”(公元前716年)到“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所涉及有三十多处,虽因篇幅所限而未将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影响一并相举,但从这数十处记述可看出中原政权在与北方民族政权产生军事冲突互动时的明确态度倾向——敌对与轻视。公元前714年,北戎侵郑,郑公子突谈“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8]66,说明郑人眼里的戎,组织纪律观念极弱,战争以掠夺为主,缺乏群体意识,讲究个体得失,人与人之间毫不谦让。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管敬仲之语则要求中原诸国联合起来共讨之:“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8]256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客观差异亦被有意夸大:晋国大夫伯宗谈狄“俊才虽多”但与中原礼教文化相异:轻薄祭祀、“耆酒”、弃贤臣、无视姻亲、无视君长等级、重才轻德等[8]762,相反地更重视个体智慧、力量、能力,蔑视群体文化规矩。
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儒家“华夷之辨”文化观影响下的结果,代表了当时中原文化对北方民族文化的普遍看法,有着一定程度的对立性,而这也严重影响了后世对待北方民族的态度,导致了后代无论是文学还是史学,罕见对北方民族政权史实的记录,同时也导致了后之研究者多认为戎乃所谓“文化落后”之族。童书业曾言:“东戎、西戎、狄、巴等都是华夏族的近亲,并非真正的异族,不过因其文化落后,以至风俗语言等都和华夏的人有不同罢了。”[10]杨伯峻认为:“戎,文化落后部落或民族。”[11]台湾学者陈盘:“春秋时代,东西南北四边,更有不少文化落后民族,这类民族,称为蛮、戎、狄。”[12]《春秋》《左传》所载北方民族诸部与中原政权的征伐冲突确为客观史实,而郑公子突、管敬仲、童书业、杨柏峻、陈盘所语则代表了先秦当时与后世在中原礼教文化影响下一脉相承地站在单一民族文化立场上所考量的态度——以中原之己度北方之人。事实上,民族文化本无先进落后之别,是随不同的地区生活生产方式应运而生的结果,正是由于存在差异,才使得不同文化的交融、融合拥有了必要的价值和空间,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有倾轧博弈,就必然有和睦共谋,春秋时期另一文史典籍作品《国语》对北方民族政权的观点就更为暧昧,和睦与对立在文本中交互上演:对立可见“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周语中》)[9]38“戎、狄无亲而好得。不若伐之。”(《晋语七》)[9]294“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齐语》)[9]162“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楚语上》)[9]349;但同时也透露出和平共处的思想,认为不可与北方集团轻易起争端,会招致祸患:“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晋语四》)[9]247“夫和戎、狄,君之幸也。”(《晋语七》)[9]294“戎、狄怀之,以正晋国。”(《晋语八》)[9]318
当然,无论是战争倾轧、会盟依附,还是联姻通婚,这些互动中必然存在着外交使者的角色以及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外交交往过程。典籍文献虽所记不多,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两位一展才具的北方使者:《韩非子·十过》篇记述了一位西戎使者由余,他出使秦国时以一番上古帝王由勤俭而建立伟业、其后又因靡侈而国家衰微的宏论,使秦穆公惊艳不已,这位人才最终被穆公设计与戎王离间后,投奔秦国官拜上卿;还有一位西戎使者戎子驹支,晋、鲁、宋、卫、郑、曹、莒、滕、薛、杞、小邾和戎子驹支会吴于向地,晋大夫范宣子于会盟之上声色俱厉地责备驹支,驹支则义正词严予以反驳,申明诸戎绝非范宣子所指忘恩负义之辈,又以精彩的论述谈了戎晋之关系,才思敏捷,语言逻辑性与感染力齐备,瞬间扭转了局面,而后赋诗《青蝇》而退。
另外,除以上所论诸番交往之外,《左传》《国语》与诸子典籍及成书时间稍晚的《周礼》《礼记》中存在着些许对北方民族的社会生产、生活、文化的记述,可在字里行间找到些端倪,也由此可以窥见北方民族的生产生活情态。可以看到的是,客观上北方民族的社会情形和文化与中原是大不相同的——戎子驹支于会盟之上语:“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赞币不通,言语不达。”[8]
从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来看,北方民族诸多政权中,并非全部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形态,有的保持着四处迁徙、流动性强的游牧生活:“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8],有的也开始了种植业与定居的经济形式:“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8]生活情态方面的相关记载更是丰富,《晏子春秋》可见养狗的生活爱好:“戎狄之蓄狗”少的养五六只,多的可养十几只[13];《韩非子》与《吕氏春秋》可见好饮酒之习:“戎王许诺……设酒张饮,日以听乐”[14]“戎王……饮酒昼夜不休”[15]卷二十四,以至于战争中周王靠在其饮酒时突击而取胜“戎主醉而卧于樽下,卒生缚而擒之”[15]卷二十三;另外,北方民族都有着本民族的语言,可见有关“戎言”的记载:“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15]卷四。从周王朝极为重视的“礼”来看,北方民族是不重祭祀的(或者说他们祭祀的方式不被中原礼教文化所理解)“平王之东迁也……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8]可见在周人看来,戎人的祭祀披头散发是不庄重的。
在普遍被认为成书较晚的《周礼》《礼记》中,明确而深入地阐述了关于“五方之民”格局的问题。《周礼·秋官司寇》可见“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傅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16],而“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也在《礼记》中被多处所提,可见“五方之民”的认知已经基本形成。这样的思想在安介生先生所著《历史民族地理》一书中有明确论证:“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五方之民平等观……华夷五方格局论基本体现了先秦时期华夏族人士民族观的总体水平”[17],可见《礼记》所构建的这一思想的合理性,显示在当时人们的“天下”概念中,承认“他族”的广泛存在,且中原华夏与“他族”具有朴素的“平等”地位。
不可否认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典籍常将“夏”“夷狄”对举,倡导“以夏变夷”“以夏化夷”,有着一定的倾向性,但客观事实上,“夏”与“夷”的区别并不在于所谓“文化”的“高低”,其差别究其实质是地域的生产生存方式的不同,进而导致了生活习俗、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等方面的不同。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同,而并非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礼记·王制》载:“凡民之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温,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机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中国、夷、蛮、狄皆有安居,知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方语不通,嗜欲不同”。[18]说明自然环境不同则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使文化传承和价值趋向亦不相同,而文明的发生就是在自我相因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出现的。王夫之曾对中原文化和夷狄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总结:“华夏有城墩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而“夷狄则自安逐水草,习射箭,志君臣,略昏宦,驰突无恒之素。”[19]从政权与文化发展的地理区域来看,北方民族诸部的发展并不仅仅限于周王朝以北地区,就是在中原的腹地,也有相异于华夏文明的多种民族繁衍、发展。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明确说周时“河北真定、中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洛阳为王城,而有杨距、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天下特五分之一耳。”[20]说明进入周地,就连河北、洛阳等所谓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区也有包括北方民族在内的多种少数民族生存发展,这样亲密交互的地缘背景下,无论是战争、会盟,还是联姻、嫁娶,这些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接触,都会发展为混合与同化,而最终成为一体。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原与北方的地缘交互之下,与北方民族诸部的渊源最深还要属秦国,不仅在地理区域上最为接近,而且于文化精神方面也最为相似。秦地并非成周之际所建,诸侯之中成型较晚,至周孝王时才封土得名。原先只是一处附庸之所,由于秦襄公积极护送避犬戎之难的周平王,周室才“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21],而此地在封秦之前,实际上被北方民族戎狄占据经营多年,周王朝无力征讨,俨然是另外一方水土。《后汉书·西羌传》记“及平王之末,周遂凌迟,戎逼诸夏……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在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戎狄遍地,此地的风土人情即所谓“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22]这样,秦人身处草原民族各部的环伺包围之下,自然深受游牧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而这样在游牧文化包围和影响下的秦地风貌,在《诗经》这一先秦文学的不二代表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展演。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提到,由于秦地迫近北方民族,民俗已与羌胡接近,“修习战备”、“鞍马骑射”、崇尚勇武,所以《诗经·秦风》才有“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谐行”这样慷慨风流雄壮的歌谣。[23]这说明秦地风情深受其周围北方民族诸部的影响,有着与游牧文化相一致的好勇、尚武、爽利的文化精神,而这一文化的精神以及其所崇尚的对阳刚、力量之美的追求,使得《诗经·秦风》卓然而立。《秦风》十首中,《小戎》尤其可见:“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全诗所见秦军军容之齐整,装备之精良,气势之威武,征伐之宏大,竭尽描绘军马、战车之上的各种饰件,尽显军队的孔武威风。该诗语言铿锵,节奏顿挫,营造出的紧张、严肃的征伐氛围又与思妇内心沉积着的好勇尚武精神相谐。虽然也有“言念君子,载寝载与”的款款深情,但更多的是对驾着战车出征的丈夫由衷的赞美与自豪,思妇也渴望同丈夫一样奔赴沙场、建功立业。这样直接的表达,使得一种刚直铿锵的力量跃然纸上,可见秦人举国尚武,对刚健英武的颂扬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心理。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情感的表达便爽直利落而非拖泥带水、委婉曲折。这样的精神反映与情感表达,在《秦风》诸诗中都有迹可循。尤其是其中描绘战争的诗作,一改《诗经》中其他战争诗的哀怨低沉、悲苦凄婉,转而颂扬和彰显战争带来的力量和由此而产生的“人”的价值的充分体现,是一种“舍我其谁”的壮烈英雄豪情,一种渴望一展英姿的昂扬情怀,一种建功立业的强烈梦想,热烈奔放、雄健豪迈、乐观高昂的英雄主义情怀深表其中,而这种精神与情怀也正是秦地人民在与北方民族深入交往、融合之下的产物,有着游牧文化所特有的豪情壮彩。
综上所述,先秦文史典籍为后世提供了客观的可以被清晰认知的北方民族历史景观,社会生产、人民生活、文明发展、与中原政权的互动关系等方面被清晰界定。无论是民族的生产生活情态、衣着饮食偏好、政权统治结构的陈述,还是与中原集团政权或战争、或会盟、或外交、或联姻的互动与联系,又或是在北方民族影响下的秦晋之地所呈现在《诗经》这样的抒情文学作品中的尚武豪情之壮美,北方民族的身影都是先秦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的角色。同样,文史典籍作品中对北方民族的描绘所呈现出的民族之间激烈碰撞与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亦不容忽视——从夏政权的建立,至秦统六国成为大一统王朝,北方民族诸部也有着不断建立、发展又或消融的历史过程,这些均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基础。
[注 释]
①该文载于《观堂集林》卷十三。
②关于这一时期北方民族的变迁记载,参考于《鬼方昆夷猓狁考》(王国维)、《中国民族史》(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任邱、王桐龄)、《春秋少数民族分布研究》(舒大刚)、《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先秦民族史》(田继周)。
③关于“鬼方”是特指还是泛指,此处采用《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载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观点,认为“鬼方”为泛指,“高宗伐鬼方”不是记述武丁对某个鬼姓之国的征伐,而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对周人泛称为“鬼方”的西北游牧诸族之“多方”的战争。
④此事迹学界尚有争议,此处主要采用《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载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等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