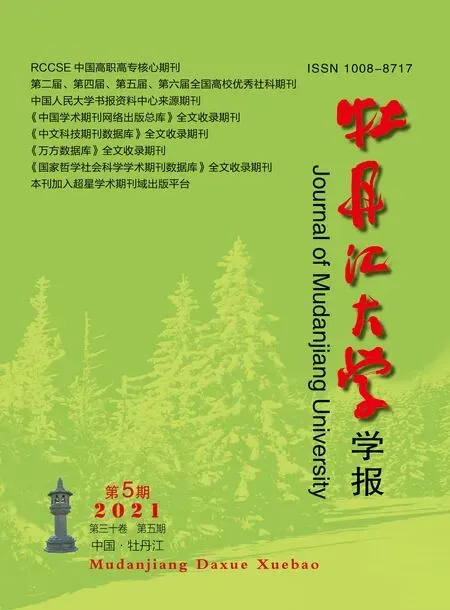麦克尤恩《阿姆斯特丹》中的女性形象与两性关系探微
杨水平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阿姆斯特丹》是当代英国 “国民作家” 伊恩·麦克尤恩(1948-)首部 “布克奖” 获奖作品。作者认为 “没有《阿姆斯特丹》,就不可能写出《救赎》。”[1]148此作可谓麦克尤恩写作生涯的转折点,学界主要关注该作的政治主题、叙事策略与反讽技巧等,对书中零星散布的毫不起眼的女性人物研究甚少。而女性主义与两性伦理关系是贯穿麦克尤恩作品的核心主题。麦克尤恩曾言: “我有个爱观察的习惯,我关注两个领域,一是父母怎么跟孩子相处……一是男女如何相处,夫妻也好,其他关系也罢。”[2]6
小说始于已故女人莫莉·莱恩的葬礼,从而引出她的老情人,报社主编弗农·哈利戴、作曲家克利夫·林雷、外相朱利安·加莫尼,以及她的丈夫富商乔治·莱恩。故事围绕上层男性展开,唯一重要的女性人物莫莉一出场就离开了人世,因此有关该作女性人物与两性关系的研究可谓寥若晨星。本文从文学伦理学与女性主义视角解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两性关系,揭示麦克尤恩所呈现的女性在当代男权社会中遭受的压制与迫害,面临的困境与无奈,进行的艰难抗争,即使女人通过自身努力变得独立而优秀,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在男权社会的劣势地位。同时,成长于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环境,麦克尤恩在刻画女性人物时难免表现男性的优越感以及对女性的鄙夷与偏见;但是他对受压制的无助的底层女性也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因此,伊恩麦克尤恩既批判了传统的父权制与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也打破了一般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固化与偏见。
一、中心与边缘:传统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压制
《阿姆斯特丹》中,无论是男人争相追逐的漂亮又能干的女人莫莉,还是为保全家庭而忍辱负重的模范妻子罗丝·加莫尼,无论是克利夫在湖区目睹的被强暴的女子,还是警察局里酒醉嘶吼的年轻母亲,她们都是当代女性的代表,是当代女性生活状态的缩影。莫莉美丽聪慧,独立自主,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可谓是新女性的典型代表,但她最终沦为男性玩弄和鄙夷的对象。 “完美” 妻子罗丝同样遭遇了身居高位的丈夫的感情背叛。书中微不足道的女性小角色要么被家暴、被遗弃,要么被囚困、被暴力侵犯。
权力总是意味着控制与支配。在男权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权力首先体现在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压制与支配上。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 “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3]11女性的身体除了生产性还担负生殖性功能,这意味着女性的身体要遭受双重压制。男性不仅直接暴力伤害女性的身体,也通过社会习惯、审美与道德价值观念等无形的力量规训女性的身体,使其符合男性的审美与需求。当代社会女性已经失去了身体掌控的权力,她们的身体正被主流文化所操控。影视节目中的演员、广告杂志中的模特无不拥有消瘦和紧致的身材,这正是无形的社会权力对女性身体的规训。莫莉 “四十六岁上还能翻得出完美的侧手翻。”[4]10四十六岁的年纪也能身型矫健,这显然是自律、克制和大量运动的结果。其次,在她临终之时, “性情活跃的莫莉成了她那位脾气乖张、占有欲极强的丈夫乔治的病室囚徒。”[4]9-10乔治严格限制她的来访者和人生自由,莫莉的最后时光过得凄惨而痛苦。 “哪怕是在最严格的医疗机构的管理下,她也能比在乔治的看护下拥有更多的自由。”[4]67此时莫莉丧失了对自己身体支配的能力,她的身体成了乔治报复和泄愤的工具。
男性对女性直接的暴力更是让女性的身体雪上加霜。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身体通常是男性施暴的对象,泄欲的工具。主人公克利夫在湖区远足偶遇强奸犯,他目睹了受害女子无助的挣扎, “她空着的那只手在地上乱抓乱挠,可能想找块石头当武器,可这么一来只使得那个男人拖起来更容易了。…… 她突然发出一声呜咽的哀求,克利夫很清楚地知道他该怎么做了。”[4]105很遗憾,克利夫并没有出于良心与正义去解救这位可怜的女人;而是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继续他的创作,他间接成了强奸犯的帮凶。
《阿姆斯特丹》也揭示了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 “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躺在并在一起的两把椅子上熟睡。年轻的母亲被关在一楼一个单人牢房里,度过她醉酒的恢复期。在整个头一天里,克利夫时不时地就会听到她痛苦的尖叫和哀鸣,”[4]177从这位痛苦的年轻女性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权力机关对其身体的规训与惩戒,更是其背后艰难的生存状态。她痛苦的尖叫与哀鸣强迫我们推测与思索这位女性的命运。虽然麦克尤恩没有给她机会道出悲惨命运的缘由,但我们完全能窥见她的人生。她为什么带着六月大的婴儿进了警察局?她很可能是位单亲妈妈。为什么她醉酒了?她很可能对生活绝望而用酒精麻醉自己。麦克尤恩无疑是借用这一典型案例呼吁社会对底层的年轻母亲给予关注。作者还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 “两个嘴里嚼着头发的女孩跑来寻求保护,她们俩是双胞胎,摊上了个有暴力倾向的老爹,结果受到了警局亲昵又打趣的对待。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大声控诉她的老公。一个年纪很老的黑种女人,骨质疏松症害得她身子弓得像个虾米,被女婿从家里赶了出来。”[4]177-78故事主人公弗农被迫辞职后,妻子曼迪一心想如何安慰他,可他一进家门, “就跟她发了一阵雷霆之怒。”[4]170无论是双胞胎女孩还是满脸血迹斑斑的女人,无论是权贵太太曼迪还是底层老妇人,她们代表着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的女性,她们都在遭遇男性赤裸裸的暴力迫害,被男性当作出气筒、被毒打、被遗弃。
此外,小说也指出女性成了权色交易的工具。以 “老淫棍” 指挥家朱立奥·鲍为代表的权贵们利用地位和权势控制和玩弄女性。 “那个年轻的姑娘,真是漂亮极了,可是她演奏并不完美……今晚她将跟我共进晚餐。”[4]187《阿姆斯特丹》中女性人物只是配角,字里行间却清晰地呈现了她们的身体遭遇男性肆意的侵犯和压迫,这种赤裸裸的暴力真切地反映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家庭地位。正如安吉拉·罗杰在《伊恩·麦克尤恩对女性的刻画》一文中指出, “他的早期作品中包含很多女性人物被虐待或杀害的例子,她们成为了男性压制的牺牲品。”[5]12
二、压制与反抗: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抗争与崛起
19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涌现了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相继诞生,仅英国就拥有9000多个女性协会。麦克尤恩的创作正始于此时,女性主义思潮对麦克尤恩的创作影响深远。《阿姆斯特丹》不仅呈现了女性身体被男权所压制,也展现了以莫莉和罗丝为代表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抗争与崛起。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指出个体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的, “在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它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6]1
新女性莫莉具有多重身份,她正是利用其身份与身体向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发起了挑战。她是知名 “美食评论家,既睿智又迷人,又身兼摄影师和敢于创新的园艺家,连外相都爱过她。”[4]10“派对女王” 莫莉的社交身份在书中尤为突出,她的葬礼足足有两百多号人参加。麦克尤恩运用 “互文性” 叙事技巧,借用《尤利西斯》女主角莫莉这一形象来隐射她的放荡不羁。两位莫莉都是性感迷人,拥有众多情人的已婚女性,她们都符合男性界定的 “荡女” 形象。麦克尤恩笔下的莫莉放荡不羁,其丈夫乔治 “对她的风流韵事束手无策” 。[4]12她打破了男权社会把女性定义为被动而温婉的淑女形象,她掌控着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控制着仰慕她的男人。莫莉懂得 “异装癖” 加莫尼的隐秘心理。 “善良的老莫莉。她一直都是那么富有想象力而且那么有兴致,她肯定一直鼓励他更大胆些,将他更深地带入他的绮思梦想中,”[4]84叛逆的莫莉鼓励外相加莫尼大胆呈现其女性特质,敢于藐视与对抗男权,敢于遵从内心的需求,颠覆了男权社会中的贤妻与淑女形象。
如果说莫莉是通过身体在与男权社会做斗争,那么罗丝的武器就是话语。话语与权力密切相联,福柯 “把话语看作权力关系的网络,认为话语始终是与权力和权力运作交织在一起,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3]3。话语是权力的一种形式。罗丝的教育背景、职业形象都是她的话语可信度的关键因素。 “她以惯常用来安抚那些绝望中的父母的嗓音跟他说话,缓慢、轻柔、轻快而非低沉。”[4]113面临丈夫的丑闻,她勇敢而坚定地出面为其公关。面对公众演讲,她轻松自如,娓娓道来,大众都被她的冷静,睿智所折服。 “她语气中带出来的说服力与其说源自于她的阶层,或者她作为一位内阁大臣妻子的身份,还不如说是来自她本人杰出的专业成就。”[4]142报纸纷纷报道这位 “‘新型贤内助’, 她既有自己的事业,而且还为深陷困境的丈夫勇敢战斗。”[4]146在媒体面前,她把主编弗农打得落花流水,赢得了阵阵掌声, “在等级森严的医疗体系中一个人竟然能上升到如此的高度,再单纯地称之为‘医生’就已经不合适了。”[4]140罗丝可谓是能经荣辱,共患难的全能贤妻。罗丝的智慧、才能与努力赢得了大众的对女性的尊重与认可,打破了传统上男性对女性智商与情商的贬损与诋毁,颠覆了把女性定义为软弱无能的家庭妇女的传统偏见。
三、男性作品与两性共体:麦克尤恩对女性人物的双重态度
玛丽·伊格尔顿曾言, “签署男人姓名的作品不一定本身就排除了女性因素。这种情况虽不多见但你有时的确能在男人署名的作品中发现女性因素:这的确是事实。”[7]407《阿姆斯特丹》虽然符合典型男性作品的特征,但也包含了一些对女性同情和两性合体的关注。
首先,该作中的男性人物非富即贵,他们拥有权力、财富与高贵的身份,无论是外相加莫尼、报社主编弗农、知名作曲家克利夫,还是富商乔治、指挥家朱立奥,他们都代表着以男性为中心和主体的权力系统。两位重要的女性莫莉和罗丝,一位是美食评论家,一位是医生,她们都是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人物。确切地说,她们的作用主要是帮助塑造男性形象。正如马尔科姆所言, “在处理女性角色时,《阿姆斯特丹》要么让她们死亡,要么让她们不在场,几乎都是没有呈现出的边缘故事人物。”[8]13莫莉被塑造为 “荡妇” ,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罗丝是 “贤妻” ,是男性价值体系中温顺、贤惠的妻子。美国女性主义者巴巴拉·韦尔特曾指出,男权社会所期待的理想女性应该是 “虔诚的,纯洁的,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 。[9]83这也间接反映出作者对女性的态度。男权社会中男人一方面希望女人聪慧、独立、能干、淫荡;一方面希望女人温柔、屈从、贤惠、贞洁。
莫莉除了作为富商乔治的妻子,还被描述为水性杨花,被男士追逐又嫌弃的 “荡妇” 。除了克利夫、弗农和外相加莫尼,莫莉的情人还包括王室的法律顾问、诗人普尔曼等。她跟王室的法律顾问, “两人在一张废弃的台球桌上表演亚当和夏娃的活人造型,他只穿了条小紧身裤,她只剩下胸罩和内裤。”[4]13而这时的莫莉却勾引着克利夫, “她当时假装去咬那个苹果的时候曾直直地望着他,咬得咯咯的牙齿间露出淫猥的微笑,一只手支在撅起来屁股上, 就像杂耍戏院里戏仿的妓女形象。”[4]13麦克尤恩肯定了莫莉敢于表达自我,不依附于男性的新女性特质,但也把她塑造成了结局悲惨的 “荡妇” 。
罗丝是典型的理想伴侣,善良、温柔、大度、体贴;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她对丈夫关怀备至,即使面对丈夫跟另一个女人的亲密关系和异装丑照,她也以家庭为重,出面压制丑闻。她温柔地抚摸着丈夫的头,即使已经准备出门了,又不放心地返回楼上安慰他。 “她以惯常用来安抚那些绝望的父母的嗓音跟他说话,缓慢、轻柔、轻快而非低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完全好起来的。’”[4]113生活中她体贴入微,为了不惊醒熟睡的丈夫,她轻手轻脚,但是她仍旧遭遇了丈夫的情感背叛。她显然是男性视觉下的完美女性,这无疑否认了女性作为常人应有的愤怒、脆弱等情感,是对女性的不公正刻画。
此外,一些其他细节也能窥见麦克尤恩与所处时代对女性的看法。着装一直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和要求。女性被要求穿着符合身份的衣服,如裙子,头巾,高跟鞋等。 “一身黑色裤装的娘儿们。”[4]198表达的是对裤装女人的轻蔑。不仅否定女性张扬个性,着装自由,也低估女性的智商与能力。当弗兰克当上主编跟下属讨论专栏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就是雇个把智商中等偏低的,也许雇个女人,写写那些,嗯,无关痛痒的东西。”[4]148“比如不会操作她的录像机啦,我的屁股是不是太大了之类?”[4]148作者明显表现出对女性能力的鄙视。还有 “就像那个谁,那个搞妇女参政运动的女人。”[4]15此处提及的伊瑟尔·斯密斯,妇女参政运动的领导人,也反映出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权主义的蔑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智商和能力都被普遍地低估和轻视。
莫莉和罗丝这两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女性人物与她们的结局都契合了安吉拉·罗杰关于麦克尤恩的女性观, “麦克尤恩从积极方面描写女性,她们抚育的似乎不仅是她们的后代,也包括她们的男性伴侣,仅仅是作为情人的女性没有好结局,但那些辅助伴侣的女性才有好结局,其他的被都刻画为受苦受难的形象,这似乎是非常男性的视角。”[5]24-25因此,麦克尤恩在他刻画女性人物时未能摆脱传统男权主义思想对女性的偏见,但他也控诉了男性霸权对女性的迫害,对受压制与无助的底层女性也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因此,伊恩麦克尤恩既批判了传统的父权制与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固化与偏见。
结语:
通过散见于《阿姆斯特丹》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莫莉与罗丝两位女性,我们能真切地窥见当代女性的生活状态,她们既被男权中心思想所束缚和迫害,又勇敢地与传统男权思想抗争,打破了传统对女性的限制与定义。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反映了麦克尤恩在刻画女性人物时难以摆脱男权视角中的偏见。同时,他也控诉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迫害,表达了对受压制的无助底层女性的同情。正如安吉拉·罗杰所言,《阿姆斯特丹》中 “女性人物的优势仍旧是与她们滋养男性紧密相关的,她们的价值完全归于她们对男性的假定值。更恰当地说,麦克尤恩拥有希腊先知提瑞西阿斯了解男性秘密内心的能力,而不是看透女性心思的能力。”[5]25当代我国社会中也不断出现女性被家暴、被侵害、甚至被谋杀的案例,麦克尤恩展现的女性与其现实生活迫使我们思索当代女性的命运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