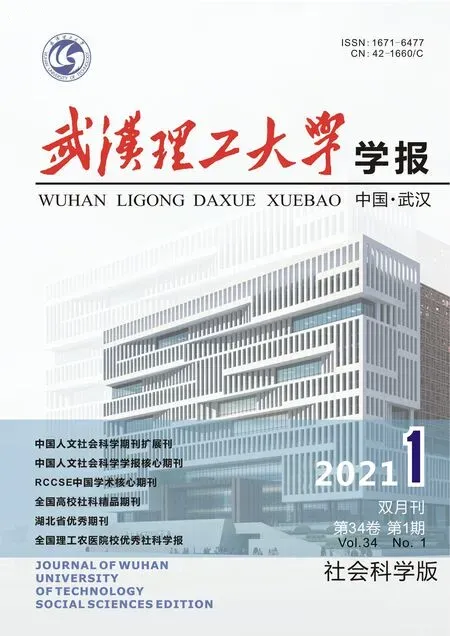“中国古典哲学走出去”之思考
郭继民
(中山大学 南方学院, 广州 510970)
关于“中国哲学如何走出去”的话题(或曰“哲学话语权”问题),近两年,学术界谈的较多。以笔者浅见,中国(古典)哲学走出去,首先是态度问题。就是要承认并尊重中国文化,中国古典哲学同古希腊、古印度的哲学同样伟大,同样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承认并尊重古典哲学,才可能去钻研它、研究它。其次,要有学术担当和学术愿力。就近三百年而言,哲学的中心一直在西方,由英国而法国,由法国而至德国。正如叶秀山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十九世纪是德国的‘天下’,列维纳斯说,二十世纪哲学无过于海德格尔;及至二十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做着德国人过去做的工作。”[1]284-285今天,时光已转进21世纪,“哲学中心”能否若季羡林先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样转向中国?笔者以为,即便有此可能,亦非自发的,它需要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付出艰辛的努力。其三,且不言中国能否成为哲学的中心,即便从学术传承与交流的角度而言,我们最切实的要务乃是做好基础工作,须把自己的哲学智慧完整地呈现出来,把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把握好“走出去”的几个技术问题或“走出去”的细节问题,再渐次地让中国哲学智慧推广出去。
关于前两个层面,较容易理解且学界讨论亦多,故本文拟在第三个层面上进行展开探讨。
一、将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完整地呈现出来
探讨“中国哲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之前,首先要把中国哲学讲好,倘若压根不能讲好中国哲学,那么“走出去”的问题就可能沦为空谈——此实则涉及到“中国哲学如何讲的问题”。
“中国哲学如何讲”的问题,换言之,即谓“如何把中国古典哲学呈现出来”的问题。从学术发展之路径而言,中国哲学的呈现方式大抵分为三种;一为“照着讲”,即按照文献资料的顺序,不走样地再叙述;二是“接着讲”,即顺着古哲的思路,把哲学引向深入,讲出古人“应有”但却未曾讲出的东西,冯友兰先生即持此主张;三是综合地讲,即把中国哲学放在世界智慧的背景下,将其同人类的其它智慧相融通、综合,以彰显其特色,张岱年先生所主张的“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说”大致如此。
三种讲法,实质上体现了三种思维模式,“照着讲”体现了静态思维,其特征为哲学智慧的再现;“接着讲”体现纵向思维,为哲学智慧的延伸;“综合讲”表现为综合辩证的思维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不同哲学智慧的融合。就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我们自然应该注重“接着讲”与“综合地讲”。事实上,自“五四”以降,学术界也一直在后两种讲法上下功夫,且讲出了新意,譬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牟宗三、张岱年等大学者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就当下人们对古典哲学普遍存在的隔膜现象而言,“照着讲”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这里倡导的中国哲学“照着讲”,绝非照本宣科、机械地叙述,而有其特定的内涵,即通过对古典哲学的再理解、再把握的基础上,把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完整地呈现出来。
首先,“照着讲”是要把哲学问题讲准。这里的讲准,要求讲述者将中国哲学能以客观的姿态,尽可能准确地将其哲学智慧原型呈现出来。这势必要求讲述者既要熟悉文献,亦要通透义理。中国哲学,其智慧博大精深,其问题同样也错综复杂,不同学派间存在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因此真正把哲学讲“准”并不容易。譬如,作为文本的《老子》同孔子的时间的早晚问题(冯友兰认为孔子早于《老子》,理由是“无”针对“有”而来,首先要“有”,然后才有与之对反的命题出现),儒、道依何划分?法家、道家、儒家有如何关联?名家缘何衰落?墨家同道家的关系如何?问题可谓多多!此外,“照着讲”势必涉及到学理的问题,儒家之道同道家之道的通性何在?庄子之自由同郭象之自由有何区别?佛家之“空”同道家之“无”的分际何在?汉儒与宋儒的分殊如何?如此问题,举不胜举。欲厘清此种问题,既涉及到文献的问题(辨别文献的真伪颇需功力),亦关涉到讲述者的态度问题;倘若讲述者对某派哲学抱有成见,或缺乏相当的功力,怕是很难讲准。
其次,“照着讲”须把哲学问题讲透。讲透需建基于讲准的基础之上。将问题讲准,目的在于让人有一个客观准确的了解;而讲透则是问题本身的深化,它既涉及到问题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趋势等较为宏观的视野,更牵涉到问题的细节——因为“透”总是关联着细节,问题不能追问至细节,就难以讲透,就难以领会中国哲学的妙处。一般而言,对于中国哲学稍有研究者,大抵都能“大而化之”地给出所谓“春秋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之宏观概括,然而若具体到细节,譬如先秦的“仁”、“诚”、“道”、“几”、“自然”等概念的含义为何?魏晋时期的“空无之辩”、“自然与自由之辩”(“独化”与“无待”的差异)、“才情之辩”等内涵如何?宋代的“理、气之辩”“理、欲之辩”“心、理之辩”“情、理之辩”是否厘清?……诸如此类细节问题,绝不在少处。无疑,若缺乏扎实的文献功夫和对细节的探究与体察,是难以呈现古典哲学的精彩之处的。
再次,照着讲,须把哲学问题讲通。讲透要求重视和把握细节的妙处,讲通则强调整体上的融会贯通。中国古典哲学门派众多,但主干大致可归结为儒、释、道三类哲学。因此讲中国哲学,必须对此“三家”有一个融通的理解和把握,此乃从事中国哲学的学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毋庸讳言,由于学科的精细化,使得一些学者疆域自治,彼此不能贯通——治儒者不懂佛学,治道(家)者对儒学不通透,治佛者对儒、道不熟悉。更有甚者,即便从事某一类哲学者亦未必真正贯通。譬如,从事两汉儒学的研究者竟然对宋明理学不甚熟悉,甚至相当隔膜。遗憾的是,学界这种状况并非个案。此种态势下,即便“照着讲”都困难,又何谈“接着讲”?须知,“接着讲”须建基于融通的基础之上,譬如冯友兰先生之所以能接着宋明理学讲,熊十力、牟宗三之所以能接着陆王心学讲,皆在于他们对儒释道有着融通的把握和娴熟的理解。对于儒、释、道之通,牟宗三先生曾有妙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通儒必然能真切地体会到道家和佛学的精髓,同样对道家、佛学有真正研究的人也必然懂得儒家,因为三者在境界上是通的。非但儒释道是通的,每一学派亦应该是通的;然而,后学却学派林立,此固然与其学养不足有关,亦与其缺乏博大胸怀有关。
把哲学讲通并不是简单的事。倘若不能贯通三家智慧,那么所讲的哲学是不圆融的,至少不能把中国的智慧完满地呈现出来。客观地讲,当下既精通儒释道又透悟西学的大学者不是太多——甚至真正能贯通儒释道这三家学问的大学者亦不多见,这尤须当今中国哲学同仁的共同努力。
最后,要把哲学问题讲活。所谓讲活,并非外在的活,而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决定了必须讲活。就活之特点看,中国哲学表现有三:其一,中国哲学根底上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是活泼泼的学问;其二,中国哲学的表现形式是生动活泼、不拘一格的,或格言、或寓言、或诗歌、散文乃至小说,概而言之,“文史哲”浑然一体,具有鲜活流动之质感;其三,中国哲学不是死的知识,而是具有强烈现场感的“生活的智慧”和真实的生命体悟。鉴于此三个特点,讲述中国哲学须扣紧生命这个根本指向,即便涉及到的哲学概念亦须向生命上收摄;要以灵动的方式讲述中国哲学,以鲜活的故事来讲哲学,让“载道的文献”灵活起来;要将古老的智慧同现实生活链接起来,让“现场感的智慧”充盈当下并试图化为方法论,来提升我们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上述标准衡之,“照着讲”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同样需要心血、心智的付出。对不少从事中国哲学的学者而言,“照着讲”仍是一门基础性的功课,也是当下努力的方向。道理很简单,只要做好“照着讲”,才可能更好地“接着讲”乃至“综合创造地讲”;同时,也只有在全面系统地把握中国哲学的基础之上,才可以真正知晓中国哲学特质与精华之所在,才可以把精华之处显扬出去。
二、把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呈现出来
从事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不仅仅意味着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全系统对待之,亦不仅仅停留在讲通、讲透、讲活,还必须练就一副火眼金睛,要能从浩瀚的哲学文献中攫取中国哲学的“特别处”与“闪亮点”,要能在长期的思考与体悟中凸显中国哲学之特质①。一句话,从事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者须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此亦是让“中国哲学走出去”的学术层面的核心工作之一。
笔者认为,探讨“中国哲学之特质”或曰“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大略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眼。
其一,要将“生命哲学”的意蕴凸显出来。
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根底上是生命的哲学,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之灵魂乃为首先握住‘生命’者。因为首先注意到生命,故必注意到如何调护生命、安顿生命。故一切心思、理念及讲说道理,其基本义皆在内用。而一切外向之措施,则在修德安民。”[2]当然,这并非说西方哲学不重视生命,但就主旨而言,西人的精彩在于思辨之知识,而中国哲学则重视生命,其精彩处亦在于生命;与印度哲学相比较,印度哲学同样重视生命,但他们更重视“来世的生命”,中国哲学对生命的重视是“全方位”(此言中国哲学尤重生命本体之研究)的,但主要针对现世之生命。这种“现世之生命”,并非仅仅重视物质之存在,更是重视人格(修身、修德)之养成。人格乃是精神的生命,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华夏民族的一切优良传统皆建基于此,无论儒家经典《易经》所凸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还是道家“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以“无为”为特质的谦让文化;无论墨家站在平民立场所践行的“尚同、节葬、非攻”的兼爱主张还是法家带有策略性的“法、术、势”具体制度之设计,根底上在于成就生命,安排生命,实现生命,以及最终完成生命,实现生命的价值。中国古典哲学也涉及思辨的内容,但总体观之,不占主流,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中国古典哲学“也重视思辨,但只占次要的地位。中国的思辨是为实践而思辨的,西方的哲学是为思辨而思辨的。”[3]也许今天看来,中国古典哲学难免存在偏颇之处,但是其对“聚焦现实之生命”的特质是显然易见的,此乃其生命力之所在。尤其是儒家,更具有生命的担当感和强烈的族类意识,譬如,孔子“文不在兹”之文化承载,孟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气与“舍生取义”的道义担当,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生命承担与族类意识,无不透显出其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此乃元气淋漓的生命哲学之宏大气象。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学术史、文明史,乃是围绕生命之证成而展开,今天我们探讨的诸如以人为本、仁爱、勤劳、谦让、节俭等诸多传统美德(核心价值)皆从生命哲学这一总根源中流淌出来,尤其值得我们传承和发展。
其二,要将人之“内在道德的主体优位”显扬出来。
中国哲学的核心在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道德。关于伦理道德哲学,西方亦不缺乏,然其最大不同点在于,中国的道德根底上是内在的、自律的,而西人的道德就主流言则是外在之他律(康德哲学同样推崇内在道德,强调道德自律,此为国人所熟知),依靠上帝之监督,或以外在“规制”(惩罚)来获得。中国哲学强调道德内在,人本质上就是天道的承载者,是道德的主宰者。此如《中庸》所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意识就是道德意识。道德由天命下贯,并凝存于心中。良知被唤醒,便是仁心发动,与天地宇宙打成一片,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即其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大程子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陆九渊谓“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及至王阳明,更是开出“致良知”之妙理。鉴于“仁义内在”的道德主体优位之考量,历代圣哲之要务就在于唤醒人之内在之德性,以使得人能“以德配天”,挺立于天地间。古哲(从孔孟至程朱、陆王,皆然)如此,今哲亦然:冯友兰先生所勾勒的人之“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境界之说,意在激励人们要完成崇高的人格;方东美先生提出的由“三阶九层”的“人格超生论”②亦反映了现代大哲对“人性善”的期许;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皆将“挺立道德主体人格”置于要位,皆在于凸显道德之价值。无疑,此与西人匍匐于上帝之下的卑微之状截然不同。
中国古典哲学之所以探讨道德,还在于:以中国圣哲视野观之,道德是内在的,是“求之在我”(孟子),是“吾欲仁,斯仁至矣”(孔子),是简易之极的。而知识则不然,因为知识是“外在”的,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是孟子所谓“求之由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这种取向与西人截然不同。中国古典哲学承认道德内在,承认道德“操之在我”,但并不因此就“放任自流”,因为要完成这个“简易”之德,是需要诚意、慎独等一系列的修炼,需要猛下工夫,缺乏工夫的道德言说为中国古哲所不耻。
顺便提及,中国古典哲学对道德内在的视野及“道德优位”的认可,尤其凸显了人格平等的理念,“人人皆可成尧舜”,“途之人可以成为禹”,即为人之德性平等、人格平等的最好注脚,这一点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可谓弥足珍贵。
其三,要把“真善美合一”的境界哲学之特质豁显开来。
中国古典哲学追求道德,追求至善,但这个善不是孤立的,而是同美、真(诚)相互贯通的。西方哲学求真,求美,亦求善。然而,其真善美之追求与东方显然不同,要点有二:其一,西人的真善美更多的表现为理论的诉求与知识的开拓,与实践未必合拍,故而其关于真的理论尽管缜密、可信,但关于真的行为则未必“果真如此”,此诚如王国维先生总结的那样,“可信者不可爱”;其二,西人关于真善美的探讨就整体而言乃是割裂的,因三者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大哲康德极力将三者“粘结”起来,虽付出巨大心血,但限于西人思维二分、知行二分,结果亦难尽人意。时至今日,以西方学术观之,真者自真、美者自美、善者自善(此言即便在研究领域层面,三者亦是割裂的)。
中国哲学则不然,其真善美在理论体系上圆融一体,相互贯通。孔子所言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谓将真善美视为有机的整体;孟子在《尽心·章句下》中有言:“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之之谓神。”此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真善美的有机性、圆融性——追求仁(可欲之物,此做“仁”解)就是善,把这种“善”切实地充实于自身就是信(真),把这种“充实于自身的德性”发扬下去就是美——当真善美完美地结合于一体定能引领社会风气,这就是圣人的境地了。关于“充实”之义,牟宗三先生曾论之:“所充实的是什么呢?那必是‘天道性命相贯通的这个立体的骨干’。”[4]中国哲学之真善美在行为上表现为“知行合一”。知仁曰真,行仁曰善,而依据仁所呈现的过程就是美,三者是统一的。固然,古典哲学之道、仁、义未有严格的定义,在逻辑上未必可信;但是君子却能根据本心(良知)实践出来,此乃是其最可爱处,最感人处!关于中国哲学家的知行合一,以研究逻辑学名世的金岳霖先生曾评价道:“(对中国哲学家来说,)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自传。我们说的并不是哲学家的才具——他可以是二流的哲学家,也可以具备他那种哲学的品质——那是说不准的;我们说的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5]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中国古典哲学家即便其学识二流,然却体现着“知行合一”的诚之品格,体现着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其四,要将中国古典哲学的“和”之包容品性宣扬出来。
“真善美”之所以能完美地融为一体,其根蒂在于中国古典哲学“和”之特色。虽然中国在秦汉以来形成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但大一统下的政治观并不排斥古哲“和而不同”的包容哲学观。中国古典哲学自诞生起,就传承“和”的包容观念。包容只是笼统的说法,细讲来,中国哲学中包容(和)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乾·彖传》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及《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从自然万物并存、共处的角度来探讨“和”之价值;《国语》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则从事物发展、存在的角度探讨“和”的意义;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则从为人处世的角度对“和”进行探讨;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从生成论的角度谈“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则是从“人心向背”之战争维度探讨“和”;……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提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6]的“交往原则”,可谓是中国哲学古典之“和”在当代的诗意表达。
总之,“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和”的包容品质,内在地要求人们与天合、与地和、与人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正是在此哲学理念下,包容性显示出开放性的特点,异域的学术思想(尤其以佛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方可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中华民族在学术思想史上也因此呈现出博大气象与豁朗之局面,春秋时期的诸子兴起、魏晋时期的儒道争雄、宋明时期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乃至今天哲学界仍然“中西马”鼎足而立且有会通、交流之势,皆是以“和”为底色,并因此大大繁荣了思想学术。
同时,这种独具“包容”品质的“和哲学”(亦有学者如张立文先生称之为“和合学”)也切实地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方针,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新中国的诸多大政方针皆打上了包容哲学的烙印,建国初所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国际交往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一国两制”的勾勒与实践,当今我们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局势的把握,皆是“和”之包容特质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今天,“互联网”拉近了国际间的距离,然而国际关系日益复杂、人际矛盾愈发彰显,人与自然的关系益发紧张……,因此,如何将中国古典哲学的包容品质彰显出来,如何将中国的“和”哲学大力地宣扬并运用到实践中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其五,要将系统、整体的圆融思维模式呈现出来。
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思维模型乃是“系统、整体”的有机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把任何个体都置于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宇宙格局之中,个体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它通过“非线性”的方式在时空中沉积、发酵,直至产生宏大的影响。此思维原型当来自于有天人之学之称的《周易》,《周易》首先通过“观物取象”的直观思维,将事物按阴阳的方式分类;继而以“八象”(即八卦)的方式将宇宙囊括其中,其中卦卦之间、爻爻之间、卦爻之间皆有着错综复杂(即错卦、反卦)之联系,而每一卦、每一爻皆又对应着不同的时空。由此,天地人、时空、自然万物乃凝结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此种思维一经流淌而出,便一发而不可收,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以其对中国形上哲学的影响而言,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孟子》)乃至由此工夫而达到的“与天地参”的天人合一之哲学理境,道家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庄子·齐物论》)及“道通为一”的哲学观,佛教中国化之典型代表如天台宗之“一念三千”、华严宗之“四无碍”(即理无碍、事无碍、事理无碍、事事无碍)、“十玄门”之义理等等,无不突显了整体、系统的哲学思维,尤其是华严宗与天台宗,更是将这种有机思维推至极为圆融的境地。以其对具体的有形文化影响而言,以“家天下”而延伸出来的“大一统”的政治观念,以调和阴阳、把人体视为小宇宙的中医文化,讲究整体布局、气韵流动的艺术文化,综合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为指导的“负阴而抱阳”的建筑(风水)文化,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五味杂陈(调和)”的饮食文化,甚至带有术数性质的择日、占卜、星相等民俗抑或神秘文化,其根底莫不是“整体思维”在实践中的妙用。
无疑,承载这种整体思维的工具——汉字,更是具备此特性。汉语的用法非常灵活,除非你懂得整体的意思,否则靠单纯的语法分析是很难凑效的。物理学家F·卡普拉这样描述:“中国人的思维并不采用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发展一种与西方相去甚远的语言。许多中国的词语既可以作名词、形容词,也可以作动词。因此它们的序列主要不是取决于语法规则,而是句子的感情内容。”[7]80何止是理解句意如此,理解中国古典哲学亦然。如果不能透悟“整体有机思维”模式,是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无论是我们“和”文化的包容品质还是“真善美”合一的哲学理境,无论是对生命价值的倚重还是道德内在的优位定位,其中始终贯穿着系统、整体的独特思维模式。
相对于理性的逻辑思维而言,这种有机思维模式充满混沌性、直观性乃至神秘性。然而,它的价值是无法否认的,即便在科学认知领域也是如此。正如F·卡普拉指出的那样:“我把科学和神秘主义堪称是人类精神的互补体现,一种是理性的能力,一种是直觉的能力。它们是不同的,又是互补的。不能通过一个来理解另一个,也无法从一个推出另一个。两者都是需要的。”[7]243他还从物理学的角度对中西两种思维进行比较,认为“人类文明能否存在下去也许就取决于我们能否进行这种(思维的)变革,它最终取决于我们采纳东方神秘主义某些阴的态度的能力,要有体验统一自然和协调生活的艺术”[7]245。正是基于古典思维所具有的过去与未来的双重考量,从事中国古典哲学的学者一定要把这种系统、整体的东方独特思维模式呈现出来。
当然,正如光与影子的关系那样,光愈强,影愈暗,哲学文化亦然。古典哲学的优长从反面看也是其缺陷:譬如重视生命忽视了知识的开拓;重视德性忽视了法制的建设;重视“统一”忽略了差异;重视“和合”而忽视了对立、差异;重视了混沌思维忽视了分析思维。然而,我们必须知晓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完美。中国古典哲学虽然存在诸多弊端,然而却能让中华民族传承五千余年而不衰,这难道不是奇迹?!难道不值得我们继承、拓展与弘扬?!
三、处理好“走出去”的几个技术问题
讲好中国古典哲学,彰显古典哲学的精华,是“中国古典哲学走出去”的基础工作——当然是奠基性的工作;中国哲学欲走向世界,还需做好几个“技术性”的工作——此技术工作当然奠基于前两步的基础之上,笔者姑且称之为几个关键的“技术问题”——它既包括学术表达体系的构建、语言的翻译及问题的切入点等关乎学术的“技术问题”,也包括善于把握人类共性的问题、善于把握机遇等关乎视角、敏锐性等“技术(巧)的问题”。
首先,要构建好中国哲学智慧的“表达体系”,此乃关乎中国古典哲学能否走出去的“学术前提”。
中国古典哲学注重生命的体悟,不注重语言的言说——虽然在中国古典哲学崇尚有机、系统思维,但在表达(叙述)层面较零散。相反,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多是连贯的、以专著的形式出现,按徐复观先生的说法,西方哲学家思想的结构表现为其著作的结构,“他们著作的展开,即是他们思想的展开,这便使读者易于把握”[3]70;中国哲学家则很少能意识到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他们的思想结构,他们的思想零星地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之中,甚至信札之中;同时,在同一篇文章或一段语录中,又常关涉到许多观念,许多问题。因此,要把中国哲学“说”好,就要在整理上下功夫,不但要认真对待每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而且还要认真对待整个哲学史。关于这一点,第一部分已涉及到。除此之外,今天的学者还需在“体系表达”上下功夫,正如第二部分所述,中国哲学至少有五大特色,我们要把五大特色贯通一体,使之成为融贯的体系。这个更像“写家谱”一样,非常基础但又颇费功夫,且十分必要。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需要有志者艰苦的付出;同时,这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替古哲把“散乱的珍珠”串成适于现代人接受的体系同样是一种创造:理清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融通各种学派间的矛盾与困惑,既需要严谨的逻辑方法也需要极高的文字修养。惟其如此,我们的哲学智慧才能易于接受,且不说为外人接受,即使对国人,也同样如此。
其次,要把我们的哲学精华翻译好(转化好),此乃思想交流的关键。
中国有着丰厚、深邃的哲学智慧,自为国人称道,然却不为外人所知。之所以如此,固然有诸多历史的原因,亦有文化自身的原因。譬如,汉字难学,汉语难学,古汉学尤其难学,由古汉语所传达的哲学思想则是难上加难!据哲学家熊伟先生讲,德国大哲海德格尔对汉语之难,竟然带有敬畏的态度,“在关于康德的《先验辨证论》的一个专题讨论班上,当一次发问无人回答时,海氏说,‘这并不难,又不是中文’,可见海德格尔当时似把中文视为不可企及的事”[8]115。且不说当下的大多数国人对古汉语存在隔膜,即使是专业人士亦未必能完全理解汉语的古义。此种态势下,若让古典哲学走向世界,确有难度。因此,这就需要一流的翻译,能用典雅的外文表达出古典哲学的神韵,这尤其需要懂外文的哲学大家,或懂哲学的语言大家,若二者缺一,恐怕皆难以表达出古典哲学的神韵。众所周知,古典如《周易》《论语》《老子》,虽在数百年前就被翻译为英文、德文等诸多语言,然而当时的翻译多停留在字面的对译,难以表达出中国古典哲学之智慧。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佛教的做法。佛教之所以能传入中国,与鸠摩罗什等大师的翻译分不开,为了翻译佛经,他学习中文数十年,以至于能用文言文写作出一流的文章。上世纪,冯友兰、方东美二先生皆以典雅的英文分别著述《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在国际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哲学赢得了一席之地。惜乎当下我们尚缺乏这样的大家,如何培养复合型人才,如何让一流的哲学人才同一流的翻译人才进行无缝对接、融洽合作(当然能将二者融于“个体”更好)亦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复次,要精通至少要熟悉西方哲学思想的精华与套路,以便寻找学术会通与思想交流的关节点,并借此提升中国哲学的品质。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进行学术交流或文化传播,固然需要“说出自己的”,同时还要“知晓别人的”,否则,将会陷入自说自话的“独角戏”之境地或陷入隔靴挠痒的尴尬之中。我们自信有古典哲学智慧,同时还要能了解其他民族的智慧,这样方能通过比较,更好地知晓中国古典哲学的优长与不足。同时,也只有通晓异域哲学之智慧,一则我们可以找到沟通与传播的契机和关节点;二则可借此进一步提升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哲学智慧的提升需要碰撞与刺激,更需要交流与融合。叶秀山先生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提出这样的看法:“从某种意义来说,西方哲学的希望在于‘非西方’,希望在‘东方’,在‘东西方之融合’。”[1]279事实上,哲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展开了这个融合的工作:关于西方人以中国哲学来提升其哲学层次的,如果说在黑格尔时代,还较罕见,那么在20世纪则逐步展开。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尔,虽然其晚年发出“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世界”的说法,然而晚年的海德格尔对中国哲学充满兴趣,其高足比默尔教授在1991年于北大讲学时讲到,“海德格尔专心致力于弄清中国世界,皆因其看法是,没有中国语言的知识,没有对中国世界的明见,就不可能有真实洞察的通道”[8]128。至于汉学界的名家如费正清、爱莲心、史华泽、耿宁等,已默默耕耘数十年,早已取得较丰厚的成果。中国人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来提升中国哲学品质的更是举不胜数,其中尤以“现代新儒家”这个群体为典型。以牟宗三先生为例,其为融合康德与儒家哲学所提出的“智的直观”“一心开二门”“良知的自我坎陷”“圆善论”等理论,可谓在融合会通的基础上将儒学乃至康德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让哲学说“中国话”,本意并非要“中国文化主宰世界”,而在于取得学术交流的发言权,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宰制下,一些学者甚至都不敢承认自己的哲学,他们的研究无非是跟着西人后面亦步亦趋。此固然取得了对话与交流的机会,然而“亦步亦趋”的姿态本身,已决定了他们所研究的哲学无非是拾人牙慧而已。今天,我们让哲学说“中国话”,须在对等的基础上,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心态下,敞开胸怀,合理吸收,平等交流,以达到融合贯通、绍述并提升中国哲学的品质之目的。
再次,要把握机会,在国际合作与国际文化交流中展示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
当下国际间的交往愈来愈频繁,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宣扬我们的文化理念、哲学理念,展示东方古老的智慧。就政府层面而言,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即带来传播文化的契机,譬如,国家元首外访时的讲话③所秉持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理念,即彰显出东方古老智慧的当代价值,至于讲话中所引用的老子、孔子及其他古代经典文句,亦不在少数。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区区数百字访谈中,国家领导人便引用了韩非子、《诗经》、《老子》及唐代诗人李涉等经典著作,此从一侧面向世界展现出古典哲学的智慧、厚重与博大。至于国际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人文学科的交流,有幸与会的学者则更应该抓住机遇,本着平等交流、共同提高的原则积极宣扬自己文化的特色。近百年来,伴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利及八国联军的入侵,国人曾一度失去了自信,认为“一切都是外来的好”,这导致了如下两种心态:就积极意义上,我们能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外来的优秀文化;就消极意义而言,则失去了民族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经过近60年的建设,尤其是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在实现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今天,中国人须昂起高贵的头颅,不卑不亢地宣扬东方的智慧。须知,正如西方的科学属于全人类一样,东方的智慧虽为华夏民族所培育,然而它同样是“共命慧”,属于整个世界、属于全人类。我们有义务来宣扬一种中正、圆融的智慧,使之为国际间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可能性的思路和方案。
最后,抓住机遇,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展现中国古典的哲学智慧。
在具体的事务性活动中传播古典哲学的智慧是非常有效的,因为这种事务性的活动具有“零距离”、“接触时间长”等特点,譬如,随着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如高铁、天然气管道等)日益走出国门,尤其随着“一带一路”策略的实施,我们可以在这个“新丝绸之路”中弘扬东方文化,让更多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分享东方古老的哲学智慧。当然,这需要高层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古典哲学修养。
当下,日益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的人类面临诸多共性的问题,如瘟疫问题、能源问题、气候问题、生态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自然灾害问题,等等。诸种问题的解决当然涉及到科学的谋划与技术的参与,然而仅有科学和技术是不够的,它需要有一个大系统、大地球观的考量,要有大局观和整体意识,要有系统思维和人文思想的参与,而这一点单靠西方的智慧是难以奏效的,它同时需要“中国智慧”的参与。事实上,在国与国关系的重大问题上,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一直贡献着古老的东方智慧。今后,我们更要发挥自己独特的有机思维优势、博大而包容的胸怀及尊重生命、尊重主权的“和”文化思维,在具体事务的解决中把东方独特的经典文化与智慧贡献于世人。
注释:
① 一般而言,“特质”未必一定是精彩的,但对中国哲学而言,则大致如此。因为言其特质,乃至在中西比较的视野而言,没有比较,何有特质?另者,中国哲学的特质恰恰凸显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彩,至少主体如此。
② 九种人分别为:自然人、活动人、理性人;艺术人、道德人、宗教人;高贵人、神性人、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人。其中,依次每三种为一层级,共三阶,笔者称之为“三阶九层”。
③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的《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讲稿中,引用了范晔、魏源及冯友兰的经典文句;在《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讲话中,则引用了东晋葛洪《抱朴子》中的文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