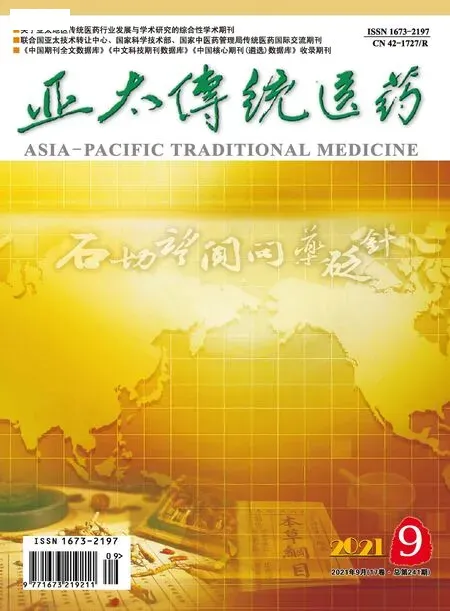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二则
文 玲,文 敏,赖桂花,曹建雄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410208)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已在国内得到基本控制,该病属于中医瘟疫范畴,正如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所言:“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伴有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及肾功能损伤在临床上少见,中医认为其属“肺肠合病”及“肺肾合病”范畴,病情较复杂。“湿毒”是主要致病邪气,基本病机特点为“湿、毒、瘀、闭”。曹建雄教授是湖南省中医防疫专家组成员之一,擅长内科杂病及恶性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曾在岳阳抗疫40余天。通过整理部分资料,现将曹建雄教授收治的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伴有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及肾功能损伤的患者治疗过程报道如下,以与同道共享。
1 病案举隅
1.1 新冠肺炎突发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病案
患者陈某某,男,71岁,住院号:1115533,因“发热一周”于2020年2月9日入院。既往有“肺气肿”“高血压病”及“糖尿病”病史,有“COVID-19”密切接触史。2月4日至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查肺部CT示右肺下叶磨玻璃影,考虑COVID-19可能,2月8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收住感染病房治疗。入院复查肺部CT示双肺病灶较前明显进展,新增双侧胸腔少量积液。入院诊断:①COVID-19(普通型);②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③糖尿病(Ⅱ型);④肺气肿。
治疗过程:入院后予莫西沙星抗感染,α干扰素、利托那韦抗病毒,免疫球蛋白增强免疫力,甲强龙抗炎等治疗,发热咳嗽等症状有所好转。2月13日患者出现腹痛,查体全腹部肌紧张,压痛、反跳痛,紧急行腹部CT及立位腹部平片,考虑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并发急性弥漫性腹膜炎。急诊全麻下行腹腔镜探查发现十二指肠溃疡并穿孔,于当日上午完成全麻腹腔镜下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穿孔修补术。术后予亚胺培南抗感染,输注丙种球蛋白增强免疫力,血必净及乌司他丁清除炎症因子,同时给予禁食、胃肠减压、抑酸护胃、维持电解质平衡及内环境稳定等治疗。
术后第2天患者仍未排气、未解大便,腹胀,予开塞露、乳果糖灌肠均未见效。刻下:发热,少汗,口干,胸闷不适,稍咳,咳少量黄稠痰,小便黄,舌苔黄腻,舌质红,脉弦数。经湖南省中医专家曹建雄教授会诊后,分析其属于疫病(疫毒痰热阻肺、肠腑闭结证),予宣白承气汤加味灌肠:大黄10 g、石膏15 g、杏仁10 g、瓜蒌仁15 g、厚朴10 g、枳实10 g、槟榔15 g、白芨15 g、桔梗10 g、贯众15 g、甘草5 g。1剂后患者开始排气排便,5剂后大便正常,但纳食不香,在原方基础上减大黄为3 g,加太子参15 g、麦芽10 g、山楂10 g,改为口服。5剂后患者发热咳嗽已除,胸闷无,纳食及睡眠改善,舌苔薄黄,舌质淡红,脉沉。
按: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1],新型冠状病毒会造成胃肠黏膜不同程度的坏死。此外,精神因素、非甾体类药物、糖皮质激素等均会导致胃酸分泌增多,进而破坏胃肠黏膜屏障,形成溃疡。该患者在住院期间突发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并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病情凶险。术后又出现排气排便障碍,西医灌肠效果不理想。曹建雄教授在辨证论治及辨病论治的基础上,分析患者属于疫病中的疫毒痰热阻肺、肠腑闭结证。肺开窍于鼻,热毒疫气从口鼻而入,闭阻肺气,导致肺气不宣,水液代谢障碍,痰液内生。内生之痰与热毒疫气相搏结,闭阻于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的通降助力大肠传导糟粕;且肺为“华盖”,能通调水道、濡润肠道,故肺气失于宣降时,大肠传导失司、失于濡润,致便秘。此时应遵循吴鞠通倡导的“肺肠同治”治法[2],治以宣肺止咳、泻热通便,予宣白承气汤加味。宣白承气汤取其宣白、承气两方之意,为清宣肺热、顺调腑气的上下合治之剂。本案患者发热、咳嗽有痰、便秘,符合宣白承气汤的辨证要点。方中大黄苦寒泻热结,石膏清肺热共为君药;杏仁、瓜蒌仁宣肺化痰止咳、润肠通便,槟榔、厚朴行痞气,枳实散结气,与大黄合用,则可荡涤胃肠热结积滞,皆为臣药;白芨入胃经收敛止血,桔梗宣通肺气,贯众清热解毒,共为佐药;甘草性平调和诸药。整首方以泻下为主,兼以宣肺化痰、清肺解毒之功。肺为邪所害,湿毒化热内传阳明,腑实壅滞,气结不通,则肺气愈闭,此乃恶性循环。故肺病及肠者,不可只顾一方,应相兼而治;既要宣降肺气,又要畅通肠腑。宣肺即是通腑,通腑即是宣肺。该患者初期不能口服中药,只能给予高位灌肠(250~300 mL)。COVID-19突发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时应严格把握手术指征,做好围术期防控预案。对于术后腹胀、排便不畅,应早期中医辨证予中药干预灌肠治疗。
1.2 尿毒症患者感染COVID-19病案
患者李某某,女,44岁,住院号:1128702,因“发热咳嗽伴尿少5天”于2020年2月9日入院。既往有“尿毒症”病史9年,长期坚持血液透析。2016年行肾移植术,半年前再次肾功能恶化,此后行血液透析2次/周。刻下:咳嗽,单声咳嗽为主,咳稀痰,头微痛,微恶风寒,发热,鼻塞咽干,无明显胸闷气促,无汗出,精神状态差,乏力,纳食欠佳,口中乏味,少尿,舌苔白,舌质偏红,脉弦。西医诊断:①COVID-19(重型);②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③肾移植术后;④贫血;⑤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中医诊断:疫咳(咳嗽微喘证)。入院前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双肺CT提示双肺磨玻璃影,血常规白细胞和淋巴细胞均降低,总蛋白、白蛋白偏低,心肌酶升高,二氧化碳结合力明显偏低,肌酐、尿素氮明显升高,住院期间尿素氮最高达19.69 mmol/L,肌酐最高达851.95 μmol/L。
治疗过程:入院后按照COVID-19诊疗方案,经中西医结合施治,在抗病毒、抗炎、稳定内环境、免疫营养支持及规律血液透析的同时,予杏苏散加味。3剂后患者发热咳嗽已除,但小便量仍然极少,每日300 mL左右,恶心呕吐,纳差,双下肢浮肿明显,大便稀,舌质淡胖,苔白,脉沉细。为改善患者二便情况,湖南省中医专家曹建雄教授通过辨证论治及辨病论治,辨其属于肾衰病(脾肾虚衰、湿浊内蕴证),方用大黄附子汤加味:大黄3 g、附子10 g、煅牡蛎30 g、白参15 g、制地龙15 g、麦芽10 g、山楂10 g、鸡内金10 g、益母草15 g。5剂后患者大便成形,小便量明显增加,每天600 mL左右,双下肢浮肿较前明显减轻,精神状态好转,饮食正常,舌苔薄白,舌质淡红,肌酐维持在300~400 μmol/L之间。出院前两次复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皆为阴性,双肺CT示磨玻璃影基本吸收,血常规白细胞、淋巴细胞恢复正常,水电解质酸碱平衡,总蛋白、白蛋白基本正常,肾功能维持稳定,心肌酶正常,于2月22日,患者出院。这是我省继湘雅医院之后的第2例COVID-19并尿毒症患者出院。
按:尿毒症患者感染COVID-19,临床上少见。新型冠状病毒累及的器官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的器官分布有关,而肾小管是ACE2高分布的场所,因此肾脏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靶点之一。陈永文团队通过HE染色和免疫组化技术对6例死亡患者进行肾脏解剖,发现6例患者均有急性肾小管损伤[3]。肾脏损伤也是存在于危重患者中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对于有基础肾脏疾病的患者,应重视肾功能监测。尿毒症患者感染瘟疫毒邪时,属肺肾同病,治则应当以“治急”为先,故前期的中医治疗是以驱除瘟疫邪气为主。本案患者初期受凉燥邪气,肺失温润,出现咳嗽稀痰,鼻塞咽干,头微痛,微恶风寒,苔白脉弦的凉燥之象,遂以杏苏散加减。中期患者发热、咳嗽好转,但因患者存在尿毒症病史9余年,久病导致脾肾虚衰。加之新型冠状病毒对肾脏的进一步损害,使患者在住院期间肌酐等肾功能指标进一步升高,小便量极少,大量毒邪蓄积体内。中医认为,脾肾者,水液代谢之官也,三焦者,决渎之官也,水道出焉。脾气虚,则水谷运化无力,不能升清降浊,故大便稀,乏力,纳食欠佳,口中乏味。肾气虚,则气化失常,湿浊毒邪内蕴三焦,三焦不通,故小便量少,下肢浮肿。其病机为脾肾虚衰(本)、湿毒内蕴(标),王肯堂主张“治主(本)当缓,治客(标)当急”,该患者治疗上应以温肾泄浊、畅利肠腑为主,待湿浊毒邪之标除后,再补益脾肾。尿毒症属于中医“肾衰病”,此病病势危重,非一般温补脾肾之剂所能奏效,故用大黄附子汤为基础方。大黄附子汤乃温下之剂,方中重用附子,削弱了大黄苦寒之性,保留大黄降浊排毒的功效。“浊”乃阴邪,附子为温药,可温肾阳而泄湿浊。大黄为将军之官,走而不守,主泻下,可通腑泄浊。两药合用温肾泄浊之功强,共为君药;煅牡蛎用在此,除可潜阳安神、制酸外,兼有吸附湿浊毒邪之意,配合大黄泻下之功,使湿浊之邪更有出路,为臣药;党参、太子参益气健脾,麦芽、山楂、鸡内金消食和胃降浊,益母草利水消肿,制地龙化痰活血通络,皆为佐药。尿毒症患者感染COVID-19时,其病机属于“肺肾同病”,治则应在辨清缓急轻重、标本虚实的基础上审因论治、分期论治。大黄、煅牡蛎等中药对于降低尿酸、尿素氮及肌酐,改善肾功能有确切疗效。研究表明,中成药“肾衰康”中的各味中药对尿酸、尿素氮和肌酐均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其中就包括了大黄和煅牡蛎[4]。多项临床试验表明,大黄附子汤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患者均有显著疗效[5-6]。因此,常有医家辨病论治,将大黄、附子、煅牡蛎这三味药用于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治疗中。
2 结语
目前,COVID-19的治疗主要以抗病毒及对症支持治疗为主,辅以中医辨证施治,临床上中西医结合诊治可以达到优势互补的作用。西医要严格把握手术指征,做好抗病毒、抗感染、抗炎及血液净化等治疗;与此同时,中医也要辨证施治,既病防变,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优势作用。只有中西医两者相辅相成,临床上才可取得较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