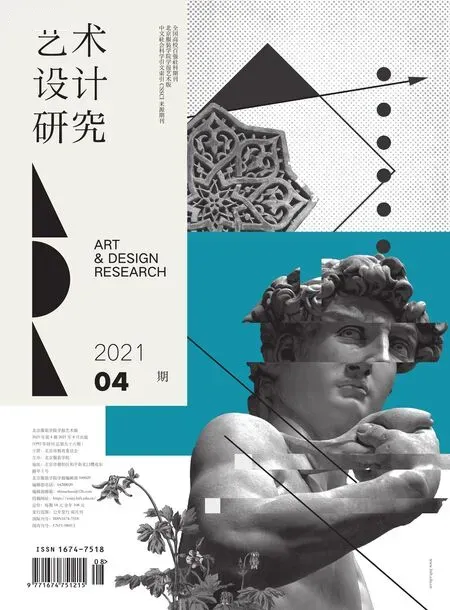现代性的时态更迭:时尚及其时间逻辑研究
熊亦冉
时尚的发展与演进总是取决于特定的时间性,它对于时间节点的划分不仅“在”时间“之中”发生,而且“通过”时间发生。因此,时尚带有特定的时间感,它是一种立足于现在的优先主义,并始终体现为持续求新的倾向。此处的“时间”指的是社会语境中被流行体系所裁定的时间坐标体系,它在“现在—当下”的纽结之处通过对“过时”的排斥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展现了以季节为节点、以流行风格为表征的时尚话语建构。现代性的时间维度借助对新奇(Novelty)体验的重塑,实现了由连续性的历史时间到过渡、偶然的非连续时间经验的转变,这同时也蕴含着不同于线型进步观的“重新发现新异”的过程。通过对时间之流的截断、裁定与分类,时尚由此展现了对于现代性的时间经验的重塑与反思。
一、现代性的经验结构
在波德莱尔的定义中,现代艺术一面是转瞬即逝的现代性,一面是永恒①。前者强调的是作为当下的“此刻”,后者则指涉古典艺术的精髓与要义。因此,现代性在重现新事物的同时,还揭示了新旧世界的对立及其不稳定性,因为“现代性只是命名了过客本身”②。时代的美学和风气通过时尚展现出一种双重魅力,它既是艺术的也是历史的。这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对于“此刻”的强调,以及对于“尚未”发生之物的关注。前者会在顷刻间转变为过去,而后者则会以崇尚未来和追求新异的形式塑造时尚的内在时间尺度。对于持续求新的现代性而言,时间予以参照的正是短暂的“偶然”与稍纵即逝的“此刻”。
1、作为时间裂隙的“此刻”
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指出,黑格尔哲学以“世界的终结”为前提和预设,实现了对于时间的废除。因此,“现在”通过辩证法实现了它的永恒化,其本质是作为现代性起点的历史目的论,它将绝对精神视作人的本质与历史的再现,并以此为终点强调了绝对理念的螺旋上升以及不断复归的永恒运动。对此,历史持有固定的方向和目标以及趋于终结的使命;同时,“现在”被赋予永恒化的形式,传统则作为“过去”而遭致废除。绝对理念将自身的现在永恒化,时间由此实现了其本质上的永恒性。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尼采更为关注现实的生存,而非空洞的逻辑和作为隐喻的真理。他否定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主张以人的生命本身即强力意志为核心,探究生活的意义与本真性,其对应的时间逻辑即永劫复归的循环时间意识。
在本雅明看来,现代性的实质是历史本身的时间化问题。因为现代性在原则上意味着对传统的破坏,而最直击本质的颠覆路径在于,如何以否定线型时间的方式实现对传统形式的抵抗?历史究竟是如何被时间化的?时间透过怎样的社会形式对历史发挥了作用?过去与未来又通过怎样的时间化形式予以传递?通过对现代性辩证意象的阐释,本雅明强调了唯物论编年史中的断裂时刻及其对于历史连续体的破坏,并由此批判了历史主义,认为这是一种架构于“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之上、区别于以往时间序列的“当下时间”③。他对历史主义的指责基于机械论的因果模式以及历史的移植,因为因果链条本身无法实现历史的可识别性。这同时意味着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不再只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意象,其间存在着“跳跃”的状态。与此对应的正是从历史连续体中爆破和抽离的时间,以及由这种新异的时间逻辑所带来的此时此刻(Now-time)。因为意象并非囿于连续性的时间范畴,而是以“停顿”(Caesura)的形式逃逸了线型时间。
“停顿”的概念最初由荷尔德林提出,而本雅明则在借用的同时强调了与之相关的历史状态及其时间形式。“当下”的时间节点由此开启,这种对于“当下”或“此刻”的经验开始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经验。在历史主义那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世俗世界线型时间轴上的已逝部分,是匀质而空洞的时间组成。在本雅明看来,“当下”并非只是过去与未来的中介,而是更具拯救意义的弥赛亚时间碎片。因此,停顿的辩证法以“当下性”和辩证意象的典型形式显现出来。换言之,“当下”蕴含了历史的瞬间及其潜能,并具备了无限敞开的可能性。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维度得以概括为“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④,而永恒则蕴含在每一个“当下”之中。并非历史的连续性,反而是停顿与中断,才使得历史自身摆脱了空洞的逻辑演绎与线型的年代秩序。这意味着“必须把一个时代从物化的历史‘连续性’中爆破出来,但同时它也炸开一个时代的同质性,将废墟—即当下—介入进去”⑤。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性的经验结构及其不连续性,以及它的短暂易逝与震惊体验,不仅可以视作经验结构的转换,而且同样意味着社会结构中时间与空间逻辑的变化。在这样的时间结构中,作为拜物商品形式的时尚如何体现了现代性所特有的时间量度?既然传统体验正在被震惊所打破和改写,那么这种特殊的时间体验又如何与个体感知相结合?对此,本雅明从现代性的感知结构出发,以时间逻辑与历史哲学的本质特征为线索展开了分析。以19世纪的时尚现象为例,空间投射聚焦于拱廊街,而主体则是作为现代性他者的游荡者(Flâneur)。本雅明尤为强调游荡者对于都市的感知维度,因为他们是现代性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同时也是现代主体的原型。其中,城市巴黎呈现为历史完整序列中的重要节点,因为在他的笔下,19世纪是由整体原初历史集结出的时代新形象,同时也是辩证意象的一种新形式。存在于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始终是对商品幻象的狂热,对新奇的永恒追求,以及沉迷于拜物的现代性情绪。
2、新奇与“新”的逻辑
新奇通常与时尚相关,且往往表现为相同事物永不停息的重复以及与当下时刻的绝对一致性。最初,新奇带有渎神的色彩,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令万物焕然一新。而古典与现代之争又使得“昨天的”与“今天的”截然相对。这一对立最早始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彼时以异教著称的“旧与新”的循环开始呈现为对于过去的阻断,现代因此逐渐具备了新奇的意蕴。新时代意识的进一步深化发生在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借由中世纪重新恢复了古代抑或远古的权威,而现代的优势恰恰在于它能够模仿古代。进而,“新的”时代愈发成为描述某一阶段性质而非历史分期范畴的短语,它更多地用于表征某一时段的新奇,并以此与逝去的时间相区别。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时代的质的维度得以进一步彰显⑥。时间维度也开始更具动态效应,并重新焕发出新的历史力量。到了19世纪下半叶,“新的”时代观念在本质上愈发接近于现代性本身的时间图式,并因此展现了它的审美与时尚面向。对新事物的最终肯定首先起源于波德莱尔的论述,他的美学观点将现代和新奇结合在一起,并将稍纵即逝的美与时尚的价值予以提高,因为所有新事物都包含着永恒的美所无法企及的元素。某一时期的现在性(Presentness)得以突出,其原因在于它不仅指涉时间,同时还以新奇的特征展现为某段时期的历史标识。换言之,“现在”的历史意义及其抽象内涵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
而本雅明则借助寓言与象征的区分,阐释了现代性背后的时间图式及其转换逻辑。具体而言,寓言与象征所对应的历史主义观点截然不同。后者与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相对应,意味着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的紧密关联。这种象征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其背后的运作逻辑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线型进步时间观。但前者所对应的实则是碎片化的历史残篇,它包含着人为的、相异的元素序列,本质上既是对于统一性的抵抗与颠覆,也是对其反整体性与反全面性的异质诠释,甚至是对于痛苦与堕落状态的某种呈现。这种状态能够更为本质地彰显历史的本真性及其对世界的原初建构。因此,寓言所直面的是世界本有的辩证性,并试图在外部建构自身的意义。这一辩证意象在19世纪的表现形式正是新奇。
因此,对于现代性的时间结构而言,其核心在于对现在时的建构。时尚的时间特质表现为内在于现代性自身的时间性差异,即基于年代时间与历史时间差异的“新”时段。这并非年代意义上需要接续的“下一个”时段,而是具备新奇特质的“另一个”时段,即历史时间的断裂。作为永劫复归的不变量,新奇使得有差异的历史时间与“连续—均一时间”的同时性相对应。因此,“人们并不是将时尚当作永恒的真理去接受,而是将其看作某一个时代的特征而将其长期保存。在历史中,新首先是以时尚的形式运作的,因为激进的历史性总是以新的名义发生”。⑦
与新奇相应的时间逻辑表现为从聚焦当下的“此刻”(Now)过渡到转瞬即逝的“刚才”(Just Now),这也正是时尚的时间图式所遵循的运作轨迹。古典与现代的对立转变为现代与当代之争,现代性的自反本质也愈发展现为某种双重化:一方面表现为新奇,另一方面又持续地转换为另一种永恒同一的“新”,正如流行的风尚在“时兴”的同时已经趋于“过时”了。因此,永久与中断之间的因果关系得以颠倒,曾经的中断时刻开始转变为时尚运作的永久性条件。但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我们无法真正定义何谓“最新的”,对于“现在”的体验亦无法以这种方式得以真正命名。时尚的本质由此表现为它始终如一地推翻自己所创造的体系,或者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不断地被“重估一切价值”。
二、时尚的生产逻辑
日常是经验得以重新历史化的关键场所,而时尚则充当了关联日常与现代性的重要环节。二者既为对方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又在双方的张力中彼此抗衡。作为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媒介之一,时尚创造了新的历史化及其相应的时间形式,并为历史主义时间逻辑的转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同时,时尚的运作还以此生成了新的辩证法,使我们得以反思历史时间中的“现在”与“当下”。
1、作为时间术语的“现代性”与“日常”
流行体系以“入时”“过时”“当季”等形式建构了时尚的时间化模式,并通过日常状态予以体现。日常由此成为了将现代性的经验结构重新历史化并发挥其潜能的场所。正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日常生活既是对现代性“作出的反应,又和它相呼应”,它是“现代性的背面”,是“我们时代的精神”⑧。因此,现代主义经验与商品形式共同构成了时尚的时间逻辑的真正来源,并表现为与之相对应的时间辩证法。“作为崇拜对象,商品注定只是用于日常消费的,它显示出两个紧密相关的特征:一是明显的自足性,或者说独立于生产过程的特点;另一个是要求有新奇的表象使它们在面对竞争产品时魅力四射。马克思创立了关于第一点的学说,本雅明创立了关于第二点的学说。……在第二种情况下,商品的标准化与时间的腐蚀性影响这二者都只有通过否定才能得到确认”⑨;而本雅明则由此认为,时尚在对新奇的崇拜中持续地从最切近的过去中重新构成“古旧”(Antiquity)。
与之类似的是,海德格尔同样在批判历史主义的前提下,肯定了现代性的时间逻辑是经验再塑形的基础。他所提出的“日常状态”(Everydayness)概念不仅内在地隐藏于现代范畴之中,而且辩证地与历史经验相关联。“每天”(Every Day)并非日历上的具体时间节点,而是展现为时间表征的弦外之音。尚未来临的明天恰恰是昨天的已有之物,而前者则是日常烦心所期待的。在日常状态中,一切事情都是同一,但时间却始终予以分化的形式。“闲暇”的断裂性力量在日常的时间图式中极为重要,它直接体现为对时间主题的中断以及对辩证法特定意义的彰显,因为闲暇在本质上正是“日常中的非日常”。
此外,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还从集体时间特性的角度论证了“日常”,他认为时间并非人们与生俱来的感知,而是需要后天学习和理解才能掌握的概念。时间与其说是被观察和度量的客观对象,不如说是经由测定才作为象征的表达,并发挥着联结个体与社会的功能。埃利亚斯指出,时间至少具备三个社会功能:第一,时间的排序使相同社会中的个体认识到,借助时间所指引和维系的共同记忆模式,群体能够获得对时间和事件的共识,时间由此具备了沟通功能;第二,时间同时还具备指向功能,以指导人们行事的节奏与节点;第三,时间具有调节行为与感受的能力,人们以此协调集体共识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
因此,时间是置于关系之中的,它并非静态的符号表征,而是运作于行为之间、具备社会功能的关系性存在。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推演,时间成为不断转换意涵、可以随之调节的动态象征。在这一意义上,埃利亚斯的“型构”(Figuration)概念为社会时间的日常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⑩。而对于“型构”的强调又是以对“社会”的不同理解为前提的,这同时也决定了特定的社会潮流将如何制衡和影响个体对自我时间经验的规划,即以何种形态呈现以时间为表征的惯习,从而应对特定的时间节点(如某个被划定的流行周期)。在“型构”与“进程”(Process)之间,起决定作用的正是时间的协调机制。这一机制在宏观层面上体现为文明进程中世代传承的外在强制力,在微观层面上则展现为日常生活观念对于时间经验的内化,并转化为群体间的行动交织与趋从。趋从的面向之一则是时尚的效仿与接受,它以惯习的方式嵌入动态的社会生活之中。
2、时尚体系与社会时间
现代性内部始终存在着对新奇事物的持续追求,但在时尚领域,它却与真正的创新完全相反。因为此处的“新”并非本真性的新,而仅仅是以“新”为面具永劫复归的相似之物,进而表现为复古与怀旧的潮流。通过对历史主义传统的重新利用,生产逻辑实现了自身的时间运作,并在追求新奇的基础上为其赋予合法性。以年份和季节为基准的时尚周期予以普遍地执行为共时化的媒介,并由此形成了以时间的均一化为特征的全球消费空间。
对此,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认为,时尚的特征蕴含着两种严格的相关原则:一方面是受制于模仿(Imitation)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新的合法性时间,即社会化的“现在”,它已日渐成为当代时尚的座右铭。因此,时尚中隐含着巨大的社会时间倒置,它使得现在与过去相得益彰。这一时间辩证法也意味着自身逻辑的持续反动,即时尚在生成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语法上的毁灭。因此,每一种时尚都同时体现了短暂和永恒。时尚的流通正如商品的流通一样:不断翻新但又永劫复归。
齐美尔(Georg Simmel)也曾指出,时尚总是处于过去与未来、存在于非存在之间,它在从众与出众的动机中维持平衡,而这种张力则以转瞬即逝的魅惑方式予以展开⑪。因而,时尚的吸引力在于自身的短暂性,其根源与宿命完全基于它对变化的强调。但变化本身并不会改变,这正是时尚的本质与特性所在。同时,时尚背后的经济动因表现为持续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永恒的变幻与兴奋。时尚受制于这样的逻辑,并被永不停歇的创新冲动所控制。“‘追求新意’正是在摆脱了所有意识形态的动机和理据的时候才体现了我们文化的现实……‘新的’事物本身已经成了一种自我证明—它不需要提及进步的概念或类似的东西”。⑫
换言之,转瞬即逝的反面是持续轮回的生产逻辑,特定的生产方式在社会运作的诸多假面中,隐藏了自身的历史本质与特征。同时,时尚的运作及其再生产逻辑又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一方面,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创造出了不断更新的社会关系图景,但另一方面,它在运作中又遮蔽和印证了自我复制的实质。在商品不断翻新的表象背后,是持续重复的再生产、流通与交换逻辑。现代性的体验借助这一生产逻辑得以颠覆和驯化,时尚周期的循环由此只是规则运作的结果。因此,时尚的时间结构既构成了现代体验的根本,又随之粉碎了传统的时间维度。
三、再造过去:时尚中的怀旧与复古
现在与永恒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现代主义时间向度中的核心议题,而二者的同一性则必须在怀旧中才能得以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艺术生产归根到底都是以历史记忆的系统为导向的,而这个系统则时常以时尚为根基。因为对每一个时代而言,当一种新的思想和艺术时尚形成之后,首要任务都是去捍卫属于本时代的时尚,或者可能将会在未来成为时尚的东西⑬。正如保罗·利科在《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中所得出的结论—只存在着一种时间,且这种时间始终是历史的。历史时间的总体化问题由此被分解为总体化、去总体化以及再总体化等诸多形式的循环,历史意识也持续地借由叙事实现自身建构。因此,时尚通过重构和溯源过去而得以生成新的风格。对此,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这样分析时尚的时间逻辑:“通过采用当下根据‘不再’和‘尚未’来划分时间的相同姿态,时尚也与那些‘其他时间’建立起了特殊的联系—毫无疑问,与过去,或许也与未来的联系。因此,时尚可以‘引用’过去的任何时刻,从而再次让过去的时刻变得相关”。⑭
1、怀旧与复古
怀旧(Nostalgia)所彰显的是对不复存在的故土或家园(Nostos)的渴望(Algia),以呈现为一种远离家乡的痛苦情感。柏拉图就曾论述灵魂从起源之处远离,并渴望找回真正的处所。海德格尔则把后来的哲学“基调”定义为怀旧⑮。怀旧是与失落和流离相关的情感,也是一种带有自我幻想的浪漫。同时,怀旧的影像总是双重影像的叠加—过去与现在、梦想与日常生活。在17世纪,怀旧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治愈的情感疾病。19世纪末,弗洛伊德则在致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信中将怀旧“情结”视为主体重复过往方式的倾向,并认为它是力比多(Libido)历史中的残存,是现实发展过程中的停顿。如今,怀旧演变成了无法治愈的现代状况,它既表征了集体记忆的共同体情感,又成为抵御历史剧变、获得稳定感与连续性的渴望。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怀旧是对现代时间观念的一种反叛,也是获取新的时间经验的特殊形式。尽管对过去的缅怀持续存在,且对于未来的渴求一直缺乏方向,但这种追逐却从未停止。正如卡夫卡在《启程》中所描述的那样—“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的”⑯。因此,新的时尚并非总是来自全新的形式,而是不断与旧有形式发生关联,并通过改造和颠覆释放出新的风格。因为“新”是从对“旧”的引述、对传统的解读中产生的。“入时”与“过时”分别表示不同时代中的形式循环,或不同时期彼此差异的风格在同一流行体系中的并存,进而以循环或重复的时间维度交替变化。
以时尚中的复古(Retro)现象为例,“Retro的概念往往意味着风格和时尚的重现,这些风格和时尚能唤起对并不遥远的过去的记忆”⑰。复古在时间逻辑上意味着断裂,因为它总是以超脱语境的状态来表达对于过去的理解。也是在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复古使过往去神话化了,它使得现在远离了大众文化的观念形态,甚至形成了一种脱离于当下的“现实”视角。通过对形象与风格的辨识、捕获与复制,复古试图与历史意识一起,激活对于过去的公共记忆。时尚由此成为一种“符号的漂浮”,其特征在于包括时间在内的固定参照物的丧失。⑱
与“Retro”密切相关的是“Retrotopia”,即“怀旧的乌托邦”或“复古的乌托邦”。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人们愈发希求回到过去而步入怀旧的时代。各种“怀旧的乌托邦”正在从莫尔式乌托邦的双重否定中出现⑲。现状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分裂与矛盾的时代,一个任何事物都无法保证自身的连续性与确定性的时代。这种不协调状态的根源在于,尽管我们已被抛入高度全球化的状态,但全球化意识却仍处于诞生的阵痛期。这也正是格罗伊斯(Boris Groys)强调的时尚“反乌托邦以及反极权”的含义,它同时指向现代和后现代的乌托邦形式及其差异性。⑳
复古以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复活过去,从而使历史成为了具备持久性但又被解构得空无一物的神话。它以中止或断裂的形式生成行进过程中的反推力,并随之构成了对历史连续性的一种反叛。这既是衡量和建构历史的新方法,也是理解历史的新途径。对于时尚而言,历史风格以去语境化的方式得以重新利用,同时又以复古的形式再现了过去的某个侧面,传统由此在持续的演变过程中以动态的形式建构为某种特殊价值。事实上,复古中的怀旧情绪始终透过不同代际的回忆而得以过滤、选择与重建。
因此,从时间逻辑上看,复古不仅召唤了过去,同时也呼应了未来。此处的过去是似曾相识的过去,是被重复和再造的新近过去,并以此将现代折叠进了传统的时态之中。复古以询唤历史记忆的方式、以去神话的姿态重塑了对当下与过去的认知,从而实现了与历史无意识的合谋。因此,复古以断裂和碎片化的时间逻辑重构了历史,并以反进化(De-evolution)的方式反思了过去。作为现代性的典型症候,复古在把握现代观念的基础之上,不断巡弋和窥探现代性的边界及其有效性。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本身的后撤又重现了集体记忆与传统的历史形式。
2、“拉弗定律”与风格的循环
对于时尚在不同代际的演变,时尚理论家拉弗(James Laver)曾概括出了“拉弗定律”(Laver’s Law),以此预测了任何一种新的时尚在150年间受欢迎的情况,并试图阐释时尚潮流的生命周期。该定律将时尚变化的复杂循环和风格演变压缩成时间表的形式,突出地体现了品味与时尚的交错变化。拉弗认为,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渗透着时代精神中的情感与知识分配。他将“时代精神”的原始思想范围扩大至现代性理论,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愈发受制于时间意识,而时尚始终是时代精神演变历程中最敏感的主题之一。作为文化的某种特殊载体,时尚在一定程度上见证或规定了隐蔽在时代精神中的重要观念,并为我们确定了与品味相关的诸多生活细节,它涵盖了姿态、语言,甚至想法本身㉑。因此,趣味与风尚的流变将断裂与停滞的共时形式纳入了平行的历史模式之中。
如拉弗所说,“没有什么比时尚的优势更能显示时代的胜利”㉒。他所提出的演变规律意在强调现代生活中的时尚在多大程度上见证了时间的变化逻辑。因此,从根本上说,时尚的本质既是短暂的又是循环的,当一种时尚被引入另一种新的风格中时,它会尽可能地缩短时间周期,从而创造出最大效应的时尚系列。至此,如果再次借用本雅明的理论,我们将会发现,时尚的流行及其当下性只有在与过去发生关联时,或只有它再次外化为过去时才能真正地获得意义。怀旧与复古的实质在于,它会抽离被忘却或被压抑的过去及其痕迹。此处的过去更多地经由一种解释学的传统予以传递,因为时尚的复古风潮最终会选择性地操纵品味的循环,并决定着对于潮流的再阐释。
结语
时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在短期内将流行的趣味或风格强立为新的规范与准则,并加速予以推行,当它人尽皆知而陷入平庸后,又将再次寻求新的风格作为替代物。在时间秩序的永恒运动中,现代性不连续的时间逻辑得以进一步展现。由于现代体验的核心在于它的即时性,因此,一方面,时尚不断地传递着强烈的现在感,它的时间框架—当下性—正在日益普遍化;但另一方面,每一种时尚希求保持永恒的渴望都将被翻新的逻辑所中断。在此意义上,当下既是共时性的聚合,又是时间的中断及其对于历史时间序列的脱离。时尚现代性的时间逻辑由此既存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内部结构,又持有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性,因为它必须通过现代主义的经验结构和再生产逻辑对风格进行调和。这既关联到社会生产的时间逻辑,又与历史主义的时间化形式相互指涉,新奇、怀旧和复古都是它最为鲜明的表征。它们代表了时间结构的不同面向—“过去”经由“现在”而产生回响,同时又指向通往“过去”的路径。
时尚由此提供了一种非因果性的历史模式,它将流行周期置于一个自主的时间区域中,并从中生成了以风格和趣味为基准的现在、过去和未来。这些时间节点以及与之对应的时尚现象共同构成了流行体系,该体系并非基于同质的进化,而是以相反的形式界定了断裂的时间序列。复古也并不只是过去在记忆中的重现,而是指涉当下经验中的再现实化。因此,不同的时尚周期不再被视为同一因果链中的某一环节,而应当被理解为独立的语义单位。与时尚相关的时间经验由此鲜明地体现为以停顿辩证法为表征的断裂性,以及各自独立的多元时间轴线,而这恰恰开启了我们对于时间特殊性的一种理解。
注释:
①(法)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31页。
②(法)阿加辛斯基著,吴云凤译:《时间的摆渡者:现代与怀旧》,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③ 张小虹:《时尚现代性》,台北:联经出版社,2016年,第40页。
④(法)斯台凡·摩西著,梁展译:《历史的天使:罗森茨维格、本雅明、肖勒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2页。
⑤(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炳钧等译:《作为生产者的作者》,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⑥ 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249.
⑦(德)鲍里斯·格罗伊斯著,潘律译:《论新:文化档案库与世俗世界之间的价值交换》,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8页。
⑧ 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The Athlone Press,2000,p.24.
⑨(英)彼得·奥斯本著,王志宏译:《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8页。
⑩ Norbert Elias,What Is Soci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12.
⑪(德)齐奥尔格·齐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77页。
⑫ Lars Svendsen,Fashion:A Philosophy,London:Cromwell Press,2006,p.28.
⑬ 同注⑦,第28页。
⑭(意)吉奥乔·阿甘本著,黄晓武译:《裸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8页。
⑮ 同注②,第17页。
⑯(奥)弗朗茨·卡夫卡著,叶廷芳译:《卡夫卡文学代表作》,北京:九洲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⑰(美)伊丽莎白·E·古费著,王之光译:《回潮:复古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4页。
⑱ Jean 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New York:Sage Publications,1993,p.140.
⑲(英)齐格蒙特·鲍曼著,姚伟等译:《怀旧的乌托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
⑳ 同注⑦,第27页。
㉑ James Laver,Taste and Fashion: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George G,Harrap and Company Ltd,1937,p.198.
㉒ Ibid.,p.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