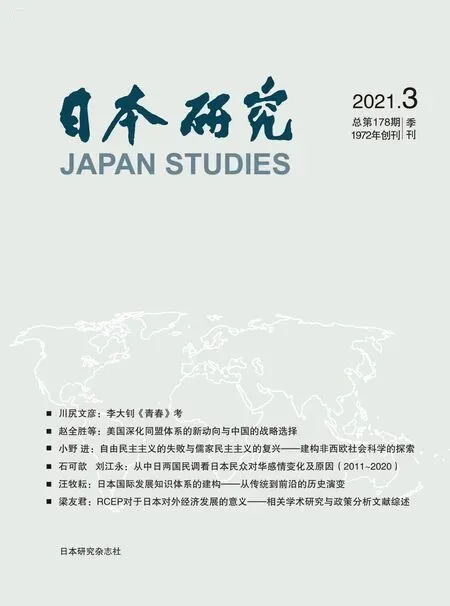李大钊《青春》考
[日] 川尻文彦
本文将探讨李大钊(1889~1927)的早期思想,主要以其在日本留学期间撰写的《青春》为考察对象。李大钊是中国近代思想领域中众所周知的重要人物,笔者也曾在另一篇论文中对其进行过考察,故在本文中,关于李大钊的生平事迹,笔者仅做简要介绍。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其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是登载于《新青年》(第2 卷第1 号,1916 年)的《青春》。这是一篇格调高雅的名文,所以自民国时期起便被看作是李大钊的代表作。[1]今天,《青春》一文不仅被选入初高中生的阅读教材,习近平主席在面向青少年的讲话中也经常在开场白里提及《青春》。因此,本文为了探究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早期思想,选取《青春》作为考察对象,解读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思想活动。
一、李大钊的日本留学经历
有关李大钊日本留学经历的研究,最早的是森正夫的《李大钊》(新人物往来社,1967 年)与富田升的《李大钊——日本留学时代的事迹和背景——作为留学生》(《集刊东洋学》第42 号,1979 年),二人的贡献在于发现了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时期的学籍档案和成绩单。中国学者有关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相关记述大多依据此二人的研究。在此之后,丸山松幸对李大钊的生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①丸山松幸《李大釗伝記資料覚書(一)》,《人文科学科紀要》第71 辑,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 年。之后的(二)—(五)也连载于《人文科学科紀要》。
李大钊在1914 年一二月份的时候来到日本,[2]并于同年9 月8 日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现为“政治经济学部”)学习。在当时,日本的大学实行9 月入学制度,1921 年4 月才更改为4 月初入学制。至于李大钊到达日本的具体时间,其本人在之后的文章《物价与货币购买力》(《甲寅》第1 卷第3 号,1914 年8 月)中写道:“残冬风雪,乃从二三朋辈,东渡瀛岛”,对“残冬风雪”的解读虽有分歧,但大致应为1914 年一二月份。另外,从早稻田当时的学籍档案可知,“二三朋辈”指的是李培潘和张润之。[3]二人在北洋法政学堂学习期间,都是北洋法政学会的成员,后来与李大钊一起赴日留学,一同入住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宿舍。
李大钊等人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该学堂的学生被早稻田大学认定为具备攻读日本大学的入学资格,所以他们没有履修高等预科,得以直接免试入学。在二战前,早稻田与其他私立大学(以明治大学、法政大学、中央大学为代表)一样,为了确保学校运营的财政来源,采用了“学部、大学预科、专门部”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4]这种三者并置的特殊的课程体系设置,为许多亚洲学生打开了在日本留学、升学的大门。在当时,留学生难以直接进入学部学习,但是,进入私立大学的专门部则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即使没有预科毕业资格也可以参加考试。②高田幸男《明知期东京的中国人留学生诸相》(藤田直晴編.東京:巨大空間の諸相[M].東京:大明堂,2001)、高田幸男《近代亚洲的日本留学与明治大学》(高田幸男編.戦前期アジア留学生と明治大学[M].東京:東方書店,2019),其中还可见与早稻田大学的比较。此外,私立大学还专门为留学生提供了学生宿舍。
李大钊等人来到日本后,没过多久便入住了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在李大钊学籍档案的现住址一栏,明确写着“牛込区下户塚町520基督教青年会内”。这一地址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户山校区)的对面,今天的穴八幡宫和早稻田奉仕园(举办各种活动的地方)一带。
关于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实藤惠秀进行了如下说明:在当时,日本有多个清朝留学生会馆,不仅能够方便留学生们在日本的生活,还是留学生团体的大本营。[5]另外,《江苏》和《湖北学生界》等报刊的编辑部也都在留学生会馆内。1905 年,在抵制《留学生管理规定》的运动期间,各省学生代表于12 月5 日在清朝留学生会馆内进行商议,坚决反对日本政府颁布的这一政策,最终决定集体回国。虽然许多留学生于翌年重新返回日本,但这一事件给清朝留学生会馆的消失埋下了伏笔。一直以来,日本独占了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这引起西方各国的不满。美国通过位于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派遣协会的里昂博士和张佩之二人前往东京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在美国驻日公使馆的帮助下,前往清朝驻日公使馆以及日本各学校,调查留学生人数与生活状态等,并于1906 年春,在位于神田的日本青年会馆内成立了华人青年会,③据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同盟的刊物《开拓者》中的两篇文章——《华人青年会》(《開拓者》第1 卷第8 号,1906 年8月)与《清国青年会》(《開拓者》第1 巻第11 号,1906 年12 月)记载,可知当时传教士们的组织运营状况,以及开展圣经、英语、数学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情况。这就是后来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该青年会以教授英语为名吸纳会员,1907 年成立早稻田分会,1910 年在北神保町设立总部,脱离日本青年会馆,从此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大本营。
据渡边祐子近年来的调查,从租借日本青年会馆的一个房间起步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于1907 年正式成立,总干事为克林顿(JacobM.Clinton),副总干事为王正廷。该会于1909 年在早稻田建成了学生宿舍,随后于1912 年在购买于北神保町的土地上落成会馆。[6]位于早稻田的学生宿舍用地是以江原素八和元田作之进的共同名义于1909 年5 月签约出租给克林顿总干事,租期为999 年。租赁费与宿舍建设费均来自英国Arthington 基金会的赞助。1916 年4 月,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位于北神保町的总馆运营上,遂将学生宿舍转让给了日本YMCA(即今天的早稻田大学YMCA),早稻田大学接受无偿转让并沿用至今(即今天的“信爱学舍”)。①渡辺祐子.もうひとつの中国人留学生史――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における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会の位置[J].明治学院大学教養教育センター紀要:カルチュール.2011,5(1):22。据说,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的相关资料收藏于Elmer L.Anderson Library(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安德森图书馆)内Kauts Family YMCA Archives 的日本YMCA 运动档案专集“YMCA International Works in Japan and the Japanese”。
李大钊同其他中国留学生开展了反对日本21条的运动,并于1915 年5 月末回到中国。关于中国YMCA 出售学生宿舍的原因,有观点指出其与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活动有关,但似乎只是会馆开展工作的需要。
二、日本留学之前的李大钊
1913 年,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创办杂志《言治》,开展言论活动。当时,李大钊和吉野作造等日本外教也有接触,为了能够读懂日语的专业书籍而潜心学习日语。他以笔名李钊(李大钊的笔名非常多,这只是其中之一)在《言治》(第1 期,1913 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的译作,颇受研究者们的关注。②《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参见丸山松幸,斎藤道彦编.増訂李大釗文献目録[M].東京:汲古書院,1970:82~84。《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为李大钊转译之作,底本为中里弥之助(即中里介山)《托尔斯泰言行录》(增补版)(内外出版協会,1906 年11 月)的附录。《李大钊全集》和李继华等编注的《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线装书局,2013 年)均未收录《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不仅是李大钊学习日语的成果,也能从中读出李大钊的某些思想。在文章开头的《译者附志》中,他写道:“日人中里弥之助氏,著托翁言行录,复综托翁言行录,结晶而成斯篇。读之当能会得托翁之精神。爰急译之,以饷当之。”文中的“中里弥之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份不详,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因创作《大菩萨岭》而闻名的作家中里介山。③斎藤道彦在《李大钊的思想——1918 年后半期》(《科学と思想》第11 号,1974 年)首次指出《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出自中里介山的编著。李大钊写成“中里弥之助”大概是依据《言行录》版权页中的发行人名。《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是李大钊最早期的成果,加之其中展现了李大钊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思想,因此备受研究者的关注。里井彦七郎指出李大钊在学习托尔斯泰思想的过程中显露出“小民性与强烈的仁爱精神”,这种托尔斯泰精神在他之后的思想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7]
森正夫认为,托尔斯泰对李大钊之后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革命就是‘悔改’”这一思想,即当祛旧恶、扬新善的心理活动得到外露时,才称之为革命。[8]里井彦七郎和森正夫均试图从李大钊后来的言论中(比如《民彝与政治》中也用相同的观点提到了托尔斯泰)解读他从《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中获得的“托尔斯泰精神”。对于二人的观点,入户野良行曾进行过批驳,但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入户野良行认为,二人均未将介于托尔斯泰和李大钊之间的中里介山纳入考察的视野,实属缺憾。即是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中里介山的托尔斯泰”是什么。入户野良行指出,学者在关注到革命精神是一种“悔改”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揭露“现代文明是虚伪文明”的“中里介山的托尔斯泰”给予李大钊的影响。④入戸野良行.中里介山と李大釗――李大釗研究ノート·その一[J].中国農民戦争史研究.1974,(4):29。续篇“入戸野良行.中里介山と李大釗――李大釗研究ノート·その二[J].駿台史学.1979,(6)”中也有提及。柳富子在《托尔斯泰与日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98 年)中指出,托尔斯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有很多以日本为媒介,但是日本对托尔斯泰思想的理解尚存许多不明之处。其中显现的是中日知识分子在“文明”认识上的共鸣。
三、《青春》(其一)
有关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的学习科目等,在森正夫等人的研究中均有介绍。李大钊入学的第一年,大山郁夫恰巧不在学校,有贺长雄代为授课。因此,李大钊后来批判有贺长雄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吧(李大钊《国情》)。李大钊说他自己受到了当时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的影响。总之,李大钊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在其著作中均有反映。
本文的考察对象《青春》刊载于1916 年发行的《新青年》(第2 卷第1 号)上。这一期的封面写有“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样,目录中有陈独秀《新青年》、李大钊《青春》、温宗尧《On Education》、易白沙《孔子平议(下)》、高一涵《乐利主义与人生》等。众所周知,从创刊到第3卷第6 号,一直都是陈独秀先生主撰,即陈独秀为主编。但是,从第4 卷第1 号开始,《新青年》的编辑体制转变为多人负责的“轮值制”。[9]原因是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新青年》随之转变为北大的同人刊物。但不管怎样,李大钊的《青春》一文在《新青年》上发表,意味着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在日本建立起深厚的关系。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十岁左右,他们是在章士钊位于东京的家中初次相见的。1914 年7 月,应章士钊的邀请,陈独秀来到(并非第一次)日本帮助章士钊进行《甲寅》的编辑工作。不久便结识了刚到日本的李大钊。也就是从那时起,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了交流与合作。[10]《青春》发表于1916 年9 月,而李大钊在1916 年5月便从日本回到了中国,并投身于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运动,忙于宪法研究会的相关活动以及《晨钟报》的编辑工作等。关于《青春》的写作时间,今天的很多研究者以文章开头所写的“远从瀛岛,返顾祖邦”为线索,推测这篇文章应该是李大钊在日期间所写。[11]
关于《青春》一文,迄今的研究者大多注重探讨该文章的哲学内涵。后藤延子回顾了《青春》的研究史,梳理了之前研究中对《青春》哲学思想的解读,包括黑格尔学派的绝对观念思想(BenjaminI.Schwartz)、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超验式哲学(M.Meisner)、具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或者“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倾向(丸山松幸)、唯物辩证法色彩的宇宙观(郭湛波)、无神论色彩的宇宙观(近藤邦康)等等。①B.I.シュウオルツ著.中国共産党史[M].石川忠雄,小田英郎译,東京:慶應通信,1964;M.メイスナー著、丸山松幸,上野恵司译.中国マルクス主義の源流[M].東京:平凡社,1971;丸山松幸.李大釗の思想とその背景[J].歴史評論.1957,(87);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香港:龙门书店,1966;近藤邦康.民国と李大釗の位置[J].思想.1964,(477);後藤延子.李大釗における「世界史」の発見――「青春」「“今”」の哲学[J].歴史評論.1976,(310):32.先前研究均注重李大钊思想的内在连贯性,重点关注《青春》在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地位以及其中蕴含的宏大宇宙观与历史观。
《青春》一文中使用了“悲壮之精神”一词,虽然李大钊并未说明该词的出处,但我们能够联想到大正时期的记者茅原华山创作的《悲壮之精神》。茅原华山是当时一流的新闻记者,他博览东西群书,善于从独特的视角解读东西方文明,是一位近年来被人遗忘的思想家。20 世纪70 年代,松尾尊允引发对“大正民本主义”的再评价,在此期间,茅原华山发行的《第三帝国》等杂志被重新加以认识。②松尾尊允称,“以己之见,大正民本主义不仅在城市,也在农村,而且扩展至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阶层,是依靠非精英阶层的劳动民众的自觉而实现的运动”。(出自松尾尊允.大正デモクラシー[M].東京:岩波書店,2001:iv。初版于1974 年发行)
茅原华山在发表于《洪水以后》(创刊号,1916年1 月1 日)的文章《悲壮之精神(令山赴我来)》③关于杂志《洪水以后》,茅原健《民本主义的论客茅原华山》(不二出版,2002年)的第五章“《洪水以后》与《日本评论》”中有相关说明。因杂志《第三帝国》的内斗而遭排挤的茅原华山,打着“宣传超东西思想——基于生活、创造国粹”的旗号于1916 年1月1日创刊《洪水以后》。其“英雄政治”“英雄主义”的主张也广为人知。《洪水以后》(创刊号,1916 年1月1日)上发表的《悲壮之精神》一文中,插入了孙中山的题字“独开生面”(见茅原華山主编.洪水以後(全一巻)復刻版[M].東京:不二出版,1984:14)。另外,在该创刊号中,还登载了戴季陶的文章《孙逸仙论》。《悲壮之精神》也收录于茅原华山《新英雄主义》(新潮社,1916 年)。李大钊也有可能参考的是这篇文章。中写道:“宇宙是不断更新的久远轮回,正如万象有盛衰,地球、人类、民族也皆具盛衰,文明生活使人类越来越远离自然。而文明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颓老之境的人类之复活再生是今日赋予人类的根本课题。”这里呈现的正是作为学界共识的李大钊《青春》中体现的“宇宙观”。
据石川祯浩的考察,李大钊《青春》和茅原华山《悲壮之精神》之间的对应关系在《青春》中存在多处,而且均是《青春》的核心部分。[12]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1)宇宙无始无终,因此,空间无限,时间无极,这是从“绝对”的观点得出的结论,若从“相对”的观点看,宇宙显示出“万象万殊”、时刻变化的特质;(2)正如地球上有生命,人类的生命也有少年期、青年期、壮年期、老年期的盛衰,但是“青春”能够再恢复;(3)人类的历史已度过了过去由进化论支配的“发生时期”,现在已到关注复活再生问题的时候;(4)西方各国、印度、中国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再生复活;(5)若拥有与无穷宇宙并行的“悲壮之精神”,就能够使国民复活再生。
李大钊继承了茅原华山的“宇宙观”,但与茅原华山的《悲壮之精神》大不相同的是,李大钊在《青春》中,将重点放在了“中国的再生”上。文中写道:“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13]接着,李大钊又对“青春中国”补充说明道:“建国伊始,肇锡嘉名,实维中华。中华之义,果何居乎?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吾辈青年之大任,不仅以于空间能致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并当于时间而谛时中之旨也……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14]“中国”即为“中华”,在空间上居于“中”。李大钊还希望“中国”居时间之“中”,期待中国的“投胎复活”。这些对“中华”和“中”的解释,是茅原华山所没有、李大钊自己独创的内容。
四、《青春》(其二)
在《青春》一文中,有一个长期困扰研究者的问题,即文中出现的拉凯尔究竟是何许人也?收录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岩波书店)中的日译《青春》,译者丸山松幸只是将“拉凯尔”音译为“ラカイル(rakairu)”,注释为“不详”,[15]坂元弘子在重译《青春》时,也沿用了“不详”的注释。[16]在中国也是一样,最新版本的《李大钊全集》(2013 年)中标注“不详”,[17]在李继华所著的《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2011 年)中,也并未探究拉凯尔。[18]《青春》是现代中国的青少年耳熟能详的一篇文章,文中拉凯尔的那句话——“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尔欲享兹幸福,当死于少年之中。”——更是中国脍炙人口的名言。可是,说话人拉凯尔究竟是何人,却一直都不清楚。直到王宪明等人发现,“拉凯尔特说,长久保持青春,是人生最高的天福。欲享受这样的天福,就要死于少年之中”这句话出自竹越与三郎①竹越与三郎(1865—1950),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史学家、政治家,号竹越三叉。求学于同人社与庆应义塾,1883 年进入时事新报社工作。后辗转基督教新闻社、大阪公论新闻社,于1890 年参与创办德富苏峰主持的《国民新闻》,成为民友社同人。著有史书《新日本史》(1891年、1892 年)、《二千五百年史》(1896 年),本着启蒙的目的主张文明史观。尔后,转入政界。的《惜春杂话》(1912 年),[19]进而得知拉凯尔是德国诗人、文艺批评家Friedrich Rückert(弗里德里希·吕克特)。②弗里德里希·吕克特(1788—1866),德国诗人、东方学者。曾在维尔茨堡大学学习法律和语言学,后任埃朗根大学东方语言教授、柏林大学教授。拿破仑战争时期,创作大量优秀的爱国诗歌。其行文流畅典雅,内容饱含深情,佳作众多。对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等东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模仿,在当时首屈一指。竹越与三郎将Rückert音译为“ラッケルト(rakkeruto)”,“拉凯尔”应是对该日译名的汉语音译。《惜春杂话》和《青春》的对应片段如下:
《惜春杂话》“三、世人皆有失乐园”
拉凯尔说:“长久保持青春,是人生最高的天福。欲享受这样的天福,就要死于少年之中。”这与古人西行法师所说的“愿逝春花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青春只有一次,一逝而不复还,若想长葆青春,就要于青春之中死去。这句话确有道理,但也并不完全。我想说的是,即便我们未在青春中死去,我们也有长葆青春之法。[20]
李大钊《青春》
拉凯尔曰:“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尔欲享兹幸福,当死于少年之中。”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21]
通过对比可知,李大钊的《青春》直接引用了《惜春杂话》中吕克特的原话。《惜春杂话》中还援引了西行法师的名句,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需要,所以被李大钊删除。在当时的日本,吕克特的这句话可能非常出名,但目前尚无相关研究可证。吕克特原诗的题目为Erinnerung(意为“记忆”,作于1833 年)。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惜春杂话》(1912 年)。作者竹越与三郎为培养那些满怀理想、前途无限的青年而全情投入,为此创作的《惜春杂话》是一部饱含深情追忆青春,娓娓讲述友情珍贵的青春赞歌,文中含蓄地展现出他的青年观、幸福观和友情观。[22]竹越与三郎在今天很少得到关注,但哲学家林达夫曾自述说非常喜欢阅读竹越与三郎的《惜春杂话》。林达夫评价竹越与三郎道:“竹越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与践行了福泽谕吉精神,他崇拜陆奥宗光,是一位拥有非凡才干的政治家,他既散发着一种洋气的贵族感,又平易近人,既是社会精英,又不失大众关怀,给我以亲切之感。”[23]
《惜春杂话》的章节构成中,开头是“一、不负青春”,然后是“二、人生即美术”“三、世人皆有失乐园”,第七到第九章为“英雄时代(一)至(三)”,最终章是“十八、民族优越主义”。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大钊将关注点放在了第一章“一、不负青春”,并在《青春》中有所体现。另外,《惜春杂话》附录中的《北京消息》①《读卖新闻》,1907 年11 月29 日报道,内容是与庆亲王、张之洞、袁世凯、肃亲王等清朝高官之间的对话,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也有可能引起了李大钊的关注。
吕克特的名言出自“三、世人皆有失乐园”,除此之外,可确定是出自“一、不负青春”部分的引用也有几处。《惜春杂话》和《青春》的对应片段罗列如下:
《惜春杂话》“一、不负青春”
余之今日主义……吾生确如卡莱尔云,不过时间所执“无限”也。无限以我所现者,现在也。若现在结束,则无限结束。[24]
李大钊《青春》
夫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以吾人之生,洵如卡莱尔所云,特为时间所执之无限而已。无限现而为我,乃为现在,非为过去与将来也。苟了现在,即了无限矣。[25]
李大钊在文中使用的“今日主义”一词在现代汉语中难以理解。实际上,在竹越与三郎的原文中出现了该词,意为活在当下,李大钊照搬了该词。
《惜春杂话》“一、不负青春”
拜伦生性放浪,时人攻之,论其来世必承地狱之苦。拜伦答之,基督教徒于前世受苦,而欲得来世之福。非基督教徒于现世逸乐,而来世之苦难,则非能辞也。唯苦乐先后之别,而无分量之异。言虽矫激过甚,但有真理之居。以绸缪之名予青春以苦,为积其所不能积之黄金而衰老者,或虽能积之而不用之,为黄金虚度青春者,余冀能思量此语。青年轻富,则老后多凄凉。然是积得黄金而不能用之,为无用之黄金虚度青春,又子孙袭其遗产,反为之承精神之不幸。两相比之,孰幸乎?[26]
李大钊《青春》
诗人拜伦,放浪不羁,时人诋之,谓于来世必当酷受地狱之苦。拜轮答曰:“基督教徒自苦于现世,而欲祈福于来世。非基督教徒,则于现世旷逸自遗[遣],来世之苦,非所辞也。二者相较,但有先后之别,安有分量之差。”拜轮此言,固甚矫激,且寓讽刺之旨。以余观之,现世有现世之乐,来世有来世之乐。现世有现世之青春,来世有来世之青春。为贪来世之乐与青春,而迟吾现世之乐与青春,固所不许。而为贪现世之乐与青春,遽弃吾来世之乐与青春,亦所弗应也。[27]
这里是一处较长的引用。竹越与三郎引用拜伦之言表示赞同,并展开自己的看法,李大钊直接照抄了竹越与三郎的论述。《惜春杂话》“一、不负青春”
爱默生曰:“汝若爱千古,更当用现在。呼昨日而不能返,思明日而未确实。汝确实把握者,唯今日尔。今夜一日,似明天二日也。”余据此意,倡今日主义,劝汝莫失青春。[28]
李大钊《青春》
耶曼孙曰:“尔若爱千古,当利用现在。昨日不能呼还,明日尚未确实。尔能确有把握者,惟有今日。今日之一日,适当明晨之二日。”斯言足发吾人之深省矣。盖现在者吾人青春中之青春也。青春作伴以还于大漠之乡,无如而不自得,更何烦忧之有焉。[29]
《惜春杂话》“一、不负青春”结尾
人当享生之乐,尤惜青春时。德国史家蒙森评凯撒,言其“以青春之杯,饮人生之水,浮沫沉淀皆共干之。”呜呼!愿吾青年,爱人生,享人生,惜青春。举夜光之杯,一饮人生甘泉。[30]
李大钊《青春》
德国史家孟孙氏,评骘锡札曰:“彼由青春之杯,饮人生之水,并泡沫而干之。”吾愿吾亲爱之青年,擎此夜光之杯,举人生之醍醐浆液,一饮而干也。[31]
这是《惜春杂话》“一、不负青春”结尾处的高潮部分。李大钊在《青春》中直接引用了这一部分,表明其赞成《惜春杂话》“一、不负青春”的观点。李大钊紧接着引用了《庄子》中的一段话,并呼吁青年“达于青春之大道”“乐其无涯之生”,随即收笔《青春》。
上文以卡莱尔、爱默生、拜伦和蒙森的名言为线索,对《惜春杂话》“一、不负青春”与《青春》进行了对照分析。李大钊从《惜春杂话》“一、不负青春”中引用的部分应该不限于此,仅依据上述对照可得结论如下:
第一,《青春》照搬了《惜春杂话》“一、不负青春”的末尾结论部分。李大钊在《青春》中虽然引用了卡莱尔、爱默生、拜伦、蒙森等人的箴言,但并不是李大钊在博览这些西方文学家、思想家的原著后直接引用的,而是“转引”于竹越与三郎引用的词句。对西方人的引用,往往不是取自原书,而是“再引用”。通过引用欧美的名人名言,以加强观点论证的写作风格非常普遍。竹越与三郎等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以及受其影响的李大钊皆采用了此种风格。
第二,《惜春杂话》“一、不负青春”的主旨(特别是结论部分)直接体现在《青春》中。可见李大钊赞同竹越与三郎以“今日主义”表达的“不负青春”之主旨,并非只是对其词句的摘抄。
《惜春杂话》是竹越与三郎对青年们的激励。“一、不负青春”以“世恐人生之短,余叹春日之短;人惧死之将至,余畏老之将至”为开头,以“呜呼!愿吾青年,爱人生,享人生,惜青春。举夜光之杯,一饮人生甘泉”为结尾。当时的文艺杂志评价“一、不负青春”,称其“充满着华丽的青春之赋。其流淌的旋律,叩击着明眸热血的青年之心,鼓舞着青春的士气,蕴藏着一股让人载歌载舞的魔酒力量。”[32]李大钊也正是被这一点所吸引的吧。
五、《青春》(其三)
《青春》用古风的玄学文体展现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亲和性。《青春》中的生死观明显与中国传统思想一脉相承。①林文孝.李大釗「青春」に見る伝統的死生観とその変容[J].山口大学人文学部異文化交流研究施設ニューズレター.2004,(5):17.林文孝是明清思想的研究者,因其未囿于李大钊研究的前人成果,所论反而新颖,颇多启迪。可以说,林文孝的认识比较接近中国普通读者阅览《青春》时的感受。在此首先对“青春之进程”(李大钊认为的“相对”)与“无尽之青春”(李大钊认为的“绝对”)进行考察。
在《青春》中,生死是轮回循环的“相对”变化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李大钊所说的“青春之进程”。这种将生死“相对”化的想法显然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传统。李大钊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与“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两句话,并接着说道,“夫晦朔与春秋而果为有耶,何以……菌、蛄独不知也?而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也?是有无之说,亦至无定矣。……其年小于宇宙自然之年,而欲断空间时间不能超越之宇宙为有为无,是亦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耳!”[33]可见,《庄子》“相对”化的生死观原本就存在于李大钊的思想中。
此外,与“相对”化的循环变化不同,李大钊将“绝对”定义为“无尽之青春”。关于李大钊的这一思想,林文孝认为有两点源自中国的传统思想。[34]其一,李大钊认为“生生”理念贯穿了整个世界。虽然他本人并未明确表达,但可看出其与朱子学思想的相似性。实际上,用中国的传统思想“生生”理念来分析解读李大钊《青春》的思想在中国的李大钊研究界颇为常见。①关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生生”理念,引用现在普遍认同的岛田虔次的说明如下,以做参考。“《易经》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系辞传),此‘生’‘生生’乃程明道(程颢,1032—1085)之思想基础。‘生生’中的‘生’有两义,一为活着,即生命之意,二为出生,即生产之意,‘生生’是包含此二义之统一体。……天地之德为生、生生,乃‘道’也。《易经》(系辞传)有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指天地阴阳之气一刻不会断绝,氤氲集散,万物化醇,即生生不息。……因天地而生者,皆承天地生生之德而生。区别于万物的人类,在这一点上也别无二致。”(島田虔次.朱子学と陽明学[M].東京:岩波書店,1967:41~42)即认为,仁者,生生之德也,与义、礼、智构成“四德”,同时又涵盖四德。此外,在季节当中,春天对应仁。春是四季之一,同时在生生之根源性上,春又贯穿了所有季节。
其二,李大钊认为“相对”的变化和“绝对”的不变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关于这一点,李大钊以传统思想为依据进行了阐述。比如他认为,《周易》书名中的“周”,并非朝代的名称,而是“常住”之意,与“变易”之“易”相对。作为该种解释的先例,他引金圣叹的《序离骚经》为证,金圣叹说道:“周其体也,易其用也。约法而论,周以常住为义,易以变易为义。双约人法,则周乃圣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变易。”[35]
李大钊进一步写道:“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出自《庄子·德充符》)此同异之辨也。东坡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出自苏轼《赤壁赋》)此变不变之殊也。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异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进程,其周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有者青春之进程,其无者无尽之青春也。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也。”[36]由此可见,在生死“相对”化与“生生”思想这两点上,《青春》所展现的生死观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与李大钊之间的继承关系。因此,与其说这是李大钊独有的观点,倒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观点。
然而,《青春》论述的重点在于创造出能够摆脱历史和传统束缚的变革主体——“青年”。为此,不仅要继承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还要思考如何改造。于是,李大钊在文中强调切断历史。如前文所述,他认为“中华民国”的“中”,不仅应解释为空间的“中点”,也应看作时间的“中点”。进一步讲,在这种认识中潜藏着一种方向性,指引“青春”朝向“近代”。反过来也可以说,这是祈盼“青春中华”之复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这些思想都是李大钊所借鉴的茅原华山与竹越与三郎的思想中所没有的。
结 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青春》的结构可归纳如下:《青春》的前半部分参考茅原华山的思想,展开了宇宙论和存在论;后半部分参考借鉴了竹越与三郎“不负青春”中的“青春”论。在整体上,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庄子》等中国经典,凭借中国传统思想激发中国读者的理解,增强对中国读者的说服力。因为中国传统生死观对中国读者来说更容易接受,从而弱化文中思想是借鉴自西方或日本的印象。由此看来,迄今聚焦《青春》中“宇宙论”的解读有失妥当。不仅如此,将《青春》中的“宇宙论”作为贯穿李大钊一生的思想,甚至统摄其马克思主义史观与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及实践,那就更加牵强了。之所以这种解读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和日本的学界中也广泛存在,除了为彰显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先驱者的功绩之外,还因为大家欲强调其思想连贯性的深层意图。
笔者想指出的是,李大钊虽然论述了中国传统的生死观、“青春之进程”以及“无尽之青春”,但其将“青春中华”置于时间轴之“中”以追求“复兴”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是茅原华山和竹越与三郎所不具有的、李大钊自己的独特之处。玄学色彩的晦涩文体以及古语词汇的频繁使用虽然也能反映出李大钊作为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所拥有的理想与抱负,但从他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展开论述的写作方法中也能看出其“新旧调和”的思想特征吧。
限于篇幅,本文仅停留在《青春》一文的分析上。在同一时期,李大钊还发表了《民彝与政治》等多篇重要论文。以这些论文为考察对象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工作留待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