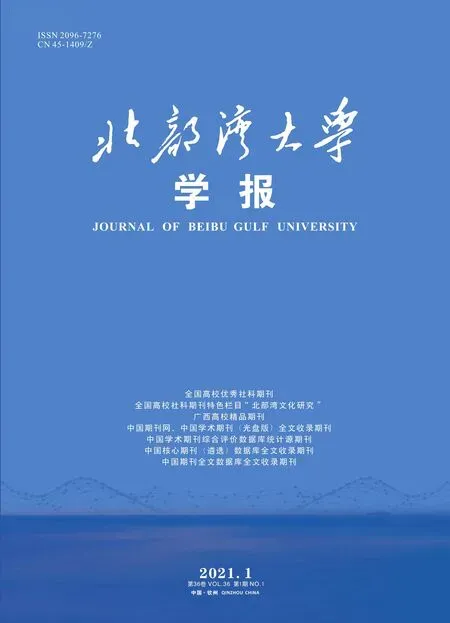两汉时期丝绸之路译人研究
潘俊杰
(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钦州535011)
中国在两汉时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影响深远,而丝绸之路上的“译人”则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两汉时期,存在着大量的“译人”群体。王博凯的《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译人”及相关问题试论》证实,西汉时期在“楚言”作为通行语的长沙国有“译人”群体服务于司法诉讼和行政事务。王子今先生的《“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从两汉的“译官”制度、西域的“导译”“译道”“译长”考证入手,探讨分析“译人”在中央王朝与西域民族关系中的历史作用,此篇大文虽然研究的是西域方国的“译人”现象及其作用,但是与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译人”有密切的联系,给我们颇多启示。王开元的《西域文化对先秦两汉诗赋的影响》,从《诗经》《楚辞》以外的先秦两汉诗赋探讨其所受西域文化之影响,文中提到匈奴语的《匈奴歌》被翻译成汉语的文学翻译事例,对两汉时期丝绸之路文学艺术的互动交流有一定作用。现有研究对两汉时期丝绸之路“译人”的来源、“译人”的类别、“译人”的职能等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限于此方面文献资料较少,本文多有大胆推论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译人
西汉张骞和东汉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文明,通过商贸和宗教等人文交流影响了其后中国和世界将近两千年。
两汉时期,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首先主要是商队,其次是两汉王朝维护管理丝绸之路的官员、驻军以及来往的使者,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期还有少量传播佛教信仰的教徒们。在所有这些群体中,充当翻译和向导的人显得尤为重要,这可能是一种古老的职业。有人说自从人类有了语言,有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需要,语言的“翻译”就诞生了。“就中国而言,远在原始社会,各氏族部落或部族之间,就应该有双语人或多语人的翻译活动,然而已无文献可征。”[1]1最早的语言翻译者被很形象地称为“舌人”,即以口舌言语为生的人。根据一些古文献记载,至少在西周时期中央王朝中已经有他们的身影,有关戎狄等少数民族向周王朝贡的记载:“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2]16是说少数民族使者不懂得中原王朝的礼仪,不等周王赐宴而是坐在朝堂门外,就只能让懂得少数民族语言的“舌人”亲自把食物端给他们。为何称为“舌人”?据说,那时人们对那些能通译几种民族语言的人感到很惊奇,猜测他们的舌头和一般人的舌头不一样,认为他们有特异的“重舌”,即长有几重舌头或几条舌头,因此称之为“舌人”。
据《礼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3]1338其中,职官的命名方法和中国古代将天下分为五个部分可以一一对应起来。首先是天下之中的华夏“中国”(居中之国,笔者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大多建都北方,从秦汉到明清的主要王朝基本如此。因此与翻译相关的“译长”职官设置较早,在《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里人数最多的就是译长。《汉书·西域传》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支、安息、罽宾、乌戈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4]3928根据笔者统计,西域50国中设置有“译长”官职的有24个国家39人,占西域50国佩戴汉印绶376名职官总数的10%还多。在这些方国中,译长人数最多的是莎车国和龟兹国都是4人,焉耆国3人,鄯善国(楼兰)、扜弥国(拘弥)、疏勒国、姑墨国、尉犂国、卑陆国、车师前国分别是2人,且末国、精绝国、于阗国、皮山国、乌垒国、危须国、卑陆后国、郁立师国、单桓国、蒲类后国、劫国、山国、车师后国皆为1人[4]3875-3921。每一个国家译长的多少是以这些国家本身人口数的多寡和军队人数按比例来确定的。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许多小国只有一个译长,甚至西域50国里除了24个较大的国家设置有译长外,其余26个国家到底有没有译长,史书没有记载。王子今先生的考证认为:“‘单桓国’只有 ‘户二十七’,也置有 ‘译长’。‘译长’在西域诸国职官机构中,都有比较重要的地位。”[5]13王子今先生进而指出:“推想 ‘译长’之下,译员的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5]13笔者认同他的观点。
根据《礼记·王制》的划分,东夷、南蛮、西戎相对应的翻译人员分别是“寄”“象”和“狄鞮”。由于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论述,本文在此只考证“象”。郑玄给《周礼》做的注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象胥”是“舌人”的一种,也是中央王朝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不过却是下层的官员,“胥”是下层官员的简称。“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6]892《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7]2835句中的“三象”显然指的不是大象,而是三名翻译人员“象”。相传为西汉初期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房中歌》有:“蛮夷竭欢,象来致福。”文中的“象”指的即是翻译人员,意思是边疆之地的人民尽情欢乐,他们的君主派出翻译人员“象”作为使者向中央王朝进贡致福。“象胥”作为下层官吏,管理着多少翻译人员呢?《周礼·秋官》可作为参考:“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十二人。”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在同一时期,中国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被开辟出来,与之相应的是翻译人员作为必不可少的职业,也出现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4]1671其中“译长”“译使”指的都是译人中的官吏,在其下肯定还有普通的译人负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具体工作。
二、两汉丝绸之路上译人的来源及其类别
秦朝在统一天下之后,建立起完备的官僚体系。而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大部分典章制度。据《礼记》载,北方的翻译人员称为“译”,而秦汉之后对所有翻译官员统称为“译”,笔者认为其大概原因在于秦汉王朝均是在中国北方建立起来的中央统一王朝,延续了古代对北方翻译人员的称谓。根据现有文献记载,秦及两汉王朝与翻译人员有关的机构和职官主要有“典客”“典属国”“大鸿胪”等。“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4]730“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属官,九译令。”[4]735可见,自秦王朝开始,“典客”和“典属国”都管理着大量的翻译官员,他们分别包含译官和九译令及下属官员。实际上,“典客”和“典属国”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字面来看,二者都有一个“典”字,“典”字在一般意义上常用作名词“标准、规范”“典故”以及形容词“典范性的”使用,此处的“典”作动词用有“执掌、管理”之意。“典客”管理的“客”是邦交国的“客人”,没有所属关系,“典属国”管理的是“属国”,它们与“典客”有内外之别;其次,从两个职官界定的职责来看,“典客”是“掌诸归义蛮夷”,核心词是“归义”的蛮夷,是从形式上、名义上对中原王朝权威的认可。“典属国”是“掌蛮夷降者”,核心词是“归降”的蛮夷,是真正意义上臣服并接受中央王朝领导和治理的民族地区政权,归义和归降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典客”和“典属国”所管理的下属官吏也就有很大的区别:“典客”的下属官吏中的译官负责外交翻译等工作,而“典属国”的下属官吏九译令则承担国家内部管理方面的翻译工作。
如果说“典客”和“典属国”以及西汉沿革之后的大鸿胪等职官管理的翻译官是中央王朝文武百官内部的设置,那么,两汉时期在西域各国设置的“译长”及其属官则是另外一个庞大的地方性或者地域性的翻译官吏群体。根据清人黄本骥编的《历代职官表》“礼部会同四译馆”第九表“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的记载,两汉时期这些翻译官依官阶排序为:译官令,九译令,主客;译官丞;朝鲜通事官及分管的译长[8]。从官秩的排列可以看出“译长”是最低级别的翻译官。
无论“舌人”“象胥”或者是译官令、译长,他们都通晓“外语”,他们的专业技能从何获得?对此进行探索,是颇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由于此方面文献资料欠缺,我们只能做一些大胆的推想。马克思认为语言产生于生产劳动过程中,翻译人员首先应该是来自于民族杂居地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通过交流熏染造就。我们知道,即使到了现在,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一些民族杂居地区的老百姓中能听懂且会讲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人也不少。因此,大量的翻译人员很有可能首先是来自民间。其次,是来自官方的招募。汉武帝在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向全国征募使者:“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4]2687与张骞一起出使西域的随行者“堂邑氏奴甘父”,是西汉与匈奴之战中被汉军俘虏,并被作为奴隶赏赐给汉武帝的驸马堂邑侯陈午,堂邑是陈午封地的地名,其匈奴姓氏名字不载,故史书以堂邑侯陈午的封地为其姓氏,其名甘父,又称堂邑父,作为张骞出使的向导。在汉武帝征讨匈奴之前,整个西域地区几乎全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因此堂邑父熟悉西域的道路,能听懂且会讲几种西域的语言也未可知。古代对于使臣的选拔不一定要求必须会外语,但是对于随从的挑选必定会考虑到向导和翻译的职能,堂邑父作为出使的随从人员,在出使过程中与张骞一起被匈奴扣押达十年之久,脱逃之后与张骞顺利抵达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国,归途虽变更路线走天山南线,但依然再次被匈奴抓捕扣押,等回到长安时距其出使之初已有十三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文献记载有:“堂邑父胡人,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4]2689文中虽未明言堂邑父肩负着向导和翻译的职能,但可以想象张骞被匈奴扣押十年后在脱逃的过程中堂邑父所起的作用。从最终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如果没有堂邑父,张骞的出使不会圆满成功。因此,在古代交通、通信以及外交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翻译人员和向导非常重要。像堂邑父这种人才在两汉时期应该不是孤例。敦煌马圈湾汉简有“都护虏译持檄告戊部尉钦车师前附城翊(一一二)”[9],其中,“虏译”透露出其身份与堂邑父有相似的信息。《汉书·傅介子传》中亦记载有介子派遣“译”以黄金锦绣诱杀楼兰王的故事。
秦汉之前,商贸意识浓厚的西亚和中亚就有了赶着骆驼的商队游走于地区和国家之间,等到西汉中期中国打通了西域连接中亚与西亚甚至更远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后,中国南方沿海的广东徐闻、广西北海、福建泉州等地也向东南亚以及遥远地区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来自民间服务于这些商贸活动及政府管理机构的翻译人才大量被使用,这是可以想象的。在两汉时期的西域和中亚有数十种民族语言,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使节以及传播佛教的僧侣操着不同的语言,虽然许多语言没有文字,但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显示至少有六种文字可知,具有语言翻译作用的人才在丝绸之路上应该也不在少数。
不可忽视的是,两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蓬勃兴起,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繁荣,译长、译使等翻译官员也见诸历史文献。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集中在岭南的两广和福建地区,主要有广州、泉州、徐闻、合浦等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译人应该也是由这些地区陆地的译人“象”转化而来的。《礼记·王制》对夷、蛮、戎、狄四方地区译人的称谓为“象”,南方地区的译人应该是在先秦时被称为“象”的后裔,两汉时期则成为“译人”的一部分。
那么,从专业分工的角度来看,译人有哪些类别呢?根据现有文献结合近些年出土的简帛,笔者略作梳理。译人至少存在以下三类。
一是导译,即翻译与向导相结合。
《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 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10]3158
《史记·大宛列传》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10]3169
《汉书·张骞传》记载:“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4]2688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到,张骞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得到过出使目的国家的协助,《史记》记载大宛“发导绎”、乌孙“发导译”,而《汉书》记载大宛“发译道”。其中“唯王使人道送我”,唐人颜师古注“道读曰导”,也就是第一则引文中的“唯王使人导送我”;而引文中的“为发导绎,抵康居”,明人凌稚隆曰:“观后书‘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则此‘驿’亦当作‘译’。”笔者认为,引文中的“导绎”和“译道”从读音和意思上皆应为“导译”或者“译导”,“译”是翻译人员,“导”是向导,二者在古代西域的出使团队中是必不可少的人员,而在很多时候,翻译人员和向导则由同一人兼任。
二是驿员(边疆地区的),即翻译与驿站职能相结合。
汉代悬泉置出土的一些竹简,可资佐证。
一六一 入上书一封,车师己校、伊循田臣强,九月辛亥日下餔时,临泉译(驿)汉受平望马益。(V1310:367)[11]124
一九三 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其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驿)骑当富,县(悬)泉译(驿)骑朱定付万年译(驿)骑。(II0113:65)[11]137
胡平生、张德芳先生认为,以上悬泉汉简中的“译”皆当为“驿”(见上面简帛释读括号内字),笔者不能完全赞同。理由是:如果我们在释读两汉时期类似悬泉置这样的关塞简帛文献时,将这些关防要塞的“译”全都改为“驿”,从文书档案的字面来看,文意通顺,这些关塞在历史上确实也是重要的驿站,而且“译”和“驿”同音,可能是假借或者刻写这些简帛的人员刻错字了?笔者认为,这种猜测经不起推敲。第一,“译”和“驿”虽然同音,但是字形差别比较大,较之先秦时期假借的用法比较普遍,到了两汉已经有所减少,尤其是官方档案的简帛刻写,从秦王朝开始要求就已经非常严格,公文文书刻写错误要受到惩罚。第二,边疆地区和内地关防要塞的驿站应该有区别,二者最大区别就在于:边疆地区的边防要塞和驿站需要翻译人员,而内地的基本不需要。因此,像悬泉置这样的要塞驿站有“译”是正常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西域地区的文献中记载有“译长”但却没有“驿长”的问题。这是因为,译长管辖的下属译员分布在各个关防要塞和驿站之中,同时也肩负着“驿”的职责,类似于当代基层公务员兼任多种具体的工作。从以上简帛释文看,这些翻译人员还兼任着“驿”的某些职能,是“译”与“驿”相结合。
三是译使,即翻译与外交使节的结合。
古代翻译人员首先要服务于外交,所以“译”与“使”在很多时候是结合在一起承担出使的使命,因此也称之为“译使”。《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章和元年,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张纡遣从事司马防将千余骑及金城兵会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7]2882文中亦有“译使”作为出使归降的重要媒介。“王利器引录《后汉书》卷六《南蛮传》所谓‘其使请曰’,《韩诗外传》卷五、《说苑》卷一八《辨物》等均作‘译曰’,可知‘译’和‘使’的关系。”[12]由此可以断定,两汉时期,在很多情况下翻译人员和出使的使节身份是重叠的。
行走在两汉丝绸之路上的译人除了服务于政府机构的人员和商贸团队的导译成员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人,他们就是佛教的传播者,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弘扬佛法。在佛教史上,大致可以肯定的是,东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传播佛教的是安世高(安息人,现今伊朗地区,生卒年不详),大约在148—171年经西域来华,译有《安般守意经》等;另外一位是支娄迦谶(大月氏人,147—?),大约在178—184年通过西域来华,译有《般若道德经》等。这两位高僧都精通数门语言,同行带有弟子,一路东行,在不同的地区给不同的民族弘扬佛法,最后到达东汉王朝的中原腹地。在此过程中,这些高僧及其弟子也就成为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的传播者与翻译者。“公元2世纪,佛教传入西域后,一种在神殿外环绕一圈回廊的方形佛寺开始在塔里木盆地流行,通称‘回字形佛寺’。于阗王国的著名佛寺遗址——丹丹乌里克佛寺,就普遍采用回字形建筑。在吐鲁番盆地,这种古老的建筑一直流行到公元9世纪,并对回鹘佛寺和石窟寺产生重要影响。”[13]这说明东汉时期西域的佛教已经比较兴盛,佛教信徒这个庞大的群体里也有不少的翻译人员,只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传教和译经。
三、两汉丝绸之路上译人的职能
译长在两汉王朝开通和治理西域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大,译长之下应该还有属员译人。译长和译人在两汉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肩负多种职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断断续续绵延千余年。译人最重要的职责首先是翻译,小至商旅贸易的中介翻译,大至民族、地域、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等官方翻译;其次,译人中的官吏“译长”在很多时候肩负着外交使命,又被称为“译使”,持节外交或者向西域等诸属国翻译颁布中央朝廷的诏命和文书;第三,译人很多时候还兼任出使时的向导、涉外驿站的管理等职能(上文引用汉简已列类分析);此外,译人最初担负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服务,随着丝绸之路打通并发展成熟后,经济文化上升为中外交往的主要内容,译人的职责也发生一定的转变,充当涉外经济文化交流媒介的功能逐渐凸显。
(一)翻译职能:“重译”
在古代要将一种语言翻译成目的语言,要通过中介语言“转译”才能完成,有时候要通过多次转译才能达至目的语言。这种现象在古代叫“重译”,有“重三译”“重九译”或“累九译”“累数译”。《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4]348《后汉书·南蛮传》载:“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7]2836上文所引《尚书大传》(卷三)“越裳氏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其中,“三象”是三名翻译人员,经过三重翻译才能朝贡并转述越裳国君主的朝贺意思,后来诸如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越裳重译”句注《尚书大传》引述前文为“重三译而朝也”。比“重三译”更复杂的翻译被冠之以“重九译”,见《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听取张骞汇报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千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10]3166前文提到秦汉时期“典属国”的下属官员有“九译令”,即是据此命名的。贾谊的《新书·保傅》中还有:“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14]无论是“累九译”“累数译”,最后都可以用“累译”来概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论曰:‘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至于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亦内属焉。”[7]2860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九”是最大的数,但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也不是具体的数量词,而是极言其多。“累九译”“累数译”,只不过是为了形容辗转翻译的复杂程度及中间转译多次的难度。关于“重九译”“九译令”中的“九译”,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中原华夏族周围的少数民族及其语言种类太多,一个翻译人员需要懂得多种民族语言才能更好地为边疆地区的治理服务;二是指中原华夏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语言不能像现代语言可以直接两两对译,而是要经过多个语种翻译人员的多次语言间的辗转、重重翻译才能成为目标语言。实际上,“累译”就是“重译”,意思相同。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出使巴蜀所奉的诏书中有:“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10]3044《后汉书·西域传》载:“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7]2910可见,重译是一种当时在边疆治理和外交中的普遍现象。
(二)充当外交使者,转达朝廷文书和敕令
翻译人员自古天然地与外交事务相联系。西汉晚期的著名儒家学者周堪在中央王朝担任过译官令,而汉哀帝的男宠董贤因为太年轻而位居大司马之位,在外交场合的一个小插曲记载了译人的故事:“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4]3737王莽篡汉期间有两则小故事中有译人的身影,其一是:“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赍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译前,欲解取故印绂,单于举掖授之。……请使者坐穹庐,单于欲前为寿。五威将曰:‘故印绂当以时上。’单于曰:‘诺。’复举掖授译。”[4]3820-3821;其二是:“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4]3823以上两则故事里的“译”,应当是跟随使团出使的“译官”或者其下属的译人。
在悬泉汉简中也初步发现了一些译官、译人接待西域邦国的记载:
一三六 以食守属孟敞送自来鄯善王副使者卢匿等,再食,西。(I0116②:15)[11]103
一四三 鸿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属田忠送自来鄯善王副使姑彘,山王副使乌不腞,奉献诣行在所,为驾一乘传。敦煌长史充国行太守事、丞晏谓敦煌,为驾,当舍传舍、郡邸,如律令。六月辛酉。(II0214②:78)[11]108
一四四 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献骆驼六匹,阳赐记。(A)
十九日薄(簿)至今不移,解何?(B)(I0309③:20)[11]109
一九二 出粟六升,以食守属高博送自来乌孙小昆弥使,再食,来。(I0110②:33)[11]136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译官、译人连通了西域等地丝绸之路上的关防要塞及其导译,发挥了重要功能。
(三)充当涉外经济文化官员
丝绸之路上的翻译人员,虽然最初主要是为政治、军事和外交服务,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别于此。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以合浦港[注]汉时隶属于交阯合浦郡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设钦廉行政专员公署,1951年改隶属广西,1955年复隶广东省,1965年再隶广西钦州地区行政专员公署,现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管辖。等为中心港口开展官方海外交往,《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4]1671“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记载”[15],文献中涉及“译长”和“译使”,后者实际上指的就是前者——译长等人,他们有翻译官和使节的双重身份。在和平稳定时期,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是主要的。汉唐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经营者,从唐代相关文献的记载也可以看出译长等翻译人员在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新唐书》中有:“译长纵蛮夷与民贸易,在所令邀饮食,相娱乐。”[16]据此,我们可以大致知道,译长在古代不仅是负责主持传译与迎奉使节的职官,有时候也充当出使外国的使节,在很多时候他们还承担着促进撮合通商贸易的事务,这种情况一直到唐代都还存在。
丝绸之路以丝绸的国际贸易命名。“贸易的主要产品是丝绸。除了用来讨好游牧部落以外,丝绸在古代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汉朝,丝绸与钱币、粮食一样可以用作支付军饷,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作为一种国际货币。”[17]10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从两个方向打通了东西方的国际贸易,因此也有海外学者认为早在两千多年之前中国与西方就已经开始了“全球化”的历程,而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的起点城市和外国使团出使的终点城市——长安(今西安),在很早就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所有这些复杂的行政措施都为我们展示出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是如何面对一个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我们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进步。”[17]10这个历史的评价很高,认识也很独特。
丝绸之路在文化方面的作用,无外乎是“走出去”和“带回来”。丝绸、陶瓷、工艺品等随着车马和海船运往东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将中国的科技文化传播到世界;反之,丝绸之路也带回许多外国的货物、科技和文化。“2003年夏,在乌兹别克科学院瑞德维拉扎院士家的花园里,瑞德维拉扎教授充满深情地谈到广东遂溪发现的南朝银碗,上面的粟特铭文表明银碗出产于石国(Chach),而石国就是这个花园所在的城市塔什干。从这个银碗可以看到粟特人航海经过印度洋抵达南中国海的轨迹。”[18]而且,“走过丝绸之路的,不仅有载着东西方货品的商队,宗教、文化和思想也在这条路上传播”[17]5。这些也充分说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和东西方许多国家的交往是世界性的,是非常成功的,而在其中翻译人员功不可没,历史应该永远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