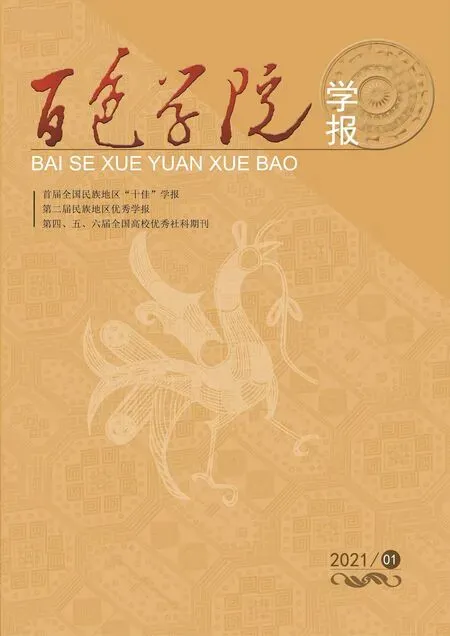民族团结视域下民族类媒体的特性、作用与发展
王首敬,于宏伟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引 言
“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1]媒体作为一种宣传介质,掌握着传播权,“媒体说什么,人们就信什么”,媒体的力量不容小觑。民族类媒体作为以少数民族为主要传播对象的载体,以其传播对象精准化、传播内容深度化和传播方式亲近化的特点,对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影响更是深入骨髓,成为推进民族团结事业不容忽视的重要载体,因此在推进民族团结事业背景下探讨民族类媒体的运行机制和改革策略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就民族团结视域下民族类媒体的特性和作用进行审视,并提出民族类媒体在推进民族团结事业中的发展策略,以期为民族类媒体改革指明一个方向。
二、民族团结视域下民族类媒体的特性
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兴起于20 世纪初叶,但其发展与繁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形成了较为系统、多语(文)种、多层次、多渠道的特色鲜明的新闻传播体系。[2]从纵向上看,民族类媒体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变迁。日前,民族类媒体形式多样,既包括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也包括新媒体,如移动媒体、社交媒介(微信、微博)、影音媒介(短视频、VR、直播)、智能内容分发平台(今日头条),正在建设成全媒体格局。从横向上看,民族类媒体始终置于国家场域之中,在不同时期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权力规训之下,民族类媒体在信息传播与推进民族团结事业中呈现出自身的特性。
(一)专属性
民族类媒体的专属性指某一特定的民族类媒体服务于某一特定民族的特性。每一类媒体都有自身的服务对象,民族类媒体是服务于某一或多个特定少数民族的,这是民族类媒体划分信息符号上“他者”与“我者”边界的基本维度。它的专属性使其传播对象更加精准化,传播内容更加深度化,传播方式更加亲近化,成为少数民族群体认识自身和了解世界的窗口,少数民族群众在民族类媒体建构的场域中凝聚集体意识。专属性的另一面则是易将其他民族人群排除在文化体系之外,语言文字表现得尤为突出,既不利于民族类媒体经济收入的增加,也不利于民族文化更深一步交流,使得其在推进民族团结事业方面略显掣肘。巴尔特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编码者和译码者属于同一文化群体,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互相影响的意识基础。[3]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因此在解码、译码过程中,容易产生文化隔阂,甚至文化碰撞与冲突。
(二)地方性
民族类媒体的地方性一方面指其是服务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另一方面指其在传递信息时地方性知识的运用。大众传媒时代,民族类媒体往往有严格的区域划分,如省、市、县级电视台等,其传递的内容多是特定区域框架内的信息。新媒体时代,依据区域划分而设定的媒体如双V 号等依然存在,抖音、快手等个人化媒体兴起,突破了空间界限,但传播内容上依然体现着地方性,即地方性知识的运用。地方性知识的运用普遍存在于每一媒体中,媒体传递的信息有时是建立在人的主观意识之上、经过加工、与当地文化交融后的信息。一方面,格尔茨认为任何一种地方性知识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和优势,也许一种文化很难被外文化的人所了解和接受,但它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含义。[4]地方性知识在媒体中的自由、适当使用,体现了我国充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实现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的存在使民族类媒体无意识之中给自己披上了文化的“外衣”,导致外来人群难以介入,无法上升为“普适性知识”,也就把自己“边缘化”了。人们在阅读信息时被地方性知识所笼罩,有时难以与普适性知识产生共鸣。
(三)敏感性
民族类媒体的敏感性主要体现在传播内容上,一是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一是民族文化的禁忌性。在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上,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 个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亲如一家,正如家庭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冲突与矛盾,民族之间有时也会出现冲突和矛盾。同时,也有西方力量教唆下产生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民族类媒体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在民族文化的禁忌性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存有一定的禁忌,禁忌性在本质上是防卫性的,是一种自我保护和保全[5],是不容触碰的。媒体在传播少数民族的文化时,始终保持着一种敏感性,充分尊重和保护着少数民族的禁忌文化,避免民族矛盾的产生和激化。
(四)内向性
民族类媒体的内向性是由权力建构的。艾森克个性问卷将内向描述为:安静,离群,内省,喜欢独处而不喜欢接触人;保守,与人保持一定距离(除非挚友);很少进攻行为,多少有些悲观等等。[6]首先,表现在害怕见“大人”。纵观民族类媒体,基于国家权力格局的影响,在面对国家媒体时,往往会将话语权让渡给国家媒体。其次,表现在喜欢独处、与人保持一定距离。民族类媒体常将自身置于边缘地位,认为自身文化体系具有特性,其他文化体系难以融入,甚至有时会处于不自信状态,因此往往缺乏与其他类媒体的交流、交汇和交融。最后,表现在安静,内省。从整体上看,民族类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始终保持与主流价值观的一致性,向少数民族群体传递科学、文化、经济、政治、宗教等信息,积极响应国家对民族团结的号召。但内向性的形成也导致民族类媒体传播向度出现一定程度的单向性。
三、民族类媒体在民族团结事业中的推进作用
民族类媒体作为以少数民族为主要传播对象的媒体,塑造了一个特定的、属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场域,少数民族群体在这一场域中寻找着自身形象,强化着族群认同。民族类媒体是推进民族团结事业的一把利剑,其主要作用如下。
(一)传播主流价值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媒体的最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上传下达”,将主流价值观传递给大众是媒体的职责所在,正如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所说,“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的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7]。基于民族团结主题,民族类媒体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体现在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五个认同”为维度,加上“两个共同”,形成“三个离不开”格局,实现“五个维护”的民族团结体系宣传上,通过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建设各族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从而实现民族团结。推进民族团结事业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正是主流价值观赋予民族团结以内涵,没有民族类媒体的宣传引导,主流价值观就无法传播,民族团结就无从谈起。
(二)塑造民族媒介形象,增强文化自觉
民族类媒体主要面向少数民族传播,以少数民族信息为传播内容,所塑造的民族形象多为正面形象,往往会将事实美好化。媒体“再现”属于“符号真实”的主观范畴,传播者基于自身立场,借助媒介符号为工具来表征真实;而受众则依据媒介图景和社会情景建构所谓的“真实图景”。[8]因此,民族类媒体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媒介形象塑造,使得少数民族人群对于自身文化有了正确全面的认知,渐渐突破刻板印象和污名化的束缚,而通过媒介形象的“镜子式反映”,人们会自觉纠正与“镜子”形象不符的方面。在对自身形象的正面认知和自身形象的不断完善过程之中,人们建立着文化自信,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实现与主流文化群体的交往互动。
(三)构建集体记忆,坚定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王明珂指出,人是通过结构性失忆和集体记忆来诠释群体的本质及维系群体的凝聚的[9],人们通过集体记忆形成民族和国家认同。在民族类媒体未走入少数民族社会之前,国家对其而言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概念,彼时的认同多是基于地理的族群认同,对于国家的认同较为模糊。民族类媒体逐渐走入少数民族日常生活,通过特定的框架创造出国家共同体的情感,以此建构国家的想象,唤起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在实践中,民族类媒体一是通过宣传56 个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一员来建构身份认同;二是通过隐喻、象征和转喻等手法,选取象征性符号再现集体记忆;三是将关于国家和政府的新闻、仪式庆典和重要事件等传媒话语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潜移默化地引起少数民族对国家事务的关注和讨论,进而将民族认同引入到国家认同,尤其是个人化媒体的出现,激发新的群体参与。民族类媒体通过建构集体记忆,将“国家”从一个抽象概念具体化和形象化,促使人民群众进一步坚定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四、新时代民族类媒体推进民族团结事业的策略
新时代,民族类媒体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要充分发挥民族类媒体的功用,规避传播中的各类问题,积极宣传民族团结思想,推进民族类媒体改革,最终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类媒体,形成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核心、以民族团结为指向的传播体系。
(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事业的基本目标,也是推进民族团结事业的路径方向。民族类媒体要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领,不断推动民族团结事业进入新时代。
(1)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史,各民族先民共同开拓了我国辽阔疆域,在中原地区治理与边疆区域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类媒体应当深入发掘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的历史,歌颂各民族对古代疆域治理与近代主权维护的贡献。
(2)一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即是一部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史,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民族类媒体应当积极宣扬各民族共同书写国家历史,增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同。
(3)中华民族世居东亚之滨、以农业立国,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借鉴,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民族类媒体应当大力传播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增强人民群众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自信。
(4)草原文明的奔放、农耕文明的含蓄、山地文明的开拓、海洋文明的包容,共同促进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民族类媒体应当不断弘扬各民族共同培育民族精神,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
(二)以推动族际交流与互动为窗口
族际交流与互动是推进民族团结事业的重要途径,更是民族团结事业的重大内容。同地域的人们享有共同的自然资源,拥有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共同的人文性格。同民族的人们有着同一个族源,有着相似的风俗习惯,有着共同的民族节日,超越了地域界限的民族共同创造并享用着民族文化。不同的地域在发展进步历程中进行着资源共享、文明互鉴,不同的民族在发展进步历程中进行着文化共享。民族类媒体应着力在内容上下功夫,既向少数民族群众传递本地域、本民族的信息,也传递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信息,还要传递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交往政策等。此外,还应当策划和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使人民群众真实地参与到民族团结事业建设中来。民族类媒体首先应当宣传同区域同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内部团结;其次,应当宣传同区域不同民族交流,促进地区团结;再次,应当宣传不同区域同一民族交流,促进更大范围、更大意义上的民族内部团结;最后,应当宣传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交流,促进国家意义层面的中华民族团结。
(三)以媒体融合与建设县级媒体为渠道
互联网的发展使社会进入技术和关系赋权时代,公共权力渐渐让渡给个人,权力格局的变化导致民族类媒体格局的变化。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中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10]因此,民族类媒体应当以媒体融合与建设县级媒体为渠道,使民族团结事业以多渠道、多形式的方式深入到人民群众中。
在媒体融合方面,首先要加强媒体技术融合,使传播的信息具有图文、视频、AR 等多种形式,避免单一化、枯燥化。其次,针对不同的APP 用户群体,做到媒体类型融合,将微信、微博、抖音、快手、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多种媒体类型有机融合,多个渠道共同发力。再次,促进不同类型不同级别媒体融合,增强中央与地方媒体、上级与下级媒体融合。
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宣传思想工作新形势新要求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是加强改进基层宣传思想工作、推动县级媒体转型升级的战略工程。[11]统览日前县级媒体发展现状,存在形式单一、新闻质量低、滞后性强、媒体人素养差等问题,亟须整治。当下,应当加强县级媒体建设,其最重要的是提高媒体人素养,防范“假新闻”,注重内容形式的多样性,重视新闻的时效性和实现实时化传播,培养一批具有民族学素养的媒体人。
五、结语
民族类媒体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媒体,具有专属性、地方性、敏感性和内向性的特性,在传媒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民族类媒体像人体的血管,作为传输载体,将民族团结的血液输送到人们的身体之内。它通过传播主流价值观,建设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塑造民族媒介形象,建立着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民族类媒体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领,以推动族际交流与互动为窗口,以媒体融合与建设县级媒体为渠道,推动民族类媒体不断在改革中推进民族团结事业持续发展。媒体,归根到底是基于人的传播,推动民族类媒体改革,推进民族团结事业,最重要的是培养一批高素养、专业化的媒体人,一批具有民族学素养的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