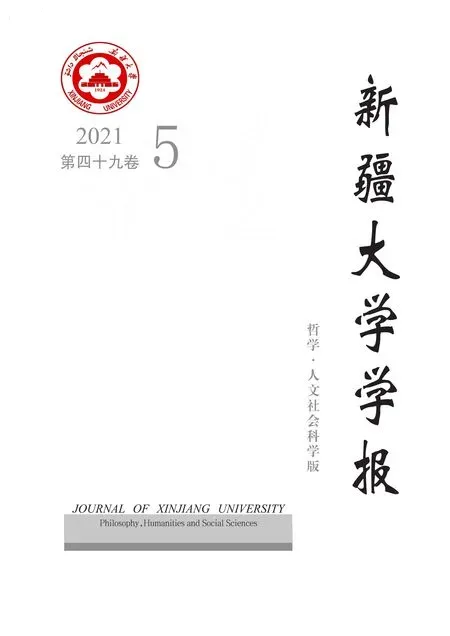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哲学解读*
——从分析哲学的视角
韩 健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230039)
一、引 言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结构主义的鼻祖。他所提出的语言学说,是语言学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多年来,国内外从各个角度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①参见胡剑波《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综述》,《外语与翻译》,2018年第4期,第45-52页。Beaugrande认为,语言学理论发展呈现出跳跃前辈(ancestor hopping)现象,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学思想反映出心灵哲学的倾向。②参见伯格兰德《语言学理论:对基要原著的语篇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第F24页。Tantiwatana的硕士学位论文从索绪尔的“差别”概念出发,认为“差别”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并指出其语言哲学的思想意义。③See Aphinant Tantiwatana.On Ferdinand de Saussure's Philosophy of Language:An Investigation of Difference.Bangkok:Assumption University,2005,pp.32-114.王寅最早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定位于分析哲学④参见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页;王寅在其文章中将分析哲学等同于语言哲学,涂纪亮则认为:“分析哲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精神哲学、价值哲学等等。”本文采用涂纪亮关于分析哲学的宽泛说法。参见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9页。,在其后的《再论索绪尔与语言哲学》一文中重申了这一点:“索氏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也是一位重要的语哲学家。”[1]江怡也指出:“我们通常把索绪尔看作一位语言学家,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把他看做一位哲学家。”[2]正如陈嘉映在评价索绪尔语言学成就时所说的那样:“一门新兴人文科学总是带着相当深入的哲学思考才能成形的。”[3]71本文拟以《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分析哲学的视角解读索绪尔对语言和语言本质的哲学思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索绪尔语言理论思想和分析哲学家们有诸多的共鸣和明显的渊源关系。
我们知道,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脱离了经学的附庸,走出了语文学时代,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是这种研究方式是“历史主义的复古主义”,即使是后期取得相当成就的青年语法学派,也被人们批判为“原子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状况的变革是在索绪尔手中完成的,从索绪尔开始,语言学步入了现代。对索绪尔语言理论思想的解读,首先要提及的是和他同时代的两位思想家,即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们都注重人类行为的研究,并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他们认为“如果忽视了行为和物体在社会中所具有的意义,就等于仅仅在研究物理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4]。我们就从这里展开论述。
二、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
上面我们说到,索绪尔、涂尔干和弗洛伊德都注重人类行为的研究。在《教程》中,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材料首先是由人类言语活动的一切表现构成的”[5]26。即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人类的言语行为,“这种行为至少要有两个人参加:这是使循环完整的最低限度的人数”[5]32。在这个循环中,涉及到心理现象、生理过程和物理过程,同时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索绪尔的目的就是将“社会的”和“个人的”从言语行为中划分开来,因此他说到,“语言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5]30。言语则不是社会集团的,它是个人进行的,“相反,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行为”[5]35。由此,索绪尔把言语活动(langage)中“社会的”和“个人的”,即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区分开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5]41而“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5]42。
索绪尔认为,“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5]36。他的这种划分是同质化运动过程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这也是全书最后结论逻辑推导的根据,即“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5]323。接着索绪尔又从语言中排除外部语言要素得到内部语言要素,从内部语言要素中排除历时事实得到共时语言系统。陈保亚指出:“同质化运动使语言研究有了客观的、可实证的基础,使研究者在研究中把眼光放在存在于集体意识的语言规则上,研究者可以达成共识。”[6]
在研究者之间有共同的评价标准,建立起可实证的基础,这点正是许多分析哲学家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分析哲学奠基人弗雷格在其《算术基础》序言中,提出的第一条原则就是:“要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7]8在弗雷格之前,休谟、穆勒等人主张从心理学的观点去考察一切哲学问题,埃德曼、冯特等则进一步将这一观点引入逻辑学中,把逻辑学看做心理学的一部分,把思维活动归结为心理活动,否认思维的客观内容。①参见李云泉《弗雷格意义理论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1页。在弗雷格看来,埃德曼等人把一切归结为主观的、内在的过程,即心理过程的做法取消了真理。所以他在谈论词的意义和与词相联的观念时强调,必须将二者区别开来。因为“词的意义不是个人的思维活动的一部分,而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共同财富”[8]40。但是“观念是主观的,一个人的观念不同于另一个人的观念”[8]40。弗雷格划分出“逻辑的”和“心理的”,目的是为了使真理有一种客观的和不以作出判断的人为转移的东西。而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将“社会的”和“个人的”区分开来,则是为了语言研究有客观的、可实证的基础。在这种追求客观性与主观性相分离,一般性与个别性相分离的思想上,弗雷格和索绪尔的目标是相同的。
这种思想也是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即核心“维也纳小组”成员们所追求的目标,例如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石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关于这两类命题的区分并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首先提出的,莱布尼茨、休谟、康德等都有过类似的论述。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分析命题是必然的、普遍的,它们的真理性仅仅来自这种命题中所包含的词或符号的定义。”[8]168-169但是“综合命题是陈述事实的命题,不是必然的、普遍的,它们真实与否必须求助于经验的证实”[8]169。逻辑实证主义者对这两类命题的区别,正如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它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是共同的;言语则没有任何集体的东西,它是个人的和暂时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分析命题是只要借助形式逻辑的判断,而不需要求助于经验的证明;相反,综合命题的真实与否必须求助于经验的证实。②参见涂纪亮《评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哲学研究》,1984年第6期,第24页。石里克以这种区分作为批驳“形而上学”的依据,认为可证实性就是证实的可能性,并将这种可能性分为“经验的”和“逻辑的”。石里克认为可证实性是证实的逻辑可能性,而经验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③参见王小滨《石里克哲学思想研究》,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8页。石里克的这种区分,包括后来的艾耶尔提出的实践的可证实性和原则的可证实性,以及卡尔纳普提出的“可验证性原则”,基本都是这两类命题的继续和延伸。
不管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区分两类命题,用以探求命题的意义,还是索绪尔将言语活动区分为语言和言语的同质化运动,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在研究者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客观的、有共同评价标准的可实证基础。这种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都排除了“语义”等的异质因素。在语言学方面,它缩小了语言的研究范围,导致了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家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弊端。如后来的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派的布龙菲尔德所说:“语言研究必须从语音形式开始,而不是从意义开始。”[9]一直到乔姆斯基前期的语言研究,都是排斥语义的,即所谓的“句法自治”(autonomy of syntax)。同样,在分析哲学方面,哲学家们也意识到绝对的可实证性是做不到的。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们认识到语言的逻辑分析不能只限于句法,还需要语义分析。如后来的蒯因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批驳了两类命题的区分以及证实理论和还原论,最终导致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当然绝对的可实证性是做不到的,但是一般的实证标准和可检验标准是需要的,否则研究者没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标准,是很难达成共识的。
三、符号:所指与能指
索绪尔在将“语言”从“言语活动”中分离开来,并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5]37同时他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5]38。索绪尔称这门科学为符号学,并且他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索绪尔在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后,进一步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5]101并用所指(signifie)指代概念,用能指(signifiant)指代音响形象,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叫做符号。索绪尔认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实体,这点也是常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如科利批判他取消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他用语言学范围内能指者对所指者的二元关系,取代了‘能指者-所指者-事物’的三元关系。”[10]354并且科利引用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的话指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促使语言哲学家检讨那种语言代表现实的主张的缘由了。”[10]354但是索绪尔明确指出:“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5]157“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5]157索绪尔反对语词和现实世界对应关系,反对“有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5]100。即“语言只是使得现实在语言的水平上得到充分理解”[3]85。
“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索绪尔的这种思想颇有拉康“语言之外无结构”和康德“理性为自然立法”的味道。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实体,用二元关系取代了三元关系,反对语词和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在这一点上,它涉及的是分析哲学甚至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一点,它在理论上区别了人和动物根本性的不同。在《礼记·曲礼》中有这么一句话,“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11]。鹦鹉学舌发出的声音再怎么像人类的语音,它也只能停留在能指层面,而没有所指的概念层面,更不会随着外界情况的不同而随时改变自己的话语。至于猩猩,相比其他动物不管多么聪明,也只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而不能用类似人类复杂的有声语言进行交流。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也只有人类才是符号性动物,所以说语言是其他动物和人类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说到底是因为动物没有“能指-所指”这样的符号内部关系。
另外一点,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思潮,或是一个流派,其内部观点非常庞杂。但是分析哲学家普遍重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注重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把对语言或语词意义的分析当作哲学的首要任务。他们认为,我们理解或叙述客观世界是在语言层面上进行的。这正是西方20世纪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所谓“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哲学的对象从纯粹主体转向主体与客体的中间环节——语言”[12]。语言被看作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桥梁,主体不可能直接认识客体,只有通过语言符号这个工具才能认识客体。这就是为什么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链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如果语言符号连接的是事物和名称,则混淆了客体和认识客体的工具及路径。
在分析哲学家那里,索绪尔语言符号连接概念和音响形象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意义和指称、专名和概念的讨论中。弗雷格认为意义和指称是不同的,他用“暮星”和“晨星”的例子来说明“与某个指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意义,与特定的意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指称,而与一个特定的指称相对应的可能不只是只有一个指号”[13]。如果用索绪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符号的所指在语言中是固定的,所指对应的客观世界中的事物是固定的,但是客观世界的事物不一定使用相同的符号来表达。莫里斯继承和发展了弗雷格的这一观点,进一步提出“所指谓”(designatum)和“所指示”(denotatum)这对概念,前者指对象的性质,后者则是指对象本身或其存在。后来的逻辑实用主义者蒯因在意义问题上,也继承了弗雷格把名称、指称和意义区别开来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把意义和指称混为一谈,就会把意义这个概念看作一种实体。①参见李国浩《蒯因本体论思想研究》,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7页。这一点正是索绪尔特别强调的:“语言符号所包含的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而且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我们的脑子里。”[5]100这里的两项要素即能指和所指,它们都是心理实体,并不直接指向客观实体。虽然索绪尔没有用名称和意义,而用了符号和所指。
关于指称论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直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前期思想,许多哲学家都将意义与指称混为一谈,他们坚持认为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示或所指称的对象。罗素就认为,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他指出,名称只不过是个简单的符号,它直接指称作为其意义的个体。②参见苟志效《意义与指称》,《学术研究》,2000年第5期,第45页。维特根斯坦也认为孤立的名称本身没有意义,它只能指称个别对象。弗雷格发现了这一错误,率先区分了指称和意义的不同。索绪尔也明确表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其实,语言符号的指称过程,才是它突破自身的界限指向外部事物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对语言本质思考的深邃之处。
四、语言的价值
索绪尔将言语活动划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又将能指和所指从符号中区别开来,并且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5]37在后面的论述中,索绪尔从价值论的角度进一步提出“语言只能是一个纯粹价值的系统”[5]157。这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运行,索绪尔认为只要考虑两个要素就够了,即所指(概念)和能指(音响形象)。关于所指,他强调“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的观念的词都是互相限制着的”[5]161-162。所指是“由于他们的对立才各有自己的价值”[5]162。对于能指,索绪尔指出:“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它本身不可能属于语言。”[5]165和所指一样,能指的价值“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5]165。就符号整体来看,索绪尔认为“使一个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一切,就构成该符号。差别造成特征,正如造成价值和单位一样”[5]168。所以索绪尔最后总结说,“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5]170。而且他还认为“一个要素的价值可以只因为另一个相邻的要素发生了变化而改变”[5]167。并且拿下棋的比喻来说明价值,索绪尔说一枚卒子本身不是下棋的要素,“离开了它在棋盘上的位置和其他下棋的条件,它对下棋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5]15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的语言的价值理论虽然重视实体和单位,但更注重他们之间的对立、差别的这种关系,而这些都是构成价值的要素,所以说“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5]169。
从上面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虽然注重实体或单位,但要理解它们的价值,首先要理解实体或单位之间的对立和差别的关系。索绪尔的这种思想与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哲学思想颇为相像。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思想,强调“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14]22。在这里,“世界”是指一切所发生的情况,“事实”是指实际存在的事态,而“事态”指的是事物的状态。维特根斯坦重视对象的状态或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象本身。他说:“我们也不能在与其他客体联系的可能性之外来思考任何客体。”[14]23同时他又说“如果我能够在原子事实的前后关系(Verband)中来思考对象,则我不能在这种前后关系的可能性之外来思考这个对象”[14]23。维特根斯坦重视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与索绪尔语言价值理论中的思想如出一辙。索绪尔由“关系”建立起来的语言价值理论的最终导向是“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维特根斯坦的这种逻辑原子论借助于他的“图像说”,最终也倒向了形式主义理论。
维特根斯坦重视关系的思想,同时也影响了他的老师罗素。罗素逻辑原子论的提出和他的外在关系说是密切相关的,而外在关系说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反对布拉德雷的内在关系说。布拉德雷等人认为,任何一个表示关系的事实,其实都是一个关于所涉及的词的性质的事实。他们否认关系具有任何终极的、独立的意义,认为只存在着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而这个实体就是意识的统一性。①参见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3页。其实这也正是布拉德雷、鲍桑葵等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即绝对精神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布拉德雷否认关系的独立意义,这和索绪尔承认在语言状态中一切以关系为基础的思想是相悖的。而罗素的外在关系说认为,关系具有一种不以它的关系项为转移的实在性,关系并没有进入关系项的定义中,这种关系具有它的终极性和实在性。这和索绪尔提出的声音本身不可能属于语言,音响形象彼此之间的差别才属于语言的思想是一致的。
另外一点我们需要指出的是,索绪尔在论述语言价值时用了下棋的比喻。他认为棋子本身的材质无关紧要,棋子的意义在于它在棋盘上的位置和其他下棋的条件。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强调:“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7]9换句话说就是,语词意谓研究要以语句为背景的。弗雷格研究语词的这种方法是一种语境定义法。索绪尔把语言符号比作棋子,认为棋子的意义要以棋盘为背景,即符号价值的确定要以其他语言符号为背景,这种思想其实也是一种语境定义法。只是弗雷格后来否定了这种方法,在之后的《算术的基本规律》中,他主张采用完全定义,即每一个谓词、关系词或函项词都应该可以用来给每个对象下定义。②See Gottlob Frege.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Vol.Ⅰ).Jena:H.Pohle.,1893,pp.26-46.但是弗雷格的语境思想却被日常语言学派继承了,他们强调语词指称的语境问题,强调语句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有是否正确的问题。在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下,后来的塞尔也强调意义与语境的密切关系。
索绪尔的语言价值论强调实体或单位之间对立和差别的关系,是这种关系决定了要素自身的性质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强调客观世界物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56。在和恩格斯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意识是社会的产物时又强调,“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5]81。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的是由它在它隶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16]。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人及物体的意义不是从它们本身出发的,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的价值也不是从它们本身出发的,都在于被定义的对象和其他对象所处的关系中,关系决定了对象的本质和意义。
五、语言的系统性,“划界”
索绪尔在谈论语言的价值时指出:“语言只能是一个纯粹价值的系统。”[5]157如上所述,语言的价值决定于实体或单位之间对立和差别的关系,“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5]170。这些语言要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是以语言的系统性为背景的。索绪尔在多处提到系统性问题,如在谈到音位时,索绪尔认为:“我们都要为所研究的语言整理出一个音位系统……这个系统才是语言学家唯一关心的现实。”[5]62在谈到文字时,他又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5]47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的本质就是由各种不同性质的符号这样的一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种要素以句段关系(rapports syntagmatiques)和联想关系(rapports associatio)结成一定的结构,使其运转起来。
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分析语言的这种思想,正是一种系统论的方法。经典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处于相互作用中的诸要素的复合体”[17]。索绪尔也认为,语言的系统性是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诸要素之间的这种关系体现的。经典系统论强调对“整体”和“整体性”的科学探索,索绪尔语言的系统性思想不仅强调“整体”,还注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问题。例如在论述句段的连带关系时,索绪尔强调:“整体的价值决定于它的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所以部分和整体的句段关系跟部分和部分间的关系一样重要。”[5]178这点恰恰是现代系统论和经典系统论不同的地方。现代系统论认为,结构和功能是系统普遍存在的两种基本属性,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结构指的是“系统内部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18]288。而功能则是指“系统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时空形式的外在表现形式”[18]290。索绪尔在论述语言的历时态(diachronie)时指出:“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5]127在历时态里,要素之间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它并不涉及要素之间的表现形式,即联系方式和组织秩序以及时空关系。这种替代关系没有牵动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属性,因此索绪尔认为历时语言学(linguistique diachronique)“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5]143。所以只有共时态(synchronie)的要素才可以构成一个系统,共时态中要素间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就是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但这并不是说历时态中要素的变化就不重要了,它是共时态中一个系统产生另一个系统的必备条件。索绪尔在论述语言的本质时,不仅提出了符号学的思想,还自觉地运用了系统论的方法,半个多世纪后的1968年,贝塔朗菲才提出系统论的科学哲学思想。
另外,从语言学史上看,20世纪早期的语言学家大多是在19世纪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索绪尔深受青年语法学派雷斯琴、勃鲁格曼等人的影响,如他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被誉为“前无古人的历史语言学最出色的篇章”[19]。而19世纪是一个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特别是印欧语言的世纪。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严重缺陷是,纯历史主义的复古主义。它的研究方向不是自古及今的发展前进的方向,而是由今及古的逆发展方向”[20]157。即使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后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青年语法学派,也被批判为“原子主义”的研究方法,“看不到语言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他们总是把语言现象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不相关联的部分”[21]。然而在《教程》一书中,索绪尔注重共时语言学的研究,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并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论述语言的符号性。所以,索绪尔在书中说到:“语言学在给历史许下了过大的地位之后,将回过头来转向传统的静态观点。但是这一次却是带着新的精神和新的方法回来的。”[5]121罗宾斯认为索绪尔开创了20世纪的语言学,他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并指出:“人们把《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比作语言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2]
纵观索绪尔整个语言理论,他所做的工作如果总结为一点,那就是“划界”。索绪尔在回顾语言学史时,首先将语言学和语文学划分开来。在语言分析过程中,多次使用“二元对立偶分”的划界方法。如对内部语言学(linguistique interne)和外部语言学(linguistique externe)的划界,对语言和言语的划界,对共时语言学(linguistique synchronique)和历时语言学的划界,对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的划界,对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划界等等。“划界”问题正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前期思想所做的工作,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中,第七个命题只一句话,即“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14]97。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所以在他看来,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把“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划分开来。“可说的”在前六个命题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不可说的”是不能用命题或语句言说的,第七个命题表示的是不能言说的,因而我们应当保持沉默。所以在该书的序言中,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已解决了全部哲学问题,“在这里所阐述的真理,在我看来是不可反驳的,并且是确定的。因此我认为问题基本上已经最后解决了”[14]21。不仅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全部哲学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要做的首要工作都是“划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3]他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看做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的唯一标准。不管是一种哲学思想,或是一门新的学科,还是一种新的理论,划分清楚概念体系之间的界限,使其思想理论明确清晰是基本的任务。索绪尔的划界工作,正是为了“摸索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5]21。从而“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5]21。
六、结 语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思想是宏大的、丰富的,包含着多方面深邃的哲学思考。正因为如此,他的语言学思想不但成为语言学的经典理论,也对其他学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便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结构主义思潮。社会学、人类学、文艺学、哲学、心理学都相继产生了自己的结构主义学派,一时间结构主义的大潮吞没了整个学术领域”[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