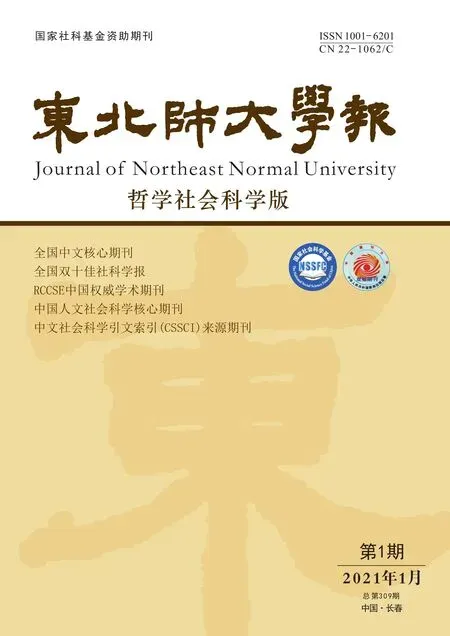中国文学表达方式之流转与写人传统之形成
李 桂 奎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文学文本采取何种表达方式,往往适配于某种文类或文体,是为“得体”,否则便容易“失体”。金人刘祁《归田志》卷十二《辩亡》曾强调:“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1]文学表达所采取的“言语”,取决于相对稳定的表达方式,即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就大致呈现出什么样的“言语”。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表达方式的真正确定是从提出“赋比兴”诗法开始的,而后逐渐流转为“抒叙议”(抒情、叙述、议论)文法。在此前前后后,又有源自绘画的“描写”笔法加入,从而逐渐形成现代众所周知的叙述、抒情、议论、描写等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学艺术传统中,人们往往根据文学体性规范确定各种表达方式的功能和用场。大致说,叙述主要用于史传、古文、小说等文类;抒情主要用于诗、词、曲、赋等文类;描写通用于书画、诗文、戏曲、小说中;议论除了直接服务于说理文,还被用于史传、小说等其他文体的论赞。当然,叙述、抒情、描写、议论四种表达方式与叙事、抒情、写人、说理四种文本创构形态只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呼应,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就中国文学传统来看,主要依托于描写的写人既经常自身以静态的“图景”形式显现,又时常在叙事的施助下以“场景”形式展现在各种动感叙述文本中。在中国传统文论谱系中,写人理论足可自成一支。它和抒情理论、叙事理论分则独立为三,合则一体。
一、从“赋比兴”诗法流转为“抒叙议”文法
在中国文论史上,“赋比兴”诗法是最早被命名的表达方式。尽管这三法后来也被人们用以评说其他文类,但由于它们主要用于诗赋,故而还是多被运用于品评诗赋。待唐宋古文、明清小说等文类全面兴起后,“赋比兴”诗法术语便被意蕴更丰富的“叙抒议”(“叙事”“抒情”“议论”)等文法术语所遮蔽,甚至在某些场域被取代。相对而言,后三者不仅被广泛地用于评述史传、古文、小说等各体文学的行文之道,而且也时常被用来评说诗词曲赋的写作技艺,用场更为广泛。
关于“赋比兴”与“叙抒议”两套表达方法术语之关系,董乃斌先生在其《从赋比兴到叙抒议——考察诗歌叙事传统的一个角度》一文中,曾从清人黄生那里找到突破口,进行过一番较为系统的梳理。黄生那番话是在指导后学诗歌创作时讲的:“诗有写景,有叙事,有述意三者,即三百篇之所谓赋、比、兴也。事与意只赋之一字尽之,景则兼兴、比、赋而有之。大较汉魏诗赋体多,唐人诗比、兴多。六朝未尝无赋、比、兴,然非三百篇之所谓赋、比、兴也。宋人未尝无赋、比、兴,然只可谓宋人之赋、比、兴也。”[2]这里,黄生不仅将诗歌文本构成要素概括为景、事、意,而且与赋、比、兴三种原初性的诗歌表达方式进行了对接与匹配,并大致描述了赋、比、兴在历代诗歌中延展变化的情形。经过具体梳理分析,董先生进行了如下总结:“赋比兴与叙抒议这两种对诗歌表现手法的概括,可以比较但不可简单对应,需在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中仔细判定,才能得出切实可信的结论。”“赋既可以是叙事,但又不只等于叙事,它还可以是抒情乃至述意。凡诗中‘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无论所陈之事是客观的事物,还是主观的心事,都应属于‘赋’体范畴。而比兴也并不就等于抒情,更多的情况下其实倒是描叙或述事,只是其描叙之事往往除诗面所写外还另有寓意而已。”[3]指出“赋比兴”与“叙抒议”两套术语之间存在一种平行互补、彼此交叉关系,可以比较互释,但不能搞简单的一一对应。既然如此,两套术语就有分别存在的理由,不妨适当地划界而论:采取“赋比兴”术语体系评赏诗歌更有效,而采用“叙抒议”术语体系评价古文、小说则会更到位。至于而今如何将二者互相融合,共同纳入现代文论谱系,则另当别论。
从“赋比兴”流转为“叙抒议”,应该发生于“事”及其孪生兄弟“物”充当了“赋比兴”阐释的关键要素之时。我们知道,“赋比兴”之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与“风雅颂”一同被称为“六诗”,指的是先秦人根据《诗经》文本创构而归纳出来的三种表达方式。后经魏晋六朝挚虞、钟嵘、刘勰等文论名家阐发,至宋代朱熹《诗集传》获得了一个较为完美的定义和解释。在历代关于“赋比兴”的诠释过程中,各家乐于以“事”或“物”作为“赋比兴”诠释的思考工具(1)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曰:“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钟嵘《诗品·序》曰:“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曰:“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二十三曰:“赋者,直陈其事。”尤其是朱熹《诗集传》所言:“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几句经常被人征用的解释,也把“事”或“物”视为“赋比兴”得以成立的关键。对“叙”观念建构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宋代李仲蒙,胡寅《斐然集·致李叔易书》曾引其语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如此说来,“赋、比、兴”表达程序是依托于“叙物”“索物”“触物”,而“叙物”“索物”“触物”的目的又是“言情”“托情”“起情”。他的意思是,赋比兴依托于“物”而得以有效运行。。总之,传统文论中“事”要素的频频出现为“叙事”观念的确立做了较好的铺垫。
当然,文学文本创构实践通常总是早于理论概括。在“叙事”观念形成之前,叙事行为已在汉唐以前的诗歌文本创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指出的汉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就是明证。哀乐之情的抒发基于“缘事”,合乎而今人们常说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与西方叙事学所谓的因果顺序相通。乐府,无论是古乐府还是新乐府,皆长于“抒情”,也便于“叙事”,以至于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一文中把许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视为诗化的“短篇小说”[4]。其中,古代乐府诗以叙事、抒情合体见长,除了在《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等汉乐府、《西洲曲》《木兰诗》等南北朝乐府中有很好的体现,还在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诗中有所体现。如汉代有首《艳歌行》写道:“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主人贤,览取为吾纟旦。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该诗通过叙述兄弟二三人由冬入夏流浪在外,得到一位热心的女主人照料,因为贤良的女主人为他们缝补旧衣、添制新衣,所以女主人的夫婿从外地回来便怀疑自己妻子有越轨行为。这时,几个流浪的兄弟只能想法自证清白,并感叹如此牵累人家倒不如归回自己家好。叙事有条不紊,抒情、议论也合乎情理,其娴熟的表达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唐代诗歌文本之创构,不仅依托于叙事、抒情的有机交融,而且也继续吸收许多议论参与其中。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长恨歌》等经典名篇自然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杜甫的“三吏三别”等诗歌,更是开启了“叙抒议”交响合奏,由此形成的“诗史”观念,历经宋代“以议论为诗”强化,一直延续到清代。尽管明清时期发生过多次关于“诗史”之说的争论,甚至有人建言以富含抒情意蕴的“心史”说加以置换,但最终并没有撼动叙事在诗歌文本创构中的重要地位。至明末清初,吴伟业在发扬光大白居易“以史为诗”传统基础上,推出了追摹唐代白居易《长恨歌》的《圆圆曲》等诗歌,再次显示了“叙抒议”在诗歌文本中的能量和分量。清代中期,袁枚将诗歌生活化、性灵化,为诗歌的“叙抒议”合奏增添了一种新的模式。
尽管“叙事”“议论”文墨在诗歌创作中屡见不鲜,甚至不可缺少,但在传统诗学观念中它们的地位时常受到质疑,有时还显得比较尴尬。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云:“《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5]人们在讨论以《诗经》为首的诗歌时,还是乐于将抒情视为其本体,并运用“赋比兴”诗法来赞美之,而对叙事并不买账。议论是随着诗体的变异,才逐渐在一定程度上被诗论家所接纳的。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曾明确指出:“叙事议论,绝非诗家所需,以叙事则伤体,议论则费词也。然总贵不烦而至,如《棠棣》不废议论,《公刘》不无叙事。如后人以文体行之,则非也。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过因谗后重,恩合死前酬’,此亦议论之佳者矣。”[6]认为“叙事”“议论”虽然并非诗歌必备,但如果运用得当,也会收获到较好的效果。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也曾指出:“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7]诗歌文本建构主要靠抒情,议论必须带有情韵才能参与文本创构,是有条件或有限的参与。直到现代,周作人还在说:“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8]在诗歌文本创构中,“叙抒议”可以并行,但三者的功能和地位并不相等,抒情为本,叙事、议论只是辅助。可见,以抒情为本分的诗歌观念是多么根深蒂固。
如前所述,一种文类或文体之所以能够形成某种独特的教化职能和审美风貌,主要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关于文类或文体对表达方式的定向选择,李咏吟曾指出:“相对而言,文体构成了作家的‘想象定势’,这是被许多人所忽视的一种创作现象。作家的创作离不开文体,因为一旦选定了文体,也就等于选择了一种独有的语言方式去表达个人的思想与情感。文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家所要表达的内容,不同的文体适宜表现不同的精神内容。叙事性内容只能适合叙事性文体,抒情性内容只能适合抒情性文体,即一个人的意象思维特别发达就不适宜创作小说而适宜创作诗歌,相反,一个人的情节思维能力特别发达就应该选择小说创作而不能选择诗歌文体去创造。”[9]15按照这种“想象定势”,一个作家选择了何种文类,也就相当于选择了与之相匹配的何种表达方式。或者说,文体的“想象定势”决定了其“表达定势”。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表达方式之所以由“赋比兴”之说流转为“抒叙议”之说,一方面是因为诗歌文类的发展变化不仅需要借助史传的“叙事”史法来救助,而且要吸取古文的“议论”文法来滋补;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宋代以来的“诗话”“文话”以及“小说话”等文类批评在相关文类的文本评点中,需要更为通用的理论武器来支撑。具体说来,“赋比兴”转换为“叙述”“描写”,更应是小说文体叙事、写人发展以及文本创构所需的必然。对此,董乃斌曾指出:“以叙事、写人为主要目标的小说,单靠‘比兴’,单靠抒情,自然是不行的。”[10]由于“赋比兴”写人只着重于对物或人本身的特质进行铺叙、比拟,且多以静态出之,故而必须依托于动感性强的叙述、描写等笔法,才能达到写人活灵活现的效果。
抒情、叙事、议论等表达方式是伴随着传统文学文本延续、文类互渗而陆续推出的,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流转过程。在这些表达方式演进、定势过程中,“叙事”优越地位的确立主要得力于“史传”。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曾明确指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11]叙事架构起古文与史学之关系,古文之长于叙事,归根结底还是由史学奠基的。从史传创作实践和后人评赏来看,自班固、扬雄称赞司马迁“善序事理”起,“善叙事”就一直被视为“良史”之才的突出表现。如陈寿《三国志》卷一三《王肃传》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12]说起来,史上最早对叙事进行确认并加以定性者,是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幾。其《史通》之《叙事》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鉴识》又言:“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13]刘知幾的叙事观念,主要生发于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本,并成为后世史传文本创构的准则和典范。
在唐代,除了从观念上对“叙事”加以认定,从一些相关记载可见,文人们已经根据文类需要开始兼顾抒情、叙事、议论等各种表达能力的训练。如白居易《与元九书》曾说:“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可见,吏部选拔人才主要依据赋、判、传三种写作能力。所谓“赋”,即以抒情为要的诗赋;所谓“判”,即以议论为本的判书公文;而所谓“传”,即旨在叙事写人的人物传记,大致覆盖“抒叙议”三种写作能力。再看小说,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有一段经常被人们引述的关于唐人小说的著名言论:“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14]所谓“史才、诗笔、议论”三种才能,大致相当于叙事、抒情、议论三种笔法:史才即叙事之才、诗笔主要是抒情、议论就是说理,为清代叶燮《原诗》关于诗歌“理事情”三要素学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除了得力于史传文类的创作经验,叙事、议论两种表达方式还因唐宋古文推波助澜的发达而得到不断提高,从而得以与抒情在文学天地里并驾齐驱。对此,何诗海曾经说:“唐宋古文运动以后,随着文人创作的单篇叙事文的勃兴,文体观念发生丕变,文与史、叙事与抒情的界限不再如楚河汉界。宋人不但重视文章的叙事功能,甚至推崇杜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这是对文学尤其是诗歌抒情传统的重大突破。自此之后,文章学中的叙事理论逐渐丰富,叙事文地位日益提高。”[15]宋代人在总结文法时索性把议论提到与叙事平起平坐的地位。如吕祖谦《古文关键》卷首总论《论作文法》曰:“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16]既强调议论文字乃古文创作的务实之举,又把叙事、状情视为古文妙笔生花处。不仅如此,宋人还将叙事、议论提到文类高度来认识。如真德秀《文章正宗》在为“文章”分门别类时,将“叙事”“议论”与“辞命”“诗赋”并列为四大文类。明代人接受了以“叙事”“议论”为文类的观念。如王维桢就特别认同真德秀列出的“叙事”一体,其《驳乔三石论文书》曰:“文章之体有二,序事议论,各不相淆,盖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创为之。宋真德秀读古人之文,自列所见,歧为二途。夫文体区别,古诚有之,然固有不可歧而别者。”[17]这里也把序事(叙事)、议论上升到文体层次来认识,并且认为二体不可截然区分。无独有偶,清代邵作舟《论文八则》也曾指出:“文章之体,虽有纪、传、志、状、碑、颂、铭、诔、诏、告、表、序、论杂体之殊,总其大要,不外纪事、议论两端。”[18]认为不论文章可区分为多少种类,总括起来不外纪事、议论两端。照此观念,蓦然回首,《左传》中那段曾被《古文观止》等选本题为“曹刿论战”的文本,虽然旨在传达人物曹刿的非常识见,但记述的重心在“论”,自然算是“夹叙夹议”了。
在叙事、抒情、议论三种笔法运作下,关于中国文学的“理事情”三要素观念得以形成(2)关于诗歌之要素,叶燮前后也曾有不同的认知和概括,如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清代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开篇说道:“诗有三要,曰:发窍于音,征色于象,运神于意。”把音、象、意视为诗之“三要”,看到了诗歌固有的音韵声律、设色构象和传神达意等因素。。其理论贡献者主要是清代叶燮,他在《原诗》中反复说:“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则,诗文一道,岂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挈诸情;挈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故法者,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19]叶燮将“理事情”视为文章与诗赋的有机构成,并指出诗歌成败的关键在于对理、事、情的把握,而所谓文章之“法”,不外乎理、事、情三者的协调组合而已。在他看来,文类之间的穿越,尤其是唐宋代以来以史为诗、以文为诗作法的尝试与实践,使得诗歌之“叙事”“议论”功能加强,被视为诗文三要素的“理事情”与“叙抒议”三种表达方式形成大概的对应关系。同时,清代把“理事情”视为诗文创作圭臬者还有古文界的刘大櫆,其《论文偶记》指出:“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20]《史记》文本虽然寄托了司马迁的人生之感,但因没有用情景烘托,故不算抒情,只能视为议论。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文学文本整体上看离不开“理事情”三要素。相对而言,叙事通常生发于客观,抒情自然触发于诗人主观,而议论的角度则多属于旁观。
事实上,“理事情”三者不仅是诗赋文章的有机构成,而且更应是小说戏曲的文本创构之道,是其广义上的写人文本三大要素。只是相对而言诗文以抒情为本,小说与戏曲同源而异流,将直接抒情变为间接寄托或寄寓,转而以叙事为主。叙事讲究头绪,本身带有较强的时间性,注重节奏的张弛、强弱、快慢。如唐传奇《任氏传》最后交代,该小说创作旨在“糅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这几句话即暗含着“理事情”三要素。清代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指出:“先生此书,议论纯正,笔端变化,一生精力所聚,有意作文,非徒纪事。”并称赞《聊斋志异》这部小说的艺术造诣说:“盖虽海市蜃楼,而描写刻画,似幻似真,实一一如乎人人意中所欲出。诸法俱备,无妙不臻。写景则如在目前,叙事则节次分明,铺排安放,变化不测。字法句法,典雅古峭,而议论纯正,实不谬于圣贤一代杰作也。”[21]在其所肯定的因素中也含有“写景”“叙事”“议论”等,强调《聊斋志异》不执着于一般的叙事,而是注重包括议论、描写在内的文章创作。然而,小说又常常兼收并蓄史传、诗赋等文体的写法,形成兼容了以叙事为要的“史才”、以赋比兴为主的“诗笔”以及“议论”优势,这些写法均可用于或佐助写人。由此反观之,考察小说写人,也可从诗文、史传那里找到活水之源。就中国古代小说文类而言,它传承了“史部”的叙事基因、“子部”的议论基因,更强调绘画传神的写人笔墨,是叙事、议论、描写共同发挥作用的“杂家”。议论通常被视为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的说教,而《聊斋志异》却能有效地将议论和描写结合,使之有效地服务于写人,为小说写人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如《赌符》于篇末“异史氏曰”非常逼真传神地写出了赌徒的丑态:“……迨夫全军尽没,热眼空窥。视局中则叫号浓焉,技痒英雄之臆;顾橐底而贯索空矣,灰寒壮士之心。引颈徘徊,觉白手之无济;垂头萧索,始玄夜以方归。幸交谪之人眠,恐惊犬吠;苦久虚之腹饿,敢怨羹残。”作者追摄赌徒的模样、心理,活灵活现。《王子安》最后写“秀才入闱,有七似焉”云云,用七种比喻写科考举子从入场到出场的精神面貌,也惟妙惟肖。近代吕思勉《小说丛话》说得更具体:“文字之用,不外说理、叙事、表情三者。古文所说之理,所叙之事,所表之情,固非通俗文所能有。通俗文所叙之事,所说之理,所表之情,又岂古文所能有乎?惟如是也,故虽文人学士,深通古文者;而好读小说,亦与常人无异矣。”[22]史家叙事,注意吸取诗家之“发愤”“骚怨”等合理抒情内核,后起小说又兼采“史”之叙事、“诗”之抒情,并发扬光大了“史传”“诗骚”共有的“赋比兴”写人传统。由此观之,尽管小说也能够负载作者情感寄寓的功能,但主要还是以叙事与写人为主导。根据不同意图,各种小说文本又可区分为以叙事为主者、以写人为主者、叙事写人兼工者。文学表达方式服务于文本写人宗旨,叙事可为写人运行,议论也可为写人而发。
概而言之,随着文学文体及其相应文本创构的演化,“赋比兴”诗法在得到不断诠释、应用过程中,逐渐发生向“叙事”“议论”流转。在宋代古文家们所持“叙事”“议论”观念的推动下,“叙抒议”术语的用场不断扩大。至明清时期,人们不仅用“叙抒议”来谈论古文、小说,也间或用以论诗,于是“叙抒议”终于取代“赋比兴”,被用以指称包括诗词歌赋在内的各体文学的表达方式。在“抒叙议”观念下,“理事情”不仅被视为诗歌的三要素,而且被视为其他文类的三要素。其中,“叙”依附于史传,发达于古文,而稗家又继承史家、古文家之“叙事以言理”传统,门类和用场尤多。且不说诸如“正叙”“特叙”“夹叙”“再叙”“勤叙”“连叙”“忙叙”“补叙”“接叙”“总叙”“两番叙出”“眼中叙”“口中叙”“叙法”“叙述之法”等这些借用前人文法术语命名的术语在小说评点中屡见不鲜,就是“草蛇灰线”“横云断山”这些写法术语也大多被用于谈论叙事,并成为叙事文论的关键词。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将理、情、气、识纳入叙事之中:“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23]42叙事不仅可以包罗理、情,而且蕴含着气、识,可见其在以古文为代表的文体文法中的地位是何等举足轻重。在一脉相承的关于各种表达方式的术语系统中,虽然写人实践早已开始于诗赋中,写人观念也早已寄生于“抒叙议”笔法及“理事情”三要素等术语中,但只有在“描写”被充分看重后,写人传统及其理论谱系才得以显山露水。相对而言,小说是最能展现作家写人水平的文体,以小说文本为样本研究文学写人也最为适宜。
二、“描写”加盟文学文本创构俱乐部
按说,“描写”表达方式的实际运用并不晚,早在“赋比兴”兴起年代即已存在,并生成了一系列“写人”文本之实,不过作为一种被命名的观念,却是随着魏晋六朝画论对文学理论的逐渐渗透,大约到了宋代才得以明朗化的。此后,它常常凭着“有声有色”“声情并茂”“有滋有味”等笔致,营造出“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惟妙惟肖”等写人、写景文本效果,并给读者以“似临其境”“如历其事”“如见其色”“如睹其人”“如闻其声”“如嗅其味”等审美感觉。尤其是在“叙抒议”观念流行前前后后,“描写”也加入了这一文学文本创构俱乐部,并为“写人”文论争取到了立足之地,使之经常出现在文艺理论的前台。
如果可以把所有生长过的海拉细胞堆起来的话,它们可能重达5000万吨。50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 100 幢纽约帝国大厦的重量。如果将所有生长过的海拉细胞从头到尾排列起来,它们可以绕地球至少三圈,相当于1亿多米。但你要知道,拉克斯本人的身高只有 1.5 米。
众所周知,“写人”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中心议题之一,且不说人物画讲究传神写照,就是人格化、人性化的花鸟画、风景画也无不遵从天人合一、物我一体,故都奉“传神”为宗旨。由于中国文学写人理论术语主要来自画论,因而要全面诠释“写人”之功能,首先必须从其赖以实施的“描写”这一表达方式说起。追根溯源,所谓“描写”,乃由“描”和“写”合成,二者有不同内涵。“写”字使用较早,一开始并非指用笔作字,而是通“泻”,指倾泻、倾吐。在“赋比兴”诠释过程中,“写”也曾不断进入阐释视域。如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谈及赋的特点时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既具有铺排辞藻、夸饰渲染的形式特点,又长于通过描述诸如对山水、风物、宫苑、鸟兽、音乐舞蹈、车旗仪仗等具体事物来传达作者情志。以往诗歌的“言志”功能转给“赋”,而自个去“缘情”了。唐代皎然的《诗式》曰:“赋者,布也。匠事布文,以写情也。”无论是“写志”之“写”,还是“写情”之“写”,都含有其原初的“泻”意,只是前者偏于议论,后者偏于抒情。“写人”观念的形成得力于由“画”而来的“写”,以及写像(画像)、写照、写生、写影、写真、写形等一批相关术语出现。在文学文本创构中,既有叙写、抒写,也有描写,且描写占了最大份额。再看“描”,这种笔法最初指描摹,有照葫芦画瓢之意,是初学书画之阶,后来与“写”组合成一个复合词,才被用以指示传达神采气韵的运笔方式。关于“描写”,周汝昌《红楼艺术》曾经这样讲过:“描写,与勾勒有一点相似:也是合为泛言,分为两义。描写实际上是包涵了‘工笔’与‘写意’的两种很不一样的意度与技法的一个‘合成词’。”[24]无论如何,描写与叙述二者都具有强大的文本创构功能。随着绘画术语“白描”的出现,“描写”的功能仿佛更是如虎添翼。北宋画家李公麟(李龙眠)善画人物、佛道神像,多用线描而不设色,笔法如行云流水,被奉为“白描”大师。在传统文论发展中,“描写”以及“白描”术语的征用进一步推动了“写人”观念的独立。
文学表达方式不仅与文类体性密切相关,而且各种文类的表达方式又可互补共融。从肩负的功能和文类分工看,史乘之著长于叙事,诗词之作长于抒情,绘画则长于写人状物。关于这种分工,宋代邵雍《史画吟》有言:“史笔善记事,画笔善状物。状物与记事,二者各得一。诗史善记意,诗画善状情;状情与记意,二者皆能精。状情不状物,记意不记事,形容出造化,想象成天地。体用自此分,鬼神无敢异。诗者岂于此,史画而已矣。”[25]绘画长于描写,与“诗史”一样,“画”具“史”性,即所谓“史画”,它可描绘历史画面,又兼有叙事功能。“写人”观念得以形成的基础虽然是魏晋六朝以来的书画理论,但其理论上得以自成门户的标志却是小说批评对书画理论的遣用。在小说文体中,叙事与写人联袂,常常通过寓理于事,将“抒情”“议论”消解、融化为无形,或借助叙事游戏暗传人生密谛,或借助写人寓以褒贬。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是一种“理事情”兼蕴的“寓言”。
放眼中国小说理论史,“描写”及“写人”与“叙述”及“叙事”的地位大致均等。明代容与堂本《水浒传》即有这样的评点:“《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在,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把描写出人物的真情视为这部小说得以获得“与天地相终始”经典资质的重要依据。清代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通过《水浒传》与《史记》比较,认为《水浒》是“因文生事”,即“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并认为“因文生事”是“为文计,不为事计”。基于此观念,他在评《水浒传》第六十九回时,针对“又见他箭壶中插一面旗,上写一联道: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这几句写董平的文字,作了这样的评点:“大处写不尽,却向细处描点出来,所谓‘颊上三毫’,只是意思所在也。”将描写视为写人细处的笔墨。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指出:“其书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然则真千百化身,现各色人等,为之说法者也。”赞美小说之所以能够各尽人情、展现各色人物,靠的也是“描写”笔法。文学中的描写之道,与绘画之画人物的道理是相通的。关于小说批评中的“白描”,人们多有总结探讨。其中,杨志平曾将其含义分为两个方面:“一者是以简洁笔墨不作修饰地径直描画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给人以一种动态感悟,从而让人体味出逼真传神之美、日常写实之境;一者是强调寓含的深意或艺术效果的传达须作自然呈现而非主观表露,以达到含蓄幽婉之美。”[26]大意已明,不再赘述。
有了“描写”“写人”观念,我们再反观一下可见,唐代诗人除了引吭高歌地抒情,也曾静下心来写人绘景。如李白《侠客行》灵活运用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等笔法写人,既总写侠客的乱发突鬓、身佩弯刀、白马银鞍、扬鞭疾骋等貌相,又具体叙述信陵君用侯嬴和朱亥两位侠客救赵之事以及他们重然诺、挥金锤救赵的豪气,还先后插入“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等议论,不仅全方位地写活了诗人心目中的侠客群体,而且抒写了对其的仰慕之情。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与《丽人行》,一为李白与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饮中八仙传神写照,一为杨氏姊妹等长安水边丽人写真,交互而综合运用了赋比兴、抒叙议等各种笔法,更是诗歌史上为人津津乐道的写人名篇佳什。
大致说,叙述的主要对象是“事”,而“描写”的主要对象是“人”或“景”。写景服务于抒情,并成为佐助写人的烘托与渲染,获得了传统诗学的高度认可。如宋代范晞文《对床夜语》就提出了“情景兼融,句意两极”抒情效果[27]。明代谢榛《四溟诗话》也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的说法[28]。清代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有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29]强调情景交融是服务于诗歌抒情的绝配。相对而言,写景与叙事的干系却不是很大,虽然王昌龄有过“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这样的说法[30],但因为史传叙事讲究客观,文学中的写景还真的难说是为了叙事。再说,叙事不需写景陪伴已能达到精彩,这是写景不是为叙事而存在的反证。写景服务于写人,仿佛是天经地义,甚至可以说写景就是写人。
另外,“写”的对象,除了“写景”,还有“写意”“写心”都属于“写人”范畴。“写意”观念最初触发于北宋绘画领域,通过意象描绘寄寓情意。诗歌的“画面感”唤起人们对诗歌之“写意”的追溯,通过寄意于形象,实现有效地抒情。
应该说,叙述与描写并无严格的界限,二者经常浑然成为一体,难分彼此,故而还有人将那些“少做作”“去粉饰”的白描称为“生动的叙述”。既然描写与叙述关联如此紧密,可能有人会说:是否可以把描写纳入叙述或把写人置于叙事之下探讨?的确,古代有叙人、叙景之说,当今叙事学更是乐于把写人包揽下来。尽管如此,二者的独特功能还是不可彼此取代的。“描写”毕竟在笔法、笔调上有别于叙述,否则中外就不会有那么多文论家来辨析二者之关系了。古今中外,很多文论家都曾以“叙述与描写”为题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辩证分析,足见“描写”是一种有别于叙述的存在。如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奇在其早期论文《叙述与描写》一文中指出,叙述与描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对现实的态度”,二者的分工是:“叙述要分清主次,描写则抹杀差别。”“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尽管他最终对揭示“人的命运”的叙述手法给予褒扬,而对“把人降低到死物的水平”的描写,尤其是对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家的“描写”颇有微词,但并没有否定二者各自的功能[31]。法国结构叙事学家杰拉尔·日奈特在《叙事的界限》一文中也曾把叙述与描写视为叙事的两种方式:“任何叙事都包括对行动与事件的表现——它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叙述,以及对人与物的表现——即今日所称的描写,尽管这两类表现紧密地糅合在一起,而且所占比例变化不定。”可以理解的是,他之所以强调“不存在描写体裁”,描写服务于叙事,“很难想象一篇叙事辅助描写的作品”,没有给描写以独立资格,是因为人们毕竟站在叙事学立场上[32]。法国另一位叙事学家托多罗夫的看法也颇类似:“描写和叙事都以时间性为前提;不过,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时间性。起初的描写确实处于时间中,但这是连续时间;而叙事特有的变化将时间分割成断续的单位;纯连续时间不同于叙述事件的时间。仅描写不足以产生叙事,但叙事并不排斥描写。”[33]他通过对叙事与描写的时间性进行分辨,指出“描写”的功能赶不上叙事。西方文论把描写视为较叙事次等的表现手法,既是基于西方叙事文学传统,也是为了维护叙事的独尊。尽管国内有的学者受叙事学影响,也持如此观念,但更多的学者已对二者平等看待,并早已进行过论述。当年,老舍曾作《谈叙述与描写》介绍两种表达方式,对二者等而视之。蒋孔阳《叙述和描写》也曾指出:“叙述是抽象的、概括的,是由作者来说明和交代的,描写则是具体的、个性化的,是由人物形象本身行为的逻辑来展示的。”[34]也是从对等视野对二者加以辨析的。
大体而言,由叙述而形成的文本带有动态感,往往依靠时间次序、速度等因素调控;由描写而形成的文本偏于静态美,往往给人以空间感,尤其是借写景而写人的部分,或渲染悲情,或渲染乐感,充满诗情画意。如果说叙述文字形成叙事文本,那么描写文字便形成写人文本(写景归根结底也是服务于写人)。在小说评点中,取自史传、古文以及八股文术语的“文法”评点多是针对偏重叙事的文本;而源自古代人物画品评术语的“用笔”“运笔”等“笔法”评点,则多系针对偏重写人的文本。
三、叙事与写人联姻及写人传统之形成
在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关于文学的写人方法,人们通常采取肖像描写(外貌描写)、行为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以及景物衬托等术语来分类表述。尽管这套术语一度发挥过较好的效力,但随着时过境迁,许多人已不满足于此,并提出诟病,甚至称它们连同“人物描写”“人物塑造”等相关术语,已与文学文本阐释的现代性渐行渐远。既然这套外来术语已经失效,那我们还是寻找并回归中国传统吧!如果对传统写人理论谱系进行梳理,可以说,所谓文学文本的“理事情”三要素更容易跟“叙抒议”三种表达方式形成交错匹配;而所谓文艺文本的“形神心”三要素反倒更容易跟“赋比兴”三种诗法形成交叉对接,二者均是传统写人文艺理论的根本。
从“抒情”“叙事”博弈、共谋、合霸诗文文本天地,到“叙事”“写人”结缘、博弈,共同占据小说戏曲的文本园地,由此带来的叙事与写人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间性关系还是依稀可辨的。在中国文学研究和理论谱系重建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特别关注抒情、叙事关系的平衡,既不偏爱,也不偏废;另一方面,又要在抒情、叙事互惠与博弈的张力之间为“写人”寻找到一个最佳位置,让其得到最恰如其分的安置。在诗词歌赋中,叙事以抒情往往是常态,理、事、情时常融通;而在小说戏曲中,叙事以写人,写人以明理,以明事理,以通情理。李咏吟曾经有过这样的概括:“诗不以写人为中心,而以写意为中心;散文也不以写人为中心,而以写事为主;戏剧虽然也写人,但这人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要‘演出来’;写人叙事成了小说的总体特性,所以,它与通讯报道、传记、历史有较多的关联。”[9]15中国写人传统奠基于“赋比兴”,而至“人物赋”“人物画”得以发扬光大,至小说戏曲得以成熟。有的小说家注重将“赋笔”运用于写小说,自然偏重于写人,唐传奇《游仙窟》是经典个案,更多小说家以叙事运载写人。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虽然总结出“倒插法”“夹叙法”“横云断山法”“草蛇灰线法”“影灯漏月法”等叙事文法,但仍然表现出“重文轻事”倾向,而写人在“文”中占了很大分量。
叙事、写人如影随形、形影不离,几乎成为密不可分的联合体。写人,离不开写事;在很多情况下,写事就是为了写人。《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本指出:“此篇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黠,一一画出,毛发皆动,即令龙门执笔为之,恐亦不能远过乎此。”第四十一回评语:“牛、卜二老者,乃不识字之穷人也,其为人之恳挚,交友之肫诚,反出识字有钱者之上。作者于此等处所,加意描写,其寄托良深矣。”依托于充满画意描写的写人不仅能够有效地传达人物面貌,而且能有效地传达人物精神境界。
尽管我们可以把“叙事”与“写人”视为一对缔结良缘的情侣,强调其相生相长、互相依存状态,但从其术语遗传基因来看,二者又有着较大差异。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叙事”更多地遗传了“史传”以时间序列编排故事的基因,“写人”则主要遗传了“绘画”以空间承载人物形神的基因。中国传统小说长于叙事,乃由史传承而来。但如果一味地局限于史家的“以简要为工”的叙事原则,那么它只能停留于魏晋六朝“粗陈梗概”时代。纵向粗放的史家叙事只有与横向铺展的绘家写人合作共谋,才能够创造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的唐传奇小说那般“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的辉煌,才能获得文体独立和成熟[36]。从这个意义上讲,由“描写”之笔形成的写人文本才是小说的根本活力之所在。后来,白描写人更是对推动小说健康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这种认知原理,再回看前面提到的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关于唐人小说那段经常被人们引述的著名言论,我们就不满足于将所谓的“史才、诗笔、议论”简单地转义为叙事、抒情、议论。“史才”固然主要是叙事,但也有一部分可分解为写人;而诗笔不再是诗歌引吭高歌的直接抒情,也应该包括才情横溢的铺叙、象喻描写;议论虽然也可以分一点给“干预叙事”,但主要是为写人而设。这样,“史才、诗笔、议论”就可简化为叙事、写人,二者共同营造出唐代传奇小说文本的审美高度。在这种生态下,诗笔与议论主要是服务于写人的。
在中国文学文本创构中,“叙事”(述事)常常是手段而非目的,在诗中它服务于抒情,正如宋人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说道:“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37]不仅“述事以抒情”在诗词文本创构中成为常态,而且叙事详细,抒情含蓄隐蔽,不同于史传叙事以简要为主。在小说中,它又服务于写人,叙事以写人宗旨较为明确。既然充当服务于写人之“手段”,那么为了达到某种文本效果和目的,即可“不择手段”,因而不妨煞有介事、若有其事地“虚构”。如为了传达武松“神威”,《水浒传》作者可以不择手段地叙述一场因不合事理而备受后人质疑的“武松打虎”故事。金圣叹评《水浒传》赞美“武松打虎”一节曰:“以近人之笔写骇人之事。”另一方面,更在于以超乎常理的骇人之事传达近乎人性的人物神威。无论诗之“抒情”,还是小说之“写人”,都在追求“真”“实”,以“事假情真”“事虚人实”为文本创构原则。只要符合人情物理,就是精彩的叙事、值得信赖的抒情和靠谱的写人。当然,即使同为小说,由于体性有别,也会存在写人、叙事的不同偏重。李小龙曾辨析道:“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传体重人,记体重事;故传体以人为主,叙事紧凑,记体列叙事件,结构散漫。”[38]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同为记梦之作,标明“传”的《南柯太守传》与题名“记”的《枕中记》相比较,前者更偏重写人,笔法也更细致入微。即使到了章回小说有所变异,以“传”为题的《水浒传》比以“记”为题的《西游记》,也仍然更长于写人。因此,研究叙事,最好以“记体”为标本;研究“写人”,当以“传体”为模本。同为评论小说,因文本有殊,评点者关注点不一,叙事写人评语也会不同。围绕《水浒传》展开的李卓吾、金圣叹评点,皆重视写人,对写人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毛氏父子评《三国志通俗演义》,多用“叙事妙品”赞美,包括写人段落,也会视为叙事;而张竹坡评《金瓶梅》、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则多用“白描入骨”“用笔精细”之类的术语赞美,多关注传神写人文本中的白描。
当然,传统小说写人文本也注意适当的议论因素的吸纳。这些所谓的“非情节因素”,在叙事学的篮子里,实际上难以安放,便通常被命名为“叙事干预”。除了有的小说作者的连篇告诫令人望而生厌,还有更多的“议论”却有效地发挥了对人物进行评头论足的作用,写人功能较为突出。另外,传统小说文本中还存在一种“以曲代言”现象。对此,有人称之为“非小说因素”,主要被用以传达人物心理以及内在情感,写人功能也较突出[39]。
总而言之,中国文学文本创构大致围绕“理事情”三要素展开,只是不同文类有所侧重。诗歌长于“抒情”,古文长于“叙事”“议论”,小说则长于写人。抒情、叙事、议论三种表达方式既可服务于诗歌抒情,又可服务于古文叙事,还可服务于小说写人。随着“描写”这一表达方式被从书画理论引入,传统文学以诗情画意为格调的写人文本创构意识更为明确,受到文论家们重视。带着“写人”眼光回顾中国传统文学天地,抒情、叙述、议论等表达方式皆可服务于写人,此乃广义的“写人”观念。狭义之“写人”主要指关于人物的形神描写,既可粗略分为形态描写与神态描写、静态描写与动态追摄等类型,又可具体坐实到人物富有神韵的千姿百态、姿态万千。即使从狭义的写人观念来看,它不仅与叙事、抒情一样各自形成文本创构传统,而且其理论建构也足以自成相对独立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