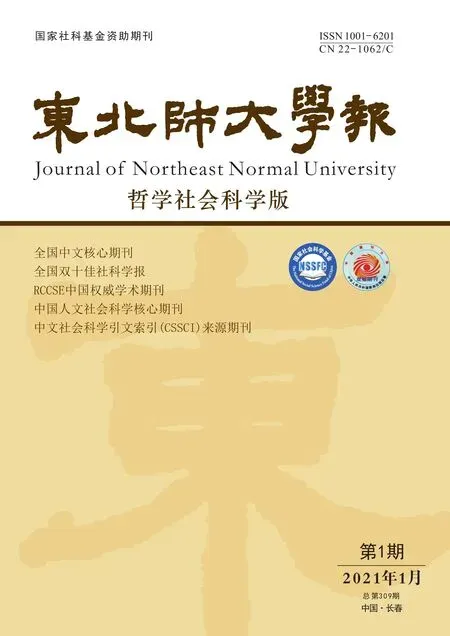文类递嬗与抒叙博弈
董 乃 斌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是文类递嬗演变史,也可以说是抒情叙事传统的博弈演进史。
文类递嬗,说的是文章体裁产生、发展、兴衰、变异的过程。对此,很多前辈学者已有所论述,有些文学史就是按此观念编写的。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或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可说是一种颇为典型而概括的说法。这其实就是说每一代有一定的热门文类,有一代的中心和主宰,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经》、《楚辞》、汉赋乐府、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小说,说的就是居于历代文学史中心的那个主导性文类(或曰文体、体裁、文学样式)。本文试从抒情叙事传统博弈的角度,来观察和说明这个现象。
抒叙博弈,是从文学表现的角度来看其内质所得之观感和结论。如果把文学创作看作一个过程,那么它的前阶段是作家头脑中的酝酿构思,后阶段则是作家借助文字(或其他媒介)把头脑中的东西对象化为作品。这个后阶段也就是文学表现的运作过程,是将作者内蕴的认识和感受外化出来的关键。没有表现,便没有读者能够见到的文学作品。文学表现手法很多,概而言之,却只有抒和叙两大类,可谓非抒即叙,非叙即抒。抒者,抒情,包括作者对主观情绪、观点、认识、感受的一切表达;叙者,叙事,指作者对一切客观事情物态的叙述或描写。其实,无论抒或叙都是一个主体在叙述、在言说,唯所叙所言的内容不同而已。“叙述”是个并列复合动词,叙与述同义,也就是言说或讲论。抒情、议论、说理和叙事、描写都属于叙述。“叙事”却是动宾结构,已说明其叙述的对象是“事”(事由、事态、事程、事果等),叙事与叙述感情(抒情)、观点(议论)、道理(说理)虽都是叙述,却不可混为一谈。
抒情叙事是两种不同的文学表现手法,但又交融互渗、错综复杂,共同完成文学的表达。在文学作品中,它们有互惠的一面,相促相益,使对方增色增重,又存在博弈的一面,即相互间有竞争比赛,在作品构成的抒叙比重上有争夺。同样的创作动机或题目,同样的素材原料,用抒情还是用叙事来表达,不同作者会有不同的习惯偏好和选择,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对文类、技巧的掌握程度也各有不同。故在抒叙二法中,必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常常存在取此舍彼、你重此他重彼的情况。而多用抒情还是多用叙事,作品的表达效果、文体性质、风格特征、读者反应、实际功能和影响范围,便往往不同。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博弈”的一种表现。显然,抒叙博弈对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品质的质地水准,甚至对其总体优劣高下良窳之差异,都有一定的影响(1)此处或可稍举例。元稹《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与《连昌宫词》所写内容相关,皆涉天宝遗事,形式一为五言小绝、一为七言长歌,一简约抒情、一漫长铺叙,二者情味功能显然有异,各有长短而实含博弈。元稹又有传奇《莺莺传》提及同时人杨巨源有《崔娘诗》、元稹有《续会真诗》、李绅有《莺莺歌》,皆以诗歌形式复述或咏唱崔张故事,虽各有情致,然皆不如原小说细腻生动。倘非小说基础好(内涵丰富,戏剧性强)而仅存此数诗,恐怕宋元后《西厢记》系列不致如此兴盛,至今不衰。其中可见诗歌小说之抒叙博弈。。
抒情叙事既是文学创作(表达)所必需,当然从文学诞生之始就存在着。抒情叙事实乃同源共生,互动互促地发展,久之乃各自形成自己的统绪,即传统(2)传统指人类行为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某些共同认识和习惯之类,犹如不成文法,虽或不自觉,却无法摆脱,自然遵守。传统是隐然的客观存在,须由人予以总结、构建和表述而显。传统在历史中形成,且非一成不变,人对它应主动认识、选择并加以改造,使之新陈代谢、与时俱进。。
至于文类的产生和递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外部原因(如社会需要、经济发展、文化演变等),但就文学自身而言,还存在内部原因,而抒情传统、叙事传统的博弈消长就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对此关注不够,今有必要予以重视。
一、记叙之需促成文字产生,史与诗乃最早的文类
谈论文类,不能不先谈文字。没有文字,何来文章?没有相当多的文章,又何谈文类?而文字的产生,就与人类记录历史和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之需要和愿望分不开(3)裘锡圭指出,文字为记录语言之需而产生,而记录语言的目的则是记事和传递信息。。
据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甲骨文多记述占卜的过程、问题和结论。钟鼎金文多记述家族历史、祖先功德或箴诫铭颂之类。裘锡圭先生论我国文字体系的产生,特举《尚书·多士》所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认为“周公特别强调殷的先人有典册记载‘殷革夏命’之事,也许我国就是从夏商之际才开始有比较完备的记事典册的。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很可能也就在夏商之际”。裘先生还指出,“在目前所能看到的内容比较丰富的成批古汉字资料里,时代最早的是与占卜有关的甲骨文,它们大概也出自当时的巫、史之手”,所以,仓颉造字的传说“把史官跟造字联系在一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1]。
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最早的文类则是史述和诗歌,也可简称为史和诗。这两种文体的产生同样是缘于人类记载史事和表述情感的进一步需求。它们原本都是实用性颇强的文体。
史述主要是记事,但记事中不免渗透着伦理裁断、价值判别和感情倾向;诗歌多因事触感而发,人生活于诸事之中,事促情动而有诗,凡诗皆不能与事无涉(4)杨国荣《“事”与“史”》一文有云:“历史与人的活动无法相分。……人的活动也就是人之所‘作’,其内容具体展开为多样之‘事’。宽泛而言,作为人之所‘作’,‘事’既表现为个体性的活动,也展开于类的领域。在个体的层面,个体所作之‘事’的延续,构成其人生过程;在类的层面,人‘事’的代谢,则呈现为前后赓续的历史演进。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类似的看法也见于柯林伍德。”(《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可以作为我们思索论述历史、事、人的生活与叙事活动关系的重要参考。人之一生是一连串的事,历史则是许多人的许多事。。在上古时代,诗歌的演唱既曾与乐、舞一起为礼仪服务,也曾承担过史述的部分职能,后来不管怎么变化,诗歌仍一直与史结有不解之缘。无论是史还是诗,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化产物。它们的形成和成熟是文字和文章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的事,标志着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唐史学家刘知幾《史通》多处论及文史之关系,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这里稍举二例。如谓“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以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2]180。著史必须用文,非文不能成史,此乃文史结缘的根本原因。刘知幾又曰:“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2]123特意把“国风”“楚赋”提出,与“人文”并列,这就更把诗文与史都联系起来了。周宣王、鲁僖公的善政,从《诗经》的《大雅·烝民》和《鲁颂·閟宫》可以看到,楚怀王和顷襄王的无道,则在屈宋辞赋中可见。这些诗文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与史的本质相同,故虽是诗篇,却足堪称史,它们的作者尹吉甫、奚斯、屈原、宋玉也就可与历史上著名的史家南史、董狐媲美。
明前七子之一的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中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校,曰劄,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诔,皆其馀音也。附之于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3]
王世贞的观点是史是一个大文类,包含广泛,他不厌其烦地列出了史这个文类的家族构成。但把四诗之一的颂及其同类的赞、箴、铭、哀、诔“附之于文”,他觉得不太妥当,但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暂时从众了。这启示我们:如果看到诗的家族也非常庞大而复杂,那就不如果断地把诗单列出来,成为与史并列的另一个大文类。这样便形成了更为清晰的诗文(史)两大文类,既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王世贞的不安也可以解除了。
二、史文的本质是记事,基本形式为散文,叙事成为一个文类
中国自古重史,很早就有史籍的产生。《周礼》《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左史、右史等职官的名目,他们的职务不同,但掌理书志、秉笔记事是共同的两项。《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4]这些史官的职责就是代表官方记录史事,主要记录君王及臣属们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情况,散体的文章是他们使用的主要载体,用文字叙事是他们的主要文学手段。史述这个文类,就是由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
古史大多遗佚,但《春秋》尚存。《春秋》是一部编年古史,文字简约,被奉为“经”。其在师弟口传中易生歧解,《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国语》等书据经而作传,其价值主要在于补充事实。唐人啖助比较《春秋三传》曰:“予观左氏传,自周、齐、晋、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5]228由此可知,《左传》等书中实包含了当时各国的多种史文,也包括了古代已存在的多种文体。它们不但充分显示了史文的叙事性质,而且显示史文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文类,除了史官的记录文字外,在古代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运用着的种种文体,都可以在史文中看到,如君王的训诰、臣子的议对、外交的盟誓、战事的檄移等等。这些文类的内容都少不了一定的叙事成分,因为只有先说清楚相关事实之后,才能引申到下文的训诰、议对、盟誓或檄移,文章才能有理有力,发挥作用。
这种情况在《尚书》中也看得清楚。刘知幾《史通》内篇第一卷第一篇《六家》云:“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2]1《尚书家》被列为第一,大致可以作为史体文章的最早代表。据云孔子整理过此书,原有百篇,搜罗了自尧舜时代起,历经夏商周,至秦统一前的重要政治历史文件(5)参见班固《汉书·艺文志》、魏徵等《隋书·经籍志》。。虽然有人认为它“体例不纯”,不够史书的标准,但作为原始史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比起甲骨文或钟鼎金文,《尚书》的文章已成熟了许多,显然经过后世文人的整理润色。《尚书》之文包括多种名目,有记录君王言论的誓、命、训、诰,也有记录史实的典谟之类文章。但归根到底,都是史文的一种。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十《书序》简要说明今存《尚书》诸篇的内容,无一例外地解说了它们与史事的关系,和它们曾起过的历史作用。如谓:“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大(泰)誓》三篇。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从远古至夏商周一代一代地解说下来,直至“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5]28-29
《尚书》是《六经》之一,古人有云“六经皆史”[6],从文学和文章学角度言之,六经的文体都可以说是史体。刘熙载云:“《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7]六经之文都是从一个特定角度记述历史上发生的事,因此皆可作史文看,都属于历史文体,而后来的诸种文体,都是从《六经》中生发出来的。故刘熙载又云:“九流皆托始于《六经》”,而刘知幾《史通·六家》所说的《春秋家》和传叙春秋史事的《左传家》,也都属经传的范围。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选文为范,分古代文章为四类:一、辞命,收帝王的诏告制令玺书。二、议论,收臣僚卿士的论说谏议对策上奏之辞。三、叙事,选录载史之文,如“左氏叙隐桓嫡庶本末”“叙郑庄公叔段本末”“叙晋重耳出亡本末”之类,大都摘录史书正文。亦有杂传,如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宋清传》,乃至碑铭文(如《平淮西碑》《柳子厚墓志铭》)及“永州八记”等。四、诗歌,选录上古至唐代符合诗教标准的古体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此书“录《左传》《国语》以下至于唐末之作”,并加按曰:“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8]1699
虽然真德秀乃道学之儒,选文标准与文章之士不同,其所选诗目,被顾炎武批评为:“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四库馆臣亦曰:“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8]1700但我们却从此书发现重要信息。那就是:
第一,在宋人真德秀心目中,中国古代文章按其实用价值来看,是四大类别,即自上而下号令天下的辞命,自下而上治国理政的议论,记载历史的叙事,抒发情感的诗歌。他打破《昭明文选》以来编选总集的习惯做法,首次把叙事性的历史记述列入选文之中,将其视为四大文类之一。梁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是不收叙事性史文的,其书六十卷,收入三十八种文体的作品,除诗赋为大宗外,颂、箴、戒、论、铭、诔、赞,以及“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凡能“入耳之娱”“悦目之玩”者无不收纳,但经、史、子之文,却是不收的。这表明萧统其时对文学的特质已有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清晰的认识,他是在努力将文学(文章、篇翰)与经、史、子,即哲学和历史著作区分开来,也可以说,他是在努力提高文学的纯度。他申说不选史文入《文选》的理由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这是指史书正文,从功用角度而言,但他对史书中的赞论文字,即史书中侧重反映作者观点情绪和文采的部分,却十分欣赏爱惜:“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翰,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9]萧统的主张代表了文学自觉、文史分家的时代要求,影响颇大,后世文家选文,排拒史著正文几成定例。
这种来自文学方面的与史学分家的要求,与来自史学方面要与文学分家的要求,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问题在于,文史两家在理念上、感情上都想要分开,但事实上史中有文有诗(诗心诗性),诗文中无不含史(史性),却是无法否认亦无法摆脱的客观事实。这种情况在史学界被称为“在史学理论上反对和排斥文学,而在史学实践中却大量运用文学的思维、手法和技法”,亦即“(史的)文本与文本理论之间,却呈现出二元对立的价值倾向”[10],迄今仍是史学研究的一大理论问题。真德秀首起变革,明确将史文视为文章,视同文学,其意义十分重大,影响也十分深远。关键就在于,把叙事的史文也算作了正宗的文章,这种对文学文类的认识,自然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真德秀所选的文章,除叙事类出自史书外,其他两类(辞命和议论)大多也是出自史书,是历史上实际发生过作用的文章或言论,往往被载入史册。所以,《文章正宗》的前三类不是史书正文,就是史书所包含的各种应用文体。再细看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些文章都有比重不等的叙事成分,无论辞命还是议论,都是“缘事而作”,而且都是要落实于事功的,它们实实在在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
由此不妨认为,真德秀实际上乃是视中国文章为史与诗两大类,而史类之文的共同特点便是叙事或至少以叙事为基础(然后才能发布命令或发表议论)的(6)这里举一例以明之。《文章正宗》辞命类和《古文辞类纂》诏令类都选录了汉高祖《入关告谕》:“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此文极短,但叙事清晰,结构分明,逻辑有力,第一说秦法苛,第二说我当王,第三说约法内容,第四说驻军霸上之故及后话。在叙清事实的基础上发布命令以安抚关中士民。后世诏令篇幅加长,结构则近似。凡应用性文体皆可做类似的叙事分析。。至于诗歌,此时已开始与史分家,其形式又与史类明显不同,故只能列为文章(文学)类别中的另一主体。《文章正宗》遂形成史、诗两大文类的格局。
文史从浑然一家到分为两家,酝酿已久,蓄势有日,可是成功却谈何容易!所缘何来呢?实因欲分虽是大势,但分不开却是根本,文史两家的因缘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瓜葛可谓永无休止。从中国文论史上的“文笔之辨”,到《昭明文选》,到刘知幾的《史通》,再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直到今天文史两界之现实状况,都显示了这一点。
三、诗与史的因缘,是古代文体内部“史性”“诗性”并存互惠博弈的根源
在文类发展上,诗体与史体是同时形成并成长起来的。史体是散文源头,诗体则是韵文源头。诗与史同样,也是一个包容很大的文类,最起码,诗还包括歌。据闻一多先生研究,上古时,诗与歌的区别就在于歌抒情而诗记事。他在《歌与诗》一文中论证了这一点:“上文我们说过‘歌’的本质是抒情的,现在我们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诗与歌根本不同之点,这一来就完全明白了。再进一步地揭露二者之间的对垒性,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诗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11]187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抒情与叙事对垒性的提法;二、原来最早诗与歌不同,歌抒情,诗记事,诗也是史的一种。
前一点告诉我们,诗歌里存在着抒情和叙事两种对垒性的成分。对垒也者,既是相对又绝不可分之谓也。叙事造就“史性”,抒情(兴发感动)则是诗的特性,是“诗性”即文学性的核心和本质。叙事与抒情的对垒,换言之也就是史与诗的对垒,这曾是“诗”与“歌”的“根本不同之点”,却也是“诗”与“歌”永恒结缘的原因。认识及此,对于理解中国文学抒情叙事两大传统及其关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而后一点,则有助于我们读懂孟子的名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12]不能否认上古曾有一段诗、史混沌不分的时期。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诗、史也在不断分化着,界限日见明显。但在诗歌源头的《诗经》时代,诗与史的瓜葛极深。《诗经》中的颂和大雅,以及小雅中的一部分,直接与一定的历史阶段、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关联,有的可与《左传》等史书对勘,有的进而成为后人(如司马迁)撰史的依据[13]。《毛诗序》解诗的思路基本上就是以史解诗、诗史印证。此点在古代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同并继承,却也曾经颇为现代的《诗经》研究者所诟病。但《诗经》研究造诣极深的闻一多这样说:“《序》指出了《诗》与国史这层关系,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献。如今再回去看《诗序》好牵合春秋时的史迹来解释《国风》,其说虽十九不可信,但那种以史读诗的观点,确乎是有着一段历史背景的。”[11]188这话就很辩证而公允。《诗经》确实有一些篇章讴歌民间日常生活,不必非要勉强去与一定的历史事件挂钩。但《诗经》的《风》诗有不少与某国某地的史事有关,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当代学者马银琴在其力作《两周诗史》中说:“《诗序》所言并非尽与诗之本旨相合,在很多时候甚至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不可依据《诗序》来说《诗》,已成为《诗序》研究者的共识。但是,《诗序》在解说诗旨时出现的不如诗义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诗序》的说辞一无是处。相反,在诗歌创作年代的判定问题上,《诗序》的说法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这样说,《诗序》为我们判断《国风》作品的创作年代提供了可以依据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本文下面的考订工作,将在《诗序》所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展开。”[14]马银琴所言同样辩证而公允,是她深入钻研《诗经》及其研究史的心得体会。另一位《诗经》研究者邵炳军,在其《德音斋文集·诗经卷》中考订《诗经》诸国风的写作时间和旨意,更完全是用诗史互证之法,行文中到处有明确的标示[15]。他们的成功实践使我们相信诗史互证的确有其合理性,不可轻易否定。只要不是胶柱鼓瑟钻牛角尖,这不失为研究古代诗歌可用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因为诗与史二者本就有其深刻的相通之处,“史性”实乃许多诗篇本就具有的一种质性。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与历史有关,故具“史性”,这是一层意思。不仅如此,就是那些描写、反映民间日常生活,而未必与历史事件相关的短小抒情诗(《风》诗中常见),其实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史性”。“史性”的内核是叙事,一首诗凡具体实在地表现了一定时代的真实生活,或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真实情绪心理,有助于后人透过诗歌了解历史生活,那就都多多少少带上了一些“史性”。今日之现实,异日即成历史,所谓“史性”应是一个开放的有生命的观念。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读诗又怎么能够通过“以意逆志”“知人”而“论世”呢?
当然,诗的叙事与史的叙事是有所不同的,此点不可忽视,不但所关注的方面各有侧重,表现方式的差异尤大。史以直笔,即直书其事为主、为基本要求,追求的是真实可信,而文字表达则要朴实无华,避免辞采的繁缛浮夸,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史官或史家能否完全做到,那是另一回事。诗与史不同,古人概括诗之表现有赋比兴三法。赋虽号称“直陈其事”,其实因为用的是诗歌语言,与史之直笔记叙已然不同,更不必说采用比兴手法而形成的曲笔隐喻、指东说西乃至指桑骂槐,为的是启发读者的丰富联想,取得艺术上的增强效应,是史述所禁忌的了。闻一多指出诗的叙事“其中的‘事’是经过‘情’的泡制然后再写下来的”,与真正的历史记述(史传或史志)不同,他举出《诗经》中的两种叙事类型,“一种如《氓》《谷风》等,以一个故事为蓝本,叙述方法也多少保存着故事的时间连续性,可说是史传的手法,一种如《斯干》《小戎》《大田》《无羊》等,平面式的纪物,与《顾命》《考工记》《内则》等性质相近,这些都是‘诗’从它老家(史)带来的贡献”。又进而论述“事”“情”,叙事和抒情,在诗歌发展中的升沉变异:“由《击鼓》《绿衣》以至《蒹葭》《月出》,是‘事’的色彩由显而隐,‘情’的韵味由短而长,那正象征着歌的成分在比例上的递增。再进一步,‘情’的成分愈加膨胀,而‘事’则暗淡到不合再称为‘事’,只可称为‘境’,那便到达《十九首》以后的阶段,而不足以代表《三百篇》了。同样,在相反的方向,《孔雀东南飞》也与《三百篇》不同,因为这里只忙着讲故事,是又回到前面诗的第二阶段去了,全不像《三百篇》主要作品之‘事’‘情’配合得恰到好处。总之,歌诗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发展是诗三阶段的进展,也正是《三百篇》的特质。”[11]190用赋比兴,隐喻指代,曲折含蓄,渲染夸张,一语多义,皮里阳秋,意在言外,层次复沓,较少事实而更多感情色彩,令人吟咏咀嚼回味不尽,这些都是诗歌叙事的特点,所谓“诗性”之表现,是它与史述明显不同之处。
诗歌叙事与散文叙事相比,有特点也有弱点。诗歌每句字数有限且固定,需要押韵,需要遵守一定的、越来越严的格律。便于吟诵记忆是诗的优长,但诗歌叙事不能像散文那样自由而周备详赡,那样酣畅而明朗,往往有意无意地造成理解障碍或阐释歧见,则是诗的一个特点,有时又是它的弱点。
即以诗圣杜甫为例,《八哀诗》是他著名的传记体长诗,王嗣奭《杜臆》云:“此八公传也,而以韵语纪之,乃老杜创格,盖法《诗》之《颂》,而称为诗史,不虚也。”[16]但浦起龙《读杜心解》则强调:“每篇各有入情语,此致哀之本旨,与国史列传有别。”[17]以诗歌作传毕竟不可能像史书本传那样按部就班、平实叙写,故了解史迹史实,还是要根据史书,诗歌只能作为参照补充。像《八哀诗》首篇《赠司空王公思礼》,全诗六十四句,可与正史本传印证,但毕竟不是史文,而是诗述。以诗歌方式述史,必常用比兴语,如以“洗剑青海水,刻铭天山石”描述王思礼随哥舒翰征讨吐蕃的功绩,气势雄壮,对仗工稳,但抽象空泛,尚待史实的充填。即使全用赋体,如“肃宗登宝位,塞望势敦迫。公时徒步至,请罪将厚责。际会清河公,间道传玉册。天王拜跪毕,谠论果冰释”一段,写哥舒翰潼关大败,王思礼西赴行在,受责将军法从事,幸有人进言将其救下。杜甫的叙述就编织了房琯恰从成都来传达玄宗传位诏书,肃宗因此宽恕思礼的情节,颇有戏剧性,却不一定是史实。就全诗抒叙比例看,叙事者五十六句,“入情语”即抒情句为八句。此诗可算“叙七抒一”之作,叙事成分重,是绝对无疑的。再如杜甫“诗史”之名的出处《本事诗·高逸》所提及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以十韵叙李白事迹,但若与孟棨前文所叙李白生平的大段文字相比,还是简略抽象得多。不过,这里的叙述充满感情,句句堪称“叙中抒”,而后十韵均为“入情语”,故此诗的“诗性”实远胜于“史性”。然而孟棨却说“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并由此引出下文:“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8]可见诗、史虽皆叙事,但要求是不同的,效果也是不同的,读者对诗歌叙事的期待也有所不同。所谓抒叙博弈,即于此产生。体现在文类上,复杂曲折的叙事、长篇大套的议论、细腻深入的分析、政治外交的应用等等,便不能不由散文承担,而诗歌因能够容纳多量的“入情语”,则更宜于兴发感动,抒情寄慨。诗文分工的内在根源应在这里。
四、有无应用性是鉴分古代文类的重要准绳
中国古代文体虽然繁多,其实可按是否具有应用性而分为两大类。散文类文体多数有应用性,即为处理事务、解决问题而写,有的其实就是一种公文或私人应用文牍。曹丕《典论·论文》提及八种文体,所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前六种都是文,也就是散文体的实用文章,唯诗赋以抒写情性、兴发感动或展示才华为主,没有实际用途,比较接近西方所谓的纯文学(当然所谓“纯”也只是相对而言)。
刘勰《文心雕龙》自《辨骚》至《诠赋》四篇,所论诗歌乐府辞赋皆非实用性文体,当纯文学概念输入后,即往往被以纯文学视之。《颂赞》以下直到《书记》,共十七篇,论述了数十种文体(有的文体可有多种名称,且有重叠交叉),绝大多数都是应用性的。有主要用于政治外交场合、军国大事的颂赞、铭箴、祝盟、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之类,有广泛用于社会生活、为各阶层共需共用的,如诔碑、哀吊、史传、诸子、论说和统称“书记”的各种文体(书信、笺记、笔札、杂文乃至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卷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所谓“艺文之末品,政事之先务”[19])。以上林林总总的文类,大都具实用性(7)也许只有《谐隐》一种除外,因是游戏文章,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仍可娱情悦性。为实用目的而写作和作品完成之后能有某种用处,终非一回事。。实用性有强弱,应用范围有宽窄,在其内部也都存在着抒叙博弈,不同作者所写同一文类的作品,抒叙的成分比例也有不同,同一作者在不同情况下所写同一文类之作品,也可能抒叙比重有差。凡抒情(含议论说理)成分较重且讲究文辞者,往往文学性较强,实际功用与流传效果也往往较佳,也就较易在文学史上留名,能够被选入《文选》或其他选集总集,可算一个标志。有的文类,因抒叙关系的变化,其实用效果(应用范围)也随之变化。如檄移类文章,最初只是一般行政公文,既供上行迎候谒见报疏之用,亦用于下行的荐举召见或责令等事务,但最后却变成专为数落敌罪、列举己德之用的露布[20]。《文心雕龙·檄移》提到的几篇名著,如载于《后汉书·隗嚣传》的《移檄告郡国书》,载于《文选》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载于《三国志·魏志·锺会传》的《移檄蜀将吏士民书》,就都是如此。唐人骆宾王的《为李敬业讨武曌檄》更是传颂千古的文学名篇。
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分体更细,吴书分文五十九类,徐书分文一百二十七类,但无论怎么细分,大体仍是诗赋与散文两部分,诗赋大致属于后世所谓的“纯文学”,既含一定的叙事成分,而抒情色彩(“诗性”)毕竟浓重;散文部分则大都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因而不能不具有较多的叙事成分,即“史性”,而文学色彩(“诗性”)则主要表现为辞采的丰赡华丽和笔端浓淡各异的情感流露。
应该说明,诗赋也曾有一段时期是有实际用途的,除诗史浑然不分的远古,历史上还有过“以诗赋取士”的时代。如在唐朝,诗赋便曾是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唐人应举前往往行卷以提升名气,寻求揄扬。行卷所用的诗,也就有了一定的实用性。再往后,诗歌还成为文人雅士应酬唱和礼尚往来的实用工具。不过这种实用性与前述那种处理事务、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还是有所不同的。多数时候(包括唐代),诗赋还是充当人际交往和自我舒泄的工具,适应人们(特别是文化人)抒发情感波澜和建构自我主体的需求。诗歌发展的总趋势还是重心向非应用性倾斜,向纯文学靠拢的,西方文学及其理论传入以后,就更是如此(8)诗歌要保持其非实用的性质和特色,而更多地吟咏情性、远离功利,实际上是一种影响很大的诗学审美观。王国维《人间词话》:“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总而言之,一切文类在文字表达上无不是抒叙两种成分的结合融会,只是比例不同、形式多样而已。诗歌之叙事有其特点优点,也有其不足和短板。抒叙的博弈促使非应用性散文叙事的兴起——即使是非应用性文章,也不是仅有抒情议论说理就够的,提笔作文,总因有事,也因有感,何况情也好,理也好,本皆由事而生,与事有关,情感的抒发、理念的阐说,本就离不开一定外物的媒介,涉物叙事自然是一切文章的必需。梁萧纲自称“少好文章”,深知文辞咏歌关乎人事,从春秋迁移,到出征戍边,凡“沉吟短翰,补缀庸音”,皆“寓目写心,因事而作”[21]。唐古文运动前驱萧颖士则说:“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22]唐《中兴间气集》编者高仲武在其书《序》中有“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之说。此类叙说,古文论中随处可见。从记事散文逐步发展出有意虚构的小说遂成必然之趋势,且又发展出敷演故事的戏曲,或与外来文化结合,发展出佛经变文的演唱之类,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发展出影视、广告游戏、网络文学等等,大大地扩充了中国文学的文类。
五、抒叙的融会结合与博弈前行,形成绚丽壮观的文学史图景
中国古典小说从历史纪事与诸子寓言中孕育发展至于脱胎而出,到唐传奇已成为诗歌的重要盟军,成为一种独立的文类。可惜旧式文人未把小说纳入他们极想“明辨”的文体之中,所以我们在《文体明辨》《文章辨体》《古文辞类纂》直到《古文观止》等书中看不到古代小说的踪影。要等文学观念更为新潮和开放的后人才能懂得小说的价值。
其实,早在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时候,诗歌的抒叙和小说的抒叙,就已经在互惠互补,同时也博弈竞赛了(9)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陈)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指李隆基杨玉环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教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汪辟疆《唐人小说》录自《文苑英华》卷七九四,《太平广记》卷四八六载《长恨歌传》无此节,详汪氏《唐人小说》此篇文后叙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3年,143—144页)。同时代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元稹)是散文的叙述中参以诗篇,诗文互促互补,后来更有《莺莺歌》(李绅)、《崔娘诗》(杨巨源)及《续会真诗》(元稹)在此基础上的咏唱。小说的叙事在发展过程中进化出戏剧性,戏剧性是叙事作品最能吸引人的因素。于是张生莺莺故事以小说为新起点继续演化,至宋则有赵德麟《商调蝶恋花》以歌其事;至金章宗时,又有董解元以诸宫调演唱《西厢记》;至元代更演为杂剧多种,而以王实甫所作的多本《西厢记》为最著名。明清至今更有长篇戏曲和各种地方戏剧,乃至影视的《西厢记》,其发展变化可谓尚未终结。唐才子沈亚之是著名诗人,也是杰出小说家,他刻意将虚构故事的叙述与诗歌的吟唱结合,把诗歌做成故事情节的一部分,又把故事的叙述化为立体的戏剧场面。他可以说是小说文类向戏剧形式演进的重要推手。读其小说《秦梦记》《湘中怨解》,犹如观赏一出凄艳精美的歌舞剧,使我们从唐传奇中体味到中国古典戏曲的情味,并由此憬悟:中国古典戏曲实乃小说叙事和诗歌抒情进化结合的新形态,一种难度更大、艺术空间也更宽广的文学类别。戏曲形式循此而大发展,而趋于成熟。中国文学史到元明清时代,会出现一个以戏曲为文坛中心的阶段,杰作迭出,实在绝非偶然。
散文的叙述大大补充了诗歌的叙述,使诗歌的抒情具有更坚实的基础、更广阔的天地,中国戏曲昭示了这一点,由此也可窥见文类递嬗与抒叙博弈的关系。
抒叙两种文学表现手法互为依靠,但比较起来,叙事更具基础性。叙事含情易,甚至可以说,凡文学叙事必带感情,文学中没有不带感情的叙事,纯叙事仅存在于非文学之中。抒情在文学中也很重要,不但叙事必含情,而且文学中还允许纯抒情的存在,有时甚至需要来一点纯抒情,乃至哲学化的抒情。中国戏曲的唱词往往就是诗,比较多的是抒情诗。小说中也不乏诗,或用以推动情节、营造气氛,或用以塑造人物、增添情趣。叙事与抒情在戏曲小说中互惠而博弈的例子举不胜举。
值得注意的是,纯抒情文体虽然存在,但很难占据文坛中心或成为主流,特别是某些自抒自唱而生活内容稀薄的抒情诗议论诗哲理诗,看今日实际状况,已沦为小众艺术,呈现衰微趋势。古代的此类作品很难进入文学史,也乏人关心。当代的此类作品,也不大受欢迎,大抵只能自娱自乐或藏诸名山。现在真正得到大众欢迎的多是叙事类作品,诗歌也不例外。故当代诗歌乃出现所谓“及物现象”,甚至就连最近兴起的所谓“极短诗”(新诗,但篇幅极短,类似绝句、俳句)也将“叙事手段的引入”作为创作实践的途径之一[23]。
《文艺报》2019年1月23日第二版(理论与争鸣)刊登罗振亚《二十一世纪“及物”诗歌的突破与局限》一文,其第一节标题“及物诗歌的优长:和现实的深层‘对话’”指出:“随着诗歌和现实生活交会点的增多和面的拓展,向日常化世界广泛敞开,诗人们自然不会再满足于相对内敛的意象、象征手段的打磨,而尝试借鉴叙事性文学的长处,把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作者以《一个农民在地里侍候庄稼》(白连春)、《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田禾)和《时间简史》(江非)等诗作为例,肯定这些诗“显示出诗人介入复杂生活题材的能力之强”,“使诗歌在抒情之外又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艺术生长点”[24]。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现象不正是显示了抒叙两大传统在新时代的博弈与互惠,叙事和叙事传统俨然成为诗歌发展的一种动力吗?毋庸讳言,我国目前还未拥有杜甫级的伟大诗人,但上述现象所昭示的方向与杜甫的诗史贡献在本质上不是颇有一致之处吗?
这篇论文在第二小节指出了当前及物诗歌的局限,呼吁更多关心时代的大问题,“遗憾的是,如今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接通自我和社会、时代的联系,最终多数人关心的洪灾、反腐、疾患、民生、环境污染等可能寄寓大悲悯的题材被轻而易举地悬置,饮食男女、吃喝拉撒、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无聊琐屑的世俗吟唱无限蔓延,将个人化降格为私人化,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24]。此话意向可嘉,但稍嫌简单绝对,日常生活写得好,何尝不能成史?岂可一概而论!被誉为“诗史”的杜诗,所写也并非尽是时代大事,关键还在于诗人的思想高度和感情质地。倒是其文末段所言颇为辩证:“在明白和朦胧之间取得恰适的点,值得诗人们斟酌。‘及物’的直接反应,是事态、细节、动作乃至人物、性格等叙事性文学要素的强化。‘叙事’在短时间内蹿升到显辞的地位,其结果也势必带来散文化和冗长的流弊,而内视点的诗歌的魅力却在于其含蓄、凝练与惊人的想象力,它的美就在于隐与显、朦胧与晦涩、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因此‘及物’诗歌不可让叙事喧宾夺主,将诗歌引入过于拘谨实在的泥淖。”其所用的语言和切入的角度,与本文有所不同,但所讨论的问题,所指陈的对象,及观点的实质,倒与我们上文所说比较接近,都涉及诗歌抒叙手法的长短优劣,涉及抒叙传统博弈及在诗歌表达中“史性”“诗性”的平衡互益等问题。这些很值得当代诗人和古今诗歌的研究者留意。
结合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可以说,若在创作中能够注意抒叙关系的平衡,在抒叙互惠与博弈的张力之间寻找到最佳位置、最合适比例,既不偏爱,也不偏废,我们的文学才能比较妥善地继承发扬抒情叙事两大传统,做到既见证时代,又反映人心,还能塑造出诗人自己的真实形象,从而达到诗歌艺术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