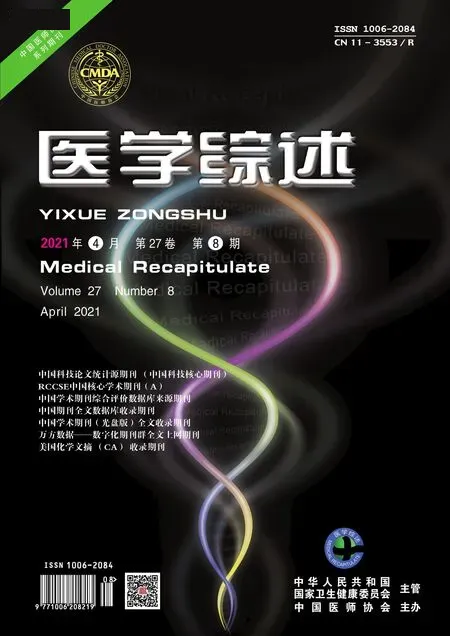肠道菌群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研究进展
王舒静,张烽,童晓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儿科,江苏 无锡 214000)
随着新一代基因测序分析、宏基因组学及代谢组学检测技术的发展,目前肠道菌群成为生物学研究的热点。肠道菌群被称为“第二大脑”,与宿主的消化、营养、代谢、免疫等方面密切相关,是人体“内化了的环境”因素。近年来,随着“肠-脑轴”概念的提出,研究发现肠道菌群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神经系统,与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3]。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一类神经发育障碍疾病,又称轻微脑功能障碍综合征,常见于学龄期儿童。全球ADHD患病率高,且呈上升趋势,全世界儿童ADHD的患病率约7.2%[4-5],我国儿童ADHD的患病率为6.26%[6]。目前ADHD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其发病风险因素涉及遗传、环境以及大脑结构功能异常等方面。在遗传风险因素下,个体受环境因素影响以及相关神经认知功能紊乱的影响,大脑网络功能失调。ADHD临床特征多样化,病理过程不同,发病机制存在异质性,其中涉及肠道菌群与ADHD之间的关系研究。现就肠道菌群与ADHD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肠道菌群概述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所有的疾病都始于肠道”,说明肠道对于人类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体肠道内寄居着数目庞大、种类繁多、并伴随人类共同进化的共生微生物,统称为“微生物群”[7],其中大多数是细菌、病毒、真菌和原生动物。在个体出生后不久,微生物定植已开始,有研究表明,在孕期胎盘、羊水、脐带血和胎粪中均有微生物的存在[8]。出生后新生儿肠道内微生物组成的多样性较低,以变形杆菌和放线菌为主,出生后4~6个月,双歧杆菌的相对丰度可达到峰值[9]。目前公认的肠道菌群金标准是足月阴道分娩以及母乳喂养婴儿的肠道菌群[10]。母乳喂养婴儿肠道中的双歧杆菌水平更高、微生物群落更多、病原体水平更低[11]。婴儿肠道菌群的多样性高于成人[12],3岁以上幼儿的肠道菌群主要为硬壁菌、拟杆菌、放线菌和变形杆菌,它们通常覆盖人体90%以上的细菌总数[13]。肠道菌群是人体“内化了的环境”因素,在人体内构成巨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与宿主的消化、代谢、营养以及免疫等密切相关。
一般情况下,肠道菌群处于平衡状态,是机体健康和免疫代谢的重要组成部分[1,14]。肠道菌群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需氧菌,包括拟杆菌、酵母菌、大肠杆菌等;另一类是厌氧菌,如双歧杆菌、乳酸菌,这些菌群构建了肠道的生物、机械及免疫屏障,保护肠道免受炎症的损害。肠道菌群不仅影响肠道免疫系统,还影响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及疾病的发生,如运动障碍、行为障碍、神经退行性疾病、脑血管意外和神经免疫介导的障碍。肠道菌群主要通过免疫系统[15]、迷走神经[2]或神经递质[16]调控神经的生理功能,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起关键作用。若针对肠道菌群进行干预可能改善疾病症状,如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可改善精神疾病[焦虑症、抑郁症、自闭症谱系障碍、强迫症和记忆能力(空间和非空间)]的症状[3]。多项研究表明,ADHD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胃肠功能障碍,与非ADHD儿童相比,更易出现大便失禁和便秘[17-19]。此外,ADHD患者肠道菌群构成和比例失衡,与正常人群有一定差异。有研究发现,青少年ADHD患者肠道菌群α多样性降低,与多动症状得分呈负相关[20]。
2 影响肠道菌群组成因素与ADHD的关系
ADHD病因不明,涉及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其中环境因素在ADHD的发生中可能起着关键作用,包括围生期风险因素、饮食结构、环境有毒有害物质等。此外,与ADHD相关的环境因素也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
2.1围生期因素 围生期是婴儿开始建立微生物群的关键时期,被认为是通过肠道微生物群调节来影响大脑发育的窗口期[21]。研究显示,ADHD与许多围生期风险因素有关,包括分娩方式、胎龄、孕期应激等;与阴道分娩相比,剖宫产分娩儿童易发生ADHD[22]。对新生儿胎粪的分析显示,剖宫产儿与母亲皮肤中的微生物群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23]。Jakobsson[24]研究显示,剖宫产与肠道菌群多样性的降低和拟杆菌、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的定植延迟有关。剖宫产分娩婴儿肠道中放线菌和拟杆菌属的丰度和多样性降低,相反,厚壁菌门丰度和多样性较高[25]。Talge等[22]研究显示,剖宫产新生儿早期肠道菌群多样性的下降与ADHD的发病风险有关。肠道菌群的组成也受到出生胎龄的影响。与健康足月儿相比,早产儿缺乏双歧杆菌和乳杆菌[26]。据报道,早产儿发生ADHD的风险较高,且ADHD的症状更严重[27]。另外,孕期应激也可影响后代肠道菌群的组成及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母体孕期压力可影响新生儿肠道菌群的组成。Grizenko等[28]研究发现,孕期母体暴露于中重度压力情况下,ADHD患儿的症状更严重。
2.2喂养方式与饮食结构 饮食作为环境因素,可影响儿童罹患ADHD的风险以及ADHD的临床表现和患儿预后。喂养方式和饮食结构影响人类肠道菌群组成和功能[29],婴儿早期的营养是影响肠道菌群组成的关键因素,其中母乳喂养可以显著减少ADHD的发生。母乳喂养婴儿的肠道菌群主要由双歧杆菌和乳杆菌属组成。而配方奶粉喂养婴儿的肠道菌群以梭状芽孢杆菌、肉芽肿杆菌、柠檬酸杆菌、肠杆菌和嗜酸性菌为主;与母乳喂养儿童相比,非母乳喂养儿童ADHD的发病率偏高[30]。
饮食结构中,多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PUFA)对中枢神经系统中神经元的发育和功能起重要作用。研究显示,ADHD患儿血浆PUFA水平低于健康儿童[31]。目前,针对PUFA对于肠道菌群影响的研究大部分在动物模型中完成。饮食缺乏ω-3PUFA小鼠的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比值失衡,补充富含ω-3PUFA饮食后,双歧杆菌丰度更高[32]。
2.3环境毒素 环境毒素(如有机磷农药)与ADHD发病有关,多氯联苯暴露可导致工作记忆、反应抑制和认知顺应性等认知行为改变。儿童ADHD样行为与胎儿期血多氯联苯水平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33]。多氯联苯使小鼠肠道内嗜黏蛋白阿克曼菌、梭状芽孢杆菌和肠球菌的数量增加[34]。
3 肠道菌群在ADHD中的可能机制
3.1迷走神经机制 迷走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控制情绪和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迷走神经-肠-脑轴是多巴胺通路(神经元奖励通路)的组成部分之一[35]。ADHD患儿在执行自我调节和情绪调节任务时,迷走神经反应性增强。中枢神经系统GABA受体的异常表达与焦虑、抑郁有关。肠道菌群(如鼠李糖乳杆菌、长双歧杆菌)分泌的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5-羟色胺、组胺等]可以通过迷走神经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Bravo等[36]的研究发现,益生菌可通过迷走神经调节大脑皮质GABA受体的表达,从而减轻焦虑、抑郁行为。
3.2免疫系统机制 人的免疫系统和肠道菌群存在相互作用,故推测与ADHD相关的免疫平衡受损可能由肠道菌群组成的改变而引发,而免疫调节异常也可导致肠道菌群平衡受损。在许多免疫介导疾病中,机体的免疫稳态被破坏,潜在致病菌增加,导致菌群失调。微生物群的改变可破坏肠道通透性,引起肠道细菌向全身循环迁移(微生物易位),最终导致全身性炎症的发生[37]。全身性炎症和其他因素可能导致血脑屏障的破坏,引起神经鞘炎,从而产生不同的心理问题(如ADHD)。ADHD患者的氧化应激显著增加,氧化应激可导致神经元损伤和神经传递异常,通过诱导神经炎症而导致ADHD症状的发展。肠道菌群可调节氧化应激[38-39],故推测部分由肠道菌群组成改变引起的炎症和氧化应激在ADHD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有证据表明,ADHD患者血清促炎细胞因子水平高于非ADHD人群[40],ADHD患者的血清白细胞介素-6和白细胞介素-10水平升高[41]。血清促炎细胞因子与ADHD症状严重程度相关[42]。粪杆菌具有抗炎作用,其表达异常会导致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粪杆菌失调引起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参与ADHD的发病机制[43]。粪杆菌的丰度与ADHD症状呈负相关,ADHD患儿体内粪杆菌属水平降低[44]。此外,Ceylan等[45]研究显示,与健康人群相比,ADHD患者体内新蝶呤的水平明显较高,新蝶呤是细胞免疫的良好指标,提示细胞免疫可能在ADHD发病机制中起作用。
3.3神经递质机制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ADHD发病与神经递质(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GABA)、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等水平异常表达相关[46-49]。神经递质可能影响细菌基因的表达或细菌间的信号传递,从而改善菌群的构成与活性。肠道菌群也可通过影响神经递质水平,参与ADHD的发病过程。
3.3.1单胺类神经递质 肠道菌群对大脑和行为的影响机制是通过它们合成与宿主神经系统结构类似的神经化学物质或其前体参与疾病发生、发展;肠道细菌可生成和(或)消耗多种哺乳动物神经递质,其中50%的多巴胺和90%以上的5-羟色胺起源于肠道,主要由肠道菌群产生[50]。多巴胺和5-羟色胺两种神经递质在控制人的情绪、幸福感和愉悦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51]。ADHD患儿肠道中肠球菌水平升高,而粪杆菌属水平降低[52]。肠球菌的增加可能使颅内神经突触间隙多巴胺水平降低,影响5-羟色胺的合成[47],促进ADHD的发展。粪杆菌减少与许多变态反应性疾病(支气管哮喘、湿疹及过敏性鼻炎等)有关。特应性疾病患儿ADHD的发生率升高30%~50%[53],推测粪杆菌减少可诱发机体变态反应,影响神经递质释放,诱发ADHD。另外,单胺类神经递质前体也可由肠道菌群产生[54-56],这些前体(苯丙氨酸、酪氨酸、色氨酸)可通过肠上皮吸收,进入门脉循环[50],穿透血脑屏障,影响脑内神经递质的合成。
3.3.2GABA GABA是一种抑制性大脑神经递质,GABA合成功能障碍被认为是ADHD的重要因素之一,ADHD患者GABA水平降低与冲动行为呈负相关[48]。肠道菌群通过分泌和吸收GABA影响其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作用。目前已知双歧杆菌、乳酸菌和大肠杆菌可以分解膳食谷氨酸产生GABA。早期给予乳杆菌干预可提高GABA水平,降低儿童ADHD的发生风险。
3.3.3BDNF BDNF是一种具有神经营养作用的蛋白质,能够促进神经元生长、发育,在记忆和情绪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ADHD成年患者的BDNF水平较低[57]。动物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可以通过产生短链脂肪酸影响BDNF的水平[49],进而间接影响ADHD的发展。
4 肠道菌群在ADHD中的治疗
目前,ADHD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行为疗法、家庭和学校综合干预等。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及不良反应限制了其应用;而肠道菌群在ADHD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故可将肠道菌群作为干预靶点对ADHD进行辅助治疗。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表明,饮食干预(如添加少量ω-3 PUFA)可显著降低ADHD的严重程度[58]。ω-3 PUFA能提高人体肠道微生物群中有益菌的丰度,降低肠道通透性及炎症的发生风险[59]。对益生菌通过肠-脑轴干预儿童和青少年认知功能调节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系统评价显示,补充特定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对儿童认知的影响尚不明确,故需要进行长期来验证益生菌对婴幼儿认知功能发育的影响[60-61]。
5 小 结
ADHD患者存在肠道菌群异常,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通过微生物-肠-脑轴的双向沟通影响大脑的功能和行为,从而影响ADHD的发生、发展及预后。针对肠道菌群特征能否成为ADHD早期识别的生物标志,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有研究显示,肠道菌群的组成和代谢可能受到饮食中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等)的影响,提示可通过饮食干预调整肠道菌群的分布,激发肠道菌群的有益功能,从而改善机体健康状况,故可通过益生菌、益生元和其他营养物质进行饮食和膳食补充可能是改善ADHD的辅助治疗方法[62-63]。肠道菌群和益生菌在ADHD防治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肠道菌群可能是ADHD防治的良好靶点,其作用仍需进一步证实,且ADHD防治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特定有益菌仍有待确定。目前,ADHD的药物治疗效果存在异质性,肠道菌群在不同个体药物代谢中的作用亟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