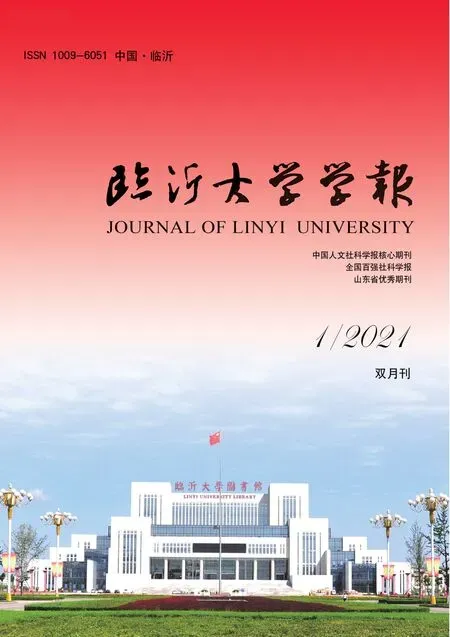劳伦斯长篇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书写研究
庄文泉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文化传媒与法律学院,福建 福清350300)
英国作家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在英国文学乃至于世界文学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他出身于英格兰诺丁汉郡的矿工之家,一生命途多舛,像游子一样常年漂泊于国内外。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创作过诗歌、戏剧、游记和小说,其中最受推崇的是长篇小说。他为世人留下了12部长篇小说,主要包括《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虹》《袋鼠》《羽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西方评论家们对他的评论一直以来都是毁誉参半,一直到20世纪50—80年代,劳伦斯研究才渐渐步入了客观公正的学术道路。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使得英国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典型的英国人变成了城市人,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狄更斯曾在《双城记》中评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1]3在这样一个最美好也是最糟糕的时代,处在工业文明荒原里的劳伦斯奋力地挥动反抗的旗帜,并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和对艺术的独特感悟力从哲学、社会、美学和文化等多个角度重新认知和把握了现实中的城市,并把它们转移到了他所作的多部长篇小说中,构成了其长篇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因此,本文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角度,选取诺丁汉、伦敦、悉尼和墨西哥城四个城市对劳伦斯长篇小说进行剖析。
一、城市书写
(一)诺丁汉:心灵的故乡小城
诺丁汉是劳伦斯家乡的一个小城市,离他的出生地伊斯特伍德镇只有8—9英里的距离。这个初步进入到现代文明的小城市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原本森林茂密、良田万顷之景成为劳伦斯旧时记忆,取而代之的是由铁盒子般的火车、冷漠无情的机器、煤烟弥漫的天空和丑陋的矿坑住宅所构成的灰色世界,满目疮痍又荒芜。正如《儿子与情人》中一开头就描绘了工业革命如黑色的旋涡吞噬了自然的生命,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像蚂蚁打洞似的往地底下挖,在麦田和草地当中弄出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土堆和一小片一小片黑色的地面来”[2]3。在其多部长篇小说中劳伦斯建构了以诺丁汉为背景的城市空间,不难发现劳伦斯对诺丁汉的情感丰富且复杂。但不管是热爱还是憎恨,诺丁汉这座城市牵动着他的灵魂,驱使着他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游走在他文学生命的源头。即使在他颠沛流离、漂泊在外的那几年时光里,劳伦斯对故乡的思念也如不羁的野马在他心上奔腾,从未停止,因为诺丁汉是他至死都念念不忘的“心灵的故乡”。
劳伦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就是以诺丁汉为背景的,小说中多次提到诺丁汉,展现了现代文明对来自农村的乔治等人的心灵冲击,如在第三部第一章中乔治和梅格结婚后去诺丁汉游玩的所见所感:“我们来到山顶,看见眼前的城市就象一片高高堆起的模糊不清的山峦。我寻找着往日读书的那所学校的方塔和圣·安德鲁斯教堂那高耸傲然的塔尖。蓝天下,城市上空一片灰暗,就象一幅又薄又脏的天幕。”[3]343劳伦斯借书中人物之眼描绘了诺丁汉的整体状貌,这座小城带着工业文明的气息迷失在灰暗的烟雾中,似有一件又薄又脏的黑色纱布笼罩住了城市的天空,死气沉沉,毫无生机,这是劳伦斯对工业化的控诉。接着他们又在维多利亚饭店吃饭,去了科威克公园,看了皇家剧院上演的《卡门》。乔治带着既紧张又害怕的心情探索了这座城市,绝大多数的事物对乔治来说是新鲜的,不断挑逗着他的神经,显然此时的乔治是一个受到城市物质生活蛊惑的生动的农民形象。
同样的描写在《儿子与情人》第一章中也有呈现,莫雷尔和他的朋友杰里步行到诺丁汉途中:“城市从他们眼前往高处伸展,在正午炫目的阳光下显得烟雾弥漫,南面远处峰顶上点缀着一座座尖顶、厂房和烟囱。”[2]26从远处眺望,即使是热烈的阳光也穿不透漫天的烟雾,这座城市依旧笼罩在灰色的天空之中,无法挣脱,显而易见工业化痕迹深深烙在了诺丁汉的土地上。第五章莫雷尔太太陪同保罗去见诺丁汉外科医疗器械厂老板,初见小城时他们觉得“这个市镇新奇可爱”,接着“他们来到一条通向城堡的窄街上。这条街又阴暗又老式,有些又低又暗的店面,几家深绿色的大门,上面有黄铜门环,还有黄赭石的台阶伸向人行道。接着又是另一家商店,那个小窗口看起来就象一只狡猾的,半开半闭的眼睛。他娘儿俩小心翼翼地走着,到处寻找‘乔丹父子’的招牌。这正像在某个荒原地区搜索什么东西,他们兴奋极了。”[2]112无法抗拒城市文明吸引的母子二人带着外出历险的那种兴奋心情来到诺丁汉,繁华的背后是狭窄又阴暗的小街,但这也足以让他们新奇激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踏入大工业中心的第一步,母亲为儿子感到自豪。这是工业文明影响下人们对城市情感的真实写照,即使过去那个优美如画的诺丁汉不见踪影,反而变得暗无天日、黯然失色也不能阻止人们前仆后继地加入城市生活,这对那个时代的乡村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
在《虹》第二章中,汤姆·布朗温带安娜去诺丁汉牛市,“男人们穿着笨重而肮脏的鞋子,缠着皮裹腿,路上满是牛粪……所以他带着她又来到了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的牛市。他们最终往回转走出大门口。他老是跟这个那个寒暄着,停下来议论这土地和牛马什么的,……布朗温带她进了缰绳铺一家黑洞洞古香古色的餐馆……”[4]71不得不说,劳伦斯笔下的诺丁汉似乎活过来了,这场景呈现了城市和乡村生活模式的过渡,农民们也走向了城市生活。
劳伦斯对诺丁汉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喜欢诺丁汉的哈格斯农场,热爱着这里的大自然。在这里,他可以同他的初恋情人吉西一起散步看没有遭到破坏的农场风光,一起讨论文学作品,并向她展示自己的创作。但劳伦斯亲眼见证了工业革命如何一步步地吞噬故乡自然的美好,亲身感受到了工业革命对人性的摧残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扼杀,所以他将自己对诺丁汉的认识和态度通过小说中的描写呈现给我们。在劳伦斯的世界中,蕴含了对自然生命力的向往,他高举着反对工业化、城市化的旗帜,首当其冲,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工业文明的排斥。如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借麦勒斯之口表达自己的态度:“我感到人类的世界注定要毁灭,是被自己的卑鄙龌龊毁灭……这一百年来普通人受到的待遇是可耻的,人简直就成了干活的虫子,他们的人性都没了,他们真正的生命都没了。我也想把机器从这个地球上一扫而光,彻底结束这个工业时代,这是个黑色的错误。可我办不到,没人能办到。”[5]229所以从生态观来看,劳伦斯对诺丁汉是憎恨的。我们可以在他的多部小说中听到他对工业文明毁坏了自然美和人性美发出了憎恨和愤怒的咆哮,他也明确说了:“我不想回到城市和现代文明中去,我想过淡泊的生活,想自由自在地生存,我不想受到束缚。”[6]40可以说这种恨和怒说到底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厌恶和憎恨,是对故乡由爱转恨的“恨铁不成钢”。
(二)伦敦:爱恨交织的英国首都
伦敦是英国的首都,经济、文化中心,离劳伦斯的故乡伊斯特伍德只有200英里,20世纪初的伦敦已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1908年,劳伦斯诺丁汉大学毕业后就到伦敦近郊克罗伊登的学校教书。对当时来自矿工之家的劳伦斯来说,来到伦敦生活是与乡村生活截然相反的另外一种生活,除去刚开始的害怕,伦敦似乎有种魔力深深吸引着青年劳伦斯。正如吉西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安顿了下来开始写他的《白孔雀》的第三稿,他开始观察起伦敦来,写信向我们描述在夜晚降临时的满城街灯……”[7]111对都市的向往引领着劳伦斯一步一步地走近伦敦。
劳伦斯对伦敦的喜爱在《白孔雀》一书中有所流露:“春天的脚步勇敢地踏进了伦敦南区,使城里充满了奇异的魔力。直到我亲眼看见闪亮的圆形弧光灯在公路两旁紫红色薄暮中象金色的气泡在滚动时,才见识了紫红色的夜晚那富丽堂皇的气派。城市的夜晚处处都展示着灯火的奇妙世界:明灯把团团金光撒在泰晤士河面上,给不安的黑夜晚增添了浮动的光彩。洞穴似的伦敦大桥车站进进出出的车灯,好像滚圆闪亮的蜜蜂从黑色的蜂房里飞进飞出,郊区的街灯在树丛中闪动着柠檬色的光彩。我开始喜爱这座城市了。”[3]356伦敦被五光十色的灯火点燃,整个城市像笼罩在梦幻之中,变得更有温度。这时的劳伦斯怀揣着好奇的心情在夜里欣赏满城灯火,迷恋上了伦敦。在《虹》中,也有关于城市灯光的描写:“灯光——城市的制服,是个鬼把戏,走着坐着的人不过是陈列的假人。”[4]404-405富丽堂皇的城市灯光更像是蛊惑人的一层银纱,看似楚楚动人,却掩盖了城市的冷酷无情。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早已变成空洞的幽灵,只追求物质的满足,行尸走肉般机械地生活着。但劳伦斯对伦敦城的夜色无疑是欣赏的,这是最现代化的都市夜景。
在《儿子与情人》中,威廉在伦敦找到了年薪一百二十英镑的工作,这让莫雷尔太太倍感骄傲。但好景不长,威廉由于过劳而死于伦敦,此后伦敦成为了保罗一家人心中的不可愈合的创伤。《儿子与情人》的出版,使劳伦斯真正走进伦敦,在伦敦绽放闪耀的光彩。可以说伦敦成就了他,却也毁了他,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猝不及防地如冰雹重重击打在他身上,他呕心沥血所著的小说《虹》惨遭查禁,同样的查禁遭遇也发生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上。可怕的是厄运还没有结束,1918年他被怀疑为德国间谍,被逐出康沃尔,又回到了伦敦,过着丧家之犬般的生活。这些遭遇使他对伦敦,对英国倍感失望与痛恨,所以战后,他便迫不及待地离开英国。黑马在翻译《袋鼠》时,通过一段话真实描绘了那时候的场景:“离开了英国,离开了他苦苦爱着的英国,形单影只,只觉得万般情感无以言表。这天很冷,海岸上白雪覆盖的锚地看似尸布一般。当他们的船驶离福克斯通港后,回首身后的英国,她就像陷入海中的一口阴沉沉的灰棺材,只露出死灰色的悬崖,崖顶上覆盖着破布一样的白色雪衣。”[8]281而且在劳伦斯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提到“不论是伦敦还是英国,都使我感到十分厌倦”[6]489,“伦敦对我来说具有排斥力,而不是吸引力。我宁肯逃到天涯海角,也不愿朝着这个世界的大都会走去”[6]547。可见,劳伦斯与伦敦有着解不开的结,他无法原谅伦敦对他的迫害。即使曾经他狂热地爱着伦敦城市的灯光和舒缓柔媚的丘陵,但最终只能带着爱恋、痛恨和痛苦离开这座城市。
关于伦敦的描写还没有结束,在《恋爱中的女人》第五章伯金奉召去伦敦的途中,对杰拉德说他厌倦了“艺术家——音乐家——伦敦那帮放荡不羁的文人们,那帮小里小气、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艺术家们”[9]54。而且每当临近伦敦时,伯金就感觉自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产生了对人类的厌恶,犹如要进到地狱里。他说:“每当火车驶近伦敦时,我就感到厄运的降临。我感到那么绝望,那么失望,似乎这是世界的末日。”[9]56甚至在进入伦敦后,伯金对杰拉德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这是真正的死亡”。可见劳伦斯笔下的伦敦城已然变成一座牢笼,困住了生活在里面的人,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变得一片乌烟瘴气,毫无生气可言。这里借两个人物的对话,展现了伦敦带给伯金的强烈的感受:丑陋、绝望、失望、厌恶等,也明确地传递出劳伦斯对伦敦的厌倦之情。甚至在第二十八章中,戈珍在坐火车离开伦敦时,望着铁桥下的河水叫道:“我再也不要见到这肮脏的城市了,我一回来就无法忍受这地方。”[9]374似是对于伦敦的恨都要在这一刻呐喊出来。工业文明侵蚀了伦敦的身体,退去激情的生命力的伦敦只是个满目疮痍的尸体。他对伦敦的态度已经从迷恋转为痛恨,就如在《出走的男人》中,借坦妮所言“我痛恨伦敦”来表明此时劳伦斯对伦敦的情感。
劳伦斯成在伦敦,败也在伦敦。他曾狂热地喜爱着伦敦,但显然伦敦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于是他带着爱恋和痛恨进行了自我流放。
(三)悉尼:虚幻而孤独的现代大城市
悉尼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南沿岸,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1922年,经历了“一战”精神迫害的劳伦斯,带着遍体鳞伤的身躯和对英国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乘船来到了澳大利亚港口城市悉尼。在这虚幻而孤独的城市,劳伦斯伴着海浪击打岩石的声音,在对故乡无声的思念与诅咒中,执笔写了一部以澳大利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袋鼠》。劳伦斯曾在写给岳母的信中提到:“悉尼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城市,它一半像伦敦,一半像美国。悉尼港好极了,在两个峭壁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入口,驶过这条水道就是一个小海,有许多港湾……但是这儿是一个奇异、阴郁和悲哀的国度,那么空旷,就好像永远也住不满似的、未开垦的土地无边无际,显得凄凉,空虚。到处都给人这种感觉。然而,悉尼是一个现代大城市。我并不很喜欢这个国家,那么原始,那么粗糙……”[7]287-288劳伦斯喜欢悉尼的蓝天、空气和大海,在这里他感到自己像个孩子,没有真正的忧愁。也正是悉尼水晶般湛蓝的天空,美丽广阔的土地和原始粗糙的风光,成就了书中一幕幕不朽的澳大利亚图景。也正是在澳大利亚,劳伦斯看到了建立乌托邦的可能性。但悉尼的空旷使他感到凄凉和空虚。
《袋鼠》中描写悉尼的片段比比皆是,初到悉尼时,索默斯所见之景:“尽管是在这庞大喧嚣的现代化悉尼的范围内,百万人流如鱼儿从城中穿过,那片地方看上去似乎也像地球上消失了一般。……那庞大的悉尼城就在眼前,可它显得虚无缥缈,倒似乎像喷洒在黑暗之上,它永远也无法穿透那黑暗的表层。……黑夜笼罩着悉尼,山下,那城市和海港灯火明灭,闪着微红的光影。……这不能不令我们的诗人再次感到恐惧和焦虑。”[8]5-11在劳伦斯眼中悉尼是一座虚无缥缈、广袤粗粝的城市。这里有可以与伯明翰相提并论的漂亮大街,公园、植物园以及悉尼港都是这座城市的特色。但这里又过于庞大空旷,“就好像永远也住不满似的”,给他带来对未知的恐惧和焦虑。“悉尼则到处是无数相互分离的平房和村舍,一片片蔓延开去,散落在高高矮矮的山包上和斜坡上。还有那些荒凉的沼泽,废弃的铁矿,波纹铁‘产品’,这一切看上去就形同末日,而绝非新的国家。”[8]78这片国土“没有中心,看似空洞一般”,似乎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可亲近。
深入到悉尼这座城市,索默斯发现“这座城很是没有实感”,是荒凉、迷茫的。“悉尼那炎热而自由自在的大街,没有丝毫的控制感。没有控制,每个人都小心走路,以不妨害别人。在便道上,步行者形成两股分开的人流,分别靠马路左边走。可在悉尼,压根儿没有什么权威的威严。这里有的是没有权威的绝对自由,空气中弥漫的是十足的自由。……”[8]335深入体会悉尼,劳伦斯发现这片辽阔空旷、风景优美的土地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隔着一道银河,每个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不轻易打扰别人。这种不真实使他感到空旷和荒凉。所以即使风光再秀丽,也无法达到劳伦斯对心灵相通和精神共鸣的追求。而且劳伦斯发现这里的民主远不是他希望的那种高度自觉的民主,所以带着孤独感、恐惧感和失落感,劳伦斯告别了澳大利亚,打破了他乌托邦的幻想,继续踏上寻找他理想之地的路途。
(四)墨西哥城:封闭而排外的古老城市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国家,首都是墨西哥城。1923年3月,劳伦斯夫妇南下来到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羽蛇》的灵感之地——墨西哥,他的足迹踏遍墨西哥大大小小的城镇,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劳伦斯曾写信给友人描述他们的生活:“这地方很荒凉,松林从山上延伸到山下,海拔八千六百英尺,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这儿的环境。但是,这儿风景也很美丽……在这儿的宁静气氛中,有某种粗犷、不可损害的东西——那就是夜晚印第安人的鼓声和喊叫声……”[6]495-497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这里古老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原始的宗教信仰都强烈地冲击着劳伦斯的内心和灵魂。他发现也许这座城市古老的文明能够复活失落的工业文明,带着这样的想法他满怀激情地写下大量文章,想借此为失落的欧洲文明点亮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在《羽蛇》第一章中凯特在看了血腥的斗牛表演后忍无可忍,中途离开这残酷又肮脏的斗牛场:“她有点凄然,透过雨幕,呆呆地望着大门,蜷缩在发白制服里的士兵,外面脏乱不堪的街道,以及街上狂流的脏水。行人都在避雨,在肮脏的棚子下,在乱糟糟的小店里。最使凯特不安的是她对这座城市的反感、恶心。”[10]17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凯特的视角描绘了雨中的墨西哥,借凯特的心理表达了对这座城的态度:反感和恶心。“她去过许多国家的许多城市,只有墨西哥城最让她讨厌,这个城市有着一种内在的、深刻的丑,那是一种丑恶的幽灵,在这个城市的对照下,即便是破烂的尼泊尔也令人愉快。她怕,她真地怕这个城市里的任何东西碰到她,怕因此而染上城里到处游荡着的幽灵的气息。当然,她知道目前最切要的是保持头脑清醒。”[10]17在凯特的眼中,墨西哥城“到处都是潜藏的丑恶”,破败的景象、肮脏的街道、凄然的雨天给人一种空洞感。墨西哥城人血管里流动着古印第安人那沉重的、富有对抗性的血液,他们容易激动、恼火、野蛮以至疯狂。这里让她恐惧、不安和厌恶,但同时印第安人原始的古老的力量又深深吸引着她,使她开始了漫长的朝圣之路。
第四章写道:“墨西哥!这个巨大的、深不见底的、危险的、干燥而野蛮的国家!每一个景区都有一个犹如虚无中产生的美丽的教堂,然而,大革命摧毁了它们,圆顶被破坏,尖塔被推倒。风景区也被夷为平地”[10]84。第五章写道:“而整个墨西哥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不管是什么新建筑,抑或任何意义上的一种进步,只要不是在首都,总是半途而废;就建筑而言,或者是完工了,但不久即被搞的不成样子,或者根本没完工就丢下不管,一副乱糟糟的样子。”[10]101墨西哥城的建筑被不同程度地毁坏,凝聚着建筑师心血的石头已然死去,古老的尘埃弥漫在墨西哥城,一种神秘而无情的气息紧接着包围了这座城。城市的颓败之感迎面而来,是一种恐怖的僵硬和压抑的空洞。这是劳伦斯对大工业的控诉,是劳伦斯对20世纪墨西哥城的深刻感受和真实写照。
青年时期的劳伦斯便怀揣着“拉纳尼姆”的理想,在一生的旅途中,他不断追寻着实现其理想的地方,最终他选择了墨西哥作为开启理想世界的一把钥匙。为此在《羽蛇》中创造了新的神——克斯卡埃多,他想用一个现代人放弃基督教信仰转而寄托于印第安原始宗教的故事给欧洲人指明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以抵抗欧洲文明。但最后墨西哥城没有改变劳伦斯离开的决心,因为墨西哥是封闭的、排外的,在这里他没有归属感,而且另一方面他的心脏另一端也系着他“心灵的故乡”——诺丁汉。
二、城市书写的地理基础
著名学者邹建军教授指出:“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甚至任何作家与作品,都存在一个地理基础与空间前提的问题,因为任何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任何文学类型也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起来,任何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类型绝对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存在。”[11]32的确,作家的现实生活活动是文学活动的前提,即文学从现实生活汲取创作的材料,反映现实地理基础,表达作者的真切感受和实践生活。劳伦斯的长篇小说与其地理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对诺丁汉、伦敦、悉尼以及墨西哥城的体验为他创作长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城市在他长篇小说中都有不同的呈现。正如拙作所指出的:“他的一系列文学创作与他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和创作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他所接触和感知的自然山水有密切的关系。”[12]38因此,研究劳伦斯长篇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就必须要去关注和了解其地理基础。
诺丁汉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也是英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劳伦斯就出生于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镇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劳伦斯曾回忆:“巴特利,阿尔弗里顿,第伯谢尔夫,这些属于哈德威克地区的地方组成了现在的诺丁汉——达比煤矿区。这里的乡村依旧,但矿井和矿区星罗棋布,满目疮痍。”[13]42可见,蕴含丰富煤矿资源的诺丁汉成为贪婪的人类不断索取物质的城市,城市乌烟瘴气也成为劳伦斯抹不去的灰色记忆。
1898年,劳伦斯从伊斯特伍德镇小学毕业,得到了他所在小学第一个由镇政府奖学金资助进入到诺丁汉中学学习的机会。之后,为了学习他每天往返诺丁汉与伊斯特伍德小镇。劳伦斯在诺丁汉中学的这段学习生涯中,受到了中产阶级学校的良好教育,这为劳伦斯文学创作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1年,劳伦斯中学毕业后,在二哥的帮助下,进入诺丁汉一家外科医疗器械工厂,他的职责是将法文和德文的订单翻译成英文。但不久劳伦斯就因患肺炎离开。在回家养病的这段时间,他常出入海格斯农场,结识了钱伯斯一家人。这里成为劳伦斯的“避难所”和“休养院”,让他感受到了自然的秀丽风光和在农村淳朴生活的乐趣。这段时光对劳伦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康复以后,他在伊斯特伍德小镇小学当教师,同时开始创作诗歌和小说。三年的乡村小学教学生涯让劳伦斯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矿工家庭。1904年12月,劳伦斯参加了国王奖学金考试,获得了一个培训学校免费生的资格。在下一年的6月他通过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考上了诺丁汉大学。就在这一年中,他开始创作《白孔雀》。直到1906年9月,他才进入诺丁汉大学。吉西回忆道:“虽然他进了大学,但劳伦斯并不想攻读学位。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写作而并非在于他的学业。”[7]49诺丁汉的工作和学习生涯为其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成为他构建城市空间的依据。他带着对文学的热爱在这座初步繁荣的城市起航。
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也是欧洲最大的城市。1908年,劳伦斯诺丁汉大学毕业后就到伦敦近郊克罗伊登的学校当小学助理教师,并且继续进行创作。初到伦敦的劳伦斯被这个城市深深吸引,他在这个城市里探索未知、开拓眼界以及体验不同于乡村生活的都市文明。在他沉迷于伦敦迷人生活的同时,他的初恋女友吉西将其诗歌投给了新潮杂志《英国评论》,杂志的编辑休佛因此发现了劳伦斯的才华,不仅帮助他发表诗歌,还成为他进入伦敦文学圈的引路人。休佛带着劳伦斯参加各种名流聚会,在此期间劳伦斯结识了许多文人名流并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这样的生活被劳伦斯的母亲莉迪娅患病打破,他开始奔波于克罗伊登和伊斯特伍德小镇之间,照顾重病不起的母亲。1911年劳伦斯的伦敦文学生涯以他患病而终止。1912年,康复后的劳伦斯与诺丁汉大学语言学老师威克利教授的妻子弗里达一见钟情,两人告别了家乡,私奔到欧洲大陆。
直到1913年,《儿子与情人》在伦敦出版,载誉归国的劳伦斯又开启了伦敦的社交活动,成为来自矿区底层的文学界天才明星,受人追捧。但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劳伦斯的长篇小说《虹》因在文中发表了谴责前些年英国发动的布尔战争而遭到查禁,自此英国出版社不敢再出版劳伦斯的小说,他也变成了声名狼藉的作家。而且由于没有出版费的支撑和伦敦物价的上涨,劳伦斯只好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城市,避居在英国的西南角康沃尔。然而,对他的迫害还没有停止,在英德战争时,因妻子弗里达德国人的敏感身份,夫妇二人被怀疑为德国间谍,被赶出康沃尔,又回到伦敦,受到来自官方的监视。战争毁灭了劳伦斯对自己国家和那个时代的信念。1919年10月,熬过大战且筹备已久的劳伦斯离开了英国。自此,劳伦斯如匆匆过客只在1923年、1925年和1926年短暂地停留在伦敦。劳伦斯在伦敦的文学界绽放了属于他的光彩,但也在伦敦从最高峰坠入低谷。
劳伦斯于1922年5月4日在西澳大利亚的珀斯上岸,在西澳大利亚,劳伦斯感受到了天高气爽的气候和蔚蓝清新的天空。他们在这里游走了半个月,但没有被珀斯和达林顿的风光留住。在5月18日,劳伦斯夫妇乘船来到了悉尼,但是由于悉尼的物价过高,他们选择住在距离悉尼40英里的一个海边衰落的度假小村瑟罗尔的一栋平房。据弗里达回忆:“那些悉尼的铁皮屋顶就在眼前,优美的港湾,可爱的太平洋海岸,空气那么清新。我们在悉尼住了一二天,两只孤独的鸟栖息了片刻。”[7]283在这里,劳伦斯伴着海浪冲击礁石的声音,在对故乡无声的思念中,挥笔写下了以澳大利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袋鼠》。弗里达还回忆了他们的生活日常:“我们沿着海岸漫步,孤独,隐秘,犹如仍处在母胎中一般,气候温和,并充满了生机,海岸那么美丽,我们流连忘返,一连几个小时地捡贝壳,太平洋的潮水把它们温柔地送上了沙滩。劳伦斯怀着虔敬的心情读《悉尼快报》。他很喜欢这份报纸,因为它载有野生动物的故事和风土人情。”[7]284悉尼的自然景象和风土人情给劳伦斯带来全新的体验和灵感。
1923年3月,劳伦斯夫妇从美国墨西哥州的陶斯南下来到了墨西哥。他游走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曾和梅布尔·道奇卢汉参观古老印第安的文明。据弗里达回忆:“在博物馆里,在阿兹特克遗物中间,我们看到了盘着的蛇和别的骇人的石雕。马克西米连举行隆重礼仪用的四轮马车,把我带到了我的童年。”[7]301墨西哥城中的古印第安文明和最原始的宗教信仰特别是阿兹台克的羽蛇神使劳伦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关于墨西哥城的描写我们可以在劳伦斯的长篇小说《羽蛇》中轻易找到。并且劳伦斯发现也许这座城市古老的文明能够抵抗工业文明。为此劳伦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无论如何,我要在墨西哥完成我那本关于墨西哥的长篇小说《羽蛇》。”[6]501
三、城市书写的意义
“劳伦斯长篇小说里的地理意象呈现与地理空间建构,与其长篇小说的情节发展、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审美创造等存在着诸多联系,研究其地理诗学问题,可以有效地破解其所有长篇小说中存在的多重思想与艺术密码。”[12]41因此城市书写集中构建了劳伦斯长篇小说中的“城市空间”,而通过城市空间建构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劳伦斯作品的独特价值。
城市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随着工业化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城镇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也不断在扩大。劳伦斯出生的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镇因为煤矿资源丰富被现代工业文明所青睐,使得当地由原来的自然秀丽风光变成混乱不堪、乌烟瘴气的矿区空间。这种直观的经历,是劳伦斯痛恨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的起源。此外,他一生走过许多城市,见证了城市创造出的前所未有物质文明成果为现代人带来的新的体验和享受,但他没有被城市物质文明的表面所迷惑,反而对城市文明的出现对人性的扼杀和人类精神的摧残表示深深的担忧。正如他在诗歌《新房屋,新衣服》中写道:“新房屋,新家具,新街道,新衣服,新被褥——机器制造的一切新的物品/从我们的身上吮吸我们的生命,我们拥有得越多/反而越没有活力,变得冷酷。”[15]181因此,工业与大自然的冲突一直是劳伦斯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而为了凸显这个主题思想,他将自己对城市的认识和体验写进他的小说中。
在劳伦斯看来,城市是人类异化的中心,在城市生活的人如同行尸走肉成为机器的工具和资本家的奴隶。劳伦斯的诗歌《蚊子知道》:“蚊子深深地知道,自己虽然渺小,却是噬血的野兽。然而毕竟/他只会填饱肚皮,不会把我的血存入银行。”[14]190劳伦斯对资本家贪得无厌榨取人们的劳动成果进行了讽刺。劳伦斯的长篇小说通过对城市的描绘揭示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并通过小说中的人物间接表达对城市的态度并塑造人物形象。如在《儿子与情人》中通过莫瑞尔的家庭矛盾,说明他们所处城市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摧残和破坏。此外,劳伦斯对城市情感的表达不仅可以引起我们对当今自然生态、人的精神生态等问题的关注,而且可以引发人们对人类生存与自然存在,人类与自然、社会、自身如何相处等众多问题的思考。
四、结语
劳伦斯一生漂泊在外,流浪过许多城市,这段经历犹如一段匆匆闪过的旅游纪录片,带给劳伦斯不同的触动和无数的灵感。在他的长篇小说里,颇具前瞻性的劳伦斯直接表达了对城市文明的批判,他认为城市的发展使人类文明异化,使人类社会中的关系扭曲,且城市工业化还破坏了自然环境,污染了城市空气。劳伦斯在《城市的生活》一诗中写道:“当我身处伟大的城市,我知道我很绝望/我知道这里没有我们的希望,死亡在等待,关心是无用的/哦,对于那些贫穷的人们来说,那些像我一样有血肉之躯的人们/我,有着和他们一样的肉体/当我看到钢铁如鱼钩一般钩住他们的脸/他们那枯槁、充满恐惧的脸/在我灵魂的深处,我哭喊,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够/把铁钩从他们的脸上拿开,那铁钩把他们弄得如此憔悴/也不能把那无形的、困住他们的铁丝斩断/来又去,工作/来又去,工作/像上了钩骇人的、僵尸一样的鱼,被某些邪恶的、站在隐形岸边的渔人戏弄/他仍不把他们放下钩,这群工厂世界的上钩的鱼。”[15]130可见身处城市空间的劳伦斯从灵魂深处感到绝望,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人如没有思想的提线木偶般被工业社会操纵着、戏弄着,他们失去思想和人性,沦为机器的附庸,对此劳伦斯倍感痛恨。为了使人们摆脱这种困境,劳伦斯在20世纪的工业荒原上奋力寻找着出路,试图用原始的文明、血的意识和自然的生命力来拯救苟延残喘着的欧洲社会,也因此为我们留下极其珍贵的20世纪30年代前多个城市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