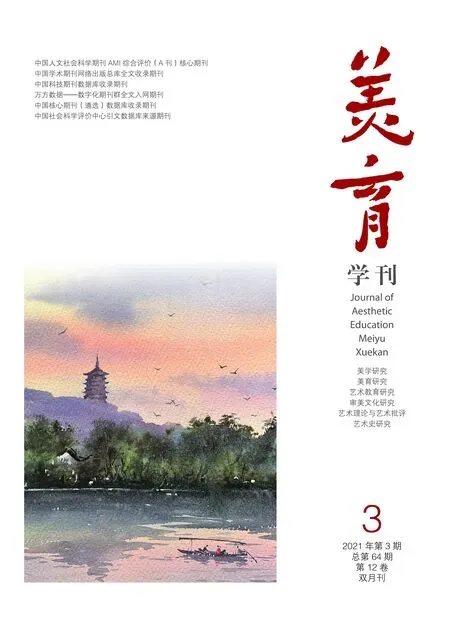从自然到政治的进阶
——论阿兰·布鲁姆的美育观
孙云霏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师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被誉为施特劳斯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作为古典政治哲学大家,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就是引导“资质较好的子弟”从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而引导的方式就是进行柏拉图《理想国》式的教育。我国学者甘阳将政治哲学与教育二者间的关系概括为,“‘政治哲学’基本落实为‘教育’,即通过在大学里从事‘自由教育’来影响未来公民和立法者”[1],也就是政治哲学需要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教育的最终目的则是实现政治哲学。“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指以文化为内容的教育,具体方式是谨慎地研习最伟大思想家的经典著作[2]1(主要是政治哲学著作)。布鲁姆无疑继承了施特劳斯的教育理念,但他引入广义的“诗”(即文学)来丰富政治哲学的内涵,认为哲学并非纯然理性的,因而将感性的诗排除在外,相反,哲学是感性地探讨根本问题、教化普通民众。在教育的具体方式上,绎释的经典也就不再仅限于政治哲人的著作,而是扩大至文学领域,包括莎士比亚、卢梭及其后继浪漫主义者的文学经典均在其绎读范围之内。这样,布鲁姆不仅强调理性地获得知识、塑造品格,而且注重培养学生对美的感悟能力,在文学教育中实现从自然到政治的进阶。布鲁姆的美育观既针对当下大学教育的弊病,又在逐层剖析后返归经典,从中追问教育如何对人的自然天性予以引导、使之升华,既提出问题又不回避问题的解决,具有迥异于激进左翼的独特面相。
一、大学教育的现状与现代自由主义
1955年,年仅25岁的布鲁姆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此后分别任教于耶鲁、康乃尔、特拉维夫、多伦多等世界一流大学,最终回到母校芝大的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多年一线教学的经历使布鲁姆对大学教育的现状有着直接了解,其出版于1987年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ClosingofTheAmericanMind)即是摆出美国大学和学生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分析现象背后予以支撑的社会观念,这引起了从当时延续至今的学界热议。
在他看来,时下的大学教育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在学科设置上,伴随科学发展所要求的专业化以及劳动分工所要求的熟悉度,大学着重于培养学生熟练地掌握某一领域的相关知识,鼓励学生在单一领域内成为专家,因此对学科和课程进行专门化、精细化的设置。并且在师资力量和奖学金分配等必要的经济投入上配合既有的学科设置,比如大部分从事教学的教授都是专门领域的专家,康奈尔大学设置福特基金会以雄厚资金支持确定专业选择的学生等。即使部分大学开始意识到学科专门化和专才教育的弊端,逐渐添加“选修课程”“组合课程”来鼓励学生进行跨专业、跨领域的涉猎,但这种设置往往流于简单拼接的表面,既不能引导学生深入地思考专业问题,也不能引导学生超越课程本身、去探索关乎人性的永恒问题。其次,从学生角度来看,他们一方面被课程设置和市场需求束缚在特定的专业领域,缺少对其他领域或问题的钻研兴趣,缺乏对课程之外的、非实用性的自我精神和品格的关注。另一方面受当下社会中的文化相对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的影响,未经思考便激进鼓吹在大学中实现民主和平等,反对传统上的师生不平等关系,狂热地参加各种形式的学生运动,最终致使盲目的激情超过理性,出现康奈尔大学黑人学生持枪要求教员们放弃大学的评判制度这类暴力事件。最后,从教师角度来看,他们被置于传统人文理想与现代效用要求的两难处境之间,前者往往是无功利的、持久性的,后者则着眼于实际利益的快速获取。这就要求其向社会现实进行妥协,舍弃耽于冥想的人生问题和重要的政治问题,转而向学生传授专门的、快餐式的知识,以及顺从学生所谓的自我培养的要求。
布鲁姆严肃地指出,从学科专门化到学生民主运动,这些大学教育的特征表象反映了教学和研究领域的深层次危机,揭示出“在我们用以解释世界的那些基本理论之间,缺乏连贯性和和谐性”[3],也就是不再有学科对自然和社会中一般性的、重要性的问题进行探讨,更确切地说,人们已经丧失探讨这些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姆并没有止于摆出问题、点出危机,而是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视域出发,逐层分析产生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众所周知,当今人类科学体系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门类。但三者的发展并不平衡,自然科学认为自身是独立的、中立的,能够做到门类自足并以看似客观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渗透进人文社科之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分析法,即为了获知一个整体,需要把它分解或分析成各个要素,拆分得越细致,得到的精确度就越高。这种研究方法渗透进人文社科中,所带来的就是学科上日益精细的专业化。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由各个要素重组和重建而成,以达至对整体的认识,要素间不存在价值冲突或分歧。这渗透进人文社科中所造成的就是统一价值的丧失,各要素都有其存在的不同价值,因而人文社科成为一个多元价值共存的领域。概括来说,自然科学向人文社科进行渗透所产生的是文化相对主义,自然科学是危机的原因,相对主义是危机的实质。虽然曼特(A.J.Mandt)对布鲁姆的观点持批判态度,但他准确地指出了相对主义在布鲁姆处的内涵,一是指缺乏可行的、可信的方法去做出价值判断,也就没有价值判断,二是指这种“认为每一观点和每一行动都与其他的一样好”的观念落实到生活中,会造成对生活的意义贬低和虚无主义,以及主体在毫无目标后所进行的自我放纵[4]。
如果说自然科学对人文社科的渗透造成了相对主义的危机,那么是否需要进一步发问,为什么人文社科能够被渗透?如果人文社科自身始终关注品性上的至善和生活中的善好,自然科学是无法对其渗透的。那么人文社科原有的形而上价值又是如何于内部瓦解的?从施特劳斯至布鲁姆的古典政治哲学的观念认为,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将爱欲与共同体关联起来,既注重人性的整全和完善,也注重人与人间共同体的建立,并且前者是后者得以存在的条件,只有具备卓越丰厚的自然本性的个体,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对他人的爱欲和对共同体的需要,并在共同体中超越本性的最利己的部分。但自霍布斯和洛克以降出现了现代自由主义思想[5]8,其既否认存在人的完满,也否认通过人的提升而达到人类社会的完满,而是主张每个个体都被自身的欲望所引导,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善恶或道德,只存在个体去全力实现欲望以及个体间为实现欲望而产生的冲突。布鲁姆指出现代自由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就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性本能理论。因揭示人的潜意识领域和非理性维度而对现代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性学,在布鲁姆看来却是一种生物学上的还原论,它将包含有想象活动的爱欲简单地还原为性行为,将伴侣间相互吸引、微妙互动的“爱”转变为可操控、可缔结的“关系”。可见,自然科学对人文社科的渗透仅是造成相对主义的外因,更深层的内因在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在其中人与社会丧失了自然的起点和至善的终点。
因此,要克服当下大学中的,乃至美国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的相对主义危机,就需要恢复人的整全性,使人自发地追求美好品德,并自然地结合成共同体——这些目标都需要教育来予以实现。在布鲁姆看来,教育的具体途径是阅读具有伟大传统的经典著作,“这些书能把各种研究整合起来并将它们与生活的关联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这种书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教育,而且是道德教育——就它们使读者涉入对善好生活的关怀而言”[6]381。“经典”并非指后现代意义上所谓的由权威和权力确立的,因而要予以推翻或解构的书籍,而是指书中探讨了有关人的重要性和永恒的问题,它们经过理性辨识,并使人终生追求与捍卫。阅读经典能够让人从庸常生活、时代常识中解放出来,逐渐上升到更高的思想境界,从而达至人的整全。
布鲁姆所持的阅读经典的观念既与其老师施特劳斯,又与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哈钦斯(R.M.Hutchins,1899—1977)有密切关联。哈钦斯任芝大校长期间,极力反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推进面向所有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n),并且成功地改革了芝大学院(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使其教育体系建基于“伟大的作品、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综合测验和大学预科”[7]之上。他在为自己主编的54卷本“西方世界的伟大作品”丛书所撰写的导言中提出,博雅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人去过一种人性的生活,使人成其为人,而进行博雅教育的途径则是阅读“伟大的作品”。他反驳认为阅读前现代作品是无用的这种观点,指出诸如“什么是善的生活,什么是好的国家”此类的问题具有根本意义,不同时代的伟人都对它予以思考和回应。因此,阅读“伟大的作品”应在本科生教育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可以说,布鲁姆既是哈钦斯在芝大进行教育改革后所培育出的优秀学者,也是其主张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二、美育的核心:从自然到理性的升华
早在施特劳斯处就已对古典政治哲学和教育间的关系予以高度关注。在他看来,哲学探求的是最重要的事物、最广泛的真理,因而处于最高级的位置。教育则是帮助人从庸常生活和时代常识中解放出来,进而上升到哲学高度,换言之,教育作为达至哲学的手段和途径。并且他主张,“自由教育,特别是人文艺术教育是为哲学准备的”[2]13,这就意味着,哲学凭借纯然理性去思考永恒问题,因而超越了人文艺术中的感性存在,人文艺术仅仅起到辅助作用、居于次要位置,并最终在至高至善的哲学里被扬弃。从施特劳斯绎释的经典主要为政治哲人的著作中,也可略见他对政治哲学与人文艺术的高低评判。
布鲁姆继承了老师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和教育间关系的论说,但他并不认为存在一个高度理性的哲学领域,人文艺术仅是达至它的手段,而认为政治哲学与人文艺术(即广义的诗)难以被截然地区分开来,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政治哲学方面来看,传统的政治生活包容着德行与激情,政治领袖也兼具才能和魅力,至高的哲学是可以被感性地谈论的,并且因感性而呈现出属于人的丰富,也因感性而更能触动人的灵魂。从诗的方面来看,自浪漫主义至现代主义都认为诗应当远离意图和目的,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否则就会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导致诗成为日益唯美却愈加无用的装饰品。但诗在它的源头处就已建构政治场景、歌颂政治领袖,并且广泛地探讨统治者品性、朋友间关系、公民的职责等问题。因此,存在“另外一种哲学——可以感性地讨论人类事物的哲学,以及另外一种诗——将优美的激情和严格的理性统一起来的诗”[6]53。概括来说,在施特劳斯那里至高至善的哲学,被布鲁姆发展为融合了政治哲学与诗、德行与激情、理性与感性的人性真理。布鲁姆对诗人也是大为赞誉,认为诗人既要洞察真正永恒的人类问题,在诗中模仿人的行为、传达政治智慧,又要深入理解与之对话的读者,运用卓越的艺术技巧吸引他们,并隐藏技巧的痕迹。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布鲁姆提倡的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教育:之所以是审美的,不仅因为审美作为一种教育方式,更因为审美本就是人的感性存在、本就关涉人性的根本问题。而教育即培养学生去阅读融合了政治哲学与诗的伟大作品,使学生从中领悟到最自然的人性,继而跟随伟大作品的理性引导,让自然的人性予以升华,最终达至人的整全和完善。布鲁姆在其重要著作《爱与友谊》(LoveandFriendship,1993)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从自然到理性的升华过程。
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契约(尤其是商业契约),并且单独的个体被束缚于集体契约。应当说,早在启蒙运动时期,霍布斯就已经提出这一观点。他认为,自然人是具有快乐的感觉主义的个人,这种个人的典型特点是主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以及道德上的虚无主义。然而,个人对潜在的危险感到极度恐惧,为满足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愿意放弃部分自然权利,允许他人具有同自己一样的权利,以期让自己能被他人同等对待。由此,人与人联合起来,超越原本的自然状态,转化为政治上的共同体。可见在霍布斯处,自然人是不择手段地逐利的个人,但这一自然状态会在后果恐惧和理性控制中被克服掉,最终个人之间会达成妥协、缔结契约并建立国家。但布鲁姆认为,按霍布斯的设想只是“将个体的自私转化成集体的自私”[8]43,个体一方面对他人许诺以有条件的权利,另一方面却期望他人无条件地来满足自己的权利,这样,所缔结的契约不过是基于个体间的理性算计和相互欺骗,所建立的国家也不过是用个体间的竞争关系代替生死搏斗。换言之,在缔结契约和建立国家后,个体仍旧保持着个体状态,对他人予以戒备和防御,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因而,从人的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过渡,远非霍布斯所述的那样直接和自明。
布鲁姆则找到另一条从自然过渡到社会的道路。他援引卢梭的观点,“自然的东西是好的。如果社会生活要求遗弃它、破坏它,那么社会生活就有问题”[8]43,也就是说,卢梭同霍布斯一样,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受欲望支配的、本质上利己的,但他并不认为自然应当和能够被去除,而是要在自然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方式引导它、提升它,最终使得人与人凭借直接的感情习惯、自然地结合为共同体。所以,首要的并非强调人的社会性、维持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要让个体回到有需要的孤立(needy isolation)、恢复个体的自然状态。那么,卢梭主张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布鲁姆通过绎读《爱弥儿》,指出卢梭意义上的自然就是自爱。自爱产生于前自我意识的层面上,既意味着不与他人发生关系、对自身拥有绝对权力,在肉体和灵魂间不存有任何分裂,又意味着对境况不如自己的人施以同情、因确信自身的优越而蔑视所谓的伟大,由此生发出追求平等的满足感。只有处于充分自爱、服从自然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y),才能抵御被从外部强加的关系和结构,并从内部逐渐地实现升华。
但是,人类不可能永远处于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必然会相互接触、彼此联系,因此需要对孤立的个体予以正确的引导,使其像关心自己一样去关心他人。卢梭认为这个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转化过程发生在男女双方的恋爱中。他指出,恋爱与性本能不同,我们之所以选择与这个人而不是与其他人进行恋爱,是因为恋爱不仅包括性的欲望,同时包括对伴侣的想象,只有想象才使恋爱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在想象中,被爱者作为爱者的理型(ideal)对象而存在,爱者在被爱者身上看到美好之物,对之产生无偏私的爱,并自然地予以追求,愿意为了美好的理型而自我约束。值得注意的是,理型自身并非抽象的存在,对理型的追求也不意味着强加的义务,相反,理型是至善的、却没有排除自然的情感或品位。这样,恋爱既是肉体欲望的投射和需要,又是对欲望的引导和升华。通过恋爱,个体超越了原初的自爱状态,在伴侣身上看到自己、获得自我意识,内在地生发出基于自由选择的道德。布鲁姆评价卢梭及其后继的浪漫主义小说,其最为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描写男女双方由自然的欲望开始,一步步地相互猜疑和试探,彼此都在意对方的看法并相应地作出改变,最终在激情与理性中达至持久的结合。
布鲁姆在霍布斯和卢梭二人分别提出的从自然过渡到社会的道路中,显然更加赞同后者。但在布鲁姆看来,“卢梭的教育是在塑造,而非唤醒”[8]48,也就是说,他认为卢梭仍然割裂了自然和理性,虽然理性基于自然,但理性自身并非是自然的,而是被后天培养的。这直接导致在浪漫主义之后,自然和理性愈加分离开来,自然被还原为生物意义上的性,而在被爱者身上投射的想象则被彻底消除。如果说在卢梭的时代,霍布斯所主张的人与人间的理性算计已经严重威胁到个体的自然天性,因而卢梭需要文学来承担恢复或重建人性的重任,那么在莎士比亚的时代,经济尚未如此地分化和渗透,因而莎翁并不需要文学去构建一个升华的过程,相反,他只是在戏剧中模仿丰富多样的人性。于是,布鲁姆从卢梭转向莎士比亚,试图在莎翁的戏剧中找到最纯粹、最丰富的自然,这种自然已内在地包含了理性。
在《爱与友谊》的第二部分“莎士比亚与自然”(Part Two: Shakespeare and Nature)中,布鲁姆绎读了莎翁的六部戏剧(1)参见Allan Bloom, Love and Friendship,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3。,它们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第一,如《爱弥儿》等作品总归是作家精心构建的,包含着特定意图,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抽象性,但莎士比亚的戏剧却是具体的,就像真实生活中的男女相处一样,“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9]。第二,这六部戏剧中所包含的感情是多样的、异质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描绘的是异教时代的爱,《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报还一报》描绘的是基督教时代的爱,《冬天的故事》描述的是混合着异教与基督教时代的爱,《哈尔和福斯塔夫》描绘的是同性间的友谊。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既无说教,又不单一,相反是具体的、丰富的,因而“犹如自然之镜,呈现人本来的样子。他的诗让我们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what is there)”[11]1也就是说,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代表着布鲁姆真正认可的自然人性。
更进一步,在莎士比亚的自然中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激情与理性,二者并不是和谐的,而是激烈地发生冲突。在布鲁姆看来,莎翁戏剧中的两位主人公(异性或同性)往往一见钟情继而深情笃意,这就意味着,莎士比亚并不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仅是孤立的个体(无论是在霍布斯还是在卢梭的意义上),相反,人与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相互联系,并且出于激情而爱得狂热。但爱始终处于世俗之中,因此激情常常受到阻碍、陷入困境,既体现在相爱双方与世俗间产生冲突,也体现在相爱的一方囿于世俗之中、难以对另一方的情感诉求予以呼应。所以,理性是自然而必要的,理性让爱能够融入无处不在的习俗,或让爱能够从习俗中解放出来,从而更为长久地保存爱。布鲁姆指出,莎士比亚赞美激情,但“从来不曾站在激情一边反对理性”[10],正是由于实际的世俗社会,使原本盲目的激情受控于理性,转化为一种对自身和习俗的反思,以达至更高的、知晓善好的智慧。莎士比亚经常让配角或局外人(恋爱关系之外)来担任理性引导的角色,如《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尤利西斯,他的理性暴露出阿喀琉斯所贪恋的不过是德行带来的虚假名声,同时指示出真正的荣誉需要依靠美德、在希腊社会内部的权力语境中获得。其他如劳伦斯神父、文森修公爵、宝丽娜侍女等也都对激情予以理性的引导。
布鲁姆对莎士比亚赞誉极高,将之视为从现代返归古典的唯一途径。如果说,莎士比亚以具体的、多样的生命经历映出人的自然本性,描绘在自然中难以调和的激情与理性,展示由激情而生发的最强烈的快乐和由理性所引导的最高贵的德行,那么,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则以形而上的方式表达相同的内涵,他借第俄提玛之口直接指出这一从自然到理性的升华就是Eros。在布鲁姆看来,只有达至柏拉图,才是真正返归健康的古典。
《会饮》篇记述了在一场饮酒会上六个人对Eros各自的赞美:斐德若赞美Eros能让爱者(lover)为被爱者(beloved)(2)lover和beloved在文中被分别译为“爱者”和“被爱者”,以此区分爱欲行为中的主动方和被动方。英勇杀敌,从而为爱者带来好名声;泡萨尼阿斯赞美Eros能够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美的范例。这两个人并非赞美Eros本身,而仅是赞美Eros所能带来的结果。接下来,厄里克希马库斯赞美Eros将爱者和被爱者结合在一起,以此确保每个个体的健康。他并没有考虑双方的灵魂问题,而仅是在身体层面做出科学控制。阿里斯托芬的出场,首先表明Eros与外在的功利结果或科学控制并无关系,继而将焦点转向Eros究竟是什么(what),也就是Eros的存在(being)问题。阿伽通短暂地偏离了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只在形式上反复赞美Eros。最后,苏格拉底对阿伽通予以反驳,并借第俄提玛之口在存在论(ontology)意义上真正地言说Eros。六种观点分别代表Eros在形而上领域的六种样态。
可以看出,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围绕Eros所进行的论争,构成全篇对话中最具启示性的内容。二人都认为,Eros属于自然、高于法律。自然并不必然地导向法律,但法律的确立反过来却需要依靠自然,并时常受到自然模糊性的挑战。因此,Eros同样并不确立法律,而是作为法律的前提与溢出。但二人论争的关键在于,Eros是不是(第一)自然的?通过Eros能不能达至个体的整全?阿里斯托芬认为Eros不是第一自然、并非整全,仅仅是对伤害予以治疗的第二自然。第一自然指男女尚未分离的“圆球人”,他们整全和自足,但这只是宇宙神才具有的。人类则处于男女分离的非整全形态,因此人只能在已失去完整的情况下去渴望完整,也即构筑第二自然[11]75-77。这样,阿里斯托芬总结到,Eros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对丧失自然的一种补偿,并且永远无法回到原初的整全。苏格拉底却认为,真正的Eros就发生在自然中,他借第俄提玛的教诲来论证,首先,Eros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介于二者的存在物,是神和人相联系的中介。因为Eros是对自身所匮乏之物的爱,所以它不属于完整而不匮乏的神的范畴,但Eros又指向对更高之物的追求,所以也不完全属于人的范畴。其次,Eros意味着渴求完整的欲望,其对人的意义在于,促使人去积极地追求、不断地提升。这一提升过程始于人的身体欲望,但在其中已经包孕着精神性、包孕着内在理性的指引,能够流畅地“从特殊转向一般,从变化转向永恒,从可见之物转向可思之物”[11]134,最终指向具有神性的不朽。最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由此Eros是自然的、能达至整全。二人观点的根本分歧在于,阿里斯托芬的Eros是平行的,仅指向对方,并没有一种超越的维度;而苏格拉底的Eros是垂直的,相爱双方能够在Eros中获得超越。
概括来说,布鲁姆在《爱与友谊》中,由卢梭所设计的从自然到理性的升华(自然与理性分裂),经莎士比亚具体地描绘在自然中从激情到理性的升华(理性内含于自然),至柏拉图在形而上领域将这一从自然到理性的升华称作Eros(自然自行升华)。三者逐层上升,形成“爱的阶梯”。而这一从自然内部被理性引导的升华过程,也就是布鲁姆所认为的审美教育的核心。
三、美育的目标:达至个人整全、实践政治生活
通过绎读柏拉图的《会饮》篇,布鲁姆提出有限的个体从内在自然出发,经过理性引导、自行升华,最终超越原本的有限性,达至个体的整全和完满。应当说,理性与启示的关系一直是古典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探求“若没有受益于超理性的灵感或启示,或没有受益于对这样的灵感或启示的服从,理性能否能够或应该成为人类存在的向导”[5]14,换言之,理性究竟能否自我提升、能否正确地引导行为?布鲁姆对此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他认为人的自然已经内在地包含了理性,理性指引也是自然内在的要求,同时,他也强调理性自始至终并非抽象的、独立的,理性从非理性(激情)中进行升华,但理性并没有抹除掉非理性,“它必须被混合以非理性要素”[12]。这样,由理性引导而达至的整全同样并非是抽象的,而是混合了激情与理性的人性真理,这一真理意味着把握关于人性的永恒问题。布鲁姆论述尼采与苏格拉底间的区别在于,对于尼采来说,语言只意味着绝对个体的表达,永远不能超越个体的视角而抵达普遍性,但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语言能够反映存在,语言是通向共同体和相互理解的最终形式[11]164。也就是说,个体的整全即对普遍的、关乎人类整体的问题予以把握。审美教育培养学生达至个体的整全,也就是培养学生对永恒的人性真理进行探索。
也应注意到,无论是在卢梭、莎士比亚抑或柏拉图的观念里,从自然到理性的升华并非发生于孤立的个体内部,而是发生在个体与另一个体的恋爱关系之中;升华也并非止于两个人的恋爱关系,而是直接与共同体和政治生活相关联。在卢梭处,男女双方在不压制天性的状态下,自然而然地结合成伴侣并组建家庭,而家庭即是前政治的单元,是将社会构成由原子转化为分子的必要阶段。在莎士比亚处,男女双方在自然的联系中相爱,但却要面对具体的国家、宗教、家庭等世俗因素,最终让爱情智慧地融入其中。在柏拉图处,爱总是因自身的匮乏而向他者进行寻找,这一从自然到理性的升华过程最终达至个体的整全和永恒的真理,进而将自然整体的技艺与城邦制造哲人王的技艺统一到一起。从布鲁姆绎读的三个人的观念中可以看出,升华过程在开始时就与他人相关联,并最终关系到人性的永恒问题与具体的政治生活。这同样是施特劳斯学派所持的基本主张,其继承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观念,认为政治哲学是为人类基本问题提供可能选择的学问,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过上善好生活,而可能的选择就是从自然到政治的进阶。但正如布鲁姆认为政治哲学与诗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文明意味着成熟的理解、反思与充分的感受力的结合”[13],因此,美育的最终目标也不是抽象哲学统治下的政治生活,而是基于人与人的直接情感,经由理性的升华,对具有“普遍性和同质性”[14]的人类永恒问题予以共同关心与追求的政治生活。
布鲁姆从当下大学教育的现状出发,逐层分析导致大学教育产生问题的原因,由此返归至古典主义的经典著作,提出自己的审美教育的观念。他认为,政治哲学与诗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审美教育所关注的对象是人性真理的问题。通过绎读卢梭、莎士比亚和柏拉图,他具体地论述了从自然到理性的升华过程,这一过程中理性由激情开始,对激情进行引导却并不排除它,同时,理性已经内在地包含于自然中,二者并不是分裂的,从自然到理性的升华也就是自然的自行升华。这样,通过审美教育,最终既达至个人的整全,又在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中塑造真正的共同体。概言之,布鲁姆的美育观就是从自然到政治的进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