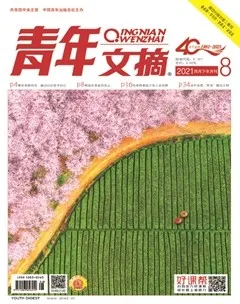宁静的牛

小时候他们曾叫我牛眼,因为我眼睛很大,像那头牛。其实我自己并不觉得。
我曾盯着牛的眼睛仔细看,很大,很圆,很单纯,好像没别的什么。
也许正因为什么也没有,我才更好奇,这样庞大受苦的动物,为什么眼睛里竟然像婴儿一样干干净净又空洞?有一回我发誓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跟着我的牛,瞧着它的眼睛,我观察那眼睛里头的反应和变化。
没有,丝毫没有变化,空空如也。你以为会有愤怒、不以为然、不屑或厌烦,乃至别的什么,但是没有。我像个精神病一样摸着牛头和牛那巨大的双眼皮,打算跟它聊一聊。很快,它拿头拱我,我避开,它也转身走了。我想这是一种厌烦或躲避的心态,但它的眼睛里没有这些内容。不是完全无,是若有若无。或者还有些可怜的、弱小的孤独,温柔的、没有任何欲望的、单纯的孤独。
我去丛林里找我的牛,林中藤蔓缠绕,我累得半死。树林里比山下更早天黑,我越往前走越能闻到夜晚阴凉的气息,所以十分着急,在苔石上摔了好几跤,荆棘刺得我手臂上全是伤痕。
后来,我在茂盛的树底下看到它,那儿布满高肥的蕨类植物和藤蔓灌木。那些植物,绿得仿佛要流油,饱满得几乎要裂开,普通草本植物都比别处的个头更高,硕大肥嫩。难怪我的牛会来到这儿。
但我仍朝它破口大骂,因为我累得半死,还在苔石上摔了几跤。我说,走!回家!可它无动于衷。通常我不让它来这儿,牛一上山就太难找了,奈何它是头喜欢开拓、不安现状的牛。牛一动不动,吃着草叶并不想离开。于是我又朝它挥动我的鞭子,它转头用那双单纯忠厚的眼睛望着我,这才懒洋洋地扭动肥硕的大屁股,慢悠悠走下山去。牛认得路,几乎是它带我走出丛林的。
我过去也曾恶狠狠地打它,因为它偷吃了别人家的青菜或糟践了一片稻苗。说实话,为这种屁大的事情而挨打实在可怜。但它好像已经习惯了,它像个石头,不哭嚎,不反抗,不咒骂,不怨恨,不记仇,甚至不动一下。它生来顺从和勤劳,那种巨大的隐忍和承受力让我心疼。我同情我的牛,但我不能不鞭打牛,不得不管教它,不得不对其错误施罚。人终究无法与一头牛沟通,但鞭子是一种交流和纠正,邪恶的纠正。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朋友,我帮不了它,牛也没打算经营这类友谊。它每天气定神闲地走来走去,待在牛栏里也忠厚得很。
兽类的某种平静有时高于人类,人役使牛马,也被牛马的朴素高贵所教育。人的复杂与兽的野蛮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互补,道德感的释放是因为人的攻击变小,兽进行的大多是弱肉强食的狩猎,而人不免被欲望和气急败坏的成见操控,不曾像兽长期聚精会神地做一件事。兽的眼睛里只有兽,熟悉后会通人性。兽的友谊传递了一种警醒。野性与直觉的灵敏,比俗人的混世厚黑学更重要,因而更单纯。
牛没有什么野心,以至于你认为永远别想改变牛,它的错误是顽固和单纯的,你没必要为此生气,你只能一次次纠正,因而鞭子的存在也是必要的。
我鞭打它,又将它视为朋友。我将牛想象成与人类似的生命,它挨的鞭子在我看来就像任何苦命人遭受的痛苦一样。这恶狠狠的抽打使我发现了我的恶,有时我会突然停下来,看着它的眼睛,为它心疼一小会儿,而它好像无动于衷。它还是眨着那无辜善良的大眼睛站在原地或慢慢走着,摇着那蚊子盘绕的尾巴。如果尼采站在我身边,看到我鞭打我的牛,他会不会抱着牛的脖子泪流满面,露出疯子和孩子那样的神情?人期望对麻木施以援手,更希望对麻木施以杀手。
只有一种办法能解决牛的痛苦,那就是解决牛。因为你没有办法帮它,你没有办法安慰、怜悯、疼爱,或照应它、爱它、请它吃饭,你跟它永远不可能成为拯教和被拯救的关系。
牛是可怜的。它总得做点什么,否则就得去死。死也是残忍,无论怎样,对它来说都是残忍,它就是为残忍而生,为接受残忍而生,它真的毫无怨恨。
我没有骑过牛,因为它脾气火暴,压根不让我得逞。我妈曾见我不甘地往牛背上攀登,很多次被它摔下来,我急得破口大骂。她说几百公斤的大黑牛要是一蹄子踩在我肚子上或其他地方,我都可能魂归西天。我就作罢了。小时候我是很猛的,年幼无知,但我怕被踩死。通过这件事我又发现了牛的骄傲,它也有它的原则和底线,有它厌恶的事情。这一点反而让我高兴,仿佛突然从一堆牛肉上看到了骄傲的灵魂。
我有时会在恍惚间产生一种大家都像牲口一样活在世上的感觉。如果我们完不成自己理想中生命的三分之一,我们的生活就是苦涩的,而现实是,多数人完成不了三分之一。那我们跟牛有什么区别?当我们发现人的眼中常弥漫某种兽的欲望,或兽的眼中透露着某种人性,这种理解就拉近了人与兽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永远是两种空白,或一种空白、一种黑暗,不会产生别的联系,唯一的联系仅仅是,它曾是我的牛。
(摘自《雨花》2021年第1期,本刊有删节,马建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