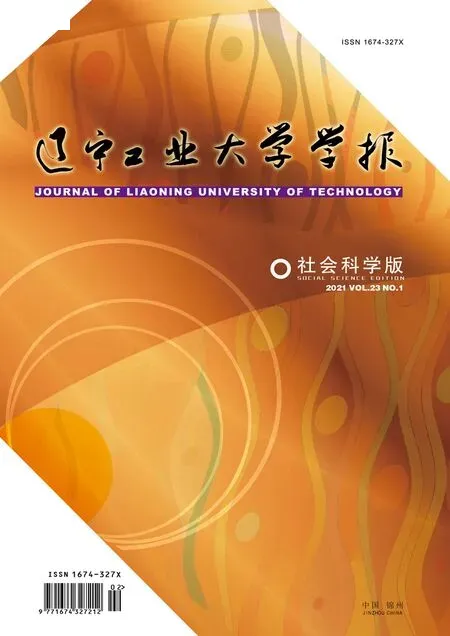论吴坤元的感怀诗
叶 翠,汪 丽
(1.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桐城 231400;2.桐城实验小学,安徽 桐城 231400)
中国女性文学源远流长,到明清时期,成就斐然,尤其在诗歌创作上。《桐城方氏诗辑·凡例》中载:“彤管流徽,吾桐最盛,如环珠(何孺人吴令则)、棣倩(方夫人吴令仪)、纕芷(姚夫人左如芬)、缄秋(张孺人姚宛),不可胜数。”[1]此外,同时代还有吴坤元与方维仪、章有湘号称“桐城三才女”。出身于诗书之家的吴坤元(1600—1679),字璞玉,一字至士。自幼聪颖过人,跟随其祖父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吴应宾学习,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十岁即能创作诗文,著有二十卷诗文合集《松声阁集》。此诗文集因受其独子潘江作品的牵连被毁,后虽在民国期间被重新辑录出版,但却因缺失一部分诗文而变得不再完整。此本共收词14 阕,诗501首,诗以五、七言为主,多为孀居后所作,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诗歌内容当为诗人感怀伤时之作,既刻画了亡夫之痛,又表现了生活之苦,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坚强自勉和向往闲适之情以及礼佛参禅之心,本文试对吴坤元感怀诗的内容及艺术特色作一整体观照。
一、感怀诗的丰富内容
(一)亡夫之痛
四十余年的守节岁月在外人看来是贞洁高尚,但其中丧夫育孤的艰辛与孤苦唯有自知。所以,吴坤元诗集中诸多诗作表达了这份不幸的滋味。
吴坤元夫潘金芝,据《康熙桐城县志》中有传记载:“字九茎,太学生。”[2]194才华卓越,但英年早逝。吴坤元与其夫妻缘分不深,但感情颇深。除了《祭夫子归西文》中“凄风楚雨,悲君自怜,霜晨雪夜,泪浸寒毡”直接表达了对夫子归西扶棺柩时的悲恸之情外,[3]还有日思夜想以至于《夜梦夫子》“谁使先生归去早,令予卅载哭流离……感君夜半犹相讯,愿逐东风叫子规”中对丈夫早逝[3],带来连绵不尽的痛苦以及梦中相见的欣喜慰藉之情。此外,还有两首在夫子诞辰日时写的诗。第一首《四月廿七日夫子诞辰》用“陇上纸灰飞不到,枕边有泪到君边”情深义重地道出诗人与丈夫阴阳相隔的痛苦[3],以及梦中流下的相思之泪;第二首:“年年当此日,滴酒向堂前。争奈经旬雨,无由叩所天。不闻纸化蝶,但觉泪同鹃。知否凭君意,焚诗益可怜。”[3]更是表达了诗人与丈夫的深厚感情。首联直叙年年都是此情彼景,日日都是伤心之时。颈联用比喻手法写出在焚烧飘远的黄纸烟灰面前,诗人泪眼婆娑,恍如隔世。整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早逝夫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的怀念与难忘之情,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二)生活之苦
吴坤元早年丧夫,既要侍奉寡居的太婆婆和婆婆,又要悉心教导儿孙,家庭生活难免时常陷入困顿之中,因而有一些诗歌描述了诗人清贫的生活状态,抒发了诗人愁苦的情感需求。在五言律诗《愁吟》中,诗人就用直白的语言:“穷苦依儿子,艰难奉老亲。荒田几百亩,愁杀未亡人。”[3]叙述了作为未亡人,上有老,下有小,每天为生计发愁。只是豆菽和水都足以让诗人欣喜若狂,正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人饱受生活的困顿之苦。
除了为生计发愁,精神上的孤苦无依才是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因而有很大一部分的诗歌抒写了这份凄苦之情。比如《秋日即事》:“老去愁逢亲友别,残年思遗子孙安。鸠杖未扶行立懒,不知更坐几蒲园。”[3]一“老”一“残”写出了诗人在暮秋时节,眼见萧瑟之景,生发风烛残年之愁感;《秋日自述》更是自述“浮沤水泽不坚强,七十三年火宅长”[3]。“四十六”“七十三”这些表示确切时间的数字,表达诗人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悲伤中度过,“向谁揩”的反问来反衬自己的孤独无依,而“不坚强”更是直抒胸臆,说明自己的脆弱孤独,倍增凄凉之感。而当诗人处在病中之时,这份凄苦更是有增无减。如《病忧》首联“老病烦忧两两催,无端一一自中来”就写到生老病死、生活烦忧接踵而来[3],令诗人难以承受,苦不堪言。这份无处诉说的愁怨到底有多深,诗人不自述,移觉到庭花:“庭花也觉愁如我,寥落西风怨未开。”[3]借花喻人,其中的愁忧滋味,令人咀嚼不止。《岁暮》中:“岂独衰慵増慨叹,更兼老病伴穷愁。医人卖药终无效,租吏敲门苦未休。”[3]更是用直白的语言倾诉出肺腑之言,笔触细腻、语浅情真,无疑正是诗人悲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和自然流露。
(三)坚强自勉
吴坤元毕竟是中国传统女性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孕育于桐城的地域文化之中,所以在她孀居的四十余年中,虽饱受亡夫痛苦的折磨和倍受生活苦难的煎熬,但并未怨天尤人,不仅培养了德才兼备的儿子,还创作了大量坚强自勉的诗歌,让人从中体味到她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在《六十初度》序文中,吴坤元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自己即使人生凄惨,家境贫苦,但仍然“耿耿历数十载如一日”[3],效仿“古贤母义方之训”[3],悉心培育出非常优秀的儿子。其子潘江在《龙眠风雅续集》中就提到吴母:“教子孙以孝友,多读书,慎取友为训,毋汲汲富贵。”[2]194
诗人的坚韧自强更是对儿孙后人做出了身体力行地榜样。在《姚鲁斋孙婿以黄白菊花见贻赋答》中诗人先以“衰年同草木”自比衰年残躯[3],又以“弱质比蒹葭”喻自己纤纤弱质[3]。但诗人并未对生活失去信心,仍借“阶庭更有芝兰种,取次来看玉树芽”来表达对生命新生的期待之情[3]。此外,在诗歌《自警》中,诗人借“紫燕黄鹂刷羽鲜,哑哑也趁晓风天”自况[3],借物喻人,表达了诗人不会虚度韶华岁月,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情怀。
当然在传统佳节之时,诗人也会偶发感慨之声:“年年九月至,愁说是重阳。五度石溪水,三秋竹径荒。人因忧覆雨,花亦畏经霜。自笑生涯拙,深秋卧草堂。”(《己丑重阳》)[3]虽抒发了重阳佳节,烦忧愁绪萦绕心间,但也只是暂时的,更多还是勉励自己珍惜当下,努力生活,莫负光阴。
由此可见,吴坤元虽也感怀命运的不公,人生的艰辛,但并未自怨自艾,更没有消极倦怠。在这些苦吟哀怨的心声中透露出的却是爱子教子的执着之行和自我勉励的坚强之志,令人钦佩不已。
(四)向往闲适
作为守节四十余载的孀妇,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竭力保持恬淡闲静之心,读书遣愁、赋诗达意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如《夜坐》:“迟睡愁难寐,羁情暂拥书。一簾新月上,半壁冷窗户。懒病才应减,高吟寒不除。瓶花耐久共,又被晓凤初。”[3]
诗人描写了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愁绪羁情导致迟睡难寐,这份愁虽萦绕心间,挥之不去,但拥有书籍,却能让诗人在静谧清冷的月夜,心静如水。《题石经斋》中和友人“旧拥琴书自古今”更是诗人日常抚琴读书闲适生活的写照[3],而“他年诗句如常在,白水青灯即此心”[3],刻画了诗人在吟诵诗句间不经意流露出的淡然心境。
诗人在写景咏物之时,经常会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无比热爱以及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之情。如描写乡村美景的《村居》,从视听多角度去欣赏秋霁下的一声声蝉鸣、午烟中的一群群雀飞,还有远处那连天的碧树、眼前艳红的霜花,让人美不胜收,表达了诗人在秋后的村居美景中,心无杂念、满足欣慰、怡然自得。
另《村居寄弟妇》:“窗前莺语细,槛外鹊声迟。愁逐霜风去,魂随午梦移。”[3]写出诗人对乡村美景充满热爱之情,对生活仍然心怀希望之感。而《何妹木笔花见投偶成》:“门远市厘春昼闲,花齐高阁更怡颜。”[3]更是颇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4]之意,在庄严静穆的日常生活中拥有安逸洒脱之情,在静谧舒怡的起居之地流露清新自然之感,表达诗人远离尘嚣、追求洒脱自由的人生态度。
(五)礼佛参禅
在吴坤元晚年衰老病卧之际,她期盼自己能够过着恬淡、闲适的生活,因此读书、吟诗、礼佛、参禅是其生活日常,希望借此来消除内心的浮躁和烦恼,从而获得安稳与平静。
如诗人在日常的读书中亦能参悟到世人所汲汲追求的荣华富贵、显赫身世,不过都是过眼云烟,身死之后一切终将泯灭归为空无。这一深刻的禅理在《阅元大师诗》中借闹市与山林、穷困与显达、生前与死后、长寿与短命等进行强烈的对比,表达了诗人远离尘嚣的愿望、空净澄澈的心境和一心向佛的虔诚之心。此外,诗人在欣赏画作之时也不忘体味禅意,用“金书蜡纸白毫光,仰视慈悲照十方”来描述慈悲为怀的观音大士的画像[3]。观音大士像之所以在诗人心中光芒万丈,正是因为诗人心中对其怀有无比崇敬之情与时刻保持的虔诚之心。
除了读书赏画不忘礼佛参禅,诗人还躬身力行去拜佛,在《礼佛》中就有载:“冲寒登草阁,雪不畏云封。礼佛常过午,经声万壑松。寂从初击磐,慧出定时钟。趺坐无他顾,须弥对远峰。”[3]从礼佛路途环境的恶劣、参禅时间的长久去刻画诗人的虔诚,从周围环境的描写表现了诗人礼佛参禅之后内心的静谧安详,表达了诗人拜佛的虔诚宁静之心。
二、感怀诗的艺术特色
(一)依情用典、善化诗意
吴坤元自幼随祖父学习,过目不忘,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在她的感怀诗中,有很多依情用典、化用诗意的句子。诗人不仅仅追求精巧的形式,展现渊博的学问,更是做到既能达意,更可传情。
如《夜梦夫子》就是诗人感怀丈夫早逝,抒发痛苦之音的一篇佳作。“谁使先生归去早,令予卅载哭流离”的现状[3],令诗人忆起往昔甜蜜的“陶潜翻受田园累,禽向初完婚嫁时”的岁月[3]。今昔对比,倍添伤感之情。因此“感君夜半犹相讯,愿逐东风叫子规”[3]。在夜深人静之时,诗人产生了迷离恍惚、如梦如幻的意识和时空交叉的错觉,似乎丈夫从未离开,依然像以往那样来到自己的床边嘘寒问暖。而尾联的“愿逐东风叫子规”则是化用王令“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诗句,将未亡人渴望丈夫能死而复生、留在自己身边陪伴自己的执着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这种伉俪之情渗透于典故之中,动人肺腑。
此外,《记梦中诗》记载了诗人潜心礼佛坐禅,日夜不眠地修行,以精进到智慧与福德的圆满,达到禅定与神通境界的感悟之作。诗歌尾联的“要知一句楞严偈,阅尽人间几烂柯”是借用“烂柯人”的典故化入到自己诗中[3],用“到乡翻似烂柯人”的典故感叹梦醒之后[5],时光飞快地流逝,怕是要穷尽一生才能达到神通的境界了,从而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向佛之心,富含禅理,意味深长。
诗人还有一些悉心教导和勉励后辈奋发图强的诗作也常借典故来表情达意。如语重心长地告诉长孙应如何精进学问的《长孙仁树就外塾》:“六岁尚不满,莫辨贤与非。虽不事姑息,未免舐犊慈。读书首孝弟,富贵非所期。愿言良弓冶,厥意在箕裘。”[3]长孙虽不谙世事,还不辨贤良与奸佞,但在诗人看来,年龄虽尚幼,但读书不可不用心,因为读书能让人厚人伦,重孝梯。因而借《礼记》里的“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来说明求学应从最基本的着手[6],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才能日积月累,学富五车,做一个贤良之才。
另有一组写给自己爱婿的诗歌,一改以往送别诗的悲凉凄怆,而采用依情用典,将写景、叙事、抒情有机融合,例如《清明寄怀井公婿客历阳》借典故表诗人对爱婿寄予厚望的谆谆教诲之情[3]:“清明雷雨益凄其,别后时牵卫玠思。游子青衫应有泪,老人白发已如丝。共知时事难长啸,偶忆诗篇一解头。地北天南归应少,春风莫遣马蹄迟。”
“游子青衫应有泪,老人白发已如丝。”借宋代诗人张嵲《有感》中的“李公白发已如丝,肯惜忠言负主知。事大不应回一语,知君不作上官仪”和清人王敬铭《灵宝道中口占》中的“游子身尝境,衰亲心历时。家书不敢说,白发已如丝。”来说明爱婿仕途的坎坷不顺,家人等待佳音的焦急难熬。最后运用翻典的手法将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7]转化为“春风莫遣马蹄迟”,表达自己对爱婿功成名就的期盼之情。
(二)意象丰富、情感蕴藉
作为一位女性诗人,吴坤元情感细腻,身世悲惨、经历坎坷、疾病缠身,因而诗人眼中“风”“雨”“月”“花”“燕”等最常见的自然万物皆着上情感色彩。当这些带上诗人感情因素的意象遍布于诗人的众多感怀诗中,则给人带来丰富多彩的审美体验,构成诗人独有的审美世界。
对于心思细腻、多愁善感的诗人来说,风雨更容易触发内心深处的孤寂、悲伤之情,引发感慨之音。在《村居苦雨》中“山城十日雨,正是暮春时”[3],写出了暮春来临之时,阴雨连绵更增诗人苦闷的愁绪;在《苦雨》中“入夏空庭雨,萧然似晚秋”[3],写出夏季的庭雨却让诗人感到一片秋意萧索,为何如此反常?原来是诗人“忆弟增惆怅,思家敢怨尤”[3],对亲人和家乡的思念之情使得诗人对眼前之雨生发出惆怅怨由之情。《晚风》一诗更是将诗人的悲凉孤寂情感寄托于冷风寒雨之中。明明才“庭树分新绿”[3],却“夏来无暑气”[3],就连夏日的疾风劲雨,却给诗人带来浸渍身心的阴寒之气,让原本炎热的夏季却似寒秋呈现一片萧瑟凄凉之景,从而折射出诗人凄凉落寞的心境。
此外,“寒月”“明月”“新月”也是诗人寄情托思之良物。如诗人在《愁绪》中借“疎枝寒月深秋夜”表自己在深秋之夜[3],眼见凋零之景,身经凉风冷雨,顿觉花叶落尽,让人倍感凄凉;《夜坐》中“一簾新月”照在诗人憩息的“半壁窗户”之上[3],令人不禁身感寒意,既是夜寒亦是心寒。而《秋夜》中诗人更着重描绘深秋时节,落叶满地,月光皎洁,月照拂捣衣石上,形成一幅秋夜明月静谧图。
在诗人的大半生中,花亦是诗人孤苦生活中的情感寄托,是诗人品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因此,诗人在《瓶梅半月奄然欲谢因折枝剪纸作帐檐额喜赋五首》中以梅喻己,表达了“为怜卒岁寒,不受三分白”的同病相怜的身世之感[3];在《月下观水仙花不开率成长句》中借“只恐花开转眼空,翻同柳絮随风浪”表达自己如水仙花般花开成空[3],年华逝去的遗憾和调怅之情;在《姚鲁斋孙婿以黄白菊花见贻赋答》中诗人看到孙婿送的黄白菊花鲜艳明亮,不禁“自叹衰年同草木,却怜弱质比蒹葭”[3],在盛与衰的对比之中,诗人感慨岁月流逝,抒发老病哀愁的感慨之情。
除自然万物,像“燕”这样的精灵,在诗人笔下也随处可见。如表达喜爱之情的《秋燕始巢》,诗人借:“参差日日燕双来,只恐深秋雁字催。辛苦梁间巢始就。莫将去住两徘徊。”[3]表达对燕子辛苦筑巢,却在深秋来临之时不得不离开的不舍之情。还有借“旅燕”寄托雪夜之时对远游在外儿子的牵挂之情。
(三)语言质朴、意境深远
吴坤元诗歌语言清新脱俗,质朴无华,善用白描手法,运用最简洁凝练的语言,描摹鲜明生动的形象,表达蕴含其中的情感,传递出自然景物营造的意境。《乡行》首联“夜对寒村月,晨侵茅店霜”选用8 个表示景物的纯名词性短语:夜、寒、村、月、晨、茅、店、霜,勾勒出一幅夜月清冷、晨霜寒彻、村庄宁静、茅店静谧的清秋拂晓乡景图[3];接下来用白描手法写出野花灿烂、落叶微黄、倦鸟归林、孤云逐雨、山色隐晦、斜阳西下的乡村之景,不着一点浓墨重彩,却让人于乡村秋景之中感受到一片生机和希望,充满了勃勃的生命力。
就是在寻常的生活琐事中,诗人也能感悟人生:“看花虽及半开时,便是微红可入诗。”[3]诗人在赏花之时,用简练语言带出眼前所见之景,由花及人,眼前的花开花易谢,悟出人生当惜时,否则,一眨眼,任时光飞逝,只能徒留遗憾在心间。尾句的“还愁后日即空枝”通俗易懂,[3]言浅意深,颇有“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之妙。
此外,诗人常年病痛缠身,不得不靠药物减轻痛苦,但贫寒的家境耗不起这样的开销。在这情形之下,诗人仍轻描淡写:“年年松阁听松声,何处松根结茯苓。”[3]将自己久居松阁,但却并未见到松根上结有药用的茯苓,然而在斗转星移的等待之中,诗人已白发如星。语言朴实凝炼,情感真挚感人,寥寥数语述心中无限感慨,营造了一幅时光流逝、光阴不待人的人生惆怅图。
吴坤元就是这样一位多愁善感、心思细腻、但却坚强自勉的女诗人。作为一位具有自己独特风韵的女性诗人,在她的感怀诗中,人生经历、情感体验、生活感悟无一不细腻融入日常生活和自然万物之中,烙上诗人情感的色彩。依情用典、善化诗意展现了诗人深厚的文学素养;意象丰富、情感蕴藉展示了诗人独特的内心世界;语言质朴、意境深远流露出诗人独有的审美情趣。正如陈潇所言“诗人的才情诗意和精神力量恰似一颗璀璨的明星,为桐城女性文学增添了耀眼的光芒。”[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