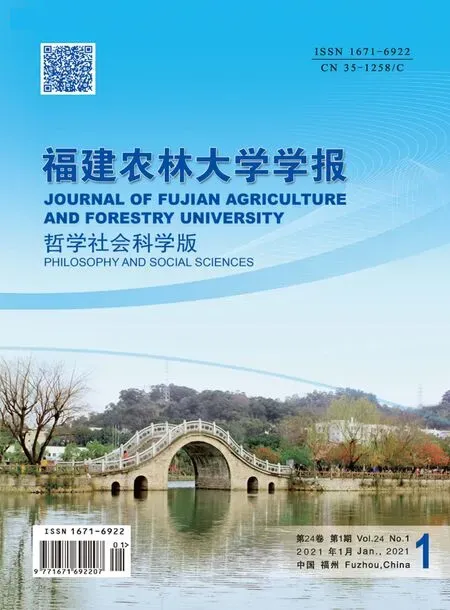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的边界识别
刘 嘉 莹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一般人格权条款如何理解是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学者认为,一般人格权可以作为口袋条款以保护新兴权利[1]。以一般人格权纠纷为案由,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案例达1万多件。一般人格权在司法实践中确实被作为口袋条款容纳了很多新兴权利, 如生活安宁权、祭奠权、安葬权、贞操权、平等就业权等[2-6]。随着社会的发展,必将出现许多新型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是否都能诉诸一般人格权保护?如果不能,那应当如何识别一般人格权保护的范围?本文从一般人格权条款入手,讨论一般人格权保护客体范围。由于篇幅限制,仅仅讨论一般人格权保护权利的边界如何确定。
一、当前司法现状与问题
(一)一般人格权保护利益司法案例类型化分析
根据检索到的案例,实践中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5类:
1.人格尊严。此类案件保护的利益十分繁杂,既有具体人格权,如名誉权、肖像权等[7],也有其他法律确认的权利,如平等就业权等。在管某朋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人格权案中,法院就援引了我国《就业促进法》第62条,认可原告享有平等就业权[8];在邓某娟等与北京手挽手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法院也认为被告邮政公司因其为女性不予录用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9]。除了以上基于人格尊严产生的具体权利外,此类纠纷涉及的利益还包括了未被法律识别为具体权利的一般人格尊严。如在彭某辉诉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等侵犯身体权、健康权和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原告认为被告网站宣传“同性恋可以治疗”实际上认为同性恋为心理疾病,构成对自己的人格贬损[10]。再如,在白某胜与成都铁路局重庆车站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原告单纯以被告不让原告进车站构成对其人格侮辱而起诉[11]。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案件中贬损人格尊严的方式多样,并不限于辱骂、泼秽物等常见的贬损人格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不当拒绝劳动者入职,或是针对某类人群进行区别宣传时,也可能构成对人格尊严的侵害。
2.人身自由。此类纠纷涉及的利益是人的行动自由。侵害人身自由的主体既可能是公职人员,也可能是具有看管义务的私主体。如在罗某与王某菊等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原告认为公安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存在不法限制自己人身自由的行为[12];再如,张某元与重庆市九龙坡区精神卫生中心一般人格权纠纷中,原告认为精神病院按照行政机关的要求排查精神病人的行为侵害自己的人身自由[13]。有些纠纷虽涉及人身自由,但核心争议点却并非人格权,如王某兰、周某雨等与徐州市鼓楼区夕阳红老年公寓、李某琴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涉案老人于养老院走失,双方主要争议点在于被告是否已尽看护义务,顺带就涉及“不得外出条款”是否侵害老人自由展开争论[14]。
3.婚姻关系及私密生活。此类案件多涉及性权利、生育权、违反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之后的赔偿,以及欺诈性抚养等两性关系和私密生活方面的利益。在欺诈性抚养案件中,既有夫妻一方因为子女非亲生导致精神痛苦,要求夫妻另一方赔偿的纠纷[15],也有被欺骗方诉第三人(孩子实际生父)要求赔偿的案件[16]。在此类纠纷中,多以损害赔偿为救济方式,但也有采用停止侵害等方式,如夫妻一方出轨,妻子不停发信息骚扰第三者,第三者起诉妻子要求其停止骚扰行为,并登报道歉[17]。
4.基于公序良俗产生的其他权利。这类权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公序良俗产生的与死者的安葬、哀悼、祭奠相关的利益;另一类是无法被类型化、随着社会发展产生的新兴权利。在涉及死者安葬、祭奠利益的纠纷中,法院通常都积极支持该种权利,如在练某龙诉周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面对逝者再婚情形下骨灰合葬争议的处理问题,法院就认为骨灰是尸体火化后的客观存在形态,亲人去世后骨灰成为其近亲属寄托思念、表达孝心、报答恩情、纪念先人等特殊感情的载体,因此,法律应当保护这种祭祀文化中的情感表达功能[18]。在谢某等诉金堂仁爱医院、周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法院在处理错领遗体并擅自处置死者遗体行为侵害原告何种利益时,也肯定了近亲属基于与死者生前特定身份关系所蕴含的精神性人格利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19]。而对于因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兴权利,法院的态度就审慎得多,并非全部肯定。如在任某玉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中,面对原告诉称其享有被遗忘权,并以此要求百度撤下和自己相关的网页链接时,法院就以被遗忘权并非现行法定的权利类型为由,拒绝了对此利益的识别保护[20]。再如,在张某燕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法院以张某燕关于性福权的诉求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为由,裁定不予受理该案[21]。
5.与具体人格权或具体侵权纠纷存在交叉的案件。此类纠纷与第一类纠纷有一定程度重合,许多与人格尊严无直接关联,且本可以具体侵权或是具体人格权纠纷为案由的案件,却被法院纳入一般人格权纠纷下审理。如仲某1与仲某2、仲某3一般人格权纠纷案,核心争议点在于校园霸凌的损害赔偿问题,此种纠纷本可适用身体权、健康权条款处理,但有的法院却将其列为一般人格权纠纷[22]。在帮工受伤、机动车事故等一些涉及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案涉权利也能够被身体权、健康权所容纳,不必适用一般人格权条款[23-24]。一些对名誉、人身的伤害、威胁,实际上也属于具体人格权的下辖范畴,但有的法院仍将一般人格权纠纷作为其案由[25]。
(二)当前司法裁判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案件归类可以看出,部分法院将一般人格权作为新兴权利的兜底条款。此种处理方式反映出当前司法裁判对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存在泛化和滥用的倾向,导致实践中凡遇新权利不决,则必诉诸一般人格权。这使得一般人格权案由纠纷的案件多样复杂,缺乏体系性。
1.一般人格权案由的滥用。实践中,部分法院混淆了新兴权利与人格权利的关系,将未被法律明确的新兴权利都视为人格利益并按一般人格权纠纷进行裁判。实践中,一般人格权实际上被当作一般民事权益保护的口袋条款,吸纳了许多未上升为权利的利益,如被遗忘权、生活安宁权等,但这些权利与一般人格权所主要保护的人格利益没有内在关联。
2.对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的区分不明。有些案件实际上可以运用具体的人格权对案涉权利进行保护。如在谭某莉与曹某红、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道祁家湾中学一般人格权纠纷中,法院将考试成绩被顶替的侵权行为也纳入一般人格权案由下[26],但面对此类顶替类案件,实际诉诸姓名权纠纷就可以给予原告法律救济。且在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交叉的案件中,法院没有加以甄别,仅仅依据涉及人格尊严这一延展性较强的概念,就以一般人格权裁判。
3.混淆了权益的识别与责任承担。在责任承担方面,法院有时略过了权益的识别,就径行判决,似乎把权利的有无与承担责任与否混为一谈。事实上,保护讼争权益不等于被告必然承担责任,识别该权利值得保护以后,仍需论证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一般的侵权构成要件。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一般人格权纠纷而言,有必要先对案涉权益是否属于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进行检验,再考虑是否符合其他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但是,许多裁判往往跳过权益识别直接肯定责任承担。
4.司法裁判尺度不一。法院对于新兴权利的识别本身存在分歧。如在有关贞操权的裁判中,法院对于该权利的看法呈现出不同的主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以贞操权仅是学术观点,并无法律依据,而且不宜在司法实践中直接认定上述权利种类被侵犯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7]。但面对同样的诉讼请求,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却认为,性是自然人重要的人格利益,明确肯定了贞操权是自然人享有的人格权[28]。
二、司法实践混乱的成因
(一)忽略了一般人格权与新兴权利的区别
司法实践中一般人格权定位的混乱,究其根本,是忽略了一般人格权与新兴权利的区别。一方面,新兴权利的价值基础并不必然源自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在客体范围上二者也存在不同,一般人格权的客体应当是基于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产生的利益,而新兴权利的客体范围实际上大于一般人格权的客体范围。实践中,有些法院将一般人格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化,将非基于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价值产生的利益包括在内,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一般人格权保护的范围与一般侵权(我国《民法典》第1 165条)的范围。自我国《民法典》开始编撰以来,关于一般人格权的争论就从未停止。目前,理论界多集中于讨论人格权是客观的权利还是仅为一般的权益[29],或是从权利法定的角度讨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如何适用[30],而对一般人格权的客体范畴却鲜有涉及。涉及一般人格权客体范畴的研究,要么将其与一般侵权等同,主张其应当作为口袋条款以保护未被法律识别的其他利益[31],要么则仅探讨宪法中人格尊严与民法中人格尊严的区别,从侧面对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作归纳[32],回避了如何识别一般人格权保护客体范围的问题。有学者就主张将一般人格权的适用范围扩大以吸纳新兴的人格利益,但没有提出一个如何识别人格利益的解决方案[33]。有学者认为因具有纪念意义物品受损而导致的痛苦、婚庆公司不按预期安排婚礼而导致的痛苦等,也应当纳入一般人格权保护,而这种主张实际上剥夺了我国《民法典》第1 165条一般侵权条款的功能[34],将导致许多与人格利益无关的新兴权利都被纳入一般人格权条款下进行救济保护。另外,还有学者提出把一般人格权类型化的主张,即将生命周期、非法限制自由、严重侮辱他人等作为类型化依据[35]。但这种主张并不能就自己提出的概念给个清晰的定义,以此适用一般人格权条款,容易导致一般人格权的泛化和口袋化。
(二)混淆了一般侵权条款与一般人格权条款的功能
混淆一般侵权条款与一般人格权条款的功能表现在司法实践中,便是一般人格权的泛化与滥用。有学者在研究新兴权利时便指出“所谓的新兴权利(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存在着强烈的将一般人格权泛化的倾向”[1]。因此,有必要对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侵权条款进行区分,并对一般人格权进行划界。本文尝试对一般人格权的边界进行讨论,提供一个可行的识别方法,以对实践中一般人格权纠纷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一般人格权权益边界的识别
关于一般人格权的客体范围,许多学者借鉴德国法,认为一般人格权就是为实现个人自由发展而不可或缺的人格利益[36]。按照德国《基本法》的规定,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保护的重点,应通过人格尊严来囊括实践中纷繁复杂的人格利益[37]。而根据德国经验,德国仅在民法典中确立一般人格权规则而不宣示其价值基础,从而将一般人格权规则蕴含的法律原则或价值基础交予司法实践,由法官在个案裁判中实现法律对人的尊重与保护。德国法官常将其民法典体系中的基本内涵通过具体构成要件一一拆解,并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裁量,体现法律的价值追求。此种做法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法官在个案中具体适用一般人格权规则时,能够对所要保护法律进行充分的正当性论证;同时,法官的自由裁量实际上具有强大的涵盖能力,能够充分包容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兴利益。但与德国不同,我国在立法时便已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因此,在我国,新兴权利的识别不应当全然照搬德国经验,而应当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进行。在如何识别新兴权利这一问题上,学界有着不同的主张。有学者试图对其正当性进行论证,但仅仅只是从法理角度阐述权利的正当性[38];有学者提出以公序良俗为依据来保护已被社会认可的非具名权利,运用利益衡量、权益比较原则来权衡诉争案件当事人各方利益与社会利益,以判定这些利益是否需要予以保护[1,34]。但是应当注意到,以上方法并没有直接对一般人格权的范围进行界定。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更精细的方案,以作为个案中的权益衡量的路径尝试。从一般人格权的条文来看,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单独作为权利加以保护有所不同,我国《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将一般人格权定义为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不再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一种权利。学界对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是否应当作为一项权利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在理论上可成为单独的权利,能集中体现人格权利中的一般价值,具有补充法律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利立法不足的重要作用[39]。但也有学者指出,人格尊严不应当作为权利被识别,而应当被视作权利保护的价值基础[31]。这些观点实际上都认为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利益应当被法律保护,但我国对权利与权益并不区分保护,在都认为该利益应当保护的前提下,探讨将此二者区分并无多大裨益。且两派观点都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内涵应当包含一些未被法律识别,但与人格尊严、人的价值密不可分的权利,因此,两种观点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结果其实区别不大。我国《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未将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本身作为一种权利表述,而是采用了“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利”的表述,表明立法者将人格尊严视为人格利益的基础价值。从法条文义出发,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衍生出来的人格利益,就是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客体范围。对于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的边界识别问题,笔者尝试提出一种两步走方案,先对权益进行类型化检测,再对权益识别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以此来构建一般人格权的边界识别框架。
(一)权益的类型化检测
本文认为,在遇到案件时,应当对权利的类型进行检测,看其是否能被其他具体权利所涵盖。这里要避免动辄适用一般条款的倾向,否则将使其他具体的人格权条款失去意义。进行权益类型化检测时,要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还要区分新兴权利与人格权利。
1.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在人格权编中,法条中有许多已经类型化的人格权利,如姓名权、荣誉权等,应当避免一般条款的优先适用。如果动辄适用一般条款而忽视具体条款,那么实际上是削弱甚至架空了具体人格权条款的作用,使这些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因而,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先区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只有当扩大具体人格权解释仍无法包含讼争利益时,才有必要考虑动用一般人格权予以保护。
2.区分新兴权利与人格权利。法院应当识别诉争权利是否与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相关。若不是,则应将该讼争利益排除在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如前所述,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人格权泛化的倾向,常常将未被法律识别而应当予以保护的利益纳入一般人格权条款加以保护,但一般人格权不应当成为所有新兴权利的口袋条款。一般人格权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而保护基于个人尊严与人身自由而产生的人格利益[28],而新兴权利是被社会广泛接受但尚未被法律肯定的自然权利[45]。可见,新兴权利实际上是一般人格权的上位概念,其范围包括了那些未被法律识别的人格利益。因此,应对案涉权利或利益进行具体检验,不能仅因为是新兴权利就纳入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从我国《民法典》一般人格权条款的文义出发,应当将一般人格权保护的范围仅限于基于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产生的人格利益;反之,那些价值基础非源自于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的权利或利益,则不属于此范围。按这个标准来区分,基于特定纪念物损坏、有纪念意义的事件的违约,不能诉诸一般人格权保护,因为其本质是基于物或事件而产生的,纪念性意义仅仅附着其上,因而,因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永久性灭失而请求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不能纳入一般人格权纠纷中。在实践中,有法院将“由于被告的过失将婚礼摄像资料永久性灭失”侵害了享有结婚美好回忆纳入一般人格权下辖范围[40],但此类纠纷本质仍是物权纠纷,侵权行为侵害的直接对象仍是物,而人格利益仅因其附着于特定物上而受间接侵害,因此,其与一般人格权要保护的客体,即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并不契合;况且,《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已为该种情形提供了救济的规范基础,不能也没有必要将其纳入一般人格权纠纷之中。同样的道理,被遗忘权、生活安宁权的利益也与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无关。实践中,以披麻戴孝闯进别人院子中的方式讨债而产生的纠纷[41],或是以短信的方式过当推广产品产生的纠纷[42],都与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没有关联,不应当纳入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中。
(二)权益识别的必要性
权利的识别通过判断讼争利益是否已经被具体人格权涵盖,以及是否与人格利益相关,已经能大概勾勒出一个基本的权利范围,接下来,应对原告诉求的权益是否值得保护进行判断。先分析该权利是否已被其他法律识别与保护,若无其他法律将讼争权益界定为权利,则对识别该权益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综合判断该权利是否应当保护。
1.其他法律已识别。其他法律已识别是指其他法律明确规定了某项利益受到法律保护。实践中也常有法院引介其他法律以肯定讼争利益值得保护。如在宋某诉李某群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双方就女方擅自打胎是否侵害男方权益产生争议时,法院就引介《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关于“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43]。再如陈某弟与徐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亦涉及生育权纠纷,法院就女方是否有权拒绝冷冻胚胎植入体内作了如下阐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的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故男性也当然享有生育权,与女性享有的生育权是平等一致的。生育权的客体是权利主体自主决定生育所体现的人格上的利益,作为权利的主体,有权支配自己的人格利益。且生育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行为,不可能只靠单方便能实现。因此,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实现这个权利。”[44]另外,在就业遭受歧视的案件中,法院也援引我国《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的规定肯定了平等就业权[45]。可见,当某项权利已被其他法律识别时,法院如想支持讼争权利,则多会转介其他法律条款,以减轻其论证义务。但法院在转介这些法律条款时,常忽略这些法律条款的性质而直接适用。应当认识到,转介其他法律条款以论证被告侵犯原告权利的前提是该法律条款赋予了原告诉权。如果该条款仅仅只是宣示性条款,则原告无法依据该条款获得救济。而识别保护性法律是否赋予了原告诉权,应当明确这样的条款仅限于除宪法外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而不包括行政规章。原因在于,我国《宪法》作为根本法,其设定的权利一般在其他法律中有所体现,故无需引用根本性权利对案件进行说明。此外,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4条来看,法院可以在民事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故这些法律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能够当然作为侵权法保护客体的依据。因此,此类条款的范围应当限制在除宪法外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规范类型中。
在实质识别上,有学者参照德国经验,认为只有当被告违反了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违反了禁止性规范课以的义务时,才能承担侵权法上的责任[46]。这样的判断要结合立法目的及规范类别来判断该条款进行,且为了保护该特定利益,该规范应对行为人课予一定的义务。上述判断在美国侵权法中也有所体现,且其参考因素更加具体,也更有利于法官综合把握。美国侵权法重述中给出这样的参照:如果该法保护特定人群(class of persons)的利益,该法规定的特定利益被侵犯造成一定损害,且该损害与法律为免除特定利益损害契合,则可以认为该法律赋予原告诉权(cause of action)[47]。按照这样的标准,在被告没有购买道路交通保险(有法律规定摩托车司机应当购买保险)出车祸造成原告损害的情况下,原告可否依照违反该法律而认为被告没有购买保险侵害了原告的利益呢?法院认为不行,因为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摩托车驾驶人出现危险时有保险能够覆盖其救治费用,而非为了保护其他行人,因此该法没有赋予原告诉权[47]。上述美国做法亦能给国内的审判提供一些参照。在上述标准下,要识别某一法律是否旨在保护原告,则需判断该保护性法律的规定是否是为了防止讼争损害发生。如果不是,应当认为该法律并非旨在保护原告,因而只是一般宣示性的条款。另外,对于立法目的,则应当结合违反法条的法律后果,综合运用解释方法来考虑。
2.基于个人尊严与自由必须确认该权利。在缺乏相关法律规范,或存在法律规范但该规范没有赋予原告诉权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该利益就被拒于司法保护之外。在相关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实质性判断,即综合社会利益、公序良俗等进行个案判断,以确认个案中某一讼争利益是否值得法律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利益识别与责任承担是2个不同的概念,应当明确加以区分。利益识别是责任承担的前提,即使法院认为原告讼争利益应当保护,也无法当然推论出此时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判断完毕讼争利益值得法律保护后,仍应按照一般侵权的过错原则,判断被告是否侵害原告的权利,原告是否遭受损害,以及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同时,还要考虑同案同判的效应,即一旦该讼争权利被司法识别,则该权利就被法律肯定,那么之后遇到相同利益诉求的案件,该种识别应产生拘束力;否则,会降低法的可预测性。
关于如何综合各方利益判断是否应当予以保护,美国侵权法提供的利益识别参考因素值得借鉴:被告预见给原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大小,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遭受的伤害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被告行为让原告遭受伤害的确定性程度,被告的行为道德的可谴责性损害预防的法律效果,被告的负担程度,对社会和司法系统的后果,保险的可获得性[48]。这些因素给复杂案件的个案裁判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如男方隐瞒已婚事实与女子发生性关系,女子诉请赔偿案件,在分析欺诈交往行为是否应当给予女方一定补偿时,应当考虑男方行为导致女方精神损害的可能性大小、男女双方主观过错、男方行为的道德可遣责性等因素并综合判断。再如生育权纠纷案,若女方不顾男方反对生下小孩,男方能否要求女方因侵害其生育权而予以赔偿?此时应考虑男方在发生性行为时,便应当意识到女子有怀孕的可能,因而可以预见自己将为人父的可能,且女子对自己身体亦有支配的权利,如男方强制要求女子终止妊娠,则实际侵害了女子的生育自由,该强制终止妊娠的要求具有道德可遣责性,因此,男方不得要求女方承担侵害生育权的责任。类似的,在侵害祭奠权、安葬权等逝者安葬类型的案件中,考虑到我国素有生养死葬、祭奠先人的传统,此时的恶意扰乱行为道德可遣责性高。规制这类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类似恶意阻扰死者安葬案件的发生,因此,识别该种利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可见,这些参考因素能给法官处理棘手案件提供一些参照。但在个案裁判时,仍然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分析被告过错程度、行为带来损害的可能性、因果关系等。当然,在思考上述因素时,不能忽略我国的具体国情。
四、结语
本文尝试提出两步走方式来识别一般人格权的边界,即先判别该权益类型,再对该权利是否值得被法律肯定作实质判断。笔者认为,一般人格权作为一种总括性权利,在适用时应当劣后于具体人格权,即一般人格权保护的是不能被具体人格权所涵盖的、与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相关的正当法益。这就意味着,应当先识别争议是否能够被类型化的具体人格权涵摄。如果是,则应当优先适用具体人格权。法院还应当识别该讼争权利是否与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相关。如果不相关,则该利益就是非基于人格利益产生的利益,则应当诉诸一般侵权条款,而不应当适用一般人格权条款予以保护。经过上述分析后,在判别与人格利益相关的讼争权益是否需要保护时,应当先看是否有其他法律已识别该权益。在其他法律已识别讼争权利的情况下,还应当判断其他法律条款是否赋予该权益被侵害时的诉权。如果其他法律没有明确赋予诉权,则原告不应当根据该条款提起侵权诉讼。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原告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在法律没有赋予诉权的情况下,应当进行利益权衡,综合各种因素判断是否应当对该利益予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