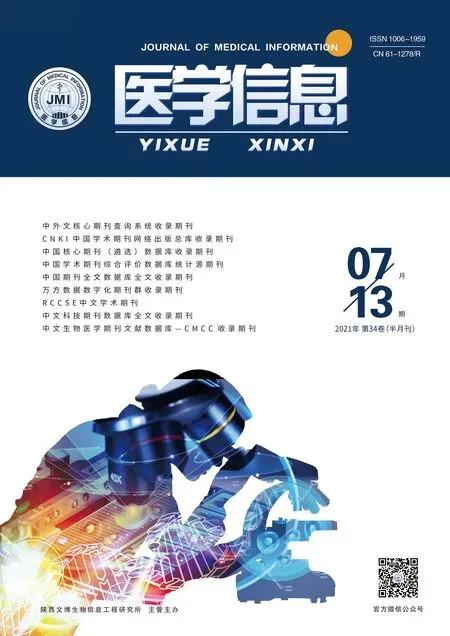急性骨骼肌损伤实验动物模型种类和选择
严名扬,唐臻一
(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急诊科1,骨伤科2,天津 300400)
骨骼肌是人类自主活动得以实施的主要物质基础和功能保障。不仅作为行动力量的提供者与协调者,而且骨骼肌功能的正常发挥能有效表现出生命体存在的现实价值。在各种类型创伤中,肌肉组织损伤所占的比率相对最高[1]。急性骨骼肌损伤(acute skeletal muscle injury)发生于各种机制,包括直接原因(挫伤、挤压、拉伤、扭伤、撕裂伤)和间接原因(例如缺血、神经功能障碍)[2-4]。由于损伤后肌肉组织血肿机化、瘢痕修复,对活动能力、生活质量构成现实的威胁;因此研究骨骼肌损伤的发病机制,了解其病理特点和临床转归,探讨相关的预防、治疗和康复措施等,一直是临床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5,6]。对骨骼肌损伤发病机制的实验研究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损伤模型基础上,各种动物模型的建立适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针对不同类型的急性骨骼肌损伤模型,各损伤造模机制、肌群、实验动物种属等方面的选择成为课题,本文现对急性骨骼肌损伤实验动物模型种类和选择进行综述,旨在为此类实验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
1 骨骼肌急性损伤的动物实验模型
在对骨骼肌损伤的研究中,准确地建立、复制出与人类疾病一致的动物损伤模型,是相关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有关骨骼肌损伤的实验研究,主要针对于骨骼肌疾病的病因研究,故实验性动物模型多采用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等损伤因子,对骨骼肌直接实施损伤,以此模拟并研究骨骼肌疾病的病理过程。动物实验模型可复制出骨骼肌急性损伤的典型病理变化,对深入骨骼肌损伤的实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目前根据损伤病因、实际操作等情况,常见的急性骨骼肌损伤模型采用的技术有:毒素注射、重物挤压缺血、缺血再灌注损伤(橡皮筋/止血带阻断缺血)、失神经支配、冷热损伤、重物坠落、挥锤、锐性不横断切割、游泳/上下坡跑、电刺激损伤等张收缩、拉伸、基因敲除或细胞等成分剔除,其它疾病引起的骨骼肌损伤模型如周围血管疾病、COPD 等。常见的急性骨骼肌损伤模型有毒素注射模型、肌肉拉伸实验模型、电刺激损伤模型、下坡跑骨骼肌损伤模型、骨骼肌撞击伤模型、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神经损伤模型等,这些模型的制作为急性骨骼肌损伤的研究奠定了实验基础。每项实验模型技术均对应于相应的动物模型,所诱导的模型建立在不同病因基础上,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1.1 开放性损伤模型
1.1.1 开放性肌肉牵拉伤模型 肌肉牵拉伤是因为肌肉主动强烈收缩(主动向心收缩)或被动过度拉长造成(被动离心收缩)引起的肌肉微细损伤,甚至肌肉部分撕裂或完全断裂[8]。这是一种最常见的骨骼肌急性损伤,其实质是肌肉组织承受过度载荷所致,易发于双关节肌或多关节肌,尤其是发生在快缩肌比例高的肌肉上(如腓肠肌),且肌肉拉伤的位置多发生于远端的肌肉肌腱移行部位。
常规对大鼠的目标肌肉进行远端外科手术,暴露其肌腱,特制夹具夹持离断的肌腱,以6 cm/min拉伸速度实施拉伸,用示波器显示并记录载荷—变形曲线,当曲线进入平台期,拉伸停止;拉伸结束后将肌腱缝合到伸肌支持带上,并缝合刀口,完成目标肌肉被动拉伸实验模型。有研究运用定负荷自由落体的方法复制了肌肉拉伤[8],其具体方法如下:大鼠麻醉后,将准备拉伤一侧的下肢膝关节固定,踝关节游离,用电刺激仪刺激腓肠肌两端,引起腓肠肌强直收缩,使踝关节跖屈。与此同时,一重物从固定高度自由下落,通过系在动物足上尼龙绳上的铜丝,以一个基本恒定的初始冲量迫使踝关节迅速背屈,腓肠肌离心收缩而被拉伤。拉伸载荷达到极限断裂阈值80%时,其肌纤维断裂可蔓延到远端肌腹部分;拉伸载荷达到极限断裂阈值90%,肌纤维断裂进一步向肌腹部分蔓延,并有肌组织的横向结构和附属组织(肌外膜、肌束膜、肌内膜)发生断裂[9]。
1.1.2 骨骼肌割裂伤模型 骨骼肌的断裂模型常常采用割裂伤技术,肌肉切割伤多由锐器暴力引起,组织断端比较整齐、血运良好,创面污染情况决定于损伤时的环境,严重者可离断肌肉或肌腱等[4]。该模型不需要借助大型或特殊的仪器设备,易于复制,且损伤后的病理生理变化与拉伤损伤后的一致。对于该项实验的组织学研究,关键是其损伤部位定位准确和一致性的损伤程度。但该模型同样面临手术通路所引起的副损伤对模型炎症反应等相关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良影响。
该模型的优点是肌肉损伤程度的一致性,为损伤肌肉不同治疗措施效果比较研究提供了保证。但存在的问题是与活体肌肉拉伤在生理及力学特性方面发生的形变较大,难以准确反映日常活动、训练比赛中肌肉拉伤的各种特征。开放性的伤口和操作所引起的炎症反应,和骨骼肌组织损伤的炎症反应与损伤修复过程发生相互影响,进而对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产生负面作用;并且拉伸实验装置和夹具选择也对实验本身产生相关的影响[10]。
1.2 闭合性损伤模型
1.2.1 闭合性电刺激肌肉牵拉伤模型 为消除造模过程中手术操作和皮肤伤口对模型稳定可靠性的不利影响,采用各种电刺激方式的闭合性肌肉牵拉伤模型被开发出来。单向慢性低频或高频电刺激导致的电刺激损伤模型,是研究骨骼肌机械性和物理性适应变化的一个很好实验模型;其变化常在短时间内发生在受刺激的肌肉,在肌肉损伤及神经肌肉功能失调等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张胜年等[11]采取两根银质针电极,刺激仪以50 V 电压刺激胫后肌群强直收缩、踝关节趾屈;同时,拉伸实验机以0.55 m/s 的速率反向牵拉大鼠足底固定板,迫使踝关节背屈,牵拉小腿三头肌离心收缩,造成该肌肉急性中度拉伤。
1.2.2 力竭性骨骼肌损伤模型 力竭性骨骼肌损伤是骨骼肌损伤的主要类型之一,多见于周期性的耐力运动项目和长期的肌肉兴奋。是因反复运动所致的肌纤维损伤,并且易发于骨骼肌离心运动时相,故下坡跑运动性骨骼肌损伤动物模型,以驱使动物在一定斜度的动物跑台上进行周期性的下坡跑等训练方式最为多见。Armstrong RB 等[12]对大鼠在坡度为16°的跑台上,以16 m/min 的速度持续90 min 下坡跑,导致肌纤维损伤发生,复制出运动性肌肉损伤模型。田野等[13]对大鼠在同样的环境下,改变下坡跑训练的持续时间和间隔,复制了力竭性骨骼肌运动损伤模型。刘姣等[14]通过递增负荷跑台运动设计一次性力竭运动模型。此外,张宏梅探讨了游泳力竭性骨骼肌损伤模型[15]。
在动物下坡跑运动性损伤模型中,肌肉抵抗体质量形成的运动负荷而进行离心收缩做功。动物最主要的工作肌群是前肢的肱三头肌、前臂屈肌群,故取材以实验动物的前肢为佳。对于跑台的斜度,根据Armstrong RB 等[12]的研究,16°是大鼠下坡跑时不打滑的最大斜度,但在实验研究中,由于跑台的胶带质地、材料不同,斜度可以适当调整,斜度越大,模型复制效果应该越好。但这类型模拟的是中轻度的骨骼肌损伤,并在中长期的观察中,损伤的骨骼肌一般均能自我恢复;对临床的实际意义不高;并且造模过程时程较长,实际可操作性欠佳。并且不同的运动方式、不同的力竭强度对骨骼肌的损伤和后期修复产生的作用具有差异性[16]。
1.2.3 骨骼肌撞击伤模型 骨骼肌撞击伤是钝性暴力直接作用于机体某部位而引起的肌肉急性损伤,常发生于接触对抗类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武术等运动)、社会工业生产、公路交通事故中,以大腿和小腿及躯干等部位最为多见。
使用撞击伤作为骨骼肌损伤的非侵入性模型,在研究免疫系统与肌肉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是必须的[17]。早期使用重物坠落技术的肌肉挫伤模型已广泛应用于骨骼肌损伤研究。Bunn JR 等[18]设计了两个撞击能量的损伤,表明骨骼肌的损伤程度在一定范围内与致伤能量成正比,并且高能严重的骨骼肌损伤在后期募集的巨噬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可能是导致骨折延迟愈合和不愈合的原因。Deane MN 等[19]通过对骨骼肌损伤的浅层(近皮下侧)和深层(近骨骼侧)肌组织的形态学等分析,总结出评价骨骼肌损伤的新模型和方法。严名扬等[20]采用具有冲头定位的撞击伤器械在腓肠肌建立了严重的骨骼肌损伤模型。Paun B 等[21]、吴安林等[22]在兔骨骼肌钝挫伤模型的制备、打击力度的关系和分期等方面对该技术进行了具体实施。
但是,这种损伤模型的局限性包括以下几点。一方面,这些模型并没有将腓肠肌从下面的骨骼中分离出来,这使得撞击反应变得复杂,并且常常因为导致的骨折阻碍了严重的肌肉创伤的模拟;另一方面,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伤害势能的参数(质量和高度)在几种挫伤模型中是不同的,理论上会导致撞击反应和组织损伤的差异[23,24]。迄今为止,仍缺乏使用具有可变参数的致伤势能的重物坠落技术对从下方骨骼分离的受损腓肠肌中的撞击反应的研究。
1.3 特殊损伤模型
1.3.1 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 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常采用肢体重物持续挤压和血管持续夹闭两项技术。骨骼肌常常因长时间缺血而引起组织器官损伤,且再灌注导致组织损伤加重,即所谓的“缺血/再灌注损伤”,而氧自由基则贯穿于这一损伤的全过程。
Akimau P 等[25]使用3 kg 的重物压迫大鼠小腿6 h、再灌注3 h 的方法设计了挤压伤模型。通过观察损伤区域巨噬细胞和形态学等变化,设计了血管持续夹闭通过股动脉闭塞2.5 h,再灌注2 h 建立模型[26]。张景达等人使用无创型动脉夹阻断右股动脉4 h,灌注24 h 建立缺血模型;并采用缺血和灌注之间,加入“实施4 个循环30 s 再灌注/30 s 缺血”操作,以建立缺血后调适组[27]。
1.3.2 烧伤、毒素损伤模型 da Silva NT 等[2]使用腓肠肌烧伤模型的研究表明炎症介质COX-2 等的释放能减轻骨骼肌的退变。同时,采用蛇毒毒素类的心毒素单次肌内注射,引起肌纤维溶解,诱导小鼠急性骨骼肌损伤后再生、修复机制[28]。缺血再灌注模型的建立主要考虑的是缺血时间和再灌注时间对损伤的影响。但通过重物挤压肢体引起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和夹闭血管引起的骨骼肌再灌注损伤,在组织学和全身炎症反应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并且两组对应的临床病症也有所不同。相对来说,肢体挤压所造成的损伤更严重,更加接近于临床上的现实状况。除了缺血本身的完整性以外;其它因素,如遗传背景等,也会影响急性缺血性肌肉损伤的程度[29]。
2 动物模型和肌肉的选择
骨骼肌损伤病因的多样性决定了相关损伤模型的多样性。对于具体的动物模型的选择还需考虑以下因素:发生于人类身上的损伤的严重程度存在个体差异,如有些模型需要采用有创操作及实验取材进行的有创操作,这些基础性的因素使对骨骼肌损伤,特别是进一步阐述诸如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在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中发挥的准确作用和调节机制的研究更复杂。并且各物种(包括人类)之间对于损伤的修复也存在着种属差异,而采用实验动物难以消除这些差异,此外还涉及到医学伦理等因素。
2.1 模型选择 损伤后的炎症反应是机体启动修复程序所必须的,因此损伤病灶区的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成为了骨骼肌损伤研究的焦点。对于涉及免疫炎症反应、信号通路等研究的整体而言,骨骼肌损伤模型应尽量减少造模过程中非主体结构的损伤。相对于非侵入性的造模方式,侵入性的(开放伤口/针道)造模方式需在实验设计上排除侵入操作对实验目的本身的影响,即使模拟的是开放性损伤类型也应该一样。
重物坠落技术导致的撞击伤模型研究应用广泛,无论是否存在骨骼肌群的暴露,多数研究采用单次撞击。早期重物坠落技术采用了平滑的撞击平面,并通过调节坠落高度致损特定的肌肉。有学者使用此类侵入性模型进行了损伤病灶和全身炎症反应的相关研究。Bunn JR 等[18]的研究显示,虽然骨骼肌伤后存在IL-1β、IL-6 和TNFα 水平改变,但是该研究缺乏假手术组进行对照,难以说明手术操作本身对相关细胞因子释放的影响。由于骨骼肌损伤的炎症反应和手术副损伤的炎症反应在同时期启动、活跃,可能进一步影响实验结果。因此,在探讨骨骼肌和免疫系统之间关系需要采用骨骼肌损伤的非侵入性模型进行研究。
非侵入的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主要使用重物对肢体的压迫或夹闭责任的血管等手段导致长时间的血供中断[25]。造模过程中没有造成撞击性暴力损伤,其骨骼肌纤维形态结构在血液灌注前一般能保持初始结构。缺血再灌注损伤和“二次打击”的研究模型适用于肢体挤压伤,并更多的用于其对全身其它系统器官的损害的研究。因此不是研究骨骼肌损伤修复机制的理想模型。虽然应用钳子夹持的挤压伤能很好的定位目标肌肉和损伤区域,但改方法仍然需要手术暴露,徒手夹持的力量大小也难以统一衡量,且机械性夹持也可能因夹持不均匀而影响研究结果。
重物坠落技术作为常规的骨骼肌撞击伤模型,具有无创、可调节、操作简便等特点。但此模型存在设备装置较复杂不易获得、拟致伤骨骼肌部位固定欠佳、致伤程度不均匀、容易导致皮肤破损和骨折等问题。为避免开放性造模和肌肉损伤单位的模糊性设计了定位冲头,该系统引入了一个接触目标肌肉和起定位作用撞击冲头,并且该冲头的使用还具有缓冲作用,有效降低了高频撞击的影响,同时将直接撞击变为间接撞击,从而实现了技术的进一步改进。
2.2 肌群的选择 不同类型肌纤维的血管化程度不同,导致不同的肌纤维类型表现出不同的代谢表型。需氧的Ⅰ型纤维通过高度的血管化为肌纤维提供丰富的血供和营养。相反地,Ⅱb 型肌纤维为非氧依赖型,其毛细血管供应较Ⅰ型纤维明显减少。虽然整块肌肉一般由多种肌纤维混合而成,但是其特性会因不同的肌肉、个体差异、物种类型的不同而不同。目前,骨骼肌挤压伤研究的动物模型主要包括腓肠肌[30,31]和胫前肌[32]。虽然这些肌肉均含有Ⅱb 型肌纤维,但是只有腓肠肌是混合型肌肉,并含有Ⅰ型纤维。此外,腓肠肌形体相对来说较大,适合各种造模操作,而不影响骨骼,对于有利减轻痛苦及伦理审查均有利;此外,还能有效降低因骨折和周围组织损伤所释放细胞因子,有利于相关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腓肠肌与肱二头肌形态相似,为扁平的长肌,常在对抗类运动中发生撞击伤。因此,腓肠肌被认为是研究骨骼肌损伤后机体反应、修复机制的理想肌肉。
受免疫和细胞因子系统的影响,不同的肌纤维类型分泌的细胞因子会有差异,如人类三头肌、比目鱼肌等在休息状态下时TNFa 和IL-18 只在Ⅱ型纤维中表达,IL-6 主要在Ⅰ型纤维中表达[33]。单个肌肉挫伤后线粒体功能的急性反应在快速纤维、慢速纤维等不同类型肌纤维中表现也不同[34]。此外,肌肉组织在破损、修复和重塑等阶段中纤维类型的差异尚需进一步研究。
2.3 实验动物的选择 啮齿动物是目前生物医学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模型动物。近年来研究显示,小鼠在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大鼠相比更加突出,这种转变主要是与小鼠模型有一个更大的遗传工具库可用有关,特别是基于胚胎干细胞的靶向基因技术。近年来改变大鼠基因组的工具,特别是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出现使两种啮齿动物之间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为特定的生物问题选择正确的模型系统时,大鼠和小鼠之间的生理、解剖、生化和药理学差异变得越来越重要[17]。
尽管常用的大鼠(Wistar 和Sprague Dawley)和小鼠(C57BL/6 和Balb/c)同属鼠类,并且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但在影响疾病研究模型选择方面,特别是在神经认知和肌肉运动领域存在差异。比较不同小鼠或大鼠模型的研究发现了两组在种属和种群层级中均存在实质性差异,这也表明大鼠和小鼠之间的全部变异程度可能尚未被认识[35]。Ellenbroek B 等[17]的研究显示,大鼠和小鼠在认知、成瘾、冲动和社交行为的基础研究中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反应,并且证明了神经变性程度的差异,说明相比小鼠,合理地选择大鼠模型作为人类疾病的“最佳”模型的重要性。此外,在结合基因敲除技术的急性骨骼肌损伤模型修复过程中,同一种类动物的不同年龄段也表现出差异[36]。
3 总结
建立有效的动物模型是研究骨骼肌损伤问题的首要环节,目前大量的模型建立为骨骼肌损伤的研究奠定了实验基础。但在实验中,动物炎症反应的启动、免疫应答的途径、各种促进修复的细胞群体的募集方式、工作性质与自然生理状态还存在较大差别,故建立更接近生理状态的骨骼肌动物损伤模型及符合运动实践的肌肉损伤模型,对深入骨骼肌损伤的实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以骨骼肌为实验靶器官的研究应该首选腓肠肌、胫骨前肌;在动物种属选择方面,大鼠是实验动物伦理、实验技术和实验物种与人类疾患相近度等方面最合适的备选。而致伤因素的选择决定于具体实验的目的,操作的简便性和标准的统一性最容易接受。因此,在同等条件下,非侵入的实验模型更有利于实验的有序进行和实验数据采集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