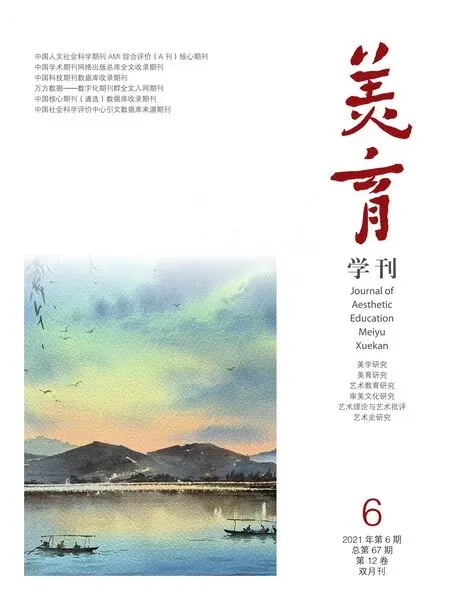李叔同的“人格美育”思想与实践探析
张 荀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福建 厦门 361012)
李叔同—弘一大师,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丰碑。他不仅是艺术家、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也是高僧大德。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俗时的求学,从事教育实践,还是出家后的修习律宗,都以人格完善作为追求,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格魅力的典范。李叔同对自身的人格完善的要求,融入了当时先进的美育观念,由此产生了“人格美育”的独特思想。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这种“人格美育”思想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李叔同的学生、亲近的弟子以及出家后结缘的各界人士。而这种“人格美育”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篇章,且在今日弘扬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演进中,具有“薪火传承”和“温故知新”的积极意义。
本文首先是梳理李叔同的教育背景,对李叔同“人格美育”思想的文化渊源进行分析,借此来分析建立完善人格、养育审美之心的审美主体在客观与主观两方面所产生的人生论;其次是分析李叔同如何以“器识为先”的思想为先导,阐发并践行“人格美育”;第三就李叔同“美而善”“温而厉”“行胜于言”的“人格美育”特征进行探讨;第四是探讨从李叔同到弘一大师,他前后一以贯之倡导的“艺以人传”和“德行兼备”的人生内涵,并以此来提升“人格美育”的人生境界和生命高度。
一、以完善人格来养育审美之心的文化渊源
“人格”在西方各学科中是一个不太容易界定概念的词汇,但大多数学科都倾向于将“人格”概括为人的内在道德和情感品质,而培养人格或者说完善人格,即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健全、健康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特征。
在李叔同的“人格美育”思想中,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德”“养人”“养心”的人生观,还具有西方文化与美学的人文精神。完善人格的树立,作为李叔同“人格美育”思想的核心,其文化渊源值得深入探索。梳理李叔同的教育背景和社会环境,能更好地了解他的“人格美育”思想的生成环境,寻找出李叔同“人格美育”思想的文化源头和理论支撑。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养人格道德”的文化渊源,李叔同的“人格美育”思想基础,来源于幼年时家庭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教育。人格建立之完善,是中国文化教育恒久不变的主题。李叔同5岁开始就在母亲王氏的教导下诵读古代名诗格言,9岁开始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儒家理学中的人格建立、存理自律、去欲从善等思想,给年少的李叔同以丰厚的人格文化滋养,使青年时期的李叔同虽然生于富贵之家却不沉迷享乐,而产生出励志勤勉、忧国忧民的性格气质。
在学习儒家文化的同时,李叔同还学习了书法、篆刻等传统艺术,这也成为他日后走上艺术道路的契机之一。“人品不高,落墨无法”,中国传统书画文化中强调,艺术家作为创造美的主体,需建立起高尚而完善的人格,从艺者必须注重品行,养成艺德。书画追求的“艺德”与儒家“仁”“乐”等思想,包含了对艺术家道德的尽善与艺术的尽美缺一不可的要求。因此,“道艺兼得”的思想实质上就是以一种完善人格来养育审美之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很早就在在李叔同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直至1935年,出家后的李叔同—弘一大师,为泉州温陵疗养院的“过化亭”补书牌匾,回忆自己在俗时即与朱熹儒学文化很有缘分,他在题记中说:“余昔在俗,潜心理学,独尊程朱。今来温陵,补题过化,何莫非胜缘耶。”[1]对李叔同来说,从小就崇尚道德,不放松对审美主体的人格涵养,首先就来源于家庭的“养德”教育。从“养德”到尽善尽美,这得益于李叔同的家庭给他的教养,而这种教养的背后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完善人格追求的文化渊源。
其次,李叔同“人格美育”的思想发展,有来自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这与他的出国留学前在上海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传统中国文化中,培养和完善人格的任务,主要交给儒家学说的自省自律和社会道德的自然约束来进行。而在20世纪初,中国以往“为往圣继绝学”的儒家教育渐渐式微,新教育理念的“与时俱进”,教育改革的“西风东渐”,使思想界的视野更加开明与开放。这个时期以美育为代表的新教育思想,吸取西方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当时的审美和伦理道德相结合,逐渐探索适用于中国的人格教育方式。当时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提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2]他把西方美学理论和中国的美学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近代美育的新观点:“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3]在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他不断摸索,以立足传统、美育救国的方式,积极地推行从审美教育到提升国民审美素质的人格美育方式。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说:“修身,德育也,而以美育及世界观参之。”[4]蔡元培的美育理念认为,一个完整健全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塑造全面完整的人,也正是美育的宗旨。
1898年,李叔同来到上海,接触新式教育。1901年8月,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特科班学习,师从蔡元培,开阔了视野,吸纳了西方的新文化,更受到了蔡元培早期美育思想的影响,这为他后来留学学习西方艺术埋下了伏笔。蔡元培“健全人格”的美育文化渊源,和李叔同之前接受的中式人格培养方式十分吻合。在这段时期里,李叔同积极学习外语,在蔡元培的提点下翻译国外论著。同时他结合文艺方面的特长,试图将宣传文艺美、养育审美心,同完善人格、改善社会风气联系起来,如创作爱国歌曲《祖国歌》和抨击封建包办婚姻的《文野婚姻》剧本等。西方文化中的平权、科学、民主、艺术教育等思想,逐渐融汇到李叔同思想中,并产生了积极的精神引导作用。
第三,李叔同“人格美育”的思想形成,经历了从儒学、西学到艺术学的自我完善历程。
审美主体的人格气质,更主要是取决于自我心性的完善,也就是人格的完善。见贤思齐,是李叔同从学之初就立下的志向;追求尽善尽美,是李叔同从小即具有的气质秉性。在社会激烈变革动荡的背景下,1905年李叔同怀揣救国梦想,遵循着美育思想的方向,东渡日本留学,在当时鲜少有中国留学生考上的东京美术学校修习西洋画科,这代表了他选择以艺术学习作为“人格美育”发展方向的思想觉悟。
李叔同经历了南洋公学求学和到日本留学的时期,接触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又在学习西方艺术的过程中将两种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碰撞不断消化,进而在“人格美育”的思考上逐渐完善。美育可以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体验和艺术美学的学习与研究,把审美特点、审美情感、审美表达体现在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等方面。这成为李叔同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后而选择的互相交融的一种文化态度,把外求艺术美与内求做人的心性结合起来,最终成为完善“人格美育”的教育思想核心。
1912年秋,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一师”)校长经亨颐聘任李叔同为图画、音乐教员。经亨颐主张注重人格教育,他曾提出“凡学校皆当以陶冶人格为主”,“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5]。他还主张不能把学校当成“贩卖知识的商店”,“教授,当为锻炼人格为目的之教育的教授”。经亨颐的一系列教育主张与蔡元培的思想一脉相承。而当时的这种教育氛围,恰好与李叔同的美育志向一致,促使他开风气之先,积极投入当时学校的“人格”的教育实践。在六年左右的教员岗位上,他强调生理与心理的协调,强调个性与群性的一致,强调知、情、意的统一,强调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将学习艺术与培养审美心作为途径,促使学生们的人格在审美心性的陶冶中转变。
“人格美育”思想的文化渊源,东西方文化具有相近的认识,都认为因不同的文化土壤,可以对人格建立产生重要影响。而兼容并蓄,吸取中西思想中的审美要求,强化艺术美学研究和审美体验,并将其运用于传播文化、宣传思想中,这不仅符合年轻的李叔同的心愿,也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教育需求。李叔同的“人格美育”思想,因他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生活经历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逐渐形成。
二、以“先器识而后文艺”作为“人格美育”的思想资源
中国文化史上“知行合一”的人生观、“德智并举”的教育观、“天人和合”的美学观,与李叔同的“人格美育”的实践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李叔同极力提倡的“先器识而后文艺”,既接受了传统东方“人格美”的精神,同时也接受了西方当代“人文美学”的精神,这对他后来以“器识”“文艺”为方向进行美育实践,运用实践艺术之“术”建立人格完善之“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先器识而后文艺”代表着李叔同“人格美育”思想的中心,以“器识为先”,才能“道术兼尽”,最终才能实现“道艺兼得”的人格教育目标。在研究李叔同的“先器识而后文艺”思想时,可以通过三方面来理解“人格美育”的实践功能。
第一,追求“人格美育”的自我完善功能。李叔同自1905年8月赴日留学,笃志学习图画与音乐艺术,至1911年3月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归国,他把图画和音乐的艺术学习,作为完善自我人文教养的途径。留日期间,李叔同师从日本印象派油画鼻祖黑田清辉学油画,努力跟上时代美术的步伐,其现存的几件油画作品具有非常浓厚的西方印象派油画特征,成为最早使用印象派技法绘作油画的中国人[6],并且在1911年以西洋画撰科四名毕业生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校外,他师从上真行(梦香)学习音乐和戏剧,并参与了一系列与音乐戏剧相关的活动:1906年冬创办春柳社;1906年初创办《音乐小杂志》;1907年2月参演戏剧《茶花女》……李叔同和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通过办杂志、结社、演艺、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认识,宣传新的文化观点理念。从学习西方现代的美术、音乐、戏剧开始,李叔同不断从人文艺术美的土壤里吸收养分,将艺术美的外化形式,内化成人格美的思想。
第二,关注“人格美育”的社会功能。李叔同着重“美育”陶养的实践,凭借图画美和音乐美两方面来进行拓展。
在图画美方面,李叔同在1905年12月,也就是抵日留学的4个月后,先后在高天梅主编的《醒狮》杂志的第2期、第3期发表了《图画修得法》《图画修得法续》。在《图画修得法》中他尝试把西方的绘画思想介绍给国内,试图启发社会对图画美的认识。他在文章第一章“图画之效力”中说:“故图画者可以养成绵密之注意,锐敏之观察,确实之智识,强健之记忆,著实之想象,健全之判断,高尚之审美心。”[7]在李叔同看来,修习图画有助于一个人在智识等方面能力的提升,而最终的结果是养成其“高尚的审美心”,是为“智育”。同时,李叔同还把养成高洁品性的“德育”作用与户外写生运动肢体的“体育”作用,都纳入修习图画之效力。以图画为美育,能对一个人在“德智体”三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从“技能”到“人格”的提升,凸显了美育的社会功能。
在音乐美方面,1906年2月8日,李叔同创办的《音乐小杂志》出版,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音乐刊物。除几位日本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其余音乐、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述,都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他为《音乐小杂志》所作的木炭画贝多芬像,是现今中国发现最早发表的贝多芬画像。可见李叔同曾花费大量心血在《音乐小杂志》上,因为他当时已经认识到音乐同样在美育方面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他曾为《音乐小杂志》题序中说:“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8]在阐述音乐艺术美的同时,突出音乐艺术美的社会功能。他在介绍西方音乐家时同样注重艺术家的“文品”和“人品”。例如在介绍贝多芬的“略传”中,他品评贝多芬为“天性诚笃,思想精邃”,以这种方式提醒大众在关注艺术作品的同时,注重艺术家的人格思想。可以说人格“诚笃”和思想“精邃”,汇融了东西方的人格美育思想,体现了美育陶养的社会导向。
第三,强调美育净化人心灵的功能。艺术美与人的真、善、美的心性的培养相关。人文的滋养,包括对东西方美学的学习、吸收和应用。儒家强调音乐于人,于社会积极的审美作用。“美育”的陶养是要“成人之美”,也要“成人之善”。美育具有净化陶养人的心灵的功能,既符合传统文化的“德行”指向,也符合当代的“人文”精神。
自1912年秋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他创作了大量饱含抒情色彩的学堂乐歌,学堂乐歌贯穿着他的“以美淑世”的美育理想。他试图通过艺术美来净化和陶养人的心灵,改变旧教育的弊端,培养有“人格觉悟”的新一代艺术家。这些学堂乐歌,在词和曲方面,人文美感突出,十分贴近当年学生们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李叔同把对“人格美育”的思考,付诸艺术教学的实践中,他通过对图画、音乐的修习,来净化人的心灵,促进学生人格、道德、智力、审美、体育的实验演进。他灌溉了艺术美的土壤,并为他的“人格美育”思想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叔同的“人格美育”思想,从图画、音乐艺术美的实践之中产生,进而发展到人人共享,寄托情怀,寄托生命的境界。美可以超越人我,不为利益得失所牵挂,艺术美聚焦美感,美回溯人文,美关照生命而后自我完善,自我超脱。1912年,李叔同加入西泠印社;1913年5月,他参与浙一师五周年的校庆美术展;1913年夏,他负责编辑学校文艺杂志《白阳》诞生号,并发表了《白阳诞生词》《音乐序》《西湖夜游记》《喝火令》《春游》;他和同事夏丏尊合作创作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1914年,他尝试在浙一师上人体写生课,开中国人体美术教学之先河;他用钢琴与五线谱进行音乐教学;1914年至1915年,他作为乐石社主任,主持出版《乐石》杂志第一至第八集;1915年5月,他参加南社在西泠印社的文艺雅集,题写凭吊冯小青碑铭等。李叔同在这个时期丰硕的艺术成果,从侧面反映了“人格美育”思想的完善,立足于自我人格自我生命的超脱,追求美与善融合的超越,昭示着“人格美育”的实践进入了更为浩渺广袤的天地。自我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人文精神互相碰撞,借助美育自我完善的功能,使他的“人格美育”思想与实践,有了一系列适合时代的创新、拓展与超越。
三、李叔同“人格美育”思想的实践特征
李叔同以“器识为先”作为“人格美育”实践中的主干,他是如何处理“美”与“善”之间的依存关系呢?他是如何以“器识为先”来统一与协调二者的关系呢?
第一,李叔同以“器识为先,文艺为后”的思想作为“人格美育”的先导。1898年,19岁的李叔同参加天津县学考试时,在文章《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中提出“器识为先,文艺为后”的观点,这成为他一生坚持以高尚修养培养自我人格实践的精神准则。它也是李叔同“人格美育”行动的师法源流,即跟随着中国先哲“人品”“德行”的脚步前行。
李叔同主张以“器识为先”来从事文艺之学,践行“美育”。人首先应该是积极向善的,倡导“人格美育”,既美且善,审美的愉悦能欢喜感人,却不能离开有忠、孝、仁、义之“善”。把“美”和“善”二者紧密相连,人即使面对困境险阻,也不会悲观迷失。“美育”需要“器识”,必先是对人的认识进行改变,重在心灵美的陶养;其次才是文艺美的滋养,要学习图画、音乐等。“以德为上,文艺次之”,这种思想,激励李叔同在文艺上的“勇猛精进”,在美育上的守正拓展一以贯之,后来出家离尘的弘一大师,更是坚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作为李叔同的门生,丰子恺对这种思想感受颇多,他在《我与弘一大师》中说:“最高的艺术家有言:‘无声之诗无一字,无形之画无一笔。’……‘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李叔同育人,亦常引用儒家语:‘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所谓‘文章’、‘言’、‘文艺’,便是艺术,所谓‘道’、‘德’、‘器识’,正是宗教的修养。”[9]265丰子恺说的“宗教的修养”,指的是弘一大师的道德精神,也是李叔同的人格精神,在俗时李叔同的“美育”“器识”,就是健全的人格。“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从净化心灵开始,从道德品行入手,“美”与“善”并举,来培育学生人文的素质,德、智、体、美和谐统一发展,以养成高尚健全的人格。
第二,李叔同以“行胜于言”来处理“美”与“善”的关系,他也采用了中西兼备、新旧融合的美育思想。处在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面临西风东渐的历史变革。李叔同既要守正,又要创新,他担当的“美育”新课题,不仅要认清中国美育的方向在哪里,还需思考采取什么的方法来拓展美育教学。
近代美育思想的出现,是从旧文化中建立起新文化,对先进的文化成果加以吸收与扬弃。傅斯年对当年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评价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10]蔡元培曾是李叔同的老师,这种中西兼备的“美育”思想,被当时年轻的李叔同接受、传承、发展。“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中国学术亦然。”[11]李叔同采取的是中西融合、新旧融合的美育思想,并注重在人文方面进行文化的守望与拓展。
李叔同择高处立,行胜于言。1906年他创办的《音乐小杂志》,内容既有介绍西方、日本音乐的篇章,也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杂纂”。在《呜呼!词章》《昨非录》等篇幅里,他表达了自己对待中西文化的思考和寻求守望与拓展的态度。用中西兼备、新旧融合来创造“美”与“善”的和谐。
李叔同敢为人先,创新践行。1906年冬,他创办春柳社,学习日本“新派剧”,他想借鉴日本“新派剧”和西方话剧新颖的艺术形式,改革中国的传统戏剧,既能反映时代题材,也能表达时代主题。1907年2月13日,在中国的农历春节,新成立的春柳社上演了《茶花女》,他反串出演玛格丽特,演出十分成功。这标志着中国话剧运动由此发端,李叔同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之一。1911年3月,留学近6年的李叔同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他的美育思想也渐渐成熟,归国后,他立即投入美育教学一线,加以实践和验证。
李叔同1911年归国后,在天津任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员;1912年春,李叔同自天津至上海,于杨白民主办的上海城东女学任国文、音乐教员;1912年秋,应经亨颐聘请,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图画与音乐教员;1915年春至1917年春,他应聘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他之所以不断地担任图画、音乐教员,是因为想通过艺术美的实践,将中西方文化和美育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人格美育”出发的美育实践,秉持守正也是创新的理念,它表现出“美”与“善”最大的兼容度,追求中西兼备,追求审美共融。
第三,李叔同用“极致认真”的态度来实现“美”与“善”的融合。“极致认真”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彻底精神,既美且善。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学时,李叔同这种“极致认真”的美育精神播下了许多成才的种子。在李叔同的弟子里,出现了大批杰出人才,有美术方面的丰子恺、潘天寿,音乐方面的吴梦非、刘质平,工艺方面的何明斋,教育方面的傅彬然等。文化一脉相承,用这种极致认真的精神来落实美育,树立人格,对丰子恺的一生影响很深,因此他这样分析李叔同的认真精神:“他受人崇敬,不仅是为了上述的郑重态度的原故,他的受人崇敬使人真心地折服,是另有背景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值得我们崇敬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凡事认真,第二点是多才多艺。……李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凡事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丰子恺认为,李叔同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十分认真:“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认真,都十分像样……都是‘凡事认真’的原故。”他对此感慨道:“这是做人认真至极的表示。模仿这种认真的精神去做社会事业,何事不成?何功不就?”[12]
丰子恺绘《护生画集》(共6集,字画有450幅),跨越了弘一大师在世到圆寂后共46年的岁月。完成《护生画集》是丰子恺对老师的承诺,他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无论多艰辛,他都坚持将6集《护生画集》完成。这种完全彻底的“极致认真”,恪守承诺的精神,正是李叔同当年“人格美育”结下的美育硕果。在当今的教育领域中,我们需要弘扬李叔同这种“极致认真”的美育精神,与近年提倡的“工匠精神”同时并举,使弘扬美育精神具有时代的意义。
第四,李叔同“温而厉”“美而善”的美育态度,是人格感化的有效方法。
“温而厉”出自丰子恺回忆李叔同在浙一师教学时的形象,他一贯以和蔼可亲、严以自律的形象实践他的美育思想,这种形象对学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据丰子恺回忆:“我们每天要花一小时去练习图画,花一小时以上去练习钢琴。大家认为当然,恬不为怪,这是什么缘故呢?应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9]264从着装形象之美到言谈举止,把人格学问外化为审美对象,对学生们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人格美育作用。李叔同在浙一师宿舍的案头上,常常放着明代刘宗周的《人谱》,他把这本集中了古代贤达的嘉言懿行的座右铭作为自己树立人格的指南标准,并以此教导学生们。“温而厉”的形象,实际上反映的是人格上的“美而善”,李叔同立身感人,把人格和艺术二者最大程度地统一协调起来。
李叔同秉持与人为善的处事态度和宽容精神,对学生加以鼓励,加以教导。在丰子恺的有关浙一师的回忆中,当有个别学生在上音乐课时看别的书,有的同学吐痰在地,李先生并不是当面批评,而是在下课后,才“和气”地进行教导,然后“一鞠躬”,严肃而和气。李先生“叮咛郑重的态度”,教人感人的诚恳态度,藏在每个受教育的学生“孩子化”的心中。正是抱着人皆可教,错皆可改,凡事“成人之美”的愿望,李叔同才能做到“诲人不倦”“有教无类”,使美育做到人格感化。正如孔子《论语》所说:“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行胜于言,美育者应“言教之余,盖以身教”。立德树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这种“温而厉”“美而善”的美育态度,在许多与李叔同相识之人的评价中都有同样的佐证。浙一师的同事姜丹书回忆说:“上人(李叔同)言教之余,益以身教,莘莘学子,翕然成风。”[13]学生曹聚仁回忆说:“在我们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他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影响。”[14]同事夏丏尊说:“李先生……这是有人格作背景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学先生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15]
美育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说明了李叔同“人格美育”的成功,特别是他在美育中一以贯之的“以德感人”“以德表率”的人格陶养魅力,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温而厉”“美而善”的态度,是李叔同对学生进行人格感化的美育,培养他人自觉地去完善人格,去提高修养。人格感化的力量成为李叔同美育中最有效的方法。
四、以“德行兼备”来提升“人格美育”的境界高度
“德行兼备”首先是以“德”践“行”,李叔同把“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的美育思想,落实为“人格完善”的建立,通过以身作则来开展美育教学。1912年秋,他在杭州西湖烟霞洞,与当时北京国立高等师范校长陈宝泉相遇,据陈宝泉回忆当年的李叔同:“乃一变昔日矜持之态,谦恭而和易。”[16]从翩翩的文艺才子转变为一个美育家,李叔同身体力行《人谱》的嘉言懿行。美育实践,沿着他所倡导“器识为先”的导向来培育人才。此时的李叔同,已经是“怀文抱质,会心独往,神会千祀之旨”[17]。在李叔同看来,“人格美育”价值最终就是“德行兼备”。他的弟子吴梦非认为,这种目标可以直接理解为“感精神之粹美”而“转向崇高隐逸与清高”。李叔同在“艺术,不论绘画、书法、诗词、乐曲、篆刻等,无一不精”,而其“教育态度:既认真,又负责”。顽皮学生“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他并不让学生感到严厉,态度极其和蔼,“这真可说是人格感化了”。[18]
“德行兼备”还需要“知行合一”,李叔同就如他的弟子丰子恺所说的“做什么像什么”,作为一位注重美育的教育家,先修自己的美德,为人师表,以高尚人格来铸造自己、感染别人,“德行兼备”需要“有人格作背景”。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傅彬然,在回忆老师李叔同时说,自己的艺术天资不高,“可是先生的学问和人格,先生的生活态度,却给与笔者毕生忘记不了的印象,并且从而得到关于教育上的许多启示”[19]210。美育者应“言教之余,盖以身教”,言教与身教配合也正是“知行合一”。
在文艺学习的坚持上,知之易,行之难。夏丏尊谈到李叔同的音乐学习时提道:“尝为余言,平生于音乐用力最苦,盖乐律与演奏皆非长期炼修无由适度,不若他种艺事之可凭借天才也。”[20]李叔同对音乐美育的“知”,与实际教学中的“行”紧密融合。据傅彬然回忆当年李叔同教弹琴时说:“教弹琴,多在课外的时间。初学时特别着重于基本的指法练习。指法有一点点错误,拍子有一点点不准确,先生就轻缓而和悦地说‘蛮好,蛮好,明天再弹一遍。’一定要达到完全准确的地步,才得‘通过’。先生的教施,实在谈不上什么方法,也从来不向同学们多说甚么话,可在他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艺术熏陶之上,全校四五百个同学,凡是怀有艺术天才的,他们的天才无不被充分发挥出来了。”[19]211通过艺术活动与学生共同陶养艺术美的方式,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李叔同的“人格美育”是以“器识为先”为“知”,以学习训练艺术美功夫为“行”。他在美术课上率先使用石膏模型与静物,使用真人模特来教图画写生,在音乐课上使用五线谱来教授音乐,举办金石书画收藏展培育学生美感,让学生参与创办艺术刊物促进艺术创作。“知”之美与“行”之美的实践,都是“人格美育”在“知行”的落实。行重于言,即在“知行合一”下功夫,“知行”二者,结合成培养人格的“德行兼备”。
李叔同在“人格美育”上的坚持,先自立个人的品格,再运用艺术与学问来为教育服务,争取做到“德行兼备”。建立人格的“善”同时建立心灵的“美”,这种思想延续在李叔同此后的人生里,从李叔同到弘一大师,他在“知行合一”的修持方面,做出了“德行兼备”的榜样。他培养的弟子如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何明斋等,都是“德才兼备”的艺术家。“德才兼备”注重德与才的共通点,注重人与学的互相融合,将人格与学问垂范于世,以此来延续传承“人格美育”。而出家后的弘一大师秉承这一思想走完了一生,他后来多次在授课、讲演中教导学生:“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1919年11月,中国第一个美育团体“中华美育会”在上海成立,它是由李叔同的弟子吴梦非、李鸿梁、丰子恺、刘质平和同事姜丹书、萧蜕、胡怀琛等人,联合中国美育界人士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内成立的。1920年4月20日,吴梦飞等主编的中国第一本美育刊物《美育》杂志出版,出家后的弘一大师题写了“美育”刊名。《美育》主张“‘美’是人生的一种究竟的目的,‘美育’是新时代必须做的一件事”,这意味着“人格美育”以学习艺术导向人生,以人为中心才能传承。以先“做人”来决定“为学”,如王阳明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人不能“至良知”,不能做到“德行兼备”,就不足以流传于世——“艺以人传”,远胜于“人以艺传”。
1922年,弘一大师在温州庆福寺写给俗侄李圣章的书信中说:“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21]他对自己任教时开展的“人格美育”实践、弘扬文艺的成果感到无比的欣慰。
“人格美育”是李叔同以极致认真的态度、知行合一的人格、自我超越的精神综合而成的美育之境与人格之道。不论是“艺以人传”还是“德行兼备”,面对世间学问,艺术的弘扬或是出世修持,都需要一门深入,久久专修,坚持不懈,这是他从在俗到出家始终秉持的信念。美育有传承的普遍性,也具有自我的超越性,“人格美育”之道,是李叔同留给我们的瑰宝,以“人格”之美传世,一代代的薪火传承。
五、结语
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人格美育”思想,融汇了德、智、体、美、劳的教育指向和旨在继承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美育形式。这同样适用于当今时代的教育,立德树人,应在提升人文素养的同时完善人格。
李叔同以建立人格来养育美育之心,以“器识”先行来践行美育之学,以“德行兼备”来深入美育之境,这样的“人格美育”思想,启发我们跟着先贤的步伐而与时俱进。美育的发展,不仅关系着个人的人格完善、心灵美的建立,而且也关系着国家、社会、教育的文明程度。我们通过学习与探索,回望百年,使李叔同的“人格美育”思想薪火传承,担负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大业。
——《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