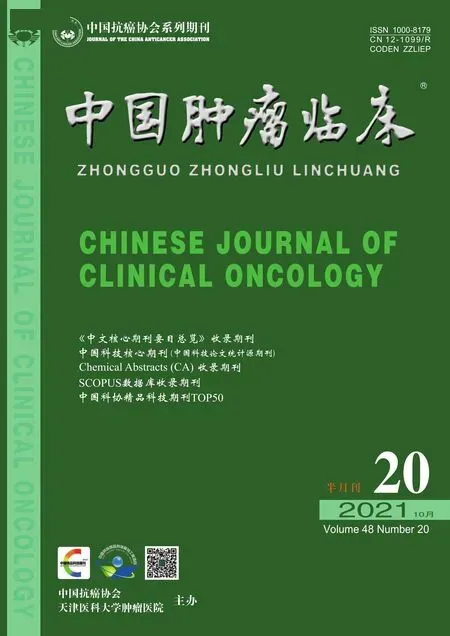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后胸壁结核1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林心情 邓海怡 杨伊霖 周承志
患者女性,80 岁,因咯血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既往无肝炎、结核病史。胸部CT 显示右中上肺中央型病灶并阻塞性炎症、肺不张,右肺门、纵隔淋巴结转移(图1A),进一步行PET-CT 检查提示右中上叶分叶肿块,代谢增高,考虑中央型肺癌,病灶阻塞右上叶前段支气管伴远端阻塞性肺炎;左上肺尖后段结节,考虑转移;右肺门、双侧纵隔淋巴结增大,代谢增高。患者行痰标本结核分枝杆菌DNA、Xpert-Mtb/RIF 试验和干扰素-γ 释放试验均为阴性,不考虑肺结核的诊断。患者经支气管镜活检标本病理学检查确诊为鳞状细胞癌,并通过22C-3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1,PD-L1)表达阴性。行基因检测未见驱动基因突变。临床诊断为原发性支气管肺癌,鳞状细胞癌,cT4N3M1a,ⅣA 期,驱动基因阴性。患者及家属考虑患者高龄,不同意化疗,经商量后,选用信迪利单抗单药治疗。患者于2019年9月开始接受信迪利单抗200 mg 作为一线治疗。

图1 肺癌病灶及胸壁结核病灶变化的影像
患者于2019年10月(2 个周期免疫治疗后)行胸部CT 显示肺部原发肿瘤病灶缩小(图1B),达到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无胸壁肿块(图1C)。经过6 个周期免疫治疗后,于2020年1月患者发现其右胸壁出现肿块。2月行胸部CT 提示肺癌病灶缩小,纵隔和肺门淋巴结维持稳定(图1D),右侧胸壁出现肿块(图1E 和1F)。患者在超声引导下穿刺胸壁肿块,经病原微生物宏基因组测序和穿刺液培养都发现结核分枝杆菌,T-SPOT 检测阳性,支持胸壁结核的诊断。而患者无发烧、咳嗽、体质量减轻和盗汗等典型的结核病症状。3月患者开始使用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和吡嗪酰胺治疗结核病,并予胸壁肿块穿刺引流。之后病灶穿刺液结核菌培养复查阴性。在抗结核治疗期间,患者继续予信迪利单抗治疗。再行胸部CT 检查发现,结核病灶明显缩小(图1G 和1H)。患者在免疫治疗和抗结核药物同时使用期间,未出现肝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患者结核病发展历程见图2。

图2 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结核病发展历程
小结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对多种实体肿瘤以及慢性感染性疾病(包括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均有疗效[1]。ICIs 治疗期间出现活动性结核病已有报道,但信迪利单抗治疗后出现胸壁结核鲜有报道。该患者在6 个周期免疫治疗后发生结核病,而且抗结核治疗期间并未暂停免疫治疗。
目前,全球可查到仅有25 例免疫治疗相关结核病的报告(表1)[2-18]。25 例患者中,非小细胞肺癌16 例,黑色素瘤5 例,淋巴瘤、Merkel 细胞瘤、头颈部鳞癌、鼻咽癌各1 例,平均年龄为67(49~87)岁。发生活动性肺结核的中位时间为免疫治疗开始的3.5(1~24)个月,中位的免疫治疗周期为8(2~41)个周期。在25 例中,7 例死亡(28.0%),只有4 例患者在免疫治疗前有明确的结核病病史,4 例患者进行了结核病筛查。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有结核病史的患者在免疫治疗后都会出现活动性结核[16]。除6 例未提及既往抗肿瘤治疗史的患者,19 例患者中17 例(89.5%)在ICIs 治疗前接受过手术、化疗、放疗或其他抗肿瘤治疗。因此,ICIs 前的抗肿瘤治疗可能会增加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13 例患者ICIs 治疗前曾使用过化疗,有报道显示使用化疗会导致活动性结核[19]。糖皮质激素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抑制剂也有导致活动性结核的风险[20-21]。在结核发生前,有4 例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其中2 例因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使用;3 例曾予TNF-α 抑制剂治疗。然而,本研究病例在免疫治疗前未接受任何抗肿瘤及糖皮质激素等治疗,并且无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终末期肾病等结核感染的易感因素[22]。

表1 ICIs 相关结核病的病例资料

表1 ICIs 相关结核病的病例资料 (续表1)
ICIs 治疗后发生活动性肺结核的机制尚不清楚,目前报道有两种假设[23]。第一种是结核杆菌导致ICIs 治疗的患者出现T 细胞的免疫再激活,类似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艾滋病患者中观察到的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一项动物实验显示,相比野生型小鼠,PD-1基因敲除的小鼠感染结核菌后存活率显著降低,肺部出现严重的坏死;对PD-1 基因敲除的小鼠组织和血标本进行分析发现,促炎细胞因子包括TNF-α、IL-1、IL-6 等显著增加[24]。另一项研究发现ICIs 治疗后,循环中产生γ-干扰素的Th1 细胞升高,而CD8+T 细胞、Th17 细胞、调节性T 细胞等无显著变化[10]。ICIs 可能增强CD4+细胞介导的免疫,导致结核感染部位出现过度的炎症反应。第二种假设是ICIs 诱导的淋巴细胞减少导致机会性感染。本研究结果更支持第一种假设。该患者未表现出任何免疫力抑制的迹象,如淋巴细胞减少,且其IL-6 增加了3 倍,并出现大量坏死,这都表明患者对结核菌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此外,患者在免疫治疗前进行的结核病相关检测均为阴性。因此,本研究病例可能在使用ICIs 后出现了CD4+T细胞的免疫再激活,对结核菌产生应答,导致严重的炎症反应。
在有评估ICIs 疗效的20 例患者中,16 例达到PR 或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达到80.0%(95%CI:60.8%~99.2%),高于ICIs 单药治疗的Ⅲ期临床试验[25-26]。该患者的PD-L1 表达阴性,且接受了信迪利单抗单药治疗,在2 个周期治疗后达到PR。因此,推测有活动性或潜伏性结核感染的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反应可能比无结核感染的患者更好。但是既往研究表明结核感染能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27]。有报道指出结核病患者比健康受试者在CD4+T 细胞的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和PD-L1 表达更高[28]。另一项研究也显示免疫治疗后出现结核病的患者,肿瘤细胞的PD-L1 表达升高[4]。结核病可能通过增加PD-L1 的表达提高对免疫治疗的反应。
对于活动性结核病患者是否继续或暂停或永久停止免疫治疗尚无共识。7 例患者同时接受了抗结核和ICIs 治疗,其中1 例在治疗期间因无法耐受不良反应暂停免疫治疗4 个月,其余患者都表现出良好的疗效。还有3 例患者经过抗结核治疗好转后重新启用免疫治疗,结核病并未加重,而且肿瘤得到控制,其中1 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但是,有1 例患者重新开始免疫治疗后出现2 级腹泻,并在此后不久因肿瘤进展死亡。因此,在决定是否停用ICIs 时,应综合考虑结核病感染的严重程度、肿瘤的控制情况、免疫治疗的疗效和患者的身体状况。抗结核药物治疗是治疗结核病的主要策略,一般不需要糖皮质激素和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在25 例患者中只有2 例(8.0%)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2-18]。
综上所述,ICIs 可使免疫细胞对潜伏性结核病产生过度反应,导致结核病的再激活。因此,在开始免疫治疗之前,建议进行结核病筛查。活动性结核病可能与ICIs 疗效增强有关。此外,在确诊活动性结核感染的患者中,抗结核药物可与ICIs 联合使用,但应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