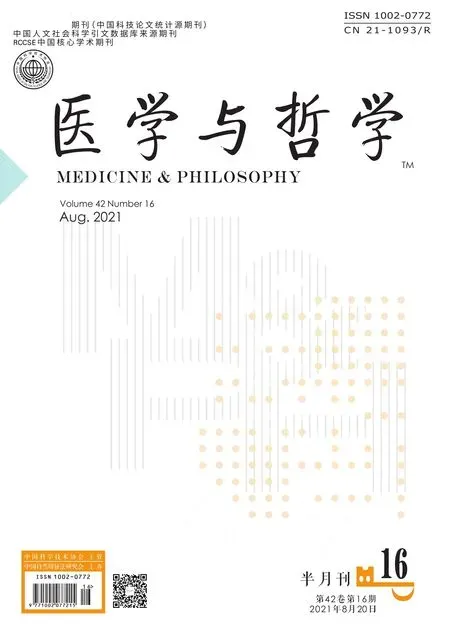近代西方中药观的变迁研究
陈 瑜
“他者”的概念[1]已在社会学、比较文化学等众多领域广泛应用,“他者”的认知成为当代科技学术史研究中的新视角。西方人对“神秘的东方传统医学”(中药、脉学、针术)的认识源自11世纪[2],但实质性的接触和交流始于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由陆续来华的传教士、商人、外交使团将中医药学西传欧洲。与对中医诊术的轻视和误解不同,西人对中药的认识是平和、复杂和微妙的:在中西文明初识的早期,传教士忠实记录在华所见中药及疗效,同时作为中国植物成为西方“博物学”的科考对象,《中国植物志》《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味药》等有关中药的研究论著在欧洲“中国热”(Chinoiserie)的推动下出版;19世纪西方医学近代化转型后,西人对传统中药的态度出现变化,在质疑的同时采取“医”“药”分离对待,甚至开始将中医学说、中药与中医群体做细致区分[3]。
1 科技史观与中药西传
中药学是中国独有的科学文化遗产,元代以前,西方对中医药的了解多藉阿拉伯人或少数商旅完成,地理大发现之后,中西科技文化交流进入新纪元,西学东传和中学西传成为两条并行不悖的双行线,西医入华的同时,中药与中医作为“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将此历程回置于近四百年的中西医接触碰撞的历史语境,尽管历经中西两大医疗文化体系之间选择、转译与沟通的多元历史演化,但它没有向着西方“技术至上主义”方向发展,而是“执拗”地沿着整体论、自然论的道路发展为人文主导型医学,这其中,西方视角对中药的多重认知最具张力。
西方人获得系统的中草药知识和较完整的中医理论开始于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殖民势力和基督教向东方的扩张。从科技发展史看,自17世纪始,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处在急剧的思想文化变革之中,以开拓、外向的心态进入了西方现代性的起点,中国这个原本神秘遥远的东方国度逐渐成了清晰的客体,“在我们的时代里,中国帝国已成为特殊注意和特殊研究的对象”[4]。中医药同算学、农学、地理学、天文历法、工艺技法等中国传统科学由各渠道介绍到欧洲大陆,西方世界开始把中国的科技文化纳入其研究视野,谢务禄(Alvaro de Semedo)的《大中国志》、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国图说》等耶稣会士的著作都体现了这一趋向。
西方对中药的认知是分阶段、复杂而多层面的,早期传教士把中医药作为一个与西医迥异的知识体系来观察研究,他们的看法在西方如何得到延展或回应,是否受中国本土因素(如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影响;在19世纪完成近代医学过渡后,学者、医生等非教会人士的认识角度有何变化,对当代规避技术乌托邦主义是否有所启示,这些均需通过史实的条分缕析进行揭示。
2 西方对中药学的认知之路
在欧洲的东方知识演进过程中,入华传教士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他们是殖民者的先遣队,也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摆渡者”,早期至近代西人视域中药观的形成即以传教士的考察、认知和著述作为主要依据,包括典籍的译介、行记、书简、论文、报告等。从时间划分,第一阶段为明末清中期耶稣会士东来时期,从利玛窦入华到最后一个传教士钱德明(M.Amiot)去世,大体历时200年,在此阶段中西医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从总的临床处理能力来看,中医甚至高于西医,他们对中药采取平视、好奇的态度;第二阶段是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时期,西方医学已经完成了向近代医学的转变,对中国本草的研究亦发生了转向,走出了发现新事物的猎奇探索阶段[5]。
2.1 耶稣会东来与启蒙时期
欧洲的“启蒙时代”(17世纪~18世纪)正是耶稣会士远渡重洋大规模来华传教、开启近世中西交触的时期,启蒙时代的哲学基础是现世主义和“对世界的科学解释”[6],他们对中国文化科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时,耶稣会士以学术辅教为手段,但是“他们的历史职能是进行观念和形象的双向传递”(费正清语),成为西方普罗大众(proletariat)认知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传教士关于中医中药的个人体验和他们的文字著作越过重洋发回欧洲大陆,深深影响了当时西方社会对中药的认识。(1)自身体验:自17世纪上半叶以来,“温饱和卫生”一直是在华传教士事业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7],多数对中医药有直接接触,许多神父都承认用中医中药治过病,并认为这一切都很好。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致友人信札述及“二种中药根经煎熬后在病发作时服用”治愈自身发热腹胀,他本人在华期间“每尝中国草根,测知叶形花色”,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因胆肾结石延请中医诊治而迷上中药,著《中药学》(SpecimenMedicinaeSinensis),鉴于此他们对中医药形成一种“折中偏于接受的态度”。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即使认为中医“对药剂量一无所知”,但依旧态度暧昧地表达了对中医药的欣赏。波兰人卜弥格(Michel Boym)根据来华近30年对中医药的了解写出《中医处方大全》,列举中药289种,数次再版,引起了当时欧洲人对中药的极大兴趣,纷纷在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来的商品中高价收购。方玉清(Etienne Faber)神父曾患重病并由中国医生治好,他认为“中国医生不只在抚脉诊断方面有非凡的本领,他们用药也极有效果”[8]。一些接触清宫的上层传教人士都接受过中医药治疗,康熙四十八年安多(Antoine Thomas)因脾胃虚损由御医茹璜诊治给予加减理中汤服用[9]。(2)知识传介:进入18世纪后,来华传教士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皇家科学院、圣彼得堡科学院等均有密切联系,把种类繁多的中国药物列入科考对象,然后将研究成果寄往欧洲。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在华期间与中国医生多有接触,他向西方介绍诸如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阿胶等常见中药,并把样品寄回法国,法国皇家科学院在1726年曾举行医学报告会,专门讨论这些中药的性质与作用。殷弘绪(Frangois-Xavier d'Entrecolles)在1736年从北京写信给杜赫德介绍以下中国药物和疗效:葛根能够退高烧、治剧烈的头痛和严重的关节炎,扫帚草(即蕨)可清除肠积气,愈合毒蛇或毒虫咬伤,研碎的荔枝核是一种医治肾结石和肾绞痛那无法忍受的疼痛之有效药剂,他驳斥了西方人对中医药的怀疑。杜德美(Pierre Jartoux)1711年在给传教会会长写的一封信中对人参的药用价值、植物形态、采集和保存方法都作了详细介绍[10],这封信被寄回了法国,之后被转载在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上。韩国英(P.Petrus-Martial Cibot)虽然认为中药存在缺陷,“其制药方法还是古人用的原始方法”,但仍然写出Armoise(《论医草 (艾草)》、Noticesurlapivoine(《论芍药》)[11]等多篇论文,发表于由法国国务部长亨利·贝尔坦创办的《中国杂纂》,该刊物还大量刊载刘应(Claude de Visdelou)、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等有关中药知识的论著报告,传教士们在欧洲掀起了中医药的小高潮[12]。
2.2 基督教新教传教时期
耶稣会被解散之后,以1807年英国伦敦会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入华为标志,英美新教传教士成为中西医交流的主要媒介,此时的西方医学已摆脱了狭隘的经验医学与神学权威的束缚,凭借近代自然科学的羽翼而得以飞快发展[13],近代医学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一阶段西方对中药学的认知呈现以下特点:研究深度增加并逐渐摆脱感性认识,不可避免地以殖民者视角审视东方的一切,来华群体增多,认识角度多元化。(1)研究与认同:他们确认中药学在过去的辉煌历史,发现中医药在某些疾病的治疗方面有优势,在化学成分和功能分析上有极大利用价值,马礼逊与专业医生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共同在澳门设立的诊所内配备各种中草药,183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郭雷枢(Thomas R.Colledge)等倡议成立中国医学传教士协会,这个学会认识到中医药治病的价值,建议用中药来充实自己的诊所。美国的传教士医生托马逊(Thomason)说:“我们发现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的药物。这对我们传教士医生肯定具有很大价值,我们已经证明了中国药物的价值”“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座未经开发的矿藏。”[14]1858年合信(Benjamin Hobson)在《内科新说》中对比中西的药物,认为部分西医用药和中医医理相通,主张西医在中国“药剂以中土所产为主……而中土所无者间用番药”。伦敦会派遣教士医生德贞(John dudgeon)在MedicalReportImperialMaritimeCustoms中说,中国医书中“记载了海藻有很强和很好的治疗特性,在这方面,中国人并没有落后于其他许多海洋国家”[15]。他还翻译了清代名医叶天士的药方并介绍到西方。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James B.Neal)在1891年递交给中华博医会关于中国药物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当时对于中国药物的研究“既缺乏广度,也远没有被外国医药工作者充分利用”[16],他建议教会诊所应当更广泛地利用中国本土药物。(2)偏见与误读:在不少来华医药传教士眼中,中医是属于过去时代的陈旧之物,近代汉学之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虽然对《本草纲目》等做了相当细致的分析,仍然认为中药“绝大多数是没有效验的草药”,甚至还有许多“奇怪而可憎的东西”[17],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认为“大多数中药都是不灵验的,还有一些味道怪异,根本无法入口”,花之安(Emest Faber)在其著《自西徂东》言“论药则以一味可医数十症,且言其轻身益寿延年,岂不大谬”,反映了当时传教士对中医的片面理解。在批评中国医学方面最有影响的是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77年他第一次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提出东方民族的医疗方面的9个问题,包括“在很大程度上对药物性质的无知”, 1890年第二次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内地会的道思韦德(Douthwaite)依旧持此观点;即使是对中医颇有研究的合信也认为“其中有大用者,如人参、大黄之类是也,有无用者,如龙虎骨之类是也”[18]。1887年来华的立德夫人认为中药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人从未将之以科学化处理,“他们用粗糙的熬制方式从药材中熬出药汤来喝,他们从未提取药材之精华,也不用精密准确的天平或秤砣来称量药材”[19]。
3 西方中药观的建构因素
任何科技文明的传播都不是理想化的坦诚相见,而是在不同历史政治氛围、话语网络甚至权力关系里的接触与角力,滥觞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中医药学是中国科技文明的一部分,中医与西医、中药与西药是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建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在它们相互认知的过程中宗教、技术、政治、传统与文化交织在一起,因此西方对中药的认知有多重构建因素,除了前文所述个人经历体验以外,主要有以下两点。
3.1 社会文化因素
启蒙时期是西方智识层面上称谓的“理性时代”,这个时期所追求的世界观与求知欲促使欧洲人不断与外界接触,彼时欧洲的近代科学也才刚刚起步,他们对中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启蒙时期那样使得中国的商业贸易相对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识界对中国兴趣如此之大。”[20]他们看待中国的目光充满好奇、仰慕,伏尔泰(Voltaire)认为:“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莱布尼茨(W.Leibniz)说:“中国人在我们之前就掌握了指南针、火药和许多草药知识”“我丝毫也不怀疑,在中国人那里肯定还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21]毫无疑问,中欧间的文化、物质、科技方面的交流及其发生在18世纪的“礼仪之争”等因素无一不影响着西方人的中国观,在此背景下西方对中医药的态度是平视而客观的,没有太多成见,甚至对于中药的接受亦具有非常浓厚的“中国文化想象”。 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建立,中国成为与进步对峙的“停滞的国家”,对中国及其文化由认同和仰慕转化为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标准的审视甚至评判,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总结,“具有异质性、落后性、柔弱性”。西方对中医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中药的认知失去了仰视的目光而偏于务实,可以看出,医学并不仅仅是对生物世界秩序的客观反映,人类的社会文化因素从来都未曾缺席,这其中既有知识关系,又有权力关系。
3.2 囿于需要的务实因素
在中西方交流之初,耶稣会士把一些常用中药寄回欧洲,由于某些药物的特殊功效,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但欧洲关心中草药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欧洲植物的药用价值,把传入欧洲的中药看作是对西药的一种补充。法国汉学家罗姹(Elisabeth Rochat de la Vallée)曾言:“当时欧洲关心中国本草志的兴趣并不主要是由于科学好奇心,也不是实用的兴趣,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欧洲药草的疗效。”[22]在此后的二三百年间,出于在华传教的需要以及近代医学的转型,中药的科学价值成为西方的关注点之一,清初来华的鲁日满(Franciscus de Rougemont)不仅在行医中运用中药,其所记的《账簿》中也有不少对中药的记载。传教士医生在华的医疗活动中,需要利用本土药物作为补充,流传下来的《澳门圣保禄学院药房的秘方》档案中,共涉及药物105种,绝大部分为来自中国的中草药,如泽泻、决明、木防已、白屈菜等[23],反映了在澳耶稣会士对中药的利用和认可。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对“医”与“药”区分对待,在排斥中医医疗水准的同时,承认中药的价值,汤姆逊(Thomson) 指出:“我们当时发现中国有无穷无尽的药物,这对我们医疗传教士而言肯定有巨大价值”。英国传教士医生道斯维德研究认为,中药效果很好并与西药药理有相通之处,如中国本土所用“雄黄”与欧洲所用的Arsenical pastes(砷膏)在很大程度上大同小异[24],他和威尔逊(Wilson)为节约医院开支曾纯化和利用多种中药[25]。法国传教士苏伯利昂(Soubrian)的《中国药物》、俄国驻华使馆医官布理士奈德(Bretchneider)所著的BotaniconSinicum等都是西方研究中国和鉴定中国植物药的上乘著作。应该说出于现实的需要和研究程度的加深,西方对中药的认识经历了平视、轻视和重新认知的复杂过程。
4 技术交流语境的实践性回应
中药学根植于传统中医理论,是具有经验性、活态性、实践性及表述性的完整的知识谱系,在世界医药学史中,都把中国誉为最早使用天然药物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国度,在近现代医学模式冲击下,中药学的发展与传播遭遇瓶颈,以全球史视野梳理西方对中药的认知演进才能洞见其内在的历史关联。
4.1 范式转换
在当今学界,社会史、微观史、全球史等新兴学科给医学史研究带来新思路,历史学和医学的学科壁垒正逐渐消解,其中知识史和物质文化史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研究取向。知识史(history of knowledge)有别于科学史和学术史,西蒙尼·莱希格(Simone Lässig) “将‘知识’视为一种现象的社会文化史”,中药学无疑是人类总体知识之一环,通过考察近代早期全球化视野下医学物质与知识随着贸易网络的流通,可以关注不同文化对传统中药认知形式的变迁。物质文化史(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视角也被运用于医学的全球史中,其研究内容即东西方药物贸易与知识的流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医学拥有极为丰富的物质内容,重要的传统医学体系都使用多样的药材,成分包括动植物、 矿物与化合物,高晞[26]、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27]、林日杖[28]、那叚(Carla Nappi)[29]等学者分别以土茯苓、人参、大黄、阿魏为研究对象,指出药物的传播与流通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医药知识在不同地点转移的历史,同时,它们的物性及物质存在方式亦随着知识体系、认知方式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样貌。
4.2 视角启新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说: “只有通过他者,我们才能获得有关我们自己的真正知识。”在与异质文化体系的比照中,跳出“自我”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自我”。在考察东西方科技文明演进中双方可以互为视角,早在16、17世纪欧洲科学界由传统自然哲学向近代实验科学转型阶段,近代科学先驱胡克(Hooke)和波义耳(Boyle)都曾将目光投向中国医学,以东方知识和技术资源为参照系审视欧洲传统的学术体系[30]。中医药学术自古至今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医学体系,作为中医药对外接触交流媒介的传教士、海员、外交使团等是西方中国知识的主要建构者,借助汉学成果和理论架构对上述认知群体进行整体归纳、个体分析,方能够超脱始终以中国和中医为本位的视野。同时,以异域和他者的经验为参照和援借,揭示中西两大医疗文化体系之间选择、转译与沟通的多元历史演化,不仅扩大了“中学西传”的外延,还可以帮助研究者突破“冲击—反应”模式,摆脱二元对立的价值框架,避免传统医药受到西方中心论与科学主义的裹挟,推进中医药文化由民族性走向世界性。
4.3 价值导向
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技是“前科学”或“准科学”,且终将以“百川归海”的方式汇入欧洲近代科学,席文(Nathan Sivin)则强调它的社会文化土壤和领略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河岸风光”[31],他还进一步提出“文化整体”(cultural manifold,或译“文化簇”)[32]的方法论: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中国科技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他反对用西医去改造中医,从而使中国医学缺失文化的完整性与一致性。传统中药学属于中国古代科学,至今仍保存独立学术体系,在比较视野下梳理西方对中药的认知过程有助于坚持中国传统科学的价值导向。文树德(Paul Ulrich Unschuld)认为当中西医学之间不存在共同点时,应避免生硬地寻找两者之间的统一性,必须尊重中医的文化特质[33];霍布斯鲍姆(Hobsbawm)认为中医存在真正的传统(genuine traditions)且无需被恢复或被发明;雷祥麟借助对近代中医转型的研究,反对割裂中医文化理论与源于自然的天然物质中药之间的联系[34]。通过梳理中医药在西方的传播脉络和认知变迁,阐释其技术因素及社会人文内涵,有助于解决异质文明播散过程中的文化融合,在文化心理、思维范式等方面构筑现实视角,平衡把握传统文化的信息传递和对现实世界文化地图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