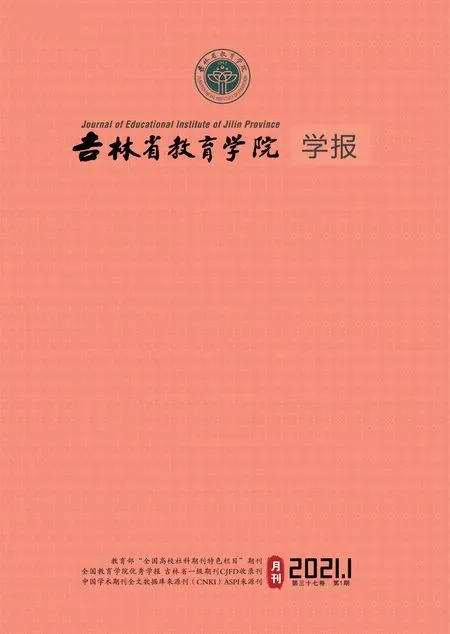语类教学法对我国民族地区多语教育的启示
单菲菲,石修堂
(凯里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凯里556011)
一、语类教学法的引介背景
21 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汉”双语教育逐渐发展为“民汉英”等多语教育。我国多语教育实践几十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发展不均衡[1]、教学资源匮乏[2]、教育内容和方法不符合少数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学生语言水平不高等问题[3]。尽管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学生优惠政策(如高考加分)以促进教育公平,但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术成功和社会提升等方面并不占优势,总体竞争力不强[4]。由于缺乏进入高层社会和获得经济资本语言的通道,少数民族学生通常被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会被主流群体认为少数民族学生很难辅导所加强[5]。总的来说,这种教育不均衡主要是由于文化因素造成的,对教育公平的诉求不能仅从考试入手,还要考虑教育资源和教育方法。近年来,国家加大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提高教育扶贫精准度,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6]。因此,探索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多语教育教学方法,对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教育公平和培养多语人才至关重要。
悉尼学派语类教学法(以下简称语类教学法)的产生背景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当前社会现实类似。20 世纪80 年代,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因文化因素造成了教育不平等,导致一些中小学生,尤其是来自非主流社会的中小学生读写能力较差。针对这一社会现象,悉尼学派从文化入手,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工具,以语类理论为基础,从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估三要素入手,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项目发展并逐步完善了语类教学法。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法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读写学习效率[7],还能缩短同一班级学生之间语文水平的差距[8]。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与主流文化同样存在差异,导致学生不能应对主流教育,与汉族学习在学习能力和学业成绩上存在明显差异。可见,语类教学法适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多语教育教学。为了探索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多语教育教学方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读写能力和学习成绩,缩短他们与汉族学生的学业差距,本文引介悉尼学派语类教学法,探讨其理论来源,介绍具体教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因素,探讨语类教学法对少数民族地区多语教育的启示。
二、语类教学法简介
语类教学法指语言教育学家马丁等人受1979年韩礼德组织的一场教育研讨会所启发,在澳大利亚发起一系列基于语类的读写能力教学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当时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方法主要考虑对象为中产阶层学生,而没有为社会边缘群体提供资源通道的现象而进行的,其主要目的为通过识读资源再分配,使处于社会弱势的学习者掌握识读资源(literacy resources),提高识读能力,从而能够在社会中为自己重新定位。识读资源指能够提高识读能力的语言学资源。在悉尼学派以语类为基础的教学法中,语类是最主要的识读资源。语类是学习者为自己在社会中重新定位的权力话语形式、是获取知识的钥匙[9]。不同社会阶层的学习者对于语类的掌握程度有所不同,识读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则会强化权力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不平衡分配。以语类为基础的教学法通过识读资源再分配,促进权力在社会中的平衡分配。因此,马丁称语类教学法具有“颠覆性”(subversive)[10]。这种颠覆性教学法正是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获取识读资源从而进一步获得社会晋升机会所需要的。
三、语类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一)语类理论
悉尼学派语类教学法行动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基于语类进行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因而,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类理论起着重要作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教学总是发生在一定语境中,这些语境形成反复发生的类型,包括对社会化起关键作用的各种语境类型。这些反复发生的语境类型被识解为情景语篇或语类,马丁进一步将语境概念发展为分阶段、有目的的社会过程[11]。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教学模式核心为语篇教学,其模式被视为“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目的塑造了语篇类型,即任何一个语篇都是通过针对一群特定对象(科学家、儿童、大众等)、关注特定的机构(科学、新闻、法律等)和操作不同的交际模式(口头的或书面的、独白或对话、视觉的或言语的),马丁和罗斯(2008)将文化语类根据不同社会目的分成不同类型并区分了他们的局部组织[12]。悉尼学派在行动研究中总结出语篇类型为各阶段学校教育提供了学生读写模型,被称为知识语类。根据三大社会目的,三大语类类别被识别:吸引读者的故事类语类、给读者提供信息的事实类语类、评判语篇观点的议论类语类。
语类教学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学习语言由理解语类开始,即理解“分阶段的、目标取向的社会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语篇得以展开。不同语篇类型的区分或知识语类增加了我们对教学知识和内容的认识,因此语类提供给我们设计教学方法的工具,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是对语法的处理,还包括了关于语言的知识。涉及不同教学阶段和活动的教学实践模型,由通过语言发展理论“互动指导”的原则所指导。
(二)语言发展理论
语类教学法的教学语境化基于韩礼德的语言发展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界定了语言学习的范围,语言学习总体包括三方面:学习语言,通过语言学习其他知识,学习有关语言的知识。语言本身就是所学实体,在教学中,教师通过对话互动为学生构建意义。通过语言学习其他知识,就是把语言当做一种学习其他课程的工具和首要资源。学习有关语言的知识是把语言当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来了解语言的运作方式。韩礼德强调语言学习三个方面同时存在、共同作用,在提供识读资源和意义构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在韩礼德他们的研究以及基于他们研究的其他后续研究中,学总是伴随教,因此学习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教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与教育观与维果茨基(1978)的“支架”(scaffolding)理念一致,即在儿童学习的过程中,成人为他们提供指导以发展他们独立控制的能力[14]。这个支架隐喻表明了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展开师生之间的对话为学生提供过渡作用,为学生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提供准备,在学生完成任务后提供详述。
“通过在经验共享的语境中进行互动的指导”原则在悉尼学派不同阶段的行动研究中被转换为一些读写教学模式,每个教学模式分别展示了不同的教学步骤,但每个模式中的教学步骤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逐步递交学生语类控制。通常,这些教学模式首先与学生建立共同点(“经验共享的情境”),然后与学生一起创造意义(“互动指导”),最后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工作(学习任务)[11]。
四、教学模式
(一)语类写作教学循环圈
以语类理论为指导,以“共享经验的指导”为原则,悉尼学派语言学者、教育语言学者和各个层次教育机构教师共同进行了一系列革新课程语类读写教学法行动研究,旨在帮助来自任何背景的所有学生进行高层级语类写作。最著名的语类教学模式为在写的得体阶段发展的教学循环圈(Teaching and Learning Cycle,TLC)[15]。
教学循环圈为一种课程语类,由解构(deconstruction)、共同建构(joint construction)和独立建构(independent construction)三个主要步骤构成。解构步骤指教师向学生讲解示范语篇,以示范语篇的社会功能、名词等为中心的现在解构活动,主要讨论语篇的分类标准和结构(如结果和因素),并在共享的语境下讨论语言的阶段和构成语篇的关键语言特征。共同建构指师生共同建议一个相关的语域,然后由教师征求学生的建议来撰写另一语篇,再经过仔细协商,将共同构建的新语篇写在黑板上。独立构建,由学生在共同构建的基础上自己独立完成一个同一目标语类的语篇。基本原则为,教师在与学生讨论完一个目标语类模型,并与学生共同构建另一个目标语类模型,并确定学生已准备好独立完成写作任务之前,绝不要求学生写任何东西。在学生还没有准备好的地方,可以对小群体学生进行进一步的解构和共同构建的循环。
(二)阅以致学教学循环圈
对于大部分学生,在TLC 教学循环中最大的困难是阅读范文和用来建构语场的相关材料。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难题,罗斯和他的同事进一步发展了将阅读指导融入写作指导的“阅以致学”(Reading to Learn,R2L)课程语类[11]。
阅以致学课程语类设计了全局和局部的教学循环步骤。局部教学循环涉及每一语步的指导交流语言,包括“准备—聚焦—任务—评价—详述”五个语步。准备语步为教师通过学生理解的口头语言引导他们理解每一句话的意思,聚焦语步为教师通过使用wh—问题和定序线索将学生的注意力聚焦到句子的特定部分的内容,随后学生的任务是根据问题和线索选择词项,然后用笔把正在协商语篇句子中的词序标记出来,然后教师对学生的任务进行积极的评价,最后教师对所协商的意义进行详细的阐释。
从全局来看,阅以致学课程语类涉及三层教学循环圈,最外层圈与以上描述作为教学循环圈相似,但“解构”阶段为给学生提供的“阅读准备”(Preparing for Reading)。除了这三大步骤,阅以致学教学循环圈还根据学生的水平和学习情况提供了更多的细致指导和具体支持。如果学生有更高层次的支持需要,则可以启动更具体的第二层循环圈的教学步骤,包括仔细阅读(Detailed Reading)、共同重写(Joint Rewriting)、个人重写(Individual Rewriting)和第三层循环圈的教学步骤,包括句字标记(Sentence Marking)、单词拼写(Spelling)、写句子(Sentence Writing)。多重循环圈为初学阅读和写作尤其是读写能力弱或外语/多语学习者提供了充分的语言支持。所有语类教学法的课程语类中教学循环圈的选择和活动安排都由教师在教学之前根据学生水平设计。在教学循环圈的设计中,语篇选择非常重要,所选语篇通常要对全班学生具有挑战性,稍高于他们的读写水平。
五、语类教学法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语教育的启示
与传统的教学理论至上而下、由词至篇的教学法不同,语类教学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教学识别语境中的语篇及其语言特征[16]。马丁的语类理论,通过对社会语境进行分层,明确了某种特定文化如何将意义潜势归并到复现的语言构型中、如何在每个语类的不同阶段调整意义。因此,语类提供了一种整体的说话方式,具有特定的语篇语义结构,这种结构具体表现为词汇语法结构。在具体的教学中,语类教学法提出可见和介入式的教学法,认为失败的学习成果与个人学习者关系不大,而在于社会结构、社会认同和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差异[18]。因此,语类教学法要求对有效读写能力所需要的技能和文化理解进行明确的展示,相应地,将与学术成功和社会移动相联系交际方式的功能、结构和体裁特征等方面知识以明显的方式展现给学生。这种明晰的教学法可能那些已经在家庭中接触到学校和中产阶层机构语言模式的学生没有很大的需求,但正是非主流社会少数民族群体和多语教学项目中师生所需要的。学校的语言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是一种话语方式或模式的转换,而这种话语方式通常与他们的家庭语言方式不同。在多语教育中,二语或三语的学习对学生来说也意味着从一种语言转入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环境。因此,在多语教育中使用语类教学法,不仅需要结合学生的经验知识,还需要使用他们的母语来帮助他们获得和控制语类知识。
(一)通过母语拉近编码取向距离
伯恩斯坦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在家庭生活互动中习得不同的语义资源,形成不同的编码取向,一般分为:“限制型语码”(Restricted Code),其依赖于具体的语境,句法简单,词语范围狭小,适合表达简单具体的概念;与“精致型语码”(Elaborated Code),其不依赖具体的语境,句法结构复杂,措辞严谨,适用于分析、推理与表达抽象的概念。学校语言属于精致型语码,因此学校教育对于持精致型语码的个体来说是符号性与社会性的发展(symbol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而对于持限制型语码的个体来说则是符号性与社会性的改变(symbolic and social change)[17]。对于少数民族学生,他们的编码取向不仅存在日常生活语言与学校生活语言之间的差距,也存在两种语言文化编码差异。因此,在引入新的语言编码时,应使用学生所熟悉的母语日常用语,通过多模态资源如图片、录音、影像、视频等方式引入目标语语场、吸引学生的兴趣,让学生逐步接触认识目标语语篇,在与学生共享经验的语境背景下恰当地引入目标语日常限制型语码作为课堂语言。
从局部课程语类来看,在准备阶段,可以大量地使用学生所熟悉的母语及母语多模态资源,构建学生的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再展示目标语类语篇,并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使学生理解新的语篇意义;在聚焦和任务阶段,可以使用母语很快让学生明白他们的任务,从而减轻他们的符号负担,快速成功地完成任务;在评价阶段,可以引入目标语简短的积极评价语言,因为在完成前面三个语步后,学生成功地完成任务并已经成功地创设了学习语境,学生能够在语境中明白这些简单的语码,在情景中学习新语言的“限制型语言”;最后在详述阶段,教师可以主要使用目标语来解释协商语篇中的句子和词项,展示目标语言知识,明示限制型语码与精致型语码的差别,使持有限制型语码的个体意识到新的社会符号资源的存在。因为在前面几步老师已经与学生进行了意义协商,为新知识的展示做了充分准备,为学生逐步掌控语类知识搭好了支架,所以最后一步就是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展示语言知识。简而言之,准备阶段为梅顿所说的知识“解包”过程,即通过学生熟悉的母语及他们的一些“限制性语言”让学生理解“精致型语码”;详述阶段为“打包”过程,即将语言知识抽象化过程,使学生以他们理解的方式获得识读资源的过程[18]。
(二)通过母语强化和再语境化语类知识
从全局的课程语类来看,在语类知识的解构过程中,还可以充分利用他们已有的母语语类知识,将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类知识进行对比,强化他们所学的新的语言知识。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前所持有地为限制型语码,因此还需要进行语码干预,以缩小语码取向直接的差异为目的,加强母语中认知或学术型语言资源的传授,提高学习者的认知/学术语言能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多语课程设置中,不应该仅仅采用单语取向,在课堂中仅仅使用目标语或仅设立目标语语言目标,而应该设立多语目标,开设多语课程。三语习得研究也证明了学生在三语习得的过程中掌握的多种语言知识、培养的元语言意识以及他们的学习经验可以帮助他们学习新的语言。因此,学生母语精致型语码的形成可以促进他们目标语精致型语码的获得。
在重构过程中,可以使用学生所有的母语和目标语口头和书面的学术语类语言帮助学生前面阶段所协商的知识,如语篇结构、句型、重点词项等,将经验知识再语境化;还可以使用学生的所有交际意库的资源以巩固所学语类知识,扩大学生的最终交际意库。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多模态资源如图片、录音、影像、视频等方式引入目标语语场、吸引学生的兴趣,使用学生的日常交际用语让学生逐步认识接触目标语。另一方面,使用学生日常用语和/或他们的母语语类知识引导学生阅读理解目标语语篇,标记重点词项,这些活动帮助学生解包新的语篇。此外,使用L1/L2口头或书面语类知识引导学生用所协商地语类知识再语境化。总之,在教学过程中,应打破单语路径或单语目标,使用加西亚和李巍等人提出的超语(translanguaging)[19]方式让学生灵活地运用他们的多语资源掌握新的话语方式。
六、结语
语类教学法提出明晰可见的教学方式,提倡在教学中将特定知识语类及语篇结构通过在共享知识背景下互动的方式展示给学生,从而让所有阶层的学生都得到获取学术知识和社会提升的通道,这种教学法正是缺乏主流社会文化和语言知识的少数民族学生所需要的。因此,语类教学法可应用于我国少数民族多语教育中,但在具体应用中应该结合中国少数民族具体情况再语境化,构建中国特色多语教育教学方法。我们应该结合学生的文化背景,充分利用他们的语言知识,为他们搭建支架,从而使他们逐步掌握学校知识,发展多语能力,成为国家和社会所需的少数民族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