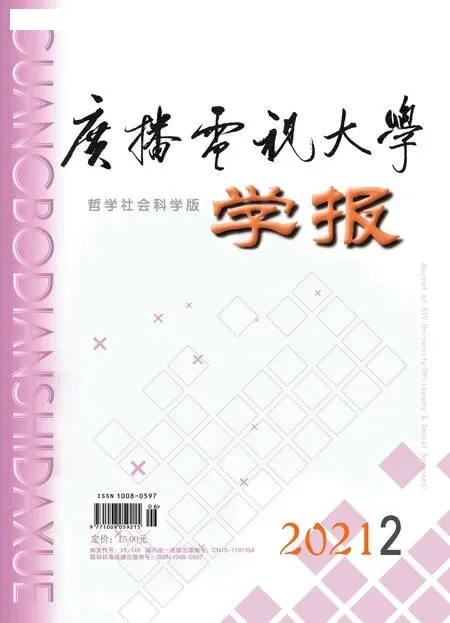人神共娱:素朴的湘西傩神信仰——论沈从文作品中的“霄神”形象
王梦琪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沈从文生活的湘西是汉、苗、土家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他以优美抒情的笔调展现故乡湘西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湘西一带隶属巫傩文化圈,自古是我国巫傩文化盛行的地区,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解《九歌》时有言:“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1]。湘西崇尚巫傩的风俗民情,为沈从文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资源,深刻塑造并影响着沈从文的文化观念。他诸多湘西题材的小说,如《神巫之爱》《龙朱》《凤子》《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都有对巫师、傩祭仪式、傩神信仰等巫傩文化要素的详细描写。这些与现代文明截然不同的古老巫傩文化,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增添了神秘而浪漫的色彩。从巫傩文化去解读沈从文文学作品,是追溯和探寻沈从文创作心理的一个重要视角。学界已有成果常从广泛的巫傩文化视野进行研究,①针对某些具体的神灵形象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却少有探讨,②因此从巫傩文化角度分析沈从文文学创作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譬如其小说、戏剧中多次出现的“霄神”形象。
“霄神”是湘西凤凰地区民间信仰的重要傩神之一,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着墨较多、具有明确名称的傩神。沈从文早期曾以这一傩神为题目,创作了独幕短喜剧《霄神》(发表于1926年7月28-29日《世界日报副刊》第1卷第28-29号),此外“霄神”形象还出现在同时期戏剧《鸭子》(发表于1926年7月17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84期)、小说《山鬼》(发表于1927年7月16日、23日《现代评论》第6卷第136-137期)等作品中。正如小说《神巫之爱》《凤子》等是解读湘西巫师酬傩仪式的文学作品,戏剧《霄神》《鸭子》以及小说《山鬼》堪称探究湘西地区民间“霄神”信仰的重要文本。本文以《霄神》《鸭子》和《山鬼》为中心,从文学视域着重探究近现代湘西地区的民间“霄神”信仰及其背后的精神文化蕴意,以期丰富从巫傩文化层面分析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研究。
一、“霄神”的形象建构
《霄神》《鸭子》和《山鬼》所提及的“霄神”是近现代湘西汉苗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信奉的神灵,然而少有文献记录这一神灵的外在形貌,因此关于“霄神”的形象特征往往仅是“据说”——“大神是身长不过一尺,头戴红帽,身穿花衣,脸如冠玉”。[2]P33“一尺”之高,“霄神”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神,“霄”“小”谐音,因此民间也将“霄神”称为“小神”。沈从文在《山鬼》中借村民之口提到了“霄神”的神力,主人公毛弟的兄长疑因“得罪了霄神”成了“癫子”,而霄神“在大坳地方”只能主掌“生人死人给人以祸福”[3]P342,不具备使人发癫的能力。该小说文本里从未出现过“山鬼”一词,仅提到了“霄神”,结合小说篇名,因此可以提出一个疑问,即“大坳地方”的霄神是否就是“山鬼”?笔者认为,沈从文笔下的“霄神”与“山鬼”在形象上形成了一定的同构性。首先,“大坳村”四周皆是群山,百姓在家中、庙里都供奉神灵,再加之山上有强盗,“山鬼”下山不无可能。再者,经凤凰籍学者刘一友实地考察,结合自身生活经验,他在《沈从文与湘西》一书中认为,凤凰人口中的“霄神”与屈原《九歌》中的“山鬼”实则是“一脉相承”[4]P149的。《九歌·山鬼》通常被视为祭祀山神之作,“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的“山鬼”是人们想象的能够守护山川丛林的神灵,在上古时期鬼神不分,随着人类认识观念的不断发展,鬼神概念也逐渐分化,后世还认为屈原笔下湘楚地区的“山鬼”或是“山魈”是种生长于深山的猿猴类生物,“山魈”“山鬼”被敬称为“魈神”“山神”,又因“魈”同“鬼”义易犯忌,此后又衍变为“霄神”。[4]P149“霄神”常被当地人称呼为“霄娘娘”,是“当地人并不欢迎但又不敢不欢迎的一位妖精”[4]P146,因此,“霄神”在神格上一般被认为是同“山鬼”一样妖精似的女神,正契合了《霄神》中人们所猜测的那般:面容美丽如玉,喜好漂亮衣服。“霄神”或是“山鬼”,都是可以保佑人们的神灵,某种程度又反映出湘西民间传统、素朴的泛神观念。在巫风浓厚的湘西地区,“霄神”诞生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人们敬畏自然界力量,进而敬畏由想象力赋予生命的诸多神灵,这些神灵们既具有通天达地的非凡神力,又充满着某种人的特性,形成了人神杂糅的神灵形象。
当地人敬畏霄神,因为她具有“生人死人给人以祸福”的能力。《霄神》主角舅舅周必富一出场就正“跪于神前”祈福,将霄神称作“菩萨”“大神大帅”,口中振振有词,向霄神请求“老幼清吉,六畜兴旺”[2]P29;《山鬼》中毛弟妈为了大儿子“癫子”的平安,向各种傩神许下“愿心”,因此“霄神”既承载着人们对风调雨顺、平安兴旺的深切向往,又保持着山间野猕般调皮、爱捉弄人的性格,使人又爱又恨,这也是湘西人们“并不欢迎”她的主要原因。《鸭子》正展现了霄神性格淘气的一面。经营卤鸭肉的葛喜发不想将鸭肉卖给占便宜的痞子,为了对付他便偷偷将篮中的鸭肉藏在了抱兜里,并谎称是霄神抢去了。当葛喜发提及“霄神”时,痞子“心虚”地打断了他,“那东西灵敏极了,也许听到。”[5]P46由此可见,霄神还有偷抢人财物的顽劣行径。根据美国学者金介甫《沈从文传》、刘一友《沈从文与湘西》中的证述,当地所信仰的霄神时常会钻进平民家中捉弄人,或有人不小心得罪了她,使她生了气,霄神便会“大闹”一番,“偷盗破坏人家财物,直到被人劝解才罢休。”[6]也正因如此,《霄神》中舅舅看到所供奉的酒壶被打翻在地时,向霄神请求不要“发气”;《山鬼》中“癫子”起初发癫可能是“得罪了霄神,当神洒过尿,骂过神的娘”[3]P342,使霄神发了气,为了解决发癫的情状,请求了巫师从中解“禳”。
沈从文在戏剧和小说中所设置的故事情节,以浪漫和写实相结合的写作笔法,还原了民间信仰中霄神的性格,她既可以赐福,保佑人们的生产、生活,又会降罪于人,施以小的惩罚,但通过巫师的介入便可得到解决。可见,霄神虽然性格有些顽劣,但终究还是一个性情豁达的善神。在《霄神》《鸭子》与《山鬼》中,沈从文对“霄神”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形象描写,而是将她放置于汉苗人民的精神信仰之间,融入当地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通过人们的日常话语间接地把她的形象建构起来。虽然“鬼神”本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幻想出来,借以解释超自然的现象的东西,但我们又能感受到,人们幻想出来的神灵有时又成为“实体”,霄神似乎就真实存在着,虽然见不到她的踪影,然而又实实在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成为湘西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之,我们可以从沈从文有关该神灵的文字里能够获悉的是,“霄神”与民间巫傩信仰息息相关,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所普遍信仰的傩神之一。霄神与人们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充裕着强烈的烟火气息,在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背后,她的形象建构蕴含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和丰富想象。
二、“霄神”的信仰仪式
霄神是湘西地区掌管地方的主要傩神之一,且当地有悠久深厚的信奉和祭祀神灵的传统,这从沈从文在《山鬼》中的描述可见一斑:“大坳村子附近小村落,一共数去是在两百烟火以上的。管理地方一切的,天王菩萨居第一,霄神居第二,保董乡约以及土地菩萨居第三,场上经纪居第四。”[3]P345关于寻常人家祭祀霄神,《霄神》中有诸多祭祀细节的描写,例如舅舅在家中堂屋陈列“三牲香烛,良酝黄楮”,还准备“杀猪宰羊,为大神寿”,外甥牛二疱子预备“买三个钱香,两个钱纸,去磕个头”以敬霄神;[2]P30-31《山鬼》中提及岁末会有“苗巫师来到家里穿起绣花衣裳打锣打鼓还愿为全家祝福。”[3]P341沈从文还借助《山鬼》中“癫子”的视角还原了乡间庙宇里的祭祀活动:“癫子上庙里去玩,奇怪大家拿了纸来到此烧,又不是字纸,还有煮熟了的鸡,洒了白的盐,热热的,正好吃,人都不吃倒摆到这土偶前面让它冷,这又使癫子好笑。”[3]P345可见,筹备猪、鸡、羊等三牲,备好佳酿,点燃香烛、黄楮,焚烧祭祀专用的钱香、钱纸,磕头致敬,这是湘西民间寻常人家一般的祭祀方式。除了家家祭祀傩神之外,村落里还会举行更大的表演活动,例如《山鬼》中提到的“木人戏”。沈从文在小说《长河》中也做了进一步解释,“通称木傀儡为小戏,人唱的为大戏”[7]P181。无论是木偶戏还是人的表演,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在酬傩仪式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常在“农事起始或结束时”[8]表演,主要有“酬谢土地”“公众娱乐”[8]的目的。美国学者金介甫认为沈从文戏剧和小说中的“霄神”,应当也是湘西地区“傩戏诸神之一”[6],这一点在沈从文同时期创作民歌集《筸人谣曲》(1926)前言中得到了验证。
沈从文一直有将湘西地区的文化艺术展现给中国读者的抱负:“我还希望……把我们那地方比歌谣要有趣味的十月间还傩愿时酬神的喜剧介绍到外面来。此外还有苗子有趣的习俗,和有价值的苗人的故事。”[9]此后,沈从文在1979年致金介甫的回信中也专门谈到戏剧《霄神》的故事“出于本乡本土”[10],是家乡酬傩仪式中的一部分。可见,沈从文在1926年接连创作《鸭子》《霄神》等有关民间“霄神”信仰的独幕笑剧正出于他的那份抱负,因此戏剧《霄神》《鸭子》是可以作为酬神的喜剧来理解的,这两部戏剧具有傩剧、傩戏的性质。傩戏、傩剧作为民间酬傩的一种仪式,“通过献牲(猪、羊、鸡等供品)和演出节目以取媚神灵,使得神愉快地为人间驱鬼逐疫,降福呈祥,以求人寿年丰、六畜平安、天下天平”[11]。沈从文《霄神》中的“三牲香烛、良酝黄楮”既是祭祀神灵的供品,同时还是傩戏、傩剧中表演的道具。金介甫曾在《沈从文传》中提到,沈从文所写的此类笑剧“多半在夜间举行”,由殷实的人家筹办法事,并会有巫师主持,戏剧的表演者一般也是筹办方的贵宾,同时还是“苗民宗教人的儿子——舅父和外甥之类”。[6]《霄神》的情节设置正是如此,外甥因赌博输了没钱吃饭便潜入舅舅家祭祀霄神的厅堂,假装霄神显灵哄骗舅舅,想偷食供品,最后被舅舅发现差点一顿捶打。金介甫认为表演者“舅舅”与“外甥”的这种血缘关系,更进一步地增加了酬傩表演的喜剧效果。这些傩戏、傩剧设置类似《霄神》舅舅与外甥、《鸭子》卖家与买家等冤家对头之间的“一场斗智,看谁能压倒对方”[6],通过一系列插科打诨,呈现出滑稽风趣的极具故事性的表演形式,既可以达到取悦神灵的目的,同时还具有娱乐民众的效果。
此外,沈从文创作《霄神》《鸭子》等酬神笑剧还有一个重要的契机。《霄神》《鸭子》创作的同一年,周作人翻译的《狂言十番》(1926)在北新书局出版,沈从文在1979年致金介甫的回信中谈及“《霄神》,可能受当时周作人译日文《狂言十番》或《希腊拟曲》影响而成”[10]。从《狂言十番》和《希腊拟曲》的内容形式而言,沈从文创作《霄神》《鸭子》等独幕笑剧更多应该是受到日本狂言的影响,
《鸭子》正文之前有“拟狂言”三字也能够确认这一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湘西地区傩戏、傩剧本身的内容表演就是以喜剧、笑剧的形式开展的,这一点恰与日本狂言不谋而合。谈及日本狂言,湘西傩戏、傩剧与狂言可谓是本源同宗,狂言这一艺术形式在广义上是能剧的一部分,它穿插于能剧剧目表演之间,是一种即兴幽默的短剧。能剧与湘西傩戏、傩剧相同,也源于人类的宗教信仰及祭祀活动,它的形成最初是受中国傩礼影响。湘西傩戏与日本能乐,虽有表演形式和地域之间的差异,但究其本源是相同的。湘西傩戏、傩剧与狂言、能乐的表演目的及其效果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取悦神灵,兼以娱人,致力于达到一种人神和悦的境界。然而类如湘西傩剧等中国傩戏表演至今没有像日本狂言或能剧获得长足的发展,这种巫鬼文化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难上大雅之堂,且因涉鬼神,颇有忌讳,几乎没有文学家对此进行记录或创作③,沈从文《霄神》《鸭子》等戏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傩戏剧本创作的空白。这两部有关“霄神”的独幕戏剧从“戏剧”和“傩仪”的角度而言,作品形式本身就属于酬傩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傩戏的现代创作和复原,这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之于中国传统傩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贡献。
三、信仰的精神寄托及流变
沈从文在1926-1927年接连创作了三部以“霄神”为主题的戏剧或小说,其中以独幕喜剧《霄神》为代表,将湘西地区民间“霄神”信仰及其祭祀仪式表现详细地呈现出来。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民间的“霄神”信仰全面进入到湘西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且深刻影响了他们的道德精神谱系及民族心理性格的形成。应当注意到的是,沈从文所生活的湘西地区在近现代随着苗汉等多民族之间不断融合,傩文化与儒、释、道随之交汇合流,传统傩神信仰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民间信仰不断趋于多元化,“霄神”信仰产生及其流变就受到道、佛两家神话谱系的影响,戏剧《霄神》中舅舅就曾将“霄神”称为“菩萨”,可见傩神信仰与其他神话体系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使原始的自然神灵信仰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不同文化的相融中,“霄神”并不是当地人民唯一信仰的傩神,也还排不上“第一”的位置,沈从文在小说《山鬼》中有过描述,除霄神外,民间还信奉天王菩萨、土地菩萨等神灵,此外小说《长河》提及湘西地区还有敬奉火神、伏波元帅、财神、天后等庙宇[7]P39。即便如此,“霄神”信仰的力量在湘西地区依旧没有减少半分,始终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并进而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成为现代道德法治文明尚未出现时期的替代物,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着传统道德规约的职责。
沈从文笔下的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神”早已与人相融合,带有浓重的人间烟火气,“霄神”正是如此。这些神灵就在乡民之间,或许只是不曾显现其形态,但却促使人们在精神观念上达成共识。傩神信仰甚至在湘西人民的内心形成了一种类似道德法制的规约,使他们敬畏天神,不犯违禁之事,否则将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即便被“霄神”这样的“小神”发现,也会对其不端行为降罪和制裁,例如《山鬼》中提到的使人“发癫”。沈从文在《霄神》中就展现了傩神信仰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规约性,舅舅在神前祈祷时提到自己“平日诚实待人,与物无忤”[2]P30,唯恐自己内心不诚而惹怒霄神;《鸭子》中痞子抱有不劳而获之心,葛喜发猜透他的心思,偷藏起来鸭子并托词是霄神拿走了,痞子虽心有不满,但当提及“霄神”时言语之间也有些心虚和惧怕——“好,好,我们莫谈这个吧,那东西灵敏极了,也许听到”[5]P46。可见,“霄神”虽性格有时顽劣去拿取什物,但终究是一个能够主宰生死、赐予祸福的神灵,人们敬畏他们的神力进而以此反省和约束自己的举止行为,以免触犯神忌,引发灾祸。这种质朴的民间信仰既是维系人与人之间道德谱系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撑,同时还塑造了湘西人民自然朴素的民族性格。《山鬼》中毛弟妈具有“全份”的“天上的神给了中国南部接近苗乡一带乡下妇人的美德”——“像强健,像耐劳,像俭省治家,对外复大方”[3]P341,又如《霄神》中平日始终“诚实待人,与物无忤”的舅舅。他们虔诚信奉神灵,祈祷平安,恰反映出傩神正是湘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心灵的寄托。
湘西的神灵大多如《山鬼》中所描述的混居乡间,“在乡下长大”[3]P345,同乡下人一样,也很朴实,他们可以说是神性与人性的混合体,同时还带有一点“魔性”[12]P360。可以发现,人们虽然对“霄神”等神灵有所敬畏,但从未将他们束之高阁,而是使他们更加贴近地进入日常生活。其实在湘西地区,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对于“神”的界定相对比较模糊,有时甚至“人神不分”。沈从文曾在散文《沅陵的人》中提到当地伏波宫里供奉的神明实则是汉代将军马援[12]P360,《山鬼》中有权管理地方的“保董乡约以及土地菩萨居第三,场上经纪居第四”[3]P345,“保董”等实则是保障地方农务和日常秩序的职务,而当地人民将之与“土地菩萨”相提并论,可见在湘西地区人与神的界限不再完全平行,而是相互交叉的。湘西地区对神灵的信仰具有多神、泛神的性质,沈从文曾描述沅陵一带的妇女买来纸张、香烛回家“做土地会”“事实上就是酬谢《楚辞》中提到的那种云中君——山鬼”[12]P354。而“霄神”“云中君”“山鬼”和“土地神”如今看来并不是同一种神灵,但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地区人民眼中似乎是一样的,因此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祭祀行为多具有相同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渗透,传统民间信仰在现代文明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人对天神的敬畏,在近现代社会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更早时期,人们对于神灵是极度敬畏的,然而随着多民族的融合与湘西地区不断对外开放,近现代以来外界政治经济精神文明传入湘西,物质、金钱、权力至上的都市文化也逐渐侵蚀着朴素的乡民心理,使他们在传统的信仰心理上也发生了变化。人神界限不断模糊,敬畏之心渐趋消缓,有时人的力量甚至超过了神力,来主宰人的命运。沈从文在《山鬼》中就展现了政治文明对于传统信仰的干扰,政府官员捉来一些乡下老实人,强加以“与山上强盗有来往”等莫须有罪名,来“罚钱”“杀头”,这些政府官员“比霄神来得还威风,还无端”,而当地人却还将之认作是“命运”,[3]P343可见当地人从未思考过要去反抗官府的恶劣不公平的行径。沈从文在这里既以讽刺的口吻批判了地方政府的横行肆虐,同时又表现出对地方人民思想保守冥顽、毫无反抗精神的担忧与无奈。此外,戏剧《霄神》《鸭子》中将赌博等娱乐手段使人的堕落化也写了进来,外甥牛二疱子、痞子这两个人物形象对神灵虽有一定敬畏,但赌博等恶习使他们形成了贪图便宜、好逸恶劳的性格,沈从文也借此隐晦地表现出现代都市文明中的负面内容对人们精神信仰及内在品格的冲击。
傩神“霄神”既能带给人以祸福,同时又潜藏于乡民日常生活之间,有时还有一些顽劣,即便如此她依旧是湘西人民普遍敬畏和信仰的神灵。人们通过一系列的祭祀方式取悦神灵,傩戏是其中一种重要的酬神仪式。沈从文创作的独幕喜剧《霄神》《鸭子》就来源于当地酬祭“霄神”的实际表演。沈从文更进一步将当地傩戏重新创作成为新的文学作品,创造性地延续了湘西傩剧、傩戏艺术的生命力,并在作品中进一步肯定了“霄神”等傩神信仰的价值及其意义。沈从文不仅表现出民间朴素的“霄神”信仰深刻影响了湘西人民的道德精神谱系及地方心理性格的塑造,同时还在作品中进一步表达出对现代文明冲击湘西乡土文明的担忧和思考。沈从文有关“霄神”的戏剧、小说,向读者呈现出湘西地区独特的民间信仰风俗,体现出对家乡湘西地区民间传统文化和地方精神特质的深切关注,也使其文学创作更多了一份神秘与浪漫的色彩。
[注 释]
①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1985)较早指出沈从文与苗族的血缘联系决定了他创作上中国南方楚文化的印记,巫鬼文化传统给沈从文的创作带来了浪漫幻想色彩。向柏松《沈从文与巫风》(1991)、邱文清《沈从文作品中的“傩祭”现象初探》(1998)重点讨论了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巫傩文化要素。进入21世纪后,谭桂林《巫楚文化与20世纪湖南文学》(2000),肖向明《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2007),罗宗宇、翟翊翔《傩文化与沈从文的创作》(2013),张翠敏 《“女神”形象的原型回归———沈从文“神话”情结的典型体现》(2015),李萍《论沈从文故乡题材作品中的信仰崇拜文化》,吴正锋《论沈从文创作与湘楚文化精神》(2017),李美容《人文地理学视角下沈从文神性“湘西”的书写》(2019),颜芬《论湘西巫傩文化与沈从文的文化意识》(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易瑛《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象——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版)等论著,对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巫傩文化意象及其影响有较为详实的分析。
②目前美国学者金介甫在《沈从文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中对沈从文早期笑剧《霄神》的创作渊源有过较为详细的考证,邱文清《沈从文作品中的“傩祭”现象初探》(1998),罗宗宇、翟翊翔《傩文化与沈从文的创作》(2013)两篇论文仅谈及戏剧《霄神》的创作,但并未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③“傩戏一向遭受文人的鄙弃,没有任何剧作家愿意为傩戏编写剧本”。参见曲六乙、钱茀《东方傩文化概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