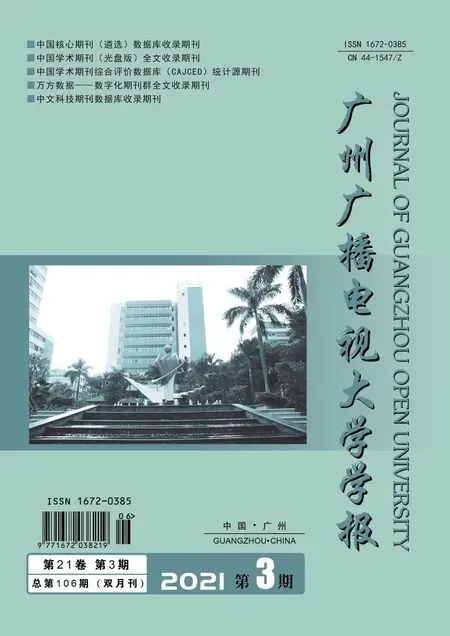岭南莞邑文化演进轨迹的历史考察*
李永芳
(广东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东莞 523083)
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绵延的精神血脉,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莞邑文化是以广东东莞地区为地域依托,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包括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在内的区域文化体系,其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加强莞邑文化的理论研究,充分开发和利用东莞地区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仅能够彰显该地区的魅力和风采,为促进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而且对于拓宽和加深岭南文化乃至汉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不无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于岭南文化的研究可谓著述充栋,而对其组织“切片”莞邑文化则着墨不多,甚感薄弱。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弥补学界这一缺憾,对莞邑文化的发展轨迹做一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推动该专题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先秦时期:莞邑文化的起源与雏形生成
据史料考证,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东莞境内东江沿岸开始聚居的原始人群,已经能够使用多种较为先进的细石器,从事渔猎和农耕,从中可窥见“南越文化朦胧的曙光”[2]。这一时代的文化遗址目前在东莞境内已发现18处,具有代表性的是南城蚝岗、企石万福庵、石排龙眼岗、虎门村头等史前文化遗存及谢岗先秦遗址。历经夏商,时至西周,南越作为一个族体已经形成,南越文化也就成为其重要标志。
上述表明,南越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定型。与之相应,作为其体系下的子文化——莞邑文化亦具雏形,其文化特质在物质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1)特异的饮食风俗。即居民除了把稻谷作为主粮外,还把鱼类、贝壳等水产以及虫、蛇、鼠类等作为嗜食之物。(2)鲜明的服饰特点。即居民以棉、麻、蕉、葛、竹、絲等纤维为衣料,所制衣服简单凉快,适应南方气候。(3)多彩的穴居建筑。即居民由初居洞穴发展至山区半地穴式的建筑以及平地而起的茅草房,在沿海与临河地区则是“干栏式”的建筑形制,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用瓦盖房顶的木构建筑。(4)独特的舟楫交通。即人们因生活在江河水浒,故不仅“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而且“善于造舟”[3],舟楫是其主要交通工具。正是基于这种物质文化,相应的精神文化亦同时产生,其中包括一些迷信风俗,譬如笃信巫鬼等。
二、秦汉六朝:莞邑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南北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即已频繁发生,这使包括东莞在内的南越文化得以改造和发展。一是中原文化的影响。譬如周天子曾对南方诸蛮等“凡其出入送逆(迎)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商代伊尹曾制定四方献令,对南方各民族“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4]。二是荆楚文化的影响。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于是南平百越”,荆楚文化长驱直入。荆楚文化对南越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稻作文化、青铜文化、城市文化以及移风易俗等方面的传入,直到秦灭楚后荆楚文化才为强大的中原文化所代替[5]。三是吴越文化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岭南先民即与江浙先民有所接触,楚灭越后,部分吴国越人流入岭南,更多的吴越文化传入并被融合为南越文化之一部分,时至今天仍斑斑可考,“广州语多与吴相趋近”[6]。四是巴蜀文化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张骞出使大夏,见到从印度转贩过来的蜀布和邛竹杖等货物,即是由四川运来南越再转往印度的[7]。另据学者考证,在广州五仙观里,五位仙人手中所持谷穗之少者,便是江淮、巴蜀无名水稻栽培技术传播者的化身[8]。时至秦汉,岭南先后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于是中原汉文化与南越文化接触更为紧密并逐渐融合。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地区后,随着军队与汉民的迁入,他们把中原地区的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技术以及生产方式等带到岭南,于是新的文化风貌逐渐形成。尤其是大量铁器农具的输入以及大片荒古土地的开垦,大大改变了岭南地区“无积聚而多贫”的状态。东莞之所以成为岭南经济文化最先发展地区以及现今最发达地区,显然与此历史传统不无关系。
秦末汉初,赵佗曾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长达95年,但其政权依然坚持了秦汉政权的基本政治制度,并且糅合了各个民族的文化政策,使得由秦开辟的汉文化传播渠道更为畅通。如赵佗在位时曾采取了鼓励汉越通婚、办学教民、移风易俗等一系列措施,使南越人的汉文化意识不断加强,加快了汉越民族的融合过程。汉高祖刘邦曾对赵佗治理岭南的功绩高度称赞道:“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9]。赵佗死后不久,南越国被汉武帝平定,由此揭开了汉文化直接在岭南传播新的一页。由于中原和楚地大批农业生产工具的输入,岭南地区大面积密林深谷得以开垦,稻作及经济作物栽培业得以长足发展。至东汉初,桂阳郡属下粤北各县“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社会风俗大有改观。
六朝时代,随着移民高潮的出现,岭南地区成了中原各阶层人士的避难场所和落籍之地,由此汉文化在岭南的传播也就出现了第一次转机。这次移民高潮,持续时间长达近300年,大大改变了岭南地区的文化结构和精神面貌,是岭南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和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
三、隋唐五代:莞邑文化与汉文化的趋同与丰富
自隋开京杭大运河,五岭南北交通状况大为改善。唐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即大梅关)新道后,该道便成为广东北上的主要交通线。且唐代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巨港,也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从而促进了南越文化与汉文化趋同局面的最终实现。大量史料表明,唐代包括东莞在内的“广府”一地,“渐渐跟上中原农业发展步伐”;所产陶瓷“釉色纷呈”;所产纤维制品“别具一格”;唐宋璟任广州都督时“将建筑文化引入岭南”;珠江三角洲兴起圩镇,“圩市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也在它们中形成”。[10]
五代时期为我国第二次移民高潮,其对岭南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入。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因统治岭南的刘氏来自中原,故“所招用多中朝名下士”,其中不少为避乱再迁世家,如刘隐对“唐世谪宦子孙遭乱不得返,及因乱避地来岭南者,多留为之用焉”。再者多为唐和后梁派到岭南的使节、官吏,“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这样,南汉境内“名流毕集,分任得宜,岭表获安”。[11]
四、宋元明清:莞邑多元文化体系的确立与勃兴
在北宋末年和南宋末期,由于金人以及元人相继南侵,致使大量灾民流亡到岭南地区,其“以珠江三角洲、东江和韩江谷地、雷州半岛等处最为集中”[12]。大抵宋元交际时期,初步形成了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因东莞隶属广府民系,故莞邑文化也相应隶属于岭南文化及其分支广府文化之下的子文化。
到了明清时期,广东文化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内外联系的加强与扩大,其发展日趋兴旺。在此期间,先前宋元时期上升为岭南文化主体的汉文化进一步生长壮大,岭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充实,从而造就了岭南文化原型。具体来说,明清时期莞邑多元文化体系的确立以及勃兴主要表现为:第一,土地利用景观基本定型。即“大片沙田为水稻占领,而围田则为蚕桑、甘蔗、水果等经济作物覆盖或是水稻所在”;部分山区“梯田成为土地利用的一种主要方式”;更有多种水果、蔬菜、花卉等作物“成为不同类型土地的占领者,参与当地传统文化空间”[13]。第二,专门化农业区域初步形成。明清东莞县的专门化农业区域主要包括基塘农业区、水草种植区和莞香种植区。其中基塘农业区主要是“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分布于东江三角洲地区。《广东新语》曾云: 在东莞石龙等地,“其地千树荔,千亩潮蔗,橘、柏、蕉、柑如之”[14]。水草种植区以莞草为主,其用来编制睡席、草绳等。在东莞厚街至虎门一带,卤田千顷皆产水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该地草田已经达到一万多亩[15]。莞香种植区以茶园为盛。东莞素有“岭南香国”之称,“人多种香为业,富者千树,贫者亦百树。香之子,香之萌粟,高曾所贻,数世益享其利”[16]。第三,手工业和加工业蓬勃发展。据[康熙]《东莞县志》记载,当时在东莞生产和贸易的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就有数种,包括“纸、笔、扇、香皮纸、干枝、干圆、牙香、片糖、白糖、胶纸扇、蜜糖、火油、莞席、白蜡、伞、靛、陈皮、蚬灰、苏木、竹青、砖、石、瓦”等[17]。第四,墟市(镇)发展繁荣昌盛。据史料统计,东莞在明嘉靖年间,墟市数量为12个,平均人口7144人,平均面积227平方公里;在清雍正、乾隆年间,墟市数量为49个,平均人口21113人,平均面积56平方公里;在清咸丰至宣统年间,墟市数量为55个,平均人口18958人,平均面积49.3平方公里[18]。其中部分墟市发展成为市镇。前述清初东莞的石龙镇,其与广州、佛山、顺德陈村等作为广东四大名镇,标志着一个城镇系列已经形成。第五,城镇勃兴和建筑文化走向成熟。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东莞在宋元县城的基础上增筑新城,主要在南、西两个方向上有较大的拓展,包钵盂、道家二山于内,城周一千二百九十九丈,城墙所围面积明显扩大。清嘉庆年间,东莞县城街巷达到77条,其中明确分列出城内街巷43条,城外街巷34条。同时,明清时期城镇建筑文化亦走向成熟。各种建筑既借鉴了中原和江南地区的建筑风格,同时又结合岭南地理特点,显示其“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已达到成熟阶段”。[19]
五、近代以降:莞邑文化的蜕变与新生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步形成,莞邑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封建文化日趋腐朽和没落,进步文化则萌芽和生长。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华侨文化的形成和参与,更使莞邑文化不断发生离析、崩塌、扬弃和蜕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莞邑文化进一步得到改造和升腾,成为时代先进文化。
首先,农业文化涅槃崛起。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东莞传统农业土地利用逐步被卷入国际市场且建立起自己的分布格局。其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日趋萎缩,经济作物地位普遍提高。譬如,传统发达的稻作文化日渐走向下坡,“光绪末年禾田多半基塘”,“将沃壤膏腴不种稻而种葵”。又如,棉花曾是东莞人传统的主要衣料来源,但由于甲午战后大量洋纱洋布流入国内市场,造成东莞植棉业境况衰微,“往往数里之内,不见一棉”[20],机杼之声很难听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不断调整和优化种植业结构,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的,按照城郊型、生态型、外向型的农业发展思路,在确保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进一步调减粮食面积,使东莞市种植业结构更趋合理。目前,东莞水果生产已初步实现了区域化生产:丘陵、山区片主要种植荔枝,其中虎门成为番荔枝种植基地;埔田片种优质龙眼;水乡、沿海片种香蕉[21],等等。
其二,工业文明逐步建立。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工业生产、管理技术的传入,东莞利用其南海边陲的地理优势,吸收新式工业技术,近代工业文明逐步建立。当然,东莞工业化的真正实现,是在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东莞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80%之多,工业企业仅有377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生产产值只占30%左右。而改革开放40年来,东莞市迅速实现了工业化,逐步形成了以IT产业为主导,机械电气、纺织服装、家具、五金等产业为支柱,配套能力日趋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全面参与了国际产业分工,具备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础。2006年底数据统计显示,东莞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0.7:58.0:41.3。全市实现工业增加值1457.6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5.5%,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7%。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5512亿元。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64亿元。[22]
其三,城镇文化景观革新。早在民国时期,东莞就曾进行了以拆城墙、开马路为中心的大规模市政建设,初步体现出了近代城镇文化风格。进入21世纪后,东莞全面推进城市建设,使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东莞已经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和较为完善的城市功能,城市环境不断优化。特别是近些年来东莞涌现出了虎门服装、厚街家具、常平物流、大朗毛织、清溪电子、樟木头房地产等一批特色产业。[23]
其四,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东莞自唐代开始实行科举教育,自那时起就有众多的私塾、社学、义学、书院。到明末清初,东莞私塾已遍布城乡,课程多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等。东莞最早的书院是北宋时岑金(现香港锦田)邓姓宗族开办的力瀛书院。在明清两代的书院中,东莞共有35所,位居全国县级之首[24]。鸦片战争以后,受西方教育文化的影响,旧式书院受到改造,各级新式学堂相继设立。这些学堂或学校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对传播近代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的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0年底,全市共有小学330所,在校学生55.24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初中150所,在校学生18.79万人;高中阶段学校有66所(含民办学校18所),在校学生11.79万人(含技校);普通高等院校5所,其中本科院校2所,专科学校3所,在校学生3.83万人。另外,全市有幼儿园727所,其中公立集体办园169所,民办园558所,3至6周岁在园(班)幼儿共20.84万人,入园(班)率达95.15%。[25]
其五,文化发展与时俱进。如果说莞邑文化在近代经过历史洗礼已经脱羽,定型为一种区域性文化体系,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莞邑文化不断得到改造、充实与发展,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莞邑文化与时俱进,其开放意识、改革精神、生活方式、衣着打扮等基本元素,均已迈进在新的发展平台上。在2010年东莞市政府制定的《东莞市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了由文化新城向文化名城的战略转变,主张用十年的时间,将东莞打造成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现代文化产业名城、岭南文化精品名城等“四个名城”。推动东莞文化形态由村镇文化向都市文化转变,文化层次由基本的文化权益保障向造就高品质的文化生活转变等。重商的东莞人,善抓机遇,莞邑文化也就开启了实现高水平崛起的新征程。
结语:莞邑文化的基本特征
概括莞邑文化的流变轨迹,不难看出,莞邑文化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地理区位和环境条件的熏陶、政治制度和行政建制的影响、民族交融与人口迁移的整合、技术进步和经济规律的催化、族民潜质和历史传承的积累,等等。同时,莞邑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包含了岭南大区域文化的共性特质,又呈现出了自己的鲜明特征,即:一是悠久性。如前所述,早在5000多年前东莞境内东江沿岸就有原始人群聚居。据统计,东莞现有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35处,不可移动文物459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个、名村2个;中国传统村落6个;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1个、名村7个、街区1个,居广东全省前列[26]。二是开放性。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即从东莞所在的岭南地区出发,清代设立于广州的十三行曾是外国商行聚集的地方。近代以降,包括东莞人在内的广府人与海外广为接触、交流频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人文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以电子资讯产业为支柱的外源型经济结构,成为国际性重要的加工制造业基地。2007年底数据统计显示,全市外贸总量连续七年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成为中国综合经济实力30强城市之一[27]。三是包容性。据统计,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外来人口增长迅速,仅1986—2000年,外来人口即从15.62万人增加到254.7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3.47%。“根据从东莞市公安局以及消防队和粮食部门得到的数据表明,目前东莞市人口应在1000—1100万,也就是说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5倍。”[28]四是务实性。历史上的东莞,“自昔被人视为蛮烟瘴雨之区”[29],正是在改变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东莞人学到了更多的生存本领,培养了务实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在当代中国,东莞人的务实精神更加明显。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加工业开始向外转移,当时东莞发展工业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缺人才,但又具有毗邻香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并有几十万香港乡亲等有利条件。东莞市决定“借船出海”,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突破口,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当时有不少人把港商回来办企业看作是地主、资本家卷土重来剥削工人农民;也有人认为“三来一补”这种引进形式层次低,利润少,“两头在外两头黑”。面对这些问题,东莞没有卷入争论,而是鼓励试验,埋头苦干,让事实说话。尝试的结果是经济得到发展,群众得到实惠,东莞也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发展外向型经济、以经济国际化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向[30]。五是创新性。东莞市近些年来所获得的荣誉可充分折射和说明这一点。例如在2004年11月,东莞市当选为中国10个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之一;在2005年9月,东莞市28个镇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中全部上榜,是全国千强镇最多的地级市,其中虎门镇名列全国千强镇第一位。不难理解,这些辉煌成果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闪现着莞邑文化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