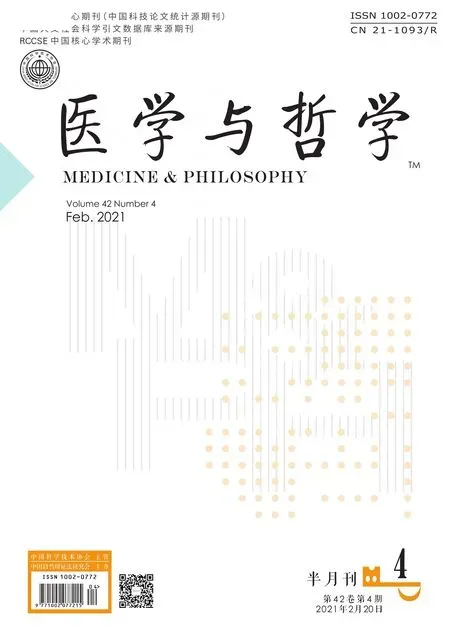疾痛意义建构与生命代价承受*
——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的叙事
曾书清
1 关于“常态”与“病态”的讨论
就健康问题的生物性而言,按照现代西方生物医学体系所做的划分,健康与疾病同属机体的两种表现形式而外显或内隐于人类躯体,分属正常状态与异常状态。人们看待健康和疾病的态度截然不同,疾病往往被视为“生命的阴面”和一重不受欢迎的麻烦身份,显然,我们都希望避免疾病这重麻烦的侵扰,只乐于保持健康状态[1]。尽管我们都对“生命的阳面”心向往之并采取各种措施以竭力避免或降低发生机能障碍的可能性,但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却是,人类的生物特性决定了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会与疾病不期而遇。在大众的惯常认知中,疾病向来被安置在健康的对立面,健康状态为符合众望的“常态”,患病状态则是令人厌恶的“非常态”,“常态”与“病态”归属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
然而,医学人类学主张健康问题远不止狭隘的生物现象。健康概念现已超出生理和心理的机体辖制,应被定义为一种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多重健全状态[2],对人类健康问题的思考越来越需要将生物性之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囊括在内,医学的人文性质得以重新定义。疾病与疾痛的概念分野伴随着医学的人文转向而发生,是人类学为进一步揭露疾病的非生物属性而做的努力之一。疾痛“意在表现人的难以避免的病患经验”,注意到病人及其家人乃至与病人存在更广泛社会联结的群体,强调病人对苦痛的切身感受;当医者基于生物医学的解释模式,将病人关于包括“可怕的症状、苦楚和困扰”等鲜活经验在内的主观讲叙剔除之时,疾痛问题便被重组为作为诊断单位的疾病问题[3]1-5。由于疾痛叙事与更泛化的社会结构因素和具身化的个体经验相互依存,它们一同形塑了真实的疾病感知[4],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患病状态是病患群体及其相关社会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同疾痛概念一齐扩容的“病态”不仅意指病患生物躯体和心理体验所表现的状态,还包含独立于躯体但与病患相关联的任何态势,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意涵也应包含在疾病的发病、病程和结果中。
作为疾痛首要意义的疾病表面征兆,“异常”的躯体状态隐含着关于身体与自我间关系的认识。将病患个体放大到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整体视野中重新审视,向内看,躯体是承载个体苦难的生物载体;向外看,躯体处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中心。疾痛及其诊疗试图弥合横亘在生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鸿沟,使客观社会环境与主观内在体验循环相接,在这个意义上,躯体是社会的节点,疾痛是文化的建构。偶然扮演的“病人角色”允许个体从原有社会结构中短暂脱嵌,但社会要求脱嵌的个体有恢复“正常角色”的愿望并催使其尽快重新嵌入原有的社会结构[5],此时的躯体不仅担负着病症的生理疼痛,亦面临着来自个人、社会和文化的多重结构性压迫。医学在两种角色的转化过程中起到不容小觑的关键作用,符合社会期望的就医活动即为行之有效的主要释压途径。但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某些情况下,“病人角色”的扮演并非偶发甚至该角色有可能具有先天属性,在客体看来为“非常态”的“病态”,事实上便成为病人日常面临的“常态”。“病人角色”理论在显露其局限性的同时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一个残酷的社会事实,即被迫长期扮演“病人角色”的某些病人与社会的脱嵌将在所难免,加诸躯体的多重压力亦难以舒缓。当“病态”成为“常态”,难以避免的社会脱嵌问题以及病患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仍然存在,但必须提出,这并不意味着疾痛的意义世界在“正常”社会角色的长期空缺状态中必然走向畸变。
为探讨上述问题,本文以脊髓性肌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SMA)患儿家庭为研究对象,尝试从疾痛叙事的个体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SMA是造成婴幼儿死亡最常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以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的退化为病理学标志[6],是较常见的罕见病。按发病时间和病情进程,儿童期SMA划分为3种类型:Ⅰ型为婴儿型,多在3个月内出现严重的全面性肌无力,多数在2岁内死于呼吸衰竭,是最常发的类型;Ⅱ型为中间型,患儿可独坐但不可独立或独走,可活过4岁且多数可达成年期;Ⅲ型为少年型,2岁以后出现近端肌无力[7]。起病时间和疾病进程依个体而异,但确定无疑的是,进行性肢体肌无力和肌萎缩等临床症状将随疾病进程的推移而逐渐加重,病人的运动功能随之受限。由于SMA是一种尚无特异治疗方法的基因缺陷病,幼年发病伊始,逐步发展的患病状态将陪伴患儿直至生命终点,对疾病进程的应对占据其家庭生活的日常状态。在“SMA病友之家”志愿者的支持下,笔者与有意参与研究的部分患儿家长取得联系,作为补充,还通过其他途径接触到一些成年病友,通过社交网络进行线上访谈。
2 “痛在我心”:疾痛意义的建构
由于某些人类苦难持久现于躯体,疾痛经验组成非专业人士对自身疾病的解释模式。不仅如此,这种躯体性特质还参与“形塑体验的不断变化的概念类别,以及导致苦难并塑造概念类别本身的社会制度安排”[8],这提示我们应将症状放在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境况中去诠释,因为疾痛的意义正是在前因后果中得以体现。本文摘取两个有代表意义的家庭讲述,分别是一例SMA-Ⅰ型和一例SMA-Ⅲ型,透过具体而微的案例分析其疾痛的意义世界何以建构。
案例1:阳阳在出生6个月后即诊出SMA-Ⅰ型,这是威胁患儿生命的重症类型。确诊那天,阳阳被院方断言“基本挺不过两岁”,因为现有医疗水平仅能舒缓病症而无有效治愈方案,无奈之下,省儿童医院的医生给出两个选择,“要么住ICU住到你们不想让他住了为止,要么带孩子回家拍点照留作纪念”。年轻的夫妻俩在门口徘徊许久,最终决定在出院协议上签字把孩子带回家,购买吸痰器、咳痰机、呼吸机等设备自行护理。与医生判断一致的是,阳阳的机体退化进程很难遏制,两岁生日之际出现严重的痰堵窒息,一度停止呼吸,情况十分危急。
阳阳母亲回忆道:“我抱着孩子,他爸爸使劲拍背,我这辈子都会记得当时我自己说出来的话,我说,‘他累了,让他走吧!’这时120到了,把吸痰管插深一点,孩子就从阎王爷那里救回来了。”搬回重症病房的孩子虽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病情依旧不容乐观,当医生再次提议“放弃”时,遭到这位母亲毫不犹豫的拒绝。谈起当时的选择,她说:“那天我问阳阳说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他表示不愿意,又问他去大医院好不好,他答应了。”当时依靠设备维持呼吸的阳阳尚不具备语言能力,阳阳妈解释道:“我是他亲妈,只要看他的眼睛,我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由于阳阳无法自主呼吸,必须做气管切开手术,“我亲自送他上手术台,看着他被麻醉过去,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有多疼,真的比生生地割我的肉还要疼。等在手术室外的两个小时里我几乎不能呼吸,他出来还不是很清醒,用尽力气对我们微微一笑的那个瞬间,我觉得又有了活下去的力量。现在已经三年多了,我们也不是傻子硬要吃这个苦,只是为人父母,这是最起码的担当。说放弃很简单,可忘记需要一辈子,要真的放弃他了,我怎么会心安?自从那件事以后,再苦再累,再怎么崩溃,我都没有过放弃他的念头,除非有哪天他自己不想坚持了。因为孩子一直在努力活着,就算再不完美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她的语气里透着坚毅。
阳阳父亲一直忙着在医院和慈善组织间的对接和筹款工作,他很少表达内心情感,却能体恤妻儿的苦痛。他分享了两个令他无法忘怀的亲情片段,其一是“上半年搬家的时候,老婆又看到了阳阳当时确诊的病历,瞬间就哭了”,看见妈妈流泪的阳阳虽不明就里,还用他的挑眉“特技”去逗妈妈,阳阳爸自责道:“我真想自己承受这一切啊,哪怕是生命”!其二是“前几天原本他自己安静地看电视,看到他觉得好看的画面,会时不时地发出‘哇哇’或者乐呵呵的笑声。我一时间没有理他,突然他叫了声‘爸爸’。因为有管路的阻碍,做了气切的孩子原本不能发声的,但是阳阳还是能喊出几句简单的话,‘爸爸’叫得最清晰!我问他怎么了?他连着喊了我好几句,原来是要跟我分享他最爱的动画片。我不要求孩子完美,也不要给我争脸,更不要给我养老,只要他这一声‘爸爸妈妈’就够了”。
案例2:小菲现已成年,小时候确诊为SMA-Ⅲ型,与Ⅰ型、Ⅱ型小病友相比,她的病症相对缓和许多,接受访谈时她作为自由撰稿人已开始独立生活。在她的印象中,母亲对自己的一切都很有自信,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女强人”,正因如此,属于“乐天派”的母亲并未因女儿的疾病而惊慌失措,“没有觉得天塌下来了,相反,她该笑还是笑,该打麻将还是打麻将”。
小菲妈曾说:“不管有再多的风雨,我和她爸都愿意给她挡着,这是真话。”为了照顾小菲,这位母亲不得不收敛起事业上的进取心。由于常年给女儿护理,小菲母亲的手臂和腰部都落下伤病,而这些部位对作为舞者的她来说至关重要,母亲从未有过怨言。小菲这样讲述自己和妈妈的故事:“妈妈28岁有的我。家人发现我不会爬,学走路时脚抬不高,直到有一次‘咚’地摔在地上,随后去北京检查出脊髓性肌萎缩,伴有运动神经缺陷。我妈妈是一个女强人,可以说我降生后,这个女强人第一次有了脆弱。”提到母女关系,她笑言“我们母女可能有些什么是相通的吧”,然后分享了一个埋藏已久的小故事:“有一年夏天的中午,妈妈在我身边的床上睡午觉,我就看着她睡,后来我悄悄用唇语叫了她一声‘妈妈’,就是嘴唇碰了两下,完全没有发出声音,上一秒还在打呼噜的她忽然就转个身醒了,当时觉得好神奇,不知是巧合还是真的心电感应”。
以上两个案例中,受访者关于“心电感应”“母女相通”与“母子连心”的讲述何其相似乃尔,对亲情认识的共通性特征如此明显以至于所谓“赋予病人力量的实质”已然表露。亲子间唇齿相依的情感表达颇具感染力,正如《史记》极言“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9],俗语所传“病在儿身,痛在母心”亦深入人心,血缘连接的舐犊之爱总能使生于个人体肤的苦痛超乎躯体限制达到至亲共情,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在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中,国人以家庭为人生的起点和发展的中心,亲情被视为中国文化之本[10],内在地规定了以家本位为基本逻辑的人际关系建设原则。家庭是由夫妻横轴上的婚姻关系和亲子纵轴上的血缘关系交织而成的亲属团体,该小团体成员即以夫妻轴及亲子轴为初始框架向外扩延从而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每逢团体外的弱关系面临坍缩之际,团体成员便回归两轴交汇的原点使核心家庭重拾凝聚力。正因如此,团体成员每当遭遇疾病重创而不得不将疾病作为生活圆心时,个体总能在家庭关怀中首先获得生命存在的价值,疾痛持续影响下的生活洞见又迫使他们总结出一套用以应对家庭之外更大社会关系的特殊法则。
以病人生活环境为中心编织的疾痛意义之网将疾痛经验与现实世界首尾衔接,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乃至朋友关系和照护与被照护等社会关系交错其间,故而对疾痛意义的解析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症状是“表征”,情境是“本题”,后者延伸并定义前者的含义,专业人员的任务在于帮助病人和他们周围的人,与他们一起面对疾痛现实,也就是接受、控制和改变出现在他们生活和治疗中的个人问题和意义[3]46-48。总结来说,架构在病症“表征”之上对于疾痛的感知和应对加强了个体与其他核心家庭成员间既存的密切关系,反过来,以情境为“本题”的团体努力要求核心家庭成员协同面对疾病现实,“表征”与“本题”共同构成疾痛的意义世界。
3 “难言之痛”:沉重的生命代价
家庭成员间相互持有的共情能力有助于凝聚家庭内部的精神力量,强化家庭抗逆力。一方面,至亲之情为疾痛意义的建构提供了内在情感支撑,充当了抱恙身躯与疾苦生活之间的高效粘合剂,并在特定场合下阻断或延缓疾痛意义世界生发畸变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参与疾痛意义建构的亲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补偿疾病所致的疾痛体验,仍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可以确信的是,苦难的本质远超个人经历的躯体苦痛[11],当病痛和苦难主导了罕见重疾病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家庭内部力量对于其社会苦难的消除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换言之,病患的身心体验内在地包含了社会性苦难,此为相伴疾病始终的生命过程,亦为病人及其家庭必须承受的生命代价。
作为学术概念的“生命代价”源出于“身心痛苦-医药费用”对抗的分析框架,被用于指代晚期癌症病人求生之本能与延续到生命终点的高昂医疗开销,两种苦难的交错对癌症病人生命质量造成的负面影响[12]。在此,本文将“生命代价”挪用至疾痛叙事的分析框架中,意在强调加诸病人躯体的多重压力及病人家属经受的多维磨难。确切地说,对生命代价的探求不仅需要关注疾病直接引发的身心问题、经济问题及伴生的因应之策,更需要对被医者专业滤光镜滤除的苦痛经验及其背后隐含的社会脱嵌问题和结构性压力提起关切。与意义世界的探讨相仿,导致以上症结的根源更多地需要从疾痛讲述中觅迹寻踪。
提到SMA病人生活之艰辛,自主照料Ⅰ型重症患儿的家长深有体会,生命的脆弱一面往往具有很强的震慑力。案例1中的父亲说:“当时产检也正常,阳阳出生时还好好的,现在就已经渐渐地退化到全身功能只有眼睛能动。需要24小时戴呼吸机,咳痰机、制氧机都是必备的,每天都要做雾化、拍背、排痰……我们真的是把房间改成了ICU,时时刻刻守护,一点都不敢放松。”自从做气切手术后,阳阳总是被痰折磨得睡不了觉,家长陪伴孩子饱尝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煎熬,阳阳妈谓此为“难言之痛”。她说:“我习惯了听呼吸阀的声音才安心,有异常就说明痰又上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很害怕听到咳痰机开启工作的声音,甚至会在厨房、客厅或者别的地方出现幻听,我怕孩子又出事。只有呼吸阀发出均匀的呼吸声的时候,我的心里才稍稍踏实一点。他半夜醒了要重新哄睡,翻身,还要时时刻刻检查上痰的情况。”阳阳父亲叹息:“‘活着’这个词,对我们来说真难……”
与重症SMA病人相比,属于Ⅱ、Ⅲ等临床分型的较轻症病人发病时间较晚,同一时期身体状况也明显优于前者,但其日常生活同样深受病痛影响。在外人眼中,案例2中的小菲是位活泼开朗的姑娘,谈起疾病的感受时却难掩内心伤感,她说:“我曾经问过小时候治病的事,妈妈开始还回答几句,后来就不说了。我追问她为什么不说了,她告诉我,妈妈心里是苦过的。”追忆往昔,小菲坦言小时候的自己过得并不快乐,她的解释令笔者动容。她说:“我想上学,他们告诉我‘你不能去学校’,因为我没有力气,学校不敢接收,父母也不放心。十几岁的时候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想追星,想去上海看演唱会,他们告诉我‘你最好不要出门,那不现实’,就算我家是电梯房,下楼转几个小时对我来说都像是在过节。我妈也教育我说要认命,劝我想开点,可是我不觉得。我生病,坐轮椅,每隔几个小时就要躺下来,我为上厕所的问题纠结半生,半夜必须摆好姿势睡觉,否则就会在呼吸困难中惊醒。我的‘没用’好像被看作理所当然,每次我的尝试都被说成是‘没事找事’。为什么?试都没试过,你怎么就知道你不能改变?从小到大,家人给我的教导是希望我能快乐,可是残障到这个份上,怀着破釜沉舟的心,这样我怎么能快乐?”
当未成年子女罹患重疾,患儿所处核心家庭将提供基础性的保障力量,但仍然不足以补偿沉重的生命代价。根据以上家庭的疾痛叙事可以对SMA病人及其家人所承受的生命代价做一不完全归纳,大致包含三个维度:身心代价、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
代价之一:疾病导致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疼痛。不同临床分型的SMA病人病症轻重缓急差异较大,该疾病的进行性特征表现为病人机能的逐步恶化,对病人生活的影响日益加重,最严重者恐将危及生命。一般认为以Ⅳ型为轻,病人于成年发病,无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症状,具备独立行走能力,对日常生活影响较小;而以Ⅰ型为重,病人被严重的呼吸衰竭所困,较早丧失坐立能力,调查统计甚至显示中国SMA-Ⅰ型病人的平均生存期仅有约11个月[13],这也是案例1中的医生对患儿的治疗持悲观态度的原因所在。生理症状是疾病的外在表现形式,被认为不言自明,而掩埋于表征之下的心理折磨却幻化为挥之不去的难言之隐。进入青春期的患儿确诊后心情消沉不愿与家长分忧,常令家长忧心不已。与“正常”同龄人相比之下的劣势处境使病人易于产生“相对剥夺感”,来自社会的否定则进一步加重心理负荷。生物过程的身体变化与构建在生理病痛上的心理感受辩证相对,形成个体疾痛经验的两个侧面,两种苦痛的内外交织使身心代价难以言说。
代价之二:高昂且持续的医疗支出。医疗支出包括购买辅具、药物、照护服务的花费以及在医院手术、住院的费用。辅具可能包括呼吸机、咳痰机、站立架、矫姿座椅等,但重症病人需承受的医疗费用显然要向药物和医院费用倾斜。遗憾的是,医学界尚无针对SMA的基因治疗方法,常规治疗是通过神经保护剂、神经营养因子、改善肌肉功能等方法延长运动神经元的生存时间[14]。目前,在我国临床应用较多的SMA精准靶向治疗药物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nusinersen),对2岁以下重症患儿的运动机能退化有延缓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病人生活质量[15]。不过,诸如此类的特效“孤儿药”售价之高昂对大多数患儿家庭而言遥不可及,此外医院护理及重症监护室的经济负担也常使普通家庭迅速陷入贫困并债台高筑,持续性的高额医疗支出无疑堪称灾难。事实上,这也是诸多罕见病家庭共同面临的难题。
代价之三:“正常”社会结构的难以嵌入。在病人角色的理论视角下,病人与社会结构之间脱嵌的权利与重嵌的义务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如果说,病人身份的获得意味着个体拥有在一定时期内脱离所属社会结构的正当权利,那么该权利的失效则取决于个体何时被剥夺病人身份。如此,在包括SMA等基因缺陷病在内的疾病语境下,被视为“非常态”的“病人身份”即为病人事实上的“常态”身份且仍被赋予重新嵌入社会结构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在此成为一对剑拔弩张的矛盾关系。例如,案例1中重症患儿的疾苦已然完全打乱家长的原有生活秩序和社会关系,疾病的打击令这个家庭手足无措。再如,案例2中的小菲即对“不能去学校”“不能追星”“不能去看外面的世界”等现实遭遇提出控诉,她重新融入原有社会结构的愿望在一次次的失败尝试中宣告破裂。个体虽然期望自身能够破除社会疏离感,以疾痛之身投入常态社会运转,但突破现实处境又谈何容易。
不同临床分型和疾病进程的SMA病人家庭面临不同层次的苦痛,其中尤以重症患儿家庭为甚,“失去”成为疾痛的最重大意义。由于欠缺彻底治愈的办法,已开发的精准靶向药物只能延缓疾病进程而做不到根治,且此类药物的可及性难获保障,重症病人的求生希望在罕见病医治的“病无所医”“医无所药”“药无所保”困局中濒临熄灭。现实中的社会脱嵌与重新嵌入社会结构的个人需求相矛盾,造成难以逾越的社会疏离。综上所述,心理和生理同时经历的苦痛折磨、难以负担的经济压力与社会疏离感错杂交织,三种代价的合力作用于病人及其家庭,生命代价何其沉重。
4 结语
社会事实被划分为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前者是“应该是什么就表现为什么的事实”,后者是“应该是什么却未表现为什么的事实”,人们超科学的理想观念显然青睐于前者的普遍性表达,由此从观念学角度区分出何为“常态”,何为“病态”[16]。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的集合构成完整的社会事实,该分类体系前置地规约了二者的互斥关系,更进一步地,先入为主的偏见造就了该集合内“常态”与“病态”的互逆事实。“病态”与烙有人类社会和文化属性的疾痛概念相伴而生,是病患群体及其相关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包含病患生物躯体和心理体验所表现的状态,独立于躯体但与病患相关联的任何态势也应是题中应有之义。疾病的“病态”属性为病患开具免于承担“正常”社会角色的临时通行证明,与此同时,“常态”与“病态”的二元划分却又错误地在病患群体重新嵌入“正常”社会结构的尝试路途上设下重重阻碍。如此,病人角色理论在慢性病和遗传病等疾病的语境中暴露弊端的同时,揭露出生命代价何其沉重的残酷真相。
处在个体与社会交互中心的躯体承载着个体疾痛经验,饱尝社会性苦难。疾病既是一种生物、医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疾痛意义的建构和对疾痛的因应之策暗含其所处生活环境的社会文化特征[17],亦即疾病的文化范畴和个人意义与“异常”生物过程的残酷实质联合构成疾痛的意义世界。病人机体健康遭受进行性疾病的逐步蚕食,在躯体上和心理上留下巨大苦楚,疾痛不仅剥夺病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还对其家庭的日常生活格局造成紊乱,沉重的生命代价在多方面造成灾难性打击。家本位的思考逻辑是用以应对家庭之外更大社会关系的集体法则,罹患重疾的患儿牵动家庭,血浓于水的亲情参与疾痛意义的建构,也是病人重构自我、回归社会的精神支柱。被建构的疾痛意义虽能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慰藉,其所包含的生命代价却升为相伴疾病始终的社会性苦难,二者实难自洽,表明病人身份赋予的权利与义务之间存在张力,生命难承之重亟待释压。随着病情的发展,特别是病人在较轻症情况下,疾痛叙事的问题焦点从病房转移至家庭、社区乃至周围其他人员关系[18],彰显病人对“常态”社会生活的渴求。疾病困扰给病患生活投下阴面,共情能力和治疗的人性化则帮助病人及其家庭“向阳而生”。疾痛虽苦,情至深处,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