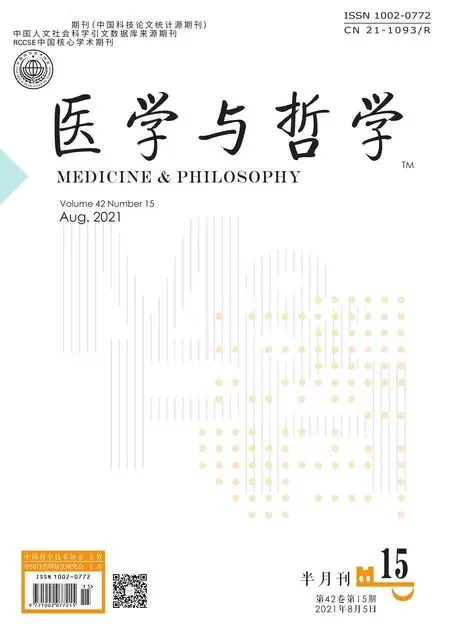新冠疫情下海外华人中医接受度调查*——以英国牛津地区为例
彭卫华 张 苗
2020年初,全球开始暴发新冠疫情。本文对这场偶然事件的关注,更具社会学视角,即给予在既定的理性社会结构中讨论“事件”原生、次生带来的诸多特殊现象的特殊分析,并试图在社会中还原“事件”暴露的社会文化现象。新冠疫情是一个世界公共性的突发事件。中医,既是一种民族文化符号,又是一种医学临床技术。在突发的新冠疫情面前,现代医疗的应对放大了其“科学研究”滞后性的弊端,而将中医作为一种实用的临床技术推向了身患紧急性疾病的患者,这是在“中医”产生的本土地域所发生的状况。但在“中医”文化的异乡、地域异乡的人群中,中医在新冠疫情中被大家接受的样态是怎样的呢?这种样态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的因果链是什么?这些文化和社会的因果链又能引起哪些“事件”性的思考,是本文尝试做出的理性努力。
1 研究缘起
以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新冠疫情于2020年年初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在疫情暴发前,本研究对于牛津地区中医的整体状况进行了初步实地调研的田野调查。在疫情暴发后,本研究采用线上方式在牛津地区华人中开展了对于中医看法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
1.1 英国疫情概况
2020年3月,新冠病毒在英国国内的传播风雨如磐。3月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首次承认,英国可能会有数以千计的人感染新冠肺炎,而同日另一媒体也报导,有卫生专家认为“目前疫情尚未在英国本土自由传播”,而在受访的1 600名医护人员中,只有8人认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为应对疫情做好了准备。直到3月5日,英国当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例,英国政府首脑科学顾问承认,新冠肺炎已经开始在英国暴发。时隔7天,即3月12日,政府官员承认英国国内可能已经有多达一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然而此时,英国政府并没有公布会采取关闭学校、取消大型活动等措施的计划。但这一切在太阳升起的第二天,就完全改变了,这一天英国遭遇了单日增加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人数为208例,是疫情暴发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天。首相约翰逊3月13日马上宣布从下周开始取消所有体育赛事、音乐会及其他大型活动。事实上,他在前一天还坚称不会效仿苏格兰地区禁止500人以上集会的做法。新冠疫情在英国瞬息万变情况,引起了许多在英华人的恐慌。不论是对疾病忧患意识的文化传统,还是之前对国内疫情新闻的重视和关注,都让此时此刻在英的华人为疫情暴发后的去留感到焦虑。
1.2 牛津地区华人及中医概况
牛津,地理上是英国英格兰地区版块之一。牛津享誉世界的标志即是牛津大学,所以牛津地区的华人很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既有在牛津进行留学深造的人群,也有为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而在牛津进行中小学留学的人群,当然也存在源于其他原因来到英国的人群,如医护工作从业人员等。
牛津地区有能获得中医治疗服务的渠道和平台。以是否直接获利为标准,平台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商业模式平台,另一种是科普模式平台。在商业模式平台中,又分为两种:商业街门店模式和社区服务模式。在牛津,提供自然疗法保健服务的商业不少,中医服务仅是其中的一种,其他的还有瑜伽馆、泰式按摩馆。牛津地区商业模式中最容易被发现的一家中医服务门店设立在最繁华的商业街。该门店主要以针灸、按摩治疗为主,兼营中药。顾客群体兼具流动性和固定性。除此之外,还有设立在社区的中医服务。通过科普模式进行传播的中医,以在华人社区中心开设讲座、免费诊疗咨询等为主要形式。宣讲者一般为中医从业者,他们一方面宣传中医药保健知识,另一方面建立客户群体。华人社区中富含中国式的“熟人社会”特色,内在蕴含中国传统组织结构特点。故而,中医的医术优良与否并不是宣讲人的重要素质因素。这一点,在新冠疫情暴发中被凸显出来。
除了中医提供服务的平台和中医的从业人员之外,接受中医的患者人群样态也有其特点。英国是高福利国家,NHS为所有具有合法身份留居英国的人员提供全员免费医疗服务。正因为如此,NHS服务覆盖面广,但却囿于医疗条件,医疗服务的深度也有限。中医在英国属于自费项目,不进入NHS 的服务体系。在英国接受中医提供治疗服务的人群根据其文化背景,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文化的同乡人,另一类则为文化的异乡人[1]。所谓的文化同乡人,是指具有中国文化或者中医文化渊源的人,如华裔、具有华裔血统的,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群。而文化异乡人则是指与中国文化或者中医文化没有历史牵连的人群。无疑,第一类人群的中医接受度是比较高的。放置在英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第二类人群的中医接受度也并不比第一类人群低。主要原因在于英国社会文化中弥漫着对“科学化”“医疗化”的抵制。所以这些接受中医的文化异乡人,更多地是出于自己文化中的“理性”背景而找到中医的。这种状况的另一个例证来自于英国与中医相关的书籍市场。
2 疫情暴发初期中医在牛津的接受度问卷调查情况
2020年4月~6月,笔者在牛津华人微信群开展了问卷调查。值得说明的是,微信群在牛津地区华人中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尤其在疫情期间,可以说微信使用渗透到牛津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2.1 问卷调查对象
疫情期间,该问卷在微信群的华人中展开,共发放调查问卷110份,回收有效问卷106份。其中男性为57人,占53.77%;女性为49人,占46.23%。其在英居住时间分布为,1年以内的占57.55%,1年~5年的占21.70%,5年~10年的占8.49%,10年以上的占12.26%。调查对象的留英原因组成则为,被迫滞留的占2.83%,移民的占5.66%,工作的占40.57%,求学的占17.92%,访学人员26.42%,其他原因占6.60%。
2.2 选择中医意愿
调查对象每年看病的频率分布情况为,一年5次以下者为86.79%,5次~10次者为11.33%,10次以上者为1.88%。而在英国就诊选择中医的频率为,从未看过中医的为45.28%,偶尔(1次~2次)的为42.46%,有时(5次以内)的为6.60%,经常(5次以上)的为5.66%。而在英国是否自己使用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中成药的比例则为48.11%与51.89%。
2.3 对中医的看法
调查对象对中医的看法的分布情况如下,疫情前对中医的印象认为有自己的优势的占61.32%,认为不科学的占32.08%,认为有效的占6.60%。而对中医药对新冠疗效的看法分布是,相信中医药有效的占59.44%,不相信中医药有效的占31.13%,认为说不清的占9.43%。在疫情后对中医的印象却与疫情前有了明显的不同,疫情后认为中医有自己优势的占81.13%,认为中医不科学的占7.55%,认为中医有效的占11.32%。疫情后会更多地选择中医药治疗的分布情况为,选择中医的占26.42%,不选择中医的占35.84%,看情况而定的占37.74%。这其中,一年看病5次以下的人群,不选择中医的占7.60%,选择中医的占58.70%,而看情况决定的占33.70%;一年中就医5次~10次的选择中医的比例是8.33%;不选择中医的比例是16.67%;看情况决定的是75.00%。
因为移民原因在英国的人群相信中医对新冠肺炎的作用有效的占比为100.00%。因为工作原因在英国的人群中对中医对新冠肺炎的作用的占比情况为,相信中医有效的占34.88%,不相信中医有效的占60.47%,认为说不清的占4.65%。因为求学原因在英国的人群,认为中医有效的占52.63%,不相信中医有效的占21.05%,认为说不清的占26.32%。
其中移民身份的在英华人对中医的信任度最高,其次为访学人员。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求学的年轻人群体对中医的接受及信任度较低。
3 思考与讨论:“礼物”——新冠疫情下的中医
从对新冠肺炎治疗的本身来讲,中国传统中医药的方法在国内的实践无疑是中医对于新冠肺炎有效的铁证。新冠疫情中中医药的事实性有效,无疑让我们国人看到了中医药“礼物”般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礼物的传递,必须考虑其实际过程和实际在场。如果礼物的传递仅仅是一种一厢情愿,那么礼物本身不仅难以成为中国式的“礼”之物以传达善意,甚至会被溢出解读为西方莫斯[2]3式的“礼物”,而更传递“交换”“互惠”意味的信息。
3.1 “礼物”的受众
在文化异乡中更多地被标签化为“文化性”和“民族性”的非主流之医药方法,其实际效用的开展却是有着诸多不同层面的屏障。撇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中各国的文化隔阂不论,尽管这一层次中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背景是中医药进行海外传播非常重要的网格背景,民间大众对于“文化异乡”的中医药观念、方法、思维接受度的实际层面是值得细致探究的。
如前所述,中医海外接受主要有两类人群。从上述调查问卷来看,文化同乡对于中医药的接受度并不是一种确然的无间隙性传递。由这些数据可以勾勒出在英华人人群对中医看法的几个维度:首先,中医作为一种具有标识性的民族符号的非主流医学,在“文化同乡”人群中的传递并不是以其医学理性知识而更被认可。调查显示,中医理论并不是他们获得中医理性知识的主要渠道,中医理性知识也不是国外华人所重点关注的。其次,更多的中医药实际运用在“文化同乡”中是作为一种“习俗”而被使用。此次调查展示了一个事实:“习俗”是中医药在华人间传播的非常重要的标签,而非一种非常正式的医疗活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劳斯(Rouse)[3]曾指出,在移民的话语中,迁徙的人群的经历只能被想象成为两种可能的方式:循环的和线性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保持自己旧的认同,铭记自己的家乡,并最终返回那里。在第二种状况下,人们抛弃了曾经的家乡和认同,在接纳自己的社会中定居并最终为其所同化。由此可见,一方面中医接受的“文化同乡”,必然是地理上“离乡”状态的人群,他们一方面通过作为民俗和生活习惯的中医延续着血统中的文化情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接受身体实际地理“在场”的行为同步化,以此来获得实际在场环境的归属和认同。在新冠疫情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中,地理在场的英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应急能力和实际提供的社会福利,凸显出了地理在场的劣势。而实际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诸如“质疑华人戴口罩”“华人街头被歧视”这样的新闻和亲身经历不绝于耳。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将日常生活中一直使用的中医药“习俗”放大为确然的治疗选择。调查显示,疫情后会更多地选择中医药治疗的占26.42%,不会的占35.84%,看情况而定的占37.74%。不选择中医的和看情况而定的占73.58%。
而在接受中医的“文化异乡”人中的状况,却是另一种呈现。笔者在与一位曾经来中国学习过中国文化的当地人访谈,在访谈时他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咳嗽、发热、嗓子痛等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在几次沟通中,笔者都曾经特意通过讲述有效病例、中医治疗的机理等方法向他推广中医治疗(中药)对于新冠肺炎的有效性,但是他依然拒绝接受的中医治疗方法(服用某中成药胶囊)。此外,还有一位已经与当地人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华人女性与笔者联系,她的丈夫和家人由于是英国某医院的救护车司机,所以她意欲获得一些中医药相关知识和药物帮助她的丈夫及其家人提高免疫。在谈话中,该华人女性谈到她的丈夫及其亲戚都“不相信”中医方法,尽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帮助其进行刮痧、按摩等养生保健,但是却不能接受服用中药来预防新冠肺炎。在几次沟通后,笔者建议其用水煮蒲公英的方法提高身体免疫能力,这种方法也被其本地人家属所接受。
以上两个个案可以看出,“中医”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即使是有过中国文化熏陶的“文化异乡人”中,依然存在接受屏障。故而,中医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疗手段而难以被接受,主要源自根深蒂固的“文化”屏障。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政府近年来在国民教育中所推崇的核心价值观也许应当作为一种背景知识进入我们的观察视野。英国政府自2011年开始将本国的核心价值观定为“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和互相尊重信仰差异”[4]。其对核心价值观的推崇,源自英国国内多元文化信仰带来的社会问题[5]。具有一定的文化传统和近代辉煌历史的英国,正是运用核心价值观教育来更好地让外来种族、外来文化背景公民融入本地文化传统。这从一个侧面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英国本土文化主体性和领导权的现实状况,即英国现状包含有多元的民族、信仰的合法居民,但是英国政府也明确在教育中强化英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主体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药作为一种特殊民族所沿袭的文化性、传统性其生存空间是有限的。无论是“文化同乡人”还是“文化异乡人”,被当地社会建构的价值理念都对中医药文化的接受和传播有离散性影响。
3.2 “礼物”受众的“传统”与“文化”
新冠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它挑战着已经自觉进入高度文明状态的人类社会,也同样对当代人类医疗技术、公共卫生健康管理是一个意外打击。然而,这场疫情的暴发也集中放大了在应对公共灾难的过程中,国家、地区间文化沟通的有限性。面对相同的公共灾难,差异性地、特色性地处理灾难成为国际化政治环境中标榜文化主体的一种有意或者无意的预设。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分歧也得到了凸显。中医作为文化内部被明显确认的特色治疗如何能够获得“礼物”的正当性而得以传播?在英国,中医作为礼物被送出,朝向的是怎样的一种受众,其传统和文化背景又是怎样的?
作为一个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英国当地民众对于本地文化传统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以牛津为例,在牛津“传统”是一个随处可见、频繁出现的单词。牛津大学的各个角落,都闪耀着历史的光芒。无论是古代历史中知名的宗教与强权斗争,还是近代历史中著名的科学与宗教斗争,抑或是某个耳熟能详的科学名词或者标榜史册的英国科学、政治等历史人物,都能在牛津循迹到渊源。牛津大学和牛津城,将这些传统都予以了强化和保留。 其次,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对于现代文明和发展,保持着相当的警惕。牛津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古老的建筑,除教堂的钟楼之外,市中心基本没有超过5层楼的楼房。牛津市的很多马路,也同时保持着水泥马路和泥土马路,因为人行道坚持不用平铺的水泥,因而人行道中常常听到非常刺耳的行李箱拖行的声音。夜间的街道,也没有灯火通明的路灯工程,路灯仅仅只是有限地照亮黑夜。市中心有集中的大规模商业区,其他地方更多见的是咖啡馆、餐馆或者小型超市,散在的商业区数量和规模都非常有限。
3.3 “礼”与“礼物”
中医作为一种被医疗事实证明了可以发挥作用的医疗行为,在此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中,能否成为一个正当的礼物?“礼”,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礼’既是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 也是历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 并作为历代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伦理观念和政治思想”[6]。可见,在中国文化概念中,礼物是承载着相互尊敬和相互友爱的高尚人际交往规范的实在之物。然而,值得关注的却是“礼物”的西方思维。现代人类学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曾经在他的经典著作《礼物:古代社会中的交换形式与理由》的引言中写道:“在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和其他为数甚多的文明之中,交换与契约总书以礼物的形式达成,表面上这是自愿的,但实质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同时莫斯在该书著的结尾从现代社会出发对原始社会形态下的“礼物”三个层面做了总结。这三个层面是道德、经济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社会学。在道德上而言,莫斯[2]147肯定了现代社会中“物”的“情感性”,他认为馈赠与回馈一方面或多或少地包含着荣誉、面子等情感,例如,在“回报总是要更昂贵更大方”,在“遇有客人、节宴或是要给年赏时”,人们就会“挥金如土”;另一方面,莫斯还肯定了社会生活中,礼物交往对于个人和人群所带来的“愉悦”和“欢欣”,正是因为如此社会中不同的人群才能“总体呈现制度”,人类社会的紧密联系才在“要走出自我,要给予”这一亘古不变的原则中得以继续。而在经济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个面向上,莫斯考察了“馈赠”“礼物”以及“利益”等观念的多重含义。莫斯认为前二者之观念“既不是纯粹资源和完全白送的呈现,也不是指生产或单纯意在功利的交换”,而是在社会中盛行的“杂糅的观念”。他也认为“利益”具有多重性,并揭示出了利益观念背后个体与集体的离散性。而莫斯也相信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他所处的现代社会,“经济理性主义”都还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价值观念,大众中的“社会共同利益”具有驱动的力量。最后,在一般社会学的结论与道德的结论中,莫斯提出“社会总体事实”的原则。从西方社会学对“礼物”的社会形塑和社会功能价值的考察中,不难看出“礼物”交换的“社会”性是礼物得以成为“礼物”的重要背景。
中国文化中的“礼”也有其背后的关系形态,但这种关系形态中的“道德”成分与以莫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所揭示的“礼物”的场域性道德不尽相同。从本次中医在海外接受度的观察来看,一方面中医作为“礼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传播的障碍,或许恰恰在于“文化”流动中的各种社会实际条件的不能;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集体联结中“共同性”也预设了中医传播必然性的出口。如何将具有现实价值的“中医”作为礼物更有效地推送至世界,是当代学者的历史任务。从文化交往理论来看,文化涵化、文化同化或者文化异化,都包含实际场域的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哲学或者文化学的问题。例如,新冠疫情作为一个突出性的公共事件暴露了全球政治生态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意识形态偏见,中医如何体现“礼物”的价值,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礼物”的正当性。中医要进行“异文化”向度的传播和交流,就必然需要展开对“异文化”条件和背景的各个维度的调查和研究,尤其是作为接受方的文化条件和背景的讨论。值得当下的中医药传播研究者关注的是,“礼”不是一场一厢情愿的给予策略,却是一种以尊重为前提的真诚与郑重;礼物的质性不仅体现在“物”的价值性,还应体现在以“命运共同体”为前提的相互与交往。而从新冠疫情暴发来看,海外“文化异乡”情景中既有有利于中医药得以开展的对现代医学的态度、对自然疗法的观念等文化场域,也有对于民族主体的明确、对异文化认同的障碍等现实不利条件,更有整个现代社会中“同质性”的人的生存境遇的现实状况。如何充分将中医药的价值性和在场的现实条件相结合,恐怕是当代中医海外传播以及中医的当代文化自觉[7]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4 结语
以目前的中医药海外传播研究来看,业内对中医药海外传播的研究中大多将“文化”与中医药的海外传播相关联。“中医药文化理论的传播是中医药文化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8]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中的实际情景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是一个偶然“事件”,正是这种偶然“事件”激发了平常状态中被隐匿的真实,偶然事件将中医“抛入”全球化国际关系真实面貌中。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跨文化交流中不仅有文化传播,还可能带来文化涵化、文化同化和文化异化等问题。以英国为例,“传统”和“文化”是当下其自身自觉进行建构和标榜的主题,如何在这样的氛围中,将同样具有“传统”属性的中医作为“共同”性意涵下的“礼物”呈现,是当下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意识。换言之,当下中医药海外传播的研究,除了要在中医主体性话语建构的基础上探究中医的礼物价值性之外,还需要从“文化异乡”的人群的生活状态、生存状态、价值观念趋向中挖掘当代中医药的现实价值,并延展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