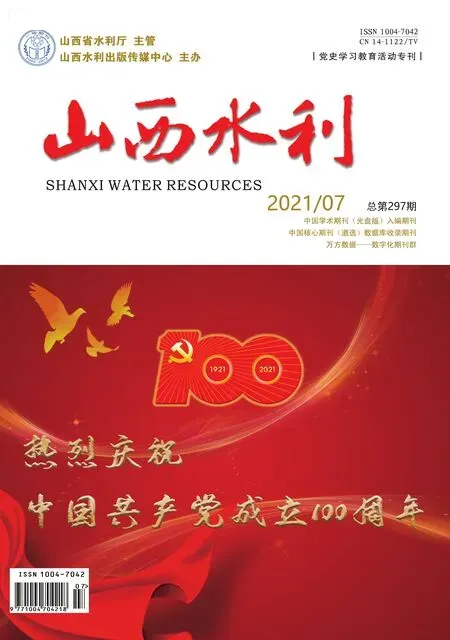一条扁担忆水情
邸青春
(山西省水利厅科技与外事处)

今年春节回老家,和妈妈一起过年。大年三十,到老院子贴对联,无意间看见一条扁担,静静倚在墙角,旁边还扣着两只生锈的铁桶,在冬日的暖阳下沉默着。像失散多年的老友,不经意间撞见,熟悉而又陌生,一股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眼角不觉泛起泪花。我一遍遍抚摸着扁担和桶,就像在与久别重逢的老友握手。这两只桶是当年当钳工的爸爸亲手打造的,扁担是三舅送的。那年,十二三岁的我从妈妈手里接过这条扁担,扛在少年稚嫩单薄的肩上,让我初步体验了什么叫担子。
年假短暂,年过七旬的老妈和往常一样,尽管腿脚不便,但还是忙忙碌碌不知停歇,变着花样做各种传统美食,生怕我们吃不饱。只是吃穿用度她还是很俭省,尤其是在用水上。尽管家里新盖了楼房,通了自来水,还有一口备用水井,但她仍然保持着“抠门”的用水习惯。洗脸水舍不得倒,留下用来洗手,洗完手再用来涮墩布、浇花、冲院子,不肯让一滴水浪费掉。卫生间有冲水马桶,但她从来不用,说太浪费水,怕水把化粪池过早灌满,还得花钱请人抽。我劝妈妈说:“现在条件好了,咱又不缺水,何必还像过去那样抠抠索索?”妈妈说:“看你这孩子说的,想想你们小时候,姥姥家那么缺水,你三舅挑水那个难。就冲着当初那份辛苦,也不能浪费,人不能忘本啊!”妈妈的一席话,令我一时无言以对,顿时一张大红脸。
看过电影《老井》的人,对黄土高原老井村因缺水引发的悲情故事一定记忆深刻,我童年时就住在类似老井的村里。
这个叫郭家庄的村子,地处岚县和娄烦县交界处。村子前面一条巨大而干涸的河川由西向东横亘。两面是荒僻的山丘和梯田,有山却不长草木,有河却没有流水。村里只有两眼几近干涸的井,平常年份勉强能供村里上千口人吃水,如果遇到严重干旱的年景,村里老百姓的生活用水就成了大问题。
人们每天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挑水,一条扁担挑着水桶,一手拎着井绳,一手还要牵上六七岁的小孩。也许你要问,大人挑水,带小孩干啥?挑水的大人到了井口边要把水桶放下,跟在早已排成的长龙后面排队等候。等轮到后,大人先用井绳把小孩吊到井底,小孩光着小脚丫小心翼翼地踩在井底冰冷的石头上,吃力地用瓢舀水倒进桶里,一会儿等水渗出来再舀。直到把水桶舀满,大人先吊水桶,再把孩子吊上来。在如此胆战心惊的打水过程中,大人无奈、小孩惊恐。这令人绝望的挑水经历,对人的耐心、体力、精力甚至人性都是一种考验。在焦躁不安中,老老实实地排队,可一个打盹的功夫,桶就有可能被别人踢到后面。这时,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和伶牙俐齿的姑娘们往往会荷尔蒙爆棚,争吵、打闹迅速引爆。一时之间鸡飞狗跳,水桶乱滚,场面劲爆。这个村里有袁姓、杨姓、范姓等几个家族,我们邸姓在村里只有本家的两户,属于小姓。男丁少、女孩子多,所以被人挤兑是常事。多年以后,我和三爷爷家的四姑聊起当年往事,她慨叹道:“唉!我妈在时经常说我脾气不好,年轻那会儿就喜欢和人们争吵打架。其实,哪呀?当初在郭家庄村每天排队挑水,经常有人把自己挤到后面!如果不打闹,一家人连饭也吃不上,回去还要挨大人一顿骂。”
当时,爸爸在太原上班,老家还有六十多岁的爷爷,妈妈带着姐姐、我和妹妹生活。七十年代末,文革刚结束,还没有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人们生活都很困难。妈妈白天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却只能领一个人的工分和口粮。其实,最缺的不只是粮食,还有水。二十岁出头的妈妈一个人挑水很吃力。姥姥、姥爷心疼女儿,每到星期天,就打发三舅步行七八里路来给妈妈挑水。三舅十三四岁,正上初中,但他从小力气大,早就作为主力给家里挑水了。三舅为人敦厚老实,在劳动干活方面从不惜力。
郭家庄缺水,附近的杨家岩村更缺水。这个村海拔高出南侧姥姥家赤土华村约四五百米。全村里只有一眼辘轳井,据说有十五丈深,井绳也有三四十斤重,我一个初中同学就住这个村。有一次他妈妈在辘轳井打水,瘦弱的女子一下撑不住,不慎滑脱手被辘轳井的摇把打落井中,酿成了惨剧。我初中时走亲戚,曾陪同学去挑水,亲自体验过这眼井的深不可测和用辘轳井打水的艰难。
姥姥她们村也好不到哪去。姥姥家住在村北侧半山腰下的东沟子,这是搬的第四个家,座落在半山腰中的两孔窑洞,这儿离最近的井大约有1公里。三舅一个人承担着三家人的挑水任务,姥姥家、大舅家和他丈母娘家。三家人四口缸每挑一次16担水,大约需要四五个小时。遇到旱季,村里的井水少供不上,三舅和村里的人们只能到四五里外的粮站深层井去挑水。
新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聂绀弩有一首名叫《挑水》的诗:
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
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
汲前古镜人留影,行后征鸿爪印泥。
任重途修坡又陡,鹧鸪偏向井边啼。
这首诗,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人们挑水的艰难场景,虽富有诗意,但也折射出人生的不易和生活的艰辛。
小时候,我常跟在三舅后面陪着去挑水。三舅晃晃悠悠、不紧不慢地挑着水、爬着坡,有时嘴里还哼着小曲或打着口哨,苦中作乐,从没见他因为每天挑水的辛苦而发愁过。
我有三个舅舅,大舅曾在北京当兵,二舅去晋城当工人,只有三舅留在村里陪在姥姥身边,没出过远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三舅难道不想出去吗?我曾劝三舅到大城市打工,肯定比在家挣钱多。他憨厚地一笑,缓缓地说:“几大家子,咋走嘛,吃水就是个大问题!”。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在农村有着“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因为三舅是家里的老三,不舍得让儿子们都离开,留个小儿子在身边。一条扁担,注定三舅此生故土难离。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么缺水呢?当地严重缺水状况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自然和人为因素。据说,娄烦在古代曾森林茂密,水草丰茂,做过皇家的牧场。但后来由于人们靠山吃山,长期过度砍伐和放牧,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河流断流成为季节性河流,只有夏季洪水暴涨时有水,平时就是大大小小鹅卵石裸露的干河滩。加之附近煤、铁矿多、石头山多,各种矿藏的严重无序开采,造成了大量地下漏斗、采空区,地下水下渗,附近村落缺水自然就成为常态。
吃水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爸爸在太原上班,也没有办法把一家老小带过去。爷爷去世后,到了八十年代初,爸爸和三爷爷商量,我们又迁回离郭家庄三十里外的兰家舍村。兰家舍其实是我的老家,这个村邸姓是大姓,虽叫兰家舍却没有一户姓兰。在我老爷爷辈因为穷困搬到郭家庄村,三代以后因为水的问题又迁回故土。兰家舍是个有将近两千人的大村子,地处平原,有三四眼水井,这里含水层很浅,一般打井两三丈深就出水了,因此也不缺水。我在县城上初中后,半大小伙儿已经长到一米七多。每周日放学回来,总要抢过扁担帮妈妈挑水。离家最近的井没有辘轳,需自备井绳来扯水。每次去挑水,妈妈都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小心。圆圆的井口有锅盖大小,从井口朝下看,能看见人的倒影,水位很高,再也不用把小孩吊下去舀水了。
用井绳扯水是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儿。把井绳上的铁钩挂在水桶的提手系上扣好,一节节顺到井底,感觉桶底触到水面,右手左右抖一下,水桶倾倒缓缓下沉,就意味着桶满了。然后两腿半蹲着,双手较劲,交替倒手,把水桶拉到井边,摘开挂钩,水桶就稳稳地放到井边了。扯水时手、眼、胳膊、腿和感觉必须协调一致才能不出差错。那时感觉看扯水像在看表演,干惯农活的后生身强力壮,扯水时动作熟练,节奏感很强,虎虎生风,如行云流水一般,让半大的小子们看得眼睛发直,都跃跃欲试,相互比拼。时间久了,自己也学会了扯水,尽管不是很熟练。当然,有时也会出意外,不小心会把桶掉到井里。此时,后面的大人们就会边玩笑,边找来铁耙,用井绳拴好,伸到井底试探,等感觉有东西挂到耙子的钉齿上,稳稳上提,桶就会被打捞上来。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村里先富起来的部分村民自己花钱打了压水井,大家就去有压井的人家挑水。压井需要倒半桶水进到筒子里引水,用压杆上下压,清澈的井水就会从斜伸的水管欢畅地流淌出来。比起辘轳井、用手扯水,压井更为方便,最大的好处是安全有保障,水也清澈见底。但老去邻居家挑水,有时不小心会把井口附近弄得泥泞不堪,邻居的脸色自然就不好看了,但碍于情面又不好说什么。大家都操着小心,尽量避免给人家添麻烦,硬着头皮继续去挑水。那时自己心里想,什么时候也有自己的井就好了。
九十年代初,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离开了家,就再很少有给家里挑水的机会,挑水的扁担又落回到妈妈的肩头。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军校毕业半年,我成了少尉排长,肩上挂上金灿灿的肩章,领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资,半年补发了四千多元。探家时,我拿出一笔钱给了妈妈。愧疚地说:“妈,我这以后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给您挑水,留点钱给家里打口井,您不用再挑水了,就当儿尽孝了。”那年,妈妈和爸爸如愿以偿花钱请人打井,买了水泵,一拉闸就可以把水接到水缸里。比起以前跋山涉水去挑水,简直就是革命性的变化,全家人像过年一样充满喜悦。
进入新时代,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在农村实施脱贫攻坚,把民生水利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兴修水库,建设大型引水工程,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多数农村终于实现了自来水进村入户。现在,只要打开水龙头,清澈的甘泉就会哗哗地喷涌而出,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农家院子里都种上了菜,夏天院子里蔬菜绿油油一片,各色的菜花姹紫嫣红,招蜂引蝶,生机盎然。闲不住的妈妈在自家小院里,也种满了黄瓜、豆角、西红柿、辣椒、葱、香菜、南瓜等各种菜。溽热的苦夏,也能够喷水浇灌或降温。院子角落里还栽了一棵樱桃树,紫红色的樱桃成熟,像一颗颗玛瑙,香艳欲滴,非常可口。院里各种蔬菜瓜果,妈妈自己吃不完,就送给街坊邻居分享,同时也会收到邻居的馈赠。兄弟姊妹们每次回家,车里自然满载而归。从以往瓜菜半年粮,一年到头少吃没穿,缺水少电,到现在衣食无忧,水电气暖齐全,天天像过年,此情此景恍如隔梦。
一条扁担,成为人们故土难迁的羁绊,也承载了一代人太多的记忆和梦想,见证了大时代的巨变。
如今,那条曾经支撑一家人生存责任的扁担已光荣下岗,安详地立在老宅的角落里,默默度过逝水流年。
不禁感叹: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之所以能从这方水土走出,去追寻诗和远方,是因为有很多人在背后替你挑起那根扁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