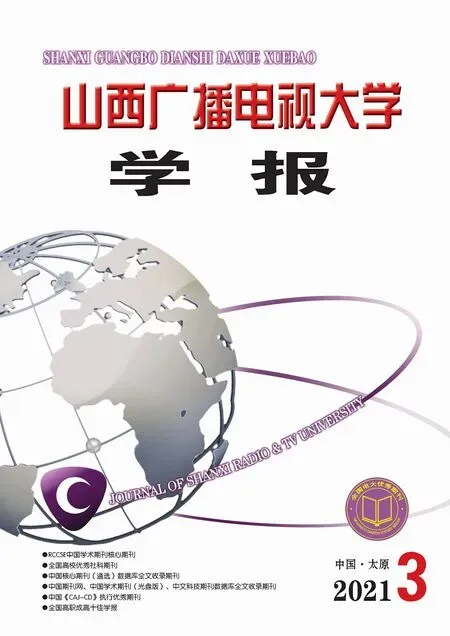从边堡事件看明中期以后边防政策的变迁
——以土木堡之变等三个边堡事件为例
段培西 杨荣星
(1.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0;2.山西开放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7)
明朝建立之后,元朝余部退往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带,后分化为鞑靼和瓦剌两部,对明朝北部边防依旧是严重的威胁。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曾多次发兵北伐,一度削弱了鞑靼和瓦剌的势力。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多以畜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以骑射为主要生存作战技能,逐水草而居,所以“虏众易合而势常强,我兵难聚并而势常弱”[1]42,他们“侵暴边境,出没无常,大举深入,动至数万”[1]41。这就使明廷一直在“战”还是“和”的问题上纠结。
明中期之后,军力衰弱,用武力应对鞑靼和瓦剌的威胁自然就更加艰难。加之皇帝“怠政”、倚重宦官,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宦官代行皇权、滥权,加重了皇帝怠政的负面影响,导致了两场危及明朝存亡的败仗。河北怀来城外的土木堡、北京密云的古北口见证了这两次战争,也见证了明中期以后边防政策的变迁。
一、“土木堡之变”及事变后的消极固守应付政策
“土木堡之变”的发生,标志着正统年间(1435-1449)埋下的边防隐患全方位暴露了出来。此次大败仗在这个时候发生,看似偶然,其实有其必然性。
(一)“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坐落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是一处重要的军事要塞。它曾经被叫作“统漠镇”,据说是隋末高开道所建立。《扣舷录》上记载,传说辽朝君主曾于此地驻扎,驻扎期间曾树立大型幕帐于此,所以又称作“统幕”,后来逐渐音讹为“土幕”,再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土木”这个名字。[2]到元朝时,原有的城堡已不复存在,有一条御道从元大都(今北京)出发,通往其草原故都开平,这里遂设立驿站和驿城。明朝初年,原有的驿站和驿城建制依旧保留。永乐初设置城堡,与榆林堡、鸡鸣驿共同拱卫首都京师。该堡周长1000余米,高约11.67米,在东、西、南三面设立城门,同时设有瓮城1座,城外有护城河,深2.3米,宽6米许。驻守此处的最高军事官员是操守,领辖官军114名,守墩军约300名。[3]325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首领也先带兵犯边,明英宗朱祁镇在冲动之下贸然率大军出征,被困在土木堡,由于后勤准备极不充分,水源被掐断,致使明军陷于危险境地。也先佯装讲和,趁明军不备,发起突然袭击,明英宗朱祁镇成为也先的阶下囚,众多文臣武将战死,明军折损过半,历史上称之为“土木堡之变”。
(二)明军失败的政策原因
当时宣府和大同都是明朝的军事重镇,距离都城的距离并不遥远,且附近还有京营重兵,然而战争开始就不断损兵折将外加丧失领地。具体原因包括以下两方面:
首先,“不花钱养兵”的军户制和卫所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北方边防废弛。军户制和卫所制是明代的基本军事制度,随着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的战事和政权建设基本完成,军户与卫所的分布逐渐扩散至全国,卫所制度亦在实操中逐渐完善。其基本形式为,约5600人编为一卫,1120人编为一所,在固定的驻地一边屯田,一边承担防务。管理层级自下而上有千户所、卫、都司、五军都督府。自给自足是军户制和卫所制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其主要目的,但在操作层面容易出现士兵及其家属忙于耕织、士兵无暇训练的状况。随着时间推移,“各卫所的兵额中只有五分之一能执勤从事军务”[4],军情紧急时各卫所临时调动兵员充数,在兵员素质缺乏保证的前提下,部队整体战斗力薄弱。本次事件中,明军从大同班师东返途中,在前哨战役时就已经折损大量兵力,余下部队于土木堡彻底战败。相较于瓦剌军,双方战斗力立见高下。
其次,明方统帅体制混乱,决策与军令一错再错。明英宗朱祁镇率军出发前,吏部尚书王直曾率群臣上书劝谏皇帝要三思而后行,但明英宗重用大宦官王振,坚决要亲自领兵。出征路上,王振倚仗明英宗的宠信对军务乱指手画脚,随行文武大臣的意见多被置之不理,结果明军内部乱成一团,以至于前哨战役一败再败。同时,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向北撤退,明军贸然追击,在得知前方败绩的消息之后就立刻陷入慌乱撤退状态。且明军残部在撤退时找不准合理的路线,致使将士们疲惫不堪,等到明军溃退至土木堡之时,瓦剌军已紧追不舍。此时兵部尚书邝埜多次建议明英宗退入居庸关以图安全可靠,但却被王振所反对。不久后瓦剌军队将土木堡围困起来,同时也先假意遣使议和并摆出一副撤离姿态,而明英宗朱祁镇却没有提防,王振下令移营就水,饥渴的明军哄奔向河,人马失序,瓦剌伏兵四起,明军二十余万人亡三分之一、伤居半,土木堡一战,明军大败。
(三)对蒙“绝贡”等若干消极固守政策的出台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景泰帝朱祁钰并整顿军务,不仅稳住了阵脚还使得挟持明英宗的瓦剌勒索未遂,随后组织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然而,明英宗复辟后将于谦当作“政敌”处死,于谦的整军成果化为乌有。几年之后也先被暗杀,瓦剌势力相对衰微,鞑靼也处于内乱之中,北部边境貌似暂无大患。
同一时期,明朝群臣持“守为策之善,而战非吾之利”[5]态度者占多数,形成了主要依托长城“固守边疆”[6]的北边边防政策,不断修筑边堡、加固长城边墙,把“固守”作为防御蒙古犯边的一项主要手段。在这一政策主导下,政治方面,明朝严格限制与蒙古的往来,不再外派使者前往蒙古;经济方面,明廷则采取多种限制措施,拒绝与蒙古进行互市贸易,人为隔绝双方的经济交流。[7]长远看来,这种做法对明朝增强自身实力并无太大的帮助,蒙古也因输入必需品的渠道被断绝而不满。蒙古积怨,自身积弱,到嘉靖年间,“各边假按伏以自全,或拾残骑以诈报。将士既无斗志,总督诸臣亦止于布列兵马,散守要害,名曰清野,实则避锋,名曰守险,实则自卫”[8]。这样一来,北部边军战斗力缺乏,碰上敌军往往消极防御,致使北部边防工作形同虚设。而蒙古鞑靼部却日益强大,最终造成了明朝严重的边防危机。
二、古北口“庚戌之变”后的强边通贡政策
“庚戌之变”的发生,无异于是对明廷和明世宗的一次严重打脸行为。明世宗时期,明朝的边患比正统年间更加严重,加之明世宗严重失职,俺达汗兵临城下,明廷只能仓促且被动地应对。
(一)古北口及“庚戌之变”的简要经过
从北京市密云县向北行进45千米即可到达古北口,古北口原名虎北口,因其西南有山名曰卧虎山,故有此名。它是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沟通燕山山脉南北交通的要道之一。汉时此处已驻兵戍守,防御匈奴。明初依地势修筑长城,洪武十一年(1378)在这一地区建城并驻兵把守,并增设门关两道,一道设立于长城关口处,称作“铁门关”,仅容一骑一车通过;一道设于潮河上,称作“水门关”。古北口与西北的居庸关同为京师的两个重要门户。
时间进入嘉靖十五年(1536),此时明朝北部边防军务完全是一副荒废之象。《明史》记载中,都御史王廷相指出边防工作有“三弊”:一是军士多杂派,一年到头不得入操,实与田夫无异;二是军营多见老羸苟且应役,精壮子弟征招不来;三是“富军惮营操征调,率贿将弁置老家数中,贫者虽老疲,亦常操练”[9]。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十余年后“庚戌之变”时官军不能战不敢战、败仗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何原因所致。
到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后,明世宗朱厚熜整日沉溺于神仙方术求长生。重用大奸臣严嵩父子,以致忠良遭到排斥甚至陷害,违法乱纪现象严重,社会秩序紊乱,朝政日益废坏,朝廷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危机愈发严重。[10]也难怪著名的清官海瑞在《直言天下第一疏》中以直白、辛辣的态度将明世宗朱厚熜大力批判了一番。
这一时期,从明朝输入蒙古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在数量与品种上都难以满足蒙古人的需要,鞑靼首领俺答汗非常希望扩大与明朝的边贸活动以获取更多生活必需品。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俺答汗向明朝第五次提出通贡的请求,但明廷害怕重蹈“土木堡之变”的覆辙,于是对此采取了拒绝态度,还处死了对方来使。于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发兵大举侵犯明北部边境,因该年为庚戌年,故此事件名为“庚戌之变”。同年六月,俺答汗的军队先攻打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二将全都战死。然而负责镇守此处的大将仇鸾却花费重金贿赂俺答汗以求“高抬贵手”,于是俺答汗将矛头指向东边。同年八月,俺答汗军冲入古北口,当地驻军迅速溃败,俺答汗军继续推进,直逼京师城下。
自土木堡之变后,京师百年无警,俺答汗的突然袭击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驻扎于京师附近的四、五万驻军要么是老弱病残,要么被达官贵人当作仆役使用,再加上兵器的缺乏,战力明显不支。明世宗调来勤王的援军裹足不前、消极应对,严嵩也要求诸将避战自保,俺答汗的士兵在城外近郊大肆烧杀抢掠,并威胁:“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11]
此时礼部尚书徐阶进谏,若无条件应允,有辱明廷尊严,应该劝俺答汗先行撤兵,再派人就通贡问题与其周旋。世宗采纳了这项建议,允诺了通贡,于是俺答汗撤兵。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初一日,俺答汗军一部分由高崖口等处退去,另一部分由古北口旧路撤走。庚戌之变期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12]。
(二)对蒙政策由“绝贡”至强边通贡并举
庚戌之变是明蒙关系在土木堡之变后经历的又一次严重冲突,其导火索是“绝贡”纠纷。关于明廷为何如此顽固地拒绝蒙古的通贡请求,胡凡在《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一文中认为,从当时的情况加以分析,其根源主要在体现在明世宗朱厚熜身上。明世宗存在根深蒂固的轻视蒙古的观念,比如他对蒙古总是秉持诸如“丑虏”“虏氛甚恶”“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这样的态度,故对蒙古事务采取的政策,反复多变。[13]
“庚戌之变”后,明世宗慑于俺答汗兵威,勉强同意通贡。嘉靖三十年(1551)在宣府、大同一带开放马市。然而不久之后,严嵩因与仇鸾争权夺利而阻挠马市开办,明世宗的态度又开始动摇,当蒙古方面进一步提出扩大边贸的要求时,便干脆关闭了马市,并且下令,凡是再提此事者处死。中央各部官僚多数拥护,但是他们又拿不出更为合适的方案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直至明世宗去世,俺达汗军多次劫掠山西、河北北部得手。
隆庆初年,戚继光接手京师附近防务,俺达汗军的劫掠大为收敛。“(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14]。但千里边疆,全都修饬,国力不允。明廷复又考虑,远征漠北已经失去了实际操作可能,自己更不具备灭亡对手的实力,长期的敌对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便不得不在对蒙政策上探求新的路径。
“隆庆和议”便在这种形势下催生,大同得胜堡成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
三、得胜堡“隆庆和议”后的封贡互市政策
明穆宗朱载坖虽然是一个在正史上显得低调的皇帝,但他让高拱等有能力的大臣入内阁打理政务,故这一时期明朝在许多方面都有了良好的改观,为“隆庆和议”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得胜堡及“隆庆和议”始末
得胜堡,位于今大同市新荣区堡子湾乡得胜堡村北。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创建,长方形,周长1700米,墙高12.67米,曾“黄土夯筑,外包砖石”[3]514。当年的得胜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三云筹俎考》记载,该堡外接镇羌堡、内联弘赐堡,这两堡之间“矢镞可及”[15],它们与长城、关隘形成严密的得胜口防御设施体系。
明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投奔明廷,成为明蒙关系缓和的契机。此后不久,得胜堡成为“隆庆和议”成功后封贡、互市的主场地。
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入关后,大同巡抚方逢时、宣大总督王崇古分析研判,俺答汗如果看重这个孙子,定会前来索人,己方就以“缚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为条件,然后“以礼遣归”。[16]如果俺答汗放弃这个孙子,则厚待把汉那吉,待俺答汗去世后,扶持把汉那吉,挑起蒙古的内斗。无论哪种情况,明廷最后都可获利。王崇古与方逢时向朝廷上书报告相关情况,并提出处置建议“许以生还那吉”,初步提出“议和”思路,“授官或赏赉……后议封爵……许以市易”,实现“华夷兼利”。[17]当时朝廷内阁首辅高拱和重臣张居正赞同他们的主张,力排反对派非议,面请皇帝批准。
俺答汗索孙心切,直奔大同,且对于明廷“缚送板升诸逆”的要求,马上应允,并说自己孙子降汉,是天遣之合。
事实上,俺答汗犯边往往只为抢掠,此时明朝边防力量得到加强,抢掠已不合算,封贡称臣且有互市在后,俺答汗心愿得遂。由此,双方和议,水到渠成。
(二)封贡互市,实现百年“和好”
双方谈判,基本上以和平手段达成,各取所需,各有所得。明隆庆五年(1571),明朝皇帝敕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后封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并在得胜堡举行隆重仪式予以庆贺,同时宣示开放大同、宣府等地的马市。[18]《明史》载,仪式中受封者不在少数,诸如:“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宾兔台吉等十人授指挥同知……”[19]8487把汉那吉,也授了指挥使一职。
隆庆和议,不久即见成效。仅大同得胜堡官市,自5月28日至6月14日,顺义王进贡马1370匹,交易价10545两,“私市马骡驴牛羊六千,抚赏费九百八十一两……”[20]当年秋天,双方立下基本规则:俺答每年进贡500匹马,朝廷赏赐同价的丝绸等物品。俺答汗的儿子宾兔、丙兔桀骜不羁,被父亲告诫,渐渐收敛。自此,“诸部无入犯,岁来贡市”[19]8488。东起延、永之地,西到嘉峪七镇的数千里边境,军民得以乐业休息,朝廷不用再在兵革上花费重金,每年节省边防费用十分之七。
隆庆和议是明朝以多管齐下的务实手段解决与外族敌对关系的重要举措,收到了明朝北边数百年间很少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效果。明穆宗在任期间的“和议”以及开放边市是两项影响深远的政策,使“疆场无警者四十余年”[21]。此后明朝与蒙古之间不再有激烈的边疆战事,边疆环境得以安定,双方得以各取所需。万历中兴,也与这两项政策的作用有较大干系。
三、结语
自明朝中期以来,以武力应对边患的做法难以为继之时,明廷没有及时采取务实手段进行调整,采取了被动的、近乎不作为的态度去应对,比如废弃有效的整军措施,得过且过,以至于边患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为日后再次于边患事件中蒙受重大损失和威信扫地埋下隐患。至隆庆年间,通过加强对边防军务的整顿并主动寻找合适时机,果断决策通贡互市,才终于摸索出一套双管齐下且相对务实的办法,北方边患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对明蒙双方而言,交流和融合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边境和平、各族人民互利相生的长久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