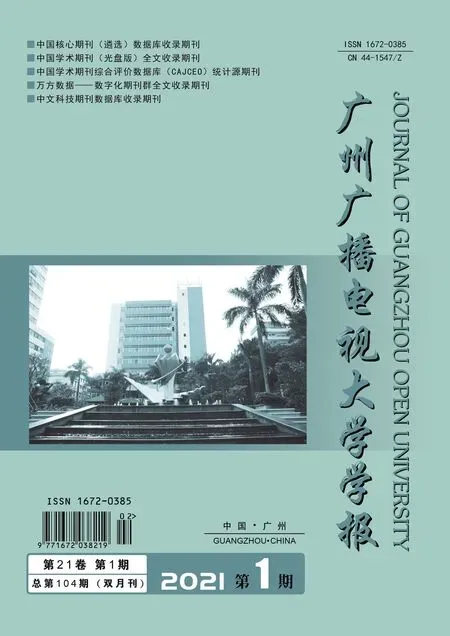《博物志》中自然异象研究
贾新宇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博物志》是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记载了山川地理、异闻异事、神仙方术等“浮妄”之言。其内容驳杂,有关自然灾害、自然异象部分也有涉猎,“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的材料”,[1]其中,自然异象往往带有神话色彩,反映古人对天的崇敬以及对大自然力量的敬畏,是早期人类对自然崇拜、向往之情的真实反映。
一、《博物志》中自然异象概况
《博物志》中的自然异象与人物、动物、植物等紧密相连,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独发生的普通自然现象,而是借助神话形式,使气象变为异象,彰显一种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博物志》中的自然异象有别于其它作品中真实的自然现象,它更可以被看作一种自然异象与动物、人物以及事物发展进程紧密相关的征兆,体现了古人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与向往。
(一)与动物相关的自然异象
《博物志》卷三《异虫》记载“肥遗”:“华山有蛇名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2]肥遗拥有独特的外形,本是蛇类动物,却生有六足与四翼,肥遗出现,则天下大旱,旱灾作为动物出现的异象与动物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从熊图腾开始,不寻常的动物或神兽被赋予神奇力量,并伴随着自然异象:如《易经》乾卦爻辞有“云从龙,风从虎”的说法;[3]《诗·大雅·云汉》中提及“旱魃为虐,如惔如焚。”[4]“魃”也成为酷热、旱灾的代言词。动物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冬眠和蛹化在当时未能被解释的生存习性,被古人视为动物与神密切联系的表现。
(二)与人物相关的自然异象
在《博物志》中,与人物相关联的异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人物身份匹配的自然异象,另一类是由人物行为动作所引发的自然异象。
1.与人物身份匹配的自然异象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身份特殊的圣人、贤者、神佛,出现时总伴随着神奇的自然异象。《博物志》卷七《异闻》收录太公与龙女的故事:“……‘吾是东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坛令当道,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雨过,是毁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风暴雨从太公邑外过。”[5]东海神女是女性神仙的一类,与海洋关系密切,出行一定会伴随“大风雨”的自然异象。这则异闻具备了小说的几种“热门要素”:神女、贤人、帝王、托梦与自然异象,这几种要素在后世传奇小说中被反复使用:唐传奇《柳毅传》中的龙女报恩,神魔小说《西游记》中泾河龙王托梦于唐太宗。而神女出行必有“大风雨”的自然异象,在后世更是被众多作者通过扩展、变形后加以运用,成为神、魔、佛等不同于凡人的一种标志。事实上,神仙菩萨与凡间具有高尚品格的贤人抑或是博学多识的圣人,乃至“顺应天命”的帝王将相,在出生或“受命于天”的特殊时刻,会与种种奇妙的自然异象相伴相生,以彰显人物的不同凡响之处。如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自摩耶夫人的右肋出生,步步生莲花;汉高祖刘邦于丰西泽中斩白蛇,后有云气自其身上显现,这些不同凡响的异象,都是人物异于凡人的身份证明。
2.人物行为动作引发的自然异象
《博物志》卷一《地》记载:“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帝,而怒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后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注焉。”[6]张华在编撰《博物志》时,囊括众多神话故事,共工怒触不周山就是其中之一。因共工“怒触不周山”的行为动作,引发了天空向西北倾倒、日月星辰向西北移动的天文现象,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河流自西北向东南流淌的地理现象,借助神话形式,用超现实的自然异象解释客观的自然现象,一方面彰显了共工的神力,另一方面,又与我国西北地势高、东南地势低的地理情况相符合,自然异象借着神话传说的形式,得以对客观存在的地理情况进行解释。范宁先生在《博物志》中辑佚黄帝与蚩尤大战:“黄帝战蚩尤于逐鹿之野,尤作百里雾,使兵士迷方失所。”[7]相较于共工怒触不周山引发的自然异象,这则异闻简单得多,是两军交战时为混淆视听由蚩尤的行为动作引发的大雾,显示了黄帝时代部落领袖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
《博物志》中收录与人物相关的自然异象,多是神仙神力的外在表现,彰显神仙区别于凡人,能够控制自然、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强大力量。
(三)与事物发展进程相联的异象
封建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天人感应学说,自然异象与当朝统治者的政治得失有着密切联系。
《博物志》卷一《山水总论》:“故地动臣叛,名山崩,王道讫,川竭神去,国随已亡。海投九仞之鱼,流水涸,国之大诫也。泽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迟,白黑不别,大乱之征也。”[8]这则异闻将自然异象与臣子、王道紧密相联:臣盛君衰、小人窃国等命运,都借助自然异象表现出来,用超越自然规则的现象给予警示。地裂山崩、川竭水沸、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自然地理变化成为天人感应的代表,与王道的存亡、臣子的叛变、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地质变化,而是代表事物发展的进程与走向,被赋予天命的神秘色彩。
《博物志》卷三《异闻》部分,还收录了两则夏桀暴政,殷商发端的自然异象:“夏桀之时……天乃大风扬沙,一夕填此宫谷。”[9]“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沉沉将灭,若疾雷之声。”[10]夏桀荒淫无度,上天降以自然异象以警示;殷商发迹,上天以日出给予征兆。中国古人认为,人和周围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天、地、人的存在和变化都在神秘的宇宙秩序规则之下,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日”可以说是代表了封建统治者自身行为的好坏,是王道的象征,在旧王朝即将覆灭,新王朝发端之际,出现两个太阳的自然异象与王朝的兴盛衰败、覆灭更迭联系在一起,是天人感应的体现,也是历史更迭发展的进程与自然异象的结合。
自然异象与神仙等非凡人联系在一起,凸显他们不同于凡夫俗子的神通;同时,自然异象与封建统治者的权力紧密相联,一方面为封建统治者增添了“天命神授”的神秘色彩,凸显他们与众不同的品德与顺应天命的“名正言顺”;另一方面也是对封建统治者的监督与警示,激励统治者实行仁政,做符合“王道”的行为决断。
(四)地理环境类自然异象
《博物志佚文》补辑:“南方炎洲有火林山,生不夷之木。其山昼夜大火常然,猛风不盛,暴雨不灭。”[11]这样神奇的火林山,超出了正常自然的范畴,是《博物志》中带有神话色彩的地理环境类自然异象。根据《中国救荒史》记载,魏晋南北朝发生过“地沸”两次,“‘地沸者’,当即火山未爆裂的状态。”[12]结合“地沸”时“烧生物皆熟”[13]的情况,火林山可能是张华对火山、火山爆发自然现象的夸张描述。
《博物志》中关于地理环境的收录,一部分是真实存在、对自然气象的反映;另一类以火林山为代表,超越了常规的自然范畴,带有神话色彩,这也是《博物志》被归为小说类的重要原因。
二、自然异象背后的神话色彩
神话是文学和文化的源头。《博物志》中收录的自然异象多与神人、圣人有关,构建出一个在自然法则下自然的人与超自然的神、兽、地理气候和谐共处的世界,反映古人较早的神话观念:一种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相处的世界。
(一)对自然法则的崇拜与敬畏
1.自然崇拜下的规则制约
在古人眼中,自然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超脱人类社会秩序之外的、为神所掌握的力量。传统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这种经济结构下,从统治者到民众,对自然气象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尊敬与崇拜。自然异象成为“神”对神的代言人——君王,是否公正有德的评判手段。君王的德行与统治,往往与自然异象相关联,这也就是“天人感应”学说。魏晋时期佛道并存,在佛教“因果轮回”教义的影响下,古人对征兆更为重视。《博物志》中“大乱之征”与“费昌归殷”两条,就体现了古人在自然法则下对君主、王道的制约。君王是“天”在人间的代言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4]自然异象、天灾是“天”对君王的警示。由于古人对自然的崇拜,给自然异象赋予“神”的色彩,自然规则下的征兆,一方面起到制约君王德行的警示作用,一方面也暗示着君王区别于常人的高贵身份。这样的自然规则制约,其实彰显了封建统治者作为在人间的“天”的阶级特权,即普通民众、臣子无法判断君王的得失,唯有通过代表“神”的自然异象,才有权力判定君主与王道是否合格。
2.自然敬畏下的祭祀祈祷
中国的农耕文明产生较早,发展较快,由于农业生产是古代小农社会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所以古人十分注意对自然气象的观察与观测。受限于当时的生产条件,生产水平低下,古人在这一时期对自然是单纯的崇拜与敬畏之情,自然气候无法被人的主观力量所掌握,为了寻求风调雨顺、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气象,古人自然而然对气候产生崇拜,并会对具有灾害性质的自然气象从主观能动性上用祈祷、语言的形式达到干涉自然气象的目的。
《博物志》卷八《史补》就有两则关于止雨、祈雨的记载:“《止雨祝》曰:‘天生五谷,以养人民,今天雨不止,用伤五谷,如何如何,灵而不幸,杀牲以赛神灵,雨则不止,鸣鼓攻之,朱绿绳萦而胁之。’”[15]“《请雨》曰:‘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神降甘雨,庶物羣生,咸得其所。’”[16]止雨部分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止雨的原因:雨伤五谷;止雨的仪式:杀牲以赛神灵、鸣鼓、朱色绿色绳子缠绕。悠久的农耕生活方式使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连绵的大雨对农作物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百姓会因此遭受饥饿之苦。为此,采取一些特定的祭祀方式,来请求气候的正常。而《请雨》部分从语言角度记载了古人请雨时的祷告之词,祈求上天厚土降雨,让万物能够各得其所。
在这一时期,雨、雪等正常的自然气象是“神力”的表现方式,而祭祀作为连通天、人的固有形式,也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这种神话色彩在后世愈演愈烈,甚至成为一种“死而复活的仪礼。”[17]而祭祀被神话的原因,溯流从源,是人类在自然气象面前无能为力,只能通过祈祷的手段,寻求心理、精神上的慰藉,是早期无法有所作为的“人”对自然法则的崇拜与敬畏。
(二)对超自然神力的向往与追求
在发现自然法则不被自己所掌控、利用后,古人对超自然的神力充满向往与追求,进而追求人与神的共同特征,“类人化”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1.神的类人化
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神”掌握着自然规则,可以操控风、霜、雨、雪等自然气象,这是“神”与“人”显著区别之一。由于对神力的向往与追求,在神话故事中,“神”往往被染上“人”的特征。《博物志》中龙女与太公的故事,就印证了神的“类人化”:神女会与人类女性一样婚嫁,并且也有婚嫁仪式。与普通人类唯一不同的是,龙女出行“必有大风雨”[18]这一自然异象的伴随,才使神与人得以区分。从叙述角度来说,“神话乃是对以欲望为限度或近乎这个限度的动作的模仿……神话表现人类欲望的最高水平并不意味着神话所表现的世界就是人类已获得的或可以获得的。”[19]神话与神作为人类欲望的最高渴望与人类想象的产物,在拥有“非人”的神通时,也具有“人”的特征甚至生活方式。“人”与“非人”的完美融合,恰好体现了人作为自然法则的产物,对超自然神力的向往与追求。这种追求与渴望愈加热烈,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神”的类人化进一步演变成人的神化,人和神的互动沟通,乃至人神通婚,使人上升到神的世界高度,获得更高的地位。
2.物类的神化
上古时期,人们认为“兽类植物只是除人之外的其他种族,并在它们身上发现了为之崇拜的力量。”[20]因此,植物、动物与人一样,可以具备“神”的特征。《博物志》中的肥遗、火林山,都脱离了普通物类的范畴,具备“大旱”“昼夜大火”的异象特征。动物、植物乃至自然事物,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彼此联系,都处在世界的法则之中,都可以被神化,甚至在很多时候“人间如果要和超自然世界能够沟通的话必须借助这些神圣的使者、神的象征物。”[21]受限于古人的认知能力,与人相比,植物、动物往往更容易成为“神化”的对象,甚至因其被赋予的神通,成为人类崇拜的对象,成为氏族部落的图腾:“把神灵同动物、植物认同一体,进而再与人类社会认同一体,这便构成了图腾象征的基础。”[22]最初图腾动物的神化,与其自身的生活习性息息相关,熊在冬季蛰伏冬眠,春季苏醒,被古人视为死而复生的神通。正是因为古人不了解熊冬眠的生活习性,才将其神化,寄予人对强大生命力的渴望与崇拜。
事实上,物类的神化自古有之,从盘古肉身化为万物,夸父手杖化为邓林,不管是有生命的“物”,还是无生命的“物”,都可以相互转化。这种不合自然法则的神化、变化,正是“充满情节虚构和主题构想的非实在的或纯粹的文学世界,它不受应该真实地符合日常经验这条规则的制约”,[23]超乎普通自然意义范畴的自然异象、浮妄之言,成为《博物志》被归为小说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结语
《博物志》作为小说类书目,包罗万象,自然异象较多。对《博物志》中的自然异象加以研究,探寻其背后的神话心理,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天人感应”“天命神授”的统治观念。在天人合一、人物与世界息息相关的背景下,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借助自然异象的形式被放大、评判,一方面成为君主行为的约束规则,另一方面也彰显其身份的不凡,自然异象也成为区别普通人与神、天命之人的重要衡量标准,成为人物特殊身份的一种表现。
这些自然异象,一方面展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以及“万物同源”的思想,在这种理念下,万事万物都是共通的,都可以被神化,成为彰显神力的载体。不管是物类的神化,还是人类的神化与神的类人化,究其原因,都是古人对自然法则的崇拜与敬畏。在这种敬畏、向往感情的驱使下,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与人、物以及“神”相结合,成为自然异象。自然异象是人类对自然现象认知的衍生,代表了人类想要利用自然力量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博物志》中的自然异象也体现了佛道并流思想环境下,魏晋之人对事物普遍联系、重视事物征兆的意识,使自然法则下的人、物毫无差别地统一起来,异象也成为古人对能够利用超自然力量美好愿景的寄托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