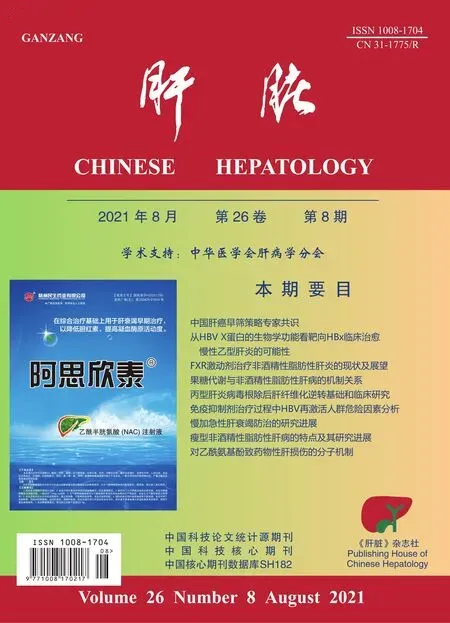丙型肝炎病毒根除后肝纤维化逆转基础和临床研究
徐贤军 陆伦根
丙型肝炎病毒(HCV)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严重的健康问题。HCV感染被认为是肝脏相关疾病(如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当HCV克服宿主固有和适应性免疫防御后,急性HCV感染转变为慢性HCV感染(60%~80%)[1]。肝纤维化是慢性HCV感染引起组织损伤后伤口愈合的结果,其特点是细胞外基质(ECM)过度累积,超过肝脏的降解能力。以干扰素(IFN)为基础的治疗方案可在一定程度上治疗HCV患者,但患者对此治疗方案的耐受性较差。一种新型高效的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可治愈HCV及其相关肝脏疾病,包括晚期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硬化并发症[2]。抗HCV治疗的主要目标是达到持续病毒学应答(SVR),SVR定义为抗HCV治疗后,血清HCV RNA检测为阴性[3]。本文主要总结HCV根除或SVR后,肝纤维化逆转基础和临床治疗前景。
在肝纤维化中,肝星状细胞(HSC)活化为肌成纤维细胞,产生ECM,ECM沉积在肝实质中,最终破坏肝脏的结构和功能。活化的HSC是纤维化形成的关键因素,相应驱动肝纤维化形成的细胞外信号。实验动物模型中,损伤解除后活化HSC的命运至少有3个方向:一是从活化状态恢复到静止状态;二是活化HSC的凋亡或自噬;三是活化HSC的衰老[4-6]。此外,在细胞模型中,HSC也可从活化状态恢复到静止状态。
当肝损伤解除时,HSC从活化状态转变为静止状态,但是与真正静止的HSC相比,它们重新被激活的速度更快。有研究表明转录因子Tcf21可以使活化的HSC恢复到静止状态[7]。其他参与HSC静止的转录因子包括LhX2、GATA4/6、PPARγ、RARβ、NF1等[7]。这些和DAN结合的转录因子可以影响基因表达,过表达这些转录因子可以使损伤肝脏中活化的HSC进入静止状态(如Tcf21)。因此,这些转录因子是治疗肝纤维化的潜在靶点。
HSC凋亡可导致肝纤维化逆转过程中活化HSC的数量减少[6]。调节HSC生存和凋亡的分子可能与ECM降解的调控因子有密切的关系。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可降解ECM,MMP2的活性和细胞凋亡有关,且细胞凋亡可能促进MMP2的表达[8]。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TIMP-1)可能是MMP2蛋白水解活性的关键调控因子,TIMP-1在活化的HSC中高度表达,抑制降解基质的蛋白酶(如MMP2),因此TIMP-1是活化HSC的生存因素[9]。程序性细胞死亡与自噬有关。自噬是一种分解代谢过程,通过溶酶体途径降解细胞成分,为HSC的活化提供能量。在HSC特异性自噬相关蛋白7缺失的小鼠中,肝损伤后HSC活化能力下降,可减轻体内肝纤维化的程度[10]。此外,抑制培养的小鼠HSC和肝损伤后小鼠的自噬功能可减轻肝纤维化的程度和减少ECM的沉积[11]。这说明自噬可以促进HSC的活化,而抑制自噬可抑制HSC的活化。
细胞衰老时细胞分裂、增殖能力下降,细胞可出现永久的生长停滞。活化的HSC衰老后,细胞停止增殖,减少了ECM的分泌,也增加了ECM降解酶的分泌,促进肝纤维化逆转。最近,有学者设计出一种特殊的嵌合抗原受体的T细胞,用于杀死表达特定细胞表面标记的细胞。使用这种技术杀死表达衰老标志物(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受体)的HSC,从而减轻实验动物模型中的肝纤维化[12]。因此,部分衰老的HSC可能在肝纤维化进展中起关键作用。
肝再生在肝纤维化过程中发挥作用。肾和肺等再生能力较弱的器官,一般在发病后3~5年可进展到终末期,而慢性肝病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发展为肝衰竭,这可能是因为肝脏独特的再生能力。这种独特的肝再生和肝纤维化之间的相互拮抗关系提示再生反应可能包括先天的抗纤维化和基质降解活性,而高度纤维化的肝脏逐渐丧失再生能力,这可能是肝脏进入早期失代偿期的关键因素。虽然这种相互作用的潜在机制尚不明确,但是一些实验证据支持肝再生可能抑制纤维形成[2]。此外,有研究表明,许多信号同时促进肝再生和抑制肝纤维化,包括肝细胞核因子4 α、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拮抗剂、肝细胞生长因子激动剂等[11]。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因子是否通过促进肝再生来抑制肝纤维化,但再生分子Wnt配体的有关研究表明,通过促进肝再生来抑制肝纤维化是一种潜在的抗纤维化路径[13]。
肝纤维化逆转的定义尚未标准化,通常指肝纤维含量的减少。然而,这个定义不能解释肝脏结构等其他变化,如肝硬化中结节大小、末端静脉塌陷的程度和ECM。在实验动物模型和人类肝病中,肝纤维化都可以逆转,但在不同类型的损伤中肝纤维化逆转的程度可能不同。在实验动物模型中,胆道纤维化是比较容易逆转的,并伴随多余胶原蛋白的完全降解[14]。在伴有肝坏死程度较重的实验动物模型和人类病毒性肝炎疾病中,肝纤维化仅可部分逆转,且具有明显的结构重塑和长期在肝脏沉积的ECM[15]。肝纤维化逆转的一个关键未知因素是无返点,也就是说肝脏病变程度达到这个点后,肝纤维化不能逆转。虽然缺乏充足的数据,但多数专家认为一旦出现严重结构重塑、血管塌陷和门静脉高压,肝纤维化逆转的可能性较小[2]。
肝纤维化的临床分期一直是SVR后肝纤维化逆转准确评估的障碍。肝组织学被认为是纤维化分期的金标准,但肝活检是有创的,且容易发生取样位置不精准。在HCV患者中,一些血清纤维化标志物(如TIMP-1、MMP2、胶原和透明质酸等)已经被广泛研究。胶原蛋白分解的血清标志物胶原裂解片段可作为肝纤维化逆转的潜在标志物,但需要进一步验证[16]。虽然,血清学检测对晚期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具有高敏感性和特异性,但对于不是晚期的肝纤维化而言,则不具有高敏感性和特异性。影像学技术,特别是瞬时弹性成像(TE)和磁共振弹性成像(MRE)是评估肝纤维化分期有前景的技术,它们可以测量肝脏的硬度且无创。在HCV中,TE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当肝脏硬度达到截断值时,截断低值可排除进展期肝纤维化,而截断高值则可提示进展期肝纤维化[17]。但是,当肝脏硬度处于中等水平范围时,TE评估不准确[17]。MRE的灵敏度更高,成像范围更广且是非侵入性的。MRE可以反映肝纤维分布的异质性。在HCV患者中,MRE较TE更容易出现假阳性的诊断[18]。肝外胆汁淤积、肝脏炎症和肝脂肪变性等也可干扰TE对肝脏硬度的测定。TE可能高估HCV根除后肝纤维化的逆转,因为DAA药物治疗会迅速减少肝脏的炎症,而炎症会使TE对肝脏硬度的测量值偏大。
SVR后肝纤维化逆转的驱动因素尚未明确。肝纤维化的逆转可能是不连续性的,可能受到肝纤维的数量及其分布、其他潜在的疾病和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长期监测SVR后肝脏的组织学变化。少数以肝纤维化逆转为特征的研究,尤其是DAA药物治疗后,也仅随访患者2~3年,因此无法追踪SVR后肝脏长期的组织学变化。考虑到肝活检的有创性,肝纤维化的遗传因素(如单核苷酸多态性)正在被广泛和研究。此外,评估肝纤维化的非侵入性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尤其是基于磁共振的方法,这使得可靠的无创评估技术在未来成为现实[18]。
肝纤维化程度可能是引起肝硬化并发症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HCV根除后,肝纤维化的逆转可改善预后。对于没有严重失代偿的肝硬化患者,肝纤维化改善可能会促进临床结局的改善[2]。目前尚不清楚,一旦抗纤维化的药物获得批准,该类药物是否适用于肝硬化和SVR患者的治疗。HCV根除后,有许多患者没有明显的临床改善,这使得抗纤维化的治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19]。虽然尝试对HCV患者进行肝纤维化特异性治疗,但是都没有成功。
目前抗纤维治疗的药物至少包括这两种:一是直接减少活化HSC的纤维活性或数量的药物;二是促进肝再生的药物。目前抗纤维化的临床试验主要是在NASH或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中进行,对于HCV根除后的抗纤维化的临床试验还没有。一种脂质体可直接将靶向热休克蛋白47(胶原蛋白适当折叠所必需的)的短发夹RNA(shRNA)传递给HSC,导致错误折叠的胶原蛋白在HSC中积累,从而促进HSC凋亡[20]。肾血管紧张素系统(RAS)在HSC和肝硬化中上调,RAS抑制剂通过降低TGFβ1的激活具有潜在的抗纤维化活性。一项临床试验正在测试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坎地沙坦在肝硬化中的作用[2]。目前尚无被批准的肝再生药物,但刺激肝脏的再生可促进纤维的溶解。在动物实验中,肝细胞核因子4 α、Wnt配体具有促进肝再生的前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肝再生和肝纤维化之间的机制联系,有助于推动肝纤维化治疗的进程。
肝纤维化逆转与广泛的临床益处相关。对HCV相关的晚期肝纤维化患者,经抗病毒治疗达到SVR后,肝纤维化逆转仍是一个重要的治疗目标。目前人们对肝纤维化逆转的机制和临床特征认识还不够深入。需要不断明确肝纤维化逆转的调控,特别是降解纤维疤痕的蛋白酶的种类和细胞来源,以及在细胞中产生和调控它们的具体机制等。从临床角度,需要更多研究来解决以下的问题:影响肝纤维化逆转的因素,包括遗传因素;肝纤维化逆转评估方法,尤其是非侵入性技术;抗纤维化治疗药物的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