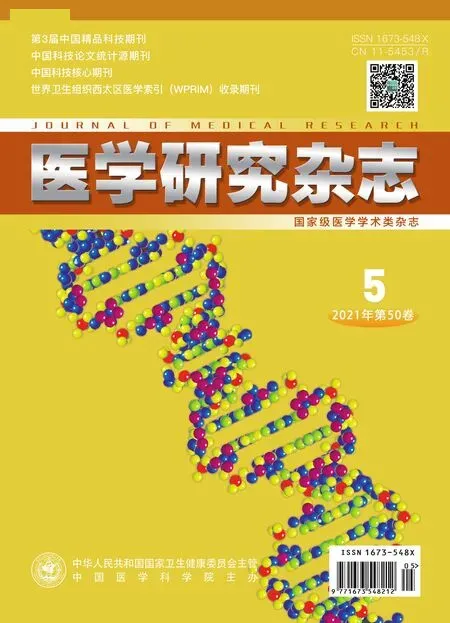肠道微生物与高血压关系的研究进展
陈雪莲 马明艳 王淑霞 李明阳 胡继宏
高血压是最常见、全球疾病负担最重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是中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据统计,2015年世界高血压患者已达到了11.3亿,中国18岁以上高血压患者2.445亿,约占1/5[1]。高血压作为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2017年有254万人死于高收缩压,其中95.7%死于心血管疾病,因此控制血压已成为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重要手段[2]。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降压药物联合治疗,高血压的控制率有明显提升,但高血压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3]。因此,高血压危险因素的研究尤为重要,但现有危险因素也只能解释原发性高血压发病的部分原因[4]。近年来,随着宏基因组技术和高血压发病机制的的研究,微生物与高血压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新的关注点。本文就国内外关于肠道微生物与高血压研究现状做一综述。
一、肠道微生物与高血压的关系
1.肠道菌群在正常人及高血压患者体内变化:人体肠道拥有最丰富的微生物群落,在正常人体内,肠道各菌群间保持着一种相对平衡状态,维护体内的各项生理活动[5]。当肠道菌群丰富度减少、多样性降低、厚壁菌门(F)和拟杆菌门(B)之比增加时,高血压的发生风险相继增加[6]。高血压前期患者的微生物群特征与高血压患者非常相似,二者代谢变化与肠道菌群失调密切相关,体内与健康状态相关的粪杆菌属、颤杆菌、罗氏菌属、双歧杆菌属、粪球菌属(均为拟杆菌门)均下降。将高血压患者肠道微生物移植至无菌小鼠,观察到血压升高可通过微生物群转移,证实了肠道微生物与高血压[7]相关。不同危险分层的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丰度存在差别,考虑可能原因是肠道微生物菌株的丰度变化抑制或减弱了与慢性炎症相关的免疫应答,对血压产生影响[8]。为此,有研究开始关注补充肠道益生菌对于高血压的影响。Gómez-Guzmán等[9]通过益生菌治疗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的实验研究首次证实,慢性口服益生菌LC40或K8/LC9可改善SHR内皮功能障碍、血管炎症、血管氧化应激、心肾肥厚,最终降低血压。
2.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与高血压的关系:随着对肠道菌群的关注,研究者发现肠道菌群的部分代谢产物也能影响高血压的发生和发展,尤其是短链脂肪酸(SCFAs)、氧化三甲胺(TMAO)、胆汁酸(BA)和脂多糖(LPS)等与高血压密切相关。SCFAs是肠道中可被宿主利用的重要细菌代谢产物,包括丁酸盐、乙酸盐和丙酸盐。这些SCFAs可通过与嗅受体78(Olfr78)和蛋白偶联受体41(Gpr41)结合发挥作用,在SCFAs的刺激下,Olfr78在肾脏入球小动脉中表达,激活后介导肾素的释放,引起血压的升高[10]。SCFAs对血压的影响与其浓度有关,较高的SCFAs浓度与肠道通透性、代谢失调标志物、肥胖和高血压相关[11]。SCFAs还可以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丰度,从而影响血压,在盐敏感性大鼠饮食中添加盐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减少粪便中SCFAs的产生,致使细菌丰度降低,厚壁菌门比拟杆菌门比值增大,血压升高[12]。近年来有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的另一代谢产物TMAO可能是高血压的又一个新的危险因素,研究发现当SHR血浆中TMAO水平升高时,血浆渗透压也随之升高,继而触发SHR TMAO-avp-aqp-2轴的调节,引起更大的水重吸收,最终导致高血压[13]。
一项关于TMAO浓度与高血压发生率关系的Meta分析也表明,循环TMAO浓度与高血压风险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循环TMAO浓度每升高10μmol/L,高血压发生的相对危险度增加20%[14]。另外,胆汁酸(BA)和脂多糖(LPS)作为肠道微生物群衍生的代谢物,也影响着高血压的发生、发展。据研究,肠道菌群能将肝细胞生成的初级胆汁酸的7α-羧基发生脱氧反应后形成次级胆汁酸,引起各种代谢疾病,针对BA的研究也已经证实BA或BA成分(胆酸、鹅脱氧胆酸等)在实验动物的多种血管上(主动脉、脑动脉)具有舒张血管、增加血流量及降低动脉压的作用[15]。LPS对高血压的影响与BA又有所不同,LPS也称为内毒素,是革兰阴性细菌外膜的组分,研究表明,LPS具有诱导全身性炎症的能力,当LPS的膜受体为Toll样受体4被激活时,会触发NF-κB信号转导并产生促炎性细胞因子,影响肠道菌群的平衡,增加高血压的发病风险[16]。
3.高血压危险因素与肠道菌群的关系: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高盐饮食、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肥胖和糖尿病等。高盐饮食是高血压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高盐饮食可通过诱导T helper 17(TH17)细胞来驱动自身免疫,降低乳酸菌的肠道存活率,对血压值产生影响[17]。Ferguson等[18]研究发现在人类和小鼠中,高盐摄入量与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有关,将传统高盐喂养小鼠的粪便过滤性转移到无菌小鼠时容易增加肠道炎症和高血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可以在高盐饮食的基础上对血压值产生影响,Liu等[19]研究发现OSA联合高盐饮食可通过增加血中TMAO水平、相关细胞因子(IFN-y)的释放和抑制抗炎细胞因子(TGF-B1),影响大鼠肠道菌群,增加高血压的严重程度。有研究显示肥胖者比正常体质量者革兰阳性厚壁菌门多20%,革兰阴性拟杆菌门少 90%,在肥胖者体内,厚壁菌门中几种细菌的减少,如白菌门、梭状芽胞杆菌门中的其他细菌的减少,与脂肪肝的增加有关[20]。同时,益生菌能够发酵难以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如膳食纤维),从而产生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SCFAs,这些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可以通过增加能量消耗,增加厌食症激素的产生和改善食欲调节来预防肥胖。此外,Karlsson等[21]研究发现,与非糖尿病患者比较,糖尿病患者肠道中厚壁门明显减少,拟杆菌与厚壁菌比值以及普氏拟杆菌与大肠埃希菌比值与血糖水平呈正相关,并且有益菌双歧杆菌数目明显低于健康人,而肠粪球菌数目则高于健康人。综上研究,不同的危险因素,肠道菌群也有所区别,这些危险因素可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数量及种类,对血压的发生、发展产生影响。
二、肠道微生物调节血压的机制
1.大脑-肠道-骨髓轴的调节作用:肠道微生物及肠道代谢活动在交感神经-肠道活动中的变化可能对宿主血压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肠道生态失调、自主神经系统(ANS)和免疫系统之间存在关联[22]。大脑-肠道-骨髓轴在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伴随着宿主神经活动的变化,交感神经活动加强会促进肠道炎症,同时提高机体的血压,这与下丘脑室旁核中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引起的神经炎症增强相关,神经炎症增强会导致神经元活动上调,而神经元活动增强则又会引起交感神经活动上调,最后导致血压升高[23]。
2.肠屏障作用:肠屏障主要作用为防止腔内致病因素进入体内循环。肠道屏障破坏后,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道内毒素、病原体和抗原暴露,从而改变先天免疫,引发全身炎性反应[24]。当高血压患者血浆中肠脂肪酸结合蛋白(1-FABP)、脂多糖(LPS)以及肠上皮紧密连接蛋白调节剂等明显升高时,发生了肠屏障功能障碍,此时高血压前期一些信号(饮食、盐、环境、毒素等)将增加促炎Th17细胞的流入,启动肠道病理,对血压产生影响。
3.稳态体调节与激素学说:稳态调节对于高血压的影响也是一种新机制。正常人群的肠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当肠道内稳态由于外界原因或病理情况被打破时,肠道生态失调会产生促炎性细胞因子和氧化应激,并增加自由基,从而氧化低密度脂蛋白(LDL),它可以抑制NO的产生,而NO又可以放松血管收缩,降低血压[25]。
除上述几种机制外,还有研究提出一种肠道菌群调控血压的新机制,即肠道菌群可以通过影响类固醇激素水平来调节血压。具体表现为高盐饮食会降低肠道中脆性拟杆菌和花生四烯酸的水平,增加肠内衍生皮质酮的产生和血清及肠道中皮质酮的水平,从而促进血压的升高[26]。
三、基于肠道菌群紊乱的高血压药物及其益生菌的应用
基于肠道菌群参与高血压形成的途径及作用机制的研究,一些以此为靶点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及其益生菌受到一些关注。Robles-Vera等[27]评估了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氯沙坦对SHR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发现氯沙坦诱导的肠道微生物群发生了变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它可通过调节肠道的免疫系统来保护脉管系统而降低血压。Han等[28]研究发现,黄芪联合丹参诱导产生了保护性肠道菌群和与肠道菌群变化密切相关的有益代谢产物,从而降低血压并改善SHR中不平衡菌群的结构和组成。徐兴华等[29]研究了贝那普利和氨氯地平两种降压药应用后对SHR肠道菌群的变化发现,药物不仅具有明显的降压作用,且对肠道微生物的门属组成、α多样性、β多样性有一定影响。另外,口服益生菌制品可降低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值,纠正菌群紊乱,降低血压[30]。由此可见,部分降压药及益生菌的补充都可通过改善肠道菌群达到降压目的。
四、展 望
大量研究正在逐步揭开宿主与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肠道微生物群在保持健康和高血压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肠道微生物本身及其代谢产物能帮助寄主完成多种生理生化功能,在长期的协同进化中,宿主和其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二者共同组成了肠道微生态系统。随着肠道微生物元基因组的研究开展和各种测序方法的快速发展,以及新的化合物被纳入临床研究,一些与心血管相关的新微生物以及代谢物将会出现,为相关疾病的诊治,尤其是心血管病的治疗带来重大提升。但同时,人们对肠道微生物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功能机制的复杂性,而环境、饮食习惯等因素也造成不同个体间菌群的异质性,这将对肠道微生物影响人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机制研究和治疗探索提出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