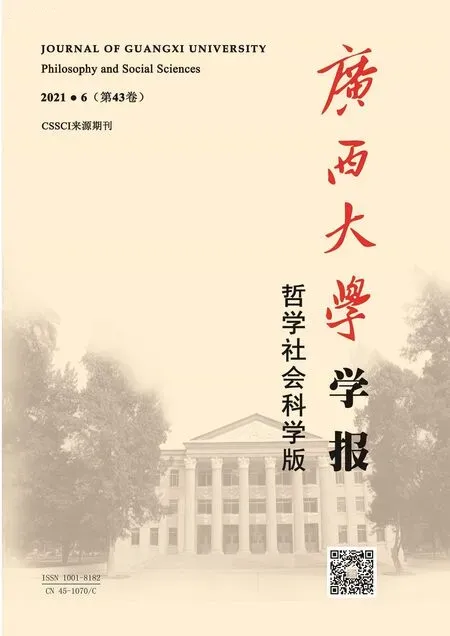被俘获成为技术系统中组件的人
——论鲍德里亚的屏幕化及其触觉性感知
屠音鞘,胡大平
生活在屏幕中,可能是对我们当今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的较形象表达之一。偏偏不是在屏幕之“前”,而是在屏幕之“中”,这正是由于我们与屏幕的双向渗透而逐渐完成的。鲍德里亚一语成谶,我们已如此深度地与技术交融、被其编织的信息网络所捕获,以至于屏幕的含义早已不限于投射-显示图像的装置,更是一个整体拟真的生命场域,一个全景的编码价值交换系统。在即将到来的“物联网”时代,已无法设想哪个物体将成为屏幕,连人自身也正在变成屏幕,马斯克的脑机芯片正如日方升。
马克思已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现代工厂制度中人被机器奴役的情形,人被贬低、物化为整个机器系统中有意识的器官,生存感受的丰富性被剥夺了。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在(后)现代技术批判理论中影响深远。而鲍德里亚令人震惊地刻画了当代资本主义借助以符码操作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如何重构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感知结构。“屏显为实”,全息现实的屏幕已成为建立所有的社会关系、意义关联的基础,人沉沦而为技术系统中被俘获的组件。
当中国为快步踏入现代化而欢呼时,却发现原产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症结也开始缠绕上身,网络、传媒等的负面信息和不法行为极大地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大型资本垄断集团也愈加明目张胆地攫取利益,这无疑对国家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突破这一困局,已是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一、技术与符号统治及被俘获的人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消费是一种凌驾于个体之上、以娱乐及享受来束缚、驯化个体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需要有人作为劳动者(有偿劳动)、作为储蓄者(赋税、借贷等),但越来越需要有人作为消费者。”[1]这一俘获人、将人作为组件纳入自身、完善自身的系统随屏幕化而升级。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以“技术与符号统治”来定义的“新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答案[2]162。技术统治仍然位居首位,符号统治乃是由于新的技术带来新的语言实践,构造出一个新的语言现实并相应地调整着感知结构,其实是技术统治加剧化后出现的新型统治/奴役形式,正是这一点凸显了“新资本主义”之“新”。
作为资本主义结束原始积累后延续至今的特色,技术统治表现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霸权”,鲍德里亚的相关分析直接受惠于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呈现了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形态,亦即“机器和固定资本占优势的阶段”,鲍德里亚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描述道:
在这一阶段,“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象化劳动的积累作为生产力取代活的劳动,然后通过知识积累而无限地增殖:“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15-16①译文中马克思相关引文有修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2-93.
由于知识、技术等以非实体性劳动资料的形式加入生产过程中,它们实际上已被资本吸收而自身转变为资本。基于这种特性,技术、科学的纯洁性、中立性仍然可能吗?至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也正是马克思的判断。对象化劳动,即死劳动,“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3]92。如是,死劳动压倒了活劳动,客体压倒了主体。死劳动、客体的霸权,归根结底是资本的霸权。随着资本成为社会的规定,大量繁殖的现代机器占领了整个工业生产系统,物和符号的无限复制性带来了等价原则,人类进入了第二级仿像时代,这是鲍德里亚所指的再生产的技术和系列的时代,社会的运转脱离了价值的自然规律而依赖于价值的商品规律。
当拟真的、诱惑的时代接替了生产的时代,“生产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了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秩序现在追求的是绝对控制”[2]77,这是受符码支配、遵循价值的结构规律的后工业社会。属于第二级仿象的符号叙事终结了,终结这一切的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必须牢记鲍德里亚接受了马克思的命题,积累下来的知识、技术已被资本吸收而自身就是资本。客体的大获全胜和主体的落败被俘,导致了主体衰退为空洞的符号、被吸收为支配系统中的一个终端,最终只留下消失后的“剩余物”。而“屏幕”就是当前这个技术世界的隐喻。屏幕一词,鲍德里亚借以指称“网络、电路、穿孔带、磁带、拟真模式、所有的录音和调控系统、所有的刻录表面”[4]119,也就是一切可归于 “拟真化捕获系统”的光电表面。这是一个绝对的完全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屏幕,一个Ecran Total②Ecran Total,法语意为大屏幕、全景屏幕,法国有同名的电影杂志,也是鲍德里亚晚期一部文集的名字,即Ecran total,Paris:Galilée,2000,英译本为Screened Out,trans.Chris Turner,London &New York:Verso,2002.。随着一体化网络及其终端接口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铺展,屏幕无所不在、无所不显,每一块显示屏、监控屏都是互联互通的即时的全景屏幕。
除了马克思,鲍德里亚同样深刻受惠于由海德格尔描述出来的生存论视域,如他也不是在“理论-静观”式的认识论层面上展开讨论,而是在主体完全沉浸在仿象了世界、历史的语言结构中的生存论层面上来考察技术和符号对感知的规定。曾经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之此在的被抛性表现在三个维度上:1.作为在世之在受共同世界和环境的规定;2.受继承下来的历史(尤其是形而上学历史)遗产的规定;3.受当前技术化的信息语言支配。此在被抛入由世界性、历史性、语言性三大维度所规定的当下,鲍德里亚则迅速将世界、历史都转移、抽象化到受符码支配的语言维度中,以此来论屏幕化,它走向“主体的消失”。世界是作为拟真符号再生产的技术物、消费品的世界,历史是作为前人的语言生产和今人的想象再生产的历史,这一切都被转移、剪辑、上传到媒体网络等屏幕上而形成符号自身交换的脱离现实的光电迷宫。世界、历史的真实都在融入语言维度时被肢解、放逐,语言脱离了世界、历史而又不断再生产出一种根除了参照的“超真实”,这是“符码的仙境”或鬼域,主体、客体步入屏幕而化为非真非幻、永恒回返的幽灵,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耍的“鬼把戏”。
总之,最后导致的历史性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我们的躯体将只是一台对我们实施远程控制的技术设备名存实亡的组件、可有可无的环节和幼年罹患的疾病。[5]19
资本走向了“真实统治”,走向对人的完全吸引和征用。这种“真实统治”是建立在符码上的统治,表现为在仿象和符码的领域内,即时尚、广告、电传网络等再生产层面上,形成了资本逻辑整体的统一性。因为这时整个生产方式都屈服于符号统治的社会关系,一切社会话语、“编码系统”包括科学、政治经济学等都按照约定的“客观”逻辑而生成出一种替代真实的“超真实”的拟真奇观。从此,人沦为屏幕系统中被俘获的组件,屏幕需要的是人作为“用户”的价值。
二、屏幕化的人类命运
人的历史性境况,从马克思的“机器体系中有意识的器官”到海德格尔的“被现代技术所促逼和订置的持存物”,再到鲍德里亚的“被系统远程控制的组件”,都与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
客体的大获全胜和主体的落败被俘,导致了主体衰退为空洞的符号、被吸收为支配系统中的一个终端,最终只留下消失后的“剩余物”。对鲍德里亚来说,技术不仅是生产力、中介,他接受了马克思的命题,积累下来的知识、技术已被资本吸收而自身就是资本,建构着物化的社会关系。显示着全息现实的全景大屏幕现在就是我们被抛入其中的生命场域,是生存论层面上的感知域,是所有一切认识论层面的认知与反思的前提。在拟真屏幕中,虚拟现实先于真实且必须自身被把握为真实,是为“屏显为实”。在这种超真实中,平面、单向度的屏幕因图像的过度饱和而发生内爆,当表意功能崩溃之后,反思也就不可能了,屏幕成为捕捉用户、令其永远迷失的群体性狂喜的乐园。
具体来看,结合现实与鲍德里亚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从以下三个维度来描述屏幕化现象:
(一)环境的屏幕化:卫星、远程技术、计算机系统、媒体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技术,使对整个地球实施24 小时全天候的监控成为现实,福柯的全景敞视式监视社会再次获得了激进表达。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与物发生关联的周围世界或环境,如今被数字技术整理成数据流,整个吸收进了屏幕之中,作为虚拟现实而被制造出来。这是鲍德里亚在《邪恶的智慧》中所说的“完整的现实”(Integral reality),它 “是一个无限量的运作工程,是关于世界的一种妄想。在那里,一切都变得真实,一切都变得可见和明晰,一切都被‘解放’,一切都趋于实现并拥有意义”[6]。完整的现实是现实的超现实化的工程,在不断强化的明晰性和完整性中,在趋向完美的真实中,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理想规划最终陷溺于屏幕上无数快闪而过的平庸图像(banal image),以资本单一绝对的真实统治而生成的现实,本身就具有根除一切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趋势。
(二)大众的屏幕化:由于虚拟世界本身成为真实世界并实际上是真实的证伪-证实场域,社会关系经屏幕而成为虚拟的意义关联。而这是一块“总体不确定的屏幕”,屏幕拟真的问/答、测试的模式似乎还暗示着一种确定的陈述价值。“屏幕,无论是电视还是民意测验,都再现无物。”[4]123屏幕与镜像不同,在这里,拟真的虚构、偶然、非参照的秩序替代了传统主体哲学镜像式表征的稳定的秩序。在无数次的触屏、问/答测试中,在信息的过度而非匮乏中,借媒体和大众的循环喂养、互相瓦解,在过去被设想为知识、历史主体的大众正在逐渐消失,“个体或大众通过逐渐融入浅屏来蚕食自身”[4]120,大众在符号统治中被抽象为“沉默的大众”,作为媒体的导体被捕获而丧失了真实的语言。沉默之沉默性不再产生于权力的封口式压制,而是产生于屏幕化、拟真化的言论、行动的过度,经此,资本的真实统治达到了消解大众革命力量的目的。人类所遭遇的隐性奴役不再表现为受压迫和未被解放,恰恰表现为一切都已被解放的超真实,正如瑞安· 毕晓普指出的:“在电视上、在大街上、在互联网上,这些抗议无论如何是无效的:确实是过时的武器。这些示威只是实施了政治参与——只是使政治拟真化——它们极力强化鲍德里亚关于政治主体和他的能动性被逐步消解的分析。”[7]44
(三)个人的屏幕化:人不仅只能通过屏幕来接触环境和他者,甚至人对自身的感知也屏幕化了。与大众的命运一样,个人的命运被编织入拟真的符码控制系统。古老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如今让渡给超级计算机的大数据算法。如今统筹整个社会一切信息、符号的数字性,“它最具体的形式就是测试、问/答、刺激/反应”[2]80。在万物对你的不断测试中,你建立起自身信息扮演的“角色”,通过回答这种拟真的塑形方式来剪辑、编码出自身的形象,在屏幕这个彻底自恋、影像回放的织网中反射出一个趋向完美的超真实的化身(Avatar)。认识你自己,什么才是“真实”的你自己?他者、比特城中的所有居民、计算机系统、甚至你自己,都已根据形成于符码的测试模式的屏幕化身来认识你。马克思看到的是人不断地生产再生产自己的社会关系也借此进行对人本身的生产,而鲍德里亚看到的是全景的拟真系统以模式生成的方式制造出消费用户。
屏幕隐喻不仅意味着人对现实的感知依赖于技术和符号的结构,还标示着完全的融合与浸没。鲍德里亚将所思推向极端:当陷落于屏幕中时,人在无意识的底层就被同化、驯服了,成了既全景又碎片式的“屏幕人”,乃至“屏奴”。屏幕化的感知是无主体、无客体的,或者说我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非主体又非客体,只具有一种无客体的主体性或无主体的客体性。鲍德里亚说道:
过去分离的东西现在到处都融合了;距离在一切事物中都被消除了:在性别之间,在两极之间,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在行动的主角之间,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在现实和它的替身之间。[8]
当拟真的网络互联式屏幕完全捕获和融合了一切人和事物之后,随着距离的消弭,传统主体-客体等对立关系也都消融了,亦即,随着不再有距离使得两极的对立得以成立,差异和裂痕被取消,所有事物都在非参照的拟真形式中趋向总体的完满。主-客体的消失-融合,留下的是一种屏幕化的无距离、非对称的关系,这时,所有的认知都是“屏幕”这一“巨大的反射平面”的空泛、脱离现实的反射效果[5]70。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今的网络世界中,只有能指与能指之间、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换,而不必指向所指和反映现实,这是纯粹反射而非反映的语言游戏。主体消失之后的“剩余物”不过是一个幽灵和其自恋的复本。
在鲍德里亚看来,主体的消失并非由于近代哲学主体神话的破灭,而是由于人类过度实施了启蒙的伟大计划——“掌控宇宙和穷尽一切知识的普罗米修斯式计划”[5]66。不是由于失败,而是由于过度完成和不断极化,权力、知识和历史的主体将现代性规划推进到越来越极端的程度以至于在大获成功的技术世界中消解了主体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性也可以被称为“超级现代性”[9]。关于主体性正日渐消解的末日宣判是鲍德里亚最具煽动力的预言,却也充满悖论,屏幕排除了独立的反思批判的可能性,却允许他这样的(反)理论家以抽象、超然的态度模拟一种后现代版本的虚无主义,这本身就显得极为荒诞。
三、身体与触觉性:感知范式的变化
屏幕作为一个“完整的现实”的全景皮肤被穿在我们身上,同时,我们也被屏幕穿在身上,成为屏幕皮肤上的毛孔。在什么意义上说穿在身上?穿在什么样的身体上?海德格尔曾经区分了两个表示身体的词语:一个是Leib(肉身),一个是Körper(身体)。“感知的独特之处是‘亲身性(Leibhaftigkeit)’:在感知中,在场者‘亲身地’在此。”[10]387因此,Leib(肉身)可以说是感知的独特特征,它相当于Körper(身体)的伸展范围。最大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界限并不相同。“身体的界限是皮肤。与之相比,肉身的界限更加难以界定。它的界限不是‘世界’,但或许至少是‘周围世界’。”[10]387其实不管是Leib,还是Körper,那都是我的身体,是我自身所是的东西,并非有两个身体,而是它们一道构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性的身体。鲍德里亚对身体一词的使用同样具有双重性,因此他才会着重提到“第二层皮肤”[2]144,这是在象征交换中包裹身体的标记和符号的网络,可以称之为Leib 的界限:一个屏幕化的周围世界,一个全息现实。它以皮肤的方式承担着Leib的感知,而皮肤的感知方式正是“触觉”。当距离被消除之后,“视觉中心主义”的社会基础崩溃了,一切感知都是触觉式的,电视电影、网络空间等拟真的领域具有十足的可触摸性。这让人联想到《黑客帝国》中,人类都是通过直插入大脑的脑-机接口这种深度触觉性的形式来进入超真实的世界。
在所有感觉中,触觉是相对特殊的。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触觉有别于其他一切感觉的特殊性:1.触觉是视听等其他感觉的基础或可能性条件,“如果没有触觉,其他感觉就不可能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感觉,触觉却仍可以存在”[11]37。2.一切感觉都通过接触而发生,但只有触觉不需要中介而“在与对象直接接触时发生”,其他感觉都必须通过中介而发生[11]92。3.“触觉是动物惟一必备的感觉”,而拥有其他感觉的目的并不仅仅为了生存,而是为了生存得更好[11]93。4.是触觉使其他感觉得以被解释,“必须通过触觉来解释感觉”[11]106。
顺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触觉之所以命名为“触”,是因为可以通过直接接触对象来感知,其他感觉则必须依赖别的事物来接触对象,亦即,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中介了的触觉,如视觉借助于敞开、光亮以“触摸”对象。那么,触觉不仅是一种基本感觉,还能统摄其他感觉。其他感觉都可以被理解成触觉的某种特殊形式,如同其他感官都可以被理解成皮肤上的某些部分。没有什么感觉比触觉更丰富、更生动的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利奥塔说:“英文词‘touch’的多义性,完美地将画家的肉体与梅洛-庞蒂所说的世界的肉体之间激动又充满爱意的接触的观念和一种独特风格的涵义结合在一起。”[12]含混模糊的触觉,将个体与世界的皮肤性接触刻画得暧昧旖旎,而由于人的身体被屏幕系统俘获为组件,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激动又充满爱意的接触”立刻就变成了在当今社会氛围和网络空间中暴露出来的透明的淫秽。
鲍德里亚发现本雅明第一个如此具体地关注到了新的技术媒介所具有的可触摸性:
从一种迷惑人的外表或从一种诱人的噪音结构来看,达达主义的艺术作品变成了一个弹道器械。它像一颗子弹一样射向观看者,它碰巧撞上了他,因此它获得了一种可以触摸的质地。它唤起对电影的要求,而电影娱乐人的成分首先也是这种可触摸性,这种可触摸性建立在不断袭击观看者的位置与焦点的变化上。[13]
对鲍德里亚来说,绘画对应于第一级仿象,照片对应于第二级仿象,而电影、电视等光电屏幕系统已经踏过了第三级拟真的门槛。触觉是多感官交互的感知方式,是去中介化的即时的信息接收。在这里,凝视与反思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图像把感觉粉碎成片段和刺激,只能用即时的反应来回答;另一方面由于距离的消除,不再可能为凝视建立观看与被观看的间隔空间。鲍德里亚写道,新技术的这种“剪辑、切割、质问、煽动、勒令的中介方式本身在调节意指过程”,结果构成一种“触觉和策略拟真场的图式”:
在这里,信息使自己成为“信息”,成为触手般的煽动,成为测试。人们到处都在测试你们,触摸你们,方法是“策略的”,传播领域是“触觉的”。至于“接触的”意识形态就更不必说了,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力图取代社会关系的观念。一整套策略形态就像是围绕着指令分子代码旋转一样,在围绕着测试(问/答细胞)旋转。[2]84
当人已完全融入屏幕化的拟真世界中,Leib意义上的身体已经与屏幕完全交融,符号系统得以如入无人之境般触摸我们、拿捏我们。这样的屏幕效应和社会氛围使人和事物处于一种纯粹而单一的展览状态而不再表征任何事情,这就是鲍德里亚说的淫秽的确切定义:“所有结构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都被展示出来,所有的操作都清晰可见。”[4]37
在福柯笔下,全景敞视建筑提供了一种微观权力运作中看与被看的不对称状态,人们时刻被无主体的目光看着。而在鲍德里亚这里,人的位置由被看转变为了被触摸,被看还有距离的间隔和躲避的可能性,而在被触摸时这些都消失了,在屏幕中的生活是完全透明和展览性的,所有的显像都趋向明晰和真实。人成为网络-屏幕系统中被俘获、被吸收、被触摸的组件,它即时、直接地感知着我们并富有策略地操作着我们的感知。马克思曾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4]而在鲍德里亚看来,早已没有固定的东西可以消散了,早已没有神圣的东西可被亵渎了,这是彻底的猥亵、彻底的意义消解。
“触控屏”或许是当前时代最佳的拟真隐喻,屏幕化的感知采取了人与屏幕之间双向触摸的形式,并不断反馈给对方。触控屏形象地把触摸与问/答、测试结合在一起,在点触之间就让人享受到最新鲜的时尚信息,调动起所有感官来饱尝多层次的感觉的交响乐,好奇却冷漠甚至带点失落,并且,“根本停不下来”。
四、余论及反思
在鲍德里亚看来,当技术与符号统治遵循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不断极化,客体完全压倒了主体、吸收融合了主体,主体和客体都消融于作为拟真之生命场域的屏幕后,物化的极端表现以屏幕化的方式出场,构造出一种触觉性的感知范式。这就是当代资本之真实统治的绝妙策略,一种新的趋向完美的社会控制模式。
不可否认,鲍德里亚对后现代技术社会的分析是石破天惊式的,以极端的前卫姿态揭露了新技术冲击人类生活时自命不凡的外表下与资本共谋的罪恶生意。瑞安· 毕晓普将鲍德里亚描述为一位“冷战哲学家”,“冷战期间,美国全球策略的逻辑和理想/目标,在鲍德里亚的理论研究中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7]39,他的语言、逻辑、修辞在很大程度上由冷战这一事变所构造并将这一切推向极端。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到20 世纪90 年代后,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激进思想逐渐失去了冲击力而变为单纯资本主义内部自身解构运动的老生常谈,甚至只在好莱坞商业电影中还有博人眼球的价值。但实际上,美国直到今日仍奉行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利用技术垄断挤轧中国,鲍德里亚揭露冷战策略家的凶恶意图和资本真实统治的真相恰恰显得与当今现实息息相关了,有助于我国在持久承压的国际环境下理解美国全球策略更深更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极端表现。
然而,鲍德里亚犬儒主义式的旁观嘲讽和对独立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藐视终究令人难以接受。一方面,鲍德里亚描绘的主体彻底被客体征服、吸收而消融入屏幕的现象确实提供了一种对当今媒体文化的理论解读,但这并不能简单武断地认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自律性力量将因人处于消费社会及全景屏幕系统就完全消解。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柄谷行人从对马克思资本论草稿的解读中发现的命题——消费的场域实际上是劳动者作为能动的主体而出现的场域——釜底抽薪地推翻了鲍德里亚理论的前提。“对于资本来说,消费乃是剩余价值最终实现的场域,也是被迫遵从消费者(劳动者)意志的惟一场域。”[15]尽管由于媒体和技术的支配,社会深度屏幕化,然而始终不能否认,人即便作为系统组件之消费用户(免费劳动力)也依然有着能动的力量,尽管受着狂轰滥炸的诱惑也并非不能做出自主的选择,其实,消费社会的诱惑策略恰恰坐实了在消费场域实际上消费者正具有能动性,因此资本的策略才采用了“唯恐不受诱惑”的形式。在后现代版本的虚无主义逻辑和屏幕化的感知面前,个人更应慎思明辨,锤炼心性工夫,树立对主体能动性力量的自信和自觉。
另一方面,当我们在评价科学技术的价值、评价历史性的屏幕化命运的合理性时,仍需保持公正和适度的原则。归根结底,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的成就,虽然总是被大型资本集团掌控而成为对人的宰制工具,但技术能够服务于社会民生也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时,正是生物技术的关键突破和应用才得以挽救人民的生命,这既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上的优越性,也表明了技术并不必然对人施加异化的命运而能够经合理的“活用”而达致服务于人的目的。鲍德里亚对技术系统的恐怖描绘显得过于非理性,而苏珊· 哈克“理性地捍卫科学”[16]的态度更应被我们接受。如马克思所说,积累下来的知识、技术等具备资本的属性且会自身转变为资本,如何开创一个超越了西方现代性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调动起技术和资本,以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反过来造成对人的异化和剥夺,这是真正严峻的时代任务。在我国已显露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那些令人焦虑的类似现象时,这个问题将越来越紧迫。